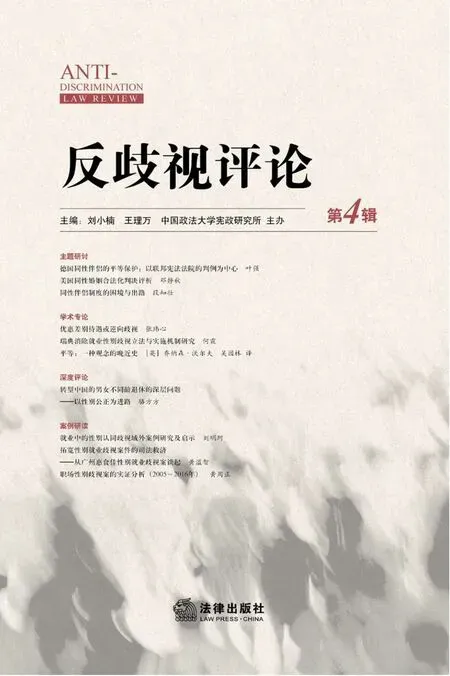德国同性伴侣的平等保护:以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为中心
叶 强
德国同性伴侣的平等保护:以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为中心
叶 强∗
2001年德国《注册生活伴侣法》的实施加快了同性伴侣平等保护的进程,然而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得益于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审查,同性伴侣与婚姻之间达到了趋同的保护效果。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解释基本法第6条第1款和第3条第2款,并在比例原则的审查中纳入严格审查基准,在同性伴侣的遗产继承、遗属养老金待遇、个人所得税申报方式、继子女收养等关键领域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裁判,但是在形式上,联邦宪法法院仍然认为同性伴侣不是婚姻,而这还需要立法者的继续努力,以及人们社会观念的变化。
同性伴侣;注册生活伴侣法;平等保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同性之间缔结的类似于“婚姻”这种生活形式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某些国家是以“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的名义出现的,但是在德国则断不能以“婚姻”称之。〔1〕德国联邦议会于2017年6月30日,以393∶226的多数决通过了由“红红绿联盟”(Rot-Rot-Grün,SPD,Die Linke和 Bündnis 90/Die Grünen)提交的《同性伴侣与婚姻平权法案》(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Einführung des Rechts auf Eheschließung für Personen gleichen Geschlechts),这部法律修改了德国民法典关于婚姻仅限于异性之间的传统定义,将结婚的权利赋予了同性伴侣。但是此事并未就此了结,根据《法兰克福汇报》(FAZ)2017年7月1日报道,执政的联盟党主席沃尔克·考德尔(Volker Kauder,CDU)对此发表异议,并考虑将其提交联邦宪法法院裁断。《同性伴侣与婚姻平权法案》的最终命运如何,将由联邦宪法法院来决定。但这部法案的通过,则标示着同性伴侣的平等保护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2001年2月16日,德国联邦议会制定了一部条款法〔2〕在德国法中,条款法(Artikelgesetz),也被称作“大衣法”(Mantelgesetz),寓意一部条款法就像一件大衣一样,涵盖了某一既定主题下诸多法律的修订内容。vgl.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Handbuch der Rechtsförmlichkeit:Empfehlungen zur Gestaltung von Gesetzen und Rechtsverordnungen.3.,neubearb.Aufl.Köln:Bundesanzeiger-Verl,2008,s.17.:《结束同性伴侣歧视法:伙伴关系》〔3〕Gesetz zur Beendigung der Diskriminierung gleichgeschlechtlicher Gemeinschaften:Lebenspartnerschaften.,其中第一条是被称作《注册生活伴侣法》〔4〕Gesetz über die Eingetragene Lebenspartnerschaft.的法律,共19条,其正式在法律层面上用“注册生活伴侣”这一称谓将同性的这种关系(以下简称同性伴侣)确定下来。直到今天,虽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了持续努力,在同性伴侣的遗产继承、遗属养老金待遇、个人所得税申报方式、继子女收养等关键领域作出了平等保护的裁判,并促使《注册生活伴侣法》不断修订〔5〕最近的一次修订是在2015年11月20日。,使同性伴侣与婚姻在保护效果上趋同,但是同性伴侣不是婚姻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仍未发生改变。
一、《注册生活伴侣法》出台的背景
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在德国历史上一直受到刑法的制裁。〔6〕戴瑀如:《由德国同性伴侣法的催生、影响与转化检视德国对同性人权之保障》,载《月旦法学杂志》2014年第1期。1871年5月15日制定的《帝国刑法典》〔7〕Reichsstrafgesetzbuch(RStGB).第175条规定:非自然奸淫,男子与男子间性交,以及人类对野兽性交,可判处监禁,甚至剥夺公民权利。这一规定直到1994年3月10日才被完全废除。同性之间性行为的除罪化,为同性伴侣的民事保护开辟了空间。
同性伴侣的民事立法过程颇为曲折。最早向德国联邦议会提出立法动议发生在1990年3月18日,当时由绿党(Die Grünen)提出,但是没有成功。〔1〕Vgl.den Entschließungsantrag der Fraktion DIE GRÜNEN vom 18.Mai 1990,BTDrucks 11/7197.之后在1993年10月4日,联邦宪法法院作出了一个判例〔2〕BVerfG,04.10.1993-1 BvR 640/93(NJW 1993:3058).,其要旨是民政局否决一对同性申请者结合的请求是符合宪法的。原因在于基本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婚姻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结合,同性之间的结合不符合“婚姻”的定义。而且从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断定婚姻关系的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虽然非婚生儿童的数量在增加,无子女的婚姻数量也在增加,但是婚姻的结合并不依赖于婚姻中的繁殖能力。宪法保护婚姻的首要目的即在于为家庭的成立和孩子的共同生活提供法律保障。
这个判例无疑为同性伴侣立法制造了障碍,但是在1994年2月28日,则发生了一件有益的事件。这一天,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份决议,要求其成员国致力于消除同性人群在各自国内法律和行政规则上的不平等待遇。〔3〕Vgl.Amtsblatt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C 61 vom 28.Februar 1994,S.40 f.与此同时,在若干欧洲国家,调整同性伴侣的法律也开始出现,这自然也就推动了德国同性伴侣立法的发展。
2000年7月,联合执政党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在联邦议院的立法程序中提出了《结束同性伴侣歧视法:伙伴关系》的草案。由于这部法律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不仅引入了注册生活伴侣这项制度,还包含相关配套措施,如税法、社会保险法及程序法等修正。这样它就受到了基督教民主党(CDU)、基督教社会党(CSU)及自由党(FDP)等在野党的抵制。当时联合执政党在联邦议院占多数优势,但是在联邦参议院则席位不足半数。
于是,经过主管的联邦议院法律委员会〔4〕Rechtsausschuss des Bundestages.建议,该法案在2000年11月8日被一分为二地进入立法程序讨论:一部分被称作《结束同性伴侣歧视法:伙伴关系和调整注册生活伴侣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5〕Gesetz zur Beendigung der Diskriminierung gleichgeschlechtlicher Gemeinschaften:Lebenspartnerschaften mit den Regelungen zur eingetragenen Lebenspartnerschaft und zu den wesentlichen damit verbundenen Rechtsfolgen(LPartDisBG).,另一部分被称作《伙伴关系法和其他法律的补充法》。〔1〕Gesetz zur Ergänzung des Lebenspartnerschaftsgesetzes und anderer Gesetze.根据基本法第84条第1款之规定,一旦联邦议院制定的法律涉及各州之利益时,必须经过联邦参议院的批准才能生效。由于第二部法律草案涉及税法、移民法、社会保险法等各州之利益,在经过联邦参议院讨论时未获通过,〔2〕戴瑀如:《由德国同性伴侣法的催生、影响与转化检视德国对同性人权之保障》,载《月旦法学杂志》2014年第1期。故而只有第一部法律通过,即2001年2月16日制定的《结束同性伴侣歧视法:伙伴关系》。后来,虽然联邦议院召集了由两院议员组成的协调委员会(Vermittlungsausschuss)来重新讨论第二部法律草案,但并没有达成有效的决议。
《注册生活伴侣法》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据统计,在2000年估计至少有4万7千对同性伴侣,在2010年达到了6万3千对,〔3〕Zensus 2011.这主要是在民政局登记后的数据。虽然那些未登记的同性伴侣未为可知,数量也肯定不限于此,但是该法的实施并没有带来同性伴侣的大幅增加。原因可能是:在这部法律通过之时,虽然承认了同性伴侣的合法性,但是却未给予其与婚姻同等的对待,而是规定了诸多不平等对待的内容。试以该法最初版本第10条规定的继承权(Erbrecht)为例,其第1款规定:同性伴侣与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时,其继承额为1/4;与第二顺序继承人或者与祖父母共同继承时,其继承额为1/2。对于共同生活期间的财产,只要其不属于土地的附属物,或者其属于为了缔结伙伴关系而赠送的礼物,同性伴侣享有优先继承权。同性伴侣与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时,其享有优先继承权的份额以其维持适当的家庭生活所必须为限。优先继承权适用于遗赠的规定。
由于《注册生活伴侣法》存在诸多不利同性伴侣的规定。在实施之后,遭遇了很多责难。联邦宪法法院不失时机地介入这些法律争议之中,逐步提高了同性伴侣的保护水平。为此以下通过若干个重要判例揭示这一历史进程。
二、《注册生活伴侣法》的合宪性
《注册生活伴侣法》实施后不久,萨克森州政府、蒂宾根州政府和巴伐利亚州政府先后提出了对它的规范审查要求,认为(1)其在形式上不合法,没有得到联邦参议院的批准;在实体上违宪;(2)既违反了基本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婚姻和家庭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的规定;(3)也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于2002年7月17日作出判决〔1〕BVerfGE 105,313-Lebenspartnerschaftsgesetz.,驳回了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判决《注册生活伴侣法》合宪。不过第一庭的8名大法官对于这三项诉讼请求并不是态度一致,除了对第一项意见一致以外,对第二项是5∶3,对第三项是7∶1,据此本文着重从联邦宪法法院对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分析来认识。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同性伴侣的引入既没有违反基本法第6条第1款保障的结婚自由,也没有违反本款所体现的制度性保障,同样也没有违反该款作为“价值决定的基础规范”的内涵。在基本法上,结婚自由并没有因为同性伴侣的引入而受到影响,因为每个有结婚能力的人在《注册生活伴侣法》实施之后,依然可以自由地走入婚姻之道。婚姻在基本特征上是异性的结合,同性伴侣不是婚姻,它只是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受到长期的拘束。基本法第6条第1款将婚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保护,即制度性保障,但是基本法并没有直接定义“婚姻”,这就意味着该款的实施需要由立法者来落实,立法者据此享有广泛的立法裁量权,确定婚姻的形式和内容。基本法保护的婚姻不是抽象的,而是形成中的,是社会的主流观念的反映,而这恰恰体现在法律文本之中。婚姻自由的意义在于,男女可以平等的组合,从而自由地形成共同生活,排除国家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同性伴侣不是婚姻,并没有侵犯基本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婚姻作为制度性保障的内容。立法者只是通过引入同性伴侣的方式,更好地服务于人的个性发展权。婚姻作为有拘束性的价值决定的意义在于:国家应该采取措施,一方面不能让婚姻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促进,这也不意味着《注册生活伴侣法》违背了婚姻作为价值决定的含义。虽然立法者模仿婚姻在构筑同性伴侣的具体制度时采用了若干相似的规定,但是婚姻并未因此受损,因为同性伴侣的制度并不比婚姻制度更优惠,即赋予更多的权利,承担更轻的义务。相反在社会救助法上,婚姻当事人享受的权利更大,例如,在个人所得税上即扣税较多。虽然在基本法文本上,基本法第6条第1款规定:婚姻和家庭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但从制宪史来看,这一“特殊”的含义只是:不能让其他生活形式比婚姻更有利。当立法者因为引入了一项制度,从而与婚姻产生竞争性关系,例如,抚养这种制度与婚姻同等的权利,却承担较少的义务,以至于混淆了这种制度和婚姻的差别,那么立法者就违背了基本法第6条第1款保护的目的。而从目前来看,《注册生活伴侣法》并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所以在这三个面向上,《注册生活伴侣法》都是合宪的。
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体系化的解释在三个层面回应了基本法第6条第1款保护的婚姻和同性伴侣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同性伴侣不是婚姻,它不会侵入婚姻自由的核心领域。在联邦宪法法院看来,基本法保障的婚姻,在内涵上,首先表现为防御权,即国家不要干预男女之间的婚姻共同生活;其次才是积极权利,即要求国家采取保护措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创设其他生活形式,只要这种生活形式不会和婚姻相互混淆。为了解释这一点,联邦宪法法院从制宪史的角度对“特殊保护”中的“特殊”作了不同于一般情境的解释。正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黄舒芃女士所指出的那样,联邦宪法法院的初衷是良好的,但解释上却将“特殊”的含义掏空了,这其实带来新的问题,还不如在承认同性伴侣也是婚姻的基础上,将婚姻的定义扩大化,从而实现婚姻独享优惠待遇,既满足了基本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特殊保护”的要求,同时也能带来“婚姻自由”“制度性保障”“价值决定”三个面向上的融贯性。〔1〕黄舒芃:《隔离但平等?从“收养同性伴侣养子女”一案检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同性伴侣法制之立论》,载《兴大法学》2014年第16期。诚哉斯言!不管怎样,这个判例改善了同性伴侣的平等保护环境。
三、公职领域中对同性伴侣遗属〔2〕在该案的语境中,指养老保险投保人死后的配偶或者伴侣。养老金的不平等审查
相对于婚姻,同性伴侣养老金的发放一直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尤其是在公职领域。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在2009年7月7日作出的一个裁定(Beschluss)〔1〕BVerfGE 124,199 -Gleichbehandlung eingetragener Lebensgemeinschaft.,具体回应了这一问题。
在该案的判决要旨中,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在企业遗属养老金〔2〕Betriebliche Hinterbliebenenversorgung.这一领域,对于公职雇员而言,联邦和州养老机构〔3〕Versorgungsanstalt des Bundes und der Länder.制定的补充养老规定,不平等对待婚姻和同性伴侣,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是违宪的;虽然婚姻享有特权,但以一种歧视其他生活方式的做法,即便造成调整这种生活方式的生活事实与婚姻追求的目的存在可比较性,也并不能依据基本法第6条第1款而正当化对其他生活方式的歧视。
本案的起因是:联邦和州养老机构,作为公职雇员的补充养老保险机构,在制定的养老规则——《养老保险集体合同》〔4〕Tarifvertrag Altersversorgung-ATV.中,对于遗属领取养老金的规定没有涉及同性伴侣。于是本案的诉愿人就对其提出了附带审查的要求。诉愿人生于1954年,于1977年作为公职雇员开始工作,并在联邦和州养老机构缴纳补充养老保险。他于2001年与他人缔结了注册生活伴侣关系,在共同生活期间没有小孩需要照顾。
联邦和州养老机构向诉愿人告知,从2001年12月31日起,他的养老保险合同需要转换,原因在于他缔结了注册生活伴侣关系。同时,在计算他的工资税时,是按照未婚的税卡来计算,而不是按照已婚的税卡来计算(注:依据这种计算方式,诉愿人缴纳的工资税较多,而领取的养老保险金则变少)。他还被告知,他的同性伴侣将不被认定为《养老保险集体合同》上的婚姻配偶,因此在其死后不能领取企业遗属养老金。为了获得此项救济,在被下级法院拒绝之后,他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
联邦宪法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联邦和州养老机构制定的规定违法了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在企业遗属养老金的问题上,要区别对待婚姻和同性伴侣,需要按照严格基准进行审查,即是否存在足够重要的区分理由。〔5〕Ein hinreichend gewichtiger Differenzierungsgrund.一般平等原则要求依据规范对象和区分特征,对规范制定者进行不同的限制,从而达到比例原则必要性的拘束条件,因此在对不同的人群进行区别对待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正当化事由。当区别对待不同的人群时,一旦这种区分和人的人格特征建立联系,那么其造成的伤害越大,审查的要求也越严格。性取向的划分即可以归入这种情况。在婚姻和同性伴侣中,依据性取向在企业遗属养老金事项上采取不平等对待,应该采用严格审查基准来审查。
一旦从这种视角来看,正当化这种不平等对待的事由仅仅发生在,一方面,遗属养老金的调整对象在前提条件和法律后果上要强于社会保险法;另一方面,现在的遗属养老金规定不需要平等对待同性伴侣,然而这样的理由并不能成立。补充养老保险设立的目的就是保障雇员的工资待遇,这种保障不会因为婚姻和同性伴侣存在差异而有所区别。与此同时,就婚姻和同性伴侣的生活负担来看,在现实生活中也具有一致性。虽然在具体的家庭中,根据每个人社会地位的不同,生活负担会有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与每个人的生活状况和就业情况相联系的,而不能将这种不同用来区分婚姻配偶的遗属养老金和同性伴侣的遗属养老金。基于这些分析,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了下级法院的判决。
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从基本法第3条第1款中的一般平等原则中解析出了不同的审查基准问题。在人权问题上,基于性别而产生的区别对待,通常纳入严格审查的范围。只有当这种区别对待具有足够重要的理由时,才可以正当化。然而事实是要能满足这样严格的条件,通常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一旦法院采取了严格审查方式,系争对象通常很难通过法院的审查。
四、公务员家庭补贴问题上的不平等审查
在公务员这一职业中,同性伴侣也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庭在2012年7月19日的一个裁定〔1〕BVerfGE 131,239-Lebenspartnerschaft von Beamten(公务员的生活伴侣关系)。中认为,因为性倾向〔2〕SexuelleOrientierung.的缘故,在第一层级的家庭津贴〔3〕Familienzuschlag.发放中不平等对待婚姻和同性伴侣,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而违宪。婚姻虽然享有特权,但是在一个比较的意义上,歧视同受宪法拘束的其他生活方式,而不论这种生活方式调整的生活事实以及它的规范所追求的目的,并不能因为婚姻的保护命令而正当化对其他生活方式的歧视。除非依据基本法第6条第1款之规定存在足够重要的事实理由,在适当衡量调整对象和调整目的之后,才能正当化这种不平等对待。
本案的事实是:诉愿人作为领取薪资第A8级的联邦公务员,自2002年开始缔结了生活伴侣关系。他的诉愿请求是,审查《联邦公务员薪资法》第40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仅针对婚姻公务员的第一层级的家庭津贴待遇。因为按照这一规定,他在2003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无权领取津贴。联邦宪法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诉愿人的宪法诉愿成立,并得到支持。理由在于: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在本质上相同的情况就同等对待,在本质上不同的情况就不同对待。因而它禁止基于人群的特征来区别对待,于是第3条第1款就落入比例原则必要性的审查之中。当基于人群的不平等对待要得以正当化,那么必然要遭受严格审查,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导致对少数人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正是基于性倾向的不平等对待产生的。
根据一般平等原则,性倾向是明确禁止作为区别对待的构成条件的。虽然在公务员薪资立法的问题上,立法者享有较大的形成余地,但是它也要考虑到构成公务员薪资立法的事实条件和适合公务员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并考虑到不同的角度,这自然就与公务员薪资的额度有关系。但是在公务员家庭补贴的事项上,虽然《联邦公务员薪资法》第40条第1款第1项在名义上区分了每个公务员的家庭状况,比如分为婚姻公务员、鳏寡公务员、是否有独立住房的公务员等,但是却造成了间接歧视同性伴侣公务员的效果。因为在这种分类中,同性伴侣被排除了,按理它与家庭条件没有直接关联,可是它并没有被纳入该条款的规定之中。
此外,联邦宪法法院也认为,对同性伴侣公务员支付家庭津贴并没有违反基本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家庭津贴的作用是一种带有社会性的,名义上倾向于家庭的具有补充功能的手段。对于公务员而言,不论他处于婚姻之中,还是处于同性伴侣之中,这种功能是一样的。从家庭津贴存在的这一立法目的出发,歧视同性伴侣的做法也并不能正当化了。
在本案例中,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一以贯之,并越来越清晰。因为同性伴侣是基于性倾向的区分,那么它就属于一般平等原则的审查框架中。针对一般平等原则的案件,通常会借助严格审查和比例原则来进行。
五、个人所得税报税方式的不平等审查
婚姻和同性伴侣在个人所得税报税方式上的区别对待是《注册生活伴侣法》实施后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德国,报税方式是选择分开报税,还是合并报税(Zusammenveranlagung),〔1〕在德国,合并报税主要采用夫妻所得分割制(Ehegattenspilitting),这被台湾学者称为“折半乘二制”,即先将夫妻收入合并除以二,适用相应的税率,然后再乘以二得到最后的应纳税额。同时在税卡(Lohnsteuerklasse)上选择几级,这决定了个人缴纳个人税的数额。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就个人与婚姻比较而言,通常个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比在婚姻中缴纳的要多,这是因为优待婚姻之故。但是在婚姻内部,分开报税还是合并报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优惠位阶,其与夫妻二人的收入高低有关。依据夫妻不同收入的事实,由婚姻当事人选择较优惠的报税方式,同样考虑了婚姻优待。
然而在同性伴侣个人所得税的报税方式上,由于排除了夫妻所得分割制的适用,同性伴侣二人必须分别进行报税,也就是把同性伴侣看作独立的两个人来对待,这就造成了同性伴侣多纳税的效果,和婚姻相比产生了不平等。针对这一问题,联邦宪法法院在2013年5月7日作出了一个重要裁定〔2〕BVerfGE 133,377 -Ehegattensplitting.,认为《个人所得税法》第26条、第26b条和第32a条第5款在夫妻所得分割制上区别对待婚姻和同性伴侣,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因而违宪。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夫妻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上,适用合并报税开始于19世纪,它是作为个人报税原则的一种例外规定在1952年1月17日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之中的。联邦宪法法院1957年1月17日作成的一个裁定认为,1952年《个人所得税法》第26条规定的合并报税与基本法第6条第1款不一致,因为这种报税方式在累计税率的计算中没有考虑到婚姻当事人的给付能力,从而造成了比个人缴纳税款多的现象,即“婚姻惩罚”效果。基本法第6条第1款规定国家特别保护婚姻和家庭,包括两个意思:第一,在消极意思上保障婚姻不受其他生活方式的歧视;第二,在积极意思上要求国家采取积极的措施去促进婚姻。
在当时的背景下,强制采取合并报税的方式,会将妇女赶回家庭,即妇女被动地成为家庭妇女。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了职业妇女,双职工家庭的出现就要求申报个人所得税方式的改进,于是德国个人所得税法此后做了较大修改,规定了夫妻可以选择申报方式,即采取分开报税还是合并报税,由婚姻当事人自主决定。随着《注册生活伴侣法》的实施,这样的问题必然会出现在同性伴侣的现实中。
本案的诉愿人自从2002年5月1日起缔结了注册生活伴侣关系,他向某地方财政局要求以合并报税的方式缴纳自2002年开始的个人所得税,但是被该财政局拒绝,而且被要求以个人报税的方式缴纳。此事件经过地方法院的审理,一直被拒绝,最后诉愿人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
联邦宪法法院审理认为,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排除了基于人群的区分,因为这种基于人群的划分导致了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为此基于性倾向的纳入比例原则的严格审查就必须适用。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对于选择个人分开报税,还是合并报税,是以家庭状况为依据的,而不是以性倾向为依据的。依据《注册生活伴侣法》的规定,同性伴侣相互之间承担的家庭责任与婚姻趋同,在家庭状况上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为此在个人所得税申报上区别对待婚姻和同性伴侣是有违一般平等原则的。
六、同性伴侣继子女收养的不平等审查
《注册生活伴侣法》在2004年12月15日的修订中,引入了第9条第7款,即规定同性伴侣一方只能单独收养另一方亲生的孩子,但是不能收养另一方已经收养的孩子。这就是后续收养(Sukzessivadoption)的问题,或者说是同性伴侣能否共同收养孩子的问题。过去有一种观念认为儿童只适合在婚姻家庭中生活,不适合在同性伴侣家庭中生活。因为同性伴侣之间不存在异性,会给孩子的抚养和照顾带来母爱或者父爱上的缺失。在心理学或社会学上,这种观念是否有强烈的实证研究作为基础另当别论,但是它在一定时期内却成为社会通念(Volksanschauung),对立法的制定产生不小的影响力。
社会是在变化的,人们对同性伴侣能否合适地照顾孩子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在2013年2月19日作出的一个判决〔1〕BVerfGE 133,59-Sukzessivadoption.系统回答了这一问题,并作了充分的论证。在判决要旨中,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基本法第2条第1款和第6条第2款赋予了儿童在父母抚养和教育下的国家监督权,由此并不能推导出同性伴侣一方有权收养另一方已经收养的子女,不过同性伴侣作为儿童的父母,却也是基本法保护意义上的“父母”;同性伴侣与一方亲生的子女或者收养的子女共同生活,构成基本法保护意义上的“家庭”,那么立法者就有义务采取措施实现这一意义上的父母功能,而创设后续收养就是这一要求的体现;《注册生活伴侣法》第9条第7款区别对待不同的儿童,即不同对待婚姻中收养的儿童,同性伴侣中一方收养另一方亲生的儿童以及同性伴侣中一方收养另一方已经收养的儿童,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
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儿童享有个性发展的权利,并处于国家的特别保护之中。儿童需要保护和帮助的理由在于帮助他们适应在社会共同体中形成自我负责的人格,因此要求立法者保障他们成长所必需的生活条件,这其中一部分是国家的责任,另一部分是父母的责任。依据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的规定,这首先是父母的责任。国家的作用在于支持父母的这一抚养和教育责任,并提供补充。从这个意义上看,由于父母是承担儿童照顾的第一责任人,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并不能直接得出国家有创设后续收养的义务。
但是,如果具有收养意愿的同性伴侣一方,在没有后续收养这一制度的保护下,他(她)就不享有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地位,不可能承担起实现儿童福利的职责。排除后续收养的适用,那么儿童只处于父母一方的保护之下,对于具有收养意愿的另一方而言,则不会产生这种效果,因为他(她)在法律上并不是儿童的父母。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同性伴侣能否构成宪法意义上的父母,从基本法第6条第2款的规定中是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的,因为基本法并没有明确排除同性伴侣不能作为父母,同时,宪法上父母权利存在的价值在于保护儿童,即立宪者认为父母比其他的人或者制度更能保护儿童福利,并防止国家的干预。是否满足服务于儿童福利的能力,并不因为父母是异性或者同性而有差别。从人们对“父母”理解的社会观念来看,今天人们也认可同性伴侣可以作为父母了。
就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而言,区别对待的正当化理由仅仅存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区分目的和不平等对待的程度是适当的。即便承认立法者并未侵犯儿童的基本权利,但是区别对待同性伴侣一方收养另一方已经收养的儿童,造成了此类儿童不能在后续收养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生活形成的机会,这实际上造成了区别对待儿童的事实。妨碍后续收养的主要理由在于,同性伴侣家庭不适合儿童的成长,这是出于一种保护儿童的目的,然而论证这种目的的社会学证据,并不充分。相反既然儿童已然与亲生父母分离,为了保护儿童,在儿童与收养父母之间建立稳固的家庭关系,有利于儿童的心理稳定和社会融合。同性伴侣作为儿童共同的收养父母,会让儿童更有归属感,也能促使同性伴侣双方强化自己的父母责任感。
基于此,同性伴侣一方可以收养另一方已经收养的子女,后续收养也适用于同性伴侣。自此,同性伴侣与婚姻之间在保护效果上日渐趋同,虽然在名称上,同性伴侣依旧与婚姻有别。
七、结论
德国同性伴侣的平等保护走过了相当长的阶段,它是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持续努力得以创造。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解释基本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婚姻家庭受国家的特殊保护和第3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实现了同性伴侣与婚姻保护趋同的效果。这一努力值得肯定,而且在对一般平等原则的适用中,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区分标准的观察,在比例原则中纳入了严格审查的要素,使立法者的保护义务十分严苛,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婚姻受到国家“特殊”保护的规定丧失了实质意义。如果说婚姻和同性伴侣在功能上相同,那么在名称上则也可以统一,即认为同性伴侣也是婚姻。然而联邦宪法法院并没有这么做,一方面可能考虑到了立法者的立法形成余地,另一方面考虑到了社会观念。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同性伴侣就是婚姻,而立法者也将同性伴侣定义为婚姻时,同性伴侣的平等保护才能真正实现,而联邦宪法法院并不能代替民意机关的工作。
∗ 叶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博士后,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宪法学,家庭法学和网络社会治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