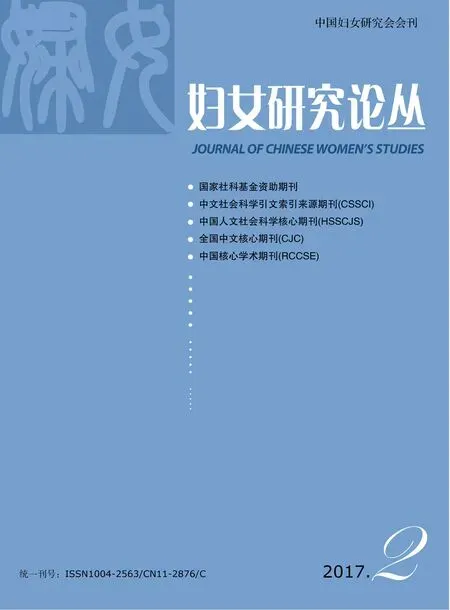《天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视野与何震的“女子解放”∗
刘人鹏
(台湾清华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新竹30013)
《天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视野与何震的“女子解放”∗
刘人鹏
(台湾清华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新竹30013)
何震;女子革命;女子解放;革命的女权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天义
晚近学界对何震的研究,大多强调了何震的无政府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话语的分离,不同于她同时代之进步男女知识分子的女权主义热衷于国族现代性,何震却不局限于国族主义、种族中心,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私有制,主张终结所有社会强权特权,达到完全的社会平等。本文以为,要理解何震的女权主义何以能跳脱国族中心及资本主义私有制,除了性别立场,还需要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视野。此外,我们也需要把何震的女权主义放在晚清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脉络中,其理论与运动是紧密联结的,知识生产模态不同于其后学院女性主义论述生产。
一、前言
晚近学界对何震(1886-1920?)[1](PP491-539)的多种精彩研究,大多强调何震的无政府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话语的分离①夏晓虹对此议题则针对历史背景讨论,她指出何震将“女界革命”“凌驾于种族、政治、革命之上”,然“仍与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关”。见夏晓虹:《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83期,第318-321页。[2](P206)[3](PP100-117)[4](P7)[5](P73)[6](PP136-168),她不局限于国族主义、种族中心,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私有制,主张终结社会上所有的强权或特权,达到完全的社会平等[3](P7)[4](P73)。 本文认为,要理解何震脱离“国族中心”的“女子革命”或“妇女解放”论述,除了性别立场,同时也需要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历史视野。这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立场,不同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②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附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家族制之废止”一节后,按语特别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与《天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1908年《天义》刊登的《共产党宣言》前有一序言说明,对马克思的肯定在于其主张“共产”、国际间劳动者团结以行阶级斗争,不同意的则是其共产制非无政府之共产,因为承认国家组织:“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万仕国著、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0页。,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③按Anarchism早期多半译为“无政府主义”。马君武《俄罗斯大风潮》是较早译介无政府主义历史的书籍,其“序言”曰:“新主义英文曰Anarchism无政府主义,今予所译之书,即所种主义之历史也。”〔见[英]克喀伯著、“獨立之箇人”(马君武)译:《俄罗斯大风潮》,少年中国学会,1902年,第2页。〕后来则有指出Anarchism其义应为“无强权主义”,如1907年真民(李石曾)译《世界七个无政府家》,于介绍克鲁泡特金时曾解释“无政府”古谊为“乃无强权也,非扰乱也”([德]爱露斯(Eltzbacher)著、真民节译:《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家》,《新世纪丛书》,1907年,第7页)。因为安那其并非只反政府,乃反一切强权;五四时期也有建议音译为“安那其主义”者。本文皆用“无政府主义”。中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与集产无政府主义(详后文)。《天义》的论述实践可以放在当时何震与刘师培(1884-1919)在日本“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脉络中,理解其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关系;也可以放在晚清现实政治的脉络中,理解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立场对于“维新”及“革命”派争论的介入[7](PP238-239)[8](P318)。 此外,理解《天义》及何震学说的另一个重点是:革命/学说/运动的紧密联结,其知识生产模式,并不同于后来学院女性主义理论生产,以“革命运动”或“活动”的精神来阅读《天义》与何震的言论,较能在当时语境中见其在晚清反满革命以及国际无政府或共产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参与或介入时事时论的动态脉络与张力。《天义》是晚清革命氛围中,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当时维新现代性的介入批判,其现实背景也包括1901年之后变法思想方兴未艾,士绅阶层亦多有参政要求[9](PP96-97)。当然,何震以女性立场提出“女子革命”“男女革命”“女子解放”等议论,介入当时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运动,一方面具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当“女子解放”或“女子革命”的立场“介入”后,也就无法单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为框架化约其女权主义。
“性别”向来是一个争论的地点,通常以充满争议的论述/实践在历史过程中出场;但这并不是天真多元的百家争鸣或百花齐放,而是血淋淋的各种身体与文化位置的争论,关系到现实的生存以及对未来的想象(亦即关于“谁值得拥有未来?”的政治)。性别理论并不是孤立超然的体系,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现实中,联结于各种其他理论/运动/思潮。晚清以来历史过程中复杂的论辩与实践,可能也需要在种种理论框架与现实脉络的来回相互对照中尝试理解。另外,单单从今日的女性/性别研究角度看,何震的女权主义似乎无法立即进入既有的辨识框架中:她没有受压迫女性的无辜姿态,既不贤淑也不女杰,又无法以“父权即暴力/女性即和平”的现成期待立即为之定位;其“女子复仇”等论说绝不回避暴力性的反抗暴力的压迫,其“女子反军备主义”则基进地④此处“基进”一词部分沿用了1990年傅大为的诠释:“一个基进者涉及到的是一社会性、位置性与立场性的问题,而非心理、生理与态度的问题。……‘基进性’(radicality)的意义,就像具有主根(radical root)的植物一样,它具有一主根深入地中,立足于一自主而独立的空间中。”傅大为:《基进笔记》,台北:桂冠出版社,1990年,第3页。反军国主义暴力;此外,其论述似也不合乎化约的“解放”想象,性道德的主张似乎保守又严峻;甚至,何震是否支持“女权”,亦非一目了然,需要费力讨论“女权”在无政府反对代议制中的意义,以及何震对“强权”的看法。如何脉络化地辨识或重估其较为复杂困难的历史与理论议题,更是格外具有挑战性,值得持续探索⑤还有一个问题是,署名为何震的文章,学界也曾有疑其为刘师培代笔之说,详见夏晓虹:《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83期,第312-313页。何震生平传记资料极少,在她名下的文章,也因种种原因常被怀疑非她本人所作,但至今并没有直接证据肯定,也没有直接证据可以否定。本文的讨论,比较倾向于分析论述历史、形态与理路,暂不聚焦于作者研究,讨论何震的学说时,就是指《天义》中署名为“何震”或“震述”的文章,此外,关于女子解放议题的讨论,亦旁及《天义》中署名“志达”“畏公”“亚公”等与女子问题相关的文章。,上述诸多问题较完整的讨论,尚待另文,本文仅是初步探讨。
二、“革命”语境中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何震、刘师培等1907-1908年在日本办《天义》报期间,投身于无政府主义论述/运动,但他们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应该不会晚到此刻才刚开始。1907年8月,“社会主义讲习会”开第一次大会时,何震发表演说就提到:“吾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故创办《天义》报,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10](P310)把创办《天义》归于对“无政府主义”的“迷信”,用“迷信”二字来描述自己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不应是初识无政府。何震婚后赴上海,曾入爱国女学。她在爱国女学期间的学习与活动,目前并未见较详细的直接讯息,但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材料,勾勒此一时期周边的革命论述/实践氛围,亦即,就论述语境而言,早在上海时已经浸染于无政府革命论述/实践的土壤中了⑥本文以下铺陈1904年前后上海的无政府或社会主义相关之革命论述环境,或1907年左右出刊的《天义》以外其他无政府主义书籍,都不是在“影响论”的框架下讨论,简言之,不是指哪位作者读过哪本书受到影响,而是就论述话语试图勾勒当时言论语境或论述土壤。当时许多号召革命或开通论述的无政府主义小册书籍等刊物,在政治监控与警察搜捕的压力下,究竟如何秘密流传,如何被阅读,被谁阅读,都不易追踪。。
爱国女学是蔡元培(1868-1940)等人发起,于1902年底开校上课[11](P250)。其教育工作与革命运动紧密相关[12](P7)。1904年何震入学,当时爱国女学已经充满了革命与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氛围。与何震共同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的周怒涛,也是爱国女校的学生。蔡元培曾说此刻“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⑦此据高平叔引黄世辉所记蔡元培口述《传略》,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0页。又,蔡元培于1902年的《〈中等伦理学〉序》已提到“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凡其说至易冲突者,皆务有以调和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9页。。《天义》的《女子宣布书》中提出“男女均去其姓”的主张⑧何震“双姓说”与“废姓说”的详细讨论,见夏晓虹:《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83期,第344-350页。又《天义》第二号署名“亚公”(女子复权会的共同发起人之一徐亚尊?)的《唐铸万先生学说》中也提到“用父姓而遗母姓”之非(见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8页)。关于废姓或从父姓或母姓的问题,并不是何震个人提出的特异主张。,在蔡元培1904年发表于《俄事警闻》的《新年梦》一文中已提及,该文提到未来理想社会废姓名、废家庭、废婚姻、废法律,“那时候没有什么姓名,都用号数编的”[13](P455)⑨直到1930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南京立法院招待餐叙时,胡汉民提出三个问题,要求会员发表意见,其一即“姓的问题(一)要姓?(二)不要姓?(三)如要姓,应从父姓,抑应从母姓?”当时蔡元培、吴稚辉、李石曾等都应邀发表意见。蔡元培仍主张“不要的好,用父的姓不公道,用母的姓也不妥当,还是不要的好。可以设法用别的符号来代替”。《关于姓、婚姻、家庭问题的谈话》(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04-405页)见《申报》1930年4月19日《昨午立法院之盛宴——解决姓、婚姻、家庭问题》,又可参考陈慧文:《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毁家废婚论》,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2015年。。《俄事警闻》自1903年12月19日起,直到1904年,几乎每期都登的一则广告是“无政府主义出版”,而从蔡元培后来的忆述看,蔡元培当时对于“革命”的认识,即认为革命只有两途:暴动与暗杀,并认为“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14](P196)。
事实上,暴动、暗杀、女子更宜从事暗杀等这些观念,早已见于1902年马君武所译《俄罗斯大风潮》[15]。该书提到俄罗斯女豪杰刺杀大将军之事,谓“妇人女子之尽力国事,较之男子尤愈易也”⑩《俄罗斯大风潮》中介绍了俄罗斯女豪杰韦拉沙嫂丽支(Vera Sassoulitsch)刺杀将军之事,而后曰:“夫俄国革命党人杀人亦多矣,何独韦女杰杀一将军而举国怜之,于此见人情之所趋,而妇人女子之尽力国事,较之男子尤愈易也。”〔见[英]克喀伯著、“獨立之箇人”(马君武)译:《俄罗斯大风潮》,少年中国学会,1902年,第13页〕但这段是马君武译文的发挥,喀克伯原著只叙述了大众对于女子韦氏的同情,叙述了女子运动的显著影响力,并没有这句。。蔡元培又提及在爱国女校的教育,包括“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⑪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6页),周怒涛即爱国女校学生中“年长而根柢较深”者。,这些内容也都已见于《俄罗斯大风潮》及1903年自然生(张继)的《无政府主义》[16]、1904年金一的《自由血》[17]等书。 这些书籍译介了虚无主义在俄国的起源及虚无党活动、各国无政府党活动情况、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等,在上海出版⑫夏晓虹讨论过这些背景,见夏晓虹:《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83期,第314-316页;另可参见张玉法:《俄国虚无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载柯伟林、周言主编:《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3-111页。。这段时间,蔡元培与刘师培也实际从事暗杀行动[18](PP179-205)[19](PP17-42)。
马君武的《俄罗斯大风潮》序言谓“人间之最可恶者,莫如野蛮时代之所谓圣贤矣……不能立足社会之外,以指点批评现社会之罪恶,出大力以改造社会,破坏旧恶之社会,另造新美者”[15](P1)。 将社会理想人物典型由顺应社会成规的“圣贤”,转变为能“破坏”社会的豪杰。1901年后反满革命气氛日益高涨,反满革命所用的话语如暴动、暗杀、复仇等,都在这些论述中出现。但此刻也有辨析之作,例如蔡元培1903年发表于《苏报》的《释仇满》,辨析“仇满”为“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20](P172),辨明“仇满”所反对的是“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以及“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20](P173)。 以上话语或话语模态,我们在《天义》中都能看到踪迹⑬仍要强调这里的意思并不是指“影响”,而是指论述形态相呼应的关系。。《天义》报《女子复权会简章》中“以暴力强制男子”“以暴力破坏社会”[10](P582),何震的《女子复仇论》使用“复仇”⑭按“复仇”一语并非何震个人激烈用语,基本上来自《春秋》经传的讨论。汪荣祖曾指出,晚清“章太炎用复仇之义来排满”,而康有为同样认同《公羊传》的春秋复仇之义,说明“复仇”之义“乃双刃之剑,既可用之革命,亦可用之变法”。可参见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李隆献:《清代学者〈春秋〉与三〈传〉复仇观的省察与诠释》,《台大文史哲学报》2012年第77期,第1-41页。等语,基本上延续着反满革命的话语模型,而对于“破坏”的强调,也呼应着巴枯宁(1814-1876)的主张⑮对巴枯宁学说的引介常见以“破坏”为重点,但《天义》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中,则可见大杉荣演说巴枯宁的“联邦主义”及其他。。何震的“反”较之政治性的反满革命,多出了性别、经济以及反种族中心的维度。然19世纪后期以来,女子问题不论在维新、革命、解放或国族论述中都常被连带提及,成为现代化过程中论述必然投资的地点之一,工农问题与女子问题的连线并不罕见,例如《自由血》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当农民困苦呻吟之日,正女子束缚压制之时。”[17](P7)只是在不同的论述框架中,性别问题有着不同的模态并摆放在不同的位置。
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在晚清酝酿排满革命的氛围中被译介,1902-1904年透过一些小册编译书籍发行,译介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俄国民粹派、虚无党、虚无主义等都有若干交涉。马君武1902年的《俄罗斯大风潮》,译自1892年英人克喀伯(Thomas Kirkup,1844-1912)《社会主义史》(A History of Social⁃ism)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一章,谓无政府主义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起源于蒲鲁东(1809-1865),但其理论得到充分发展,却应归功于俄国鼓动者,其最要为巴枯宁。马君武该书并非直译,增删发挥都有,更重要的是摒弃原著对无政府主义所持的保留态度,而使译介文字完全服务于召唤革命⑯喀克伯对于俄国青年革命热情的简介,行文之间是带着冷静理智的基调,并不与无政府主义同调,蔡元培在1920年的《〈社会主义史〉序》一文中,称之为“稳健派”,“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辨护家庭,辨护宗教,辨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且辨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5页。。《俄罗斯大风潮》指出:社会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源头,而社会主义又称“公产主义”⑰“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m,实发源于公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Socialism)。”见[英]克喀伯著、“獨立之箇人”(马君武)译:《俄罗斯大风潮》,少年中国学会,1902年,第1页。,书中很长篇幅介绍巴枯宁,提到了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时“巴氏为马格司 Marx党所屏逐”[15](P3)。 推崇巴枯宁是“以革命为恒业者也”[15](P4),而对于巴枯宁学说的介绍,则曰:“巴枯宁之社会主义,最直截爽快之主义也,是为革命社会主义,而以唯物论Materialism为之基,剖击一切推源上帝之名义,剖击一切外部之威权。”[15](P4)并说“巴氏不认世界上之有特权者。其言曰:人之有特权者,必至自杀其良知,试观人之有政治特权或生计特权者,其不怀邪恶之意念者几人乎”[15](P5)。 “又弃等级之制,无不平等之政治,无不平等之生计,弃承袭遗产之制,人人作工,自食其力,各有其分。田地为公共之物,赀本为全社会之公产。”[15](P5)亦即,此刻对巴枯宁之译介,已经带出了“反特权”、反对不平等的政治特权与“生计”特权、反对遗产继承的私有制以及资本应为全社会“公产”⑱《天义》:“巴枯宁倡破坏,苦鲁巴金言共产”,见《致中国人书》,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63页。的主张。另外,金一《自由血》于介绍虚无党之外,书中也包括巴枯宁的“极端共产”之说[17](P26)、反对财产私有、“废止遗产传袭”、“主张男女同权”[17](P118)、虚无党之女杰[17](P124),并略提及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立场矛盾等。
19世纪当帝国主义挟资本主义现代性席卷全球而造成多种不公压迫与剥削时,对抗性的国际劳工联合运动中,充满了理论/立场/路线间的大小矛盾,激烈争辩/斗争着什么才是最好/正确的运动策略与未来愿景。《天义》曾刊出恩格斯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其中已可看到当时国际劳工联合运动中各党派结盟之不易:一方面是马克思提供一个“宜与各党以满足”的政纲,另一方面亦略见对蒲鲁东等的批评,并辨析“社会主义者,中等阶级之运动;而共产主义者,劳动阶级之运动也”[10](P268)。 刘师培曾作《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该文将1873年巴枯宁与马克思之分道扬镳作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分离之始,但在上述恩格斯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倾向于以“共产主义”为自己命名。
《天义》中多篇文章表达的立场是,“共产”一派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通的,都主张财产平均,化私有为公有,以平等为归,“不得别之于社会主义之外”[10](P246)。 《天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势不两立的对立点在于:反对设政府,反对借国家之力来平均财产,因为会使得国家又成为强权或财产分配的中心。《天义》对于《共产党宣言》肯定其“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10](P270),并认为恩格斯的英文版序言“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10](P270)。 对于《共产党宣言》,亦推崇其主张“共产”,认为其要旨在于“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乃是“不易之说”;当然争点仍在于反对其承认国家组织的“民主制之共产”[10](P420)。 《天义》的终极立场是“废政府”与“公产”同等重要,同是目标[10](P50),亦即,“今之言共产主义者,欲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之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10](P87)。 “必颠覆政府,破除国界,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人人作工,人人劳动,于民生日用之物,合众人之力以为之,即为众人所公用,使人人不以财产自私,则贸易之法废。”[10](P85)
其实,不仅是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立场辨析,同样是无政府主义,当时诸多派别在运动立场、路线、策略、议程、短中长程的目标以及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方面,都有着争论。1907年“新世纪丛书”出版了多种无政府主义相关书刊。如1889年爱露斯(Eltzbacher)著、真民(李石曾)节译的《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家》,书中列了“七派”无政府主义者,包括高德文(Godwin,1756-1836)、蒲鲁东(Proudhon,1809-1865)、司梯尔(Stirner,1806-1856)、巴枯宁(Bakunin,1814-1876)、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842-1921)、梯于格(Tucker,1854-1939)、道司道(Tolstoy,1828-1910)。该书指出,无政府主义的三个主要议题是“政府”“法律”与“产业”,“诸家之作用与期望之结果亦不同。有主和平者用言语之感化也。有主强劲者行抵抗之术也。有主激烈者用凶猛之力也。有欲并政府法律产业同去之者,有欲去政府而变法律产业者”[21](P11)。另有1899年克非业(Cafiero)著的《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ie&Communisme),指出自由、平等是革命要点,“无政府即真自由;共产即真平等”[22](P6)。此外,罗列(Arnold Roller)的《总同盟罢工》(The Social General Strike)译本,书后标示“任人翻印”,书前有章太炎(1869-1936)、刘师培、黄侃(1886-1935)的序文。开宗明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纲目”提到几个重点,包括:社会之根基系于经济组织,社会的疾病如贫穷、压制、争斗等,都来自“经济不平等”,因此,无政府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将一切生产机关,自资本阶级中取回收用”[23](P1);关于政治,则认为“因有工价制度,方有资本家之立宪代议政治”,而政治为“握经济权者压制之具”,政府则为“握经济权者自卫之器”,因此,无政府社会主义“主张反对一切政府”,“待自由共产社会建设之后,其政治之特形,即为无政府”[23](P1)。 至于革命的方式,无政府社会主义认为,过去的革命是“争斗权力”,故革命者要先获取政权,但无政府的革命是为“开放被权制之社会”[23](P2),因此欲革命者“必先破灭政权”[23](P2),无政府社会主义“主张不藉立法议会为先导,而用平民之直接行动,为实行革命之捷径”[23](P2)。 纲目最后一条提到:“过去之压制,多用武力虐民,遂发生武力革命。资本家之压制,巧以经济缚人,今后欲得解脱,舍经济革命之外,无他法门。故无政府社会主义,主张社会的总罢工及非军备运动,为直接行动之妙用。”[23](P2)书中提到“总同盟罢工”的意思是:“要将目下的组织,从根本上改变起来,就是全世界的社会革命,把一切的政府,都破坏尽了,改成一切的新样子。”[23](P4)
《天义》刊登了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但对其间立场路线的差异,也予以辨析。例如《天义》摘译日本久津见蕨村《无政府主义》的《苦鲁巴特金之特色》一文,指出苦鲁巴特金与布鲁东都主张全废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对于财物归谁所有,持不同意见。布鲁东的集产无政府主义认为“凡物不得指明为何人之所有”[10](P389);斯撤奈尔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主张“凡物皆为我有”[10](P389);而苦鲁巴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则主张“凡物为众人之所有”[10](P390)。 另在《苦鲁巴特金学术略述》一文中推苦鲁巴特金学说“于共产无政府主义最为圆满”[10](P257)。 事实上,这类内容已见于1903年自然生所纂的《无政府主义》下编,该书推克鲁泡特金(译为“哥乐波度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为“近世共产主义之始祖”,而区别于布鲁东之“集产的无政府论”,及斯秦泥“个人的无政府论”[16](PP1-2)。 但自然生的《无政府主义》一书是初步简介世界各国无政府党情状,不重在理论的辨析。《天义》则辨明该刊无政府主义为扬弃个人无政府主义,而同时采用当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⑲刘师培曾说他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然與个人无政府主义不同,于共产、社会二主义,均有所采”。见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
日本人竹内善朔在回忆中曾提到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演说》中“演讲的主题,是当时人们关心的问题──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解说,俗称为自由社会主义”[24](P341)。 他指出,这是来自当时英国工党领袖哈第(Keir Hardie,1856-1915)赴日访问,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三个术语,形成一家之言,也成为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者左翼思想的用语[24](P342)。 这事在《天义》中也多次提到,较完整的是《日本社会党欢迎英开耶哈迭氏记事》。该文记录了哈迭氏访日演说概况,时一百五十余人参加,由片山潜翻译。哈迭演说内容包括,“由国内劳动者之运动,进而为世界劳动者之一致运动”[10](P307)以及“社会主义不以国界为限,并及运动之方法”[10](P307)。 哈迭主张劳动者以武力“争政权”的必要,并且主张要“与妇人选举权”[10](P307),认为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虽然相近,但应先实行社会主义,“自由共产主义”之说,应在社会主义实行之后。《天义》在介绍其说后,附加按语表示,哈迭氏“于无政府主义有微词”[10](P307),《天义》对此表示不满。次月在“时评”栏中又刊登《祝日本社会党之分裂》一文,指出哈迭访日后,日本社会党两派正式分裂,一派是主张直接行动、阶级斗争、无政府的直接行动派;另一派是排斥无政府主义,主张改良社会、救济贫民,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派。有意思的是,《天义》并不是惋惜运动分家不和睦,反而以“祝”词肯定运动中的分裂,因为多数人同奉一主义时,必然进步与保守立场之间会渐行渐远,所持主义更进者必将分离而获得展开。《天义》反对议会政策,并认为“以今日人民之苦,区区之救济决不足以谋平民幸福”[10](P290),倾向于直接行动派。
周作人曾经在回忆中提到,日本稍早已经译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但“一般的青年学生都感觉不易懂”,而“倒是不大科学的、多有空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比较的更有吸引力”[25](P678)。 《天义》中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译介,有些是针对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担心(认为无政府主义只是空想,会毁掉现今文明,只会破坏,只是凶暴等)而加以辨析,在当时崇尚“科学”的氛围里,特别强调苦鲁巴金的无政府哲学如何是“科学”的,从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方面,论证无中心、互相调和、互助等无政府主义的哲理及理想。
据《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录》,刘师培、张继等人1907年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主要问题意识就在于“中国人民仅知民族主义,不计民生之疾苦,不求根本之革命”[10](P307)。 亦即批判当时“民族主义”氛围,而立意从经济问题上考虑“民生疾苦”,并诉诸“根本之革命”。此外,《天义》创刊号社说第一篇是《女子宣布书》,提出“吾所倡者,非仅女界革命,乃社会革命也。”“男女之革命,即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10](P43)第二篇社说为“去非子”(刘师培)的《破坏社会论》,则曰:“欲实行种族、政治、经济、男女诸革命,均自破坏社会始。”[10](P46)创刊号《天义》另一版本的简章宗旨也包括“实行共产制度”及“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⑳《天义》简章之不同版本,详见万仕国、刘禾校注的《天义·衡报》“前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脚注1。。应是创刊伊始即女子革命与无政府共产革命相提并论了。唯其“女子”并不是现代西方性别论述所生产出的“身份政治”女性主体㉑这在Lydia H.Liu,Rebecca E.Karl,and Dorothy Ko.,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一书序文中已有所辨析。,而是指向历史过程中形塑出来的受压迫女子阶级及女人。何震论述中弱势的“女界”,并非指女子身体、生理或其他任何本质上较为软弱或不足㉒例如她驳“女子不胜工作之苦”之说,指出湘南、广西各地,男子不能胜任的苦役是由女子承担,见何震在刘师培《人类均力说》一文后所附案语(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3页)。,而是指在不公义的历史社会体制或结构中,或说是阶级性的斗争中,被迫处于不利或劣势的位置;并且,“弱者”在《天义》整体论述中,都是指被不公的特权压制,而不是软弱,是应该自求解放并追求平民幸福的主体,并且具有改变或终结世界不公的动能与责任。
《天义》在论述/知识生产上除了刊登译作,也从事理论的落地,回到在地历史脉络里,勾勒在地的轨迹,包括理论学说以及报道、采集与调查。学说方面,创刊号刊登了《李卓吾先生学说》,称李卓吾(1527-1602)为“中国之巴枯宁”[10](P223),在重读李卓吾的过程中,强调了李卓吾的“破坏社会”,但文中表扬李卓吾“破坏社会”,指的是“一曰破贵贱、贫富之界,二曰破亲疏之界,三曰破男女之界”[10](P224)。 在这里,“破坏社会”的意义就是指破坏社会制度中的既有阶序,破除现今生产出种种不平等且无法解决问题的政治体系,包括社会文化政治。“无政府”并不是反社会或无社会,而是最在乎社会的平等[10](P247)。 《天义》在李卓吾的学说中看到了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男女受同等之教育,自李氏始”[10](P226),也在唐铸万(1630-1704)的学说中读到男女平等的主张,作者“亚公”说:“躬为男子,于男女不平等,且痛斥其非。今之身为女子者,若犹执男子当尊之说,岂非女界之大贼乎?”[10](P230)这也看出,《天义》的女子解放不在于凝聚出女人认同,而是不论男女,都要破除男女不平等。
译作方面,《天义》有些翻译用字,也显出了在地的脉络。例如《天义》翻译的《共产主义宣言》序及其部分内容,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部分内容,其中译字的选用以及当时讨论的重点都值得留意。如bourgeois后来多采音译“布尔乔亚”,在《天义》译为“绅士阀”。这是沿用日文的翻译[26](PP350-356),但放在《天义》的论述氛围中,这就不是一个理论抽象范畴的译介,而是紧密联结到当时中国在地的社会关系,涉及“乡绅”在当时社会的某种意义。略举一例说明,1902年《启蒙画报》《杂俎:小儿怨》:“小儿说,孩儿爱爷娘,爷娘不爱儿心伤。孩儿想要强,爷娘不叫上学堂。爷娘说,我爱孩儿不爱钱,有了学堂你争先。小儿说,皇帝常把旨意下,为何官员不听话,爷娘说,不是官不听,银钱不现成,小儿说,官无银钱乡绅有,乡绅为何不出首。爷娘说:乡绅有钱自己用,那里肯向学堂送。小儿说,哎呀呀,中国百姓外国欺,欺来欺去要分离,那时乡绅做不成,乡绅为何不动心。”[27](P364)“乡绅”在这个脉络下,相对于贫困的百姓,被认为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有钱”却不顾社会公义者。这个早期的译字所反映的社会文化脉络隐约看到,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资本家-工人”之间的资本积累与劳动剥削的对于规律的分析,或是“资本”与“土地”结合而成就的私有财产逻辑,而是在早期中国脉络——并非如西方的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仍是农、商社会——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历史“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关系,理解为主要仍是农、商社会的“富”与“贫”的财富不公问题。这里主要的差异也许在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唤起的对于贫富差距的天地不仁之感,要如何转换为“阶级斗争”的唯物辩证历史分析㉓本文暂不展开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
在日本期间,是何震、刘师培集中接触并深入无政府运动/论述的时期。当时日本也有左翼妇女活动/言论的语境。据井上清的研究,1904年日本片山潜、幸德秋水、堺利彦等社会主义者曾号召中产妇女,举办妇女演说会,将要点发表于《平民新闻》。堺利彦曾讲过“家庭里的阶级制度”问题,“宣称社会的阶级制度是家庭的阶级制度——男人统治女人——的根本原因”,但他主张“自由恋爱”[28](P212)。1907年,日本社会党机关报《平民新闻》号召“受男子虐待而哭泣”的妇女充当工人农民的同志,共同奋斗[28](P215),幸德秋水的妻子营野须贺也是“无政府主义妇女革命家”,主张“无政府”及“共产”[28](P216)。此外,日本女性研究者竹中信子称“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赤旗事件中被逮捕、最后宣判无罪”的神川松子(1885-1936)“是第一位出身广岛县的女性社会主义者”[28](P321)。 她曾参加“平民社”的运动,“松子与福田英子、堺利彦的夫人为子、西川光二郎的夫人文子、大杉荣的夫人堀保子等人,在举办社会妇人演讲时热络地交谈。每个月一次的妇人演讲会中,男性演讲者有堺利彦、幸德秋水、村井知至、木下尚江、石川三四郎、安部矶雄等人,听众多的时候有三十几位女性,少的时候也有十几位”[28](P322)。 竹中信子提到,明治四十年(1907年),松子在《世界妇女》杂志上与远藤无水在“女性解放”的议题上发生论争[28](P322)。 当时松子未满 21岁,竹中信子引了她的几段文字,如:“即使没有经济能力,女性对于支配她们的丑恶男性,要打破他的头,要用力将匕首刺入污秽男性之胸膛。”[28](P322)这样的口气与何震《女子宣布书》似不相上下;但松子主张“妇女解放问题原本就具女性发展意义。要完全脱离奴隶的境遇,不论是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女性,都要获得自由的权利。要获得自由的权利,首先要获得经济自由。经济独立自由了,就没有必要再隶属男性。男性也不能再像今日这样蔑视女性”[28](P322)。 则不似何震更深入到分析经济剥削的体制如何使得男女劳工都无法真正自由解放(详后)。何震的女子复仇论或女子解放论,有没有与日本相关妇女组织或左翼妇女论述的互动或互涉,尚待考掘。
《天义》“记事”栏,除了刊登当时国际社会党、无政府党的重要活动,也刊载国际相关妇女议题,如1907年8月18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天义》于1907年9月15日即刊出了《万国社会主义妇人会议记略》,记载该会会前一天即由德国妇女发起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社会主义妇女第一次大会,记事中提到,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运动,那么妇女运动也可以是国际性的运动[10](P312),但关于这次会议讨论到“妇人选举权”的问题,则刊于次期《记女界与万国社会党大会之关系》中。可以看到当时有两派主张,一是限制选举权,要求女子要程度与男子同,才获选举权;一是年纪到了即有平等选举权。但《天义》本身对女子选举权的争取并不认为是运动目标(详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女界近事记》,记载了美国埃玛·高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到荷兰参加无政府党大会,美共和党报纸主张放逐高德曼,《天义》附记说:难怪共和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势不两立[10](P323)。1907年 11月 30日的《万国女界运动记》则记载了俄国海参崴大暴动“有多数之女革命党,图以爆烈弹破毁军舰营垒。事定以后,分别处死刑及禁锢之刑”[10](P231)。 凡此种种,可见《天义》革命性的女子解放论,对话与响应的对象,同时也是当时国际性的(广义)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不是以自己的国族为中心,而是从劳工、妇女、被殖民、被压迫的各个位置,试图作国际性的联合。
三、女子解放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视野
《天义》创刊号的《女子宣布书》一开头就从“世界”之男女立论,但并不是诉诸普世公理的抽象男女平等,而是“世界之男女,其不平等也久矣”,“久”字提示了时间性或历史性,在各地具体历史条件中所生成的不平等状态:如印度之女“自焚以殉男”;日本之女“卑屈以事男”;欧美各国,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且号称平等,但议政权与选举权“女子均鲜得干预”[10](P41)。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何震也主张女子要有选举权,这里指向的是对欧美代议制的批评,因为代议制参与者仍缺乏女性与劳工。无政府共产主义对于代议制的批判多指出:劳工阶级在革命后并没有获得政治权。何震从“世界”再落地到中国历史中,析论特定文化礼制中男女不平等形构:男女是主与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主奴关系是通过战争剽掠妇女而形成,人与物的关系则是通过婚礼财婚买卖的关系而形成。落实于日常生活,则在男女生命经验上形成嫁娶、名分、职务以及礼制上的不平等。
何震在《女子宣布书》及《女子复仇论》中都宣告“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10](P42、P49)。 《女子复权会简章》的“办法”:“对于女界之办法有二:一曰以暴力强制男子,二曰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对于世界之办法有二:一曰以暴力破坏社会,二曰反对主治者及资本家。”[10](P582)这是首先在理论上为男女范畴设计了阶级性的敌对与斗争关系,否则没有“革命”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一种“反抗”的设计,“反抗”所意味的是,意识到更为历史性与结构性的暴力。“反抗”所要求的是现状得以改变,以及未来得以开创。也可以这么说,没有反抗,也就没有权力关系,因为已经顺服于权力关系中了,这是为什么《女子宣布书》中对于“女子而甘于自屈”[10](P42)者,同样置于反对或破坏的对象,并且要“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破坏”也意味着让现状变得不稳定,以要求历史及未来的重现。然而,如果“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这话只是说女子受压迫的来源在于男子大敌,那么,解除压迫岂不是消灭或俘虏敌人即可?但何震在《女子复仇论》中,并没有讨论如何向男子复仇,如何消灭或俘虏男人㉔在《天义》的《女子宣布书》中,出现过如“如男子不仅一妻……则妻可制以至严之律,使之身死女子之中”及女子若甘事多妻之夫,“则女界共起而诛之”(见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页)之语,沿用了暴力革命话语。无独有偶,1907年日本女性社会主义者神川松子在《世界妇女》上有类似的话语:“即使没有经济能力,女性对于支配她们的丑恶男性,要打破他的头,要用力将匕首刺入污秽的男性之胸膛。”转引自竹中信子著,蔡龙保译:《日治台湾生活史——日本女性在台湾(明治篇1895-1911)》,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22页。。《女子复仇论》绝大的篇幅分析了社会文化中的各种压迫机制,如文字、礼制、学术等,她从历史轨迹指出,这些系统都暗藏性别阶序,在历史中,透过文字、礼制、学术等系统,都在生产男女的不平等。何震从性别立场指出“征之于学术,上古之世男子以学自私,既以学自私,由是一切之学术均发明于男子,故三代之书均含有轻女重男之说”㉕震述《女子复仇论》,《天义》第三卷,第1页。。几乎是由知识论的角度,指出“学术”本身的性别立场与政治,这个女性主义立场的中国学术史批判,深具理论内涵及历史价值。她的分析,使得表面客观的一些实践、程序或者曾经理所当然的合理性都变得不公平不公义,需要重新思考,或提出改变的行动。然而,反抗的设计大部分时候也无可避免会生产出新的“我们”,在女性主义论述中当然是生产出“女性”整体的身份认同,于是,很有可能反抗的设计最后也成为新的规训,透过新的权力机制,固定为另个真理的王国,成为仇视敌人的教条。但何震的《女子复仇论》指出:“盖女子之所争,仅以至公为止境,不必念往昔男子之仇,而使男子受治于女子下也。”[10](P50)值得注意的是,何震在讨论过程中,一方面析论男与女的阶级性社会关系如何在文化体制中操作出来,另一方面则不时将生存于体制性不平等关系中的“男子”与“女子”去稳定化,使之不成为身份认同的整体范畴。对何震来说,分别“男女”的机制是关键性的地点,这里生产着性别化的学术知识,部署着政治体制性的权力,同时也形构着主体经验,因此必须是一个进行政治性争斗的起点,而在她批判性的分析中,种种不均衡的历史过程得以呈现,得以重新寻找联结,不再弱弱相残以超赶强者,而是实践弱势位置之间各种解放的联结。
《女子复仇论》一方面说:“羞辱女子者,中国之学术也;戕贼女子者,中国之学术也;拘缚女子者,亦中国之学术也。”[10](P66)但她接着说:“倡此说者,亦幸而身为男子耳”[10](P66)。 “幸”指出这是偶然而非必然,也有个别男子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男子之于女子,虽主压制,然主张平等,亦有其人。”[10](P66)另一方面,同是男子,男子之间也有宰制关系,“受制异族”“受制君主”“受制资本家”,亦即男子之中也因种族、政治权力、经济关系而有着主治与被治的关系[10](P49)。 而个别女子当中,也有“自戕同类,以贻女界之羞”[10](P67)者,她认为“以女子受制于男,固属非公;以女子而受制于女,亦属失平”[10](P50)。 那么,如此一来,女子究竟如何可以“复仇”?向谁复仇?这就要归结到她所“迷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了。《女子复仇论》并不是讨论抽象普遍的女性,而是从“吾女界同胞”开始,在反满革命的脉络中,主张中国女子不应拾男子“种族革命”之唾余,革了满洲的命去换成汉族统制,她认为,若换成汉族君主,可能蹂躏女界更甚。如果不以暴易暴,只有往“无政府”的方向思考,“无政府”之外,更基础的还是“公产”:“惟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使男女无贫富之差,则男子不至饱暖而思淫,女子不至辱身而求食,此亦均平天下之道也。依此法而行,在众生固复其平等之权,在女子亦遂其复仇之愿。”[10](P50)因此,“复仇”对何震来说,就是革掉“不平等”的“仇”,使众生恢复平等㉖宋少鹏曾准确地指出:“何殷震认为女子的解放和真正的男女平等只能存在于实行公产制的社会中。”见宋少鹏:《“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7页。。不仅只是对“父权”家庭体制的批判,也包括对财产与女人私有制度的彻底推翻,思想资源还包括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想象以及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度的批判,等等。
何震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在理论基础上呼应着马克思与恩格斯,文章最后也附录了《共产党宣言》中与家庭制有关的一节。虽然《天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立场上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同,但对于资本私有制与性别压迫及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发展的认识上,二者有相当程度的共鸣。何震女权论述的中心主体不是晚清以来津津乐道的“才女”,而是当时经济不平等的现实生活里“要靠人吃饭”的女仆、女工、娼妓等。从劳资压迫关系看,男与男之间有压迫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经济独立或是有自己的职业也不见得就是解放,因为在社会上的职业,如果仍在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中,不论男女,仍然是受资本的压制。因此,对何震来说,妇女的解放并不能以“像男子一般有职业”为目标,因为从社会主义观点看,资本主义制度中,即使是男子,在劳动关系上也不是解放的,仍受制于资本家。于是,劳动者的解放与妇女的解放不可能分离。而从社会阶级看,女与女之间同样有压迫关系,《天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理想的平等不只是男不压迫女,同时也是男不压迫男,女也不压迫女。这是何震之所以没有把“妇女”作为同质的整体,而可以时时从“工女”的位置质疑女子参政是否真能带来工女的福祉,也同时揭露女子间因社会或家庭位置的不同,女子所受惨毒也可能来自女子。《天义》明确地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脉络中以阶级差异的视野介入当时新兴的男女平权议题的主轴,提醒少数女子获得选举权并不能为多数工女谋幸福。
这就涉及她对于男女性别之外与其他压迫体制的结盟与对抗,她论及女子参政运动所涉及的阶级问题、经济上“少数富民垄断生产机关”的问题、政治上国家政府是否必要的问题,这些都放在“女子解放”的议题中讨论,她的论文中时不时引述当时芬兰、欧美、澳洲等地妇女解放的议程,提出批评,论述的思想资源包括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传统诗文等等;早已经不是把两性问题抽空出来简化成单一的父权或国族议题。性别议题与革命、劳工阶级的议题联结,但也不忽略女子受压迫的特定性,而在汉族文化礼制的脉络下,提出对问题的历史性进行具体的批判分析。
我们今日阅读《天义》与何震的主张,可能无可避免地带着后来身份认同政治脉络下的女性主义理路,有着冲动想要询问“女性”问题是否在中心、性别问题是否较其他政治经济议题更根本等等,但在20世纪初何震所参与的革命运动脉络里,女子(婢、妾、娼、仆)、劳工、亚非弱族等,种种弱势位置必须透过(广义)社会主义连线,才可能看到世界问题的根源㉗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一文指出:“世界人类不平等之现象”包括:政府之于人民、资本家之于佣工、强族之于弱族;他也分别解释阶级不平等、职业不同、男女不平等之原因(见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6-106页)。另外,在《亚洲现势论》一文中,则分析了“白种加于亚洲之强权”,包括英人之于印度、法人之于安南、日人之于朝鲜、美人之于斐律宾等,主张弱种人民与国际社会党、无政府党相结合,以达到排斥强权、共产、无政府之目的(见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9-181页)。。在社会主义的思考模式中,不是从个人出发去分析个人身上的多重身份交织,而是从社会出发,去探究压迫的历史构成与权力部署。而复杂时事动态中的论述生产、知识或学说本身是一种运动,或本身即是改变知识框架的运动(例如,重新认识语言文字、礼制、法制中性别化的问题而寻求出路),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论点,或者,因着面对变幻的时事与社群的互动而推陈出新以因应,或者无可避免产生了矛盾,都是常态。例如,何震在《女子宣布书》中说“废尽天下之娼寮,去尽天下之娼女,以扫荡淫风”[10](P43),似乎粗糙地呼应着废娼论,但在《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中,则提出“卖淫之事,均由经济不平等而生也”[10](P200),并肯定《共产党宣言》“家族制之废止”一节,在按语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是:“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公娼、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10](P205)亦即,不可能在不平等的经济体制中废娼,只能把生产娼妓的经济体制废除。
事实上,《天义》中署名“畏公”(刘师培)的《论女子劳动问题》一文提出相当历史化的阐释。该文重构中国“蓄婢”制的历史,指出中国古代所谓“婢”起初是女子中的罪犯,战国以后,历代因种族、政治、法律制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状况,但该文认为,蓄婢制度并非由于阶级制度,而是由生计问题产生[10](P110)。“生计问题”即指“财产分配不平均”[10](P115),贫穷人家卖女儿是由于贫,民贫则是由于“财产不均”[10](P111),该文认为,只责备富人蓄婢并没有掌握问题,因为贫民是迫于生计而有鬻女之苦,且富人蓄婢并非用以生财,只用以服役,故非阶级问题[10](P111)。该文批评欧美各国因娼妓之制妨碍风俗而倡废娼论,且攻击中国、土耳其二国的蓄妾之风,中国也有有识者欲以一夫一妻之制取代蓄妾之制,但是该文指出,这不是风俗问题,而是生计问题。如果贫富不均,即使骤废娼妓、妾御制,但只能“废者其名而存者其实”[10](P117)。 欧美文明国虽然没有蓄妾之风,而且结婚离婚自由,但“彼之所谓婚姻者,实与蛮族之财婚无异”[10](P117),“论者不察,多以日本为娼妓国,岂知日本女子陷于此境者,即由于贫困之故乎?”[10](P118)亦即,该文对于当时用“一夫一妻”制与“蓄妾制”来分别文明国与落后国的通俗习见提出了批评,而直指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风俗,而在于“生计问题”。因此,若不能实行“公产”,对生计问题若不能大加改革,而空言改良风俗,则“虽废娼废妾之论宣传于全国,而为妾、为娼之贫女,宿娼蓄妾之富民,决非舆论及法律所能禁,则娼妓、妾御之制,亦必实去而名存”[10](P118)。
《天义》中多篇文章提到,只要有“政府”,不论是专制、共和或立宪都有特权。《女子复仇论》文中从性别角度提出的讨论是,有政府就有主治、被治之分,不要说当时西欧各国女子尚未能平等拥有参政权,即使男女可同握政权,也不可能人人都握政权,亦即,只要有分别“主治”与“被治”的机制,就有不平等,不论谁处于被治,都不平等,因此,其目标是去除制造不平等的机制,而非在既有机制下,去争夺或超赶“强”或“主治”的位置。《天义》对于当时中国大部分新式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富”与“强”,基本上采取质疑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目标是走向“贫”与“弱”,乃是从理论上看见:贫富强弱的不平等关系,根本是不公义的,必须取消。于是,贫与弱都不是主体(不论为个人或被殖民、被压迫的性别或民族群体)本质上贫弱,而是在不公义的结构关系中不幸处于劣势位置。经济不平等体制中的贫者,与男女不平等体制中的弱者,或殖民体制中的弱种,居于阶级关系中的劣势位置者,就必须联结或结盟,使制造出强弱关系的不公义体制或不平等关系本身,在历史中消失。何震在刘师培《人类均力说》后附记肯定该文“所言甚善”“与男女平等之说相表里”[10](P93)。她指出,重男轻女来自男女分工,男女分担不同的职务,又将职务分高下,平等之法不在于女子也可以做男子的职务,而是不再区分职务的高下,没有劳心劳力之分,“男子不以家政倚其女,女子不以衣食仰其男”,则“相倚相役之风可以尽革”[10](P93)。
马君武曾说:“无政府党人者,各国政府之最大公敌也。”[15](P2)当时世界无政府、共产等左翼运动几乎都处于书被禁、人被关被杀被放逐的边缘,以小册、演讲等运动的方式流窜㉘除了《天义》各种对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被放逐、被捕、被禁、被杀等的报道外,以下记述令人印象深刻:“明治四十三(1910)年六月一日,连台湾的报纸也刊载了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被捕的消息。这些人于翌年被判处死刑,报纸的报导对他们没有丝毫同情,认为他们的‘举动有如疯子一般’。”见[日]竹中信子著,蔡龙保译:《日治台湾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湾(明治篇1895-1911),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20页。。从《天义》对世界思潮及国际共产运动的各种译介的时间看,传译几乎同步,连线的动能其实相当强,当然可能都经过日本的中介。例如,1907年8月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在1907年9月15日的《天义》“记事”栏中就有报道;又如,英国《十四日评论》(Fortnightly Review)1907年5月的“Sex and Suf⁃frage”㉙在此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中文所林佩如同学,通过她在英国的同学,印到了该篇原文。一文,《天义》在1907年9月15日就刊出署名“独应”(周作人)的译文,题目为《妇女选举权问题》,但内文则将原文译为“性别与选举权”,可见此时已将sex译为“性别”。但《天义》虽然快速刊出该文,却附加按语表示:妇人参政是近日一大问题,然而“既争参政之权,即系承认有国家、有政府,与《天义》宗旨不合,因为《天义》意在“灭绝人治,弭消男子之特权,使男女归于平等,不仅以妇人参政为目的”[10](P401)。
《天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立足点,是“劳动者”或“平民”的位置。这个位置,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明现代性基本采取质疑态度,如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谓:“盖人民之幸福,在于家给人足,而不在于伪文明。今之震于西法者,炫欧美日本之文明,而忘其多数平民之苦,可不谓之大惑乎!”[10](P148)该文引用日本《女学世界》所记,其中有《伦敦贫民窟》,又引日本社会党发行之《光》,记载美利坚人自杀与他杀一则,说到“其中十分之七,均因生计不足问题”[10](P148)。 亦即,他在“文明之国”看到的不是国富民强,而是贫富不均结构中的贫民,欧美日本之文明不会是亚洲弱种的未来,而是前车之鉴。《天义》中《惨哉工女》一文谓“日本工女已尝之苦,即中国工女未来之苦”[10](P291)。 这个底层或贫弱位置联结的视野,以世界各地“劳动者”“贫民”或“平民”为出发点的视野㉚如《天义》:“近人有言,欧美文明,均劳动者所造成,吾谓昔之言国家学者,以人民为主体,谓不有民何有君,则今之言社会主义者亦当以劳动者为主体。不有劳动之人,即不能制造资本,资本家之富,孰非劳动者之所赐乎?人谓劳动者之死生,系于资本家之手,吾则谓资本家之死生,系于劳动者之手。资本家之富,劳动者之所与也。有与之之权,即有夺之之权,故今日欲行社会革命,不仅恃罢工已也。必合世界劳动者为一大团体。”大鸿:“时评”之《社会革命大风潮》,见《天义》第2号,1907年,第33-34页。,才是《天义》中何震等人的论述不可能有“西方-中国”二元尊卑逻辑,也不可能有民族主义救亡图存论的基础。《天义》当时极关注的,是世界性的各地种族及政治革命之外的社会革命风潮㉛如《天义》第2号“时评”栏中《社会革命大风潮》编按:“近日以来,革命风潮徧于欧亚,俄民之暴动、波斯之纷扰,印度则群谋独立,朝鲜则暗杀频兴,而中国革命亦起于闽粤。此皆种族及政治之革命也,而社会革命亦以近日为最繁,试举近事见诸东报者,译之如左。”编译内容包括法国制酒者暴动、德国罢工、劳工要求工作八小时运动等等(大鸿:“时评”之《社会革命大风潮》,见《天义》第2号,1907年,第32-33页)。此外,则是由无政府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角度,各文明政府对于异议者的禁逐与压制,也就无文明可言,如《衡报》短评“共和之病”:“共和政体者,专制政体之变相也。吾尝读美国宣告独立之文矣。距今百余年耳,无政府镇压策即发端于美国。近日哥尔多门女史Emma Goldman拟于英国开会,美国政府禁其赁演说场,近且禁其入境矣。此非所谓尊自由之国家乎?而倒行逆施竟若此。”见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21页。,如各国工人罢工、暴动、工时斗争等,以及欧美等各文明政府对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异议者的禁逐与镇压。
当资本主义挟帝国主义袭卷全球时,亚洲被殖民者、后进的社会,面对着革命的迫切性,《天义》预先思及革命后的何去何从问题,拒绝了“超赶”的逻辑,而主张在被压迫的位置上,基进地思考被压迫位置间的联结,以寻求避免重蹈欧美文明覆辙的方案。共产主义在经济基础上提问,而无政府主义则强力批判了民主议会制的局限,并对现代法律的阶级性或忽略阶级性提出质疑。无论是《天义》或年轻的何震,短暂的生命都还无法在这些问题上积累。何震论述中对于女子选举权、女子非军备主义、女子教育内容以及对于绅商及新政的批评等,皆非纸上谈兵,而是对于时事的介入性论述批判。而在当时,她的女性立场当然也是极其孤单而备受男性知识分子抨击的,例如,刘师培编辑的《衡报》,就刊登了同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人物张继的意见,希望改掉“女子复仇”等语,代之以当时更主流的“自由恋爱”论㉜《衡报》第四号,东京:1908年5月28日出版。。张继以“西方”革命党为例,认为应以社会革命为主,不当分男女之界,这也显示,何震的女性立场放诸世界无政府主义理论阵营中,也极其特立独行。何震的书写,不是书斋女性主义论述,也不是知识才女对劳动议题的跟风。她对当时日常社会生活的观察,处处包含了她对于贫民“生计”的分析。本文最后将以何震刊在《衡报》的一篇小文作结。
1908年8月8日,《衡报》刊登了《何震女史由镇江来函》一文,她从上海搭火车到镇江,看到的不是繁华风景,而是对于日常生活、城市小贩、物价、失业、贫穷等问题的观察记录与分析。城市车站里禁卖食物,她却观察到生活艰难的小贩仍然会在站外高呼;车上食物太贵,贫民搭车只能忍饥忍渴:
由上海至镇江,所经沪宁铁路,凡车站之中,不准卖食物者入内。卖者均于站外高呼,然下车购物者有几?故此等之小贩,生活极为艰难。而车中食物,则贵于市间数倍。一盂红茶,亦索价五分,则贫民之乘车者,亦惟忍饥忍渴而已。又各小站仅一面有车台,下车者必经轨道。稍不注意,即为车轹死。闻毙者已数人矣[10](PP784-785)。
她也记录了扬州镇江一带物价上涨的情形,三年之间贵了一倍,造就更多的贫民。镇江多家商店因钱庄剥削还不起债而倒闭,造成失业饥民:
扬、镇一带,近日物价愈贵。扬州非商埠,然鸡蛋一枚,已贵至十文以上;猪肉一斤,则需值一百六十文。较之前三年,殆增一倍,则贫民之多,可知矣。镇江各商店,闭歇者甚多,其原因均因钱庄盘剥,致负债不克偿。以致歇业。然歇业以后,则每店之中,均有十余人负闲。闻前日镇江沿江一带,破圩甚多。现徧处皆饥民矣[10](P785)。
这是极细致的现实日常角度的批判性观察。何震在短暂的生命中,虽没有从事组织底层劳动妇女的工作,《天义》短暂刊行不到一年,也很快落幕,然而,看似失败的运动,却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1]万仕国.何震年表[A].盛清社会与扬州研究:恭贺陈捷先教授八秩华诞论文集[C].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1.
[2]沙培德著,马小泉、张家钟译.何震与中国无政府女权主义[J].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3,(22).原作:Peter Zarrow.He Zhen and Anarcho⁃Feminism in China[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8,47(4).
[3]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4]Lydia H.Liu,Rebecca E.Karl,and Dorothy Ko.Ed..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5]刘禾、瑞贝卡·卡尔、高彦颐著,陈燕谷译.一个现代思想的先声:论何殷震对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5).
[6]宋少鹏.“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7]富田升著,张哲译.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明治末期日中知识界人士的交流[J].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3,(22).
[8]夏晓虹.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J].中华文史论丛,2006,(83).
[9]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10]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12]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A].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无署名).新年梦[N].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第73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初版.
[14]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A].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英]克喀伯著,“獨立之箇人”(马君武)译.俄罗斯大风潮[M].少年中国学会,1902.
[16]自然生纂.无政府主义[M].上海(无出版资料,当时在镜今书局寄售),1903.
[17]金一编译.自由血[G].上海:镜今书局,1904.
[18][美]伯纳尔著,丘权政、符致兴译.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19]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0]蔡元培.释仇满[A].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1][德]爱露斯(Eltzbacher)著,真民(节译).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家[M].新世纪丛书,巴黎新世纪书报局,1907.
[22][意]克非业(Cafiero)著,真民译.无政府/共产主义[M].新世纪丛书,巴黎新世纪书报局,1907.
[23][美]罗列(Arnold Roller,按即Siegfried Nacht)著,秋水原译.总同盟罢工[M].任人翻印,1907.
[24][日]竹内善朔著,曲直、李士苓译.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J].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5]周作人.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A].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二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6][德]李博著,赵倩、王草、葛平行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7]彭翼仲、彭谷孙主编.启蒙画报(第二册)[C].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28][日]井上清著,周锡卿译.日本妇女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责任编辑:含章
The Vision from Anarchist Communism inNatural Justiceand He Zhen's“Women's Liberation”
LIU Jen⁃p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Tsing Hua University,Hsinchu30013,Taiwan,China)
Ho Chin(He Zhen);women's revolution;women's liberation;evolutionary feminism;anarchist communism;Tien Yee(Tian Yi,Natural Justice)
Almost all the extant studies o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He Zhen(1886⁃ca.1920)point out that her anarcho⁃femi⁃nism is significantly distant from the progressive feminist scholars,both male and female,who were her contemporaries,as feminist thought of the time was centrally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modernity and its nationalist discourse.He Zhen's feminism,in contrast,was not contained by nationalism,racism,or the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agenda,but instead insisted that feminism work to⁃ward ending all forms of hierarchy in order to obtain real and complete social equality.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anarchist communism”must first be grasped before we can fully understand how He Zhen's women's revolution or women's liberation was not nationalism⁃centered.While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anarchist communism that He Zhen expoun⁃ded obviously exceeds the discursive frameworks of Western feminism,it is also distinct from Marxist communism,individualist anar⁃chism,and collectivist anarchism,all of which were also advanced in Tian Yi(Natural Justice),the journal He Zhen founded.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have to locate her feminism in relation to revolutionary projects,both within China and on a world scale,for which theory and movement were closely intertwined.These contexts are important for He Zhen's feminist thought because the revolutionary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was different from much of the feminism that followed.
D669.68
A
1004-2563(2017)02-0022-14
刘人鹏(1959-),女,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性/别研究、文化研究。
本文为台湾基金项目“《天义》与何震的‘女子解放’思想/运动”(计划编号:MOST 105-2410-H-007-066-MY2)的研究成果之一。
致谢:感谢匿名外审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本文部分初稿曾在2016年10月28-30日在北京举办的“女性/性别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衷心感谢杨联芬主办会议以及钱南秀的评论。会中得识久仰的夏晓虹、刘慧英以及新秀宋少鹏,她们精彩的相关研究是重要的奠基之作。晚近关于何震的研究,海外汉学界早期如Peter Zarrow、最近如Lydia H.Liu,Rebecca E.Karl,and Dorothy Ko等,都已经各自阐发了深刻的要义。2016年万仕国与刘禾的《天义·衡报》校注本,更是惠我良多。在剩义已无多的情况下,仍然着手写何震,也许自己补功课是动机之一。自十余年前从我的博士生陈慧文的研究中得知何震与《天义》,发现自己过去写晚清女权论述完全忽略了当时(广义的)社会主义,而在台湾20世纪90年代后的性/别运动争议的脉络中所见到的某些复杂议题,竟在阅读何震的论文中隐然发现若干呼应与资源,重新去认识一段曾经因冷战及分断历史条件而长久陌生的历史,格外充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