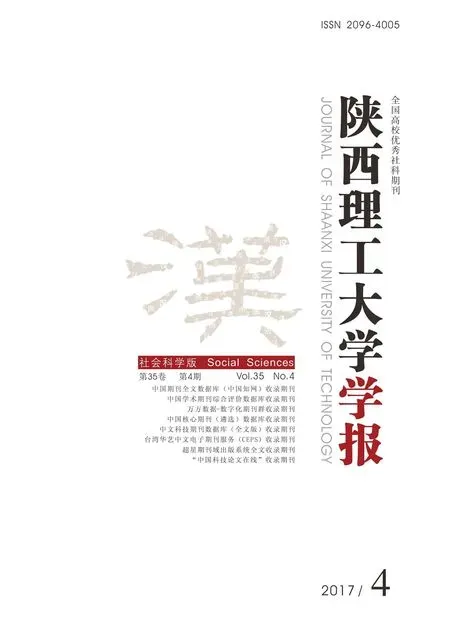乡镇女性领导干部从政状况的调查与反思
——以H市T区为例
柳楚佩, 刘 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乡镇女性领导干部从政状况的调查与反思
——以H市T区为例
柳楚佩, 刘 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乡镇女性领导干部的政治角色与性别属性之间的交叠互渗具有特殊性,体现为她们在直接参与基层治理的政治实践中因其女性身份展示出妥协、反抗和改变。通过对乡镇女领导职业、身体及家庭三方面经历的探究发现,虽然她们常处于政治上男权规训压力与女性性别自主诉求这二者的矛盾之中,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她们并不是顺从沿袭男尊女卑惯习的被动存在,她们积极发挥能动的主体意识,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的行动机会和空间;在自我性别认同方面在去性别化的同时也力求保持自身对女性美的追求与坚持;在家庭角色方面虽有内心的愧疚与失衡,同时也得到家人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她们具有多样的实践策略和自我认同,这既有利于提升民主政治的势能,也不断优化着两性之间的关系。
乡镇女性领导干部; 职业性别隔离; 性别秩序; 妻母角色; 主体
女性参政,即“女性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1]148,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它影响着政治势态的变动与女性社群的发展,从而引起学界的关注。从肇始于晚清变局的民族解放至社会主义革命唤起的阶级解放到改革开放后流行的人性解放,女性叙事始终紧扣着国家政治的脉络[2]17,而今亦然。简言之,中国女性参政议题独特地将“性别问题和民族国家的问题纠合在一起”[3]11的历史价值与“女性对政治的参与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发展”[4]311的现实价值相结合,奠定了研究女性领导干部群体的必要性。但回溯既有研究,其多从政治学视域出发,着眼于庞大的历史进程与社会整体,难免有突出大写的单数女性而忽视小写的复数女性、强调宏大叙事而淡漠日常生活之缺憾。此外,影响日盛的女性主义在认识论方面注重遭到忽视与压制的女性经验,并在方法论方面“强调多样性、地方性和情境性”[5]。
由于乡镇女性领导干部处在传统气息相对浓厚的基层社会,且作为女性群体中的另类职群,她们的特殊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探究乡镇女性领导干部在男性主导的政治生活中塑造了怎样的政治形象、体验到怎样的性别建构,她们是否面临更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而这些是如何影响着她们的身份认同和实践模式,进而是否再生或再造个体心智与整体社会的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因此我们选取了H市T区10位乡镇女性领导干部,于2016年3月期间开展调研,运用深度访谈与非参与观察的质性研究方法,记录下受访者对政治与性别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并厘析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以期拓宽深化对女性参政实践的理解。
一、 乡镇女性领导干部的政治参与:隔离与突破
宏观来说,当前我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发展虽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态势”,但“还没有完全走出低谷”[1]148,由职业性别隔离导致的政治参与结构不合理就是一个表现。职业性别隔离包含水平与垂直两个维度,体现在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与歧视,大多呈现出男优女劣的面貌,调查发现职业性别隔离亦存在于乡镇女性领导干部的工作现状中。
(一)乡镇女性领导干部政治参与的性别隔离状况
首先,水平的职业性别隔离即女领导更多分布在边缘部门而非核心部门。QL镇副镇长SC主要分管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和劳动保障事务所的工作,我们与其交流时,她指出:
“我们的职务分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看出些问题,比如乡镇女领导一般都要分管民政、社保,好像女领导不关心福利、不感性、不帮助别人是不正常的。”(H市T区QL镇SC,2016年3月24日)
其次,垂直的职业性别隔离即女性在政界多担任副职而非正职。在访谈中ZY镇副镇长DJ指出:
“每一个乡镇领导班子都配一个女性副职。女性领导作为副职加入,在一定程度可以缓和领导班子男性成员的紧张关系,女性的柔性力量是必要的。”(H市T区ZY镇DJ,2016年3月22日)
女领导“不感性”就“不正常”,“柔性力量”是“必要的”渗透着鲜明的性别刻板印象,以剥夺了照护给予者和接受者选择权的照护伦理定义女性特质,从而为男性权力占具主导地位的合理性及有效性正名。这实质上体现了性别歧视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效力,它导致带有性别偏好的政治等级秩序(体现在部门与职务的分设)的形成,并借女性身份的“自然”掩盖了这一区隔的社会建制。两性特质是依托男性与女性生理性别而形成的文化规范,作为简易的社会分工依据,它是男权制合法化的一种秩序,即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体制的重要符码。身为乡镇女领导干部的SC和DJ对职业性别分割所做的解释,体现出政治实践对女性特质的认识;其对乡镇女性领导的自我认同也产生了影响,使她们妥协于“乐意服从男性的统治”[6]67的“标准”女性构型,并通过心理定势与行为取向的循环而使所谓“天性”固着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换言之,乡镇女领导可能通过“合理”地认同自己的劣等处境而成为父权制国家性别特征的共谋,再生社会性别化的政治逻辑。
从结构角度来说,政治等级制存在于水平和垂直的职业性别隔离:核心部门的权势权重大于边缘部门,且正职的权力权威大于副职。当女性进入由男性定义、规范与主导的官僚体系时,以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为核心的性别等级制也随之启动,在资源配置方面制造出强者与弱者,巩固并传续着男性本位的国家权力及政治文化。带有男权意涵的政治性别化说明“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女性的政治行为仍然是对男性所建构的政治行为的复制而已”[7]。
(二)乡镇女性领导干部政治参与的突破
乡镇女性领导的自觉反省和自为行动引起两性气质在现实中不断变化发展。更具体地说,一方面乡镇女性领导干部因其性别的传统样态,既遭遇着女性的“弱”作为“领导”的“强”之间的对抗,又经历着这种“弱”与边缘部门、副职角色的“弱”之间的共生;另一方面她们也有其个体的自主性,挑战以男性权力为主导的性别政治体系,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的行动机会和空间。也就是说,虽然政治场域中男性统治力量强大,但是女性并不是顺从沿袭男尊女卑惯习的被动存在,她们也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发挥着能动的主体意识,调研中有两例访谈如下:
1.LL(LJ镇副镇长):其实在我看来,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是晋升也不是得到领导的表扬,而是切切实实为村民办几件好事。一个月前我在镇里举办了一次“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培训大课堂”,参加的人非常多,效果很好,我打算持续办这种大课堂。
问:是镇政府提议举办的吗?
答:不是,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给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汇报以后他们支持我做这件事。(H市T区LJ镇LL,2016年3月26日)
2.XY(XW镇副镇长):我刚进入乡镇工作时非常不适应,以前积累的工作方法也和乡镇工作完全不一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我就找到自己在医院当副院长的同学,来镇上给村民们做了一次义诊。
问:当时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的态度怎么样?
答:他们支持,镇政府可以提供场地和医护人员的午餐,就是需要我自己去联系。(H市T区XW镇XY,2016年3月27日)
乡镇女性领导通过主动地工作创新与寻求帮助,对突破政治参与中职业性别隔离具有积极意义。公民的参政权力是女性从政的前提,能力的发挥是女性能否积极参政的动因,权力和能力的正向互动有益于乡镇女领导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并逐渐改变突出性别差异的政治运行逻辑。同时,通过受访者向领导汇报和运用既有社会资本来参政的过程,反映出居于主流政治边缘地带的乡镇女性领导为“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往往需要付诸更多,才能够突破常规结构的限制。
二、 乡镇女性领导干部的主体意识:遵从与反叛
“一个主体不是一个实体,甚至也不是许多角色或位置的集合体,它更像是一系列行为、遭遇或存在方式”[8]12,“自我化”与“他者化”对“主体”的辩证意蕴在于,前者意味着女性自觉地塑造与呈现自我形象,后者则传达出一种异己的、他律的话语及实践。对乡镇女性领导干部而言,原本自我化的女性特质与自主地位在男性为中心的政治领域被他者化到边缘地位。因此她们不得不在相互博弈的价值间进行取舍并使之合理化,体现出“‘女人’代表着一种自异性”[2]286。
乡镇女领导的主体身份既有别于普遍的“女性”又有别于一般的“领导”,正是这样的独特性催发了她们的主体意识,书写出特有的生活历程。随着身心二分的认识受到质疑,身体所彰示的社会属性和象征意义受到了极大注目。对女性来说,她们的身体作为其“第二性”身份的外化与固化,“长期被男性操控、拥有,女性仅有身体的使用权,没有身体的所有权”[9]。我们平素所见的妆容、体态和服饰等等作为身体的呈现与表达,“不仅是社会区分男女性别的一个标准,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重要载体”[9]。那么不同于主流男性气质的乡镇女领导,在政治实践中是否面临、又如何应对实存身体与应然身体、公的身体与私的身体之间的冲突呢?访谈中,QL镇副镇长SC指出:
“乡镇女领导干部不能再爱美了,我一来这里工作就没有再化妆,更不会再穿高跟鞋,很少穿裙子。……女领导化妆可能不是那么严肃,没有威信的样子。这样不利于开展工作,比如我们这有征地拆迁项目,我需要和老百姓直接沟通协调,如果是一个外形时尚的年轻姑娘跟他们讲政策,他们未必会听进去,似乎有一种固定的乡镇领导形象在他们的脑子里,而我需要去符合他们心中的形象才能完成工作。(对此)我一开始也很憋屈,觉得自己爱美没有错。也许过分在意穿衣搭配是很肤浅的表现,可是这种被迫改变自己原先模样的感受是很无奈和无助的。”(H市T区QL镇SC,2016年3月24日)
“不能再爱美了”的“乡镇女领导干部”是由阳刚气质主导的政治世界对女性身体的规训,这种对女性领导干部去性别化、类男性化的实质是去弱势化、去边缘化。由于担当强势的领导职务,乡镇女领导干部需要尽力祛除那隐喻女性身份的形象元素(如“化妆”“穿高跟鞋”“穿裙子”),以朴素而干练、“严肃”且“威信”的男性化模样来“符合”男权式思维,向她们所根植的男性控制的政治体系做出顺应,这体现了男性气质“已经将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将自己当作一种主体和参照物”[6]55的本质。
身体的表达关联着主体的认同,SC对打扮是“很肤浅”的识读反映出,在她作为女性领导的身体被改造成政治化身体的过程中,其自我认同实现了“男权制思想体系的深层意识化”[6]64。从过往的“爱美”女性转化为男性化的“领导”(即使是无奈的或不全面的),一方面体现了对男女两性差异的狭隘理解;另一方面隐喻了女性领导干部作为被男权政治话语以“现代化”之名征询出的角色,社会性别意识在她们之中并不清晰。
但是,透过衣着表面的同(男性气)质化,将女性领导干部从被品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倾听她们作为主体的情感体验与行动策略是必要的。调查中,与SC体验到的“无奈和无助”不同,ZY镇副镇长DJ则在“痛苦”和“忍耐”中表现出了更多的反抗:
“我进入乡镇政府工作以来,每次去区政府开会,都会被人说同样的一句话,‘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乡镇政府领导。’我实在不明白乡镇政府女领导该是什么样子,非要把自己沦落到邋里邋遢、灰头土脸的样子才像乡镇女领导吗?……我实在疑惑我的外形和工作能力有什么关系,爱美有错吗?”
“(但是)我没有改变自己外在形象的想法。我的外表就是我内心的反映,别人的看法始终是别人的。我自认为工作能力很强,可以胜任日常的工作事务,可很多人总在评判我的外表,我感到痛苦却一直在忍耐。”(H市T区ZY镇DJ,2016年3月22日)
DJ的讲述反映了以身体为媒介而产生的对性别秩序的反思和抵抗,诉说着她悦己的表达、个性的彰显以及对自我性别的认同,得到释放的身体自主挑战着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摆布,呈现了她追求作为女性的主体建构,并践行着“避免为我论的身体变成为他论的身体”这一“身体政治的核心目标”[10]124。DJ对自我身体的认识建立在她将女性身体外形与工作能力关联在一起,即她自觉“工作能力很强”,并未从众而退让;但因外界规范的压力使她处于矛盾之中,其体验展示出女性身体反叛的可能和身体认同的意义。
综上所述,乡镇女性领导干部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始终遭遇着“性别外溢”,即对其工作角色的预期基于通行的性别规范。她们面临外界认为的应然与自己本意的应然之间的冲突,体现出男权占主导地位的性别体系;但乡镇女性领导干部在其间的挣扎、质疑与变化也表现出她们的主体意识和自觉行动。这辩证地说明了“现代社会改变了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但并没有将它消除”的事实[11]23,体现出政治实践和性别实践中的不变与变。也就是说,社会在认可、支持新现象的同时又肯定了传统差异和既有区隔,呈现出复杂且辩证的局面。
三、 乡镇女性领导干部的家庭角色:失衡与转型
中国传统社会中,性别的“内”、“外”分工不仅将家庭内部的所有责任交给了女性,侍奉双亲,养育子女,抚养丈夫的弟妹等,还将父系家族中的女性功能降低为生育能力。女性以作为“母亲”或“妻子”的身份来获得社会地位,在层级亲属制的宗族家庭内部,“母亲”身份是女性“母权”得以保障的基础。现代社会,女性进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但从家庭角度出发得到确立与称颂的“贤妻良母”形象仍具有结构规范的效力,被很多人视为女性的价值实现。产生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造就了多样态的妻母经验,以QL镇副镇长SC为例:
SC(QL镇副镇长):我结婚以后和丈夫一直与我的父母居住,丈夫也在乡镇工作,我们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只有周末。平常根本没时间去了解她的喜怒哀乐和学校生活,每晚回到家已经是筋疲力尽。我的父母也很辛苦,把我培养长大,现在还要培养我的孩子,我真是非常内疚。
问:丈夫支持你工作吗?
答:很支持。他很能理解我,因为他也是乡镇领导,在另外一个镇上。他能体会乡镇工作的不易,所以我顾不上家,他会帮我分担,不会苛责我,工作上遇到问题,我们也会相互交流。
问:目前这样的状况,孩子的教育方式应该改变了吧?
答:是的。我现在更注重用行动影响她,而不是用指挥或者命令。我想既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观察她,那索性回家以后做一个自己认为好的母亲形象,比如,对她外公外婆的关心、问候,和她爸爸的平等交流、沟通,还有增加阅读量等等。(H市T区QL镇SC,2016年3月24日)
由于乡镇女性领导干部进入公共空间,与男性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女性无法再承担传统亲职,无法将自己的社会技能定位在家庭领域,与此同时,女性在公共空间获得的社会技能导致其在家庭关系中的变化,由依附男性而获取社会地位转变为依靠自己具备的社会技能获得社会地位。对于乡镇女性领导干部来说,她们在将自己的工作与家庭平衡之后拥有独立人格,因此其母职已不再局限于在家庭领域对子女物质方面的供给,而是要求她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认可,“女人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或某种意识与非意识的层次上具备这样的能力及自我感,才能够表现出来所谓的母性”[13]23。
SC对家人的愧疚感源于传统女性家庭角色的愿望和现代的工作-家庭状况之间的冲突,反映出乡镇女性领导干部的独特境遇在于,一方面男性视事业为唯一合理的追求并不受此类冲突的困扰,另一方面女性领导干部与普通女性相比更难满足家庭需要。在对家庭提供的公共服务网络缺位的情形下,母职转型和夫妻平等作为来自家庭的理解与支持无疑对SC这样的乡镇女性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涯具有积极作用,SC也通过有意识的调试而得以避免“内”与“外”、“新”与“旧”之间的角色失衡。这种现实的变化还反映出性别秩序的改观,即平等家庭的出现为其从政现状带来了积极影响,传统家庭中的大男子主义已逐渐不再是制约女性进入政治领域担任领导的障碍。
四、 结语
受访乡镇女性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因职业改变看法而做出的妥协,对身体坚持自我生成的反抗,在家内相互合作而带来的改变,这些紧张的角力虽由政治与性别的逻辑引起,但因主体意识的增强动态地影响着具象的个体和潜藏的结构。由此,乡镇女性领导干部的生存样态反映着“保守的进步”,即她们虽在性别体系中仍出于屈从地位,但其角色丰富且地位上升。一方面,男性特权在假托自然之名、通过制度奖惩等束缚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另一方面,自主空间的扩大无疑有利于女性改变传统规约以实现作为主体的诉求。对这不完善的发展与进行中的变化来说,她们在或强或弱的职业角色、亦公亦私的身体呈现与可新可旧的家庭模式等张力之间能抵达多少政治文明与女性解放的潜能,主要取决于“主体”与男权制间的博弈。
乡镇女性领导干部在性别与政治中既获得机会也受到干预,这些经验型塑着她们的身份认同,并作用于既有的社会结构。透过这副对乡镇女性领导职业、身体和家庭的尚不全面的深描,就政治过程与性别实践的认识无疑还有待更多的观察和思索,从而让更多的女性领导出现与可见,并推进“不再要求个人符合金字塔形的等级制,而是平等的伙伴关系”[14]283,这既有利于提升民主政治的势能,也优化着两性之间的关系。
[1]师凤莲.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2]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季家珍.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M].杨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叶文振.女性学导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5]吴小英.女性主义的知识范式[J].国外社会科学,2005(3):34-43.
[6]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7]王瑞芹.妇女参政行为与政治行为文明[J].妇女研究论丛,2005(4):5-9.
[8]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M].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9]艾尤.日常生活·身体叙事·性别政治——台湾女性小说“食、衣、色”书写透视[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3-99.
[10]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2005.
[11]程为坤.劳作的女人[M].杨可,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
[12]方刚.康奈尔和她的社会性别理论评述[J].妇女研究论丛,2008(2):10-14.
[13]Nancy J.Chodorow.母职的再生产[M].张君玫,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03.
[14]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M].程志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15]李木兰.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M].方小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刘 英]
D669.68; C913.68
A
2096-4005(2017)04-0073-05
2017-05-22
2017-09-18
柳楚佩(1989-),女,陕西南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刘洁(1991-),女,山西太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性别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