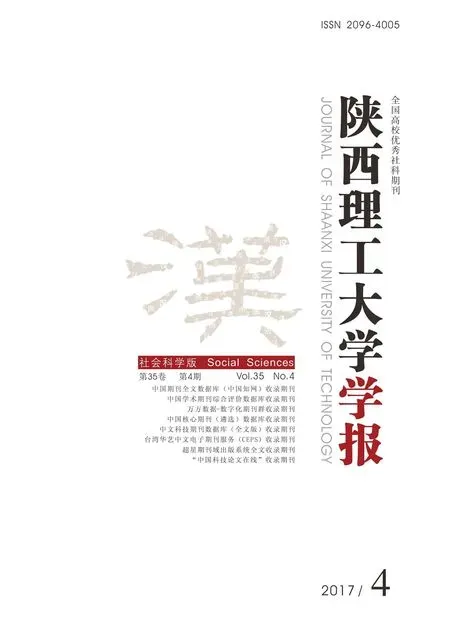从多维视角看《诗经》植物的药用价值及文学功能
刘 昌 安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从多维视角看《诗经》植物的药用价值及文学功能
刘 昌 安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诗经》植物是“诗经学”的重要内容,从孔子提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到陆玑对《诗经》名物的疏证,历代《诗经》植物研究成果丰厚。《诗经》中的芣苢、蝱、谖草等植物具有较好的药用价值,为古今中医药学者所重视。《诗经》中的植物具有文学的情感,反映了远古人们对植物的崇拜,而植物也被赋予了人们念亲思乡的情感。《诗经》除了有实用的功能外,还具有文学人类学的宣泄功能、调节功能和升华功能。
《诗经》; 植物; 药用价值; 文学功能
《诗经》是一部文学经典,其价值表现在诸多方面。作为《诗经》重要内容的植物研究,虽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其植物的药用价值研究还显不够。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诗经》植物的药用价值,并兼论《诗经》具有的文学人类学功能,以求教于方家。
一、 由孔子论《诗》引发的思考
最早对《诗经》植物关注的是孔子。孔子论诗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指出了《诗经》的重要价值,为后世开启了《诗经》名物研究的新思路。清人刘宝楠解释说:“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尔雅》于鸟兽草木,皆专篇释之,而《神农本草》,亦详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矣。”[1]689-690刘宝楠从“博物之学”的角度,认为《诗经》草木虫鱼鸟兽具有“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的价值,有别于汉儒以来对草木虫鱼的认识,对孔子观点进行了较深入的发挥,这是很难得的。而且引《尔雅》与《神农本草经》作旁证,暗示了《诗经》在博物学和药物学方面的价值,更值得深思。这里,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诗经》一书中大量使用草木虫鱼,只是一种创作的手法吗?笔者以为并不尽然。《诗经》里大量的使用草木虫鱼鸟兽,除了有后代学者总结的“比兴”手法之外,更是古代人们生活的经验体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功能。
在远古时代,先民在采集食物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态和性能,了解到植物不仅美味可口,有的还能够疗病。这样,人类就逐步积累起了对药用植物的认识。“虽然药用植物在出土文物中有所发现,比如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南渑池班村遗址的裴李岗文化层发现了大量具有治疗和健体功能的山茱萸、紫苏、黄芪等果实,但现在很难考证其在当时是否已作药用。现在文献所载传说大都将药物发现归功于神农氏。”[2]19-20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神农尝百草”行医治病的传说记载,实际上就是对人们认识药用植物的实践过程的反映。许多文献资料将“神农尝百草”作为中国医药的起始。形成于东汉时期,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类共365种,其中植物药有252种,而动物药仅67种,矿物药46种,这足以说明植物药的优势。因此,我们在读到《山海经》《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作品的时候,深感植物的作用和人们对植物的认识。
三国时吴国陆玑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以下简称《陆疏》),是第一本专门解释《诗经》中涉及动植物的书,记载了动植物的名称、外形、生态和使用价值,对后世影响很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迢远,传疑弥甚。玑去古未远,所言犹不甚失真。《诗》正义全用其说。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其驳正诸家,亦多以玑说为据。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3]5自此以后,《诗经》动植物的研究层出不穷,都试图解析动植物的名称及其含义。如宋元时有蔡卞《毛诗名物解》、王应麟《诗草木鸟兽虫鱼广疏》、徐谦《诗集传名物钞》等,明代有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毛晋《毛诗陆疏广要》等,清代有王夫之《诗经稗疏》、陈大章《诗经名物集览》、顾栋高《毛诗类释》、姚炳《诗识名解》、多隆阿《毛诗多识》等,主要注解《毛诗》和辩证《陆疏》。另外,还有一种图说《诗经》的方式,如南北朝时梁代《毛诗图》、唐代《毛诗草木虫鱼图》、宋代马和之《毛诗图》,均已失传。[4]328现存的是清代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有图有说、辨象知物,惜略有残缺;日本学者冈元凤《毛诗品物图考》,也深有影响。在当代,台湾学者潘富俊《诗经植物图鉴》,胡淼《lt;诗经gt;的科学解读》等也很好地继承了这种传统,对《诗经》研究有较大的影响。
二、 《诗经》中的药用植物
古人常将植物分为草、木、谷、菜、果五个大类,尽管不够科学,但反映了古代的生活实际和民众的生活习惯。由于时间跨度太长,其中许多物种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有些可能改换了名称,有些名称可能存在地域上或方言上的差异,有些还存在官名和俗称的不同。
近代著名学者胡朴安在《诗经学》中说,“《诗经》一切之学,包括文字、文章、史地、礼教、博物而浑同之,必使各各独立,然后一类之学术,自成一类之系统。”“知《诗经》中之草木鸟兽虫鱼,皆由实践而得者,此《诗经》所以可为博物学之祖也。计全《诗经》中,言草者一百零五,言木者七十五,言鸟者三十九,言兽者六十七,言虫者二十九,言鱼者二十,其他言器用者三百余。”[5]112-228农学家胡淼说:“据粗略统计,全书(《诗经》)305篇诗中,有141篇492次提到动物,144篇505次提到植物,89篇235次提到自然现象。”[6]1这些统计虽不一致,但反映了《诗经》植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表明了《诗经》时代人们对植物的认识和运用,即就是从今天的科学角度来看,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根据笔者的统计,在《诗经》305篇作品中,有151篇记载了植物的名称146种,其中草本植物91种,木本植物55种,不包括一些泛指性的如粱、粟、稻、稗等谷类的植物。因诗中的植物时代久远,变化较大,在今天的学科归类上,学者们尚有不同看法,故植物的中文学名和科目未列。
在《诗经》植物中,有多少可以作为药用呢?有的学者认为《诗经》“记载药物200种,其中植物药132种”[7]。台湾学者潘富俊认为有八九种,[8]10还有人统计大概有50多种,[9]38-39这主要是草本植物。清代学者顾栋高在《诗经类释》归纳《诗经》植物157类,其中草37种,木43种,谷24种,蔬菜38种,花果15种,并明确标明有17种药用植物,具体是:芣苢、唐、苞杞、芄蘭、艾、蝱、苓、蓷、葽、藚、舜、蕳、芍药、茑、女萝、白茅、白华。[10]124-130除此之外,《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等相关的著作也对《诗经》植物引用、解释,指出其医学的价值。
还有的研究者从植物的名称角度,认为“《诗经》植物药用名称未变的有4个:葛、芍药、枣、卷耳。药用名称发生改变的有33个:杞、荇菜、椒、茑、茆、柽、藻、茨、莱、蕳、菀、蓫、薇、蓷、藚、蔚、瓠、果臝、茹蘆、台、葑、女萝、苕、芣苢、莪、葽、莜、竹、朴楸、蝱、菅茅、荷、舜等。药用名称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产生了很多异名,其命名的方式有根据产地命名、根据颜色命名、根据药材形状命名、根据药物功效命名、根据药用部位命名等5种方式”。[11]在《诗经与中医》一书里涉及篇名123篇,涉及百余种药用植物,[12]在《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医药文化》一书里,作者从诗歌欣赏的角度,分析了19篇作品中涉及的24种植物的药物作用。[13]我们通过选择几种常见的《诗经》药用植物的探讨,可以了解《诗经》药用植物的价值意义。
比如《周南·芣苢》中描写的“芣苢”,从《毛传》《说文》《尔雅》,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李时珍《本草纲目》等都认为“芣苢”的功效为“养肺强阴益精,令人有子,明目疗赤痛”;还能“治妇人难产”。[14]1069清人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中也有类似的观点。[15]444
古代人对“芣苢”的认识主要为,一是芣苢据其生长的特性,有多种名称:车前、马舄,当道、牛遗、地衣等,是一种草,而不是木,二是这种草本,生殖繁盛,生长广泛,叶嫩可食,三是芣苢有医药功效,治难产,通利等,四是有特殊的观念意义,即宜怀妊,宜子孙。由于受科学与认识的局限,古人对此植物的解释也不十分准确。但从今天生物学的角度看,芣苢属车前科车前木的被子植物,有其显著的医药功效。[16]180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古人对芣苢具有的使妇人怀妊、助孕顺产等观念意义,实际上有着人类学的观念背景。闻一多先生在其《匡在尺牍》中有精辟的论述,值得思考。[17]35-65
再如《鄘风·载驰》“言采其蝱”,《毛传》“蝱,贝母也。采其蝱者,将以疗疾。”朱熹《诗集传》云:“既不适卫而思终不止也。故其在途或升高以舒忧想之情,或采蝱以疗郁结之病。”[18]34王安石也说“陟偏高之丘,以采蝱故也,采蝱者,将以除结懑之疾。”[19]50后世解诗者大都以许穆夫人哀吊娘家卫国而不得,忧思愁病,内心郁结,登丘采蝱以解忧。在传统中医观念中,人心理上的郁结不快与病理上的气血不通是一回事,气血归辙了,郁结也云开雾散。故古人用“贝母”治疗人胸臆及气血的郁堵。贝母作为古代重要的药材,本草医学书中认为贝母鳞茎入药,有润肺散结、止咳化痰作用,治吐痰咯血、心胸郁结等症。其药用,主要在疏理人的气血,使血络通畅,流而不滞,气脉循行,贯而不塞。
再如《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诗中的“谖草”,《毛传》认为“谖草令人善忘,背北堂也。”《郑笺》:“忧以生疾,恐将危身,欲忘之。”[20]244谖草,又名藼草、萱草、忘忧草等,为百合科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全草和根可入药,嫩苗有利湿热、宽胸、消食的功用。可治胸膈烦热、黄疸、小便赤涩等症。古人认为谖草有一个功用:使人忘忧,所以又叫忘忧草。梁任昉《述异记》卷下:“萱草,一名紫萱,又呼为忘忧草,吴中书生呼为疗愁花。嵇中散《养生论》云:‘萱草忘忧’。”[21]23张华《博物志》引《神农经》说:“上药养命,谓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22]22从古医典籍中可以得知,萱草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很强的解毒药性。据《事林广记》载,服食丹药的人,若日久中毒,以“萱草根研汁服之”,[23]471可以解毒。古医人的经验,鹿在兽中,性为灵警,能辨识解毒的药草而食之。在鹿辨识的九种解毒药中,萱草即其一,故萱草又名鹿葱。《本草纲目》卷十六李时珍说:“鹿食九种解毒之草,萱乃其一,故萱草又名鹿葱。”[14]1036二是萱草有轻微的麻醉性。李时珍《本草纲目》引李九华《延寿书》说,萱草的“嫩苗为疏,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14]1036大概正是这两个特点,古巫医看重萱草,认定它有使人“醉忘”疾苦或者使郁痛缓解的功效。
认为某种植物可以疗治、化解人的忧思悲愤情绪,这是古巫医的恒守观念,民间也有。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有忘忧草:“人有思哀也弗忘。取丘下之莠,完掇其叶二七,东北乡(向)如(茹)之,乃卧,则止矣。”“人毋(无)故而心悲也。以桂长尺有尊(寸)而中折,以望之日曰始出而食之,已乃商(餔),则止矣。”[24]129-130意思是人若陷入哀思悲惋不能自拔,可以采“莠”叶或桂枝条吞食,食后或睡上一觉,醒来即忧情全无,悲思顿释,达到了解忧的效果。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植物与人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产生的一种“巫术感发”,正是原始思维中出现的“互渗律”。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说:“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差不多以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以动力说的观点看来,存在物和现象的出现,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生,也是在一定的神秘性质的条件下由一个存在物或客体传给另一个的神秘作用的结果。”[25]69-70萱草忘忧的神奇作用,正是这种植物的疗效由物质向精神的转化过程。
再如《唐风·椒聊》“椒聊之实。”《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荍,贻我握椒。”《周颂·载芟》“有椒其馨,胡考之宁。”这几处都写到了“椒”,现在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诗中的“椒”应是花椒,为芸香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古人对花椒,又名檓、大椒、秦椒、蜀椒、汗椒、点椒等,叶和果都有芳香。古时女子将花椒制作后,为佩饰或居室里的香料,也因花椒果实繁多,多为赠礼,以喻子孙繁衍生息。《毛传》曰:“椒,芬香也。”《孔疏》:“椒之实芬香,故以相遗也。”
花椒的药用功能,主要有温中散寒、除湿止痛等功效。治积食、心腹冷痛、呕吐、泄泻、痢疾、疝痛、牙痛、蛔虫病、蛲虫病、阴痒、疮疥等症,出邪壮阳。还有通血脉、坚齿发、明目、美颜、轻身增年的功效。《本草纲目》据前人的观点,因产地不同,分秦椒和蜀椒,但其药性基本相同。书中引吴猛真人服椒诀云:“椒,禀五行之气而生,叶青、皮红、花黄、膜白、子黑。其气馨香,其性下行,能使火热下达,不致上熏,芳草之中,功皆不及。”特别是介绍了用椒制作的“椒红丸”,有补肾和治脾胃虚寒的作用:“服此百日,觉身轻少睡,足有力,是其效也。服及三年,心智爽悟,目明倍常,面色红悦,髭发光黑。”[14]1852-1853花椒的药用功能可见一斑。另外,古俗中还有在元日饮椒柏酒,有辟邪健身之功效。[26]7
再看《王凤·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里写到的“葛”“萧”“艾”,也是重要的药用植物。《毛传》是这样解释的:“葛,所以为絺綌也(即细葛布和粗葛布)。”“萧,所以共祭祀。”“艾,所以疗疾。”[20]267指出了三种植物分别有制器制衣、祭祀、疗病的作用,但没有指出“葛”、“萧”的药用价值。
我们知道,葛为豆科多年生藤本植物,是古人重要的生活资料,用作编织器具、织衣,以及葛根淀粉的食用。葛的药用价值主要在葛花、葛根、葛藤。中医认为,葛花性味甘、辛、凉,入脾、胃经,有和胃解酒,生津止渴之功。适用于饮酒过度,头痛,头晕,烦渴,胸膈饱胀,不思饮食,呕吐酸水等。葛花解酒的药理机制是葛花中皂角苷、异黄酮等有用成分发挥作用,改善了酒精导致的新陈代谢异常。葛根性味甘、辛、凉,入脾、胃经,有发汗解肌,解表透疹,升阳止泄,生津止渴之功。本品解肌发汗,善治外感风热,头痛强项等,且能升清阳,鼓舞脾胃清阳之气上升而能奏止泄之效。葛根含有葛根素、葛雌素、葛根素、木糖甙、大豆黄酮、氨基酸等,既可作药用,也可入食。葛藤性味甘、寒,入肺经。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之功。适用于喉痹,疮痈癤肿等。
萧,又称野艾蒿,又名荻,荻蒿、牛尾草,野艾、小叶艾、五月艾、荫地蒿等,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有时为半灌木状。全株有香气,茎生成丛,分枝多,茎枝被灰白色短柔毛。叶正面绿色,背面有灰白色密绵毛。基生叶及茎下部叶宽卵形或近圆形,多为二回羽状全裂;中部叶卵形、长圆形,在分枝上半部排成密穗状或复穗状花序,在全株组成较紧密的圆锥状花序。多生于路旁、林缘、山坡、草地、山谷、灌丛及河滨草地等。嫩苗作为蔬菜或腌制酱菜,古人亦供祭祀。萧用作药,是艾的代用品。
艾,又名艾蒿、冰台、白蒿、医草、炙草、海艾、白艾、黄草、家艾、甜艾、草蓬、艾蓬、大艾、狼尾蒿子、香艾、野莲头等。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香气浓郁。古时艾也用作祭祀时用,民间自古也有在室内悬挂艾草以避邪除病的习俗,或制成艾绳,点燃以驱蚊毒蛇。艾草的叶和种子供药用,可治心腹冷痛、泄泻、久痢、吐血、下血、月经不调、崩漏、胎动不安、慢性肝炎、慢性气管炎、寻常疣等症。
传统中医药认为,艾一是可以用于妇科疾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已有详细的引证,此不赘述。[14]938-939清初徐忠可在《金匮要略论注》卷二十也作了较好的说明。[27]299有意思的是,北美民间巫术也用艾草治妇科病。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在北美就象在古代世界一样,艾属植物有女性、月亮、黑夜等含义,主要用于治疗痛经和难产。”在这段话的注文里,他引用别人的研究后说“艾属植物在古代墨西哥似乎也有女性的含义,因为妇女在月亮节时佩饰着艾草跳舞,向灰克斯托休特尔(Huixtociuatl)女神致敬。”[28]64二是可以艾灸疗法。研究者发现,在殷商时期,人们已知道用艾灸疗病。甲骨文中已记载有艾灸治病的事例。[29]336后来主要是治由厉鬼、妖狐造成的病症,而且有浓厚的巫术意味,采艾的时间、地点、采艾之法等有许多讲究,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引用了很多资料来加以说明。
三、 《诗经》植物的文学情感
对《诗经》研究,学者们多关注其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探讨其艺术的表现力和泽被后世的影响力。其实,如果换一个视角,从植物学的维度来审视《诗经》时,会有别样的风景:草木缘情,在草木的世界里有文学的情感。
从植物与人的关系来看,上古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植物,植物对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人栖身于自然中,追随植被而迁徙,植物生长的状况直接影响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界万物中唯有植物可以按照四季更替,依照冬去春来、花开花落进行生命的无限轮回。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样看来植物的生命力更强大,更有延续性。因此,植物生命能够无限延续,永葆青春,年年硕果累累,不仅得到了造物主的恩赐,更得到了大自然的眷顾。人们便愿意相信植物就是值得敬仰的神的形象。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说:“在原始人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也不例外。它们跟人们一样都有灵魂,从而也像对人一样地对待它们。”[30]169随着人类适应和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植物与人类衣、食、住、行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发现粗纤维植物可以制成麻布抵挡风寒,植物除了可以食用之外,还可以喂养牲畜,还能疗疾,还能做染料,还能当祭物,还能当用具,还能做饰物,在男女情爱中还可以作为礼物,人们敬畏自然,自然抚慰人们,表明了植物与人相互依赖、共融共存的密切关系。
从植物与文学的关系来看,由于植物实用性的功能,强化了人们对植物的热爱,很自然的将熟知的植物形象作为创作原型展现在诗歌中,使诗歌具有了文学的情感。
在《诗经》中,有不少具有药物性质的植物引入诗歌,这些“药草”绝大多数是通过“采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些“采摘”的植物,都赋予了对亲人的思念或对故乡的怀念。在他们看来,看似单纯的“采摘”行为,实际上是要将自己的思念传达出去,能让思念的对象有同样的感受。这正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的“交感巫术”的某种形态。[25]350,450,33,292,34
《小雅·采绿》中的“终朝采绿,不盈一匊,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就是一个服役未归的征夫之妻的怨思之作,她通过采绿采蓝将自己的相思之苦传给逾期不返的丈夫,希望丈夫能如愿回到自己的身边。《小雅·采薇》中反复吟唱“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俨狁之故”这样的诗句,抒发久役在外的戍边士兵日夜盼望归乡的心情。《卫风·伯兮》中的“焉得谖草,言树之背”的忘忧草,可以使她减少心中的痛苦,把自己的思念传达给远方的丈夫。《鄘风·载驰》中“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写许穆夫人回卫国吊唁受阻而采“蝱”,以表达自己心中的思乡之愁。再如《卷耳》,同样是诗人传递情感,寄托情思的途径。这些诗歌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吟咏,有深厚的情感,说明植物在文学表达中所具有的特殊内涵。诗人常常借植物的某些形态、某些特性,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使植物也具有了人的心灵情怀,这也正是《诗经》的永恒魅力所在。
四、 《诗经》的文学治疗功能
植物是人类的绿色卫兵,也是人类疾病的克星,丰富的植物资源是一座天然的药物宝库。在我国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药物学的成就非常突出,用草药治病令世人叹服。《诗经》描写的许多植物,有的既能食用,又能祛病除疾,诗中描写甚多,不胜枚举。我们在前面选择了芣苢、蝱、谖草、椒、葛、萧、艾等几种常见的药用植物作了分析,说明《诗经》植物的药用价值历史悠久。当然,仅仅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待《诗经》植物的药用价值,未免视野不够开阔,认识不够深刻。假如我们从更宏阔的视野去审视《诗经》,从精神情感方面去认识《诗经》,从文学的阅读中领悟健康的价值意义,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
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看,文学除了传统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外,还具有治疗功能。因为现代社会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过度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家庭婚姻的不稳定,人的压力繁重等多方面的因素,使现代社会越来越失衡,这给文学治疗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文学治疗的基本原理,学者们多有论及。[31]从文学的性质与形态上来看,文学治疗的功能基本体现在宣泄、调节与升华三个层面。
文学的宣泄功能是由文学的现实层面决定的。创作者通过现实生活的素材,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具有文学的政治作用和道德力量,这些方面,在以往的文学分析与鉴赏中被突出强调,甚至到了绝对化、排他性的地步。但是,却往往忽视了文学的宣泄功能,也就是文学作品使创作主体(作者)与欣赏主体(读者)都具有了文学治疗的意义。因为现实中的人受到制度规范和文化约束的时候,内在的欲望会受到压抑,如果这种压抑长期存在,就会给人身心带来疾病。那么,消除这种心理疾病,文学是重要的手段。文学不但使个体的情感思维得以宣泄表露,同时也可以使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生活体验、思想意念、坎坷遭遇得以表达出来。《诗经》正是这样的作品。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32]2735人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很多挫折和痛苦,这种挫折和痛苦要找到宣泄的通道,以抒发其精神的悲苦,文学是其重要的渠道。在《诗经》中,有对黑暗社会的抨击: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小雅·正月》)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小雅·十月之交》)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大雅·民劳》)
有征战的悲哀: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豳风·东山》)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
有失恋的忧伤: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汉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风·子衿》)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邶风·柏舟》)
有被弃的怨愤: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卫风·氓》)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邶风·谷风》)
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小雅·谷风》)
我们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不仅能体会到《诗经》的创作者情感的发泄,而且对阅读者同样有极大的影响。阅读者可以借助于这样的情感表达,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与个人生活的情状进行同样的宣泄,这正是文学治疗功能的表现,文学消解了个人内在欲求与社会礼仪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恢复了人的心里平衡。
文学的调节功能是由文学的情感层面决定的。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创作主体与文本,有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关系。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再现与反映,必然会在创作者和阅读者的情感上有所折射,产生精神情感的共鸣。当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不公平,理想不能实现时,往往会导致精神世界的扭曲、失常,甚至会带来情感的伤害,文学在此能发挥调节的作用。对作品的创作者而言,疏导心胸,开阔视野,通过“移情”,将自己的情感在创作中得以排遣、释放,缓解内心的压抑,忘却自己的烦恼和悲伤,使自己的精神情感寄托在作品之中;对阅读者而言,当阅读到好的文学作品,能消解内心的苦闷,激发积极进取的信心,使自己内心得以放松和平衡。因为,文学的力量正在于情感的冲击力。我们看《诗经》里那些写感时伤逝,怀人思乡的作品,很能体现文学情感的调节作用。
《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毛诗序》认为是“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20]252从诗的内容看,东周大夫行役到周宗庙,看到宗庙的荒芜衰败,无限感慨,写出了这首诗以表达悲悯之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很能表现抒情主人公内心的痛苦与忧思。但阅读者在吟诵和引用的过程中,常常以此来表达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心境,诗的强烈情感转换为平和舒缓的倾诉,文学的调节功能在这里得以显现。《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全诗三章,复沓叠咏,除变换几个字外,句式一样,内容相同。诗中说,布网捕兔,反得了个小鸡。小时候生活还平静安乐,现在却遇上了多事之秋。想不清为什么,又无法逃避,还不如蒙头大睡,什么也不想说了。后世的解诗者认为是贵族的厌世之诗,但无实据。仔细玩味此诗,不难发现,诗中表达的情感除了有对昔日快乐生活的怀念,对眼前遭遇的失望外,重点还是试图摆脱精神的苦闷。“尚寐无吪”“尚寐无觉”“尚寐无聪”,三章中的最后一句,反复抒发着这种情感。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所谓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33]197这正是以文学的形式来调节人的伤痛情绪的最佳方式。清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黄氏日钞》云:“人寤则忧,人寐则不知,故欲无吪、无觉、无聪,付理乱于不知耳。”[34]326忘却生活中的“百罹”“百忧”“百凶”,以“不知”来疏导、转移、排遣、消解个人内心的困苦、忧愁与痛苦,使人在精神上获得安慰与解脱。
文学的升华功能是由文学的审美层面决定的。所谓升华功能,就是把个人的欲望提升为审美意识,从而获得精神的解放。个人欲望不但可以被文学的原始意象泄导,也可以升华为自我实现的冲动,这就是审美的要求。文学满足了人的自我实现需求,把个人欲望升华为审美意识,从而消除了无意识与意识的对立,使人的精神获得解放。在审美意识状态下,欲望被净化,心灵得以美化,心里压抑被充分消除,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主体。《诗经》里也有这样的作品。《诗经·小雅·无将大车》:
无将大车,祇自尘兮。无思百忧,祇自疧兮。
无将大车,维尘冥冥。无思百忧,不出于颎。
无将大车,维尘雝兮。无思百忧,祇自重兮。
诗很短,共三章,每章只变化几个字。从字面看,意思也很清楚。不要去推扶那大车,推着它只会蒙上一身灰尘。不要去寻思种种烦恼,想着它只会惹来百病缠身。不要去推扶那大车,推着它会扬起灰尘天昏地冥。不要去寻思种种忧愁,想着它便会使你心忧耿耿。不要去推扶那大车,推着它尘埃滚滚蔽日遮天。不要去寻思种种悲伤,想着它就会使你心事沉重增加负担。
汉代以来,对此诗有不同的解读,《毛诗序》谓“大夫悔将小人”,《郑笺》则解释说:“幽王之时,小人众多”。[20]798把诗的内容与“小人”联系,并将诗的时代定在周幽王时代,并无实据。朱熹《诗集传》又认为“此亦行役劳苦而忧思者之作”,[18]151将诗作者确定为“行役者”,似与诗意不合。清人姚际恒在《诗经通论》里说“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无聊之至也”。[35]226方玉润《诗经原始》谓“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无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无聊时也”。[33]426姚、方两人的理解,指出了诗人感时伤乱而产生的忧思,有一定的道理。但诗中为什么反复咏叹“无思百忧”呢?“百忧”究竟是指什么?
通观此诗,每章的前两句是起兴,后两句才是要表达的内容。仔细体味诗的内涵和情感,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解读这首诗。从诗的表层来看,诗歌的内容似乎与从政相关。歌者似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劝告人们绝思去忧。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是富有深意的,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可以理解。
从诗的深层来看,诗歌要表达的情感,关键是弃“大车”,弗“尘”埃,去“百忧”。诗中“车”的意象,有象征的意味,推扶“大车”,似有实现理想的举措。但诗里却表达了不要去推扶“大车”,是因为推“车”是要蒙“尘”的。“尘”埃遮蔽了人的视野,就是阻隔了人的欲望的满足。面对如此境况,人该怎么办呢?诗中的回答是:“无思百忧”。“百忧”在这里实际上就是人的欲望。如果不消除“百忧”,人就会忧愁难释,以至于患病。诗中这种对人的欲望与理想的倾诉,以及遭受的精神桎梏,是何等的深重。诗歌从精神层面的表述,可能比从现实层面的直白更具有启迪的价值。从文学治疗的功能去看待,诗人自己的理想愿望,也就是个人的欲望,在现实遭受了种种的挫折,无法实现,内心有很深的痛楚,因而要消解这痛楚,不是怨天尤人,不是愤世嫉俗,更不是去与社会对抗,而是把这愿望上升为“无思”的境界。“无思”不是压制思绪,而是要让“思”不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和升华,人的主体才能真正的自由。
综上所论,《诗经》这部文化经典,不仅以其丰富的植物文化给予先民实用的价值,而且,《诗经》中的许多作品,更具有文学人类学的意义,对人的欲望净化,心灵美化,精神升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当代文化建设和精神引领,也有裨益。
[1]刘宝楠.论语正义[M].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2]王明强,张稚鲲,高雨.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万有文库本: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4]夏传才,董治安.诗经要籍提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5]雪克.胡朴安学术论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6]胡淼.《诗经》的科学解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彭书典.本草学史和古代植物分类学史的分期及主要著作[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3(3).
[8]潘富俊.诗经植物图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9]温长路.《诗经》中的药物与治疗思想[J].江苏中医,1991(7).
[10]顾栋高.诗经类释[M]//纪昀,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八十八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张媛.《诗经》植物药用名称研究[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12.
[12]胡献国,黄冬梅.诗经与中医[M].武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13]炎继明.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医药文化:一[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14]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15]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6]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四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17]闻一多.诗经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
[18]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9]王安石.诗义钩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0]孔颖达.毛诗正义[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1]任昉.述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2]张华.博物志:外七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3]陈元靓.事林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24]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0.
[25]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6]宗懔.荆楚岁时记[M].宋金龙,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27]徐忠可.金匮要略论注[M].邓明仲,等,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28]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9]温少峰.殷墟卜辞研究[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30]詹·乔·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31]叶舒宪.文学与治疗[J].中国比较文学,1998(2).
[32]司马迁.报任安书[M]∥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33]方玉润.诗经原始[M].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3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吴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35]姚际恒.诗经通论[M].顾颉刚,标点.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王建科 责任校对:王建科 陈 曦]
I206.2
A
2096-4005(2017)04-0001-08
2017-02-22
刘昌安(1961-),男,陕西汉中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J037);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2JK0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