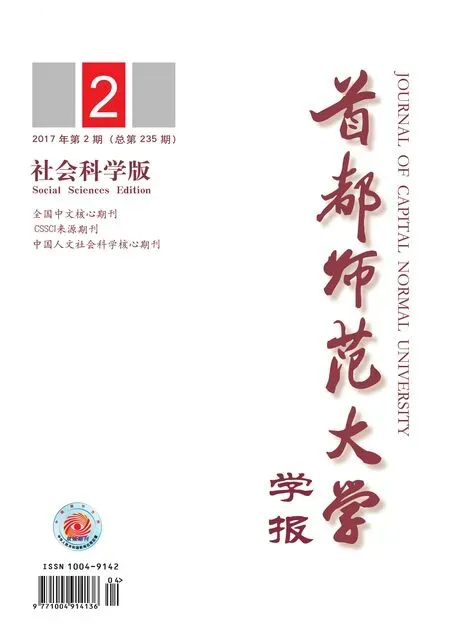独特的“早晨”——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再解读
卢燕娟
《上海的早晨》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创造了独特的“早晨”形象。一方面,小说内在于左翼文学共享的历史时间视野中,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性分野,将现代中国历史表述为黑暗的夜晚与光明的早晨的对照,体现出左翼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建构历史合法性、为社会主义建设确认现实正当性的整体诉求;但另一方面,小说区别于大量左翼文学将黑暗与光明进行截然区分的概念化处理,作家作为统战干部,他在工作实践中的问题意识与饱满的生活经验忠实地进入小说,使得小说所创造的“早晨”形象,不是概念中光明新世界弥赛亚式的降临,而是一个在现实历史进程中逐渐到来的“早晨”。这个“早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弥足珍贵,它再现了光明逐渐到来、黑暗逐渐退散的动态历史过程,记载了从暗夜中乍见光明的人们最初的不适与艰难,在留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复杂甚至艰难的经验和记忆的同时,更试图打开更广泛、更有包容力的未来想象。这个独特的“早晨”,其意义不仅指向当代文学,同时也指向对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和反思,内在于现代中国所创造的独特经验和所面临的独特困境中。
遗憾的是,在文革前的文学视野中,小说的这种独特性往往淹没在“两条路线斗争”或“典型阶级人物塑造”[注]相关文章如徐文斗《<上海的早晨>中的几个资本家形象》、王西彦《读<上海的早晨>》、阎纲《一场未熄灭的阶级斗争——读<上海的早晨>(第二部)》等同时期评论文章,参见赵文敏:《周而复研究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的普泛讨论中。文革期间对小说的批判,反而极为吊诡地揭示出小说的独特性,如工人阶级代表显得比较落后、资本家居然也有“早晨”[注]方泽生等《<上海的早晨>鼓吹什么早晨》(1968年8月21日《解放日报》),是文革期间较早、较有影响的批判《上海的早晨》的评论文章。文章判定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然而,抛开文章罗织罪名、上纲上线的初衷,这篇文章也是较早注意到《上海的早晨》所塑造的“早晨”有别于同一时期对新中国颂歌中的“早晨”形象的文章。只不过在这样的文章中,这种应当珍视的独特性成了小说罹难的原罪。等,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这一独特性背后的复杂性被简单地放置于“反动毒草”的判决中,没有深入讨论的可能性。到了新时期,小说与其他同时期的小说一样,政治上获得平反之后,很快在80 年代整体性的知识转型中,被接踵而至的新文学匆匆抛在身后、束之高阁。近年来,伴随着对20世纪中国道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经验的重新发现和讨论,小说也和其他左翼小说一样,获得了重新讨论的空间。当下,在对《上海的早晨》的重新解读中,比较集中且有深度的成果,是对包括更早的《子夜》等左翼都市小说中上海空间形象的再阐释,以及揭示出小说保留了大量充满物质色彩的日常生活经验,由此进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继续革命,抵制物欲”与现代性本身所内蕴的物质性、消费性矛盾的探讨[注]参见王亚平、徐刚:《分裂的叙事——<上海的早晨>之“叙事裂隙”,》《求索》,2014年第5期;另外张伟涛的硕士论文《革命语境中的“上海叙事”——<子夜>与<上海的早晨>比较研究》集中讨论了这一视野下的问题。。但是,小说关于“早晨”这一经典左翼文学时间形象上的独特性,以及这一独特性背后现代中国革命内部的经验与困境,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因此,本文以这一独特的“早晨”形象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上海的早晨》,并由此进入到对20世纪现代中国历史的再思考中。
一、 光明与黑暗交织搏斗的动态历史再现
现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一条前进的现代时间轴线上,将中国历史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有明确方向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把这一过程具体表述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开端,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向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注]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呼应着这样的历史概念,左翼文艺普遍以中国共产党政权(包括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政权,也包括1949年以后的全国政权)的建立作为分界线,建构了现代历史黑暗的夜晚与光明的白天瞬间交替、鲜明对照的历史时间隐喻。例如,茅盾描写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小说,就以《子夜》命名,象征着小说所呈现的历史时间是被否定的、黑暗的,这一历史时间中的一切人都看不到光明:封建地主固然被历史抛在身后,民族资产阶级也外强中干,一番挣扎之后还是归于失败,预示着光明可能性的无产阶级,在小说中也面目模糊。延安时期的民族歌剧《白毛女》,开创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代主题。歌剧开始于穷人卖儿鬻女、无力躲债的风雪年夜,终结于喜儿解放、群众合唱《太阳出来了》的光明早晨,以八路军的到来为时间分界线,创造出黑夜与光明鲜明对照的艺术效果。后来的左翼文艺,基本延续这一经典模式,建构了旧社会即黑夜,新中国即天亮的经典历史时间隐喻。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都在歌颂早晨、太阳、光明这些意象,胡风的长诗直接以《时间开始了》为题,代表了左翼文艺的这一主流历史时间叙事。
从题目就能看出,《上海的早晨》首先内在于左翼文艺从黑夜到早晨的主流时间叙事中,作者同样要通过小说讲述一个光明的共和国早晨故事。但是,小说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历史在作者的时间视野中,不是一个转瞬完成的凝固时刻,而是一个延续的、发展的动态过程。因此,小说中的“早晨”,不是一个黑暗瞬间消散、光明立刻胜利的时点,而是光明与黑暗交织、搏斗的动态历史过程。
这一时间视野首先决定了小说没有像此前的《白毛女》或同时代的《红旗谱》那样,通过反动阶级被消灭(其代表人物在肉体上被审判甚至被处决)来宣布黑暗时代彻底终结。在《上海的早晨》中,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汤阿英这些劳动者的解放,但不意味着对立势力的同时消亡。以徐义德为核心,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新中国资本家”形象。这些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于“社会主义”的资本家中,虽然有特别罪大恶极的如朱延年,最终也被镇压,但更多人则在新社会中继续存在——这种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个体免于被清除的命运,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其生活方式、政治力量、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等全方面得以保留,同时还获得了很大的生活和社会活动空间。从生活上说,他们继续保有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住洋房、开汽车、办舞会、吃西餐等充满“旧时代”色彩的活动仍然是他们进入新中国的主要生活内容。从政治上说,他们并没有被新时代排斥在外,而是活跃在政协、民盟、民建等重要权力空间中。从经济上说,他们依旧保有自己的工厂,虽然政府对剥削程度进行了一定限制,但他们仍然可以继续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利。从意识形态上说,他们通过或官方或自发的组织,“和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合法斗争”,而且在逐利本质的驱使下,在新社会继续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用尽手段压榨工人,甚至贿赂干部。小说客观地呈现了在“三反五反”中,即使对新政权持积极拥护态度的“进步资本家”如马慕韩、宋其文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五毒行为”。更重要的,马慕韩在各种改造运动中都走在前面,成为颇有影响的人物,平时在家还积极研究马克思理论和毛泽东著作。但配合政府也好,提升理论也罢,都不是为了真的认同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在新社会中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相较于其他小说对“新中国”一片光明形象的展示,小说中的“早晨”由此获得了更复杂的特征。这些来自旧社会的阴影,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到来自动消失。它们不但与光明一起进入新社会,而且积极主动地在新社会与光明搏斗,其中有一部分竟然还是被允许的“合法斗争”。在很多时刻,它们甚至能污染、毒害新社会。朱延年称自己的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改造”本来是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创造:不是在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而是通过将他们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尤其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词用于对资本主义、农业等非社会主义因素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时间方向上清晰地指向进步的社会主义未来。而在小说中,朱延年却在充满反讽的意义上使用“改造”这个词语,而且通过布鞋换皮鞋、逛舞场、请客送美女这样一些充满着旧时代阴影的腐朽行为,朱延年确实成功“改造”了大量的干部。在这里,朱延年显然逆转了时间的方向,不是朝向未来,而是朝向陈腐、堕落的旧时代,不是黑夜结束光明到来,而是黑夜的阴影顽强地徘徊在光明前面。倘若进一步对照新时代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朱延年的“改造”可谓更是入骨入心、直接腐蚀灵魂的。民族资产阶级们在新的时代往往能够接受新的生产关系、政治身份的“改造”,但在内心深处,却是难以触及的。无论是潘家父子还是徐义德,人虽然留在了解放后的新中国,却仍在香港甚至国外经营着自己的退路。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迫于政治压力,也出于对强大祖国的真心渴望,捐款捐物支援国家,但又在私密场合谈论甚至盼望着蒋介石政权能够借机反攻大陆。这些难以改造的意识横亘在小说的叙事中,呈现出作家对历史时间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历史的方向并不是一往无前的直线,总是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织与搏斗中艰难前行,黑暗在很多具体的时空中,甚至会比光明更强大有力。
应该说,在同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中,小说并不是唯一涉及新社会与旧时代阴影的作品。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祝你健康》等,都呈现了在新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阴影。但是,两部话剧都展开了新生活与旧意识的尖锐斗争,并都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胜利告终。而《上海的早晨》却始终没有设置这样的胜利。虽然小说中,朱延年最后被镇压,但是,这些阴影并没有因此退出“上海的早晨”。在小说的同一历史时间中,似乎始终并存着两个时空:一个是工厂工人劳动、生活、参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空;另一个,则是资本家们竭力保存和扩张自己社会与私人生活空间的星期二聚餐会、花园洋房、咖啡馆、舞厅这样一些充满了消费色彩甚至藏污纳垢的旧时空。两个时空始终并置,前者虽然在公众视野中成为新社会的主体,但是后者一直到小说的最后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直至小说终篇,被社会主义接纳了的徐义德,除了家里仍保留了三位太太之外,还与已经成为新政权干部的江菊霞建立不正当关系,并且乘人之危诱奸了朱延年的遗孀,而后者也凭借这一关系在公私合营的新工厂中谋得职业,他的所有这些行为并未受到任何阻碍。而小说中的“新中国资本家”们,在公开场合欢呼新时代,可是内心仍然各有打算:马慕韩掂量着自己新的权力空间,潘信诚父子审度着自己的财富地位,而徐义德带领两位夫人兴高采烈地参加完庆祝后,回到家却满怀伤感地摆出自己早年收藏的名贵手表,黯然神伤。在这一幕场景中,这些无法在公共场合出现、被偷偷珍藏的手表,构成了时间的讽喻:在新社会,它们虽然仍在忠实地记录着一分一秒的“新时间”,但却失去了自己适合的空间,只能和它们所象征的权力、财富一起,成为一种被私人偷偷珍藏、暗暗感怀的“阴暗的旧时间”。然而,这种阴暗的旧时间,却在新社会的各个角落中按照自己的节奏,与新社会的时间一起向前流淌。
如果说,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朱延年、有血债的地主朱慕堂、特务陶阿毛等作为“敌人”,他们的阴影随着镇压、逮捕已经消散,然而,马慕韩们对新社会权力空间的争夺,徐义德们腐朽、阴暗的生活,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新的历史时空中,与新政权努力建构的用劳动创造未来的光明新世界相并置、相角力,由此保留了独特的“共和国早晨”的另一种记忆。
二、 人在晨光中的艰难成长
用艺术塑造“新人”,是左翼文艺的一个重要任务。延安秧歌剧大量讲述二流子改造为劳动英雄的故事,这些在新社会中荡涤污点、获得新生的劳动者是最早的“新人”形象,保留着劳动者在历史时间中艰难成长的记忆。对如何创造“新人”、创造什么样的“新人”问题,一开始存在着不同的方向。有强调创造高大进步的先进人物,以教育人民的主张,也有更强调表现背着历史包袱的人物如何成长的主张。后者在理论上比较著名的有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说,强调要表现人民从旧时代进入新社会、内部自我更新与成长的艰苦;在创作实践上,有诸如赵树理、丁玲等作家做出的探索。赵树理后来在更激进的文学氛围中受到批评,被指责塑造的先进人物不够先进、具有农民局限性,而事实上这些“不够先进”的人物身上,恰恰保留了鲜活的生活经验,留下了人物成长的空间;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塑造了二流子出身、成长为革命者的张裕民,讲述了他不仅与阶级敌人作斗争,也与自己身上的恶习、陈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艰苦过程。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一脉络因为不符合主流标准,作家在一次次外部批判和自我规训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
《上海的早晨》置身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时空中。当时,呼应着对新中国光明早晨形象的主流叙事,文艺作品大量塑造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人”。然而,这部以“早晨”命名的小说,却从对“早晨”的复杂理解出发,塑造了女工汤阿英、郭彩娣、管秀芬们的群像。这些“上海新工人”,在某种程度上绕过了与她们处于同时代的、更有代表性的新人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形象,接续了从二流子到张裕民的故事,成为一个个沾染着旧社会污点、背负着旧时代包袱,在新社会中艰难成长的另类“新人”。
汤阿英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工人代表。她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做《白毛女》主题的延伸:和喜儿一样,因为在旧社会,父亲欠了无力偿还的高利贷,她被压榨、被凌辱。喜儿逃入深山,她则逃到城市工厂。在属于黑暗的历史时间中,空间的转换不可能改变她们的命运,虽然没有在深山“变成鬼”,汤阿英在工厂中仍然要忍受非人的剥削和压榨。正如八路军的到来成为喜儿解放的时点,新中国的成立同样也给汤阿英带来了光明的早晨。当《白毛女》终结于喜儿和乡亲们合唱《太阳出来了》的光明结局时,《上海的早晨》却进一步打开了汤阿英进入“早晨”后的真切体验。
正如小说呈现的早晨不是光明与黑暗的瞬间交替,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是随着光明的到来就自动获得新生。旧社会在她们身上不仅留下了创伤,也留下了阴影。她们进入新社会的过程,既是一个从外部结构中掌握权力、获得解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与自己身上的阴影搏斗,在艰难的自我克服中建构主体性,获得新生与成长的过程。
汤阿英在解放前被朱慕堂凌辱,并因此怀过一个孩子。这段经历既是她的创伤,也是她的包袱。在全厂诉苦动员中,要不要把这段经历讲出来,成为汤阿英一个痛苦的选择。“诉苦”对大部分受压迫的人来说,是控诉加诸自身的罪恶,自己则是道德上清白、处境上受到同情的正面角色。但是对汤阿英来说,留在她身体与灵魂上的苦难,还包含着不洁、耻辱的内容。从逻辑上说,这种把女性受到侮辱归咎于女性的思想,是陈旧的封建意识。但小说深刻呈现了在现实中,这一陈旧意识并未随着旧时代的终结而终结,仍然顽固而广泛地驻扎在人心深处。这不仅体现在汤阿英诉苦后,观念落后的巧珠奶奶由此认定汤阿英是一个“坏女人”,引发了极大的家庭矛盾。同时也体现在汤阿英同厂的女工中,这些在时代话语中被称为汤阿英的“阶级姐妹”们,当听到别人在经济上遭受剥削、在尊严上受到侮辱时,她们很容易联系自己的经历,产生真诚的理解、同情,但是面对汤阿英这样的经历,她们却难以从“阶级立场”出发加以理解同情,而是不自觉地回到陈旧的封建意识中,对她议论纷纷、另眼相看,甚至觉得她“不要脸”。更深刻的是,这种指责不仅仅是别人强加给汤阿英的,她自己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痛苦,也同样包含着基于陈旧观念而觉得自己不洁的自我否定。所以直到最后虽然鼓起勇气,在全厂工人面前讲出这段往事,但这并不是出于对自己作为无辜受害者的确认,而是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党员,不能向党有所隐瞒。汤阿英也许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个看上去非常有“党员自觉性”的想法所包含的价值判断依据,并不来自她所追求的革命意识形态,而恰恰来自革命所要否定的那个侮辱了她、伤害了她的旧时代。
与之可以并置讨论的是《白毛女》在建国后的修改。在故事原型中,白毛仙姑在被地主凌辱之后生下了一个孩子,在村干部救出白毛仙姑的同时,“小白毛”也一并获得解放。最早的歌剧版本忠实保留了“小白毛”的形象,只不过让他在出生之后很快死亡。小白毛的死亡一方面强化了黄世仁的罪恶,深化了喜儿的冤仇,但在另一个隐秘的层面,也割断了喜儿和黄世仁之间危险而隐秘的联系,使得最终走到太阳下的喜儿,不再背负着一个跟黄世仁有着血脉亲缘的包袱。到了建国以后,小白毛的形象进一步淡化,直至最终消失在舞台上。小白毛既是喜儿苦难的体现,但同时也提示着这一苦难包含着不洁和羞耻——这种不洁感,既体现出即使在左翼文学内部,陈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隐秘而顽固地存在着,同时也尖锐地指向内在于现代中国革命的一个深层困境:革命要创造一个光明的新世界,但这个新世界只能建立在旧社会的废墟之上。那些从废墟中爬出来的人们,他们身上难免沾染旧社会的黑暗、背负着旧社会的包袱甚至债务。新世界应该怎样向他们打开?在这一问题视野中,会发现,到了《白毛女》修改、遮蔽小白毛的时代,《上海的早晨》却从小说中的汤阿英、小说外的作者,都还敢于讲出有过那样一个屈辱的孩子。而且,在汤阿英自己和周围人们都觉得这是汤阿英的污点之时,通过代表党组织的余静,宣布这是地主朱慕堂的罪恶,应该随着朱慕堂被镇压而被清算、被终结;绝不是汤阿英的污点,不应成为汤阿英前进路上的障碍。在此问题视野下,这里为汤阿英打开的空间可谓弥足珍贵。
汤阿英之外,小说中的女工们也往往具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观念或行为。郭彩娣在旧时代的遭遇中养成了心直口快、敢说敢做的反抗性格,但也由于经历坎坷、没有接受更多教育的机会,缺乏思考问题的能力,且偏执狭隘。在资本家和特务的挑拨下,一度引发工人内部不团结的困局。管秀芬年轻好强,要求进步,但虚荣刻薄,一度被特务陶阿毛欺骗利用,不仅与他谈恋爱,还在不知不觉中向陶阿毛泄露消息。因此,文革时期,《上海的早晨》受到严厉批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丑化工人阶级”[注]1968年9月10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发表上海国棉二十一厂“批《早晨》战斗组”及革命工人的大批判文章,其中如《谁污蔑工人阶级就打倒谁》(《解放日报》)、《不许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文汇报》)都批判小说没有塑造高大正确的工人阶级,而是塑造了觉悟不高、满身缺点的工人阶级,认为这是对工人阶级形象的污蔑。。的确,且不说文革时期《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即使是同样创作于十七年、在文革中也受到批评的《创业史》,其主人公梁生宝及其周围的进步农民,也比《上海的早晨》中的工人阶级群像光辉得多。
在“新人”普遍向着更成熟、更完美迈进的时代,小说正是通过塑造这些“落后”工人形象,留下了“共和国早晨”独特的经验与记忆:灿烂的晨光中,不仅有来自对立阶级的黑暗力量,在新时代获得解放的劳动者内心深处,同样保留着黑夜留下的污垢、包袱。甚至,相较于资本家的投机倒把、偷税漏税,这些驻扎在人心深处的污垢是旧时代对劳动者更深刻的伤害和禁锢。荡涤这些污垢、解除这些包袱的过程,是劳动者和自己内心激烈搏斗、在新时代中努力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甚至比发动三反五反限制资本家的破坏、公私合营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艰难、更痛苦。
三、 “谁的早晨”问题:朝向更有包容力的未来
在左翼文艺习惯的叙事结构中,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往往构成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并且总是以反动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来确认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上海的早晨》却打破了这种模式。小说不仅客观呈现了资产阶级能够在新中国获得较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空间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小说中并不仅仅作为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早晨中的暗影”来展现,而是获得了这样的可能性:他们虽然不主动、不情愿,虽然与新时代存在冲突甚至斗争,但最终仍能与新时代一起前进。文革时期,《上海的早晨》遭到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如上一部分所述,批评其塑造的工人阶级形象落后;其二,就是批评小说中的资本家没有被赋予必然灭亡的命运,建构了资产阶级同样可以“有早晨”的历史叙事。抛开政治立场的分歧,方泽生等人提出的“《上海的早晨》鼓吹什么早晨”的问题[注]方泽生等:《〈上海的早晨〉鼓吹什么早晨》,《解放日报》, 1968年8月21日。当时持这个观点的批判文章,还有暑名上海国棉二十一厂“批《早晨》战斗组”的《工人阶级绝不允许资产阶级有“早晨”》,《文汇报》,1968年9月10日。,实质上指出了小说与其他左翼文艺相比的这一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早晨”确实不仅是劳动者迎接光明、艰难成长的“早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在新社会中获得未来可能性的“早晨”。这一叙事表面上看,似乎诚如文革时期的批判而言,模糊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性质,甚至在一定层面上消解其正当性。但是如果回到对20世纪中国历史和革命的深刻理解中,就会发现,正是这样一个“早晨”的存在,才解释了现代中国革命实践的创造力和有效性所在,也才赋予中国革命更有包容力的未来。
革命进程中,通过土地革命解决农村问题,革命和生产关系变更的同步性很强,也有大量优秀的作品表现这一进程。但解决城市问题——本质上是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回答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处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却是更复杂也更困难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之于资产阶级,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事实上,都还不足以构成颠覆和替代,因此新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是吸收和内化。尽管这个过程中也有“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客观来讲不像处理农村问题那样“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新中国事实上对资产阶级独创了一种“改造重于消灭”的方式,这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和遗产。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对这个特点都没有进行足够的厘清。从这个视野来看,《上海的早晨》打开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劳动者共处于“早晨”的时空可能,正是对这个特点的典型呈现。
小说首先赋予了民族资产阶级可以与新中国一起共处于“早晨”的内部合法性。在小说中,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态度复杂,而且多半抵触。但是他们毕竟没有跟随南京政府外迁或移民海外,而是选择留在大陆。这种选择虽然充满了犹豫、动摇,例如很多人还在海外或香港给自己经营退路、随时准备外逃,更甚者,在抗美援朝的开始阶段,他们还在私下传播谣言,期盼蒋介石政府能借机反攻大陆夺回政权。但无论如何,他们最终仍然选择留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其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独立,并正在迅速地强大起来。这样的新中国终结了他们在旧社会颠沛流离、还常常受到外国人歧视欺凌的噩梦,不仅给了他们安定的生活,更给了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尊严。因此,无论是进步一点的宋其文,还是始终没有从内心认同社会主义的徐义德,都发自内心地希望民族独立、国家强大。也正是基于这一认同,在抗美援朝中,这些资本家们绝大部分积极出钱出力捐助国家——尽管这其中也包含着外来的压力,但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还是这些行为的直接动力。这种认同不仅成为他们能够在新中国获得较大空间的客观原因,也成为小说中他们能够跟随新中国一起前进、不是走向末路、而是共处于朝向未来的早晨的内部原因。
其次,小说以充满希望、朝向未来的笔调,没有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重要历史事件讲述为民族资产阶级被战胜、被取消的覆亡史,而是讲述为民族资产阶级不断提高认识、努力跟上社会主义步伐的前进史。“三反五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不法行为,公私合营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然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会是一个愉快的历史进程。小说呈现了这些运动中资本家们备受煎熬的状态(比如徐义德临出门前做好被捕入狱的准备),但最终得到处决的只有罪大恶极的朱延年。朱延年处决后,他的福佑药房因被逼债而倒闭,这个细节展现了这场运动在国家意志主导下,具有相当强烈的阶级指向,这当然符合历史客观。但更大的历史客观是,上海滩超过90%的民族资产阶级“过关”了。所以作品一是没有选择“处决朱延年”作为叙事中心,二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切可能产生的不道德因素都集中在朱延年身上,使他不仅成为极少数的“反动资产阶级”代表,并且也因为他本人道德沦丧、劣迹斑斑,连他同一阶级的资本家们也对他深恶痛绝。因此,最终对他的处决就在包括大部分资产阶级都认同的道德标准中获得了正当性,淡化了处决朱延年事件所内蕴的社会主义国家镇压反动资产阶级敌人的阶级视野。这一重心转移之后,绝大部分资本家脱身出来,不仅在小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获得政府“宽大”而过关,也在小说的叙事逻辑内,免于走向末路的命运。此前的煎熬惶恐,在这一脱身之后统统构成自我净化、自我成长的必须,他们的阶级本性得到了修正的可能性,可以与整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一起,朝着社会主义未来前进。
最后,小说更建构了资本家后代们充满希望的未来。青少年始终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形象,他们总是昭示着自己所代表的民族或阶级的未来。这种象征发展到后来,变成了决定性的、甚至是血缘传承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文革时期的小说《艳阳天》,地主马小辫的儿子,虽然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且考上北京大学的青年,但作为地主阶级未来的象征,他身上只有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而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虽然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儿童,但作为无产阶级的后代,在阶级敌人面前却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而在《上海的早晨》中,如果说徐义德、潘信诚这些老一代资本家们的未来,还是犹豫的、彷徨的,他们的后人却已经能够获得更确定的光明未来。徐义德的儿子,在资产阶级家庭氛围中,成长为一个参加盗窃团伙的流氓。这样的人生轨迹显然是不可能通向任何未来的。这里似乎也隐喻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可能产生一个光明未来的判断。而在被抓进社会主义监狱、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劳动改造之后,这个在资产阶级内部已经没有希望的青年,居然幡然悔悟,开始寻找作为一个新时代青年的方向和意义。小说的最后,他参加周末义务植树活动,那个穿着劳动装、满身泥巴的青年,连与他非常熟悉的人都没有认出他来。这个情节昭示着,他不仅通过劳动荡涤了自己过去的污点,也隐匿了有原罪的家庭出身,彻底融入“社会主义劳动青年”的整体形象中。而在小说中的其他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徐义德大太太的侄女吴兰珍是积极追求进步、充满阳光的青年团员,马慕韩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进步“小开”,就连徐义德的姨太太、被作为金丝鸟常年关在家里的林宛芝,也在接触新的时代、呼吸新的空气中一点点萌发出朦胧的尊严与自由意识。在其他左翼作品中,这些出身的年轻人,往往只能代表他们的阶级走向穷途末路。而在《上海的早晨》中,他们身上一方面会体现出来自没落阶级的阴影,但另一方面,他们仍然能获得在新社会中重新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直至融入前进的新社会的希望和可能。
小说为资产阶级、尤其是出身资产阶级的青年打开的光明未来,使得“共和国的早晨”呈现出了其他左翼作品难得一见的包容性。而这一看似革命立场不够坚定的“早晨”,却真正昭示着中国革命最有创造性、生命力的精神:革命不仅仅是武力夺取政权,也不仅仅意味着劳动者在经济上翻身,更意味着建构一套极具感召力与影响力的文化认同,这一文化认同甚至能把人民的敌人改造教育为人民的内部成员。
结语
终结黑暗,创造一个光明的新世界,这是20世纪中国革命提出的最具动员力和感召力的理想。《上海的早晨》在这一理想叙事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弥足珍贵的“共和国早晨”。这个“早晨”在汗牛充栋的共和国颂歌中,真正深刻地理解了现代中国革命最深刻的意义:革命不是纯净美好如天堂般的显灵,而是在旧世界的废墟中,面对黑暗、污垢、沉重的包袱与债务的艰难搏斗;不仅仅是与敌人刺刀见红的血战,更是每一个想要创造和进入新世界的人自己克服自己、自己与自己内心的激烈战争。而最重要的是,这个“早晨”不仅仅属于作为革命主体的底层劳动者,也包含着一切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强大的中国人可以共享的希望与未来。从这个视野来说,今天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讨论,正如对这部小说的讨论一样,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