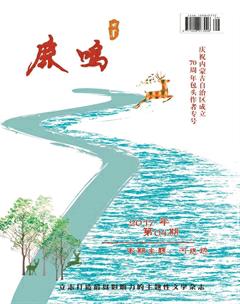饥荒富余水够吃
誓戎
小时候母亲常说这样一句话,饥荒富余水够吃。这话的意思是家里缺钱花或向别人举债借钱是经常的事,只有不用花钱随意担挑的井水充裕够用。母亲说这话有两层含义,一为调侃二是表决心。本质上说母亲生性乐观豁达,又是个极其勤快的人。家里常缺钱,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了的,一则是社会原因,当时村里走集体吃大锅饭,挫伤了农民们的劳动积极性,村集体经济长期搞不上去,再加上交国家的公粮也多。二是家里的孩子多,既要给两个哥娶媳妇又要供我和二姐上学,家里岂有不缺钱的道理。缺钱也不能逢人便哭穷诉苦,得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现状。那么解决家里吃水问题就容易了许多,村里有三口井,南头一口,北头两口,南北头以一条小沙沟为界。南头那口井离我家就一百多米,井水很充沛,只要勤快,你家的水缸经常满盈盈都没问题。大哥二哥同母亲一个秉性,都是闲不住的勤劳人,因此我家能放三担半水的大水缸时常满满当当,吃水用水很方便。当然吃水不缺也有条件,首先得这个村子地下水量丰沛,其次还得水质好。有些村子住的地势高或远离水脉,四五丈深的井底还常常井水枯竭。有的村子井水充裕但水质不好,或含氟高使人牙齿变黄疏松,或缺碘,人容易患粗脖子病。我们村有两个村名,一个叫南号村,另一个叫大水坑。南号村是从行政划分上叫的,因为清朝和国民时期,旗下设苏木,苏木下设号。号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我们村隶属于察哈尔正黄旗四苏木头号,头号又分南北号两个村。察哈尔正黄旗就是现在乌盟察右前旗。大水坑则是按地域地形叫的,是由于我们村坐落在南北走向的两条小山脉之间的一片坑地里,地貌上属于阴山山脉的余脉丰镇丘陵。我们村俗称大水坑名实相符,地下水资源的确丰富,在村庄里或村外的坡地上哪个地方打井都几乎能打出水来。曾经的国家劳模、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李国安年轻时,就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四清运动时到我们村下过乡,看到村里人没菜吃,就带领乡亲们在村西二里多地的一块芦苇丛生的台地上打了一口井,并平整出一大片菜地,使村民们夏秋两季吃上了应时蔬菜。可村里人在坑洼不平而地势广阔的地面上种庄稼却又靠天吃饭,旱灾频发。我家吃水的那口井深一丈五六,由青扁石碹砌而成,底大上小,井口由四块又大又厚的方石镇盖着。井旁是一方六尺多长的石头水槽,供村里人洗菜洗衣和饮牲口用。在我的记忆中这口井即便是最干旱的年景,井水也较充沛,未出现过枯竭现象,并且水质清澈甘甜。小时候水井旁边就是我的乐园,没事时常去水井旁玩耍,因为水井旁比别处凉爽,不远处还有个大水卜子,燕子喜鹊等鸟飞起飞落。玩得又热又渴,有大人挑水了,就向大人们提出喝几口井水的要求,大人们一般都欣然同意,喝吧喝吧没事的。我就把嘴唇紧贴到水桶的边沿上,用手稍微搬动一下水桶,快速地吮吸几口清凉的井水,然后舒坦地拍拍小肚子并长出几口气。如果是午饭不久,正巧又吃了油炸糕或荤油烩的菜,挑水人的水桶里便会漂浮着几缕细小的油花。没人挑水,在寂寞的井旁,我经常玩的节目是,跪下身子把头伸到井口,看井水里倒映着的那一孔蓝天,或是观看深窈窈的井底自己那一枚小小的但五官清晰的头像。看得腻了有时就把一两块干净的小石子扔进纹丝不动的水井里,听井里发出“卟咚卟咚”的声音,估摸着井水的深度。尽管那时还小,但农村很少有闲人,不少时候去井台上是有事情做的,或是给家里清洗菜蔬,或是给自己洗涤穿脏的夏衣夏衫。或者是看着天太干旱了,大人们盼雨盼得心急如焚,就和比我大三岁的二姐一起举行个小型祈雨仪式,帮助大人们祈祈雨。通常是我站在井台的青石板上,战战栗栗地用水兜子半水兜半水兜地从井里拔着水,二姐则在疏通着大石槽下面的水渠。我一边把水兜里的水通过没阻泄水眼的石槽居高临下地倾倒到水渠里,一边问二姐,掏水渠子干啥了。二姐说,下雨用它流水了。我再问,下多大。二姐回答,八寸八。我又问,几时下。二姐说,明天不下后天下。能浸透到地表下面八寸八的雨水,那可是连下几天的连阴大雨,是全村社员们期盼许久的甘露啊。
井台旁不但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处所,村庄人得以生存的生命之源,各种消息传播的集散地,同时还是产生各类故事的重要场所。无论古代现代,无论域内域外。据《圣经》中讲,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垂顾下在异地发了大财,派仆人老管家去故乡本族中为其儿子以撒聘娶妻子。老管家就是在亚伯拉罕故乡拿鹤城外的水井旁为以撒寻觅到美丽善良的女子利百加的。老管家跋涉到拿鹤城外时,天色将晚,他和骆驼们都走得干渴难耐,便让骆驼跪在水井旁,等待机会喝水。不多时从城内走出一群女子,肩扛水瓶出来打水。老管家对其中一个容貌极其俊美的女子说,求你把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管家喝完水后,女子又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为所有的骆驼饮饱了水。老管家看着眼前这一切,喜在心里,暗想这女子既俊美纯洁又善良勤劳,就是为東家儿子寻找的理想配偶。随即就拿出一个金环两个金镯送给那女子,并攀谈起来,得知女子和亚伯拉罕是同族同宗,更是喜上加喜。并要求利百加带他去她家投宿并且提亲。这是一个多么温馨而富有诗意的故事。那利百加女子极其俊美,那拿鹤城外的井水也定然特别甘甜特别充沛。《圣经》中的故事绝大多数是传说,这个故事可能也是一个传说。
发生在我们村井台上的这一故事却千真万确,但绝不温馨,相反这是个给人苦涩并感慨沉思的故事。一九六七年冬天,有二十名上海知青插队落户到我们村,其中女十一名男九名。有个叫黄杨红的女生,出身不好,她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兼资本家。黄杨红不但出身不好,人也长得不漂亮,牙齿有点外突,鼻子周围还有几片雀斑,再加年龄最小,可能是十六岁,性格又有点倔,知青们就常常欺侮她。文革时期是个特殊年代,这类事情经常发生,黄杨红常常是默默忍受。一次不记得因为一件什么事,男知青刘小毛欺负黄杨红太过分了。黄杨红就边尖利地哭喊着不活了不活了,边快步跑到井台上跳入井里。知青点建在我家院子东面的一片枳芨滩中,离水井不到二百米,黄杨红的哭喊声惊动了村里人,那时村里人多,大人们纷纷奔到水井旁,拿绳子的拿绳子,下井的下井,打捞井水里的黄杨红。可能是那年夏天天旱,井水水位不高,未将黄杨红淹没,黄杨红被社员和知青们救了上来。公社领导知道这件事后,严厉地批评了刘小毛等男知青,并怕类似的事再发生,就把黄杨红抽调到公社机械厂当了一名车床工。据说当时村民在井底救捞黄杨红时,她并不配合,又喊又叫又挣扎,是刘小毛趴在井口使劲央求,黄杨红才配合着被吊了上来。万幸的是这次事故黄杨红只是头部受了点轻伤。黄杨红跳井后南头的户家有几天没到井上挑水,吃水只得绕远道到北头的水井去挑。隔了几天,南头的人们包括知青实在不愿受远道挑水的劳顿,就想了一个办法,大家齐动手把井里的水用水桶拔吊出绝大部分,等于换了一次井水。接着就又开始食用南头的井水了。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有条件的家庭大部分在自家的院前屋后打压安装了压水井,不用起早贪黑地到井上挑水。再后来,公家每户补贴一千多元,家家户户在院前的空地里打了口小机井,一合电闸,纯白的井水呼呼冒出,不出两分钟,注满水缸。村民们随心所欲地用着水,几乎不费什么力 ,真正做到了母亲生前所说的吃水富余那程度。这既得益于国家的农村政策好,又得益于我们村地下水资源丰富。村中的那口井现在还在,只是很少有人光顾它了,那孔寂寞而布满苔藓的井口,日复一日地映照着寂寞的蓝天。
留守在村里的人水绝对够吃,并且是未经污染的优质地下水。他们的饥荒是否还富余,不得而知。至于我在城市包头已生活了三十多年,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还给读研的儿子存了部分钱款准备他成家立业用。只是家中水管中的自来水,水质越来越差。家中的纯净水管时而供水时而停供,因此常常为家中的饮用水费周折,有时从单位拎一桶有时上水站买一桶,有时只得喝有明显异味的自来水。母亲曾经形容过的饥荒富余水够吃的情形,四十多年过去在我身上却打了一个颠倒,变成了饥荒无有水不够吃了。仔细想想饥荒没有只是暂时的,孩子结婚在大城市买住房,自家那点存款无疑杯水车薪,还不得替儿子背巨额外债。没有纯净甘甜的水喝恐怕将是长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