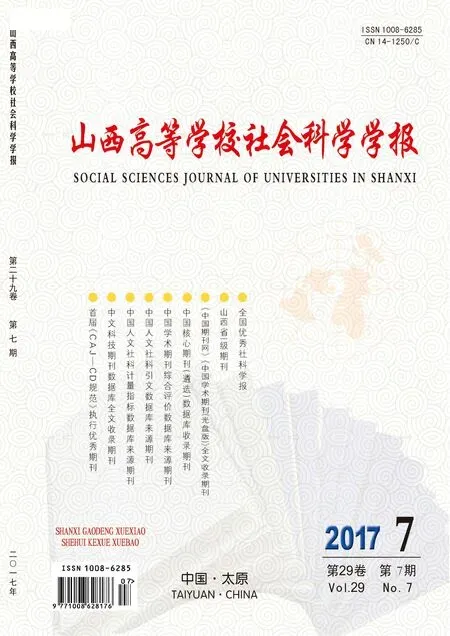从传统到现代:在依附与独立之间彷徨的中国女性*
唐善梅
(南京审计大学 艺术教育部,江苏 南京 211815)
从传统到现代:在依附与独立之间彷徨的中国女性*
唐善梅
(南京审计大学 艺术教育部,江苏 南京 211815)
衡量一个社会文化心理自信与否尤其是男性精英自信与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男性对待女性以及女性自身对待自己的态度。所谓传统对中国女性的压制与束缚并不能一概而论,诸多思想束缚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先秦至汉唐女性几乎没有国家与社会层面的束缚,其天性纯朴自由;宋元明清女性被要求“三从”“守节”,其天性被压抑受戕害。现代社会女性观的树立可以从西方女权主义思想中吸收营养,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自身要追求精神独立,从社会角度来说要从制度设计层面对女性的权益给予保障。
传统;现代;依附性;独立性;中国女性
自人类从母系社会进入到父系社会以来,女性沦为了“第二性”。男女两性不能够以平等的姿态分享这个世界,在经济资源、社会地位、话语权力等方方面面,男性全部掌握了主导地位。衡量一个社会经济繁荣与否是根据物质产品指标,人口数量、粮食产量、财富总量等;衡量一个社会文化繁荣与否可以根据精神产品指标,诗词歌赋、书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衡量一个社会文化心理自信与否尤其是男性精英自信与否,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男性对待女性以及女性自身对待自己的态度。
在封建社会,女性受到三种权力的束缚:父权、夫权、子权。所谓“三从”,实际上都与女性情感自由有关。在家从父,父亲做的主无非是在不尊重女儿个人意愿情况下为女儿选择门当户对的夫家。出嫁从夫,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是针对女性的意志自由,重点防范的仍是“红杏出墙”的风险。夫丧从子,限制的仍是寡妇的再婚自由。在这样一套规范中,女性的身体安全是给予保障的,无论是父亲抚养女儿,丈夫养活妻子,还是儿子赡养母亲,唯独压制的是女性个体精神的自由。另外,女性所受的压迫还有男性知识分子所设计的思想藩篱和政治制度,以及来自女性自身的内化与自我压制。
但是所谓传统对中国女性的压制与束缚并不能一概而论,并不是每项传统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很多思想束缚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传统并不是厚重无比甩不开的包袱。历史上的中国女性也不都是活得暗无天日,直到现代社会来临。如果把历史粗略地划分为几个大的时代,尤其是具有典型性的几个时期,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中国女性精神自由度的演变图。
一、中国传统女性观的历史演变与文化制度解析
(一)纯朴自由的先秦汉唐女性
先秦时代民风淳朴,无论男女都没有受到礼法的束缚,自然本性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保持着文明初期特有的自由性情。《诗经》中有不少诗篇是关于男女之间爱情甚至性爱的描写,例如《国风·召南·野有死麕》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直译为:一头死鹿在荒野,白茅缕缕将它包。有位少女春心荡,小伙追着来调笑。林中丛生小树木,荒野有只小死鹿。白茅捆扎献给谁?有位少女颜如玉。“慢慢来啊少慌张!不要动我围裙响!别惹狗儿叫汪汪 !”),既含蓄又自然健康。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形象,无论男女都是健康美丽的,充满了原始的活力。女性的自由同样体现在恋爱上,《诗经·鄘风·柏舟》记载一个女子有了合适的意中人,父母不同意,她就直率地抗争*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直译为:发誓至死不另求!我的母亲我的天,为何对我不相信!)。《诗经》里塑造的不少女性充满了野性、活力和自然的美。孔子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汉代尚武,女性美的一个要件是身材高挑丰满。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上,贵族妇女大多身形高大丰腴,与身边的侍女形成鲜明对照。男女关系相当通达,墓葬中男女裸体恩爱图像屡见不鲜。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饮,结伴同路,甚至同车而行,女子也能单独会见男宾。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上,画着一位插笄的女子与着帽男子并列而坐,其旁又有两个女子对坐宴饮,这就是汉代宴饮男女“杂坐”的情境。汉代妇女改嫁是家常便饭,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好指责的。汉景帝的皇后王氏曾经离异并与前夫育有一女,也没有因此“污点”影响自己的儿子当皇帝。曹操在遗嘱中还特别嘱咐他的妻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汉朝人尚武之风使得军队战斗力强大,尤其是武帝时期,出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军事名将,在对匈奴作战中取得军事战争的胜利。贵族社会经常比武,文人名士也都文武兼备。当时的汉民族无论在智力上还是体力上还均保持着对少数民族的优势,总体上处于民族自信时期。男人活得舒张,也没有针对女性制定各种条条框框。虽然董仲舒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构建了“三纲”的思想体系,也被当时的统治者以政治权力加以独尊,但是还没有成为深入民心的思想观念。
唐代是个女性解放的年代,女人以丰肥壮硕为美,着装自由,婚姻自由,外向泼辣,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小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唐朝女人的惊世骇俗不仅体现在袒胸露乳的“时装”上,也没有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等清规戒律,离婚改嫁习以为常。唐肃宗以前的唐代公主,再嫁者达二十三人之多。无论是文人还是普通百姓,对自由恋爱采取宽容态度,“男女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所谓的节烈观念实践者不多,《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的烈女节妇,宋代有267人,明代达到36000人,而唐代只有51人。唐人的女权意识历史上空前绝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就出现在唐朝,她还选拔任用了上官婉儿等一批女官。唐代女性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唐代女性性格独立而刚强,小说中的女性大多侠气逼人,与其他朝代中国人喜欢的女性形象大异其趣。与“妇女解放”并行的就是“体育精神”,唐代的皇族以马球作为“皇家运动”。唐朝初期的几个皇帝具有少数民族血统,骨子里具有豪放的气质,大都自信大度,人格健康,实行开放的统治政策,没有民族歧视心理,任用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军事将领。据统计,唐代少数民族宰相即有二十四人,分别来自十五个民族。君臣的森严关系淡化,文网宽疏,信仰自由,没有禁区,文人大臣们言无禁忌。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长安成为一座国际型大都市,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文化上大胆吸收和融合,以博大胸襟采撷异域文化精华。唐朝人的民族自信达到了中华民族的鼎盛时期,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为后世谱写了辉煌壮丽的盛唐之音。
(二)压抑束缚的宋元明清女性
宋朝是其开国皇帝通过武力从前朝的孤儿寡母手上夺得的政权,所以宋朝帝王特别忌惮武力和军人,唯恐以同样的方式失去政权。因此宋朝的国策重文轻武,文官受重用、升迁快,武将受打压。除了限制武将,宋代连续七次颁布了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种法律禁令。民间尚武之风尽失,开启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男人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日益强大,天生的骁勇善战使宋朝时刻有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宋朝的知识分子虽然得到了统治者的优待,不会动辄被消灭肉体,顶多是政见不合遭遇流放。但精神上受压抑,对外是面对强悍的少数民族武力难以抵抗,不能立马扬威;对内盛行文弱书生,老老实实寒窗苦读消磨一生。体力上的柔弱同时伴随着精神上的压抑,宋代的男性知识分子只有剩下磨练意志一条出路了。反向内心的修炼就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以对“人欲”的消灭作为修身高境界的象征。没了自信的中国男人开始靠守节来获取安全感,尽心竭力坚守一些本来无所谓的行为准则。男人活得如此压抑,各种束缚的规则自然也投向了身边的女性。从唐到宋,中国女性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内敛柔和;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妇女却只能站在重重帷帘之后,掀起一角悄悄向外张望一下;唐代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小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宋代妇女却裹起了三寸金莲,行不动裙,笑不露齿;唐代妇女以丰肥壮硕为美,宋代追求瘦弱纤巧。女性的弱态病态才能让文弱书生们有安全感。从宋代开始,男人开始了处女嗜好,三寸金莲普及,男人致力于把女人如同粽子一样用礼教和衣服重重包裹起来,要她们三从四德、站不倚门,要她们性格怯弱,弱不禁风。窄瘦贴身、交领深掩的窄袖衣是宋代流行的女装。宋代男人宣称,女性的贞节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如果女人不守贞节,国家的道德就会崩溃,会招致亡国灭种的危险。男人通过这种方式把亡国灭种的责任转嫁到了女人身上,通过盯着女性守贞节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所谓中国女性的含蓄美并不是自古就有,女性裹小脚等陋俗也不是自古就有的。
元代虽然短暂,但对于汉民族来说确是一场噩梦。马背上的蒙古族不了解汉文化的价值,深受汉文化气节教育的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被大面积消灭。幸存下来的只能接受民族歧视政策如同囚犯和奴隶苟活于世间,甚至生活起居都要由蒙古人控制。知识分子不能考取功名,不能做学问,只能写写杂剧小曲谋生。以《水浒传》中的妇女观为例,提到英雄人物爱习武,肯定附上一句“不爱女色”。才貌双全的女英雄扈三娘还要被指婚,被许配给矮小丑陋好色的王英,她的反应是“低首伏心,了无一语”,这种描写显然反映了底层民众对女性的要求。
明代虽然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但是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似乎比异族统治者更懂得如何统治百姓。作为穷人,他反感贪官,制定了很多严厉惩罚贪官的残酷刑法。作为白丁,他对知识分子也毫无尊重之意,只要不能为朝廷所用就可以用诛心的方法惩处,想通过做隐士保持气节在明朝也不可能了。在强权面前,知识分子想保持气节已经是很困难的事了,于是这个节又被转移到了女人身上。“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男人为了保存肉体而无法保持的气节只有通过女人失去肉体来保持了。明朝是贞节烈妇牌坊最多的朝代。那时的普通妇女只有通过嫁人才能获得生存资源,如果不幸守寡,再得不到夫家或者娘家其他亲人的支持,要想守节就只有饿死了。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的女儿,就死在了所谓的节上。道德原本是为了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使人类社会生活更加有序,但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道德规则却是摧残肉体生命的,尤其是女性的肉体生命。
清朝是第二个少数民族政权,原本以蒙古人和满人为主的清朝后宫对女性的束缚也没有汉人多。但是后来清朝的统治者学习汉文化作为治国之策,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对妇女还是用了“三纲五常”那一套。小说《红楼梦》中写到的贵族女性尽管都很精彩,但无论是善于管家的王熙凤、才气逼人的林黛玉、还是豁达豪放的史湘云、冷静沉着的薛宝钗,都不能实现对命运的自主。尤其在爱情婚姻选择方面,或者选择死亡,或者服从安排。贵族女性尚且如此,那些丫鬟仆人的命运就更是由不得自己了,全部操纵在主人手里。少数选择生命自主的女性,像尤三姐、司棋等,最终都是用死亡来实现这种自我完成。这不仅仅是某个女性个体的悲剧,而是女性作为社会中和男性对应的一个群体的悲剧。
(三)物质独立的新时代女性
五四运动时期,欧风美雨开始吹沐中国,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候,男性精英开始意识到国民母亲对于强国的重要意义,倡导“废缠足”和“天乳运动”,去除戕害女性身体健康的陈规陋习。在男性精英的鼓励下,一些“摩登女性”开始了冲破枷锁的自我解放之路。这种解放首先从身体的解放开始。新女性开始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有的喊出了“公妻”“男妾”的口号。新女性主要集中在两类群体。一类是接受新知识的女学生,她们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所以很多人向往革命,她们要改变当时的社会和女性群体的命运,她们以战友的身份与男性并肩作战。另一类是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交际花,她们得到的是比普通妇女奢靡的物质享受和公开场合的社交自由。表面上她们不再受封建礼教的限制,不再受男人的压迫,甚至很多人可以玩弄男人于股掌之中,但是她们只是依附了更加位高权重的男人而已,因为她们自身并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她们是奢靡物质生活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其他人的消费品。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两类摩登女性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一类女性,革命时期是一起流血牺牲的战友,革命一旦成功还是被男性统治者要求退守家中。那才是当时的主流观念。
解放后女性获得了劳动权利。其实古代妇女也并不是只是在家洗衣做饭,不从事生产劳动;妇女们从事的纺织工作一直都是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只是妇女在家从事生产,没有公开的大规模的社会化劳动而已。解放后政府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下子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各个领域涌现出了各种女性形象,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等等,只要男人能从事的职业女人都能干。妇女在获得空前的社会地位时也要忍受着生理上的痛苦,因为生理期、孕期等特殊时期的女性还是需要保护的,不是什么都和男人一样就是获得了解放。
即使是劳动权利、经济权利获得了平等,也不是立刻能带来心理上的独立意识和安全感。20世纪80年代的妇女杂志上刊登最多的一类文章就是控诉“陈世美”的故事,那么多的“秦香莲”通过媒体、通过组织,利用行政力量和舆论力量向身边的“陈世美”施压,挽救自己的婚姻。虽然男女都一样工作挣钱了,但从心理角度大众还是认可“秦香莲”们的弱势,频频利用道德的力量打压“陈世美”们。道德的力量是可以挽救形式上的婚姻,但是弥补不了破裂的感情,并不能真正给女性带来幸福,除非女性自身的心理真正强大起来。
心理上的真正强大与身体上的解放又不能完全划等号。80后的女作家卫慧、棉棉们通过文字作品,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阐释现代女性的解放。在她们看来,似乎女性被压抑的性得到了解放,女性就获得了身心自由。但似乎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在情感深处都会达成共识,放荡不羁的生活并没有给女性以心灵的自由,有的只是更深的空虚和无聊,每一颗狂放心灵背后都有一种对稳定与专一的渴望,即与一个普通男人过上稳定的生活。
二、当代社会如何树立现代女性观
(一)女性自身追求精神独立
西方女性的解放之路不可谓不波澜壮阔。女性从作为男人的财产到取得公民权,每一项权利的获得都伴随着积极主动的争取。西方历来不缺女王、女皇,政治领域并不是女性的禁区。女性参与政治也不会违反道德。但中国社会少有的女性政治强人即使管理能力超人,也确实取得了不凡的政绩,但是在史书的评价里总是很难获得正面的评价。如果你是一个好政治家,就不是一个好女人。似乎在政治的规则里一个女人不做出一些心狠手辣有违女德的事就很难取得成功。
男性精英为女性设计的精神枷锁已经通过知识系统成为受教育女性的一种内在规范。班昭作为历史上少有的才女也没想到用自己的才华与男子抗衡,而是写了《女诫》来规范女性同胞的德行。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论出身、论能力、论品行都不输给徐,但是在他们的婚姻中张处在被抛弃的弱势地位。尽管她的才能可以让她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她的品行赢得了徐志摩父母的认可成为徐家真正的掌门人,但是她就是无法赢得徐志摩的爱情。抛弃妻子的徐志摩可以不顾任何舆论压力娶陆小曼过门,张幼仪在多年寡居改嫁时还得征求哥哥们的意见,在未获首肯的时候还得征求儿子的意见,最终才获得了后半生的幸福。这样的一种精神枷锁束缚的不仅仅是普通女性,还包括张幼仪这样有完全独立经济能力的女性。她们生活在现代,但她们的观念仍然是传统的。
当代女性摆脱了传统的很多压迫,可以和男子一样读书接受教育,可以有机会独立思考。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个体女性到底应该怎样生存呢?女性可以参加公共社会劳动,社会职业中有很多适合女性做而且女性也能做得很好的职业。女性有自由恋爱的权利、自由结婚的权利,没有哪个父亲会把门当户对当作唯一的结婚理由了。《婚姻法》既保障了女性离婚的自由,还通过财产分割等条款保障女性的经济权利。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传统的幽灵在游荡。一些女性自我选择回归传统。“废缠足”运动虽然从制度上进行变革是很快的事,但是从制度出台到思想观念的变化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担心女儿大脚嫁不出去的思想还是束缚了百姓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男方的家长不会因为女性脚大而拒婚,移风易俗才能真正地实现。然而现代的女性主动穿起了高跟鞋,有些鞋跟的高度使脚面的隆起弧度像极了曾经的小脚。唯一的区别是过去的女孩是被迫的,现在是自由选择的。革命的女性为了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和封建家庭的束缚争取参加社会工作的权利,而现代的职业女性为了金钱、职位等主动依附更有权势的男性。更有一些女性追求不劳而获而选择被男性包养。还有些女性选择了退出社会工作,回家当起了全职太太,当然也有很多男人认为这是自己有本事的表现。百年革命后我们仍然摆脱不了的是传统的生活观念。但我们还是要看到历史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很多人可以生存下来,不再为吃口饱饭斗得你死我活。如果人类都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生存问题,是否下一步就要思考如何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的问题。女性也是如此,回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女性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女性开放时代。所有的羁绊和束缚都可以思考一下它到底来自哪里,是政治制度的设计,还是思想观念的压制,抑或是真实的内心需要。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前人的努力使女性群体摆脱了重重压迫。但对于个体而言,如果不顺从群体的生活方式依然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如果说我们的社会还需要进步的话,那就是女性从注重物质满足开始向注重精神满足过渡,不要为了物质的虚荣放弃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独立。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一些容忍和宽容,让每个女性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心真实的需要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生活在群体的压力之下。孔子当年要恢复周公之礼,希望在礼坏乐崩的年代使社会恢复秩序。他所设计的这套礼的秩序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既符合人性,也符合中国人群居的心理。这套秩序考虑到了女性的安身立命,忽略了其个体的精神自由。首先是家庭的建立不以爱情为基础,以传宗接代为目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保障的是具有名分的妻的利益。妻子也许和丈夫没有心灵上的沟通,但是可以掌管家庭的财产。即使没能生育可以通过过继的办法通过嫡长子继承制保障经济利益。但是那些和男人有更多心灵沟通的青楼女性,尽管她们更有才华,更懂得男人的精神需要,但是她们却很难获得安全的经济保障、世俗社会认可的名分。像李清照和赵明诚这样的精神伴侣世间少有,所以才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更多的才子佳人谱写的还都是爱情悲剧。身与心,灵与肉总是难以两全。
基督教对男女关系有这样的理解,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的,女人是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男人需要女人,否则会孤独。单身或者丧偶的男人很难健康长寿。一个人要和多少人一起群居才能抵抗孤独?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多大的家族可以让一个人有安全感?如果从分工的角度讲,更大的群体分工可以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但从精神的角度讲,一对相爱的人就足以使个体摆脱孤独。原来我们需要的是如此简单,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即可。这不仅仅是宗教的启示,现实生活中诸多人有这样的感受,有的时候多得超出了人的需要以后带来的不是满足而是烦恼了。但还有一部分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总以为越多越好。穷怕了的人对物质的渴求仿佛总是无止境的,害怕孤独的人总希望融入更大的群体之中,精神不独立的人很难抵抗孤独。现代女性观本质上是要追求精神上的独立。
(二)社会制度设计保障女性权益
真正两性和谐的社会应该是每个男女都实现灵与肉的和谐。家庭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更是精神成长的场所。我们的很多制度设计打着以工作事业为重的名义将家庭的分裂视作理所当然的牺牲,人为地制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是传统的幽灵盘踞在人的头脑里,对现代家庭的伤害也就是对女性的伤害。社会对男女两性的社会期望和角色塑造不同,同样是对家庭不忠诚,男人更容易获得多的谅解,甚至是女方家人的谅解;而女方则得到更多的谴责。对于女人来说,事业不成功没关系,但家庭不幸福确是很致命的。女人的幸福来源依然和过去一样有很多的支撑点,除了现代社会赋予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夫妻的感情、老人和孩子的幸福依然与女性幸福本身息息相关。每一个智慧的女人都应该经营好自己的家庭,这也许是古老的中国智慧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当然现代女性观的确定也需要相应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我们的职业制度设计不能简单考虑男女平等,对女性生理上的关心和照顾不是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也没有必要因为平等而刻意消除男女之间天然的差异。如果说经常出差的工作不适合女性,经常喝酒应酬的工作不适合女性,自然在岗位职责设计上特意考虑女性需要照顾家庭,女性需要带孩子,给职业女性以更多的宽容。因为这样的设计不仅仅是为某个个体考虑,而是从女性整体特点考虑,兼顾的是全社会和一个个小家庭的和谐。既然女性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劳动,也承担了生产未来劳动力的职责,从整个社会角度就应该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产而失去工作机会或者好的工作岗位。即使当前劳动力人口已经出现短缺,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从独生子女转变成允许生二孩,但是这种因生二孩而造成的成本代价均由女性来承担的话,那么政策制订的初衷就难以实现。这是社会层面从制度设计角度应该考虑的。
[1]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2] 李钊平.唐豪侠传奇女性观刍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100-105.
[3] 许总.也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观[J].江苏社会科学,2010(2):226-232.
[4] 孙康宜.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J].江西社会科学,2004(2):206-217.
[5] 王泽庆.孔子的女性观[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1):73-75.
[6] 汲军,朱小阳.朱熹女性观的推行与传播[J].江西社会科学,2006(9):194-197.
[7] 柯倩婷.训诫女人:儒家女教的知识生产与话语机制[J].妇女研究论丛,2016(3):15-24.
[8] 秦方.近代反缠足话语下的差异视角:以19世纪末天津天足会为中心的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16(3):63-70.
[9] 石晓玲.清代士绅家族对女性的道德形塑:以女性忆传为中心[J].妇女研究论丛,2015(5):80-88.
[10] 王小健.服制与礼俗:周代妇女“三从”的礼仪符号及制度展现[J].妇女研究论丛,2015(5):64-71.
[11] 孙玉荣.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女性教育[J].妇女研究论丛,2015(1):41-46.
[12] 单炜鸿,高乐才.论东北妇女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107-111.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Chinese Women′s Wandering Between Attachment and Independence
TANG Shanmei
(DepartmentofArtEducation,NanjingAuditUniversity,Nanjing211815,China)
To measure whether a society has confidence in its culture or not, especially whether its male elite have confidence or not, there is a very important indicator,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apart from men′s treatment about women as well as women′s own attitudes toward themselves. The so-called repression and bondage that the tradition has exerted on women in China cannot be generalized due to the fact that many ideological repressions have their specific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re was almost no repression coming from both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so women remained pure and free in nature; but in the following four dynasties includi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women were required to observe “three obedience” and to “preserve chastity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concept of women in modern society can be established by absorbing nutrition from western feminism, getting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ideas, and women′s seeking the spiritual independence.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 the design of system.
tradition; modern; attachment; independence; Chinese wome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群体行为视角的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养成:理论、测量与评价”(14YJC710036)之成果。
2017-04-07 [作者简介] 唐善梅(1978-),女,江苏新沂人,南京审计大学艺术教育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0.16396/j.cnki.sxgxskxb.2017.07.008
C913.8
A
1008-6285(2017)07-0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