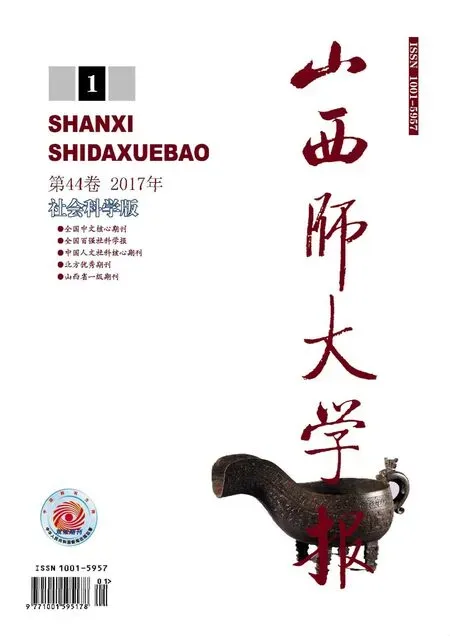论孙歌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刘 成 才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衣带水的两个亚洲大国和世界两大经济体,如何处理中日关系,不但关系到两国之间的发展,更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日两国在文化渊源上同根同源,但特殊的地缘政治以及近代以来复杂的国际纠葛,造成了两国之间深深的隔膜,阻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与深层次交往。这种隔膜不但存在于两国普通民众之间,也存在于两国知识分子之间。因此,如何消除隔膜,破除成见,建立中日知识分子对话和交流的机制与平台,进而促进两国深层次交流与对话,也就成了当下有关日本研究非常重要的学术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孙歌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会有更深刻的认同。
一、“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遭遇”作为思想原点的竹内好
作为日本现代最负盛名的思想家,竹内好在中国更广为熟知的身份是鲁迅研究专家,但文学专业出身的孙歌“遭遇”的却是“不断扩散放射能”[1]危险的思想家竹内好。孙歌认为,与竹内好的思想遭遇“改变了我认识世界的方式,改变了我在历史中寻找先知的习惯。我开始重新思考永恒的意义,重新思考现实和历史、后人与前人的关系,重新审视‘进步史观’在规定方向时的狭隘性和排他性,甚至重新思考政治正确应有的和可能的内涵。”[2]封底
所谓思想史意义上的遭遇,“只有在自己与对象都具有主体性并且都具有流动性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3]4,在孙歌看来,在思想史视野中考察竹内好一系列的行动,如出版“遗书”《鲁迅》,组织思想科学研究会、鲁迅之友会、中国之友会等学术组织,提出“国民文学论”“近代的超克”“亚洲主义”等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一系列重要论题,甚至在1960年为反抗岸信介政府强行通过日美安保条约而辞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职务等,这些理论与现实努力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寻求日本进入世界史的方式,即日本如何在克服盲目追随西方的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主体性,如何在否定自己的同时找到自己独特的“近代化”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孙歌与竹内好在思想史上的遭遇,意味着她与竹内好互为他者,并借助竹内好研究寻求自己作为主体进入历史的方法。
因此,对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孙歌推重的是竹内好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可能性的追寻。竹内好强调“我的目标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4]146,在他看来,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一生有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之前,鲁迅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是对它的准备,这一关键时刻到来之后,就决定了鲁迅直到生命尽头的人生,这一关键时刻就是竹内好所理解的“回心”。“回心”指的是鲁迅在作品中讲述的都是过去的自己,现在的鲁迅,通常在作品之外,竹内好把鲁迅的这种“回心”式的写作称之为“作为行动的文学”:“它不为既定观念所束缚,也不为理性框架所归纳,它永远在既定的结论之外。”[4]51正是这种“作为行动的文学”,才让鲁迅共享了他所身处的现代中国最基本的矛盾,一个古老而博大的文化在现代这一转折时期何去何从这一最深刻的矛盾和痛苦鲜活地呈现在鲁迅的作品中。
在孙歌的理解中,鲁迅已经成为竹内好反思与批判日本近代化的精神参照。竹内好把近代以来日本奉行的原则命名为“优等生原则”,“优等生原则”让日本从近代以来学习与尊奉的对象只是西方强国。在竹内好看来,虽然“优等生原则”让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学习西方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日本也在成功的同时失掉了作为亚洲国家的自我主体性,而主体性的丧失直接导致日本在二战中走向自我毁灭这一失却自身“历史”之路。与此相对照的是鲁迅的“作为行动的文学”“拒绝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4]206的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象征的则是中国近代在转折时的特有气质。鲁迅身上体现的正是中国近代特有的气质,近代以来的日本缺少的正是这种主体内在的矛盾与挣扎。正因为日本文化内在地不具有这种自我否定,所以近代日本才会抽象地让“傻子”去拯救“奴才”,这使竹内好非常痛心,因为“如果没有使自己成为自己、为此而与困难相拼搏的无限个瞬间,那么自我会丧失,历史也会丧失吧”。[4]183在这个意义上,孙歌坦承竹内好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如何以自我否定的方式重建主体,以及如何提防“抽象”的侵蚀。也就是说,与竹内好在思想史上的“遭遇”,让孙歌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在瞬间进入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的真切方法,竹内好已经成为孙歌作为主体进入历史的思想“原点”。
孙歌在思想史研究中与竹内好的“遭遇”,对今天中日两国的知识界都有着启发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竹内好所面临的日本的时代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转变,反而变得更为严重了。当下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同与追随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对亚洲的认同感,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也主要集中在欧美等西方强国,对亚洲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主体性的构建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研究。因此,孙歌与竹内好遭遇时感受到的以自我否定的方式重建主体,对中日两国知识界依然具有警醒意义。对竹内好来说,“日本文化作为日本文化而存在,是不能创造历史的……日本文化只有否定了日本文化自身,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化。”[4]176对中国的研究者也同样,只有在否定自己的同时才能“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也才能真正进入自己的“近代”,进而在否定的基础上重构主体。只是,这一否定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但对研究者来说,这一痛苦则是时代赋予的重任。
在这个意义上,重读孙歌多次提及的有关竹内好的著名插曲,就特别值得我们深思:著名汉学家增田涉在竹内好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时心脏病突发随之而去,竹内夫人照子不由在心里唤道:夫君,请你罢手吧![5]216在当下这个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面临着时代提出的艰巨任务,研究者对“中国”主体的追问还不能轻易地“罢手”,唯有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去重建主体,才是研究者进入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真切的方法,以及研究的真实生命与意义所在。
二、“作为方法的亚洲”与构建“东亚知识共同体”
孙歌的日本思想史研究,重点关注的是竹内好、丸山真男、沟口雄三这些日本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学者,沿着他们的研究路径进入日本思想史,并逐渐搭建起有关“亚洲/东亚”的论述体系,试图构建东亚知识分子基于共同的历史和现实处境能够共享的“东亚知识共同体”。在孙歌的理解中,虽然“东亚”和“亚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域概念,但由于东亚是“亚洲”论述最大的产地,特别是东盟的成立及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与中国(10+1)以及东盟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韩国、中国、俄罗斯、印度9国和欧盟形成对话伙伴关系等一系列东亚区域合作机制,更在客观上强化了区域性的“亚洲认同”,所以,思想史论述中的“亚洲”与“东亚”是几乎相等的两个概念。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亚洲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亚洲崛起”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但是在当代中国,把当代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单位来讨论并构建所谓的“东亚知识共同体”进而形成东亚意识,却面临着很多艰难而尴尬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虽然中国社会一向不缺少“东亚”论述,但只有在经济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时,“东亚”这一范畴才能在中国的舆论和思想乃至理论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况且,经济视角中的“东亚”是以现代化程度作为论述指标的,对很多现代化程度不高的东亚国家来说,存在着明显的偏颇。
个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传统的天下观对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中国在潜意识中被当然地当作亚洲的代表来看待;另一方面,最早提出亚洲论述的日本,把这一最初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概念赋予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战争,其联合亚洲各民族对抗欧洲霸权的理论意图被转换为日本“代表亚洲”的军国主义阴谋,给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带来了难以遗忘的战争伤害。在此背景下,讨论作为共同体的“亚洲/东亚”,自然会在知识分子心中激起对战争责任的警醒与追问。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中国自从被迫融入世界“现代”起,在知识分子心中,中国的核心问题一直就被认定为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中国要实现“现代”首要的任务也是学习西方,进而超越西方,而与近邻的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问题几乎没有出现在知识界的知识生活里。所以,在知识分子的理论视野中,中国作为当然的亚洲大国是不需要亚洲论述的。这导致了“亚洲”论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中一直难以摆脱实体化的意识形态陷阱而成为真正有效的思考和认识的方法,也使得论述中的“亚洲”概念充满着歧义性和暧昧性。
作为“东亚知识共同体”的主要推动者和理论阐释者,孙歌认为虽然“亚洲/东亚”概念充满着歧义性和暧昧性,但中国知识分子对“东亚”的漠视已经引起了非常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深入讨论“亚洲问题”并形成与韩国、日本等国家知识分子共享的“亚洲”思考,建构“东亚知识共同体”,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紧迫性。
在孙歌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东亚思想资源漠视所带来的最直接的负面效应,就是知识分子在处理与东亚国家共有的历史的时候,局限在从感情纠葛去理解二战历史,这种非常肤浅的历史理解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与朝鲜半岛近代以来思想历程的惊人的无知,致使我们本应与东亚各国的知识分子共享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却因为战争伤害而背负着沉重的过去,甘于占有各自的历史,无法正面清理这段复杂历史,这也使得我们与日本、韩国这些东亚近邻之间的“距离”远远大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因此,构建“东亚知识共同体”,追问“东亚”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可能的问题,“不仅事关区域一体、民族和解、经济共荣之类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对‘合’与‘分’的简单理解,培养对国际关系问题更深刻、更理性的观察角度”。[6]
所以,孙歌在亚洲研究中特别警惕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而导致“亚洲”在被抽象了的情境中变成一个不及物的概念,变成一个为使用者提供安全感的符号,甚至变成某种话语上的霸权进而成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论证,如何使“亚洲”摆脱实体化的陷阱而真正成为有效的方法,是她在推动“东亚知识共同体”建构中主要的理论努力。在她的理解中,由于“亚洲”叙述容易被知识者不加反省地用于对亚洲的自我肯定进而对抗以西方为中心的叙述,反而更容易被知识分子建构为新的话语霸权以支持某些现实的政治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孙歌认为东亚三国的知识分子也会在这种霸权关系的形成过程中扮演同谋的角色。
孙歌关注的例子是日本生态史学者梅棹忠夫和比较经济史学者川胜平太的亚洲研究。梅棹忠夫在西亚和南亚旅行听当地人说“咱们都是亚洲人”时,觉得当地一切都与日本不同,他因此认为决定国家之间差异的是生活样态,并据此把西欧与日本划归为第一地域。比较经济史学者川胜平太则呼吁日本应强化与海洋国家的经济文化联合,从而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文明。梅棹忠夫与川胜平太虽然不是右翼知识分子,但他们的理论却潜在地支持了“日本优越论”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亚洲”研究也在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形成中扮演着同谋的角色,孙歌因此追问:“在今天地域史研究与解构国民国家的思维定势日趋强固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会因而轻视了历史紧张本身对我们宿命般的渗透?”[7]
正是因为这种追问与警惕,孙歌非常推重韩国学者的“东亚”论述。白乐晴的“超克分断体制”理论[8]犀利指出当下朝鲜半岛被分成两个独立政体,其背后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朝鲜战争,他认为这种现状也是南北政权及周边国家自觉维系的结果,因为各方都从这种被分断的体制中获利,因此都不会积极促成朝鲜半岛的统一。为了“超克”当下的这种分断体制,白乐晴呼吁把朝鲜半岛等作为周边国家纳入考虑范围。与白乐晴的理论思考相呼应的是白永瑞“双重周边视角”东亚观,即“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迫走上非主体化之路的东亚代表的周边视角,以及被东亚内部等级秩序所压抑的东亚代表的另一个周边视角”[9]26,在他的理解中,“将朝鲜半岛等作为周边国家的视角纳入考虑范围之内不是为更多地积蓄亚洲的知识,而是与东亚成员主体的责任感相伴的真正意义上的联合”。[9]278故而,他大胆地提出实现东亚和解的理论设想,认为“实现真正的和解与和平,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东亚每一个人的责任”。[9]245孙歌认为,虽然韩国学者的“东亚”论述在现实政治下只是一种理论努力和美好愿望,或许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但他们的理论思考却不会把追究战争责任和强调不要遗忘历史等行动导向仇恨,并通过自己的理论思考为这个残酷承担历史责任。
与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思考相比,中国知识界的亚洲思考依然局限在已有的思维定势里,与韩日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还没有建立最基本的理解与沟通,中国知识分子对“亚洲/东亚”思考的漠视背后暗藏着的是知识分子对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肤浅理解,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处理现实政治问题的局限性。在孙歌的理解中,这意味着东亚各国知识分子要想达成真正的对话,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不仅仅是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更重要的还必须面对知识分子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建构是孙歌进入现实的入口和方法。但是,孙歌在“亚洲/东亚”研究中只做认识论的讨论,因此,她不给我们提供某种确定性的结论和读者可以直接使用的关键词,提供的是用常识无法生产的视角和方法,我们从她的“亚洲/东亚”中发现的是自己看待问题的局限性以及对自己的反省与批判,这是孙歌的“亚洲/东亚”研究更具有理论启发性的意义所在。
在这个层面上,孙歌认为“亚洲/东亚”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现实世界格局中弱势群体对于平等与自由的政治诉求,而且是打破西方式均质化普遍性想象的理论诉求。”[10]67而对知识分子来说,“亚洲”思考以及“东亚知识共同体”的构建,则是打破自己思维局限性与自我批判的媒介,知识分子应在这种思考中介入现实,承担起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
三、知识的存在方式及知识者的时代责任
特殊的地缘政治以及中国被侵略的痛苦民族记忆,造成了中日两国之间深深的隔膜,这种隔膜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两国之间的正常交流。而如何消除隔膜,破除成见,建立两国知识分子深层次对话与交流的平台,进而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就成了当下有关日本研究非常重要的学术使命。孙歌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构建中日两国之间对话平台的努力,进而拷问知识的存在方式以及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
由于被侵略的痛苦记忆,“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被作为一个拒绝承担侵略责任的整体而顽固地存在着。可惜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这场侵略战争进行反思的时候,也受这种固化印象的影响,只局限于立场上的表态而未能进行深入的探究,这种思维上的惰性在降低知识分子思考水平的同时,也在阻碍我们对历史的深入探究,进而成为我们进入自己被侵略历史的障碍。孙歌认为,在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上,就非常集中地暴露了两国知识分子以不同形态存在着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和对于战争历史的肤浅态度。
作为中华民族被侵略残杀的证据,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具体历史事件,它已经演化为中国人对战争记忆的象征符号,昭示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以及战后影响中国和日本关于这场侵略战争记忆的情感符号。正因为这种被符号化了的情感记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在处理有关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时才特别注意那些能够“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11]前言的信息,也正是这一潜在的情感需求使得在日本国内没多少反响的东史郎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在孙歌看来,《东史郎日记》的主要内容是东史郎记录他侵略中国时在华北、华东、东北、中原辗转流窜的经历,而在这些记录中,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内容只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即使是在这很少的内容里面,记录的也只是日军屠杀中国士兵,并没有日军在大屠杀期间对南京普通百姓的残杀。这也就表明,中国媒体和知识分子把《东史郎日记》当作南京大屠杀证据来极力宣传时,其实对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暴行的指证力度是非常有限的。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把东史郎塑造成反省侵略的真正英雄形象时,所遗忘的恰恰是战后日本国内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反思,如家永三郎对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侵略历史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诉讼官司。可见,由于既定的日本想象,中国的传媒借助东史郎再一次强化了民族记忆的创伤,但却遗忘了那些对日本侵略历史真正进行反思的学者的理论与现实努力。中日知识分子和传媒对待《东史郎日记》的不同态度,对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处理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能力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中国传媒和知识分子对东史郎的声援中,日本人因不反省战争责任被看作一个整体而遭受谴责,并被简化为仇恨的象征符号。在这种被简化为象征符号的整体性想象中,中国传媒和知识分子忽视了日本国内知识分子为阻止国旗国歌法案通过进行的艰苦斗争,以及他们为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一系列努力。这些日本知识分子的行为有力地反驳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对日本人的整体想象。当然,在日本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中国”概念中,中国也被想象成一个没有议论自由和没有司法独立的整体。
中日双方知识分子和民众在这种彼此整体化的想象中,争执的关键集中表现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上。在孙歌看来,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对有关大屠杀的文献和材料进行考证,而完全不会顾及那些大屠杀幸存者对这场历史事件的情感记忆。孙歌在研究中追问的是这种历史学的绝对合法性,因为这种历史研究所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感情记忆的丧失,而丧失了感情记忆的历史往往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死知识,不具有对现实的生命意义,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利用,成为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持者。当中日双方的知识分子为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字争执不休的时候,有关侵略和反侵略历史的真正反思已经被忽略了,而有关大屠杀的研究也只能游离于表面,不能被有效地组织进对当下时代状况的讨论和思考中去,研究的结果也只能无奈地被简化为抽象的仇恨记忆符号,最终避免不了因这种抽象的符号化而被遗忘的命运。
而当中国知识分子纠缠于这种被简化了的感情记忆的时候,其实失掉的是与日本国内的有识者共享这段历史进而促使思想形成的真正契机。同时,在孙歌看来,在这种被简化了的感情记忆背后,暗藏着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化的冷漠与无视,这种思维背后的逻辑与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崇拜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元化思维方式,它让知识分子推崇暴力性的思考方式,而不鼓励平等与多元化,这种思维方式也是鲁迅和竹内好所尖锐地讽刺过的“奴才心理”。
而对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只有摆脱这种被抽象所简化了的情感记忆的思维局限,把日本变成一个独立而平等的研究对象,进而把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变成我们思考与反思历史的“方法”时,才能有机会与日本学者共享这段双方共有的历史,也才可能真正进入自己的历史,我们也才能真正找到“自己”,进而走向世界。可惜的是,在孙歌看来,当下知识分子有关日本的研究显示,我们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来面对这段复杂的现代史,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处理这个时代留给研究者的沉重的“中国课题”。
因此,孙歌比较看重沟口雄三对中日知识共同体的理解,“知识共同体,极端地说,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经常提出和发现问题。所以,我们并非在制造一个团体,而只是在制造一种知性之间的对话。”[12]对中日知识分子来说,不断地追问知识的存在方式以及自己的社会责任,不断进行自我否定,这才是知识共同的基础。而如何进入与东亚各国共有的历史,如何处理纠缠着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的感情记忆,现实中的主体如何在开放的状态下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研究者在面对中日之间相互缠绕的历史时所必须承担的沉重的责任。
四、结语:思想史面对的中国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已经日益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和世界各国的联系也愈益紧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可能简单地从局部经验出发去理解中国问题了。但是,由于学科分工日益狭窄,知识被日益制度化,很多研究者只能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之内来谈论中国问题,习惯于为自己所理解的“中国”问题总结出正确的解决方法,并把自己基于专业知识所做的判断放大为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研究面对的只是“部分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地面对“中国”。
孙歌在她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从探究最基本的学理问题出发,并将学理问题的探究转换成对社会现实关键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解读,在这种解读中,我们得到的不是她给出的作为结论性的解决方案,而是她在解读过程中看待问题的方法。她的研究给我们提供的不是确定性的结论和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关键词,而是用常识无法生产的视角和方法。在孙歌看来,这正是她介入社会的方式,也是她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这种介入社会的方式看似和“中国”问题很远,但却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接近“中国”问题。
“从终极结果上来说,与生活不相联系的学问根本不存在,任何学问都是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追问出发的。”[4]270竹内好的追问让我们在面对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问题时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当代中国的命运共同跳动,拷问那些限制我们的观念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打碎那些束缚我们观念的锁链的生成方式,追问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生存在当下的时代。这既是我们生活着的“中国”提出的思想史课题,更是时代赋予研究者的重任与光荣使命。
[1] 孙歌.“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J].世界汉学,1998,(1).
[2] 孙歌.竹内好的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孙歌.文学的位置[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4]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
[5] 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6] 孙歌.歧视是最不可饶恕的态度[N].第一财经日报,2012-12-27(C3).
[7] 孙歌.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J].读书,2002,(2).
[8] 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M].林玉珍,等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9] 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2011.
[10] 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2011.
[11]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M].张国仁,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12] 沟口雄三,孙歌.关于“知识共同体”[J].开放时代,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