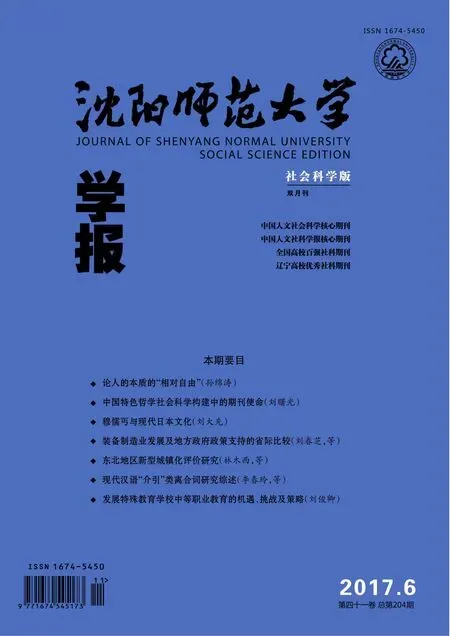伪满洲国与假亲属关系
——以穆儒丐《新婚别》为个案的考察
罗鹏
(美国杜克大学 亚洲与中东研究系,美国 北卡 27708)
伪满洲国与假亲属关系
——以穆儒丐《新婚别》为个案的考察
罗鹏
(美国杜克大学 亚洲与中东研究系,美国 北卡 27708)
满族作家穆儒丐于1942年发表在《麒麟》上的短篇小说《新婚别》不仅探索了婚姻真假的问题,而且涉及军队甚至国家的结构与本体论问题,是一篇长期被忽略又值得深入探究的作品。具体说,小说描写文英与凤姑的“虚礼假面子”婚姻可以作为当时伪满洲国社会/政治状况的一种比喻,包含了家庭、军队与国家的思想矛盾,特别值得分析的是典礼与信念对这些社会结构的创作所起到的作用。
穆儒丐;《新婚别》;国家;典礼
“我们是结婚,不是讲虚礼假面子的”[1],这句话是满族作家穆儒丐于1942年发表于“满洲杂志社”新办的文学期刊《麒麟》的中篇小说《新婚别》中的主人公赵文英结婚前说给未婚妻凤姑的话,意在强调他们是为结婚过日子,而不是“讲虚礼假面子”的程序。然而细读小说,却发现整部小说都充斥着“虚礼”与“假面子”。文英因为经济条件和漂泊的状态本不想结婚,且婚后他须立即离家,绝无有婚后生活。因此,小说描写的不是夫妻的婚姻生活,反而是该婚姻所依靠的一些“虚礼”与“假面子”及其带来的后果。
一
细分析文英不想结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更忠诚于军队。他于宣统三年(1910年)入了队,四年后收到母亲来信,劝他赶快告假回家,以便办成婚事。不过文英“不但无意于结婚,连家里的事几乎都不敢说不敢想。”[1]2他担心自己没钱,很难养活一个家庭,所以觉得自己暂时最好不结婚。但军队领导劝他赶快回家,说道:“告假结婚,也不是没有前列,何必发愁呢?”[1]3于是,文英同意了回家办婚事,不过他只能请15天假,其中包括在路上时间,所以他一到家就必须尽快解决婚事,然后立即回军队。因此,穆儒丐小说主要描写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婚后文英的妻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文英结婚是由于一些传统礼教跟面子因素,而小说强调是这些因素的后果。
虽然小说描写的主要是一些小家庭情节,却也包含更广阔的意义。具体地说,小说所探索的婚姻真假问题,还涉及军队甚至国家的结构与本体论问题。比如说,军队与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关系?国家与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理想是什么关系?此外,《新婚别》的故事虽发生在民国初期,但同时也可投射到20世纪40年代的伪满洲国历史,并且间接地反映伪满洲国背后的一些政治状况:比如,所谓的伪满洲国”中的“国”字与“伪”字有何意?
文英的未婚妻凤姑是个孤儿,寄住在叔婶家,过得颇不如意。因此,凤姑得知文英要回家娶她,自己就无比快乐。但凤姑无法理解,为何文英不能在家多住一段时间,而必须立即回军队。凤姑问文英为何非要当兵不可,为何不退队和她一起生活。有趣的是,文英的回答,强调的不是政治理想,而是他与军队的一种充满自相矛盾的感情关系。他说,他刚入队时,本觉得他打错了主意,觉得军队不适合他,但后来发现一师人“都有志愿”,于是慢慢接受了这种新的生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文英与军队的关系类似于包办婚姻,婚后慢慢地习惯了对方。反讽的是,这个比喻性的“包办婚姻”后来直接影响了文英跟凤姑真正的“包办婚姻”。他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跟新娘住在一起,是因为他非要立即回到他另外一个“新娘”——军队的怀抱。
此外,军队本身在这段时期也经历了一种巨大的改变。小说第一段就说明:
赵文英之被选入禁卫军,是在宣统三年,那时全军已然毫无遗憾的组织完竣……同时革命志士,排清先锋,别军的一位将领蓝天蔚,也想与武昌呼应,于演戏中,欲以实弹解决禁卫军,也不知道是事机不密,也不知道是主义的冲突,到底未能实行,禁卫军连夜撤回北京师[1]4。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文英由原来的支持清朝禁卫军转为支持替代清朝的民国政府,因此,他忠诚的对象主要是军队本身,而不是军队所代表的政治制度。如果把军队看成是一个婚姻的比喻,这种比喻性婚姻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的“家族”(即军队所代表的政治制度及政治理想),反而在于其“婚姻体制”(即军队系统)本身。在这里,政治理想变成一种副作用而已,是军队本身的体制。
这样看来,文英与军队的关系在一方面类似于一种传统的包办婚姻,但在另一方面类似于一种新时代的“自由恋爱”婚姻。一方面,像包办婚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文英与军队所代表的政治理想的关系是依情况而定的;不过另一方面,像一种所谓的自由恋爱中的爱情关系一样,文英为了参军就自愿地离开家并且没完全符合母亲的要求。无论如何,结果都是文英忠诚于其对象本身(即军队、婚姻),而并不是忠诚于其所代表的政治或家族理想。
文英对婚姻的十分矛盾的看法也反映在他对“定礼”与“财礼”两种传统习惯的态度。到了结婚的时候,养活凤姑的叔叔婶娘向文英家要了一笔“定礼”钱,叙述者强调那时候在北方定礼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落后的习俗:
在北京,无论城里城外,往外聘女儿,就没有一家向男方要钱的,无论家境怎样寒,全以嫁女要钱,是一件可耻的事。“财礼”两个字,在北京人大都很渺茫,一点观念也没有,不怎么姑娘叫赔钱货呢。除了真穷得没了络儿,把女儿给人作小,那当然得提钱,甚至要求养老,但是那是婚姻上的变则,也许根本提不到婚姻,一半皆以为旧式婚姻,全是买卖婚姻,可谓钱到家,还得重行检讨[1]23。
反讽的是,凤姑的叔叔就是一个“地道北京人”,但他还是坚持要一笔钱当作定礼和财礼,而文英家不得不同意。文英把钱给凤姑的亲戚这一举动,强调了婚姻所包含的经济意义,使“新娘”带上了一种商品化的含义。
虽然文英在强调自己婚姻并不是一种“讲虚礼”,可他后来接受的是所谓的“定礼”与“财礼”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虚礼”的表现。再说,当作一种典礼的婚礼本来就是一种“虚礼”,因为所有的典礼就有一种“虚假”的意义。典礼本身就是一种表演,不过这种表演可以创造真实的后果。
二
此外,文英决定跟凤姑结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孝顺母亲。他的母亲一直想要一个孙子,又因年纪大,也需要有人在家里陪她。因此,文英希望凤姑会代替他照看母亲:“只要她(凤姑)贤惠,到底能替我孝顺您。”[1]11文英这段话一面强调他对母亲孝顺,一面又说明他希望凤姑替他尽孝。即,文英希望凤姑会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担本来属于他孝顺的责任。结果,孝顺从伦理理想概念转型“商品化”,而变成一种可以传递于交换的物品。
总而言之,文英虽然向凤姑强调他们“不是讲虚礼假面子的”,但实际上,从文英接受凤姑叔叔对“财礼”的要求,到他后来让凤姑替他尽到对母亲孝顺的责任,文英与凤姑的婚姻依靠的完全是一些“虚礼”的习俗。同时,文英与凤姑的婚姻虽然不能说完全是靠“假面子”,但婚姻还是从头到尾都反应一些与面子有关的要求。不过小说还说明该婚姻对凤姑来讲还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影响了她的道德观和身份认同。
成婚以后,凤姑哭着劝文英退伍,让他留在家里与她一起生活,文英的反应十分有趣。叙述者解释说,“这时候文英,把刚被凤姑的眼泪所软化的柔肠,复兴强化起来,军人!军人!军人在模仿宝玉太可笑了”[1]27。在此,文英发现自己对凤姑的感情开始被浪漫化了,必须提醒自己一个军人不许有《红楼梦》所代表的情感。当然,文英在否认自己与贾宝玉相同的过程中,作者同时也是在提醒读者《新婚别》与《红楼梦》这样类似于言情小说的作品是多么相似。并且,像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一样:“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新婚别》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也基于读者的眼光,而不完全在于文学文本本身。
《新婚别》提到《红楼梦》这一段很像吴趼人1906年的小说《恨海》中的一个细节。《恨海》中,仲蔼的未婚妻虽然抛弃了他,然后去上海当妓女,不过仲蔼一直保持对她的“忠”。过了很久,有一天仲蔼的同事带他去上海的一家妓院,仲蔼就开始嘲笑他们:“世人每每看了《红楼》,便自命为宝玉。世人都做了宝玉,世上却没有许多蘅芜君、潇湘妃子”[3]。后来他又加了一句,说“宝玉何尝施得其当?不过是个非礼越分罢了。若要施得其当,只除非施之于妻妾之间”[3]228。《新婚别》与《恨海》的男主人公都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为婚姻中的一种反标准。但是两者中间也有重要的区别。《恨海》中的仲蔼觉得《红楼梦》所代表的浪漫感情应该保留在(男人与妻妾之间的关系)“婚姻”内,而《新婚别》中的文英却想说服自己类似的感情必须排斥到(军队的比喻性的)“婚姻”以外。但两部作品的男主人公都认为对现代婚姻而言,贾宝玉所代表的浪漫感情都是“假”的,而且是必须被排斥的。
《新婚别》与《恨海》两部作品有许多相似之处。两部小说不仅都用《红楼梦》讨论一些婚姻与爱情的问题,而且小说情节都发生在十分接近的历史阶段。《恨海》描写的是发生在1901年义和团运动时期背后的一些情节,而《新婚别》主要描写的是一些发生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一些情节,而且两部小说都用失败的婚姻来反映当时中国的政治转变。一方面,情节中婚姻的失败直接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混乱:每次都是因为叛乱或大战,阻止了试图结婚的双方(《恨海》)或导致双方婚后无法在一起(《新婚别》)。此外,两部作品中的爱人都有一方表现出比较理想的态度。比如说,在《恨海》中,仲蔼的未婚妻虽然抛弃他去卖身,仲蔼对她还是一直保持一种纯洁忠诚的态度。就是说,新娘虽然颓废,新郎还是理想化。而在《新婚别》中,被理想化的不是新郎(文英),反而是被抛弃的新娘(凤姑)。文英回军队以后,凤姑就十分辛苦地试图养活自己及她的婆婆,甚至有一段时间凤姑不得不去城里卖身。但跟《恨海》刚好相反,这里凤姑的卖身行为所表现的不是她的道德堕落,反而是她的极端孝顺及忠诚,说明她愿意牺牲自己,为了扶养自己的婆婆——即从未和她一起生活的丈夫的母亲。
这里十分反讽的是,虽然文英与凤姑刚结婚的时候,凤姑的亲戚要求“定礼”与“财礼”钱反映了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度,但婚后凤姑不得不卖身却是出于她对婚姻理想的忠诚态度。两者都是非常典型的把女人商品化的过程,不过小说中两种作法的作用与意义刚好相反。前者强调传统婚姻所依靠的一种经济关系,而后者指的是当作新娘的凤姑自我商品化以便实行一些传统伦理理想及一些当前生存的需要。
三
《新婚别》虽然发表于民国初期,但文本偶尔会提醒我们其“理想读者”并不是生活在以小说作为历史背景的晚清/民国初的人,而是生活在穆儒丐写作时的伪满洲国的读者。比如说,小说开头描写文英如何从支持清朝的禁卫军转为支持替代清朝的民国政府时,还写道:
……可是自此以后,革命排清的风潮,蜜也似的甜,醴也似的浓,醉着人们的心,济着人的口,“不推倒清人的政府,国家万不能富强,人们也万不能自由的!”真的吗?那就用不着问[1]4-5!
“真的吗?”一句,虽然这里不清楚疑问的对象是谁,但再往下有类似的疑问句,而其(想象中的)对方更加清楚:
……老百姓!真不知你们烧了什么高香,但是它们没放弃吗?……放是放了?青年的先生们也许想象不出来,我告诉你们吧,它们双方所放的机枪子弹……[1]5
在这里,描写晚清到民国的转变时,叙述者提醒我们该文本的理想读者本来就是40年代伪满洲国的青年人,并且还暗示这些历史情况对“当代”读者也许会显得比较陌生。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作者关心的不仅是这些晚清/民国的历史状况,而且是伪满洲国的社会/政治背景。
具体说,小说描写文英与凤姑的“虚礼假面子”婚姻可以作为当时伪满洲国社会/政治状况的一种比喻。像文英与凤姑的婚姻一样,伪满洲国也是在一种“虚礼”和“假面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单位。虽然伪满洲国表面上是一种独立的国家,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假国而已——一种模仿独立国家的日本殖民地。不过,就像文英与凤姑一旦结了婚双方都开始把婚姻看成是一种真实的关系一样,类似的,虽然从某种政治或法律的角度来讲伪满洲国不过是一种“伪造”的国家而已(即,伪满洲国),但是对所有属于该国家的人民而言,这个社会/政治结构还是有现实的功能跟意义。
再说,在这一方面,伪满洲国跟其他国家也有些共同之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推出所有的现代国家都依靠一种“想象的”基础,并且这种基础在某种程度总是借用人们对家庭与家族的理解作为一种思想背景。不过安德森也强调所有现代国家虽然都依靠一种想象的基础,不过对属于该国家的人们来讲,这些国家都有一种完全现实的存在。换言之,像一个传统的婚姻与家庭本来是依靠婚礼及其他的“虚礼”性典礼造成的,模仿一种大家庭的家国也是依靠许多本质上的“虚假”的政治典礼造成的。
在《典礼理论,典礼做法》一本书中,凯瑟琳·贝尔说明许多对典礼的理论都认为典礼的“内在逻辑”在于一种“对思想与做法的分化与再聚合”[4]。她的结论是虽然人家经常以为典礼会创造一种共同信念,她却认为“典礼活动并不促进信仰或者确信,反而典礼做法允许很多不同的理解,而只要求参与者接受做法在形式上的合一”[4]186。这样看来,典礼就像鲁迅眼中的《红楼梦》一样,不同读者会在同一个文本找到不同的意义。
就像鲁迅对《红楼梦》与贝尔对典礼一样,安德森认为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国家的存在不基于大家对它有一种共同的信念跟理解,而刚好相反,是基于国家本来就是一种空白的结构,允许大家对它有不同的理解。换言之,国家的核心不在于它所代表的思想或者概念,反而在于表面上的形势——只要大家能够对其形势保持一种共同的认同,他们就能够投给它许多不同的信念与概念。斯拉沃热·齐泽克则就利用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的想法,进一步地认为社会或国家不仅是空白的结构(他们说明“社会不存在”),而且认为其核心其实是一些基本的思想敌对与不一致性,而与其有关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刚好是在掩饰这些不一致性,掩饰“社会不存在”的事实,掩饰人家对它的认同的必然失败。
这样看来,《新婚别》暗示了伪满洲国不仅是一种蓄力并且伪造的社会结构,而且作为故事背景的清朝及民国——再加上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一些包含内在的思想敌对与不一致性的“虚礼假面子”的后果,而且托给这些社会结构一种现实意义刚好是这些内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意识形态系统。按照这样看来,国家与军队的模型并不是典型的家族,反而是一套假亲属关系——人家模仿亲属关系以便建立或者巩固一些新的社会关系。
[1]穆儒丐.新婚别[M]//詹丽.伪满洲国通俗作品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25.
[2]鲁迅.绛洞花主:小引[M]//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177.
[3]吴趼人.恨海[M]//张振钧.中国大众小说大系:近代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228.
[4]Bell,Catherine.Ritual Theory,Ritual Practi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6.
Manchuria and Fictive Kinship Relations——A Case Study of Post-Wedding Separation by Mu Rugai
Carlos Rojas
(Institute of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Duke University of USA,Durham North Carolina 27708)
The short story Post-Wedding Separation by Manchu author Mu Rugai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Qilin in 1942 explores not on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al and fake marriage,but also structural and ontological considerations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the military and even the nation.In particular,the story’s description of the “empty ritual and false face”marriage between the protagonists Wenying and Fenggu can be taken as a metaphor for the socio-political status of the contemporary state of Manchukuo,and specifically its reliance on a set of ideological contradictions at the familial,military,and national level.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role that ritual and belief play in constituting this sort of social structure.
Mu Rugai;Post-Wedding Separation;nation;ceremony
I206.6
A
1674-5450(2017)06-0051-04
2017-09-07
罗鹏,美国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詹 丽 责任校对: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