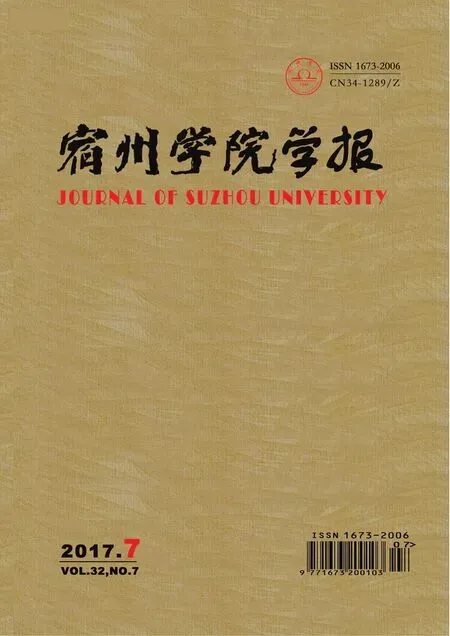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际对传统文化心态的一点反思
郭奇林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厦门大学漳州校区, 漳州,363105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际对传统文化心态的一点反思
郭奇林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厦门大学漳州校区, 漳州,363105
“爱好和平”与宣扬“同化力”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两大典型特质,旧社会这两大特质也存在消极与片面。“爱好和平”的误区具体表现:一是明哲保身,乐天安命;二是以己度人,委曲求全。“同化力”在宣扬过程中表现的片面与消极表现为:一是“同化力”取得的成绩被过分高估,掩盖了其消极与片面的部分;二是包容有余,排斥不足。所谓“以静抗动”、以“不变应万变”,实乃忍性大于钢劲,被动多于主动。
传统文化;爱好和平;同化;胸怀宽广
中华民族胸怀宽广、谦和守礼,这与传统农耕文明长期进化而形成的隐忍退让的性格不无关系。其中,为人乐道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爱好和平,二是中华民族有着极强大的融合力。这两个方面归纳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所展示出的精神特质。受自身文化系统的熏陶,这一精神特质在历史上屡建奇功——“安五胡,辟疆界”,且能以其博大的胸襟于囵囫中败敌于无形,因此也长期受到了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的推崇。客观地看,把它说成是民族的精神特质也好,说成是民族文化的特质也好,受人推崇的原因不外是出于宣扬民族精神的伟大,光大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爱国情结。然而,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却不能不看到这一精神信仰背后隐藏的消极,以及由此所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又因长期遭受人们好喜讳忧的漠视,其潜在的危害更难以小窥。
1 旧社会爱好和平之误区
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极重伦理道德的国家。历史上,受儒学泛道德主义影响,伦理道德一度弥漫在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各方面的思想始终处于道德奴婢的地位,缺乏健全的发展”[1]。从历史角度看,传统伦理道德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是为封建专制服务并以其存在为前提的;但从现实角度看,它是一种精神产物,既存在于思想层面,又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一下子退出历史舞台,而且,由于它在民族精神、思想、文化以及社会风俗方面长时期产生的隐性的支配作用,它所造成的民族心理影响也将长期存在,包括负面影响。
比如,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下的个体有如下两个特征:其一是明哲保身,乐天安命。明哲保身最早见于《诗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后儒家阐发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思想,而道家进一步将其世俗化,提出所谓“守柔处下”“全性葆真”“以无厚入有间”“安时而处顺”不与人争的吃亏哲学。然而,明为吃亏实为滑头。这种思想一度在旧社会的官场中颇为“畅销”,成为官僚政客们结党营私、阿谀奉承、卖身投靠的手段和护身符,而后来者视其为国粹的“经典”而领其衣钵者也不在少数。在这种视个人幸福、身家性命和既得利益为第一的道德中人们是很难看到有多少正能量的:官以之购仕民以之容身,该说的不说,该做的不做,不思进,先思退,人各为阵,一盘散沙。旧时期的中国社会由此积袭了多少无为守静、懦弱与堕落,亦不知消融了多少刚健奋进、无畏和志气。
如果说明哲保身是知其厉害不可为而退身自保的话,那么乐天安命则恰好为其找到一个很好的归宿。封建社会,儒、道学说教导人们放弃抗争,顺应变化,所谓“事之变,命之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欲将原本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合理化,贫富各安其位,人人均不做非分之想,收息事宁人太平治世之功。应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弱民思想与政治统治的有机结合是极有功效的:一是数千年封建体制颠扑不破;二是造就人们千百年来迂腐沉沦的状况。“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自足自得”以及“难得糊涂”的消极思想和行为不仅没有因其无为堕落而消失掉,而且还深深扎根于部分人们的心里,在民间大行其道,广为流传,还被视为“达观”的美德被人称颂。
其二可定义为以己度人,委曲求全。传统伦理道德造就以理性主义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即早启的理性和高度的自觉。历史上一直在中国文化中占主流的孔孟学说“主张心思气力用在自己一面而非向外用力,用在对付他人”[2]。所谓君子立身处世首先在于修己正身,对待他人也要反求诸己,正人先正己,以己之高度觉悟去体悟他人,以己之长度他人之长,不以己之私度他人之短。这样就养成了中国人爱讲情理的民风。但是,以己度人看到的难免多是他人的长处,凡事得从好处想,其中不好之处也多能善解,本心虽好却失之偏颇。这就是能大义凛然、不屈于淫威者古今少有,而如东郭先生之流的烂好人却不乏于世的深层原因。同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既能善解他人短处,则必怀隐忍退让,有以希求而成全之心。这样,虽立身修己,但在是非面前往往委曲求全,假如事小则图息事宁人,事大则落得全身自保。而此一举可兼收“立身”“宁人”“自保”之三功,又暗合民众长期受传统教化养成的怯懦无为的心理,“知足长乐,能忍自安”遂成了处事的良方。可是,容忍终非上策,能忍未必自安,一味地委曲求全带来的决非理想的和平,更多的恰恰是恶势力的猖獗和暴力的横行。对恶的隐忍退让,无疑是对正义的亵渎,以此做为善举,“不仅将姑恶养奸”,助纣为虐,“且将培养懦弱畏事的性格”[1]。
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忍耐力之大,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少有的。其部分原因,无不与以上两个特性有关。“中国传统观念向以苟安、柔弱为教”[3],所尊奉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个是“崇封建之礼教,尚谦让以弱民性”;另一个是“以雌退柔弱为教,不为天下先。”[4]梁漱溟认为,“国人安于所遇”,遇事“彼此调和妥协”,“力求平稳妥帖,不肯走极端”[5]207-208,所谓“宁忍辱,恶斗死”[6],实在是近代国民性格的一个生动写照。然而,如此之懦弱不尚力,却为中国人赢得了爱好和平的声誉,岂知民以德而懦,国因民而弱。近代以来,“外人一向把中国看作是和平文弱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也不加深究以为是一种美称,以为是超出野蛮的高度文明的表征”。然而,和平文弱终不是船坚炮利的对手,委曲求全总归是一相情愿,爱好和平,和平却偏偏离你而去,苟安忍耐,又怎敌得过弱肉强食者的吞噬。百年近代史,一纸沧桑泪。先有八国联军,再有日本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各怀鬼胎难以联合,故此西摩尔慨叹:以列强之武力亡中国实属下策。然而,当时人却不解:八国联军最终难奈我何。日本,一东瀛弹丸岛国却久逞寇志,屡屡有欲亡华夏之野心,原因何在?实窥中国民心软弱可欺罢了。
其实,爱好和平本无可厚非,然总以己腹度他人之心,焉有不偏差之理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从小如若受此“博爱”的教育,自居大国欲怀天下心而播中华文明于世界,恐怕理想空大难切实际,放松警惕自不必说,心理和意识上也会输人一酬。
2 “融合”不只是伟大
为中华民族胸怀见证的另一伟大是:中国文化的融合力极强。其一,“当他统治异族时,固常能使其同化融合于自己——不独以武力取之,且以文化取之”;其二,“就在他被统治于异族时,由于异族每要用他的文化来统治他之故,卒亦使其同化融合于自己——先失败于武力,终制胜于文化”[5]309。而后者尤凸现国学之博大精深、伟岸宏厚,深为传统社会文化所推崇和赞赏。之所谓“征服者终成被征服者”,这一说法尤其为“中华武功”竞势不如人而愤愤然的某些国人报了不平,甚至油然而生自豪感、优越感。客观地说,中华文化悠久绵长,其伟大之处,就“融合”“同化”一说也只显示其一个侧面而已。但现实中的历史是无情的,在总结它的“个性”、 褒贬它的得失的时候, 有限的文字毕竟无法掩饰曾经的一幕幕“山河破碎”“哀鸿遍野”以及人民流离失所的事实。当然,也无法向人们展示这其中看似伟大豪迈,实则悲壮忧伤的无奈。诚然,不可否认,今天我们国家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的形成得益于此,但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过去的经验未必适宜于现在,也更难适宜于将来。应该看到,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处逆境而终能同化异族——“反败为胜”,原因主要还是当时中原的汉文化要远远领先和高于入侵的异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异族每要用到他的文化来统治他的”[5]208缘故。这其实是文化上的差距而造成的一种自然趋势,即落后的要向先进的学习,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并保证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如若换一个角度,设想当时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文化上领先的不是我们而是入侵的异族,其结果就难免堪忧了。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我们历史上曾经取得的成绩?成就毋庸质疑,不用刻意渲染就摆在面前,因为大家都喜欢的缘故而日渐发扬光大,因此往往被人估高。估高其实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我们却很难再看到它的另一面——隐性的消极的一面,这包括其本身的缺陷和它带来的负面影响。
梁启超晚年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曾指出中华民族的同化力特别强大,其主要意思说:一是中国地广人稀,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容纳力;二是“文化体系即立,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受其含盖,难以别成风气”;三是中华民族爱和平,尚中庸,素以平天下为己任,国家观念淡薄,对他族的习俗一向很是尊重,“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囿,而欢迎新份子的加入”,“故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四是我之文字不能不被用作“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之条件下,渐形成一不可分割之大民族”[7]。应该说,这些特点从思想文化方面较客观地概况了中华民族有容乃大的个性,尤以第三点更为生动、精辟。梁启超所言,中国地大人稀,自然容纳力强。这在当时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却不能把它认作真理。要说自然容纳力强,几百年前可以这么说,但几百年后的现在就不能这么说了,一是此间土地本身容纳力会有一定的限度,二是中国本身人口数量的增长更是个大问题。梁启超说中国之文化体系可涵盖他族之文化体系使其难成风气。但确切地说,所谓的“同化”也就是融合,不见得我之体系全存彼之体系就尽失,而是彼融入我,我亦受其影响,只不过其中主次成分有别罢了。说难成风气,是说此一主次格局难以打破,历史上我们的文化远高于对手,而在今天却是以经济、军事、科技和综合国力的对比为依托,同时还要面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侵蚀,这一优势显然难以继续保持。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的文化优势不被动摇,但是敌手若以残绝之手段必欲亡我而后快,这时区区文化岂不孱弱?假使说是中华民族爱和平对他族一贯尊重的品质能一定程度地减消敌方的对抗,但疑问是,这能否保证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敌人都管用,抑或就不被当做软弱可欺而加以利用以资侵犯、宰割之目的牺牲品。
应该看到,尽管我们的文化精深宏厚、理性见长,但某些时候优点往往也正是缺点:古老的农耕文明塑就了中华民族稳健内省的文化个性,但包容有余排斥却不足。所谓“以静抗动”、以“不变应万变”,实乃忍性大于钢劲,被动多于主动。的确,历史上我们曾以如此之“被动”与“忍性”同化过一些民族,赢得过一定的胜利,但这硕果的背后何尝不是浸透着武力不济、受制于人、含辛茹苦、忍辱投身的沧桑与无奈,即使最终不被灭亡而“翻盘”获胜,这其中又有多少胜算不是寄托在敌手疏于防守、麻痹大意的侥幸因素上?中华民族重道德自省、内力取胜,素以“隐忍退让”“委曲求全”行事,每每希望通过自己的“息事宁人”,甚至不惜被动挨打来换得他方的同情而罢手,和的观念远重于战的观念,只知以和求“和”,不知以“战”求“和,甚至大敌当前亦心存侥幸,望得他途以求豁免,不思进先思退、自缚手脚,结果往往被动,受制于人。今天赞美我们“同化力”强的时候是否应该把这一切也赞美进去呢?
3 结 语
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与儒学道统的结合,使得数千年中国历史无不浸透着“民懦国弱”的气息,又因封建制度下的武力对内多余对外不足,防民甚于防川,情形更是雪上加霜,尤以近代面临瓜分豆刨、国事岌岌可危的局面为最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受制于人的历史。但我们的任务依然严峻:昔日的列强还窥雎四周,昨天的敌人依就企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尽管我们的经济、军事、科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思想上的警惕意识不仅不能松,而且更需要加强。历史上,我们吃了软弱退让、被动挨打的教训,但今天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思想依就应受到批判。应当承认,传统文化泽惠后世的同时也有它不可否认的缺陷,所谓不破不立,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际,更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揭开那些似是而非的面纱,检视其遮蔽的弱点,为我国文化强国的建设之路提供更多现实和有益的启迪。
[1]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
[2]梁淑溟.今天我们应该当如何评价孔子[M]//东方学术概观.成都:巴蜀书社,1986:95
[3]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65
[4]陈独秀:答李大槐[M]//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625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6]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M]//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23-24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1-2
(责任编辑:刘小阳)
K1
:A
:1673-2006(2017)07-0006-03
10.3969/j.issn.1673-2006.2017.07.002
2017-04-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国从海防到海权的思想衍变研究”(14BZS053)。
郭奇林(1974-),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