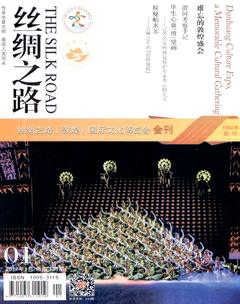至今犹忆李将军
薛俱增
耤水之南,文峰山阴有故堆,长眠天水南山阿,李广也算是魂归故里。
中国人说李广,会加一个前缀——“飞将军”。许多人还会想到“龙城飞将”。读过史书的人都知道,“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 成纪,即今甘肃天水一带。当地人无需翻史书,就说李广是“曹(我们)天水人”。天水市区,至今还有“飞将巷”等地名,可见家乡人民对李将军的缅怀和爱戴。
李将军的事迹,煌煌典籍,悠悠众口,已经说了2000多年,早已不必多说。这位19岁从军,体格魁伟,虎背猿臂的“良家子”;这位精于骑射,胆略过人,亲射虎,石没镞的神射手;这位一生清廉,家无余财,爱兵如子,“宽缓不苛”的指挥官;这位戍边44载,身经70余战,匈奴口中的“汉之飞将军”;这位历任八郡太守,一生不得封侯的沉默寡言人;这位时乖命舛,迷途失道,最终饮恨自刭,尸骨湮灭无闻的白发老将军;这位死后“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的绝路断肠人……诚如太史公所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千秋万载,只要有人类在,他的事迹和精神必将口耳相传,汗青相续,永远传说下去。
初冬。午后。拜谒李广墓,正好。
初冬,落叶几乎凋尽,没有萧萧秋声之乱耳,没有悲情霜叶之炫目,万物收敛沉潜,一切删繁就简,但还不过于肃杀,人的心绪也更加清宁。
午后,冬阳暖暖的,人世多好,活着多好!就算面对着一个墓园,也不过于凄惨;就算面对着一段冷酷的历史,因着后背的温暖而平添直面的勇气,好比一个幽深的寒潭,因为阳光的折射,使人觉得那潭水并不砭人肌骨,而有了跳进去一探究竟的冲动。
李广墓,全国仅此一座,位于山脚二级台地,被村庄包围。进入石马坪村,顺巷道上坡,走2里路即到。正值拆建改造,土石狼藉,路边也缺少必要的指示牌,以致来访者往往于村中迷失方向。李广出征,正是因军中缺少向导而迷途误期,酿成千古悲剧。世路艰险,紧要处真的只有几步啊!
李广墓园近期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和早年的荒凉破败相比,如今规划严整,气象更为肃穆。门楼高耸,斗拱巍峨,园内古柏森森,翠竹冬青高低掩映。展厅正门,朱漆大匾上书“飞将佳城”,两边是清人联句:
虎卧沙场,射石昔曾传没羽;
鹤归华表,树碑今再赋招魂。
展廳里,有明清时期的李广画像,均据史料摹画,可以一睹将军威仪。明代为黑白,清代为彩绘,均为坐像。耐人寻味的是,画像中的李广均身着蟒袍。明代,蟒衣是皇帝对有功之臣的“赐服”。清代放宽限制,蟒衣列为“吉服”,凡文武百官,皆可穿用。李广一生未封侯,却蟒袍加身,反映出民间百姓的愿望指归。
展厅内存有碑石一通,上镌“汉将军李广墓”,系清代乾隆四年(1739)于墓场前所立,碑石已有残损,字迹模糊。有李广古印模真迹八方,系历代出土与国家收藏。有李广的官方印信五方,分别为:雁门、北地、云中、陇西、天水太守章,封泥殷红清晰。其他三郡的李广太守印信惜未面世。金石寿久,难以磨灭,它们真切地昭示来者,李广是一位真实可信的历史人物。展厅内的诗书画作都是对这位“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的悲剧英雄的赞颂、景仰和叹惋。毛泽东也曾手书王昌龄《出塞》诗,且作“向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改“但使”为“向使”,盖有深意在焉。
墓道两旁的草地上,伫立着两匹汉代石马,造型古朴,风格粗犷,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可惜这两匹无辜的石马,已被谜一般地斩首,只剩下阔大的肚腹和浑圆的臀部,展现出掩饰不住的力量与速度。它们是在哀鸣思战斗吗?是要奋蹄踏匈奴吗?它们遭遇了和主人一样悲惨的命运,却死而不倒,不离不弃地护卫着主人的坟冢,护卫着这个只有一盔、一靴、一战袍的衣冠冢!
祭厅里有新塑的李广坐式铜像,甲胄严整,神情冷峻地眺望着北方那遥不可及的远方,那里是他守卫了40多年的大汉疆土,那里是他出生入死70余次的北国沙场,那里是他引刀自刎、含恨九泉的荒漠绝域……铜像后面的背景墙上,一字一字镌刻着那篇史家绝唱《李将军列传》。司马迁,这位以笔为刀、忍辱负重的史学家,这位惺惺相惜、千古同调的悲情知音,在时间无垠的荒漠里,驱遣着一支文字大军,护佑着李广将军。
山衔夕照,残阳如血。蒋中正题写碑铭的石塔静静矗立在半球形的墓冢之前,各自投下异样的影子。墓顶上枯草丰茂,铮铮如铜丝,株株枸杞夹杂其间,鲜红的果粒在夕阳的映照下更加殷红欲滴——莫非,这就是将军孑立天地之间,横刀向天大笑的滴滴血泪?这就是将军冲锋陷阵白刃纷纷,铠甲上洒落的串串血珠?这就是将军“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的拳拳忠心?
墓门对面,是“飞将戏楼”。戏楼前,时光很慢,晒太阳的村民一堆一堆,甚至有人搬来躺椅曝背。如果有戏登场,他们一定是忠实的看官,只不知是否看彻李将军戏剧般的人生?这眼前的戏楼,身后的李广,中间等着看戏或者已经入戏的各色人等,哪一个是更真实的存在?
黄昏,没有风。墓园中,两株玉兰树早早地含笑成苞,像一颗颗烟花,静等春风来燃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