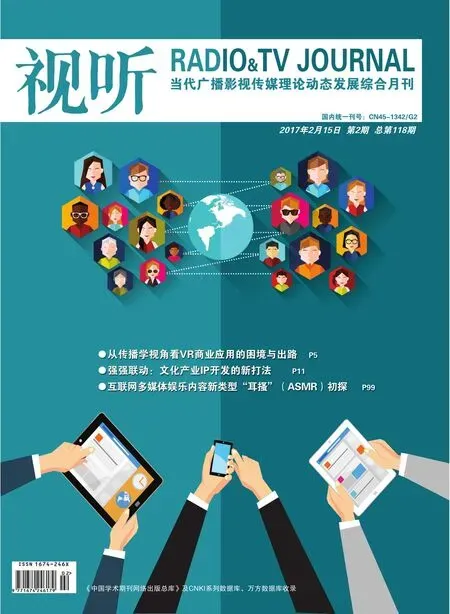内地“小妞电影”的叙事危机和瓶颈
□马彧 陈璇
内地“小妞电影”的叙事危机和瓶颈
□马彧 陈璇
小妞电影是经好莱坞舶来的一种新的电影类型,在市场上以“以小博大”著称。本文基于女性主义理论,对内地小妞电影进行人物塑造、主题内涵、价值观和文化层面的文本剖析,指出缺乏真正的性别视角和女性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内地小妞电影遭遇叙事危机和瓶颈的重要原因。
小妞电影;女性主义;叙事危机
小妞电影(chick flick)是经好莱坞舶来的一种电影类型,主要讲述以女性为主角的都市故事。一般认为,1961年由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主演的《蒂凡妮的早餐》(Breakfastat Tiffany's)是全球小妞电影的先行者,随后《西雅图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1993)、《律政俏佳人》(Legally Blonde,2001)、《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等一系列影片缔造了小妞电影的经典范本。而2009年一部由金依萌执导、章子怡主演的《非常完美》成为内地首部“吃螃蟹”的小妞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美女漫画家试图夺回劈腿男友却最终发现真爱另有其人的故事。“它(小妞电影)的前身是Melodrama(家庭伦理剧或情节剧),它的血亲是Romance(爱情片)。”①但它与爱情片却不完全等同,小妞电影还时常表现女性在人生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因此也表达自我成长主题。
小妞电影是女性电影与都市爱情片融合的一种新的亚类型影片,本身没有表达女性主义电影所涵盖的愤怒情绪,也很少具备女性主义锋利严峻的批判性质。在性别冲突这一层面,小妞电影追求的是一种两性平等、认同与尊重的和谐关系。但是,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我们发现,近年来中国内地小妞电影所构建出来的两性的和谐、理解与平等,其实是建立在牺牲女性独立和自我主体意识的精神层面基础上的。
一、迷茫困境中亟待男性“拯救”的女性
《滚蛋吧!肿瘤君》中乐观坚强的熊顿在影片遭遇了男友背叛、身患癌症的双重打击,《亲密敌人》中艾米因为男友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自己而赌气分手,《等风来》里程羽蒙因为职场失意而被“流放”尼泊尔……小妞电影中的女性大都存在情感缺失的迷茫状态,她们或事业受挫或爱情遭受打击,失业、失恋,而影片正是借助于这样的契机才能顺利展开叙事,比如《非常完美》中苏菲遭遇了爱情被明星插足的窘况,心有不甘的她誓要与其开展一场“夺爱斗法之旅”,然而不管她再怎么闹腾,最终都需要在男性的援助下确立自我。《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文佳佳用奢华物质筑起情感的堡垒,看似从物质枷锁里走出来,最终却依旧与郝志定情在帝国大厦,“家庭成为叙事最后的中心,成为重归男性秩序的象征。”②《我愿意》中的唐微微是个事业有成的优秀女性,然而年过二十的她不免会陷入“大龄剩女”的社会怪圈,在闺蜜的屡次安排下结识了人到中年的杨年华,完成了从焦虑女青年到安稳少妇的转变过程。现阶段的小妞电影中,不管女主人公是亲近可人的淑女、神态优雅的女神,还是不拘小节的女强人,都会在心理困境中呈现茫然无助的状态,像热锅上找不到方向的蚂蚁一般无所适从,然后等待男性骑士的完美救赎,从而获得内心伶仃忧虑感的缓解。“小妞”不具丝毫侵略性,作为男性的“附属角色”存在,这证明女性其实从未挣脱女性主义者莫尔维(Laura Mulvey)提出的“凝视”的桎梏。
小妞电影在内地发展的近七年时间内对传统的性别范式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流动与变更。比如“女汉子”形象,她们直爽开朗、行事果敢,形象上常常是短发,平板身材,女性特征(丰乳翘臀)不明显。但是,这类去女性化的女性,其内心的恐惧和对自我的否定感比遵循男权准则的“正常女性”来得更为强烈。《撒娇女人最好命》中张慧为了追求呆板的龚志强硬是苦练撒娇技能,《失恋33天》中的白百荷则更因为“不够女人”使男友出轨其闺蜜。
在这一类电影中,身为“拯救者”的男性,则以另一种阴柔的形象出现,最终与女主角呈现一种新型的性别和谐。这看似颠覆了原有的性别刻板印象,但事实上,这种非此即彼的性别倒错恰恰又证明了性别之间的壁垒坚实无比,愈发强化了性别区隔。只是将原有的刻板印象中的男女形象、性格特征颠倒而已,并没有真正颠覆什么。正如戴锦华所说,“类似影片的表达常在逃离一种男性话语、男权规范的同时,采用了另一套男性话语,因之而失落于另一规范。叙事的窠臼成就了关于女性表述的窠臼。不是影片成功地展示了某种女性文化的或现实的困境,而是影片自身成了女性文化与现实困境的症候性文本。”③
小妞电影中的男性有别于传统电影的侵略性的、大男子主义的形象,他们或是流落异国他乡的魅力大叔或是文青气质浓郁的二手古董商贩,是时尚文化语境里不折不扣的“暖男”。《非常完美》里摄影师常瑞在苏菲摔伤后的悉心照料让人谓之“暖”,《命中注定》中冯大理明知方圆对自己无意却依旧一心帮她寻找“宋昆明”也让人谓之“暖”。虽然他们外在的表现形式迥然有别,但内里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作为拯救女性的骑士形象而出现的。这一形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泰坦尼克号》(Titanic,1998)里深情不羁的杰克到如今更具诱惑力和实用层面的“暖男”,人物内里的本质仍然是万年不动的骑士。
阴柔男形象是骑士类型的时代变种,在他们身上能够察觉到更为细腻的女性特质,当然他们在片中的“功能”还是以救赎女性为主。《失恋33天》的王小贱,为人刻薄、挑剔、阴损、爱化妆(这都是一般认为女性才具备的特征),但他能在关键时刻守护在黄小仙身边。他作为小仙的临时男友在表现婚礼救场的戏份时一路高歌猛进,顺利地将整个剧情推向了高潮。末尾王小贱表白时的一句“黄小仙,我陪着你呢”则将英勇的骑士精神发挥到极致。所以阴柔男和女汉子的搭配看似是性别倒错,但事实上在男女本质的附属关系上并没有太大改变。
还有一种与性别倒错相似的结构是姐弟恋,《一夜惊喜》中张童宇救米雪于陡峭的小山坡,时刻陪伴米雪并保护她的安危。小妞电影的感情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男性,而女性则一直被影片放置于低于男性的次要地位。无论“小妞”们如何努力,都依然被剥夺了通过自我途径获得幸福的权利。
二、爱情主题无益于女性自我认同构建
在叙事策略上,内地小妞电影通过依托类型化的爱情主题来规避叙事难度,使主题被局限在浅显的表层阶段,而对爱情母题的单一阐释无益于建构女性的自我认同。“身份意识是表述主体性的重要方式,对具体身份的探求是认识自我、确立自我的渠道。”④而女主角身份构建的过程中,大多数依赖于外化的符号和男主角骑士般的爱情。
小妞电影中的女主角都仿佛是因爱而生,将爱情和婚姻视作毕生最大的愿景。《杜拉拉升职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杜拉拉依靠自身努力获得升职后并没有发自肺腑的喜悦,因为她和王伟的爱情迷失了,而她最后与王伟在泰国相遇时才真正焕发活力。因此影片传达给观众这样一个观念,如果主角最后没有重逢,那杜拉拉余下的日子就都如行尸走肉般消极存在,没有爱情滋润的女性便不配得到生活的礼遇。
对比一些国外优秀的小妞电影,爱情在《西雅图夜未眠》中是安妮倾听电台时触动心弦的感动恸哭;在《乌云背后的幸福线》(Silver Linings Playbook,2012)中是能豁出去为彼此做同样疯狂的事;《实习生》中,安妮·海瑟薇选择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尽管她的丈夫出轨了,但影片并没有用简单的“仇男”“渣男”情绪来应对,相反,影片对丈夫给予了同情之理解,因为他也陷入妻子创业成功、自己成为家庭煮夫的困境当中,最终他们实现了对婚姻、爱情、事业的更深入的理解。《再次出发》(Begin again,2015)中遭遇男友出轨的音乐才女格雷塔和失意潦倒的音乐制作人丹和相遇在纽约的街头酒吧,双方凭借对音乐的默契合作完成了彼此的相互救赎,这种感情,似乎比爱情更厚重。格雷塔拒绝了男友的回头,无意再作为男性附属物品的她渐渐在音乐中寻回曾经丢失的自我认同,从而拥有了较为完整的人格属性。
内地的小妞电影中,尽管“小妞们”都是现代都市白领女性,经济独立,拥有一个职业身份,甚至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但她们的“职场”身份只不过是帮助展开叙事的一种手段,并不因此赋予女性其他独特意义。女性职场的表现多数情况下只停留于符号的表达上,比如出场的气势、高大上的工作场景等等。而故事一旦展开,所谓职业身份的女主人公身上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她开始像一个没有工作、没有事业、无所事事的悬空人一样,只知道寻找爱情,除了爱情,她什么都不操心。《剩者为王》中职场几乎成了盛如曦和马赛情感发酵的最佳场合。被誉为“职场教科书”的《杜拉拉升职记》,在改编成电影之后,为了强化职场菜鸟杜拉拉与销售总监王伟的办公室恋情而将职场进阶过程置于边缘地位。片中唯一能表现杜拉拉工作能力的是她主持公司的一次搬家活动,而这场“搬家混战”也不过是为接下来王伟与杜拉拉的单独相处做前期铺垫。
内地小妞电影以爱情为唯一主题,首先当然根缘在于当代都市文化女性自我主体身份的缺失,但从期待视界的角度,类型电影暗示受众接受并认同这种观念或人物,将现实世界与自己和银幕上的人物合二为一,互相缝合。然而,这种期待视界又反作用于类型电影的创作,成为类型电影创作的桎梏或枷锁。
从上述角度出发,由“小妞专业户”汤唯参演的《华丽上班族》具有独特的意义。它至少揭示了“小妞们”幻想得到骑士情感慰藉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苏菲通过个人奋斗坐到了财务主管的职位,变成乡村女逆袭的典型代表,可惜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她遭遇了未婚夫的漠视,情感缺失的苏菲便将这份空缺转移到了中层主管王大伟的身上。但王大伟却视她为填补财务窟窿的“救命稻草”,借“情感慰藉”之名对苏菲实施精神控制,最终苏菲被清扫出局,沦为高层内讧斗争中的牺牲品。苏菲这个人物,与火爆一时的电视剧《欢乐颂》中的樊胜美类似,她幻想通过与富二代恋爱改变自己的身份,但富二代并没有骑士精神,所谓的拯救也并不存在。
三、物质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欲望人生
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川流不息的夜色街景、光怪陆离的时尚派对……这些碎片化形态拼贴出的现代化城市景观共同构建了电影文本中纸醉金迷的“乌托邦”。
在解构小妞电影都市文化呈现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小妞”的生活背景大抵被设置在中国最繁华的都市,这些大都市行走在国际潮流的前沿,对多元化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存有更高的包容度。比如被誉为帝都的北京和被比作魔都的上海,“小妞”所从事的职业似乎是千篇一律的写字楼白领,她们的心理层面也都患有一定程度的高楼症候,即全面地接受物质主义和消费文化。《穿普拉达的女王》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表达了一种对所谓时尚、物质、高端等虚伪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否定,虽然很多观众(女性)走出影院之后,第一时间冲向的仍然是普拉达专卖店,但内地小妞电影中,几乎完全看不到这种表达。
小妞电影中的年轻女性喜爱利用奢侈名牌(物质世界的符号能指)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实现自我认知,一如《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文佳佳;而有些则通过外表、身材的改变获得自我认同,一如《整容日记》的郭晶。这些电影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地将物质欲望表达隐藏在较深的层次,偶尔还会有一些嘲讽。比如《非常完美》中的反面角色腹黑女Cici,对处于中高产阶层的李莉、陆小夕和处于小资产阶层的苏菲的态度有天壤之别,落井下石的她还“好心”地帮苏菲摘除了衣服标签,致使苏菲陷入无法退还的尴尬窘境。
而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就彻底揭掉了这层纱,开始了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崇拜。影片立足于邻家女孩林萧的女性视点讲述了与毒舌女王顾里、神经大条女汉子唐宛如和镇定优雅的软妹子南湘之间的悲欢离合,按照人物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将片中女性划分成二六九等。顾里正因为存在足够的资本底色,所以在姐妹团体中才拥有最高的话语权,她无时不刻不在享受着其他二人对她的臣服。中产家庭出身的林萧和底层阶级出身的南湘在竭尽全力地恪守属于上层社会的游戏准则,效仿尖端人士的生活品位。讲述者、小康之家的普通林萧貌似独立自强,但骨子里则充满对“霸道总裁”的膜拜仰慕,当然这种仰慕是通过所谓爱情来实现的。白马、帐幔、丝绸、火花等符号在暖色柔光的慢镜头MV中化身欲望投射,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盛大聚会场景相比,这些华丽秀堆砌得生硬而空洞,丝毫没有投射主人公的情感和展现时代的疯狂。这种迷离而空洞的城市景观背后依旧是镜头语言里表面女性视点下隐含的男性视角。“电影将女性欲望和快感的实现全部归结于物质,过分夸大了新女性主义对消费社会的认同,否定了新时代女性要求经济独立的根本需求。”⑤
小妞电影得以受市场认可,起缘于新时代环境下的“她经济”的渐成气候,即“女性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围绕着女性理财、消费而形成了特有的经济现象。”⑥小妞电影是“她经济”社会背景下“她文化”的一种展现方式,这种方式实则被建立在“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之上。“对于电影,女性观众的首要身份是消费者,她们通过观影也许增强了一些主体性,但这仅仅是作为消费者的主体性,而不是性别关系中的主体性。”⑦
四、小妞电影的瓶颈
整体看来,当下的内地小妞电影无法承担起引领现代都市新女性自我成长的重任。一味地在期待拯救、寻找爱情、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内地小妞电影陷入叙事窠臼瓶颈,人物形象塑造上刻板平面,故事模式单一化,缺乏性别视角,女性性别意识难觅其踪,谈何女性电影?对于物质主义消费文化的沉迷,结合现代都市的物化空间,小妞电影本身就很容易步入欲望叙事的陷阱。如果没有清晰的女性意识和性别视角来抵抗“凝视”的眼光,小妞电影就更容易丧失自我,反而成为男权文化规训社会、整合社会的“帮凶”。这也是当下内地小妞电影陷入困境的最终原因。
注释:
①洪帆.小妞快跑[J].电影艺术,2011(01):90-93.
②秦喜清.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68.
③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6.
④秦喜清.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176.
⑤宋帅.大陆小妞电影的女性形象分析[D].华东师范大学,2015:47.
⑥⑦周培勤.“她经济”视角下解读小妞电影的女性凝视[J].妇女研究论丛,2015(01):61-70.
(马彧: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陈璇: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