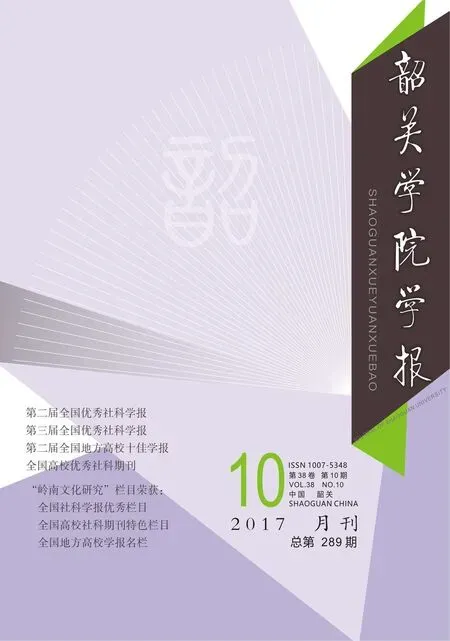地方立法技术科学性之探讨
杜国胜
地方立法技术科学性之探讨
杜国胜
(韶关学院 法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法律作为一项产品,其生产过程离不开技术的把握和运用。立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和阶段都与立法技术具有紧密的联系。立法技术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有效性、法律的质量、法律的科学性及可操作性,进而影响到法律实践的有效性。由于地方立法的特殊性,地方立法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对地方立法技术提出了独特的要求。在地方立法中,精确地把握和运用其科学的立法技术,是地方立法机关生产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法律产品”的关键所在。
地方立法;法律产品;立法技术;科学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法治十六字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代替了原来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一大历史性进步,是对当今中国“法治”内涵最好的诠释。关于法治,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过经典性论述:法治指的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1]。由此可以看出,“新法治十六字方针”中“科学立法”有其深刻的法哲学基础和法理根基。法治社会崇尚“良法”之治,而立法是否科学直接关涉到立法结果——“良法”的出台。“科学立法”对立法技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立法者通过高明的法律内容确定技术,实现法律制度的科学和理性,制造出和谐一致、符合客观现实、可操作性强的‘法律产品’。”[2]相较于全国性立法,地方立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对其自身的立法技术也提出了独特的要求。在地方立法过程中,如何提高地方立法技术科学性,制造出合格的地方性“法律产品”,无疑是地方立法者、专家和学者所要研究和探讨的前沿课题。
要科学地掌握地方立法技术,促进地方立法技术科学化、合理化,务必在深刻而透彻地理解一般立法技术本质的基础上,时刻了解和掌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立法需求,始终如一地贯彻地方立法宗旨,综合运用各种立法技术。惟有这样,地方立法者才能在地方立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丰富自身的立法技能,提高地方立法技术的科学性,不断生成合格乃至优秀的地方立法“产品”。
一、立法技术之精髓
(一)关于立法技术的学术之争
关于“立法技术”这一概念,国内外学者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从宏观方面来看,主要有广义、狭义和折中等三种学说。“广义说”将与立法技术有关的一切问题都纳入立法技术范畴。该类学者主张:“从广义上说, 同立法技术有关的一切规则都属于立法技术的范围, 因此, 立法技术的规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规定立法机关组织形式的规则……第二类是规定立法程序的规则……第三类是关于法律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的方法、法律的文体、法律的系统化的方法等方面的规则。”[3]207-208“狭义说”将立法技术仅局限于法的表达技术。“折中说”则在两者之间提出自己不同的主张,认为立法技术的范围并不能包含所有与立法技术有关联性的问题, 但也不仅仅停留在法的表达技术层面。周旺生先生是此种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从纵向和横向两种角度,对立法技术作了如下区分性界定:“纵向立法技术, 是把立法看作是一个活动过程, 在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在每个阶段的具体步骤上, 立法所要遵循的技巧和方法。其内容主要包括:(1)立法准备阶段中的立法技术;(2)由法案上升到法的阶段的立法技术;(3)立法进入完善阶段的立法技术;横向立法技术, 即从平面的角度观察立法,其内容主要包括:(1)立法的一般方法;(2)法的体系构造技术;(3)法的形式设定技术;(4)法的结构营造技术和法的语言表述技术[4]183。
从微观方面来看,有关立法技术的学说主要可分为“规则说”、“活动或过程说”、“方法或技巧说”等三种学说。“规则说”将立法技术定性为“细则”或“ 规则”, 如苏联法学家凯里莫夫认为:“立法技术在一定的立法制度中, 历史地形成、最合理地制定和正确表述法的规定,以达到最完善表述形式,所形成的规则的总和。”[5]“活动或过程说”认为,立法技术是一种特殊活动或者过程,如我国台湾学者罗成典对立法技术给出了如下定义:“立法技术是依照一定的体例, 遵循一定的格式, 运用妥贴之词语(法的语言), 以显示出立法原则, 并促使立法原则、或者国家政策,转换为具体法律条文之过程。”[6]“方法或技巧说”则指出,从本质上来讲,立法技术是一种方法或技巧。例如,中国学者吴大英和任允正,在他们编著的《比较立法学》一书中,将立法技术定义为:“立法技术,就是立法工作实践所形成的方法或技巧的总和。”[3]207我国著名的立法学家周旺生先生也主张:“立法技术是立法活动中所遵循的、用以促使立法科学化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7]
(二)立法技术的基本属性
1.立法技术是一种经验和知识
立法是立法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专项活动,是一项高智慧的脑力劳动。在这项实践活动过程中,立法者通过长期和反复地从事立法活动,不断增强对立法对象理性、客观和科学的认识,逐步积累其立法经验和知识,并反作用于立法实践,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法律产品”。立法技术具有一般性技术共通的属性,如上述关于立法技术概念学说中“方法和技巧说”。
2.立法技术应当具备“科学化”属性
“中国立法技术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即使有关立法技术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亦有待深入和走向科学化。”[4]178立法技术虽然是立法者在长期立法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关立法活动的经验和知识,但是,其与一般性经验和知识有着本质性不同。一般性技术中的经验和知识与掌握者个体的自身社会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而立法技术因其根植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服务于立法科学。科学立法“必须以客观规律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并使法律规范严格地与其规制的事项保持最大限度的和谐,同时,法律的制定过程尽可能满足法律赖以存在的内外在条件”[8]。因此,立法技术应当走理性化和科学化发展道路,避免仅凭立法者所谓的一己之“经验”,大搞、特搞“经验立法”和“主观立法”。一般性技术中的经验和知识,因其与个体的独特的社会经历有关,可能成为区别于其他个体的显著性特征,但立法行为是有组织的集体性的智慧活动,立法技术中的经验和知识不应为个别立法者独占,应当上升到科学化和理论化层面,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知识财富。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属性在上述众多学说的“广义说”和“折中说”中都有所体现。
3.立法技术的成文化与非成文化并存
“任何法律制度中,确定性和可操作性都是立法者追求的最为基本的目标。”[2]从形式上看,一部完整有效的“法律产品”,必须具备统一、严格的规范化形式,便于人们理解、掌握和遵循。因此,关涉法律形式方面的立法技术,如法律常用词语表述技术、法律条文表达技术、法律结构技术、法律责任设置技术、法律修改形式规范技术、法律废止形式规范技术等,应当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以确保法制的统一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2009年制定了《立法技术规范(试行)》,是将立法技术成文化、制度化的重要体现。上述关于立法技术概念学说的“广义说”和“规则说”就体现了立法技术成文化的属性。
作为“经验”的技术,常常以结果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由此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验或技术的“结果性”上,似乎忘却了其过程。殊不知,就经验或技术来说,“过程”性经验或技术往往比“结果”性经验或技术更为重要。众所周知,人们的经验或技术是在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取得的,但是不要忘记,人们在运用这些经验或技术解决新问题时,是在力图还原之前的活动过程。可见,经验或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活动过程的再现。由于“活动过程”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呈现“时空上”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立法技术很难以成文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立法准备技术、立法预测技术、立法规划技术,等等。这些立法技术只能以非成文化的形式存在于立法者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上述关于立法技术概念学说中“活动过程说”就体现了立法技术非成文化的属性。
二、地方立法自身的特点及发展规律
(一)地方立法权限法定化
新修订的《立法法》对设区的地方立法的权限和范围作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72条第2款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同时该项还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之精神,地方立法在立法权限上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1.立法事项的限制。地方性立法事项,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三个方面,除了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之外,地方立法不涉及其它事项。2.地方立法内容的限制。地方立法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不得同本省、自治区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3.对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力的限制。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二)立法目的所具有的地方性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次修改有其重要的法理依据,那就是:我国是单一制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立法体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确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然而,我国地广人多,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为了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适应各地方不同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性立法机关立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必须在我国建立统一、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立法法》修改的法理基础告诉人们,地方立法权的设立是服务于各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各地方之间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相差很大,所以各地方的立法目的呈现多样化态势,具有较强的地方性色彩。
(三)地方立法发展的渐进性和超前性并存
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具备可行性特质,能够在法制实践中得以践行。如果法律要求人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是与法律制度可行性的要求严重背离的。因此,地方立法机构制造出的“法律产品”要想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并最终得以施行,就必须符合社会实践,充分体现本地区经济水平、历史传统、人文背景、民情风俗等地方特色和发展规律。而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大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地方立法活动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走渐进化发展道路,避免在立法过程中急功近利,从而走向“主观立法”、“封闭立法”、“政绩立法”、“工程立法”等与“科学立法”相悖的错误的立法道路。
地方立法的渐进性并不否定立法“超前性”存在。《立法法》第73条第2款规定,除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外,在本法第72条第2款规定的事项范围内,就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事项,设区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方立法需求就会出现不一致情景。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的法律制度的时机尚未成熟,地方超前立法就会填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空白,促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另外,立法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相对于中央,各地方处在立法活动的“前沿阵地”,掌握着第一手立法实践材料。因此,地方超前立法有助于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为后发赶超全面小康提供法制保障。
三、地方立法技术科学性之要求
生产产品,必须具备相应的产品生产技术,而每一项技术都具有其基本属性。了解和掌握某项技术的基本属性,是获取与传承该项技术必备的前提条件。技术为产品的生产注入了效率,先进的技术更是为产品的生产节省了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产品的出产率,但未必能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唯有注入科学元素的先进技术,才能完成这一重任,地方立法技术也不例外。因此,地方立法技术要具备科学性,地方立法者除了了解立法技术的基本属性之外,还必须深刻了解和把握本地区立法特点及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做到以下几个基本点:(1)始终如一地贯彻地方立法宗旨;(2)将立法技术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之中;(3)坚持人文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统一;(4)成立立法工作专家委员会;(5)法律规范表达形式统一性与创新性协调。只有把握好这些关键点,地方立法技术才能走向科学化发展道路。
(一)始终如一地贯彻地方立法宗旨
每一部法律都有其特定的立法目的,规定立法宗旨是立法的基本要求。行为的目的性是一个理性人最基本的素养,立法者的立法行为亦不例外。国家之所以要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就是因为各地方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而这些法律问题还没有达到用全国性的统一法律规制的程度。由此可见,地方立法宗旨是地方立法者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客观能动的反映,是地方立法所制造出的“法律产品”的基本内核,是地方立法存在的生命线。
地方立法机关所制定出的每一部单行法,都有其独特的立法宗旨,且位于单行法条文之首,其它所有条文都为之而生、为之服务。立法者要想获取科学的立法技术,其必须在立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始终如一地贯彻立法宗旨。在运用每一项立法技术时,应以“服务于立法宗旨”为第一要义。否则,即使掌握了最先进的立法技术,也因其缺乏科学性而使得“法律产品”背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不能有效地规范和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而且还会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使原来的社会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凌乱。正如一个技术非常先进的室内装修工程师,倘若其在工作过程中,不时刻考虑房屋主人的需求,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对雇主来说就是次品、甚至是废品。由此可见,地方立法者要想拥有科学的立法技术,或者使其立法技术变得更为科学,就必须时刻牢记立法宗旨,否则,就无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立法技术。
(二)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从形式上看,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出法律法规和规章所体现的是地方立法者的意志。然而,地方立法者的意志不是孤立的,不是任意而为的,而是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实践的能动反映。也就是说,地方立法者的意志一定要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走科学立法道路,摒弃“主观立法”、“经验立法”、“封闭立法”及“政绩立法”。
科学的地方立法技术是为地方立法宗旨服务的,而地方立法宗旨是立法者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的主观能动的反映。因此,地方立法者必须时刻将自己置身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立法知识和经验,使自己的立法技术走向科学化。前文分析过,立法技术既是一种结果,但更多的是一种“活动或过程”。研究和掌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行规律,才能把控科学的地方立法活动,提炼科学的地方立法技术。
(三)坚持人文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统一
法律既是一种人文现象,又是一种自然现象。科学立法要求:立法不仅要倡导法律与人文现象的契合,而且要倡导法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一个立法行为如果仅仅考虑立法过程涉及的人文因素,就很可能背离“科学立法”而走向“经验立法”。相反,当立法过程在考虑人文因素的同时,应予自然因素以充分的注意,注意某一事态本身所具有的由自然因素决定的情势,便走向“科学立法”。这一点已为无数的立法事实所证实,如生态环境保护法、动植物保护法,等等。
仅考虑法律与人文现象的契合,不顾及法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人文与自然人为地隔离开来,这样的立法过程所获取的立法技术将与“科学性”无缘。
(四)成立立法工作专家委员会
“活动或过程”是立法技术的基本属性之一。无论是国家立法行为,抑或地方立法行为,皆是一种高智慧、专业性很强的法律实践活动。从立法预测、决策、规划、创议,到起草法案、构造法的体系、设定法的形式,再到法的语言表述、法案审议,最后到法的解释、法的修改和法的废止,无不是一项法律专业性很强的活动,需要立法工作专家委员会主导和参与。
与其他科学活动一样,科学的立法活动是一项专业性活动,因此,地方立法技术不是零星地散落在某个个体身上,甚至不归属于某一位或几位专家,而是掌控在立法工作专家委员会的集体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立法技术的科学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集体”,而不是“个体”。
(五)法律规范表达形式统一性与创新性协调
“立法语言”和“法律规范结构”是法律规范表达形式两项最基本的元素。立法语言技术和法律规范结构技术,关涉到社会大众对“法律产品”的理解和把握;关涉到法的施行、适用和遵守;关涉到其他立法技术的有效性发挥。
立法语言是一部法律的生命,是传达立法者意志的载体。清楚而准确地传递立法者意志,让社会大众准确地理解法律规定的内涵和实质,是立法语言最根本的要求[9]。19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法学家、新功利主义创始人德国学者鲁道夫·冯·耶林曾有句名言:“立法者应当像哲学家一样思考,但像农人般说话。”[10]立法活动既是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同时也是平民化活动,地方立法者在尊重历史传承、遵循专业手法和技术守则的同时,应当使立法语言尽可能地通俗易懂,处理好专业化和平民化直接的矛盾。“法律必须确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11]地方立法活动是一种地方文化,是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土壤的人类文化,这就要求地方立法者的立法语言技术既能体现全国法制统一的要求,也要具有地方性特色,处理好地方立法语言的统一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协调关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2009年制定了《立法技术规范(试行)》对法律规范结构做了统一的规制。地方立法者在运用“法律规范结构技术”时,应确保地方法律规范结构与《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保持协调一致。如果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出的“法律产品”,在法的内容结构、语言的表达逻辑及法律条文等要素上缺乏统一性,将会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造成很大的困难。无论国家还是地方,对法的表现形式、结构设置、语言表述等都必须是统一的,其他立法机关只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统一的立法技术规范基础上,作一些适当的补充[2]。
四、结语
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既是《立法法》授予的结果,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呼唤。其不仅是地方立法者的立法职责,同时还承载着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和庄严的责任。要忠实履行好立法职责、圆满完成党和地方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地方立法者必须走“科学立法”道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和运用科学立法技术是“科学立法”必备的条件和途径。地方立法者在地方立法实践过程中,要深刻领会立法技术的基本属性,时刻把握本地区社会发展的命脉,顺应地方立法自身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要求,不断地总结经验,将立法技术和地方立法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立法技能,使自身的立法技术不断走向科学化。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99.
[2]刘用安.立法技术:精无止境[J],人民论坛,2009(10):14-15.
[3]吴大英,任允正.比较立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
[4]周旺生.立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郭道晖.当代中国立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 :1106.
[6]罗成典.立法技术论[M].台北:文笙书局,1983 :1.
[7]周旺生.立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53.
[8]关保英.科学立法科学性之解读[J].社会科学,2007(3):76-92.
[9]李培传.论立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65.
[10]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 :110-111.
[11]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292.
On the Scientificity of the Local Legislative Techniques
DU Guo-sheng
(Law School,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Guangdong, China)
As a product, the productive process of the law cannot do without the mastering and using of technology.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link, aspect and stage of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legislative technology. The scientificity about the legislation,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validity of the law, the quality of law, the scientificity of law and the operability of law,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egal practice. Because of its particularity, local legislation posesd the unique challenges to the local legislative techniqu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local legislation, it is the key for the local legislative bodies to produce qualified and excellent “legal products”with accurately grasping and applying scientific legislative techniques.
local legislation; legal product; legislative techniques; scientificity
D901
A
1007-5348(2017)10-0045-06
2017-05-28
杜国胜(1965-),男,安徽池州人,韶关学院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法学理论、地方立法。
(责任编辑:廖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