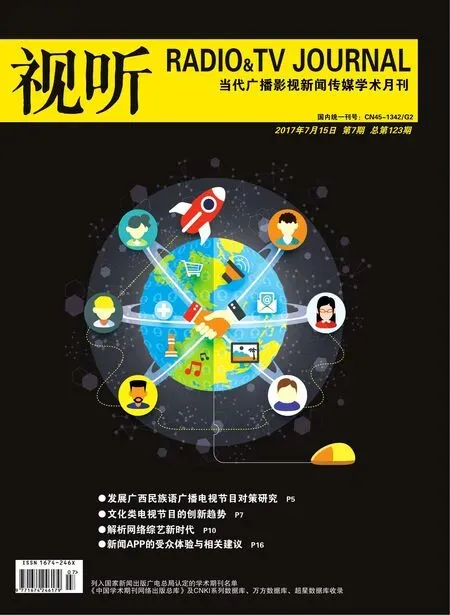电影本质下对亚洲青春片中“物哀”与“纯爱”意象分析
——以《七月与安生》《情书》《假如爱有天意》为例
□ 乔淑一
电影本质下对亚洲青春片中“物哀”与“纯爱”意象分析
——以《七月与安生》《情书》《假如爱有天意》为例
□ 乔淑一
近年来,中国青春题材电影方兴未艾,但是也因同质化倾向严重等问题而口碑不佳,这就需要从电影本质出发去真正理解青春电影。本文通过电影本质理论,对中、日、韩的三部青春电影《七月与安生》《情书》《假如爱有天意》中的“物哀”与“纯爱”意象进行分析,为中国当下的青春电影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电影本质;亚洲青春片;物哀;纯爱;宿命
伴随着青春题材电影类型的成熟,这种原本只是小众的电影类型却在电影平台上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青春题材电影多以对青春的追忆为主线,对爱情的认知为主题,以友情与爱情冲突、三角或多角人物关系为公式化情节,以其娱乐化的内容、准确的受众定位和良好的市场营销而广受欢迎。青春题材电影可以分为青春片、青春偶像片、青春励志片。近年来亚洲青春偶像片比比皆是,但青春片却相对较少。戴锦华曾在其著作《电影批评》中指出,青春片“在于表达了青春的痛苦和其中诸多的尴尬和匮乏、挫败和伤痛。可以说是‘无限美好的青春’的颠覆。‘青春片’的主旨,是‘青春残酷物语’”。因此,青春片不同于青春偶像片的风格与基调,而是展现出一种淡淡的“物哀”情绪与“物哀”中的“纯爱”意象。①
一、物哀与宿命——电影是时空的艺术
“物哀”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是一种悲剧式的美学意识。齐藤清卫把“物哀”归结为“哀怜的情趣”“对对象的情爱”“控制情绪的一种心情”“与静观谛念相联系”四个方面,认为“物哀”是一种与开发性的积极情感相远离、比之情绪更接近于热情的、属于感情范畴的一个概念。②进入21世纪以来,这本独属日本青春片的“物哀”也渐渐渗入到亚洲其他国家的青春片中,形成它们自己的风格。宿命论作为一个哲学学说,强调各种事件、行为都必须服从于命运,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实际做的事,我们无力去做任何事。“物哀”和“宿命”这两点可以传达青春片的叙事特点,尤其是“宿命”一词,必然带着时空的转换的特点。
电影《七月与安生》是一部典型的关于爱、分享、记忆、离去的青春片,讲述了安生在回家的地铁上遇到了自己和闺蜜七月多年前爱过的苏家明,家明的名片被安生带回家并放在自己珍视的“记忆”的盒子中,安生孩子阴错阳差打开并拨打家明电话而由此展开的两个女孩从13岁到27岁的关于成长、友情和爱的故事。与很多青春片着眼于爱情不同,《七月与安生》更多的着眼于“爱”与“情”,故事开头带有一些宿命或带有命运安排的意味。七月安稳的家庭环境注定了她是典型的“乖乖女”:遵从妈妈的话穿着保守的内衣,留着乖乖的学生头或者是披肩发,按照父母的路线学习—工作—谈恋爱—结婚。复杂的家庭则使安生放纵不羁爱自由,人生晃荡而颠簸,她不爱穿内衣,觉得是束缚,在青春期时弄了象征另类与反叛的爆炸头。苏家明的出现使她们分裂你我,过上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生活。七月和安生的人生在27岁到来之际更像是二者的转化,七月成为安生,安生变成七月。然而,当经历了人生种种,安生万水千山走遍,终于回归她所向往的却不曾拥有的安稳生活,她进入课堂学习,也留起柔顺的直发;七月在习惯了波澜不惊的安稳生活后,决心剪短头发出去体验安生的漂泊。不论是安生早有预设的希望自己27岁死去却没有死去,还是七月在宿命中于27岁死去,都像是一种“循环”,一种宿命,从童年到少年到成年,从现实到回忆到臆想再到现实,而在这种层层铺垫的宿命中,又带着些许的无奈与感伤。这种生命无情的嘲讽与无法改变命运的哀叹,恰恰也表现出“物哀”的情绪。
“青春电影教父”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也是一部关于爱、记忆与离丧的优美青春片。博子对未婚夫藤井树(男)的死无法释怀,于是往他当年的地址寄了一封信。可是,博子却奇迹般地收到了回信,她既带着无法相信的感受又带着难以自拔的喜悦。观众作为全知的主体,自然已经知道博子寄出的信其实是寄给了“自己”,那个外貌特征与自己几乎一致的“自己”。虽然并没有看见彼此,却能够意识到彼此之间的镜像关系,影片交替的时空中,一个是现在时,一个是过去时,却隐含着宿命的悲凉之情。“物哀”要求敏锐感受人生无常以及瞬间的微妙感觉,命运的无常总是被岩井俊二有意地凸显出来,而在这种无常中,宿命无疑是最为不可琢磨的。
在韩国电影《假如爱有天意》中,梓希收拾房间时无意中发现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都是她母亲初恋时的信件。在不断对母亲的青春爱情回忆的同时,梓希也在经历着与母亲颇为相似的爱情。从叙事结构上来看,这部电影是分段交叉式结构,一条线索是母亲桔希与吴俊河的感情,另一条线索是梓希与尚民之间的感情;一个是过去时空,一个是现在的时空,却因为书信与项链串联在一起,母亲的“悲戚”爱情在女儿的身上实现了归属。母亲的爱情段落中始终弥漫着“物哀”的情绪:母亲出身高贵,与俊河的普通身份有着巨大差距;泰宇在两人感情上有过介入,后来却为了成全两人而试图自杀;俊河为了桔希不再纠结而去参加战争,最后一次见面千方百计不让心爱的人发现自己已经失明,并谎称自己结婚。尤其是很多年后在饭店的约会,桔希与俊河“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物哀”情绪在升华。在导演看似随意的时空转换中,却因为“书信”“彩虹”“项链”“照片”这些隐喻式的视觉符号形成了一种宿命,人生兜兜转转,有缘起有缘落。
《七月与安生》《情书》《假如爱有天意》同属于青春片,它们不同于“青春偶像片”通过美好的爱情、甜蜜的往事给观众制造的“白日梦”幻想,这三部影片运用电影的时空表达了青春中的“物哀”与人生中的“宿命”。三部影片都没有回避死亡,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使三部影片增加了哲学的意味。
二、纯爱与美学——电影是视听的艺术
“纯爱”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始见于日本文学作品,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文风寡淡平和、洁净唯美、悲伤寂寥的川端康成。纯爱电影本身并没有明确固定的定义。
在《七月与安生》中,安生的现在时大多是采用一种冷色调。而安生在少女时代是一个爱自由的小姑娘,她穿着明艳的红色,涂着明艳的指甲,有火一般的热情。如果沿着安生的成长线看,安生相关的视觉构造是一点点在发生变化的,从最初的少不更事,到外出漂泊,无论是她出场时的光线还是衣着都有着一个从明到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细微的变化,那就是只要七月在,安生就是明亮色;七月不在时,安生就是暗光、暗调。在七月与安生的童年时代,她们在阳光下踩着影子,无忧无虑,明媚而温馨;少年时代,因为苏家明的出现,她们经历了心理上的一丝波澜,在“酒吧”“寺庙”这几个压抑、局促的地方,影片对光影也是作暗色处理。光线色彩的变化,诠释了人物心理的变化和剧情的走向。
青春片大师岩井俊二还有着“映像诗人”的美誉,他对镜头和光的应用形成了“岩井电影美学”。同时,岩井俊二在人物设置上喜欢通过“自我”分裂,将自我的不同性格分裂在一部电影之中,这种分裂是通过不同的色调和光影来表达的。在《情书》中,渡边博子和藤井树(女)容貌相似,性格却不尽相同,博子安静、内敛,藤井树(女)活泼、可爱。博子的出场时多数是逆光摄影,人物语言也不多;而藤井树(女)出场时的光线色彩是明亮温馨的。不仅“视”,“听”也体现着“岩井美学”的特点。美国电影作曲家赫尔曼曾说:“音乐实际上为观众提供了一系列无意识的支持。它总是不显露的,而且你也不必要知道它。”《情书》中的音乐淡雅而迷人,用钢琴声贯穿整部电影。影片一开始,博子躺在雪地上时,观众可以明显地听到钢琴声,但随着博子渐渐远去的身影,钢琴声好似不再那么明显。这并不是说钢琴声消失了,而是观众会沉浸于电影与音乐的融合,体会导演营造的意境。
电影的色彩结构有两种,一种为客观写实,一种为主观表意。“纯爱”的标签下,《假如爱有天意》在母亲的爱情故事中,用的是偏黄的色调,整体呈现暗色调;在梓希的爱情故事中,则主要用粉色奠定浪漫的基调。偏黄的色调不仅表示了对过去的回忆,代表着过去时空,实则也暗示了情感的不美满;粉色代表浪漫、美妙、纯纯的爱恋,暗示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导演主观表意的方式,给了观众提前预知的能力,但是又包含具体情节上的悬念。
画面和声音都会影响电影的视听表达,也会影响影像整体风格的构建。在“纯爱”这一标签下,青春片的视听语言显现出一定的类型模式,而且此种类型模式会帮助观众有意识地去理解剧情的发展走向。但对于《七月与安生》《情书》《假如爱有天意》这三部优秀的青春片来说,它们显现出创作上一些表现风格的相像性,但绝不是照抄照搬,而是“作者风格”下的有益探索。
三、青春残酷与哀而不伤——电影是作为现实的映像
意大利作家莫里亚克说:“你以为青春是好事吗?青春如同化冻中的沼泽。”在《七月与安生》中,青春的残酷就在于开始不分你我的姐妹走到了互分你我、相互指责;《情书》中,青春的残酷在于“我爱你,你却爱着像我的她”;《假如爱有天意》的青春残酷在于“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却不能在一起”。在青春片中,总有挚爱离去,总有“伤逝”之悲,总有茫茫宇宙中冥冥的生命的轮回。
电影的本质是其作为现实的映像。德国著名心理学家、电影理论家阿恩海姆认为“电影并不是机械地记录和再现现实的工具,而是一门崭新的艺术”,“一切罪愆全在于人类永远企求在艺术上达到逼真化,人类为力求控制这些自然物质,使设法塑造这些形象,这种原始的欲望是促使人类去创造逼真形象的动机之一,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推动人们不仅止于抄袭,而且还要创造、解释和塑造的艺术要求。”③以上三部影片虽分别传达出了“物哀”情绪,但也始终体现着对现实的关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是“哀而不伤”的。《七月与安生》的最后一幕,安生站立在玻璃墙前看到了自己,她对镜子报以微笑,镜子中的她在移镜头中变成了微笑的七月。七月与安生个性鲜明迥异,却最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互相为之满意。《情书》中渡边博子穿着红色的毛衣对着雪山大喊“你好吗?我很好!”这其实是对感情的一种释放。《假如爱有天意》中,虽然母亲没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但是梓希却与母亲心爱的人的儿子、自己的爱人走到了一起,这不能不说是对命运无常的些许慰藉。
四、结语
李银河在观看完《七月与安生》表示“中国电影终于可以看了”,这不得不说是对青春片这一类型电影的莫大肯定。固然,每个人的青春年华都终将逝去,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记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化为乌有;即使青春时代有诸多的青涩、纯美、残酷、尴尬、幼稚甚至梦想迷失,但是这并不等于记忆会随风烟消云散。青春、爱情其实是人性的舞台,是社会人生百态的一个窗口。《七月与安生》《情书》《假如爱有天意》这三部极具代表性的青春片,不论是在口碑、质量还是商业上均比较成功。面对国产电影青春片的泛滥、“叫座不叫好”的现象,如何从丰富多彩的生活出发,去除概念化、表面化,如何把电影与电影本质联系起来,把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是值得导演们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戴锦华.第五章精神分析的视野与现代人的自我寓言:情书[A].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②蒋俊俊,吴晓敏.论岩井俊二《情书》中的“物哀”意识[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8).
③程英.阿恩海姆电影美学思想中的格式塔心理浅析[J].安徽文学:评论研究,2008(3).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评电影《七月与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