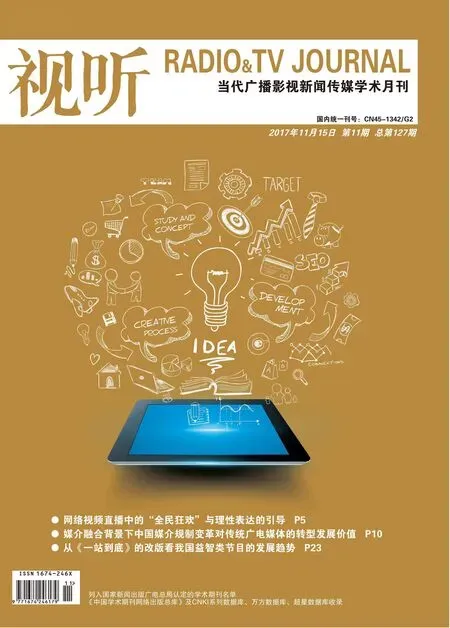网络视频直播中的“全民狂欢”与理性表达的引导
——基于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阐述与思考
□ 王长潇 位聪聪
网络视频直播中的“全民狂欢”与理性表达的引导
——基于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阐述与思考
□ 王长潇 位聪聪
从个人角度看,网络的匿名性给予用户进行自我呈现和建构虚拟人格的狂欢广场;从行业角度看,虚拟的狂欢秀场引发了对于商品符号意义的新追求,推动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从社会角度看,低准入门槛的网络直播消解了原有的话语表达体系,尚未成熟的新体系中失范现象屡屡发生。虽然网络直播中仍乱象丛生,但这一媒介形式终将找到理性表达的平衡点,进而重构我们的信息交互和消费模式。
视频直播;狂欢理论;话语秩序;虚拟人格
苏联杰出思想家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本是其探索文化美学和诗学的命题,但也适用于很多社会命题的解释,本文将从该理论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情况,对网络视频直播的现状进行分析。巴赫金在其著作中围绕着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三个重要概念对该理论进行了论述,狂欢节期间人们可以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彼此平等地尽情欢乐嬉闹,他认为“狂欢节实际上已成为容纳那些不复独立存在的民间节日形式的贮藏器”①。狂欢式使狂欢节不再受特定的时间、场所限制,而是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狂欢化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叛,“狂欢的节日广场文化总是在不断地颠覆等级秩序、消除尊卑对立、破坏严肃统一、瓦解官方和民间的界限,让一切边缘化”②,这与当前网络直播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直播间的情况有着完美的契合,它建构于虚拟网络基础之上,依赖于其独特的视觉性、社交性和互动性建立起全新的狂欢广场,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全民参与其中的媒介奇观,而这一奇观正在从多个层面消解和重塑我们熟悉的生活状态。
一、仪式与面具:虚拟人格的建构
狂欢理论的前提是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第一世界是充满秩序的权威的存在,后者是则是倒置的存在,供人们亵渎和嬉笑,加冕和脱冕是狂欢节所特有的仪式,正是这种仪式性的行为实现两个世界的转换,赋予狂欢节特有的内涵。与现实生活不同,狂欢节中的加冕对象是地位低下的小丑或者奴隶,人们戏谑地给他们穿上国王的服装,这种喜剧式的仪式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叛与区分。巴赫金还指出面具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狂欢节怪诞诙谐的象征,是对统一和雷同的否定,通过佩戴面具,实现了参与狂欢者的匿名和人格的重建。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正在逐步走向民主法治的理性社会,但与虚拟的网络世界相比,现实世界由于发展尚不成熟而仍旧存在着诸多权威、不公和特权。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视频直播平台就成了狂欢广场,在这里人人平等而自由,拥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表达权。当网络主播和观众进入直播间,戴上耳机打开麦克风开始直播或观看直播时,就完成了一种仪式,完成了角色转换,脱离了原来社会框架中的自我,开始进入狂欢世界。
窥私欲、表现欲、模仿欲、被认同欲等等,这些在现实世界被理性压抑和控制的本能欲望在匿名的环境中被放大。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地位、组织等基础上的信任,在某种程度被网络直播平台创建的“超自由”运行机制所破坏,所有参与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或被搁置一旁,或被抛之脑后,随心所欲地进行虚拟人格的建构。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人都在某一意义上进行着表演,针对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对象按照不同的要求在前台扮演着不同角色③。他认为的前台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这也对应着狂欢理论中的第一世界,在这里人们总是被赋予各种标签,在表演的过程中,表演者总是按照某种预设给予观众某种印象,换句话说当处于观众的注视状态下时,演出者时刻都在通过建构虚拟人格以满足观众的需求。后台是个人生活空间,是自然放松的,处于后台的表演者才呈现真正的自我。
网络直播将舞台场景拓展到了原本属于后台的个人生活空间,原本不适宜出现在前台的生活化形象迎合了受众窥视后台的好奇心,看似属于主播私人生活的卧室、厨房等场景变成了他们的秀场,完成了后台前置的转换,而这种转变不易为受众所觉察,他们认为主播所展示出的生活和性格就是他们的真实面目。媒介技术的进步让受众的体验更为生动真实,而越觉得真实时,说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就越不清晰。直播在形式上看似真实,是主播私人生活私人观点的真实呈现,实际也是表演者为获得认同和满足,甚至是经济利益,戴上面具进行的构建虚拟人格的精心表演。为了博得观众眼球,吸引更多的粉丝为自己刷礼物,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主播们热衷于在直播平台搭建的狂欢广场上,构建各种匪夷所思的虚拟人格,甚至不惜做出触犯法律的行为,这也是造成当前网络直播中怪象丛生的根结所在。
2016年11月,拥有67.8万粉丝的主播“快手杰哥”直播做慈善引起关注,一时间十几万人在线围观。画面中荒凉的背景里,一名男子给一群穿着破旧的村民发钱,旁边还蹲着几个孩子。当我们感慨于人间大爱时,事件却发生了翻转,网友爆料发钱者在直播结束后又将钱收回,这一行为的目的纯粹为了增加观看量和吸引粉丝“刷礼物”。被曝光后,该主播为了表示悔改之心,又在直播中喝掉一瓶消毒液,最终以被送入医院收场。无论是直播“做慈善”还是直播道歉,都是主播为了吸引粉丝,刺激观众的收看欲望而制造的噱头。然而这种跳梁小丑般的演出并不是特例,狂欢广场上“直播造人”“直播女生寝室”等等一系列乱象屡屡发生,虚伪的面具背后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甚至是人性底线的公然挑战,是迎合部分观众恶趣味,追逐个人经济利益的私欲作祟。在享受狂欢广场带来的自由和愉悦的同时,用户应在合理合法的表演框架内进行人格建构,而不是单纯图一时之快,而造成框架失调,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二、符号与消费:全民狂欢的商品价值
狂欢节中加冕仪式既是仪式性的表现,也是象征性的行为,通过加冕普通人在狂欢广场上拥有了国王身份,获得暂时的虚拟的狂欢快感。网络直播中主播在自己粉丝的簇拥下,一呼百应,也完成了“加冕”,成为自己直播间中的“国王”,这种满足感并非物质上的获得,而是一种符号化的虚拟的满足。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认为“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④,换言之今天消费者由原来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转变为对符号化了的地位和身份的追求。这也是一种后结构主义范式下的理解,我们不再关注消费行为本身,更在意的是消费过程中的快感与满足和消费行为背后的意义建构。结构主义范式下的传播学理论认为,传播的意义在于信息的传递,符号的功能就是传情达意。在网络直播中有大胃王直播自己如何吃掉十人份的饭,有的直播对着手机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语,有的直播自己玩游戏,有的甚至就是直播自己睡觉,这些直播内容在传统传播学者看来无聊、无味、无意义,根本没有任何观看的必要;然而粉丝并不在乎主播播出的内容是否有传统观念中的“意义”,而只在意观看过程中心里的满足,这种满足可能是通过对照建立起的自我认同,可能是单纯的陪伴的慰藉,不管为了何种目的,他们默默地观看着直播。各直播平台纷纷推出“游艇”“飞机”“钻石”等虚拟礼物,当粉丝们给主播“刷礼物”达到一定金额时,屏幕上会出现特效,主播也会中断直播内容,对进行“打赏”的粉丝进行感谢,并与之互动。粉丝们购买的礼物往往价格昂贵,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在直播间这一特定场景中,货币转化为视觉符号,甚至转换为直播与自己的互动,在直播间中成为其他粉丝的关注焦点,在互动过程中满足自我娱乐的需求。
网络直播平台作为媒介技术与商业经济合作的产物,处于商业化的运作机制中,盈利是它的先天使命,难以摆脱商业资本的操控,这一背景下的全民狂欢便具有商品价值。直播行业已经进行过两次升级换代,进入直播3.0时代。UGC时代,将个人小视频上传到视频网站,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实时直播,但这是直播的雏形。之后出现了以游戏直播为主的YY直播、六间房等网页端的直播,受技术限制,其应用领域和受众范围有限。如今的直播已经进入了“随走、随看、随播”的移动视频直播时代,直播的场景由室内的网页端发展到室外广阔的空间,应用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准入门槛,所有人都可以拿起手机进行直播,这极大地推动了直播行业的发展。目前国内已注册的直播平台有200多个,仅2016年一年就有100多家直播平台创立。网络视频直播行业是一种“眼球经济”,谁能抓住观众的眼球,谁就是赢家,为此各大平台热衷于争夺优质的主播资源。网红是网络直播平台资源争夺的主要战场,他们靠自身颜值,或翻唱歌曲、或直播化妆过程、或灌输心灵鸡汤、或插科打诨来吸引粉丝围观和赠送礼物,完成价值创造的过程。明星也是直播平台的必争之地,Angelababy曾为一美妆品牌代言,并在直播中为推荐该品牌而使用其口红,一时间引发近500万人观看,更是在不到两个小时卖出了近万只。另外papi酱、罗振宇等有着自己想法和固定受众的自媒体人,也是直播平台所争夺的对象。罗振宇的《逻辑思维》本身拥有较大的受众群,他在录制节目时在映客上做了同步直播,这一举动吸引了10万粉丝观看。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直播平台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疏于管理,对直播内容不加限制,对主播的失范行为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导致低俗浅薄的节目内容不断出现,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快手作为当前最活跃的网络直播平台之一,日活用户和流量都在同类平台中位居前列。但由于过分看重利益,快手平台的审核标准极为宽松,直接导致平台上一些主播做出博眼球的极端行为。震惊之余,人们纷纷要求封杀快手。
直播平台的失范还表现在主播们为了获得粉丝关注,进而加冕成为“国王”,而使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在消费社会中,网络直播中粉丝在观看主播节目,进行符号消费的同时,成为了商品,具有了商品价值。受众商品论认为,受众是被生产的,他们在观看传统媒体制造的节目同时也转化成为商品,并被卖给了广告商。主播们一方面极尽所能吸引粉丝围观和送礼物,从直播平台获得分成;另一方面将数目巨大的粉丝打包卖给广告商,通过在直播中向粉丝推介产品达到商业推销的目的。Papi酱虽不是网络主播,但作为2016年最成功的网络红人,一条广告卖出了2200万,美妆主播纷纷在直播中推销各类化妆品,游戏主播纷纷推荐同类游戏,这些都是“社会意义的欲望”所激发出来的需求。关注量就是效益,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部分网络主播穷尽各种手段吸引粉丝,侵犯个人隐私,挑战道德底线的行为屡见不鲜。
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只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法规人伦的行为,从长远看不利于直播行业的发展,想要获得长远发展和更多的经济效益,行业内必须形成规范,进行自我约束。目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下发通知,规定网络视频直播平台需持证上岗,这对于从平台层面进行监管有积极意义,可以督促网络直播平台对签约主播的内容进行审核和把关,然而更重要的是每个参与者把握尺度,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内容生产。
三、解构与重塑:颠覆的话语狂欢
狂欢节中不再对演员与观众进行区分,所有人都积极参加到狂欢式之中,人们在种种粗俗、戏谑、自由和无拘无束的亲昵中释放自我,打破常规,不受教条、敬畏、权威的约束,对原有的规范和秩序进行挑战。巴赫金突出了狂欢广场的重要性,认为它具有全民参与性,是普通大众进行狂欢产生共鸣的场所,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而亢奋的,积极地表达着自我。他所强调的全民性与当前全民参与直播的状态有着一致性,网络直播平台的出现为全民发声提供了完美的狂欢广场,从宏观社会角度看,狂欢广场的出现在多角度重塑了原有的社会秩序。
一方面,网络直播平台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介的“中心化”倾向,使信息交流方式更为平等开放。相比较于传统大众传媒一对多、非实时、几乎无反馈的传信息播形式,网络直播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不再是观众围绕着电视广播转,接收“填鸭式”的信息灌输,而是“去中心化”地自主选择播什么、看什么、交流什么、反馈什么。尤其是弹幕的出现,使主播与粉丝可以实现实时互动,真正实现了无脚本、无彩排、观众决定内容的生产方式。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麦克卢汉认为,一切技术都是人的感觉的延伸,媒介即讯息。我们的社会经历了部落化—去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电子媒介的使用,使得原有的人类活动领域不断“缩小”,逐渐形成一个部落,由此提炼出“地球村”的观点⑤。网络直播这一媒介形式的使用使得信息传播交流模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它真正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将人际传播的感受嫁接于大众传媒形式,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实现了“面对面”的、即时的、互动的大众传播,人们仿佛回到一个部落之中进行信息交流。
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形式大行其道,传播者与受众的角色定位逐渐模糊,传播者的权威地位下降,网络直播平台更是消解了两者之间的界限,提高了以往传播方式中受众的主体地位。狂欢节上不论身份地位,人人平等,观众和演员也不再被区别开来,每个人都积极参加到狂欢阵列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存在,而不是被动消极的客体。换言之,它强调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主体性和交互性,两者之间身份地位存在着转换。网络直播的流行给了普通大众发声的机会,原先大众传播形式中沉默的受众也开始拿起麦克风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个直播间俨然就是一个个小型的电视台演播间,他们或嬉笑吐槽,或展示才艺,或灌输心灵鸡汤,这种话语表达权的获得消解了传者与受众的距离和隔阂,传播活动中受众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法国社会学家福柯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所谓的话语不再是表情达意的符号,也不是现实与语言之间的摩擦面,而是有着自身的规则,用以建立秩序及言说之物的界限。这种话语权并不是人人均而有之,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和“知沟”的存在,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社会精英的手中,他们控制着媒介表达形式和内容,进行着议程设置,掌握着社会的声音,普通受众则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网络直播中的受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事物有着自身的理解和评价,有着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不再处于被支配地位,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充分表达着自我的观念,进而解构了原有的话语秩序,建构出一个更为平等开放的话语逻辑。这种为大众所掌握的话语制度的确立,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长尾理论”看,即使看似再小众的文化也有特定的受众欣赏,仅仅依靠主流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内容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受众的不同需求,网络直播的发展可以丰富文化形式,满足不同人的文化需求。
随着原有社会规范和话语秩序的消解,新的话语体系尚未完全成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差错,存在失范现象。马克思主义传播观强调精神交往的重要性,认为其与物质交往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基础和根源,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网络视频直播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运行机制,但仍是一种现实的社会交往,是人类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我们在研究网络直播的同时,“不能忽视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和社会制度对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的制约作用”⑥,应该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和理解。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人们的关系物化,物质的丰富也带来精神上的孤独与空虚。当原本严肃的、权威的秩序被瓦解,大众沉浸在短暂的麻痹和狂欢之中,过度释放自我甚至一时迷失自我,这给当前的网络直播失范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如果大众只是沉溺于自由声音的获得,找到情绪的宣泄口,而不重视自己发声的质量,那这种权力终将是虚妄。
四、结语
网络视频直播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狂欢广场。新的表达形式在内容上难免存在过度的自由和意义的浅薄,现有的国民素质又难以推动“大众”向“公众”的转化,于是网络视频直播平台中的失范现象屡屡发生,用户也难免一次次沦为“乌合之众”。对待网络视频直播这一新的媒介形式,我们应坚持其作为一种媒体技术的中性原则,它为社会创造着新的信息交互方式和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但其本身没有价值导向。我们不能任其无序发展,如果只是单纯追求话语狂欢带来的虚幻的自由,那么我们终将陷入更大的空虚之中,弗罗姆曾说“唯独当我们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时,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力才有意义”⑦,只有融入人文主义情怀和足够的理性思考,在内容和形式充实创新,网络直播的全民狂欢才能在理性与非理性中找到平衡点,减少网络不良行为,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注释:
①[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50.
②刘庆华.巴赫金狂欢理论视角下的微博现象[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2):135.
③[美]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1,34,211.
④[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3.
⑤[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33,96.
⑥许正林,李名亮.微博“交往理性”的现实性质疑[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3(03):38.
⑦[美]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M].许合平,朱士群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113.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视频社会责任失当成因及传播正能量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XCA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长潇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位聪聪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