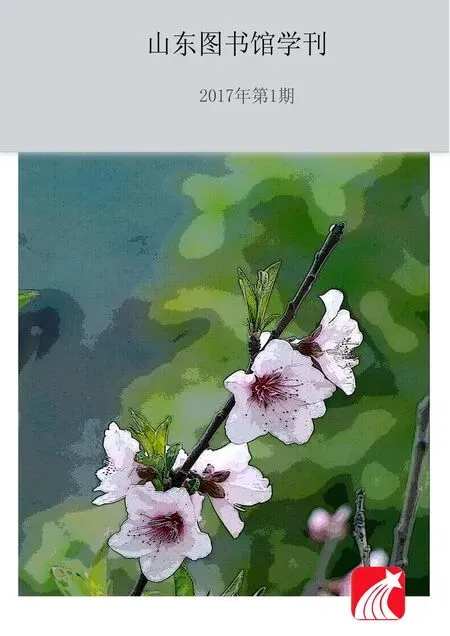国家公开古籍数据库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影印出版的影响
——在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数据库发布座谈会上的发言*
杜泽逊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国家公开古籍数据库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影印出版的影响
——在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数据库发布座谈会上的发言*
杜泽逊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这次国家图书馆的古籍资源数字化,包括古籍普查的数据库,很大。古籍普查的数据库没有图像,但是它的用处非常大,它的成果属于科研成果。我们参加国家清史项目,编了《清史艺文志》。清史委的人老让我们对原书。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量太大。问题就在于,如果原书摆在你面前,难道你就能得出正确理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现在中华书局的书上面有版权页,那还要版本学家干什么?所以古籍目录,它的标准著录,是科研成果,不是见了原书就能正确著录。所以这个庞大的古籍普查数据库,它是古籍界的一个科研成果。学科门类就是版本目录学,它是学,不是一般工作。这个数据库是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科研成果,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历史上第一回。善本书目虽然出了,却不仅仅是善本的联合目录。那么这一次就不是光善本了,所有的古籍都在普查之列,这是非常巨大的科研成果,要这样定性。我们确定一个版本的性质,确定它的年代,也许还有一些办法,而确定它的稀见性就不好办了,这有赖于资源的调查。前一段时间,我向刘蔷老师请教一本书《荔园文草》四卷,这本书只有她那儿有,它的年代并不早,道光刻本,雕版印刷,小小的。我就跟她说该书非常稀罕,她也很高兴,因为是清华大学收藏的。也就是说,稀见性是有赖于资源调查的,而资源调查的手段,是古籍普查,这没什么难理解的。所以这个数据库是非常了不起的科研成果。
第二个就是图像,古籍资源数据库,沈乃文先生刚才说的已经是大行家才能说出来的话,我想这个是里程碑,沈先生刚才表达的意思和我想的一模一样。有了文字才会记录文献,比如书吧。有了纸张又转变了,有了印刷又转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人们的一些特殊的愿望,比如在嘉靖年间就成批量地翻宋版,满足一种意愿。因为宋版少了,而人们重视这个东西,只好翻版。这个翻版的工作一直到什么时候?大概到黎庶昌,就翻得很像原件了。因为那个时候有照相技术。中间翻宋版的很多名家,有黄丕烈、张敦仁、胡克家、刘世珩等,很多。有了影印技术之后,就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影印本,这就比翻刻强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雕版就变成照相了。这个影印就到了《中华再造善本》。这一段的量非常大。比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以古籍影印走得离我们非常近,而且还在继续。
接下来的转折是古籍的图像发到网上。这之前哈佛大学善本通过国图挂出来,还有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内阁文库等等,他们挂出来比我们早。可他们的数量有限,现在国家图书馆挂的这个量非常大,速度快、方便,就像沈先生说的,可以说在短期内超越了所有海内外的古籍资源的数字化。所以这个会改变我们的古籍整理的生态。在这之前刘俊文教授他开发了一个“中国基本古籍库”。1998年我和罗琳、刘蔷等上台湾开会,看到“中研院”开发出来的《南华经》的宋版,它就开发了一部,是全文检索加图像。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数据库,回来就向刘俊文先生提建议。刘先生说没有钱。后来可能有了钱,他们开发出来一万多种书。现在高等院校里面对“中国基本古籍库”高度依赖。后来又开发了“方志库”,就实现图文并茂了,也是高度依赖。没有这个东西好像没法过了,就好像没有冰箱可以过,有了冰箱再没有不能过了,那么一个感觉。手机也是这样。国家图书馆这次的两库,应该是个转折点,是个里程碑,它会改变你研究的生态。
古籍资源数据库对于影印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方自今社长在这里,他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影印会有一个较大的挑战,它不会让影印萎缩,而是会让影印进一步地提升水平,让古籍影印学术化,这是第一。第二,精密化。学术化,选择什么品种?比如增加校勘记,加上学术性的序跋、索引。精密化,是指影印过程当中讹误最小化。因为有了图像,可以对照,你就有所畏惧了。前天我们一个学生赵兵兵看《中华再造善本》当中郑樵的《通志》,发现它少了一页,不是一页而是一拍,把第6页的A面和第7页的B面连成一个了,中间就少了一拍。如果是少一整页的话,一定是原书没有,如果少一拍,那就是漏了,要么漏拍、要么制作过程中多翻了一拍。这个学生觉得很郁闷,说老师这少了一拍,他说没有办法。但是过了大约一小时,他又高兴地告诉我,国家图书馆已经挂出来了元刊本,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影印的精密化,你有了这个数字资源以后,就是一个监督。过去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黄永年先生《古籍整理概论》里面专门有一章叫影印,我觉得这一章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因为有了数字化进一步提高功用。对底本选择的挑战性大了。因为你有可比对的东西了,就知道你选的好或不好。影印过程中的全部附加值到底有多高?就像底本选择一样,影印本身也有评价的重要指标。简单影印要受到挑战。也就是说影印什么书?影印什么本?怎样影印?这三个问题应该是对影印检验的三个方面。
我上午到琉璃厂待了一个半小时,买了一部民国时期影印的《蜀石经》,有八本,回来给吴格先生看,我们就议论。《蜀石经》,据专家的意见是宋拓,刘世珩和他的儿子收藏,以前徐森玉先生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蜀石经》的文章,写的可能是最好的一篇,他就提到刘氏影印出来是八本。为什么是八本呢?大批量的题跋、题词、题诗、题签以及校勘记,附着在拓本的前面、后面。这样我们想象的《蜀石经》的影印应该是拓片,而实际上附加的东西的页数超过了拓片,这些附加的东西就构成了民国影印本独特的珍贵性,就不是那个拓本能代替的了。所以,简单的影印可能会受到挑战。《四部丛刊》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书有校勘记、有附录和跋,有张元济的,也有其他先生的,这样《四部丛刊》的影印本和《四部丛刊》的底本就有了区别,有了底本,也要校勘记,所以影印本的提高,可能会因为数字化加速。至于点校本,那就更好了。因为古书要校,不同的文本要校,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也要校。从书目上看到的同一版本,他们之间印刷的早晚、修版情况,无法区别。从版本鉴定来说,科学院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上对后印本也著录出来了,但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并不谈什么初印、后印。不比对的话,它的差别会很大。宋小字本的《晋书》,《四部丛刊》里有,以前是蒋氏衍芬草堂、丁氏八千卷楼和聊城杨氏海源阁各藏一部,它的字体、版式、行款是一模一样,但是仔细地比对才发现是三个版,可是在这个问题上,版本学界似乎还没有认识。因此《再造善本》就印了海源阁这一部,另外那两部就不了了之了。如果单独都挂出来,自然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数字化对鉴定版本、整理古籍都有巨大的促进。像稿抄本的鉴定,光靠我们古籍专家是不行的。有的人正好研究这个人,对他的书法、笔迹,打眼就能认出来。因为我们平常整理山东文献,对王献唐的字,可以说一打眼就看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是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古籍专家,对王献唐不熟,他也可能不知道是王献唐的稿本,上面没有署名,那就是一个写本。既不知道是不是稿本,也不知道是谁的书。可是到山东图书馆,唐桂艳他们就能认出来,因为他们天天能见到的东西。我们如果挂出来了,自然就能发挥全社会的学者、文化人物的智慧资源,有很多图书就可以确认下来。原来定的抄本,可能是稿本,原来不知道的作者,可能就知道了。所以对稿抄本的鉴定也有较大的促进。
对数字化工程,国家图书馆的这个工程,它的历史意义、里程碑意义,对将来学术研究的巨大促进,怎么样高评都不高,非常了不起的一步,也是一个槛儿,也为全国的公共馆、大学馆、博物馆,其中博物馆尤为严重,树了标,毕竟国家馆是全国的老大,老大做什么样,老小就必须得学,不学他会有压力,所以这个历史意义更大。我就说这些。
*2016年9月28日下午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召开古籍普查数据库、古籍资源数据库发布座谈会。吴格、沈乃文、李国庆、罗琳、杜泽逊、刘蔷、卢云辉、计思诚、史睿、方自今等专家出席并发表意见。会议由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主持,张志清副馆长到会发言。现将教育部长江学者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的发言整理发表,以饗读者。
册府说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