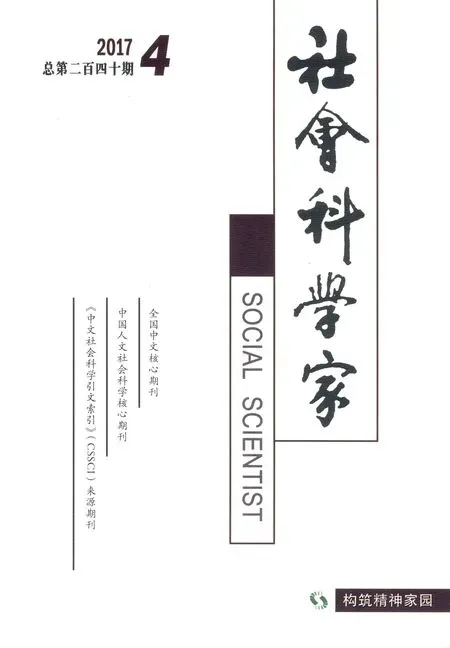批判与构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话语的发展
刘 慧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4)
批判与构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话语的发展
刘 慧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4)
“共产主义”思想是马恩关于未来社会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就必须对“共产主义”话语出场和演变过程展开科学的研究。马恩“共产主义”话语的发展是一个夯实话语基石、确定话语介质、完善话语目标的过程。因此,对“共产主义”话语的把握也主要从以上三方面着手,以此正确把握“共产主义”话语的特点,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话语;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认为,话语是基于客观实践的需要通过社会交往而对现实发展所形成的回应。“对于作为一个话语实践的特殊的话语的分析侧重于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社会性的,都需要关联到话语从中得以产生的特殊的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1]对“共产主义”话语的研究必须回归到文本分析,通过对马恩“共产主义”话语运用的分析,探究“共产主义”话语演变的历史进程,为共产主义信仰的确立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一、批判性出场:“共产主义”话语的提出
共产主义思想早已有之,但概念的使用却是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巴黎的秘密团体中出现。随着法国卡贝和德国魏特林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共产主义”一词在欧洲开始流行起来。马恩“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共产主义”话语的形成基石。“共产主义”作为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思潮,其形成与发展的空间展开主要是在批判性社会思潮的视阈下得以进行。
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探索在对同时期各种学说批判的话语情境中展开。1843年,马克思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写道:“新思潮的优点又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做的结论,也不怕同各种现有势力发生冲突。”[2]这一时期“共产主义”话语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马克思交叉使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即是说,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语境中,二者是相同位阶的概念。他从“异化”和“私有财产”的视角出发,集中批判了两种“共产主义”学说,其一,是以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为代表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这一“共产主义”派别由于没有正确认识私有财产的本质,所以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仅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展开,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定义为人与财富的关系;其二,是以萨米、蒲鲁东和盖伊为代表的“民主的或专制的”、“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因为没有揭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因而并未揭示共产主义的本质。
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3]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社会主义”展开了批判,包括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话语处于批判语境之下,作为一种对时代困境的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各种“社会主义”理论解释力的批判性解读。
当然,马恩对各种“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他们也承认理论不完善的客观必然性。一方面,“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4]“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指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等人)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5]另一方面,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在现有社会经济状况等各方面条件并不完备的情况下,理论越是完善,便愈发纯粹。所以,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仅仅是“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4]
二、多维构建:“共产主义”话语的确立
马恩“共产主义”话语是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以“解放”和“重塑”为话语介质,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话语目标的有机体,历经借鉴吸收、自我扬弃到逐渐确定的过程。
(一)话语基石:两个伟大发现
19世纪7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正是基于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基于新的唯物史观的发现,“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4]基于剩余价值学说,马恩以新的视角为切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生产的过程进行了揭示,从而有力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在,阐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须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4]继而指出“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于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3]通过对同时期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缘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生产状态无法提供历史因而只能从头脑中勾画未来社会的结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也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
(二)话语介质:“解放”和“重塑”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解放”是其重要的话语介质。对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的解放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与探索贯穿其思想转变与发展的全部过程。
1843年青年马克思受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认可青年黑格尔派的无神论思想,希冀通过宗教的批判达到政治批判的目标。在《莱茵河》报工作期间,马克思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德国现实状况,也日益感受到理论对现实解释的乏力。随后,他将目光转到了德国“社会”,将宗教批判视为一切批判的开端,整个解放路径转变为通过宗教解放达成政治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依托费尔巴哈人本学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和“哲学”的相互关系,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也被称为“哲学共产主义”。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主要区别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阐明政治解放所实现的仍然是以资产阶级权利和政治参与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的政治解放,他主张无产阶级要进行“彻底的革命”,继而实现普遍人的解放。随后,借助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的分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各种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5]在《神圣家族》一文中,马克思从实践批判着手,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否定,阐明了世俗共产主义思想。即“世俗社会主义的首要原理把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作为一种幻想加以摒弃,为了现实的自由,它出了要求有理想主义的‘意志’以外,还要求有很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解放”有了全新的认识,“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6]作为历史活动的“解放”,成为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问题,简单地说即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革命化的前提是要认清现存世界的状况,其中包括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脚腕高,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6]马克思第一次全面阐发的他的全新的世界观,从物质生产出发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实现了从世俗共产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渡。
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中,“国家”是其话语形成的另一重要载体。在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国家是“虚幻共同体”,并主张用“自由人联合体”来取代“虚幻共同体”。在“虚幻共同体”中,国家是为解决基于分工所产生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矛盾而产生的一种“独立形式”,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国家”这种形式下掩盖的斗争实质是阶级斗争。
马克思从个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类政治命运的终极关怀出发,提出了国家消亡的理论。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和国家批判说、国家建设理论形成有机的整体。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消亡仅是从国家性质的角度阐释,它要突出的是国家建设功能。无产阶级要对国家秩序进行“重塑”。无马恩关于国家的发展中更为强调通过对国家职能的释放,对人的管理逐渐转化为对生产过程和对物的管理。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三)话语目标:人的价值的实现
马恩对人的价值的关注贯穿其思想的整个发展进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分析,摒弃了国民经济学家探讨问题时的“虚构的原始状态”,主张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指明了要阐释清楚“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的本质联系。”[3]马克思认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而要消除私有财产只能通过工人阶级解放自身的政治形势得以实现。因而,必须要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战友;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产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
第一,“生存条件”改善的需求是价值产生的重要源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整个生活状况而进行的反抗,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尊严的余地。”[3]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也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6]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所呈现的画面成为“一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从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开始,这场斗争就不可避免地透射着对价值的追求。
第二,价值实现的基础在于以革命的方式实现联合。一方面,共产主义并非单一的党派性学说,它的目的在于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另一方面,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对自身“肮脏东西”实现彻底的抛弃,达成利益共识,完成对自身价值的塑造。
第三,价值追求的多样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在此处,马克思更强调的是个人对原有关系的一种“重塑”。而这种“重塑”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使个人获得自由。在《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中,恩格斯主要从经济基础入手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经济的谈论,落脚于价值的追求,尤其是对他人关于“民主”、“自由”的反驳,更是涉及了教育等内容。
三、建设性回归:“共产主义”话语的特征呈现
(一)“共产主义”话语的渐次独立化
对未来社会的探索中,马克思“共产主义”话语的形成表现出逐渐脱离他者话语的特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中,带有深厚的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痕迹,主要依托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通过将“政治解放”扩展为“人类解放”,将“哲学批判”深化为“经济学批判”。1844年,马克思在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也谈到:“您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理解了您的著作。”[2]及至《哥达纲领批判》时期,已经依托辩证唯物主义,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独立话语。
(二)“共产主义”话语的开放性
第一,“共产主义”话语的超民族性。1843年前后,马克思在思考德国现状的时候,希望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找到一条适合德国发展的解放之路。在其探索中,无论探索视野,抑或探索标的,都不仅仅在于解决德国一国之问题,而是展现出鲜明的世界情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6]“这些”国家指英法等国。
第二,“共产主义”话语的借鉴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行管理做出了分析。“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4]马克思把拉萨尔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恰恰说明,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存在一些资本主义“色彩”,这种“色彩”并非是“倒退”或者是对资本主义“模仿”,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也正是要克服或借鉴的要素。因此,资本主义的某些痕迹会存在,新生社会要经过自身的不断调整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三)“共产主义”话语的阶段性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对价值的追求需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谈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认为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仅消除了一定的“不公平”并没有实现完整的公平。在这一阶段中,个人收入会呈现出不同水平是必然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了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国家和各项权利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7]
通过对马恩“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析,不难发现,从话语的提出、构建到完善,是一个依托话语情境、奠定话语基石、确立话语介质、完善话语目标的过程。它们四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共产主义”话语发展的强劲动力,推进“共产主义”信仰的生成和发展!
[1]诺曼·费尔克拉夫,殷晓蓉.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1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2;421;291;50;105;20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5;789;796;798;363.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197.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9;527;206-261;297;527;528;185-186;527;11.
[7]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A811
A
1002-3240(2017)04-0033-04
2017-02-02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主义本质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启示研究(批准号TJSK15-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阶段成果;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慧(1984-),女,山西吕梁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法学博士。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