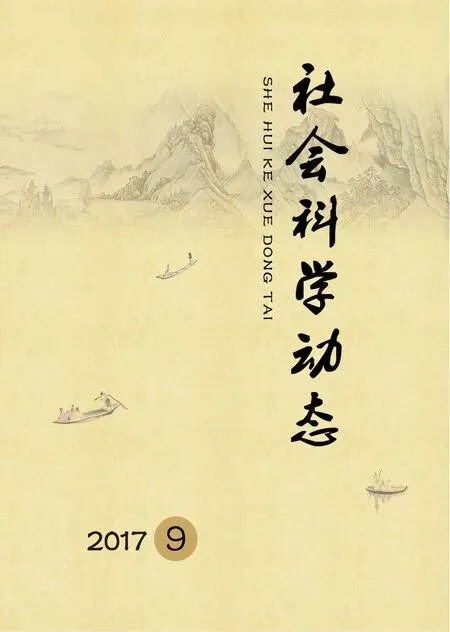“后诺奖”时期莫言小说研究的瓶颈和路径
——兼及莫言研究的分期问题与刘广远、王敬茹商榷
姬志海
“后诺奖”时期莫言小说研究的瓶颈和路径
——兼及莫言研究的分期问题与刘广远、王敬茹商榷
姬志海
自2012年10月到2017年5月,国内外学界对莫言研究的批评文章骤然增多,这无疑意味着针对莫言及其小说创作的研究,更大一股蓄势待发的学术发展性与突破力正在启动。这其中,刘广远、王敬茹在其发表的《莫言研究综述》一文中提出了针对莫言研究30年的“三分期法”:1985—1990年,探索期、高潮期;1990—2000年,质疑期、批判期;2000—2010年,成熟期。此种观点实可商榷,1995年(莫言《丰乳肥臀》的发表),2006年(莫言被授予“福冈亚洲文化奖”)和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这三个节点理应在莫言研究的分期中得到必要之体现。又及,针对“后诺奖事件”以来学界关于莫言研究的新焦点、新瓶颈以及可能性的解决方案诸问题,也没有在其文中得到应有之体现——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后诺奖时期;莫言研究;新意义;新焦点;新瓶颈;新路径
一、“后诺奖”时期莫言研究的意义、概况和瓶颈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发展流变一直都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莫言更是这其中不可绕开的重量级作家之一。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的发表,“重感觉叙事”的莫言开始为文坛所侧目,其后《金发婴儿》、《爆炸》、《球状闪电》等一大批同类型中短篇小说接连发力,特别是1986年以《红高梁》为代表的红高粱家族系列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问世更使莫言成为拥有众多读者的先锋派小说家。从90年代的《酒国》 《丰乳肥臀》开始,莫言尝试狂欢化的多声部叙事技巧,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进入新世纪以来,他更是以《檀香刑》《四十一炮》 《生死疲劳》 《蛙》等多部均可堪称经典的长篇小说文本,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小说作家,跻身于世界一流小说大师的行列。2006年7月,继巴金之后,莫言被授予了“福冈亚洲文化奖”,时隔六年,他又一举斩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个中国籍作家。
倘以“莫言”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即可发现,自2012年10月到2017年5月,国内批评界对莫言及其小说创作的批评文章骤然增多。与此同时,一大批国内知名学者还先后在北京、济南各地举行了若干场针对莫言创作进行专题分析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以《当代作家评论》 《小说评论》为代表的重量级学术期刊也先后开辟针对莫言小说的研究专栏……影响所及,越来越多的台湾学者与海外汉学家也先后接踵加入到这一讨论和互动中来。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关于莫言及其小说的研究势必成为一个吸引国内学人和国外汉学界乃至国外文学界众多研究目光的新的“磁极”和“黑洞”。也即是说:针对莫言及其小说创作的研究,更大一股蓄势待发的学术发展性与突破力正在启动,更多具有巨大创新潜力的、新的学术知识生长点也正在形成。
笔者以为,在莫言获得诺奖以后的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对之进行研究不仅仅是学界盲目趋时的“大势”所趋,从更深层面的意义上来讲,它还是建构更科学、更合学术逻辑的中国现当代白话小说史体系的学术要求。自2012年10月11号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迄今,学界关于“莫言是否已经超越了鲁迅、中国当代小说是否已经全面超越了现代小说”的争论就一直众说纷纭、聚讼不已。大体看来,对此问题持质疑态度的学人不仅是大有人在似乎还略占上风,先是有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在京专题学术研讨会上传檄在先,声称“我认为他(莫言)是不会获奖的。所以他获奖后我受到了莫大的打击。诺贝尔奖让我失望,诺贝尔文学奖失去了起码的文学性的水准,除非全球已经没有真正的文学了”①;继而又有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发难于其后,其在2013年2月下旬的《文学报》上断言: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整体上与现代作家之间的差距委实不可“以道里计”云云。②以莫言及其小说创作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小说作家和当代小说到底该进行怎样的文学史定位?当代作家的小说究竟是否应该进行经典化的学界认证?莫言(包括另一位汉语小说作家高行健)等在国际上接连斩获文学奖项的事实本身能否视为中国当代小说取得世界认可的佐证?时至今日能否认定中国当代小说作家和作品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特有的时代特色,并足以与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及其经典创作可以颉颃并举,从而已经成长为新的一代之雄?上述这些疑问,相信大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莫言及其小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中得到启示和解答。
总体看来,历经众多研究者的广泛探讨和深入对话,学界针对莫言及其小说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表及里、渐次深入的过程,也初步积累了一些可喜的研究实绩和优秀的学术成果:就国内来看,除了发表在各级刊物上的专题文章,以及众多资深学者的研究著作(如张志忠教授1990年出版,2012年修订后再版的《莫言论》;贺立华和杨守森等于1992年发表的《怪才莫言》和1997年作家钟怡雯的《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等)以外,尚有1992年、2005年和2006年分别出版的三套《莫言研究资料》和200部左右被中国知网收录的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当然,有关莫言的研究不仅限于国内学界,而且远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就笔者所接触到的研究材料来看,大陆之外的莫言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日本、法国、越南和港台地区。
以下,笔者拟对学界关于莫言及其小说研究的基本观点、主要思路和研究范式等问题做一次简单的扫描和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分别就当下学界在莫言研究中面临的研究范式上的瓶颈问题、30多年来的莫言研究阶段的划分界限问题、2012年“后诺奖事件”以来学界围绕着莫言研究所出现的新的聚焦点问题进行阐述和评析。
早在1997年,陈启德先生就初步罗列了截止到彼时学界关于莫言研究的四种向度③:即一是“怪味”寻踪,“对莫言作品大胆的艺术探索,色彩语言运用的奇特,莫言作品中的生命意识、酒神精神和莫言‘高粱地’的传统文化精神进行研究”,这以张卫中在《论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张志忠的《莫言文体论》、张清华的《祖宗遗产的启示》和胡河清的《论阿城、莫言对人格美的追求与东方文化传统》等为主要代表。二是审丑扫描。针对莫言《红蝗》 《丰乳肥臀》等文本创作,一批学者“集中而又犀利凶猛地批判了莫言的反文化、非理性的书写丑恶事物”,这以杨联芬的《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贺绍俊、潘凯雄的《毫无节制的红蝗》,王干的《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创作批判》,张学军的《莫言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夏志厚的《红色的变异——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红蝗〉》和颜纯钧的《幽闲而骚乱的心灵——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莫言小说》为代表。三是感觉探微,主要探讨了莫言作品独特的语言风格,以钟本康的《感觉的超越、意象的编织——莫言〈罪过〉的语言分析》、朱向前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大卫的《莫言及其感觉的宿命》和杨联芬的《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等为代表。四是文体透视,对莫言小说中自觉践行的文体意识进行了归纳。以朱向前的《莫言小说“写意”散论》和季红真的《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为代表。
1995—1997年可以视为莫言研究的第一次小的高潮,因此陈启德先生对此所作的综述和总结大有必要,这之后,越来越多的批评文献将视域重点集中和聚焦在了莫言小说既定的文本自身的探讨和分析上:诸如对莫言艺术创新的研究;对其作品中所展现的民间立场、生命意识、女性主义、欲望化书写、审丑、结构主义叙事学、狂欢化叙述层面的研究;对隐藏在其文本间的东西方文化的共鸣与碰撞的研究;或者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忖度其小说的主题研究(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主题研究多是国外学界的研究用力所在)……
应该承认,学界针对莫言及其小说的研究的确斩获和积累了不少不乏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迄今很少有学者能够从M·H·艾布拉姆斯的“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接受”这一整体的、系统的角度对莫言及其作品创作进行“博观”“圆照”式的综合评价(当然,张志忠教授的《莫言论》有过这种努力的方向,但其对莫言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文本的研究分析尚有待深入,且类似的综合性研究专著毕竟屈指可数)。按照M·H·艾布拉姆斯的解释,文学活动有四大要素,即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作为文学活动组成部分的文学批评,也要兼顾这四个要素。倘若“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就是说,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④的话,就会造成文学批评的偏执,偏执的结果就自然分别形成了以作者创作为依据的“作者中心”范式、以文本的语言结构为依据的“文本中心”范式和以读者接受为依据的“读者中心”范式——应该看到,虽然也有不少论者在“作品”之外的其他三个领域偶尔提及,却缺乏全面综合的眼光和专门深入的论述。这种有失片面的研究,似乎与莫言小说所取得的不菲实绩及其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地位颇不相称。也难以(倘若仅从作家在文本中说了些什么来考察的话)令人信服地解释莫言及其小说创作的复杂性及丰富性——这也即是目前学界关于莫言及其小说创作研究的亟待改进之处。
所幸这种失之偏颇的研究界窘况正在发生令人欣慰的转变,笔者通过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在一些著名高校的硕博论文中发现,一种从“反映论,创作论,文本论,接受论”这一互相通约的、整体的、系统的观照角度切入到莫言小说的研究努力已经初露端倪:比如2011年山东大学宁明的博士论文《论莫言创作的自由精神》、2012年复旦大学斋藤晴彦的博士论文《心理的结构与小说——用分析心理学解读莫言的作品世界》和2013年西南大学左秀的硕士论文《制度困境下的生命追思——以莫言〈蛙〉为中心》,都分别从作家的创作主体性、作家创作的心理挖掘、作家与其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写作体制之间的关系变化等层面来着眼,昭示了这种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学术创新方面的潜力。
二、莫言研究的分期和“后诺奖”以来学界的新焦点
针对莫言研究界更新速度快、更新频率高的客观事实,为了将来研究者的研究便利计,笔者以为对30多年来的莫言研究历程进行阶段上的划分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也就对渤海大学的刘广远、王敬茹在其《莫言研究综述》⑤中提出的“三分期法”格外关注,但笔者在阅读之后发现,刘、王在参照和借鉴黄萍在《莫言小说研究述评》⑥中提出的按照历时顺序分期的三分法(即是发端期1985年、高潮期1986年—1990年、拓展期1990年—)的基础之上建构的所谓新的“三分期法”(即是1985—1990年探索期、高潮期;1990—2000年质疑期、批判期;2000—2010年成熟期) 是大可商榷的。首先,这种新“三分法”说完全忽视了1995年(莫言《丰乳肥臀》的发表),2006年(莫言被授予“福冈亚洲文化奖”)和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这三个节点在莫言研究的分期中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性。其次,这种所谓“三分期法”,也主要针对的是莫言2010年之前的创作,而实际情况是2010年特别是2012年以后迄今的莫言研究又有了最新的变化和趋势,没有引起二人的注意,正是基于此,笔者通过对上述两种三分法进行适当的整合之后,将学界针对莫言及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5—1995年,可以视为是初步探索期;
第二阶段为1995—2006年,可以视为是深入探讨期;
第三阶段为2006—2012年,可以视为是发展成熟期;
第四阶段为2012年诺奖事件以后,可以视为是高潮和新变期。
在上述的四个阶段,针对莫言及其小说的研究和对话中,各批评者和诸位学人之间既有着共识和默契,更有着矛盾和分歧。这其中的矛盾和分歧自1995年莫言的《丰乳肥臀》付梓以后开始急剧凸显,并随着莫言研究的深入而日趋激化,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探索期的研究文献大多限于对其成名文本《透明的红萝卜》和改编电影获奖后名声大噪的“《红高粱》家族系列”的追踪式评论,这时对莫言的创作批评还属于比较肤浅的阶段。90年代以来,莫言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跳跃式的发展、转型期,多声部共鸣式的狂欢化诗学的小说美学创作元素逐渐进入到莫言的小说试验中来。1995年,彰显着强烈的“伦理狂欢”色彩的《丰乳肥臀》的发表让文坛对莫言的创作重新瞩目和深入地探讨,由于莫言超前的小说意识、先锋的小说风格超越了当时学界的接受视域,是时大量的批评文章充满了道义讨伐色彩颇浓的质疑和批判,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批评者(以陈晓明、张清华教授等为代表)高度地肯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划时代的”文学史意义。2006年之后,伴随着莫言被授予“福冈亚洲文化奖”的轰动效应和越来越多的重量级的长篇小说的先后问世,批评界对莫言小说的研究有了更加理性和深入的探讨与争鸣,莫言研究开始进入成熟期(从硕士博士的论文情况来看,2002—2006年四年的硕博论文统共只有不到30篇,而在2006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高校研究莫言及其小说创作的毕业论文就激增到了前四年的五倍之多)。而到了2012年10月以后,如前所述,由于“诺奖事件”的直接推动,学界对于莫言的研究进入了高潮和发展新变期,这期间除了许多知名高校的硕博论文继续关注莫言及其创作之外,出现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围绕着“莫言是否已经超过了鲁迅、中国当代小说是否已经超过了现代小说”的话题,学界一度展开了激烈地争锋,且至今这个学术公案都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
如前所述,这次争锋首先由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对莫言获奖小说的含金量进行质疑和口诛笔伐在先,继而又有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教授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火药味儿”更足的檄文《因莫言获奖而想起鲁迅的一些话》殿后,如果说肖鹰教授的批判还只限于莫言自身小说创作的话,那么郜元宝教授则是把讨伐对象无限地扩大到了所有当代小说作家身上。二人不无偏激的观点旋即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许多学者都先后著文对此予以批驳,许多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也围绕着该论争先后举行。
在以黄桂元先生为代表的不少学者看来,“郜教授对当代中国文学已经超过现代文学的说法耿耿于怀,使人莫名其妙,因为并没有人作如是说,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一种虚构和想象”⑦。这句话仿佛在向读者传递这样一种信息:郜教授的这种——在没有任何人开口设问的前提下,无中生有地“一个人演双簧”,非得要在“当代中国小说”和“现代小说”二者之间较雌论雄、争长竞短,分出个强弱高下不可——的行为,委实无异于找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荒唐之极。其实,在这貌似荒唐的漫画背后,未必就单单是郜教授一个人在那里孤军与“风车”大战。因为事实上,自从莫言成功问鼎诺奖这一文坛重磅信息传出迄今,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就一直在酝酿、发酵,彼时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与郜教授持相同、相近观点的学者、批评家不仅是有,而且数量上也绝不会只是寥若晨星的少数几个。
黄桂元教授对二人观点的批驳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共鸣,这其中,针对郜元宝教授们在莫言之于鲁迅、中国当代小说之于现代小说二者关系上所持的这一不无“意气”和“偏激”的论断,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的观点似乎更为中肯,他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汉语新文学出现了一个‘准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长篇小说,可以被称为是五四以来最成熟的、最复杂的、技术含量最高的长篇作品,中国文学从五四时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到了一个总结性阶段、一个收获期……莫言获奖不仅是‘新时期’文学的总结,也是整个汉语新文学一百年历史成熟的标志。并不是莫言的作品说明汉语‘新文学’成熟了,而是整个汉语‘新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成熟和收获的局面。这也是莫言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级作家的背景和基础。事实上应当把鲁迅、巴金、沈从文、老舍、莫言、余华、贾平凹、王安忆、张炜、铁凝、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作家看成一个整体,汉语新文学就是这样一个整体。”⑧
客观地讲,莫言们较之于鲁迅们、中国当代小说较之于现代小说,或许从整体而言还不能说是业已形成了双峰并峙、秋色平分的格局,但两者之间似乎也并不存在着什么清晰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所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前者之于后者,既有其不容讳饰的诸多“不及”之处,同时亦有超越先贤们的不菲创作实绩——以鲁迅们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作家所取得的创作实绩委实让人高山仰止,足以彪炳于文学史册,对于这一点谁也不能、也不想去否认,但是,中国汉语新文学的长河,却不能因他们的消逝隐耀而干涸断流。所谓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譬之文坛则才人代出而风骚各擅。薪传至今的中国汉语新小说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理所当然地也会取得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建造属于他们时代的自己的丰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顺理成章之事。对此,评论界不应该总是热衷于缅怀逝者,醉心于贵“昔”贱今、厚远薄近。事实上,以莫言们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沿着由鲁迅们为代表的无数开路先锋开辟出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时,在继续鲁迅们未竟的事业、替他们修残补缺时,也在替他们发扬光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文学平台上,在总结和处理这后30年的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世界文学这三者之间的继承和对接关系的同时,在随同时代的移形换位,60多年以前对鲁迅们产生过极大影响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实质上就是现代主义)诸理论已经被今天汹涌澎湃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挤出文学中心的今天——必须阐明的是,虽然西方的同步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早在“五四”时期就已传入中国,但其始终都处在强大的 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压迫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展而尽显其孱弱一面,这种情况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大大改观——以莫言们为代表的当代作家在新的空间和高度上的所作出的开拓与创新成就,已经远非当年的现代作家们所敢梦想!
三、“后诺奖”时期莫言研究的新路径
所谓“圆照之象、务在博观”,针对既往研究中研究者人为割裂文学活动四大要素(即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所造成的研究偏颇,笔者以为,对于莫言及其小说文本的研究应该采取的是相对“折衷”的态度与更加综合多元的方法。
这里所谓的“折衷”是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倡的一种总体批评观,《文心雕龙·序志》云:“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⑨“折衷”意即“折中”,意思是说对作家的批评应该是持论公正、恰如其分。即是所谓“扣其两端而权衡之”——针对莫言及其小说创作来说,就是须采用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整体把握与个案解读相结合、历史原则和逻辑原则相结合的系统多元的研究路径,通过共时与历时的纵横对比,把莫言的创作放进整个中国百年白话现代小说的谱系和发展流脉中去衡量,做到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的同时兼顾,以此全面、多元、流动发展的宏阔视野来全面观照莫言的独特贡献和创作得失,而不是一味地进行廉价地吹捧或者是充满学究气的简单棒杀。
这里所谓更加多元的方法是指在结合“反映论,创作论,文本论,接受论”这一互相通约的、整体的、系统的观照角度切入到莫言小说研究的具体操作环节之时,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与之相应的不同的研究方法(由于预计使用到的中外文艺理论、批评方法很多,笔者下面还要进行必要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任何文艺理论或者研究方法本身并不存在着什么清晰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别,而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分。它们在研究不同的对象时各有自身的优缺点,因此应该加以灵活地运用。在使用各种批评理论时,一定要注意它们的适用性,坚决避免把文本丰富无比的信息当作是个人演练新的批评方法、时髦的批评术语的实验平台和表演现场。应该积极地把自己的研究结论放在和前人的学术既有成果的对话中去,尽量开拓表面上似乎不可通约的各种理论视域、学科领域之间的可能性联系。力争在对莫言及其小说解读中,最大限度地将那些从前被忽略和删除的、处于各种理论缝隙之间的、因为自身不具备某种批评理论的特色而显得“无色调”的内容和信息展现出来。
循此思路,笔者以为针对莫言及其小说创作的研究不妨从以下五个层面,依照时间的和逻辑的双重次序进行:
第一,莫言创作所面临的历史前提;
第二,莫言的自由主义主体精神;
第三,莫言小说的创作实绩与不足;
第四,莫言创作的独特贡献及其文学史意义;
第五,莫言作品的阐释与接受。
在第一层面的叙述里,拟解决的问题是——莫言在其作品中写作的对象和表现的内容来源——即是莫言“写什么”的问题。研究者不妨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反映论等作为研究这方面的基本方法,即把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其表现的对象必然是作为其形而下基础的特定社会存在的理论。以莫言生长在其间的共和国60多年以来的客观历史真实为中心(兼及其作品上溯的不同时代的历史叙述,当然,这种叙述也是经过修饰的,但文学研究又不得不在既定的历史记述里进行)作为解读其创作表现对象的材料准备和来源的问题。固然,文学表现是以人为中心的,但是,这里人的思想情感、性格行为又必然和特殊的历史阶段相联系。
在第二层面的叙述里,拟解决的问题是——莫言作为体制内作家是如何处理自身的作家主体性与体制的规范要求之间的关系的——即是莫言怎样写的问题。研究者不妨借助知人论世研究、传记研究和心理学研究以及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等作为批评理论进行深入探讨。
第三层面应是论述的重点,在此一层面的叙述里,拟解决的问题应是作家莫言的创作主体性是如何在对体制规范的接纳和潜逃中具体表现在其形而下的文本之中的:从小说作为反映时代苦难、映照客观生活真实、社会痼疾、历史真相的工具和载体的层面而言,莫言表现出了其对于社会良知的尊重、默认、遵从和坚守;在这个意义上的莫言是个有什么说什么的老老实实的记录者;从小说作为愉悦心灵感染读者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个层面上来说,莫言又以其先锋的姿态、神秘独特的故事资源、变幻莫测的叙事技巧、自由狂放的叙事语言屡开风气之先,始终处于对传统叙事逃离、超越乃至颠覆的不太老实的胆大妄为特立独行的叙述者。在这一层面,研究者不妨采取时间线索的纵向表述,对莫言作品的艺术探索做开放的追踪式批评。这里研究者不妨借助的批评理论有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批评中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利奥塔的解构宏大叙事理论、女性主义批评、身体意识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祛魅理论、异化理论和重建主体性的理论等等,并在肯定其创作实绩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乃至缺陷之所在。
在第四层面的叙述里,拟解决的问题是试图表述莫言在整个中国现代白话小说100年发展谱系中的位置问题,他带给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他现在的民族化转向带给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启示是什么。本章研究者不妨将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出可行性的比较,弄清楚他们之间的承传与发展。
在第五层面的叙述里,拟解决的问题是对莫言作品的传播与接受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者不妨借助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和伊赛尔、姚斯的文学接受理论进行研究。
以下笔者就这种综合研究范式自身具有的潜在创新可能性及其应用价值略作展望。
如前所述,依据M·H·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必须要兼顾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四个要素”的观点和刘勰“折中”的文学批评准则,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莫言及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尽管非常丰富并且具有呈几何倍数上升的趋势,但是这种研究往往只能流于“片面的深刻”而缺乏整体的观照。尽管张志忠教授的《莫言论》以及笔者上文所列举的若干篇硕博论文中的研究路径对于目前的莫言研究现状有着某种纠偏救弊的良好导向作用,但是,作为践行这一综合研究方法的开拓者,他们的研究积累还不是非常的深厚,其中仍然有许多没有说透的或是没有说到的或是虽然说到但是依然尚有可以商榷余地的地方。比如,在他们的论著中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有失“折衷”的倾向,均有对莫言创作的不足和缺陷方面谈得不够深入之现象。其次,在一些针对莫言及其小说研究的硕博论文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学术硬伤,试以宁明的博士论文为例,就可以对这种研究中存在的武断、随意性进行斑豹,其若干观点的确让笔者不敢苟同:宁明在其博士论文《论莫言创作的自由精神》⑩的前言中断言:“而到了90年代和21世纪,……自由空间可谓史无前例,一切内容都可以呈现,一切观点都可以表达,原先的禁忌全部成为创新的靶子,包括性,包括道德,包括习惯,包括习以为常,价值观彻底实现了多元化……在这场创新型的‘文学革命’中,真正实现了‘创作自由’,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以为这种表述大为可疑,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的松绑的确是推进文学繁荣的不容否认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种境况似乎还没有达到所谓的“彻底实现了多元化”的地步,至少当代体制内外的中国作家在其任何付梓的文本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方向还是有的吧,对这种创作环境的陈述可以以“一元多向”(这里的一元就是上述的两个坚持,多向是不同的审美和价值取向)来概括似乎更为合理。彻底多元化和一元多向貌似是差不多的表述,但后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直接限制或者决定了莫言小说的取材领域和方向却毋庸置疑。笔者以为宁明先生的这种论述无形中就放大了作家的创作主体性,有为情造文的致命缺陷。不能作为支撑其论点的材料和论据。其次,宁明以为作为小说作家的莫言对于自身主体性的体认所赖的自由精神主要是从西方过来的舶来品——这里宁明先生应该是断章取义地采用了湖北大学刘川鄂教授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说法,对此种结论,笔者仍然认为过于轻率,笔者以为,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客观地浸透在中国传统优秀文人的血脉里的,从先秦到清末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坚守自身主体性的作家群的存在,他们才敢于以其哀情著书、以其哭泣著书、以其不平著书、以其发愤著书、以其性灵著书、以其怨毒著书、以其怒吼著书……他们的这哀情这哭泣这不平这愤慨这性灵这怨毒这怒吼汇聚起来的巨浪洪波,不断地冲决封建正统思想中的由“发乎情止乎礼义”、“美刺讽谏”、“诗教”与“载道”……等共同搭筑的堤坝,终于成就了中国古典文学渊停谷储,钟灵毓秀,洋洋乎大观,郁郁乎文哉的辉煌。这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对于主体创作自由的追求和捍卫精神作为基因密码传递给了莫言,而这一遗传基因无疑从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莫言们的小说创作。
通过以上讨论,不难发现,在处理学界既有的莫言研究分期的问题上,1995年、2006年和2012年这三个特别重要的年份不仅要考虑进来,而且应该将其作为划分莫言研究阶段的重要节点矗立起来。在“后诺奖时期”莫言研究的方法上,针对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学界应该采取更加广阔的多元视角——即是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接受”这四个可以互相通约的扇面——作为进入的研究路径,惟其如此,才不致在研究中失之偏颇,从而在这种内外结合的综合研究视阈中开掘出更多的学术创新点和“知识增量”来。
注释:
① 参见高旭东等:《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② 郜元宝:《因莫言获奖而想起鲁迅的一些话》,《文学报》2013年2月21日。
③陈吉德:《穿越高粱地——莫言研究综述》,《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253页。
④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⑤ 刘广远、王敬茹:《莫言研究综述》,《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⑥ 黄萍:《莫言小说研究述评》,《新世纪论丛》2006年第4期。
⑦黄桂元:《被消费的鲁迅与被纠缠的莫言——兼与郜元宝先生商榷》,《文学报》2013年4月4日。
⑧ 张清华:《从鲁迅到莫言,这是一个谱系》,《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11月2日。
⑨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页。
⑩ 宁明:《论莫言创作的自由精神》,山东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论文,2011年。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后诺奖时期’莫言研究的综合路径”(2014236);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三十年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家创作嬗变论”(KYCX17_0008)
I206.7
A
(2017)09-0055-07
姬志海,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