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和墨香
臧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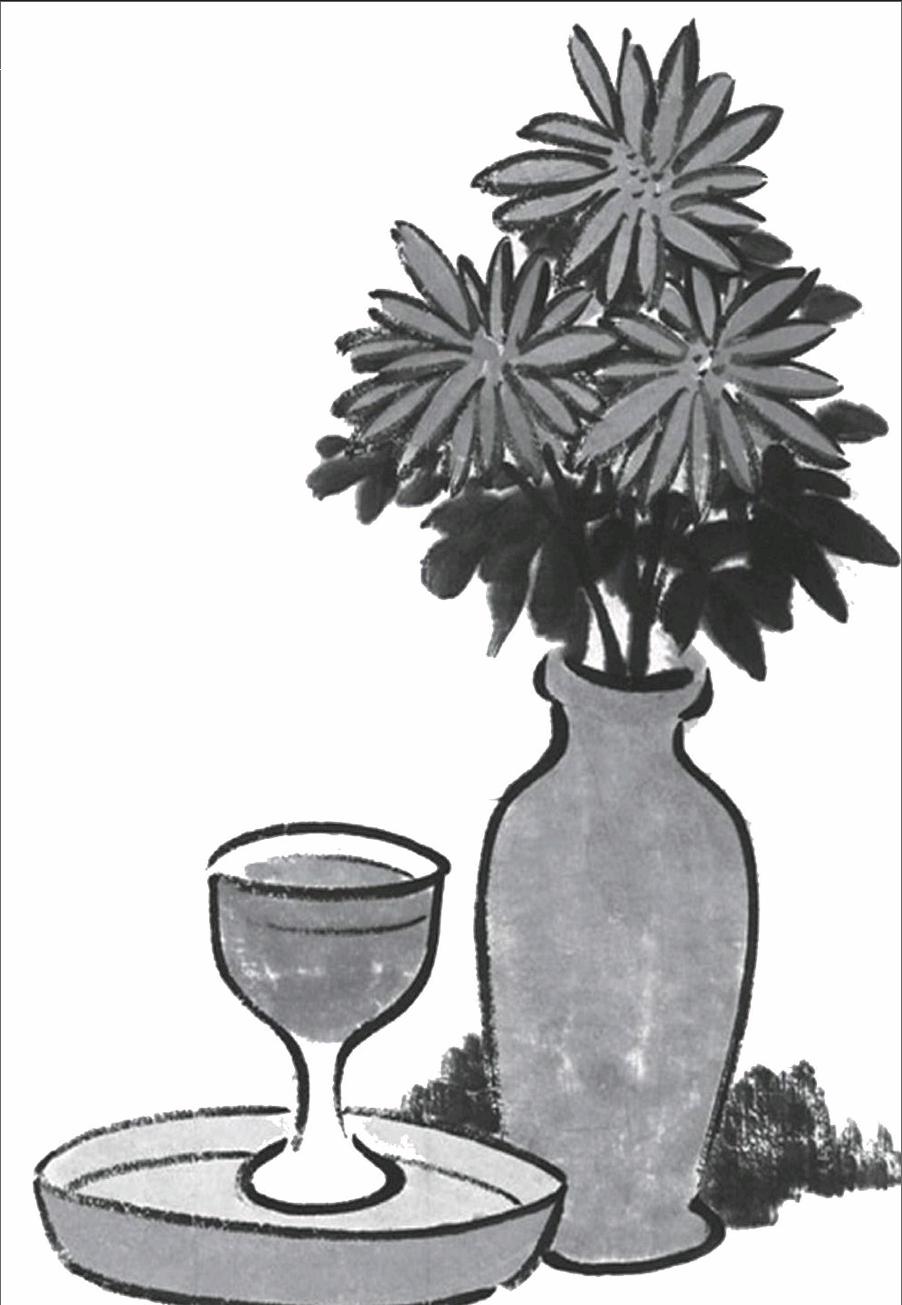
我的四合院,幽静宽敞,足供盘旋。我的会客室不大,七八人便告客满。看上去,它并不富丽堂皇,但风情别具,典雅朴素。四壁书画,虽非长廊,古有陋室之铭,我则重友情和墨香。常令嘉宾游目,神色飞扬。
我爱朋友,也爱书法。50年来,我恳挚而热情地向文坛前辈或同龄作家索求墨宝。半个世纪的积累,得30多幅,会客室不能容,有十余轴还珍藏于内室。古人云“以文会友”,我是书画满墙。
我的这些文友手迹,不少作为插页印在书上和书法杂志上,有的出版社,要求辑成一册出版,为我婉言谢绝。可以自豪地这么说:我成为拥有如此之多的“作家字”的收藏家了。
东墙第一幅,是王统照先生的。王先生,在作家中,以书法著名,学欧带赵,功力极深。笔笔含蕴,味厚耐看。此幅,写的是杜诗,没有月,从“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句中的情味看来,可能写于晚年。款式甚特别:“克家补壁统照。”缀于最后,令我异常亲切。
接着是冰心同志的,她极少用毛笔写字,也没见过她的“词”作。这一幅上,写了一首“旧作”词:“敬毛主席词二首。”为求她的字,如同索债,5日一封信,10日信一封,她在寄字的信上有这样的话:“克家:看到你的来信,我浑身急得出汗!”我得此“二希”,吟诗志喜、志谢。诗云:“高挂娟秀字,我作壁下观,忽亿江南圃,对坐聊闲天。”
排在第三的,是闻一多先生为国捐躯的前二年,为贺我“四十初度”而挥毫的,从昆明寄到我重庆寓居“歌乐山大天池六号”。写的《诗经》里的一首诗:“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闻先生治印有名,在这幅字上所用的一方,在别处不曾见到过。字与印,成为双璧,弥足珍贵!
再下边是郭沫若先生的一幅,1944年写于重庆天官府四号他的住所。字,写得极洒脱自然,精神贯注。所写内涵,意义深远,从事写作的人,极可取法。兹将全文录出如下:
“生命乃完成人生幸福之工具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欲求人生幸福之完成。必须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均充实具足,以文艺为帜志首,尤须致力于此,内在生活,植根欲深,外在生活,布枝欲广,根不深,则不固,枝不广,则不闳,磐磐大树,挺然而独立,吾企仰之。”
聞、郭先生的两幅字,抗战胜利第二年,我作为爱人郑曼的眷属乘拖轮从重庆东下,大江中船几次颠危,条幅受到浸润。到北京之后,
重新装裱,有此际遇,故倍加珍惜。
紧挨着郭老的是于立群同志的手迹。我与立群1938年相识于武汉,是熟悉的朋友。她书法有功力,能大能小。给我写了一幅,我说:再写一幅。这幅写的是毛主席的《清平乐》词,时间是1975年3月。她有时来访,坐在西边沙发上,凝视闻先生写的那条字上的钟鼎文,长达十多分钟,日不转睛!郭老草书学孙过庭,立群同志也同一路数。
唐驶同志是老朋友了,少我近10岁。他博识多能,我曾以七律一首相赠,其中颈联是:
“追随鲁迅悃诚布,
媲关唐俟佳话传。”
他追随鲁迅,杂文到了乱真的程度。唐驶同志能文,也能诗。条幅上写的是首五律,步胡绳同志国庆诗原韵的。
唐驶左手是沈从文先生的。我称沈从文为先生,不是一般意义的,他是我“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老师。他是著名作家,成绩卓著的学者。能诗,书法,章草有名,他写给我的这幅,颇为出众。行长,每行多达30字,共四行,未角又缀蝇头小楷二行。下落:“克家老友雅正沈从文乙卯年七月逢四”。解放后,二三十年,住处相距不远,我不时到东堂子胡同51号去谈心、话旧,甚是亲切。他几次到我处来,送我乾隆时代的深红彩笺和古墨,但敲开我会客室的门,放下东两转身就快步而去,我追之不及,感受颇多。我知道沈先生为人纯朴、亲切、谦逊,对事刻苦、严肃、认真。
转到北墙。
东面高悬吴作人老友的一幅金鱼。抗战刚开始,他从法国归来,到了“第五战区”,我们在鸡公山初识了。解敢以后,他一个小院,我一个小院,两院相望,来往时多。50年代,他给我画了一幅画:芦苇池塘,一鸿翘首,另一飞鸿翻身作下落状,极富诗情,我久看不倦,像读一首含蕴的好诗。不幸,“10年间”化为飞灰!四凶垮后,函作人再补了这幅。我在信上说:光画金鱼觉单调。他添了荷花荷叶,但总感以金鱼比飞鸿则不如远矣。可惜飞鸿己沓,连指爪也没留!
北墙正中,高悬一特大条幅,上面只写一个“寿”字,硕大无朋,触目动人!这是刘海粟先生的大手笔。上款:“克家诗人八秩大寿”,下款是:“刘海粟年方九十”。这个“方”字极有味。他年已耄耋,出国旅游,十登黄山作画,乐此不疲。
刘海粟先生大作的下手是诗友刘征为我八十寿辰以工笔拓的一株老树,根深叶茂。他诗文俱佳,是我要好的老友,而对他长于绘事,我却是新知。
从北墙到西墙。
首先是俞平伯先生的手书诗三首,系泉城济南名胜“历亭事”“北极阁”“张公祠”记游之作。这几个地方,我十分熟悉,读了这些诗,觉得亲切而富于情味。小楷,工整而雅致。这幅字,写于1957年,系函求得来。
张光年同志,1938年初会于武汉,再见于重庆,三欢聚于首都北京。交深情亲,是我老友。多年交往,印象最深的,是咸宁干校那段共同的生活。田间劳动,月夜值班,冲风淋雨,生死相依。14年前,我曾写了这样一首诗赠光年:“难忘江湖旧日情,经时相念不相逢。南天犹忆中宵里,对坐微吟共月明。”大前年,我八十生日,光年来贺,并赠我一诗,系他记干校生活的长诗《采芝行》中的一段,上款题云:“克家兄长健康长寿”,光年比我小8岁。他的字,颇流
利,诗也多味。
下边,请看叶圣陶先生的字与诗。诗云:“己凉庭院蛰不语,风拂高杨似洒酒。一星叶隙炯窥予,相去光年知几许。”诗,极富哲理意味;字,极工整,一笔不苟。上款题云:“克家先生命写字,书去年秋所作小诗以应之,希两正。”从诗与字中,也可以窥见叶老之为人,这幅字写于1975年7月。
与叶老的字并肩而立的是茅盾先生的一幅。茅盾先生十几年来共为我写了两个条幅,在奸人横行的年月里,朋友告诫我说:
“字上的诗,恐有碍!”我仔细推敲,确实。茅盾先生的这首诗,写着:“读稼轩词,七气年夏作”,第二年就写给我了。首联:“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尾联:“扰扰龟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听劝告,我另换了他一幅,系写一个外国女歌唱家的,富有爱国情调。我把此事面告了茅盾先生。他沉思片刻,说:“说的是。”
老舍先生,在京这些年,我每隔二三星期总去看望他;有时他也来电话约着一同去吃小馆,并嘱咐带着“大姑娘”。高兴时,就给我写几个字,现存二幅,一竖,一横。一题“学知不足,文如其人”,一题“健康是福”。字较大,魏碑体。另一幅,在胡絮青同志画的扇面上,写了四个大字:“诗人之家”,己损失,但曾留在相片上,永存人间。我每每对着老舍的字(一在客房,一在内室),睹物怀人,心怀凄怆。
何其芳同志,我们30年代同时登上文坛,多年相交,晚岁而情弥笃。60年代初,他给我写了一幅字,写的是他自己的近作“戏为六绝句”。劫火中,己化灰飞去。我请他再写一幅。1976年1月他就亲自送来了。写的是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3周年而作的七律14首之一。他的字像他的人,极端正。事后,友人告我說:“这幅字是其芳穿着棉大衣趴在桌上写的。盖图章,没印色,现向邻居借用的。”我听了,感动之至!那时,他的问题还未落实,神情有时恍惚,在此情况下,为我如此认真地写了这幅字!
西墙殿军是端木薛良的一幅。我和端木,1938年武汉定交。他是个多面能手,小说、诗词、书法,都显示出他的才华不凡。这幅字,写的他的一首旧体诗,字与诗,堪称“二美并”了。他与我,都受到王统照先生的赏识奖掖,对王先生亲爱又尊敬。他这幅与王先生的那一幅,遥遥相对,巧得喜人。
郑振锋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他为人豁达大度,可敬更可亲。我西墙上首高挂他的一小横幅。来宾对他这幅字特别珍视,因为,他的手迹极少。这幅字,没写年月,可能是40年代末写于上海,笔走龙蛇。茅盾先生吊他的诗中有句:“下笔笔浑如不系舟”,字如之。横幅上写的是一首五言古诗,研究郑先生的专家曾问我:此诗是古人之作还是郑先生个人写的?我也回答不出。郑先生此幅,与东墙上曹靖华、冯至二老友的两个横幅,相互影照。靖华同志的二尺幅上写的是董必武同志赠他的两首诗。字体别富情趣,“华”字第四笔,欲飞向天。冯至同志这一幅,原系一封信,联缀而成。
会客室的书画尽于此了。内室还存有十余幅,它们是胡絮青、王子野、廖沫沙、华君武、吴伯萧、王亚平、周而复、陶钝、方殷、程光锐……诸位好友的手笔。令我痛惜而又感到遗憾的是,田汉先生在上海给找写的一个条幅,云烟满纸,气韵流动,充满了乐观放达的精神,而今已经人字俱亡了!
我苦心收藏的这几十幅字,大半是72年后求来的。少数前辈的字,侥幸孑存,是因为“文革”初期,我一一掩面卷起,收拢于南书房,“造反”大将们来抄家,一张封条,一把大锁,使这些无价之宝,免遭大劫,幸甚,幸甚!
这几十位我尊敬而亲切的朋友的手迹,它映照出我们之间的深厚感情,也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每一幅,成为我的连城之璧,对着它们,好像对着朋友的面。这一幅幅字,这一个个好友,是我精神世界里的“半壁天”!它们、他们,牵动着我的心,也牵来无限往事的幢幢之影。这些朋友中,一半己舍我而去了,可是,情感是无间生死,能超越时空的。他们人虽己逝,但在我心中活着!而他们的字,也留在人间,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