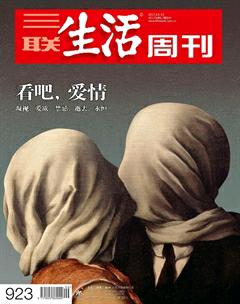《洛神赋图》:无望的人神之恋
艾江涛
人生有如朝露,功名、爱情不过一瞬。既然如此,只需刹那的绚烂与温存就好,又何必祈求长久呢?
甄妃之谜
黄初四年(223)的五月,32岁的鄄城王曹植,和哥哥任城王曹彰、同父异母的弟弟白马王曹彪一起应诏到都城洛阳觐见魏文帝曹丕。转眼之间,曹丕即位已三年多了。三年多来,大权在握的曹丕对与自己曾争立世子的曹植严加防范,不但派官员严加监视他的行为,诛杀他身边的谋士,还把他的封地一变再变,而没有自己的命令,曹植等人不得擅离属地,甚至无法面见母亲与其他亲人。
这次朝觐的经历并不愉快,先是曹植到京后久不获召,苦等之下只得上表陈诗自责,才最终得到曹丕接见。后来,曹丕又因不满曹彰平日与曹植过于亲近,而且态度强硬,因此将其设局毒死。七月间,曹植准备上路东返封地时,曹丕又下令禁止他与弟弟曹彪同行,悲愤之下的曹植,在东行路上写下诗作《赠白马王彪诗五首并序》。
而在后世的一些研究者看来,曹植的另外一篇千古名作《洛神赋》,也写作于这趟旅途,赋作序言中的“黄初三年”实为笔误。除了共同出现的“洛川”“太谷”等地名,学者陈葆真判断的标准是,两首作品同样动人肺腑、感人至深,依其情绪之波动程度与艺术成效的高超而言,创作时间应极为接近,创作背景也应相关。
抛开写作时间的争议不论,《洛神赋》究竟写了什么东西呢?话说旅途中的曹植从洛阳一路东行,返回自己的封地甄城。忽而夕阳西沉,人困马乏,一行人于是在洛河边的草地上停车喂马。曹植信步走在林木之间,纵目远眺烟波浩渺的洛河,神思恍惚之际忽然抬头“睹一丽人,于岩之畔”。曹植不由问一旁的车夫:“你看见那个美人了吗?怎么如此漂亮!”车夫回答道:“臣听说洛水之神名叫宓妃,莫非你看到的就是她吗?她长什么样子,臣倒很想听听。”
于是,大诗人曹植便将宓妃的美貌大加描绘一番,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文学史对美女最为经典的一段描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洛神之美,不仅在于身材,而且服饰华美,体态优雅,明眸善睐。见到曹植后,这位女神不但不害羞,还有点调皮地在水波之上徜徉嬉戏。
心旌摇曳的诗人,恨不能通过水波传情,情不自禁解下腰间玉佩相赠,没有想到,女神很快举起琼玉做出回应,并指着潜渊约请诗人前来相会。魏晋时人极为看重玉纯洁高贵的品质,以玉比人也是当时的风尚,比曹植小近20岁的玄学家夏侯玄便被人形容为“玉树”。用佩玉作为信物交换,自然是定情的意思。可就在这时,诗人的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他忽然想起周朝人郑交甫被汉江神女虚赠玉佩相骗的传说,犹疑之下不由敛容定神。这一切自然无法逃过女神的眼睛,她忽而舞动身躯,发出哀婉悠长的声音,很快娥皇女英、汉水女神等各路女神都结伴而来。最后在叮当作响的玉鸾声中,宓妃坐着六龙共驾的云车离去。离去之前,她掩面而泣,“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尽管人神殊途,两情无法相悦,宓妃仍一片情深:“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回过神来的诗人,驾船寻找,彻夜难眠,但短暂的相与已杳不可寻,只得在怅然若失中再次上路。
回头来看,这段情深意长的入神之恋,真如刘勰所论,建安作家往往“怜风月,狎池苑”,故而对女性的形态和心理体察入微便能写出吗?对曹植来说,洛水之神宓妃背后有无真实生活中的原型呢?至少在民间的传说中,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此人正是曹丕的妻子甄氏,《洛神赋》原名《感甄赋》,所写实为曹植与甄氏的一段悲恋传奇。据学者傅刚的考证,这个传说至少在中唐时期已然形成,并见诸元稹的诗中,“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唐人的开放、安史之乱后的安定生活,令百姓似乎开始酝酿起世俗的爱情理想,并不管其是否为名教所接纳。
当然,使这一传说真正深入人心的,是宋人尤袤所刻《文选》中李善的一条注解。在这条注解中,曹植与甄妃的恋情变得完整起来:曹植少时曾与上蔡县令甄逸之女相恋,后来此女被曹操赐予曹丕,令曹植心意难平,以至于晝思夜想、茶饭不思。曹丕登基后,一次召曹植入朝,特意拿甄妃用过的枕头给他看,令后者痛苦不已。当时甄妃因为郭皇后的谗言而被处死,曹丕也有悔意,后让太子留曹植宴饮,随后以枕相赠。曹植在回封地途中,在洛水旁将要休息,忽然有一女子前来相告:我本托心于你,奈何无济于事,这个枕头是我出嫁前的用品,现在伴你左右,以达我情。我被郭后以糠塞口,披头散发,羞于见你。说完后便不见了。曹植于是悲喜交愤中写下《感甄赋》,后来被曹丕的儿子魏明帝看到,改为《洛神赋》。
相信这段人神之恋背后的传说,伴随曹植悲惨坎坷的遭际,更为打动人心。只是历代学者对此颇为质疑,最大的疑点是,甄氏本为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建安七年(202)被曹丕夺为妻子时,曹植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洛神是效仿《离骚》中的“宓妃”,以表达没有机会建功立业的失意与对曹丕的忠心。
有趣的是,无论后人如何阐释,但至少在当时,人们还是将他简单地视为言情之作,东晋画家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便以曹植与宓妃的人神爱情为题而画,也正因此,萧统才将《洛神赋》置于楚人宋玉之后,名列赋选的最后一篇。这一点也为陈葆真所注意:“画家们所关心的,远非如何解析《洛神赋》的内文,或它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何关系。他们所关注的,在于如何诠释和表现这则美丽而哀伤的恋情和诗意。”
传神阿堵
才气纵横的曹植在后世备受推崇,南朝刘宋时期的诗人谢灵运更曾言:“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洛神赋》作成后更是一纸风行,并很快受到画家的青睐。顾恺之之前,从东晋明帝(322~325年在位)开始,许多画家便着迷于这篇赋文,纷纷将其绘成故事画卷。
顾恺之对这篇赋文情有独钟,则还有另外的原因。据传,顾恺之以“画绝、文绝、痴绝”的“三绝”著称于世,他的画深受当时大政治家谢安器重,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他不但长于绘画,而且素有大志,曾担任大司马桓温的参军。只是,桓温死后,其子桓玄对其颇有轻慢。一次,桓玄拿一片柳叶说是隐身草,要顾恺之鉴赏一下。谁料顾恺之刚接到手里,桓玄便对着他撒尿,还戏言法宝显灵,以至于他看不见顾恺之。在故宫博物院古代书画专家金运昌看来,正是这种落魄才子、失意志士的共鸣,让顾恺之感同身受,因而创作《洛神赋图》。
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原作已佚,流传于今传为顾恺之所作的三卷《洛神赋》,实则均为宋代摹本,其中就有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被乾隆皇帝题为“洛神赋第一卷”的北京甲本。徐徐展开这幅长达572.8厘米、高27.1厘米的绢本彩卷,犹如看一册情节完整的连环画,赋文中的内容像电影一般在脑海中依次浮现。据陈葆真的研究,《洛神赋图》这种以连续式构图去表现故事的细节,常见于六朝时期敦煌石窟中的佛教壁画。画卷中,人物、车船、动物、山石、水流依次展现出来,水波从左向右流动,人物的裙裾则向后飘,仿佛逆风而行。比照于赋,全卷分为邂逅、定情、情变、分离、怅归五幕场景。
按陈葆真的划分,邂逅又可分为离京、休憩、惊艳三个片段。只是在北京甲本中,离京的片段已经散佚。在休憩一段中,两名侍从拉着三匹马,这些马或倒地打滚,或低头吃草,或仰头回望,一副人困马乏的样子。接着是一组九人的群像,众人簇拥下君王模样的曹植,正站在洛河之畔,眼睛朝前平视。而接下来的惊艳片段,便是对洛神超凡美丽的具象展示。首次出现在画卷的洛神双髻高耸,身披彩色罗衣,手握圆扇,裙裾飘逸,正扭头与曹植双目相接。为了描绘洛神之美,画面甚至依次出现八个赋中比喻她的事物,“惊鸿”“游龙“秋菊”“春松”“浮云”“流风”“朝霞”“芙蕖”,引入想象。
而在定情环节,则是洛神一连串在水面嬉戏的图景,为洛神美貌与姿态俘获的曹植,接下玉佩以表衷情,只是“赠物”的片段没有出现在北京甲本中,反而在辽宁本中有所体现。情变一幕则包含“众灵”与“彷徨”两个场景。洛神在与众灵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戏清流”“翔神渚”“采明珠”“拾翠羽”后,与曹植彷徨而视。画面中,曹植坐在床榻之上,望着洛神踌躇不能离去,而洛神则侧身回望,眼帘低垂,心中的眷恋既让她无法离去,悲伤又让她无力凝视心中的爱人。
然而离别已无可避免,风神屏翳张开大嘴,吸气收风,川后使水流平息,冯夷鸣鼓,女蜗清歌,洛神乘着云车腾空而去,仍不忘回眸顾盼。怅归一幕,曹植乘大船追赶不及,上岸后独坐相思,画面特意以两支蜡烛表现他耿耿难眠的心境。随后的驾车返归,曹植如别离时的洛神一样,仍不断扭头回望,流连忘返。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古来多少爱恨离愁,尽在四目相对之间,而难以言表。《洛神赋图》的传情达意,令人黯然销魂之处,也正在此。如果细细浏览画卷,不难发现,自曹植与洛神从邂逅到分离,两人的目光便再也没有分离过,即使一方已杳不可寻,目光依然流连于对方消逝的方向,为之久久不能释怀。
顾恺之曾在《魏晋胜流画赞》品评绘画之难易:“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自此,“迁想妙得”成为中国画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所谓“迁想”,是指艺术创作中的想象,通过充分的思索与联系,把握对象的内在气韵,以实现“妙得”。而对于人来说,最能传递神韵的莫过于眼睛,所谓“传神阿堵(六朝人口语,即这个,代指眼睛)”。据《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顾恺之画人物,数年目不点睛。有人询问原因,他回答:“四体妍蚩,本无善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为了体现人物的神采风韵,出于想象有所增删也在所难免。据说,有一次,顾恺之在画“玉人”裴楷的时候,在他脸上无端增加了三撇胡须,理由则是“裴楷英俊爽朗,有见识,有才具,这三根胡须正是他的见识才具”。
在学者易中天看来,这正是魏晋人所追求的真实,真性情,是一种心理、情感和艺术的真实。换句话说,要理解《洛神赋图》中那难以实现的人神恋歌,必须回到那个悲歌慷慨、战乱纷争却偏讲风骨的时代,回到魏晋风度。
人神之恋
在曹植之前,人神相恋便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母题。在《离骚》中,屈原便以对女神的追求不得,比况君臣不谐、人生理想无法实现的悲慨。屈原追求的女神,有来自昆仑山的高丘之女,有伏羲的女儿宓妃,有身居瑶台的娥氏女,还有夏朝虞国国王的两个女儿,不过,此时的宓妃只是与昆仑山有密切关系,尚未成为明确的洛水之神。
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中接续了屈原的话题。《高唐赋》的巫山神女主动大胆,出现在楚王的梦中,并自荐枕席与之欢好。《神女赋》的女神则多情而持重,在盘旋往复中最终不知所终,只留得楚襄王一人惆怅垂涕,也为后世文人贡献了所谓“襄王有梦神女无心”的永恒话题。无论如何,人神交接并非易事,《高唐赋》中楚王虽然一亲芳泽,但赋文后段大量对山水奇险的铺排,却暗示着追求的艰难与终成虚幻。
屈原、宋玉笔下的“人神之恋”,多发生于云梦之台、云梦之浦等神秘缥缈之境。据后世学者研究,其背景多与包含性活动的原始宗教儀式相关。《墨子·明鬼篇》说:“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所属而观也。”陈梦家先生解释说:“属者合也,谓男女交合也。”闻一多的研究,更认为巫山神女即为楚之先妣,是楚的高襟神,不但掌管行云布雨,也掌管着男女之事。
《洛神赋》的人神之恋,显然承接着这一传统,正如其赋前小序所言:“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此赋。”然而,曹植寄寓期间的身世感怀自不待言,如果不是这样,也就难以理解为何在他笔下的爱情,不论是《洛神赋》中的“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还是《感婚赋》中的“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愍志赋》中的“或有好邻人之女者,时无良媒,礼不成焉”与“哀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于生离”,都是一种单向而无望的悲剧。
除了将身世并入对爱情的书写,千载以下,《洛神赋》的感人之处,还在于那份一见倾心、流连顾盼的痴情,正如清人顾春说谓“那曹子建的《洛神赋》、元微之的《会真记》,皆因是有所慕而无所得,才写得那样迷离惝恍,这便是痴情了”。这份情痴,实在是魏晋人特出的风度。顾恺之在当时便以“痴绝”著称,据说有一次,顾恺之与谢瞻一起值夜班,望着窗外明月,一时兴起,随口吟起诗来。一旁的谢瞻听到后称赞了他几句。没想到受到夸赞的顾恺之,开始没完没了地吟诵起来。最后,谢瞻实在太困,便让仆人从旁陪他,吟诗一直到天亮的顾恺之竟然没发现身边早已换人。
痴的背后,是重情而真率,这也是魏晋名士的基本要求。简文帝司马昱便曾如此点评一个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真率,便足以超过其他人许许多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谶纬之学与宗教迷信极为盛行,再加上玄学风气与佛教传播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志怪小说。这些本意教化的小说,反映了时人的一种生命观:神鬼经常在观察每个人的行为,并随时准备给予他们公平的奖励或惩罚。其中便有不少人神相恋的故事,最有名的莫过于孝子董永与仙女的故事。《洛神赋》的广泛流传,也吸引了当时小说家的重新创作,曹植与洛神的恋情也被转变为玄超与知琼之间的爱情故事,被收录于干宝的《搜神记》中。
据载,玄超是西晋时期的官员,曾职济北,在陈葆真看来,这让人想到曹植一度受封的济南。玄超一度与仙女知琼相恋,知琼的名字显然与玉相关,使人联想到曹植曾以玉佩相赠洛神的情节。后来,两人的秘密恋情因为被泄露给友人而中断五年,这似乎也与曹植与洛神那发生在刹那间的情变对应得上。巧合的是,玄超与知琼再度相逢的地方鱼山,正是曹植的埋葬之地,两人定居的洛水则为曹植与洛神的邂逅之地。
如果这段恋情确实本于曹植与洛神,不难看出,其中所包含的后人对那段无望的人神之恋的祝福与祈愿。有趣的是,曹植本人对流布民间的道教神鬼传统大概并不相信,他曾在《辩道论》一文中批评当时方术之士的虚妄。《洛神赋》中无望的人神之恋,固然有屈原、宋玉以降香草美人的抒怀传统,却也折射出那个伴随自我发现的乱离之世的审美倾向:人生有如朝露般短暂,功名、爱情,不过都是只堪感忧的一瞬。
打开汉魏之交的那些诗篇,触目皆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己晚”“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这样的感怀忧思。既然如此,只要刹那的绚烂与温存就好,又何必祈求长久昵?“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与宋人不同,在他们的眼里,重逢已然无望,刹那即是永恒。
写到这里,我忽然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洛神赋》中刹那凝视的爱情,竟让我想到波德莱尔的那首诗:《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诗是这样写的:“大街在我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嚣/走过一位穿重孝、显出严峻的哀愁、/瘦长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丽的手/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群裳;//轻捷而高贵,露出宛如雕像的小腿。/从她那像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一样的眼中,我像狂妄者浑身颤动,/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尽管你已經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
(本文写作参考陈葆真《(洛神赋)与中国古代故事画》、易中天《魏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