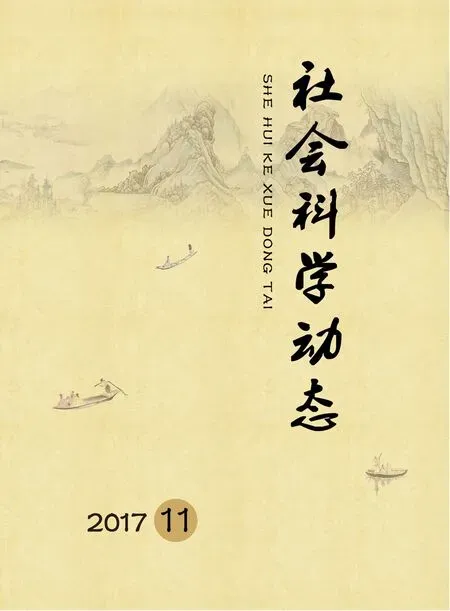湖北民国新式剧场的发展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演进
熊 霞
湖北民国新式剧场的发展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演进
熊 霞
民国时期,承担一定演出功能的传统茶园和会馆戏园逐渐向新式剧场转化,城市公共空间进行了重新整合与构建。新式剧场的出现,标志着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与演进。剧场空间不仅在建筑、场内设施等物质层面和经营管理模式等文化层面进行了重要的革新,而且其空间活动对民众与社会的关系影响深远。新式剧场不仅是民众文化休闲方式变迁的窗口,还是社会动员及大众教育的重要平台,其发展折射出都市生活的活力及社会生态的嬗变。
湖北;民国;新式剧场;公共文化空间
传统茶园、会馆和公所戏园等旧时的公共演出场所,将广大民众从狭小的私人空间引向广阔的公共领域,为公众聚集与文化休闲提供了设施层面的保障,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城市公共空间进行了重新整合与构建,承担一定演出功能的传统茶园和会馆戏园逐渐向新式剧场转化。新式剧场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物质设施景观,更对民众与社会的关系影响深远。
辛亥革命后,湖北迎来了新式剧场和舞台建设的高峰,专门性、综合性剧场不断涌现。新式剧场的大众性和公共性,使其天然地成为都市现代化进程中新型的、重要的公众文化空间。它不仅是民众文化休闲方式变迁的窗口,还是社会动员及大众教育的重要平台,其发展折射出都市生活的活力及社会生态的嬗变。新式剧场的出现,既是演出场所的更替和革新,更是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与演进。
一、新式剧场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剧场是1867年英国人在上海建立的兰心剧院。该剧场在建成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主要为上海的外国人服务,极少有中国人光顾。直到1907年中国观众始有机会进入该剧场观看演出。这座现代化的西式剧场让国人大开眼界,促发了国人尤其是茶园戏院老板对演出场所进行改良的热情。在此背景下,中国第一家由国人自建的新式剧场“新舞台”很快于1908年在上海诞生。新舞台以兰心剧院为参照,并在考察欧洲、日本剧场的基础上建设而成,其规模、结构和设施为观众带来了完全不同于茶园戏院的全新体验,生意兴隆且长盛不衰。“新舞台”获得巨大成功后,各大戏院老板和资本家纷纷效仿,其建筑及经营模式迅速传入湖北。1908年,在上海“新舞台”的影响下,湖北的第一座新式剧场汉大舞台在汉口北京路口成立。
民国成立后,在政府大力发展工商业政策的刺激下,湖北迎来了新式剧场和舞台建设的高潮。以湖北商业重镇汉口为例,自中华民国成立到20年代,汉口出现了各种新式舞台和戏院15座①,湖北剧场建设进入第一个高潮阶段。1919年,当时湖北最大的综合性文化游乐中心汉口新市场(即后来的民众乐园)在汉口六渡桥的建成开业,成为湖北剧场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新市场被誉为与上海大世界、天津劝业场齐名的民国三大娱乐场之一,场内“杂陈百戏,游人如织”,剧场门前常年车水马龙,盛况空前,原来一度荒凉的六渡桥逐渐成为汉口最繁华的地段之一。新市场成功的运营和丰厚的经济效益,吸引着大批投资者追捧和效仿,于是各种戏院、舞台及综合性剧场纷纷涌现,带来了二三十年代的兴建剧场之风。从1921年到1933年的16年间,武汉兴建各种剧场27所(其中包括武昌4所)。据1934年《汉口市政概况》统计,当时在汉口已有37家剧场戏院②,包括正俗戏院、劝业场、共和大舞台、光明大戏院、上海大戏院、凌霄游戏场等大型剧场。在此前后,武昌建有共和舞台、乃园游艺场;宜昌建有和记舞台;沙市建有鄂西大舞台;光化建有老河口游艺园等③。
新式剧场迅速占领演出空间,旧时茶园、戏园难以为继。为寻求生机,它们纷纷改造,开始扩建、改建,并改牌换记,向新式剧场转化。1914年汉口的春仙茶园率先改名为天仙舞台;1919年原新民茶园改名为美商大舞台。还有一些比较老的茶园,如天一茶园、清正茶园,尽管没有改换门牌,但在经营上已经是凭票入场的新式剧场模式了。湖北其他中小城镇的茶园,如应山的贤乐茶园,沙市的聚仙茶园,以及黄石港的五六所茶园,均已演变成新式剧场性质的戏院了④。民国初年,称为茶园或舞台的剧场,交叉出现,1920年前后,茶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新开的剧场,大多命名为舞台或戏院,有的还加一个“大”字,如天仙大戏院、维多利大舞台、汉口大舞台等。
许多会馆和公所戏园也被改造为新式剧场。茶园尚未出现之前,出于祭祀宴宾或喜庆娱乐的需要,会馆和公所多设有戏台以供演出,如清末汉口的山陕会馆有7座戏台,江西会馆有2座戏台⑤。随着民国时期新式企业的兴起,传统的地缘组织逐渐退出了汉口的历史舞台,各地区、各行帮在鄂设立的会馆和公所的主要功能丧失,便被改造为新式的戏院。具有代表性的“长乐”大戏院便是由原来的“两湖会馆”改造而来;孝感的六也茶园,其前身也是福建会馆。
新式剧场的经营者多为地方上的青洪帮头目或军政要人。民国时湖北剧场的数目不断增加,彼此竞争十分激烈,业主之间相互倾轧,常常为一戏院之产权或营业权,争执不休对簿公堂。再加上演出场所大多非太平之地,因犯忌引起风波或藉故滋事时有发生。如辛亥革命初,汉剧演员在襄樊演《梅龙镇》,因“吃粮当兵吃下等酒”一句台词,引起当地驻军不满,导致戏院被砸⑥。为了正常经营或支撑台面,戏院的经营者多为有背景的军政界或青洪帮头目,有的老板虽非此类人物,亦必须请有权有势者作为后台。因此,时局的变化或政界人事的变动,经常影响戏院的兴衰。一些戏院人员系临时凑合,无长期合同,无固定资金,有剧团就干,没有就散,故而改牌换记之事也很多。
二、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与演进
相比于传统的演出场所,新式剧场的建立为观众带来了不同于传统演出场所的现代的、全新的体验,改变着公众的审美眼光和空间观念,促进了公共文化空间的演进。作为新型文化空间,近代剧场不仅在建筑、场内设施等物质层面进行了重要的革新,还在经营管理模式等文化层面进行了有力的改进。
从物质层面而言,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近代剧场的演进主要体现在:
首先,新式空间的建筑规模普遍扩大。在大型茶馆戏园和会馆戏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式剧场,其空间布局、设施以及经营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之前的影响,在规模上普遍偏大。就座位数量而言,大型的戏院有的达到1500甚至1700多个。地方政府在1946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在汉口,超过1500个座位的戏院有3家,最大的“天仙大戏院”以演出楚剧闻名汉口,拥有1740个座位。即便是最小的“黄金大戏院”也拥有830个座位,比同时期的大部分汉口电影院的座位要多⑦。
其次,舞台设计及背景技术大为提升。1919年,以汉口新市场为代表,湖北剧场开始建立镜框式带唇边的新式舞台。新市场内设九个小型剧场和游艺场,剧场为镜框式舞台,台高一米。场中部的杂技厅,也建镜框式带唇边舞台,观众厅呈扇形,半圆形转楼可通往后台。1933年,新记大舞台(原共和升平楼)重修,也建立了镜框带唇边舞台。
镜框式舞台对三面突出的开敞式舞台的替代,有利于布景的设置和舞台效果的改善。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新式舞台出现了五彩布景、机关布景等舞台美术装置,灯光照明、布景吊杆和转台等机械设备也开始使用。声光电与舞台背景的融合,为观众带来了新奇、愉悦的视觉体验,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剧场已经很会利用新式机关背景来招徕观众,尤以新市场为最。1926年元宵节,新市场内“共和京剧班”全班合演《天下第一桥》,耗资数千元设置机关背景,有活动水景,有利用光、电作用的幻术“法力宝剑”和在空中忽隐忽现的“千手千脚佛”。武汉三镇市民纷至沓来,一饱眼福⑧。当时的清芬剧场和美成戏院,都设有布景房,均是民国时期以多演机关布景连台本戏闻名湖北的新式剧场。
再次,新式空间的安全、卫生、文明意识增强。鉴于旧时公共演出场所坍塌、火灾事故的频发,1927年1月,湖北政务委员会教育课发布了一个《大纲》,规定演出场所“须合乎优美、卫生、防火、避灾诸条件”⑨。后来的湖北政府当局,为制止事端滋生,在戏院最后一排设有持枪的军警“弹压席”;为防火灾等意外事故,要求戏院增设太平门和消防器材。由于政府的监管,兼之逐渐专业化的经营方式和日趋成熟的商业运作,剧场建筑的安全意识大为增强。明显改善的是建筑材料。新式剧场初由木结构改为砖木结构,很快又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流。如1933年重建的和记大舞台,采用了砖墙结合钢筋混凝土的主体结构,不仅建筑较前坚固,而且剧场照明由煤气灯普遍改为电灯,也减少了火灾隐患,安全性明显提高。卫生条件也改善很多。旧式茶园卫生状况极差,空气质量恶劣,厕所极不卫生,茶壶、手巾也不能及时清洗。新式剧场建立后,厕所比早期规范,并设置男女厕所,一些戏院还放置了吐痰用的痰盂,并普遍配备电扇、冷气。1927年改建的上海共舞台,已经配有冷暖气设备,剧场建筑基本上完成现代转型。
从文化层面而言,近代剧场的改进主要体现在:
首先是经营范式的改进。旧时茶园剧场的管理体制主要是案目制。茶园、剧场的戏票最初掌握在被称为“案目”的特殊群体手中,戏票通过案目再辗转至观众手中,其功能类似于今天的“中介”。由于案目人员活络,人脉广泛,在信息闭塞的茶园时期,案目在演出信息的传播和分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着茶园的生意和经营。所以案目在戏院的经营管理中至关重要,实际上成为戏院的股东和经营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戏院的演出和经营。但进入新式剧场时代后,案目的优势逐渐消失,功能趋弱。相对于旧时戏院的池座设置,新式剧场的设置更加科学合理,剧场内一人一座,票面上可以印制与座位一致的号码,观众购票之后可凭票对号入座。而且在民国中期,现代报业的高度发达,及巨幅海报、霓虹灯的广泛使用,使人们了解演出信息的方式和渠道更加广阔。随着电话在上层社会的普及,订、购票方式也渐趋多样化,观众既可以在剧场售票处购票,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此,案目印制并每日分送的戏单,已然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多余和浪费,案目的功能和优势丧失。
与此同时,传统案目制的弊端日益暴露。由于案目素质参差不齐,为了大量获利,他们或大量私印戏票对观众进行变相敲诈,或私自抬高票价从中渔利,或利用经营剧场之便,不顾演剧质量包场演出。尤其被人诟病的是,案目的服务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选择性,案目服务的达官贵人被款待有加,而普通观众被怠慢、歧视甚至被侮辱之事则时有发生。案目制已经无法适应剧场的发展,甚至严重干扰了近代剧场的正常运营,要求废除案目制的呼声逐渐高涨。在此背景下,案目制最终完全被以对号入座为核心的现代票务制取代。票务制的实行,不仅保障了观众的经济利益,还为观众观演活动的公平性、民主性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并使管理更为科学和便利。
其次是观演模式的演进。传统的茶园不仅是观戏之所,更主要是娱乐消遣之地。茶园观戏模式十分松散,观众席总是喧闹异常,喝茶、洗脸、做生意、谈生意的人们随处可见。一些演员在演戏的过程中还要由检场上台送茶喝,演戏和看戏均受影响,演出更多时候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新式剧场对茶园的松散进行了改进,规定剧场内不准喧哗走动,喝茶送茶、抛手巾、要小帐等与观赏无关的活动都被禁止。在湖北,汉口大舞台率先彻底废除泡茶,实行对号入座等方法,提高了观众观演活动的兴致。新式剧场的规定让观众有了一种“剧场心理意识”,周围气氛的无形制约,使观众能不受干扰集中精神进行观戏。新式剧场内观赏活动的严肃化,使观戏从消遣宴乐活动的附属地位中独立出来,单纯地成为人们文化休闲的一种方式。观演模式的演进,有力地提升了剧场空间的文明和现代化程度。
三、民众文化休闲方式变迁的窗口
作为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其成长与演进不仅体现在自身功能的完善,更表现在空间内民众和社会的关系变化中。新式剧场将观戏等文化活动独立出来,不仅为戏曲等传统艺术形式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更促进了新的观赏形式,如看新剧(早期话剧,或称文明戏)、看电影等多种休闲方式的产生。新式剧场成为民众文化休闲方式变迁的重要窗口。
新式剧场诞生后,深受湖北百姓欢迎的传统地方剧种——汉剧有了显著发展。美成戏院、长乐剧院、满春戏院、共和舞台、宜昌合记舞台、沙市鄂西大舞台等近代剧场成为汉剧演出的重要场地。位于汉口清芬路的美成戏院,原名丹桂舞台,初建于1913年,30年代改建为美成戏院。民国时期,汉剧名伶余洪元、余洪奎、周小桂等常在美成戏院演出⑩;著名演员周天栋、徐继声、刘金屏、袁双林等曾组成“栋联汉剧团”,进入美成戏院演出。该剧场设有布景房,因多演机关布景连台本戏而闻名武汉。楚剧取得租界外演出的合法地位后,在北伐将领、戏剧爱好者李之龙的支持下,进入汉口新市场(时称中央人民俱乐部)演出,楚剧《小尼姑思凡》在俱乐部的上演被称为“楚剧革命第一声”、“平民艺术革命的新纪元”,楚剧影响力日益深远。清末进入武汉的京剧,到了民国时期更加盛行。20年代前后,满春茶园、怡园、老圃游戏场、新市场大舞台、新记大舞台(即汉口大舞台) 等剧场剧院,均有本地与外地京剧戏班演出。
民国时期的艺术舞台,最鲜明的特征是“新剧”开始进入剧场并成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休闲形式。新剧即话剧,早期称新剧,也称文明戏,1928年由戏剧家洪深提议将名称改为“话剧”。这种以对话为主的戏剧形式,迥异于我国传统戏曲而接近西方戏剧。
辛亥革命前夕,在日本新派剧和欧洲戏剧的影响下,中国早期话剧即新剧诞生。辛亥革命后,武昌首义的成功为新剧进入湖北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1912年春,应新式剧场汉口大舞台(原共和升平楼)之邀,著名戏剧家徐半梅领导的社会教育团从上海来到汉口,带来《谁先死》、《明盲目》等新剧,在汉口大舞台上演达3个月之久,新剧逐渐被熟知和接受,并得以迅速推广。“五四”运动带来了新文化运动兴起,新剧以旧剧所没有的“革命性”受到社会的广泛注目,在汉口各大戏院争相上演,形成湖北话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1920年,新剧团体“导社”和“醒民社”成立后,开始在汉口舞台上引入新式机关布景,使观众耳目一新。“这两个剧社以各自不同的作风,使新剧在武汉得到了空前未有的推广,成为那几年中一个最受欢迎、剧团最多的大剧种。三新街的长乐戏园、满春茶园、康生花园、立大舞台等十多个主要的戏园,都长期演出新剧,一直到1925年被北洋军阀禁演,形成了一个高潮。”⑪由于新剧关注时事,政治色彩浓,为当局不满。1925年,军阀当局对新剧演员横加迫害,新式剧场的新剧演出转向沉寂⑫。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新剧在湖北再次兴盛起来。新市场建成7周年纪念时,特邀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来此演出,使新剧在鄂进一步盛行,湖北迎来新剧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抗战初期,武汉成为全国救亡宣传活动中心,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新编抗战新剧,如《塞上风云》、《东北之家》、《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在湖北各地新式剧场频频上演,新剧、新式剧场与民众关系更为密切。明星、光明大戏院、天声舞台、新市场大舞台、世界大戏院等剧场,成为新剧上演的主要空间。抗战胜利后,在中央大戏院、世界大戏院、维多利亚影院等剧场,仍有《升官图》、《啼笑因缘》等新剧上演。
作为西方人娱乐生活方式的代表,电影在清末进入湖北汉口后,因其新奇、贴近生活及丰富的表现手法受到国人的热烈追捧。在专门的电影院出现之前,不少茶园、剧场为扩充也兼营电影,如清末的满春茶园、荣华茶园、共和舞台、沙市大舞台等,为招徕顾客,也放映电影。影院诞生后,不少影院也成为演出场所,兼做剧场,如百代影剧院、光明大戏院。位于法租界福煦将军街江边的百代影剧院,是湖北地区第一家专业电影院,专映外片,但也时常上演京戏,刘筱衡、小杨月楼等曾在此演出⑬。兰陵路的光明大戏院,既兼营中外影片,也是重要的演出剧场。其后台极大,夏天两端皆可看戏。顾无为组织大华剧团在此演出文明戏《啼笑因缘》,曾把汽车搬上舞台,轰动一时。也演过京戏,梅兰芳曾率领剧团在此出演。1930年尚小云与苟慧生也曾分别率领剧团在汉同时献艺,形成对打台,苟慧生在汉口大舞台,尚小云就在光明大戏院⑭。
民国时期在湖北最重要的综合新剧场新市场,传统和现代的休闲娱乐方式基本在这里集中荟萃,百戏杂陈。“新市场”内建有剧场、书场,主要用于放映电影、魔术表演、女子京戏和汉剧表演。书场演出,则种类繁多,有大鼓、苏滩、双簧、三簧、四簧、快书、淮调莲香等数十种之多。单就大鼓来说,又有京音、梅花、戏迷、梨花等11种。另有雍和厅的武技杂耍、单弦拉戏、木偶戏、群芳会唱等演出。“新市场”内,传统和新式的娱乐形式基本无所不包,场内剧种之多,以至于要由《汉口新市场日报》介绍,作为民众的消费选择指南,并由场门口的售票处按日零售。新市场内还增设乒乓球、网球、蓝球、游泳池、溜冰场等体育运动设施和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可谓包罗万象、雅俗共赏。丰富多彩的娱乐形式使它成为民国时期湖北百姓理想的“民众乐园”。
新式剧场的诞生,丰富了湖北民众的文化生活,尤其是新剧、电影等新型休闲方式的出现,使百姓生活日趋时尚和摩登。新式剧场成为见证湖北大众文化休闲方式变迁的重要窗口。
四、社会动员及大众教育的重要平台
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与演进,为政治精英集团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新型空间新式剧场不仅仅是纯消费性的大众娱乐场所,更肩负着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这突出表现在剧场对社会公益事业和政治活动的参与中。新式剧场的大众性和公共性,决定了在这一文化空间内进行的公益事业和政治动员,往往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教育效果。
新式剧场为筹捐义赈和慈善义演等公益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设施和空间保障。1920年以后,但凡有救灾、兴学、劳军活动及发生国内外重大事件等,便会有募捐义演,相沿成习,形成风气。湖北境内各新式剧场先后为辛亥首义伤军、罢工工人、北伐战士、抗敌战士、贫苦老弱、难童等人群及市政事业筹措义款。剧场还进行公共性的社会宣传,如“拒毒宣传”、“认购国债宣传”、“党义宣传”、“抗战宣传”等。
由于剧场里戏曲伶人本身具有的宣传优势,以及对市民阶层特有的号召力,在政府的组织下,舞台上活跃的戏曲界便成为新式剧场里较为积极的公益事业参与者。1920年11月,京汉名伶余叔岩、余洪元、张天喜、王长林等数十人,应汉口红十字会之邀,在汉口原英租界大舞台为华北灾民筹捐义演。汉口市民连群结队往观,争先恐后解囊,“来宾之踊跃,当晚已收券一千六百余张,诚盛况也……座客以诸君慨解仁囊,莫不鼓掌称快”⑮。1922年10月,汉口慈善会请欧阳予倩、王无恐、余洪元等艺员假座新市场、兴记大舞台、满春茶园各处演剧筹资。1927年,汉剧界明星余洪元、傅心一、李彩云等,在首义公园共和大舞台义演,以筹捐援助上海罢工及慰劳北伐士兵;同时,汉口剧业全体在老圃游戏场也在进行援助上海罢工工友的筹捐演出。1933年1月,武汉地区名伶票友方阶声、王友袁等人在共和舞台为辛亥首义老弱残废伤军筹赈演剧。1936年5月,汉口市政府还曾借用新市场的新舞台及凌霄大舞台,排演《林则徐拒毒壮史》、《毒》等新剧和歌剧,进行禁烟拒毒宣传周活动。
抗战初期,湖北武汉成为全国救亡政治文化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在汉成立后,于1938年4月组织了壮观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这一时期剧场、影院成为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的重要空间,推动抗日文化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当年4月9日歌咏日晚7时,在汉口光明大戏院举行了盛大的“歌咏音乐会”。剧场内演唱了《救亡进行曲》、《胜利的开始》、《保卫大武汉》等抗日热曲,音乐家冼星海和张曙也亲自上阵献演。戏院内人山人海,前来观看的群众十分踊跃。汉口光明大戏院也是全国文艺界第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之地(1937年12月31日成立),在抗战初期充分发挥了其抗战宣传作用。4月11日戏剧宣传日,湖北武汉三镇的新市场、凌霄游戏场、长乐大戏院、明记大舞台、维多利亚大戏院、天声舞台、美成戏院、共和大舞台、满春大戏院、天仙大舞台、汉兴舞台、粤汉舞台等12家剧院,皆分日夜两场免费上演汉剧、楚剧、平剧等抗日剧目,甚获好评。4月12日电影宣传日当天,汉口的7大剧场影院,包括光明影戏院、世界影戏院、新市场、上海大戏院、明星大戏院、中央大戏院、维多利亚纪念堂均从下午3时起上映或加映《火中的上海》、《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特辑》等抗战影片和新闻片,社会反响极好。这一时期,由于剧场空间承载的歌曲、戏剧、影片等具有强烈的爱国和民族色彩,在抗战时期发挥的社会动员功能尤为显著。
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与演进,为政治精英集团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喧闹繁华的汉口新市场,除了娱乐休闲,政治动员也是主要内容。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原本商业色彩浓厚的新市场一度成为革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伐军会师武汉后,曾将新市场更名为“血花世界”,意为“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并由此衍生“血花”剧社、《血花世界日报》、《血花旬刊》等团体和报刊,政治寓意浓厚。新市场内的空间部署和格局也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场内添置了漆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倡导者格言标语,将原雍和厅改为孙中山总理纪念堂,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政府要员和国共两党进行演讲的重要场所。官方的重大政治活动也常在这里进行,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湖北省总工会、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会及太平洋沿岸国家劳动民众发起召开的太平洋劳动会议等都曾在此召开⑯。新式剧场的政治性功能大为加强,这表明,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时常成为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⑰。
五、结语
新式剧场的诞生,标志着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和演进。作为新型文化空间,近代剧场不仅在建筑、场内设施等物质层面进行了重要的革新,还在经营管理模式等文化层面进行了有力的改进。相比于旧时传统演出场所,新式剧场的建筑及设备上的先进,改变了城市的物质景观,也日益成为市民休闲文化消费的一部分。新式剧场是近代化的产物,除了物质外观,其成长发展还有赖于先进的经营管理体制。新式剧场在经营范式和管理模式上进行了重要革新,如传统案目制向现代票务制的转型,观演模式由松散到规范等,这些革新推动了剧场文明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剧场空间得到进一步成长。
剧场空间的演进还体现在空间内民众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中。新式剧场内,传统艺术形式得以保留和完善,新式休闲方式也得以催生和发展,新式剧场成为民众文化休闲方式变迁的重要窗口。剧场空间还肩负着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它不仅为进行公益事业的各界人士提供了必要的平台,而且时常成为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新式剧场在公益事业中承载了戏曲、歌咏、电影等各种文化娱乐产品和形式,以及各种政治动员活动,因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决定了剧场空间被赋予了动员民众、移风易俗、引导社会风气的政治性或公共性使命。
注释:
① 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②⑤⑫⑯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文化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189、149、280页。
③④⑥⑨⑩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文艺(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143、144、144、146页。
⑦ 任晓飞:《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近代汉口的公共娱乐空间与大众文化(1912—1949)》,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⑧⑭皮明庥等主编:《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195页。
⑪ 余笑予:《回忆武汉的新剧运动》,载《武汉戏剧》1957年合刊。
⑬ 《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页。
⑮ 《红十字会演剧筹赈之第一日》,《汉口中西报》1920年11月29日。
⑰ 胡俊修、高洁:《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塑造市民品格》,《光明日报》2014年8月27日。
J892.4
A
(2017)11-0105-05
熊霞,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所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