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里程碑上的女性光辉
博衍/编译
天文学里程碑上的女性光辉
博衍/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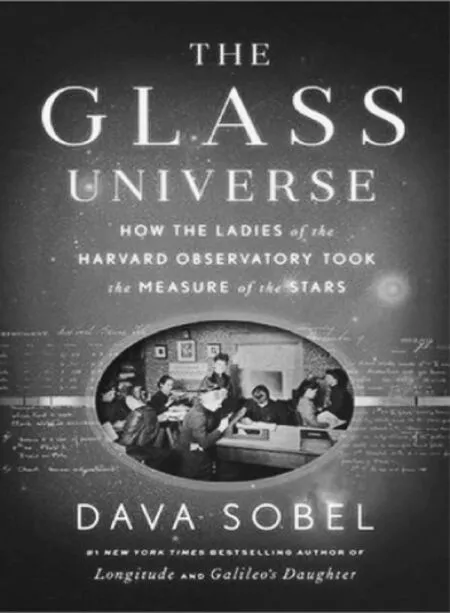
《玻璃宇宙:哈佛天文台的女性如何测量恒星》,达瓦·索贝尔著
在19世纪末,哈佛大学天文台主任爱德华·皮克林(Edward Pickering)聘请了数十位女性,让她们在玻璃底片上测量拍摄到的恒星的性质,其中一些人的名字耳熟能详。亨利爱塔·勒维特(Henrietta Leavitt)发现了可变恒星(造父变星),它们变亮和变暗的时间与光度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宇宙的庞大规模及其膨胀;安妮·坎农(Annie Jump Cannon)对恒星光谱的分析促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恒星类别字母表:OBAFGKM(助记为“Oh Be A Fine Girl/Guy Kiss Me”);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施金(Cecilia Payne-Gaposchkin)发现轻元素(氢和氦)是恒星的主要成分。
目前大家对上面提到的这些情况很熟悉,但历史学家达瓦·索贝尔(Dava Sobel)关于哈佛天文台女性的新书以不同的视角讲述了这些故事。一些人认为皮克林是在剥削这些女性,她们日常工作的报酬低于男性同行。皮克林强大的女性团队被称作他的后宫。但索贝尔将皮克林刻画成领先于时代的女性学者拥护者。她仔细印证了这些女性的细致研究和深刻见解是如何实现了那些突破的,以及两位受过科学教育的女继承人是如何为整个领域提供支持的。
《玻璃宇宙》并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其中涉及哈佛大学天文台80余年历史中的众多人物,而且索贝尔还介绍了一些技术细节。但如果你坚持读完必将受益匪浅,其中不止有作者的引证,还有作者描述天文台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
皮克林在1877年成为哈佛天文台的主任。代理主任阿瑟·塞尔(Arthur Searle)承认,“天文学家的工作与簿记员一样沉闷。”天文学工作依赖于夜复一夜的精确测量。对于女性而言,望远镜穹顶太过寒冷而粗糙,并不是适合她们的工作场所。但皮克林招募了少数女性职员,她们主要是天文学家的姐妹和女儿。她们负责像计算机一样记录天文数据。

天文台里的女性,中间席地而坐的是安妮·坎农,坐在制图桌前的是塞西莉亚·佩恩
一年后,在一次赴怀俄明州观看日全食的旅行中,皮克林遇见了德雷伯夫妇。亨利·德雷伯(Henry Draper)来自纽约,是一名富有的医生和医学教授;而他的妻子安娜对天文学充满了热情。他们从自己的私人天文台拍摄到了明亮的恒星,其中一些像是被棱镜分开的光带。亨利因病突然去世后,安娜请求皮克林帮忙完成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皮克林竭尽所能维持天文台的运转。他请求天文爱好者予以资金支持,甚至出售草屑。但他没有钱聘请任何人。1882年,他在报纸上刊文征求包括女性在内的业余爱好者帮助他监测200颗变星。每天晚上每颗星都需要进行数百次观察,以便跟踪其光线如何变暗和变亮。对于那些有时间并且愿意做这些工作的女性,他欢迎她们提出申请,而这些工作“在家里只需透过开着的窗户就能完成”。有几个人做出了回复并接受了任务。
同时,皮克林也对德雷伯夫妇发现的恒星进行了研究。在它们的光谱中,皮卡林发现了很多细节。他请求安娜资助他扩大这个项目。就像电子成像已经提供了今天的数据洪流,摄影技术意味着天文学家可以从研究单星转移到研究多星。安娜·德雷伯以她丈夫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基金会,捐赠了她的望远镜并出资新建了一个能够拍摄广袤天空的天文台,它能够在一张底片上捕捉数百颗星星的光谱。德雷伯恒星光谱目录就此诞生。
威廉明娜·弗莱明(Williamina Fleming)是对这些底片进行研究的首批计算者之一,她最初是皮克林前任主任的女佣,孤身逃离苏格兰时还怀有身孕。后来,她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拥有官衔的女性。作为天文照片的管理人,她掌管着底片库和计算人员团队。弗莱明发现了10颗新星和数百颗变星。
皮克林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教育家,他在哈佛大学为女性设置了天文学课程,还曾在周边的女子学院寻找新的工作人员。一些毕业生来自瓦萨学院,她们曾接受过彗星发现者、1865年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天文学家的玛丽亚·米切尔(Maria Mitchell)的培训。德雷伯夫妇的侄女安东尼·莫里(Antonia Maury)从瓦萨转学过来,加入了皮克林的团队。莫里创建了明亮恒星光谱的分类系统,还根据彼此相互绕行的“双子”星的光谱特征甄别出密近双星。
1888年,皮克林找到了一位捐助者,从而将自己的摄影延伸至南部天空。再一次,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出手相助。凯瑟琳·布鲁斯(Catherine Wolfe Bruce)在70多岁时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除了在秘鲁资助了一部望远镜,她还为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设立了布鲁斯奖。该奖项至今仍由太平洋天文学会颁发。
到1895年,皮克林聘请到了自己的校友亨丽爱塔·勒维特和安妮·坎农加入进来。勒维特对缓慢变化的恒星光度进行了测量,并用墨水在玻璃底片上对其进行注释。索贝尔用优美的文字描述了这些数字是如何从烟花般微小爆发的变星中产生的,还描述了每颗恒星怎样“在光线的合唱中留下自己独特的痕迹”。勒维特检查了一些靠近模式恒星的恒星。模式恒星标记在一个连着把手的小的方形玻璃上,这块玻璃有点像苍蝇拍。勒维特将其称为“苍蝇疾行者”,因为它太小了,无法对苍蝇造成太多伤害。
坎农毕业于威尔斯利学院,她是第一位受聘使用望远镜的女助手。我们今天使用的恒星分类系统,就是她对弗莱明和莫里的恒星分类系统进一步完善的成果。索贝尔提到,每当坎农无法估计大小时,她就会把原因记录下来,例如用“c”表示多云或用“m”表示月光。
1903年,皮克林从百万富翁、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那里为自己“伟大的玻璃照片库”争取到了一笔资金,壮大了自己的团队,进而获得了更多的数据。勒维特在麦哲伦云中探索到了成千上万的变星。在索贝尔的笔下,位于银河两侧的变星“就像两队迷途的羔羊”。近距离地观看了16颗变星后,她发现了一个趋势:更明亮的变星周期更长。皮克林称这一发现卓著非凡。这些恒星变亮的时机显示了它们的真实亮度,而其亮度可以与它们表面上的微弱度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距离。这些造父变星今天仍然被当作示距天体。
哈佛大学的许多女天文学家都要出差旅行。坎农注意到,在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没有女助手”,也没有“一个德国女人”参加天文学协会的汉堡会议。在加入太阳联盟恒星光谱分类委员会时,她写下了作为唯一一个坐在长桌旁的女人的感受:“由于我已经在这个分支领域做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作,所以有必要由我来进行大部分的报告。”
皮克林1919年死于肺炎。坎农在讣告中写道,“他会因自己的热心肠而被人怀念,而正是他让我们相信自己和自己的能力。”
1921年,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哈洛·沙普利(Harlow Shapley)出任哈佛天文台的新任主任。他在威尔逊山天文台观察到勒维特发现的变星后,认为他们是“悸动或振动的气体物质”。到了年底,勒维特因癌症离世。沙普利称她是“从事天文学工作最重要的女性之一”。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沙普利全神贯注地研究了银河系的范围。1920年,沙普利与赫伯·柯蒂斯(Heber Curtis)就银河是否包括整个宇宙或是否存在类似的星系等问题进行了一番争论。答案取决于到旋涡星云(夜空中的气体风车)的距离。沙普利认为他们只是气体,而柯蒂斯则认为它们包含恒星,而且非常遥远。沙普利的观点在1924年被“推翻”,当时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宣称,仙女座星云中的造父变星证明星云本身就是一个星系。
很快,一个新的毕业生出现了,她就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塞西莉亚·佩恩(Cecilia Payne)。尽管在大学完成了自然科学的学业,但因为当时大学不会将学位授予女性,所以她并未获得正式学位。听过沙普利在伦敦皇家天文学会的演讲后,佩恩对他如何“与星辰同行并像密友一样谈论它们”感到十分惊叹。在沙普利的鼓励下,佩恩完成了博士学位——这是哈佛大学第一次将博士学位授予女性。
佩恩喜欢做饭、缝纫和娱乐。她认识到,尽管曾经认为自己是“女性角色的反抗者”,但她真正的叛逆行为是“反对被视为下等人并且被当作下等人对待”。1924年,佩恩在《自然》发表了关于最热恒星的论文。她回忆了沙普利对她的帮助。“我写字,他打字,然后邮寄出去……我不想告诉他我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打字员。”沙普利要她署上自己的全名,作为论文的唯一作者。“你会因为自己是一位女性而感到羞耻吗?”他问道。
1933年,佩恩穿越了北欧,在那里她遇见了谢尔盖·加波什金(Sergei Gaposchkin),一个在德国面临纳粹迫害的俄罗斯逃亡者。“我知道我必须帮助他逃跑。”她写道。她安排他来到哈佛,3个月后他们就私奔了。当佩恩在1956年被授予正教授职务并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女正教授时,她宣布:“我发现自己被放在了薄楔上一个不可能的位置。”
今天,亨利·德雷伯星表仍然还在使用,而旧底片正在被数字化。正如索贝尔所言:一百年繁星之夜的记录仍然独一无二、价值连城,而且无可替代。
[资料来源:Nature][责任编辑:朝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