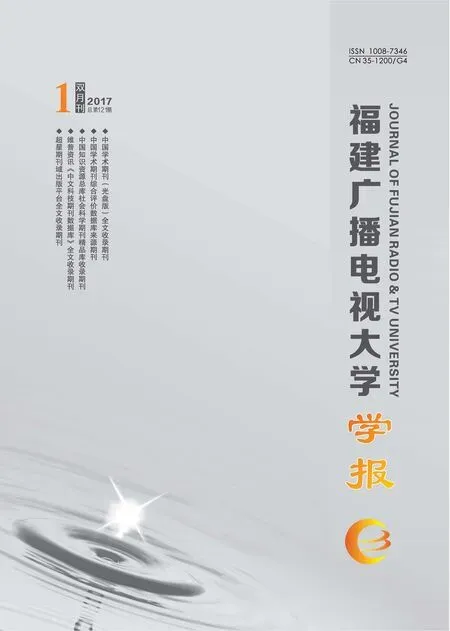谈南翔小说《回乡》的语言特点
胡明晓
(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深圳,518000)
谈南翔小说《回乡》的语言特点
胡明晓
(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深圳,518000)
南翔小说新作《回乡》讲述了“我”的大舅从台湾回乡省亲的盘根错节,故事有历史之殇、家国之痛,读来哀伤,其精妙之处是:善用名词和动词,注重文字的韵律,多维语言身份的构建与认同。
小说 《回乡》;语言;特点
小说是用语言写成的。文字印在纸上,看不见颜色、听不见声音、摸不到造型,小说创作者用文字,一种无声的语言,让读者看见了表演、听到了音乐、触到了丰碑。短篇小说新作《回乡》,让读者看到作者南翔对生活和创作、语言及表达的坚守,以至于漫读中有种错觉,以为这是非虚构文学的集结,再现作者的大舅从台湾回乡省亲的盘根错节。故事有历史之殇、家国之痛,读来自有无法言说的哀伤,本文无意探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仅从语言层面略微一谈,以飨读者。
一、善用名词和动词
小说《回乡》语言简洁、凝练、朴素。采用的句式很少有装饰性的成分,善用名词和动词,少用形容词,没有夸张和浮华的词汇。作者用干净、简洁、表达力强的词语组成短句,勾勒出一个又一个场景,演绎出大舅回乡省亲、原配的儿子广福及小舅因大舅的“海外关系”之苦,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最终大舅以海峡另一边家庭的裂伤,弥补当年背井离乡时留下的无尽遗憾。广福用生父的资助,盖起瓦房,年复一年一遍又一遍地刷新房子,导致白血病不治。广福临终前,将大舅回乡又离去时送给他的金镯子托付给“我”,让“我”这个外甥仔设法还给大舅在台湾的妻子,弥补当年钱迷心窍的种种不妥。小说用质朴的语言,把故事情节写得具体、逼真,人物性格塑造得扎实、厚道,读来酣畅淋漓而又回味无穷。
正如装饰性的形容词不足以表达小说《回乡》的语言之妙,笔者不拘泥于感官感受,试图肢解语言的构成,分析词性以及功能,意在朴素的咀嚼,探寻小说语言的奥秘。笔者用国家语委“语料库在线”的汉语分词和词性自动标注功能对《回乡》全篇进行分析,结果如下:字符数(计空格)11583个,其中分词7875个,普通名词(n)1945个,时间名词(nt)180个,方位名词(nd)104个,处所名词(nl)74个,动词(v)1629个,趋向动词(vd)81个,联系动词(vl)107个,能愿动词(vu)72个,形容词(a)442个。随机列举如下片段,佐证名词和动词在小说中的体现。
片段一:大舅/n 在 兴致勃勃/a 谈/v 讲/v的 时候/n , 广福/n 最为 安静/a ,只是/ 埋头/v 抽烟/v , 一支 续/v 一支;他 给 大舅/n 续/v水/n 也 勤/a , 大舅/n 才 吃/v 了 一两口 茶/ n , 茶缸/n 里/nd 还是 满/a 的 , 他 就不时 去/v 续/v 。我 注意/v 到了/v , 这个 寡言少语/ i 的 表哥/n , 除了 左/nd 嘴角/n 不时 抽动/v以外/nd ,目/n 无/v 表情/n , 嘴角/n 是/vl一条 银亮/a 的 伤疤/n ,抽动/v 的 时候/n 就更加醒目/a 了。
片段二:我 讲/v 其实 看出/v 一点点 来了 , 大舅/n 投给/v 他 的 关注/v 的 目光/n最多/a ; 还有/v 一点 , 每次 广福/n 给 他 续/v 水/n ,他 都 要/vu 抚摸/v 一下 杯/n 盖子/n ,相当于谢谢/v 的 表示/v , 其他 人/n 包括/v 我 妈/n 和 小舅/n ,续/v 水/n , 端/n 糖果/n , 送/v 瓜子/n ,大舅/n 均 没有/v 这方面/ n 的 表示/v。
再如“我”回忆小舅在家庭经济困难时,找“我”的妈妈半要半拿各种物资,“我”妈妈佯作不知,还将辛苦挣得的私房钱赠与小舅。妈妈熬着种种苦痛挣私房钱的画面,让读者过目不忘:
片段三:后来/nt 母亲/n 去/v 塘口/n 打/ v 石头/n ,是/vl 提前/v 到/v 街上/nl 铁匠铺/n 买/v 了 两把 光锤子/n ,找/v 隔壁/n 的 炮撬工/n 老严家/ns 镶嵌/v 了 竹片/n 把子/n。
母亲/n 给 弟弟/n 的 一点点 钱/n , 纯然/a 是/vl 她 的 私房钱/n ,是/vl 靠/v 她 即使风雪/n 天/nt , 来/vd 例假/n 也要 裹上/v 绑腿/n 、 披上/v 雨衣/n , 去/v 塘口/n 挑/v 土方/n 、 打/v 石头/n 、扛/v 毛竹/n 、装/v 车皮/n 挣/v 的 辛苦钱/n 。
根据“语料库在线”的汉语分词和词性自动标注功能对小说《回乡》文本分析:名词占使用词汇的29.2%,动词占使用词汇的23.9%,形容词占使用词汇的5.6%。名词和动词表达占优,是更具有活力的语言表达。相比之下,形容词的滥用会让句子有堆砌臃肿之感。
二、注重语言的韵律与节奏
优秀的作品和平庸的作品读来区别之一,便是语言是否有音乐感。好的作品读来有歌唱般的节奏,抑扬顿挫,起伏错落,入耳入心。注重字和词的位置及数量,注重声音的抑扬轻重,研究阅读中的发声和节拍。《荀子·礼论》:“清庙之歌,一唱而三叹也。”意思是一个人唱歌,三个人相和。后多用来形容音乐、诗文优美。所谓“一唱三叹”,是中国自古以来对戏曲或是对文学作品的要求,细品小说《回乡》的语言,可见一斑。
片段四:小舅/出身/卑贱,自小/谨慎/圆滑,这个/时候(轻读),自然/也/不会/怠慢/那些/平日/或许/从不/踏进/家门/的/真假/亲戚(轻读)。高矮/不拘/的/茶杯/用尽/之后,他/就/喝令/老婆/从/厨房里/端出/一摞/碗/来/泡茶,几片/粗茶/打底(上声),几粒/炒熟/的/黄豆(去声),几丝/生姜(阴平),再是/擂碎/的/粗盐(阳平),那是/可以/从/
上午/一直/饮到/月光/西斜/的(轻声)。
我国古代早期研究声调的语音学家沈约,曾用两句著名的话来描述谢灵运诗歌的韵律之妙:“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意思是一句诗里,最好不要有声韵母相同的字;两句相对的诗里,轻重的位置要不一样。小说的语言不以格律为准绳,也可完全不讲韵律和平仄,音韵优美,也不在于字数的固定,可通读全篇,朗朗上口,也有文脉和节奏之说。这种韵律感不是随意堆砌而成,例如几片、几粒、几丝,打底、黄豆、生姜、粗盐,声韵调的交错而不重复,是有生命的组合,贯穿写作的全过程,有文气的辗转承接,才有文字的神采飞扬。
小说的语言由固定的节奏和韵律去波动,在长短气息间抑或得到体会,从而推动情节轻重缓急的发展,镜头的快慢贴进,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片段四:短句、短句(换气)/短句、长句(换气)/短句、长句(换气)/短句、短句、短句(换气)/短句、长句(结束),时而舒缓,时而湍急,亦或抑扬,张弛有度,读来文脉清晰,雅致俊秀。细品小说语言,不难发现语言节奏和作品情感紧密相连。例如大舅因入厕困难而难以启齿,继而要提前返程时,小舅提出要抱着大舅解手。作者描写小舅的姿态很可笑,弱小的身板在高大魁梧的大舅面前不成比例,语气却是真诚的。此处对小舅的说话语气兼有描述,虽有调侃的意味,揣摩其中也是舒缓而情深的笔触,涵盖对大舅身体状况的担忧和对小舅行为谦卑的理解,作者的感情在这些人物姿态、行为语言、语气语调中轻轻落下。较之先前写大舅出恭遭罪,不慎摔倒,两腿上翘,屁股朝天,将大舅扶起后,累得气喘吁吁,却见大舅兀自捂住裆部时的紧张与不堪形成对比。此处快节奏的语言表达,将大舅、小舅的身体状况、生活窘况一展无遗,读来揪心,竟有些透不过气来。
小说描写人物的语言承载了作者情绪的波动。例如作者对表哥广福的描写,当所有人都围着大舅寒暄表功时,那个一语不发、默默添水的人便是广福,可见喧闹中的沉闷与压抑,就此埋下伏笔。当大舅有苦难言时,广福则拿出上好木料做好的枷凳给大舅使用,于苦闷见用心,于细节见真情。随着小舅的邀功心切,一再刁难挑衅,将广福内心的怒火与不满逼得无处可逃,终于彻底爆发,如山崩地裂般的情绪宣泄:“广福弓在那里没应答,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了两下,忽然双手举起枷凳反身就套在小舅脖子上,一使劲将小舅压趴下来。便听得小舅锐利的尖叫,那是锯片锯到了钉子的声音,撕心裂肺。”广福袭击小舅成功,连说带骂,连哭带嚎,场面甚是热闹,一时间大家都慌了手脚。处处皆是短句,字字戳人伤痛,作者前期埋下的伏笔如火花四溅,表哥广福在作者对其语言的描写中,压抑至再压抑,至无法抑制的压抑,直至无可挽回的大爆发。作者忙而不乱,情急之中描述得一清二白,表哥广福在哭诉与众人的拉扯中立体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为人物悲惨的命运再次埋下伏笔。
三、多维语言身份构建与认同
作者的两部中短篇小说集《绿皮书》、《抄家》有良好的语言意识,适当运用方言写作,并从语音、语汇、语法等方面渗入语言相关学科知识,体现了较高的语言修养和文学造诣。小说新作《回乡》,“我”的大舅从台湾回湘东北之汩罗省亲,小说人物的语言由此有了出处和显著的地域特征,使得作者运用这一优势满弓射雕,尽情发力,达到方言融合小说创作的又一个新高度。
片段五:母亲宽慰这个胸怀不宽的弟弟:哥哥得了老大一直没得照顾,心里有几多亏欠,如今回来多把广福一些钱,也是一方弥补。又道,哥哥十八九岁就漂洋过海出远门,吃几多的苦头!口袋里又有几多钱攒哟!
注解:这是“我”母亲宽慰“我”小舅时说得话。“我”母亲,汩罗人,年轻时随“我”父亲辗转广州、韶关和乐昌等地,最后在赣西落脚。母亲的话有湘方言的显著特点,对自家兄弟,更是发自内心的劝慰,字里话间乡音难改,乡愁易辨。
片段六:待得广福的哭声渐歇,他走过去,将一方蓝印花手帕递给广福,柔声中含着严厉道,男子汉,该担当的就要担当,该放弃的就要放弃,又不是细伢子,有脸哭么!
注解:这是“我”大舅的语言,与原配夫人所生骨肉广福近在眼前,却已成年,大舅的对儿子的话严厉却不失慈爱,用词讲究,该担当的就要担当,该放弃的就要放弃,颇有军旅男儿走天涯的气势。一句,又不是细伢子,有脸哭么!戎马一生,也抹不去亲情乡音在言语中的烙印,还有父亲对儿子的怜爱与要求。
片段七:他儿子悻悻然道,鬼晓得他唦!我要不是带媳妇到东莞打工去了,还不晓得要害死几个人!
注解:这是广福的儿子说得话。父亲广福弥留之际,在东莞打工的儿子回来临床伺候。“我”对广福行为不解,问起为何一年四季刷房子,广福的儿子在回答中使用了湘方言,也使用了普通话。如果按照片段五“我”妈妈使用的湘方言,在表达“多”的含义时,通常用“几多”来讲,而广福的儿子在鬼晓得他唦(湘方言)用过之后,说,我要不是带媳妇到东莞打工去了,还不晓得要害死几个人!这位小说人物在言词中用“几个”代替了“几多”,有农民工进城工作生活之后,语言蜕变的痕迹。
片段八:我问,你姆妈还好唦?
注解:这是小说主人公“我”对广福的儿子说的话。“我”受过精英教育,在大学当教授,显然是受母亲语言的影响,和亲人在一起时,使用湘方言,亲情难掩,再现真实的语言生活,以及“我”难以言说的乡愁和对亲人的关切与思念。
小说的篇头、篇尾部分,分别引用了台湾诗人洛夫的诗集《我的兽》,其中《边界望乡——赠余光中》的诗句,“我”的精神审美以及知识结构可以窥其大概。然而,本族群的人内部交际用方言,外部交际用普通话,小说人物的语言也体现了方言的特殊功能,即团结亲朋、亲近乡邻,这是社会语言学家们所说的方言的潜在声望。小说中的“我”是广福儿子的表哥,自觉运用湘方言而非书面语体,自然而生动。
片段九:用自带的照相机给夫君的三姐弟合影,请姐姐居中,两个弟弟旁立两侧,那种一脉相承的血缘表征,顿时昂然于镜头之外。
注解:描述大舅作为亲人的精神风貌。
片段十:众人在听一个带着乡音的陌生人彼岸的故事,这些故事与他们的生活与兴趣毫不相干,所为何来?
注解:描述大舅讲在外经历见闻时的语言,带着乡音。
片段十一:大舅形象伟岸,足有一米八三,如果不是长相相若,佝偻背脊的弟弟以及面容沧桑的姐姐,与他不像是一母所奶的同胞。
注解:描述大舅的外貌特征,暗示大舅与亲缘外在不同。
片段十二:大舅的声音堪称洪亮,洞穿屋宇,正是在他不肯屈服时代迫压与变迁的声音里,我甄别出了他、母亲与小舅的血脉承传。
注解:描述大舅的声音,透过声音再写内在气韵,与母亲、小舅的血脉之亲。使得《回乡》主题愈演愈浓。其中有两处写了大舅的声音。从语音面貌的方音色彩、音质的浑厚透亮再写血脉传承,让人看得见、摸得着、数得清。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概念追问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小说《回乡》用故事情节、人物语言交待了“我”、大舅、妈妈、小舅、广福、以及广福的儿子的来龙去脉。小说人物如同现实生活的人,拥有多重身份,并通过语码转换和语言风格的转换,完成不同身份的切换,构建语言身份认同。例如“我”是大学教授,在城市或曰在外族交际中,用诗歌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对待自己的表亲,一句你姆妈还好唦?就完成了知识分子形象和有农村生活经历的表哥身份转换。语言身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身份并存。大舅在同族人前乡音用畅谈往事,在儿子面前,间或书面语和湘方言,读来亲切感人,乡情跃然纸上。
小说在创作中,无法遵循教科书式的规则,正如山川大地海洋的质朴,无法用精密仪器去测量。小说创造的灵魂是自由的,评论者只能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感受,描摹情景,品味其中,小说《回乡》用生机勃勃的语言再现大舅从台湾回乡省亲的林林总总,读者若有深切体验,那无疑是作者的人生态度和对写作本真的追求,通过语言的效力,得到淋漓的表达。
[1]董洁.“城市新移民”的语言身份认同[J].《语言战略研究》,2016,(1).
[2]胡明晓.浅析南翔小说中的方言介入现象[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2).
[3]张炜.奔跑女神的由来[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4]付义荣.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5)[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责任编辑:钟 晴]
I206.6
A
1008-7346(2017)01-0090-04
2017-02-20
胡明晓,女,湖北荆门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