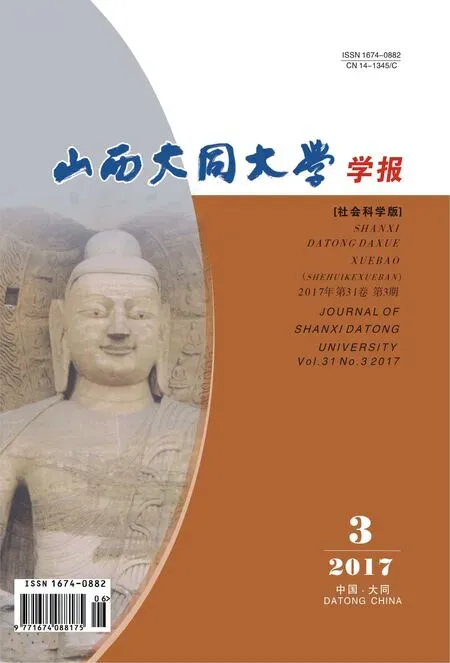“灵的文学”唤醒
——抗战时期老舍的宗教情怀浅探
李东芳,冯喜梅
(1.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北京 100083;2.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0009)
“灵的文学”唤醒
——抗战时期老舍的宗教情怀浅探
李东芳1,冯喜梅2
(1.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北京 100083;2.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0009)
作为一个受洗的基督徒,老舍之于基督教的接受是一个动态的历程。相对于晚清乃至五四的启蒙者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老舍与他们既有共性又有独特性。青年老舍对基督教的接受并不是将其作为终身信仰的追随,而是有选择性的理性接受。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老舍已经远离了形式上的基督教,但是在精神上,还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牺牲自己,服务社会,不顾个人乃至家庭幸福,而将国家乃至人类的光明作为一生奋斗的诉求等等,无不体现了基督徒的殉道与自省意识。基督教并未使得老舍走向超验神学对上帝的追寻,但是却开启了他对人的心灵的探索。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中,此种倾向尤甚。特别是1941年之后,老舍着意于用“灵的文学”对国民进行“灵的生活”的唤醒。《四世同堂》是此创作主张的集中显现。
基督教;老舍;灵的文学;理性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老舍无疑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源:立足民族文化本位,却能够直击传统文化死角的痼疾;瞩望西方文化,却又能够冷静洞穿现代性的迷思,而质疑其合法性,可谓一种兼具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跨文化视角,站在人类文化共通性的立场上,而非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带着偏见看问题;它首先是一种比较后的理性思考,只有对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利弊皆有审视与反思的人,才能够具有这样的视野与胸怀。而这种理性思考离不开老舍早年的宗教活动参与——包括加入基督教会和参与佛教的慈善活动。
这种宗教影响,形成了老舍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视点:既不因热爱本国文化而护短;也不因盲目崇拜他国文化而自卑。正如《四世同堂》中所说的:
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地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够客观的来观察的旁人,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儿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1](P87)
老舍的世界眼光,与历史学家汤因比不谋而合。汤因比强调,为了持一种公正的全球观点,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把自身所处的特定国家、文明和宗教当作文明的中心并认为它们比别的国家、文明和宗教优越,这样的历史立场是全面认识世界真实景象的巨大障碍。
老舍身上传统人格和现代思想的结合,以及这种世界性的眼光,其根源为何?在我看来,离不开对基督教文化的理性接受和辨析,这是老舍和老舍一代作家的共同特点,但其中老舍又有其独特性。
一、老舍之于基督教文化接受的共性与独特性
回顾上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宗教的思考,不难发现老舍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接受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独特性。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看到了宗教对启智中国民心的积极作用。如梁启超认为:只有通过精神的新生才能获得民族的生存与强大,而宗教对这种精神新生是必不可少的。宗教的巨大社会功能在于不仅在国家叙事上能够促进民族的精神和凝聚力;而且在个人叙事上也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希望;能够超越现实生活的凡俗,使人格得到高尚的提升;宗教还能够通过唤醒人们道德上的约束与敬畏,在增强社会和谐的同时,也能增强个体生存的勇气。
在梁启超眼中,只有宗教信仰才能救世立国。这个宗教其实指的是“一般的信仰”,就是凡是对于某种事物或者“主义”有绝对的信仰者,即为“宗教”:“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凡对于一件事情有绝对信仰,那事情便成了这个人的宗教。”[2](P269)梁启超相信,信仰对社会有益而且必要。特别是佛教精神可以作为改造国民性、改良社会文化的有效途径。
章太炎也认为若要振兴中华民族,可以用宗教发起民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并指出佛教为代表的宗教,是社会改造和文化建设的基础。[3](P276)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破灭,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弊病的根本原因除了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之外,还在于新的时代缺乏一种新的文化的引领。而继承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重重困境:它既是培植君主专制制度的土壤,同时又滋生了反科学、不讲究理性、愚昧落后的宗教迷信。所以新文化的启蒙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既要激烈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积弊,提倡科学理性,斩断封建迷信的迷思;另一方面是向西方寻求新的精神资源,寻求科学和民主的力量,企图唤醒民族灵魂。这个改造方案具体体现为批判性地反思传统文化和借鉴欧洲文化。其中,以宗教启蒙作为文化启蒙的工具,是很多五四一代启蒙者用来“改造国民灵魂”的方案之一。章太炎、陈独秀、胡适等均撰文表达了对于宗教的态度。[4]
比如章太炎提出,去除六道轮回、不重现世、只重来生、六道轮回与地狱天堂的佛教,而着重于借用佛教破除凡夫俗子、芸芸众生的“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等国民劣根性。[5]并说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6]陈独秀认为应该清除基督教中的创世说和灵异说,而吸取和保留牺牲精神、宽恕精神和博爱精神。在陈独秀看来,要拯救黑暗的中国,就必须寻求一种新的信仰,即把西方基督教中耶稣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浓厚的情感移植在中国国民的人格构成中,也就是把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培植成为一种中国人的国民素质。继之,他又明确提出,新文化包括宗教内容。“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份,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7]自“五四”文化先驱者们至其后的一代作家们,在民族文化反思与对西方文化的观察中,都曾希望以宗教的崇高信仰、高尚人格、人与人的平等互爱来实行对国民道德的启蒙。
再如胡适在《基督教与中国》一文中认为,应该摒弃“神学结构”和“迷信行为”,而独取其“道德学说”。认为“天国不在天上也不在心里,是在人世间”,“靠上帝不如靠自己。”[8](P1173)以上所举乃是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富有代表性的基督教观。
也有的启蒙者是从宗教唤起崇高的情感的角度,吸收基督教文化精髓的,周作人是比较有代表性一位。他说:“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为传染的力量的薄厚和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才是最高上的艺术。”
不同于周作人等从情感的角度发现文学与宗教的共同性,老舍更着重于宗教的道德功能。在这一点上老舍与梁启超、章太炎和陈独秀的基督教观有着某种一致性,就是力图用宗教精神重塑国民的道德观,从而完成国民灵魂的改造。所以他们摒弃了基督教教义中的“神”的部分,而侧重于基督教对于人格的淬炼。学界关于老舍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中,对此多有共识,认为老舍是从救治人心的角度,希望从文化上开出药方,拯救积弱的国民,其实就是从道德和国民心态上,希望唤醒个体的公民意识。如徐德明先生所述:
老舍终其一生对人类抱有宗教情怀,同情与拯救人世的苦难的使命渗透在他人格中,从而凝成他一贯的救世态度与灵的文学的美学追求,在文学与救世的双重任务中,他往往暂时牺牲了文艺,形成他感人至深力量的仍在文艺,救世的社会努力更应被人充分理解。[9]
虽然一些启蒙者对于宗教济世的思想存有怀疑,如鲁迅晚年也曾对章太炎的以宗教倡革命的思想表示怀疑,认为这似乎只是一种“高妙的幻想”。[10]在鲁迅看来,宗教可以是一种个人人格的修养,但是未必可以作为群体行为。但是毕竟作为一种启蒙的尝试,这种努力是可贵的,应该予以理解。
对五四一代启蒙者来说,宗教更多的只是一种启蒙大众的手段和工具。借助信仰的目的不是通过神秘的宗教体验唤醒狂热的宗教感情,来解脱不幸与苦难,得到心灵的宁静;而是借用宗教来净化情感,荡涤私欲,激发出崇高人格而不堕卑琐苟且,忘己济世,服务社会的公民意识与国民精神。
五四一代学者中,“鲁迅宣示的灵魂自我审判;冰心追求一种爱;许地山宣扬宽容主义;郭沫若宣泄复活意识,坦露内心的忏悔;徐志摩排泄不尽感伤;巴金呼唤人类至上;曹禺思考人间的罪,艾青永远追求一种光等。”[11]而老舍吸收基督教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崇尚与人为善和救世主义”。也就是说,老舍是以宗教的道德观(包括基督教的赎罪与佛教的因果报应等观念)作为评判社会伦理的尺度。
早期的基督教体验加上欧游经历使得老舍初步形成了现代思想。对于曾经看过世界的五四一代先进的知识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看到祖国与西方社会巨大的差距而流露出的焦虑与苦闷更加让人感到无助,从而引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思考。
二、入教动机:身份隐痛与救世理想
青年老舍力图凭借基督教的道德化力量,拯救人心,延续了五四一代乃至晚清启蒙者的宗教观。和其他受过教会教育或者出生于牧师家庭,深受基督教熏陶的作家不同——比如林语堂是出身于牧师家庭,冰心上的是教会学校,而老舍加入基督教与之不同。一方面没有条件长期浸淫在基督教的宗教教育里,另一方面,教会学校多是比较贵族化的教育,老舍家境贫穷,连上学读书都是由佛教居士刘善人(即后来出家的宗月大师)提供学费,怎么会接受基督教呢?
老舍在自述中陈述早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母亲,主要影响他的性格:“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老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12]一个是刘善人,影响了他的人生观。[13]刘善人就是《宗月大师》中的宗月和尚和《正红旗下》中的定禄大爷。老舍从母亲身上学习到善良、勤俭、吃苦耐劳;从刘善人身上则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为何老舍不是皈依佛教,成为一名居士,而是亲近基督教,最终受洗呢?让我们还原一下历史场景:老舍是在1922年上半年,受洗加入了基督教。正如关纪新先生在《老舍评传》《老舍与满族文化》中指出的,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后,失去了曾经有过的特权和优越地位,生存面临危机,很多旗人穷困潦倒,处于社会的边缘。《正红旗下》也对旗人的窘迫处境做了描述。
23岁的青年老舍担任京师郊外北区的劝学员,在北京教育界遭受了排挤和打压(实干者遭受排挤成为后面系列小说中的反复出现的场景,甚至成为老舍批判社会的一大情节模式),出身寒门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的青年老舍,可以想象当时那种郁闷的情绪,同时又沾染了不良生活习惯,遭遇了肉体上的病痛折磨,即“二十三,罗成关”,肺病使他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不得不静养了一段时间。就在此内外交困的时节,经舒又谦和赵希孟等几位满族朋友的介绍,他介入了基督教的圈子。参加了宝广林举办的英文补习班,参加了“青年服务部”的社会活动,并参加了“率真会”,经常讨论如何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满族朋友为何可以成功地说服青年老舍?我认为还是与老舍的民族身份认同有关。众所周知,老舍的父亲是一名旗兵,死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战火中,而辛亥革命后的排满,使得年幼的老舍对于身份认同有着一种敏感的隐痛。
青年老舍的满族朋友宝广林牧师,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神学系,当时主持缸瓦市基督教会。1922年在京沪两地,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基督教本色运动,即提倡中国基督教会的自养、自治、自传,并且提倡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相融合,重新诠释基督教教义。宝广林牧师所主持的缸瓦市教堂,正在酝酿将缸瓦市的管理权从英国伦敦会手中拿回,而建设由国人自办的中华教会。
这种基督教的本土运动,一开始就让处于“身份”困惑中的青年老舍,寻找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触动了老舍不甘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民族情结,可以想象遭遇现实困顿与理想无着双重打击的青年老舍的心是怎样一下子与之契合的。从伦敦会手里拿回教权,对于老舍来说,与抵抗侵略、抗击外侮的反帝运动似乎有着同样的性质。它激活了幼年老舍父亲死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创伤性记忆,从心理学来分析,家族创伤往往成为一个人潜在的隐痛,可以塑造生命个体面对外界的应对方式,比如谨慎;也可以转化成一种内在信念,比如爱国。在老舍身上,兼而有之,老舍的性格从小便显示出中年人的沉稳与成熟,情感不外露,摒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浪漫主义的感伤,寡母养大的童年经历,使得老舍自幼便显示出面对世事无常的坚韧与担当。父亲阵亡于保卫京城的战火,作为家族史潜藏在老舍的记忆深处,使他对于“洋人”有着一种本能的警觉和排斥。(这在其作品中对于洋鬼子之类中国人心态的描写,可以看到其情感倾向。)
那么,基督教作为外来文化,怎么会吸引到这位敏感的青年的?
基督教固然是外来文化,但是满族好友的推荐,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并且教会活动提供了做善事的平台,青年老舍正是想要一展宏图,小试身手,想要通过做善事改变社会。教会的大量慈善活动锻炼了老舍演讲、写作、协调组织的能力,使得老舍一下子从寒微家庭的封闭与满族身份的郁闷中走出来,冲破了现实的瓶颈,发现了广阔的天地。
再加上,青年老舍的才干很快受到教会的重视,教会提供了一年在燕京大学学习的机会,并且得到了赴伦敦任教的机会。而这对于一个寒门子弟来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会替代性地完成了对于青年老舍这个师范专科生的高等教育:不但有做事能力的培养,更有对于人格、理想、生命意义的教育,这些使得老舍获取了“尊严”。
“人的尊严”这个词反复出现在老舍的笔下,可见是青年老舍的一大诉求,换言之,“尊严”在此可以理解为价值感,即人之为人的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非儒家文化按照社会地位和等级严格划分的“价值”。在教会里体验到“人”的价值,是很多教徒入教的动机,比如《老张的哲学》中,赵四就是因为在教会做事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平等而入教的。
基督教义中超验神学的一面从一开始就不是青年老舍感兴趣的地方,他更加倾向于陈独秀等五四一代前人的基督教观,那就是从救世、服务社会的角度吸收基督教的道德功能,改造社会。
青年老舍在大量的教会社会活动中获得浓郁的宗教情怀和实干能力,奠定了他一生的奋斗目标、思维方式和情感倾向。
1918年,老舍担任京师公立第17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校长(现北京方家胡同小学);
1921年夏,老舍在缸瓦市基督教堂兼任西北城地方服务团附设铭贤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校务主任。
1922年,受洗入教后,为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起草规约草案,完整规定了教会宗旨和体制等内容。
老舍参加的教会活动有:
1922年,应聘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国文教员,并被特邀为“查经班”主讲。主讲《新约》《旧约》等。
1922年7月,老舍起草了《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草案》。
1922年12月,翻译宝广林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一文。
1923年,主持儿童主日学。
1922—1924年,他还担任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主日学的总干事,参与山海关、沈阳耶稣青年团的夏令营活动,到基督教会灯市口地方服务团兼任干事,负责灾荒赈济、办女工工厂、卫生知识宣传等活动。
似乎,青年老舍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
然而,我们从其创作中,如《老张的哲学》《二马》中,看到青年老舍对于教徒的功利动机,以及基督教作为殖民主义工具的警醒,反映出青年老舍作为五四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维和理性素质。也能够看出他对基督教的接受并不是将其作为终身信仰的追随,而是一个身心困顿的青年,在黑暗的社会找不到出路时的精神休息站,是对其有选择性的理性接受。
当然,这些教会活动,增强了老舍的胆识和实干能力,乃至后来老舍回顾说,他的志愿是——“那时候我颇自信有些做事的能力,有机会也许能作作国务总理什么的。”[14]在这有些调侃的幽默中,可以看出青年老舍的理想志在“做事”。
正如凤媛通过对《小玲儿》的分析,发现“虽然正式受洗,但并不代表老舍对于基督教就全心皈依。”而是内心充满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既有丧父之痛和末世旗人被主流社会冷落的孤高寂寞,也有入教后无法形成真正的身份认同的内在焦虑,而这种焦虑又在参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事业和本色化运动才得以化解。”[15]故而青年老舍加入基督教,正是他寻求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济世之举。可见老舍对基督教一开始的入教动机就包含着希望做事,服务社会和实现个人理想,看到基督教教义具有改造人心、呼唤良知,使人们过上有“灵”的生活的社会教化功能,也释放并缓解了由于身份认同带来的焦虑,使身心得以安顿。
似乎老舍在30年代以后已经远离了形式上的基督教,但是在精神上,还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因为老舍身上具有牺牲自己、服务社会、不顾个人乃至家庭的世俗幸福,而将国家乃至人类的光明作为一生奋斗的诉求等等,无不体现了浓厚的宗教意识。
三、宗教情怀的流变
由于国内意识形态环境的影响,建国后老舍本人和家人均对其基督教入教一事保持低调。如胡絜青女士所言,老舍在家里从来没有祈祷,过圣诞节等宗教仪式。老舍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对自己与基督教的关系基本不提。
但是我们反观老舍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还是能够看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其实老舍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的青年老舍的入教体验,对教会慈善活动有一些认同;30年代回国后,中年老舍渐渐淡化了基督教精神,在作品中流露出对基督教的进一步反思;40年代的中年老舍,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都有所改变。总体上,对于老舍之于基督教经历了从理性的选择性接受,到反思与批判,再到形式疏离、提纯吸收的过程。
20世纪40年代,随着对中国革命的深入了解和对世事阅历的体悟增进,老舍在集大成的鸿篇巨制《四世同堂》中对宗教的“批判与反思”的态度就非常明显。
20世纪20-30年代,老舍还将基督教理解为一种拯救人心、启蒙精神的工具,但是到了抗战时期,一切在战争面前都显得脆弱,信仰变成了一种安慰剂,瑞宣和钱诗人都从战争的残酷中警醒,把“爱国”,把国之安危之于个人生命尊严的重大意义发挥到极致,回旋的主题是爱国主义,是“国家至上”成为核心信仰。不过这信仰的内核仍然是一种宗教精神。
宗教精神的核心为何?
闻一多先生说过:“人生如果仅是吃饭睡觉,寒喧应酬,或囤积居奇,营私舞弊,也许用不着宗教,但人生也有些严重关头,小的严重关头叫你感着不舒服,大的简直要你的命,这些时候来到,你往往感着没有能力应付它,其实还是有能力应付,因为人人都有一副不可思议的潜能。问题只在用一套什么手段把它动员起来。一挺胸,一咬牙,一转念头,潜能起来了,你便能排山倒海,使一放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了。那不是技术,而是一种魔术,那便是宗教。”[16]
老舍汲取的基督教精神与之有类似之处,就是在普遍宗教的意义上肯定基督教有克服人性弱点,提升人格的作用,其逻辑是基于此:一是人类与“兽类”(动物)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有超越性灵性追求,而动物只有吃喝等感官需要;二是人应该具有超越现实利害的精神寄托,比如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牺牲世俗幸福乃至生命,人不应该是情感和原欲的奴隶。老舍多次提到但丁的《神曲》对他的影响。但丁的作品中,面对人的存在,由于受到阿奎那的影响很大,从超验神学本体出发来建构人的存在的,强调人的知识与理智,把基督教的信仰和爱看得高于一切。在这一点上,老舍与但丁是有区别的,他对于基督徒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敏感,拒绝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而迷失国族之间的差异。
在朝戈金先生统计的老舍关于宗教方面的5篇文章、译文和讲演录中[17],可以清晰地看到老舍先生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更加使我们确信老舍通过亲身体验和加入过教会活动,才能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
1920年代基督教本色运动影响巨大:即要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名”,由中国人自己对它实行“自养”“自治”“自传”。老舍在此期的教会活动也是本色运动影响下的产物。[17]可以基本判定,老舍入教与其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当时青年老舍身份的边缘化,涉世未深的处处碰壁的苦闷,使得同是满族人的宝广林牧师的介绍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在老舍生涯中的“人际传播”模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何以青少年时代的老舍对于资助他上学读书,有莫大恩惠的宗月大师并未使得他皈依佛教。不过,去宗月大师主持的粥厂参与慈善工作的经历,增添了他对“向善”人格的渴望。
对老舍而言,基督教既是一种救治人心的重要工具,更是一种锤炼个体人格的重要手段。从他在缸瓦市基督教会工作时,为儿童写的《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18]一文中可以看出,老舍是力图通过基督教的礼拜仪式来培养儿童的谦卑心等人格品质。老舍的第一篇译文是翻译宝广林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19],文中宣扬道德、同情、克制、服从等基督教教义以及通过“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的大同途径,都足以证明老舍是从提升道德、淬炼人格品质的角度吸收基督教文化的有益成分的。
赴英国前后,老舍更加坚定了改造社会,建立新文化的双重理想。这在他创作于伦敦的三部长篇小说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揭示社会黑暗,暴露社会问题,是其作品的主题。
老舍的这种创作追求,一直延续到1929年他离开英国,经新加坡回到山东济南教会学校齐鲁大学任教。山东时期,老舍的宗教视野主要聚焦于从“救治人心”入手启迪民智,同时引入新文化的思想。
据刘涛先生考证,老舍于1932年9月18日在济南一个教会学校做过一个《以善胜恶》的演讲,认为今日社会之所以恶劣,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心不良;而经济困难,科学不发达,以及农村破产只是表层的原因。而这种人心不良在中国的突出表现是:“知恶而去作恶,尚可救药;现在的一般人是已不知自己所作的是恶,试想这个人心坏到如何的程度了呢?”[20]
由此,老舍提出只有依靠宗教,才能使人们知善恶,最终以善胜恶。该文提出,若想改造社会,必须有善的信仰。要想救世,非得有宗教信仰一般的意志力才行。因为邪恶并不能战胜邪恶,不闻不问的态度也不能战胜邪恶,只有唤醒人们心中的善,才能够具有挽回人心的希望。
进入抗战时期,在创作了宣传抗战的一些通俗作品之后,老舍再次回归到自己的创作主线上,即将文艺家的责任定位为“灵魂”改造。
1941年,他发表了著名的《灵的文学与佛教》一文,提出“因为人民缺乏灵的文学的滋养”,使得“我国的坏人甚至比外国还要多些。”而藉此对一直“着重于做人”的文化提出了质疑:“着重于做人的人,却有很多简直成了没有灵魂的人,叫他吃点儿亏都不肯,专门想讨便宜,普遍的卑鄙无耻,普遍的龌龊贪污,中国社会的每阶层,无不充满了这种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提出“灵的文学”的美学追求的著名论文,在评点儒释道三家为中国文化代表性文化时,指出儒家和道家均没有什么,而唯独从印度泊来的佛教文化,提出肉体之外,还有灵魂,要能够使人过上有灵魂的生活。可见,作者希望“灵的文学”,能够激发人们的良知,能够使人明白光明的值得追求,以及黑暗的可怕,可以洗涤人们不良的心理。这与梁启超的佛教救国论有着相似之处。
同时这篇论文,还指出了佛教在中国已经传播2000余年,然而并未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上去,送入到人民的脑海去,而“致使中国的社会乱七八糟,人民的心理卑鄙无耻”。并且佛教传播不利,使得很多佛教徒存有不正确的观念,以为祈求就可以保佑自己的一切。作者批判了这些不正确的信佛方式,进一步指出,真正的信仰是要使人们“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使大家都拿出良心来”。所以,借助宗教使国人打开良心,启迪良知,开发人性中善的力量,是老舍宗教情怀的核心。
可以说,这篇演讲是老舍文艺思想的集大成,也是一个分水岭。老舍的宗教情怀,并没有严格地区分基督教和佛教教义的不同,而是在普遍宗教的意义上,推崇宗教可以使人超越肉身,发现灵魂。换言之,基督教并未使得老舍走向超验神学对上帝的追寻,但是却开启了他对人的心灵的探索。老舍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中,此种倾向尤甚。
1941年以后,老舍着意于用“灵的文学”对国民进行“灵的生活”的唤醒。《四世同堂》是此种创作主张的集中显现。
注释:
[1]老舍.四世同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A].张钦士编.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C].燕京华文学校,1927.
[3]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A].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7.
[4]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J].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刊《生命》,1922(03).
[5]章太炎.革命之道德[A].太炎文录·别录[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6]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A].章太炎演讲集[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7]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A].新青年[C].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转引自《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袁伟时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8]胡适.胡适文存:三集卷九[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
[9]徐德明.老舍的宗教态度与创作[J].民族文学研究,1999(04):49-56.
[10]鲁迅.太炎先生二三事[A].且介亭杂文末编[C].上海三闲书屋,1937.
[11]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D].上海:华东师大博士论文,2001.
[12]老舍.我的母亲[A].老舍全集(第1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3]老舍.宗月大师[N].华西日报,1940-1-23.
[14]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A].老牛破车[C].晨光出版公司,1948.
[15]凤媛.一个非典型基督徒的心灵地图[A].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第七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重庆,2015.
[16]闻一多.从宗教论中西风格[A].闻一多全集(第3册)[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7]朝戈金.老舍关于宗教的佚文[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02):215-218.
[18]老舍.真理周刊,1923(16-21).
[19]老舍.《生命》月刊第三卷,第4期,1922年12月.
[20]刘涛.老舍佚文三篇辑校[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02):192-196.
“Spiritual Literature”Swakening——Research on Lao She's Religious Thoughts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LI Dong-fang1,FENG Xi-mei2
(1.Depart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100083; 2.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As a baptized christian,Lao She to the acceptance of Christianity is a dynamic process.Comparing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ven the“May 4th”enlighten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Lao She has both generality and uniqueness to them.In youth Lao She accepted Christianity not as a lifelong belief to follow,but selective rational acception.In the 1930s,Lao She had been away from the form of Christianity,but in spirit,was a standard Christian:sacrifice oneself,serve the society,regardless of the individual and family happiness,and regard the country and even the light of human as a lifetime struggle of appeal,and so on,all reflect the Christian martyrs and introspection consciousness.Christianity dod not make Lao she to pursue the transcendental theology of god,but opened his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 mind.Especially after 1941,Lao She the nation's spiritual life attempted to awaken the by“Spiritual literature”.“The Yellow Storm”is the creation of the opinion.
christianity;Lao She;spiritual literature;rational
I206.6;I207.42
A
〔责任编辑 裴兴荣〕
2017-02-25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老舍创作”(14WYB021)
李东芳(1972-),女,山西大同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跨文化国际理解教育;冯喜梅(1971-),女,山西大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1674-0882(2017)03-004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