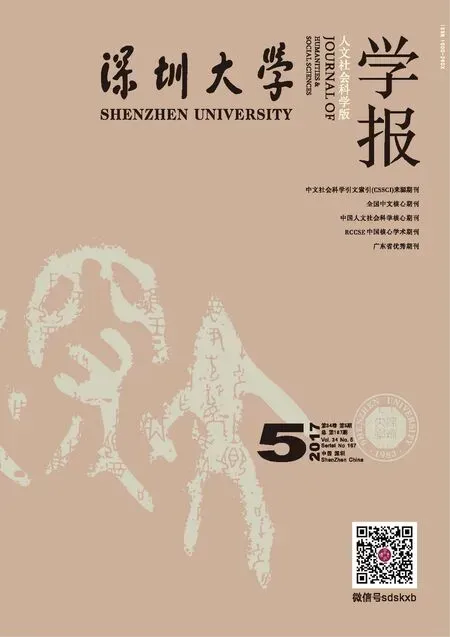极致的真实:传媒艺术的核心性美学特征与文化困境
刘俊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编辑部,北京 100024)
极致的真实:传媒艺术的核心性美学特征与文化困境
刘俊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编辑部,北京 100024)
传媒艺术主要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艺术形式,同时也包括一些经现代传媒改造了的传统艺术形式。“仿真”是鲍德里亚“仿像”观点的第三等级,指的是一种摹仿之真,彰示着传媒艺术的美学特征。传媒艺术摹仿真实的符号群本身便呈现出构成物质世界的假象,以至于艺术接受者越来越不辨“仿真”之真与现实、客观、原始、朴素之真的区别。以动态影像为基础性艺术元素的传媒艺术,由于日常化、连续性、包裹式地用动态影像这种“真实的符号”代替“真实本身”,而表现出极度、极致地聚焦、呈现和张扬“现实”的美学风格,这成为传媒艺术和传统艺术在美学特征上的一个极为核心的区别。同时,传媒艺术与传统艺术在摹仿真实问题上有重要区别,如传统艺术之“意”与传媒艺术之“形”、传统艺术的距离存在与传媒艺术的距离消解。这些特征和影响背后也必然存有“仿真”这一传媒艺术美学特征背后的大众文化困境,如艺术接受者易被庸常化、被均一化、忽略对本质层面的追寻等。
传媒艺术;美学特征;传统艺术;“仿真”;大众文化批判
一、引言:何谓传媒艺术
纵观人类艺术发展史,有一个庞大的艺术族群是人类最先熟悉的:人类将自己的情感、思想和想象与特定的材质和形式相结合,表现出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特殊世界,造就了音乐、舞蹈、文学、建筑、雕塑、绘画、戏剧等蔚为壮观的艺术族群。我们称这一艺术族群为“传统艺术”族群,传统艺术族群曾长期稳定地构成了人类艺术世界的全部内容。
然而,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大众传播的勃兴、大众文化与现代性的塑成,人类艺术发展的长河终究出现了分流。分流的起点是19世纪上半叶摄影的诞生。这一分流从微小到磅礴,逐渐形成了另一庞大的艺术族群,这便是主要由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组成的艺术集合。这些艺术形式在创作、作品和接受方面具有艺术的共性,它们拥有着与传统艺术具有鲜明区分的三大特征: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我们将这一艺术族群命名为“传媒艺术”(Media Arts)。
如果说音乐、舞蹈、文学、建筑、雕塑、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可以支撑起一个艺术族群,也便是传统艺术族群;那么,以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为主的艺术形式,因其内部共享诸多逻辑一致的共性(如科技性、媒介性、大众参与性),外部又与传统艺术族群有鲜明区别,它们同样已经支撑起了另一个赫赫的艺术族群,也即传媒艺术。
通过反复的比对与归纳以及在艺术史与传媒史的考察中定位,我们认为,传媒艺术的最基本特征是逐渐鲜明的科技性、媒介性、大众参与性。之所以将这三性视为传媒艺术与传统艺术最具区分度的特征,有诸多原因,例如此三性分别主要体现了二者在艺术创作端、传播端和接受端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差异,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此外,此三性分别主要对应着艺术评判端对真、善、美的思索与探求,从更加宏大的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我们,人类对于世界的把握方式大概有科学的、宗教的、日常生活的、艺术的四种,从这个角度看,科技之真(科学的)、传播之善(宗教的)、大众参与之美(日常生活的)最终统一为对艺术、对传媒艺术的终极问寻等等。
具体来说,在科技性的框架下,使得传媒艺术呈现出如下具体特征:(1)在创作上走向机械化、电子化、数字化的无损与自由复制创作;(2)在传播上走向非实物化的模拟/虚拟内容传播;(3)在接受上走向人的审美感知方式的“重新整合”。
在媒介性的框架下,使得传媒艺术呈现出如下具体特征:(1)在创作上走向艺术信息的日常性“展示”;(2)在传播上走向逐渐强烈的社会干预色彩;(3)在接受上走向“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诉求。
在大众参与性的框架下,使得传媒艺术呈现出如下具体特征:(1)在创作上走向集体大众化创制;(2)在传播上走向“去中心化”传播;(3)在接受上走向体验“变动不羁的惊颤”与追求快感审美。[1]
这些均与传统艺术的手工性、膜拜式、精英化创作,实物性、圈子式、中心化传播、单感知、静观式、无功利接受有划时代区别。
总之,无论怎样,作为当前最能融科技与人文于一体的艺术形式与品类,传媒艺术显然已经深刻地建构和影响了人类艺术的格局和走向,成为当前人类最重要的审美对象和审美经验来源。
我们界定,从狭义上说,传媒艺术是指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借助工业革命之后的科技进步、大众传媒发展和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在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中具有鲜明的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的艺术形式与族群。传媒艺术主要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艺术形式,同时也包括一些经现代传媒改造了的传统艺术形式[2]。我们甚至可以将人类艺术简单分为传统艺术和传媒艺术两大对应对举的艺术族群。
二、问题的提出:对传媒艺术特殊性、整体性美学特性的亟待把握
(一)面对的问题:两种传媒艺术研究的缺憾
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是当下最主要和最成熟的传媒艺术形式,其主要表现方式是借助电子科技手段和大众传媒载体相结合,呈现的连续不断、声画配合的动态模拟影像。
如前所述,很大程度上说,传媒艺术已经成为当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频度最高、接触渠道最便捷、接触欲望最强烈的艺术形式。我们如今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对周遭世界的接触、记忆、认识、判断、反馈在相当大程度上借助传媒艺术得以完成,人们对内心世界欢愉、悲楚、奋进、彷徨、憧憬、留恋的表达在相当大程度上借助传媒艺术代为呈现。对个体如是,对群体而言同样如此:当今世界太多的政治对垒、经济博弈、社会相照、文化角力在相当大程度上都需要也必然有传媒艺术的不断参与以广域传播。在这种人类社会普遍地浸润其中甚至无法摆脱的传媒艺术环境中,作为艺术学理论的关注者、思考者,我们需要深刻地关照这种新环境下的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的特征与困境。
纵然传媒艺术在当下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但我们在研究中还是出现了显著的问题和不足,亟待回应和补足。这也正是本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就本文关切而言,这种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为两点。
第一,传统艺术的整体性研究大盛,而传媒艺术的整体性研究不足
一方面,我们对传统艺术族群有清晰的整体式研究,我们清晰它们共持的命名、属性、本质、特征、功能、价值,更重要的是从对传统艺术族群的整体考察中,我们抽离出了当下通行的一般艺术学理论;但另一方面,我们对传媒艺术族群的整体性考察,却极为不足甚至全然缺失。也即,一般艺术学理论因其依托于传统艺术品种类型而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常常无暇顾及电影电视,特别是新兴媒体艺术所呈现出的具有差异性、独特性的景观与状态,甚至经常做出相反的判断。而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兴媒体艺术等研究和学科,则更多寻求对各自特色化的规律与规则的阐释,又较少甚至疏离于抽离出一般艺术规律的学理法则[3]。
第二,对单体传媒艺术形式的美学研究大盛,但对传媒艺术的整体美学特征特别是核心性特征研究不足。也即,当前我们对摄影、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等传媒艺术的具体艺术形式的美学特征,有不少讨论和辨析;而从传媒艺术的“艺术家族”“艺术族群”的整体意义上,对传媒艺术的较为核心、重要而典型的美学特征和品性的提炼与阐释却极为不足。况且美学的重要追求很多时候并不在于“科学那种单方面的或分门别类的精确研究,而是力求探索人的丰富与完整特性”[4],对一种完整性的探问本就是美学的重要旨趣。
而解决不了这个整体性问题,一则很难明确把握传媒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深度独立区别;二则也使得传媒艺术的整体性研究可能仅仅停留在艺术学领域的命名、概念、特征界定阶段,而较难深入拓展至艺术哲学、美学的领域。况且,因当前受大规模、高密集、连续性、普遍性的动态影像包裹而导致的人的认知方式、认知结构和认知结果的变化,更使得这种传媒艺术美学品性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亟待探讨的问题,也是美学研究中不应忽略的重要部位。
狄德罗“美在关系”的观念提示我们:美的本质是一种关系,美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要放到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中来考量,要放到社会涌进、历史前行的关系中来思辨。深入来看,不仅接受者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接受者的审美感知结果,而且艺术形式所培养的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如何看待物质世界这个问题,同样应是“美在关系”的题中之义。
在传媒艺术的淹没中,人被培养得“仿真”式地看待物质世界,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已被深刻地影响,我们对“仿真”或者说极度的、连续、大规模、长时段地反映“真实”的这个传媒艺术的美学特征便不可不察了。特别是当前数字新媒体技术发展,使得这种“真”已经是“真”上加“真”。更重要的是,在未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的普遍性、深度式介入生活,“仿真”取代现实世界的客观真实,并非只是一种我们的担忧,而是有可能彻底变成现实。这使得本文所探讨的话题,更有紧迫意义。
美学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自上世纪开始到本世纪至今,文化的发展在两个方面特别令文化学者、美学学者关注:一是消费化,二是媒介化。这也正是本文在考察传媒艺术关键性美学特征之后,对其在消费化和媒介化两个维度上进行文化反思的必要性所在,这个反思以大众文化为切口,具体原因后文将述。
(二)传媒艺术“实践”的发展,呼唤对艺术“研究”的动态回应和引领
在艺术史发展的新阶段,就艺术内部而言,传统艺术学和美学理论、观念难以解释发展变化了的传媒艺术实践;就艺术外部而言,传媒艺术实践的发展更是超越了艺术领域与范畴的限制,以跨领域、跨范畴的状态与最新的科技、媒介、社会文化状况相结合,它已不是艺术学和美学甚至已经不仅是一套有关艺术、审美和哲学的理论,而应具有兼容性、整体性并成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总和”的反映。
我们如果不在吸收传统艺术学和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深刻观察、思考与辨别传媒艺术“作为艺术”的最新发展状况,以及传媒艺术“不仅作为艺术”的跨领域、跨范畴发展现实获得新知,我们不消说能否稍稍解释一下发展变化了的人类社会、万千世界,就连搞清艺术和美本身是什么,恐怕也面临诸多新的障碍。
当艺术生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却常常还固守于许多传统的角色和认知之中,究其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与传统角色相关联的,是一种体系的力量,这种力量很难被打破,这种力量甚至神话般地交织着我们的文化和政治结构所产生的意义。”[5]不过,确如詹姆逊所说:“老的美学传统几乎拿不出足够的理论储备来解释这些新作品,因为这些新作品吸纳了新的交流手段和控制论技术。”[6]“在这种情势下,与其恋恋不舍地沉浸于艺术的往昔之光荣、艺术美感之圣洁与崇高,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需要一种新美学。”[7]时至今日,作为对艺术和美的实践的回应与引领,艺术学和美学理论研究亟需切实进入到一个动态发展的状态。正如约翰·拉塞尔所说:“当艺术更新的时候,我们也必须随之更新。我们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种休戚相关之感,有一种与之分享和被强化的精神力量,这正是人生所应贡献于时代的最令人满意的东西。”[8]
三、传媒艺术的“仿真”美学特征
(一)传媒艺术的“仿真”问题
将美进行理论化抽离是一个人类的难题;从当下风风火火的网络实践中,抽离出美的理论总结更是一次艰苦的尝试。艰苦在于难以将研究对象推出一定的距离之外进行陌生化观照;艰苦也在于这种例如关于美学特征的抽离,也常常难免挂一漏万。
好在虽然我们长期将美学定义为关于美的“科学”,但其实我们的思考材料,常常是美“感”、美学甚至被称为“感受学”,而不是刻意去追求一些冷冰冰的什么确定的数据或论断。“感”可以是形象的、主观的、灵活的,但因艺术接受者、研究者的个体差异,可能存在不少结论上的不同。
西方美学在研究涌进过程中呈现出至少三个维度:哲学的美学、心理学的美学、艺术学的美学。哲学的美学研究的是美的本质,这是本文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本文对传媒艺术美学问题的思考,更多的从艺术学和一定的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加以观照。
如前所述,当前传媒艺术深刻地改变了人对物质世界的认知。现实中邻家的长短故事往往不及影像作品中的家长里短,显得离我们距离更近;现实中相对波澜不惊的社会生活,被影像作品中的杀伐乱象所替代;现实中宁静平凡的感情,相对于影像作品中断裂起伏的情感周折,显得如此不真实。于是,日久天长,在默默的积累与培育里,我们眼中的物质世界不再是现实中那些平常的人事、平稳的社会、平凡的感情,而是传媒艺术所呈现的虚构的人事、杂乱的社会、跌宕的情感。正如海德格尔的名言:“从本质上看,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9]
传媒艺术对真实的摹仿还实现了符号的自由流动,即传媒艺术呈现的内容可以超越古今、超越地域、超越阶级。就此,夏代的神话、商代的车马、汉代的兵戈、魏晋的衣袖、唐朝的庙堂、宋朝的街市、明朝的战船、清朝的宫廷都不再只与远年的未知有关;就此,希腊的神庙、罗马的教堂、法国的荫道、英国的学府、美国的街区都不再只与异域的神秘有关;就此,贵族的奢靡、中产的浪漫、贫民的哀寂都不再只与隔膜的壁垒有关,而是均一一真实可感地呈现于眼前。“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在1927年曾兴致高昂地大声疾呼:‘……[……]一切传奇,一切神话和迷思,所有的宗教创始者与宗教本身[……]都在等待他们以光的影像复活,而英雄人物纷纷拥到我们的门前,想要进来’。”[10]况且当下的社会,人逐渐被物化和异化,步履飞驰,人情淡漠,传统上人们用于接触人情社会的时间,更多地被投放于对传媒艺术的凝视中,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把握便可能更多地被传媒艺术营造的“仿世界之真”所左右。如果说当下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越来越取决于五块用于传播的屏幕:电视屏、电脑屏、手机屏(含移动终端屏)、电影屏、户外屏,当然未来也会有如VR屏等;那么,从更广阔的层面上讲,“仿真”效果不仅是传媒艺术的特征,它也是当下现代传媒整体的“功效”。
我们把传媒艺术所营造的物质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个比真实世界更为真实的世界;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信息、观点与整体感知,多是由传媒艺术“告知”我们的,而不是我们亲自经历的。所有这一切,与一位出生于1929年的法国学者的学说相吻合,这便是鲍德里亚与他的“仿真”说。
“仿真”是鲍德里亚“仿像”观点的第三等级,它指的是一种摹仿之真,而不是现实、客观、原始、朴素的真实,但是这种摹仿出来的真实比现实、客观、原始、朴素的真实还要真实。他认为当人类进入到传媒艺术时代,摹仿真实的符号群自身就构成了物质世界,不必再有什么参照去界定摹仿得像与不像。
正如鲍德里亚认为的那样:“它只是一个庞大的仿象,这时,就无所谓真假了,而是仿像,也就是说,该系统永远不再与‘真’(real)发生交换,而只是与自身进行交换,在一个没有所指、没有边缘、没有中断的循环体系中与自身进行交换。”[11]
“一旦拟像越来越密集地出现在人类生活中,人类也就被数不清的拟像包围于其中,以至把拟像的世界看作现实的世界;另一方面,因为数字技术的出现,作为影像成因的指涉物如今可以在电脑上自主生成,拟像和其真实指涉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这更是对人类文化的走向带来深远的影响。”[12]所以,“这已经不是模仿或重复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戏仿的问题,而是用关于真实的符号代替真实本身的问题,就是说,用双重操作延宕所有的真实过程。这是一个超稳定的、程序化的、完美的描述机器,提供关于真实的所有符号,割断真实的所有变故。”由此,鲍德里亚得出了一个结论:“在通向一个不再以真实和真理为经纬的空间时,所有的指涉物都被清除了,于是仿真时代开始了。”[13]
其实,在鲍德里亚之前,李普曼于20世纪20年代在他那本被誉为“传播领域奠基之作”的《舆论学》中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并提出“拟态环境”这一新闻传播学经典概念。李普曼认为人的实际活动范围和注意力都有限,不可能对于与自己有关的整个外部世界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于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于是,在人们与真实的物质环境之间便存在一个由新闻机构的报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是经过新闻机构有意无意地选择过的。人的行为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拟态环境”的反应,并且人们不会有意辨析“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的区别,往往把“拟态环境”当做真实环境来对待[14]。传媒的报道内容比事实本身更重要,甚至当真正的物质世界现实被呈现的时候,反而让我们不敢相信,目瞪口呆。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说源自对纸质新闻媒体的把握,而本文辨析的“仿真”说则从与纸质新闻媒体无关的艺术和美的角度思考,可见,当人类进入到大众传播和传媒艺术时代,突然对这一话题有了基于不同艺术和传媒样态的共同思辨,有了基于艺术学、美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的共同关切,更见这一问题对人类认知与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
(二)“仿真”:极致的真实是一种极端之美,是传媒艺术和传统艺术在美学特征上的一个极为核心的区别
作为美学问题的“仿真”,其实体现了传媒艺术的一种对真实的极端表现力,从美的意义上看,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之美。
显然,以动态影像为基础性艺术元素的传媒艺术必然导致“仿真”成为一个核心性问题,这个核心性问题牵涉出的是如前所述的,其由于日常化、连续性、包裹式地用影像这种“真实的符号”代替“真实本身”,而表现出极度、极致地聚焦、呈现和张扬“现实”的美学风格,这成为传媒艺术和传统艺术在美学特征上的一个极为核心的区别。当然,传媒艺术的“仿真”问题自然不是其唯一的美学特征,其存在也离不开传媒艺术的综合性、丰富性、融合性、互动性等重要美学特征。
我们并不是说传统艺术那里没有对“真实”复制的欲望、冲动和实践,只是传统艺术更多是“模仿”,而以影视为代表的传媒艺术更多是“模拟”。进入传媒艺术时代,艺术逐渐走向非实物化的模拟甚至虚拟传播。模拟与模仿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却大不相同。一个“拟”字,便表征着艺术不仅通过创作再现现实世界,更通过传播建构现实世界、创造新的“现实世界”。而等到传媒艺术的数字虚拟技术时代来临,我们在思考艺术问题时,究竟哪个世界“在先”,哪个世界“在后”,也变得值得争论起来。
与传统艺术不同,传媒艺术已不再仅表现世界的一个场景定格,或是只是即时展现即时反馈,而是走向了至少是一段时间内 (比如一部电影的时间)“连续不断”地模拟、虚拟现实世界的样子。现实世界也是以这种“连续不断”的时间线的状态存在的,所以这种对现实世界类似性的追求也就更加逼真。这种模拟/虚拟还通过大众传播而最大限度地影响无限多的艺术接受者。传媒艺术通过对日常生活经验世界的不断复制传播,不断让接受者不自觉地笃定:“仿真世界”便是现实世界;并让艺术接受者习以为常地依据“仿真世界”去判断与思考[1]。
况且我们对于“真”的判定,在传统艺术和传媒艺术那里也不尽相同。
相对而言,传统艺术之“真”更多地呈现了生活之真与艺术之真的两隔。创作者与接受者对艺术之真与生活之真即便有融合的理悟与体验,也与个人的艺术体悟能力有关,即少数人能达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式的生活场见闻与艺术场体验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物我两忘。
而传媒艺术对生活与艺术两隔的模糊,从客观技术的层面上已经达成了,这甚至使接受者在艺术接受过程中大可不必动用太多主观元素。传统艺术或许仅带给我们人类自然能力可触及的真实,而当下的传媒艺术因为将“真”深度融入日常生活,而锻炼了我们对“真”的接触频度和认知广度,这也是对人类艺术创造与接受能力的全新锻炼,这种锻炼是传统艺术无法提供的。
(三)关于“真”的一些补充思考
“仿真”已经试图对人和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大规模、连续性、包裹式的“仿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是建立在极度张扬“真”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视觉文化。在鲍德里亚的“仿真”世界里,“真”的概念本身已经被消解,这彻底颠覆了近代哲学的“主—客体”思维模式,对近代哲学的追寻也是一次反驳。
思维如何通过表征而达到“真”的目的这一形而上学的问题,是整个近代哲学思考的命题。笛卡尔的二元论提出了身、心分离的问题,之后欧洲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争论着如何看待世界之“真”这一“表征”问题:笛卡尔将世界之“真”寄希望于“我思”,洛克诉诸于人类的感觉和经验,休谟走向不可知论,而康德则提出一个折衷主义的方式——先天综合判断,将认识的表征或表象问题与形而上学对绝对真理的追求问题割裂开来,重新陷入二元论的套路。黑格尔则力图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综合表征与真理问题的割裂,最终达到表征或表象与真理的完美统一。到了20世纪,分析哲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考仍然离不开表征问题。对近代哲学的表征问题构成真正挑战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哲学不再关心认识问题,真理也不再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符合问题,而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则彻底地摧毁了近代真理这座大厦的根基,消解了传统哲学的表征问题。只是与德里达等其他哲学家不同,鲍德里亚是从现代技术尤其是电子媒体开始了其对传统表征问题的追问和发难[15]。可见,无论对于“认识论转向”时代的经验论美学、理性论美学、德国古典美学形态和派别,还是“语言论转向”时代的诸多美学流派,关于“真”的命题的思辨都是一个相当核心的问题。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仿真”的摹仿本身便是一个对象化过程,它是“使对象的对象化”,通过对象认识自身,通过对象化形成反观,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思维。
此外,这里尚需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思考“仿真”之时,不仅要关注“外部真实”,更要关注“内在真实”和“哲理真实”。也即,不仅关注传媒艺术“真实”记录的社会功用和美学特征,还要“开掘当事人的心理情态、精神世界,寻找人物的内在动机”,并且“在对个别事件和人物心理的深刻的情感体验中,渗透进艺术家独特的对于世界、人生的哲理思考,从而超越个别事件、人物的局限,提出某种具有人类普遍性意味的命题”[16]。
第二,自柏拉图以来,艺术就被认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一个可以让人们驰骋想象的虚拟领域。如果说今天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今天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成了艺术作品[17]。传媒艺术“仿真”的美学特征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参与这种模糊艺术与现实之间边界的进程,推助着当下尚存边界争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达成。
四、传媒艺术与传统艺术在“仿真”问题上的区别
传媒艺术与传统艺术在事关“真”“仿真”等艺术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不少区别,本文仅以两个相对典型的思考框架,对本文所及问题进行进一步说明。“传媒艺术”与“传统艺术”只有一字之差,但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在面朝二者时却有显著的艺术认知和美学感受的差异。
(一)传统艺术之“意”与传媒艺术之“形”
中国传统艺术是重“意”的艺术,艺术作品大多不在于多么相像地描绘了物质世界,而在于艺术家笔锋流转间、宽袍大袖里、刀火石凿中、墨印吞吐下情感的抒发、意念的表达、个性的流淌、价值的流露、风雅的吐露。
虽然对形神合一的“意境”之追求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主观表达的不彻底性,但在这种艺术表达中,艺术家召唤着接受者进行积极的审美想象,在虚实相生中不断体悟着作品。“司空图所说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只有通过欣赏才能捕捉到,正所谓艺术‘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18]
再来看西方艺术的情况,虽然“摹仿说”影响了千年的西方艺术创作观念、实践与评价话语,但相对于当下的传媒艺术而言,西方艺术也曾不断地、执着地追求“神似”。“西方文艺理论虽然是‘再现’说雄踞了古典艺术时代,但是人们对艺术的欣赏仍然在于形式的创造性。不同的绘画流派、诗歌流派、小说流派,卓有成就的作家或艺术家,都是体现为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形式和方法。黑格尔认为艺术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但也重视艺术形式创造的因素。”[19]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曾提及:“艺术的这种形式的观念性特别引人入胜的并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心灵创造的快慰。……一种使人感到快乐的表现必须显得是由自然产生的,而同时却又像是心灵的产品……这种对象之所以使我们欢喜,不是因为它很自然,而是因为它制作得很自然。”[20]
而随着人类艺术不断涌进,传媒艺术终究已经普遍性地影响到人类生活,并且让当下的现代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于是在声与画的摹仿里,很大程度上说,人们逐渐被“仿真”氛围培养得多只会用“像”与“不像”物质世界里的人、事、物来评判传媒艺术作品,甚至评判所有艺术形式作品。场景像不像,人物像不像,情节像不像,甚至气氛像不像……对艺术作品的“形似”审美期待愈加成为人们在审美感知过程中下意识的反应。
像与不像固然是传统意义上审美感知的重要维度,传媒艺术尚没有发展到反置传统艺术的程度。但我们在肯定传媒艺术存在的同时,绝不能忽略另一个被我们千年敬畏的维度:审美感知的魅力还在于对未知结构的探寻,对艺术家“意”层的揣摩,在虚实相生中体会艺术作品背后的余味,是一条能让人瞬间抵达精神高度的重要通道。
(二)传统艺术的距离存在与传媒艺术的距离消解
在传媒艺术的声画变幻不羁中,接受者被完全卷入其中,总在期待着下一个画面、声音、人物、故事,就此全身心地将自己置于传媒艺术的“仿真”里,逐渐不给艺术欣赏“心灵距离”的介入以缝隙,因为艺术接受者参与欣赏的不再仅有大脑与精神,还有全身心的调动,包括外在物理、内在生理层面的调动[1]。
艺术作品不再将接受者推出到一定的审美心理距离之外,而是“图像把感觉粉碎成连续的片段,粉碎成刺激,对此只能用是与否来即时回答——反应被最大限度地缩短了。电影不再允许你们对它发问,它直接对你们发问。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现代传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求一种更大的即时参与,一种不断的回答,一种完全的塑性”,并且“观众参与了一种现实的创造……电视图像迫使我们每时每刻都以一种痉挛的、深深运动的、触觉的感官参与来填补内容上的空白”[21]。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文学文本阅读与传媒艺术“仿真”呈现的区别中便可有所体悟。文学文本阅读的过程是一个内视的过程,接受者将文字经过人内传播,内化地辨别、组织、整理,最终在内心呈现出视觉图景。相对于传媒艺术的直观呈现而言,文学文本阅读的内视过程是将他者甚至文本本身与创作它的艺术家推出到一定审美心理距离之外的内心体悟。而传媒艺术对视觉图景的直接呈现,不需接受者脱离这个被电子/比特不断呈现的景观,而走向内心视觉那另一套“观看”系统。接受者只需粘黏在影视作品的光影进程中便会“看”得最为真切,而不是将作品推到一定距离之外去戒备着、警醒着观看。
另外,传媒艺术的部分样态,其欣赏场所具有客厅化、生活化的特点,再加上观赏时很多时候不需要专业知识的深度参与,后现代氛围里对符号解释有极大的开放性,技术发展也存在使主客之间的关系不断瓦解的可能等都加剧着这种“距离消解”。
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区分传媒艺术与文学的接受特征,并非鼓吹文学终结论,或者刻意将传媒艺术与文学对立。恰恰相反,“内在视像是文学与传媒艺术相通的基本要素。文学之所以融通于传媒艺术,或者说传媒艺术需要倚重于文学的,首在于文学的内在视像”;不过,“我们可以对美学的本质主义进行质疑甚至解构,但是,不能将审美降低到仅仅是表层直观的拼贴或快感的充斥。审美当然要给人以表象的愉悦,而同时更是情感的牵动与感荡。”[22]如果我们的创作仅限于置接受者于“仿真”的表层易懂中,而不协助艺术接受者去追求精神高度的激荡,那么传媒艺术作为“艺术”样式与“美学”维度而存在的合理性,便终将被质疑。
五、对传媒艺术在“仿真”问题上的文化反思
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固有的物质形态和符号形式的变化与更迭,规定着信息被塑成新的形式进行传播,这往往会深刻地影响受众的感觉过程、认知方式、心理体验与行为取向,甚至可能引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组织方式变化。电影、电视、新媒体时代与传统的纸质媒介时代相比,人的感觉、认知、心理与行为方式变化很大[23]。“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因此而产生的思想、情感、时间、空间、政治、社会、抽象和内容上的偏向就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就具有不同的认识论偏向。”[24]媒介环境学给了我们一种思考媒介、人、文化的关系的维度。在传媒艺术的世界里,包括艺术信息在内的信息呈现方式已经发展变化了,这必然影响到受众在感觉过程、认知方式、心理体验与行为取向的变化,接受者文化认知、文化行为、文化生态和集体性格的变化更是题中之义。
鲍德里亚的“仿真”观涤荡出传媒艺术重要的美学特征,但传媒艺术“仿真”的美学特征也有其文化困境。传媒艺术既是塑成大众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大众文化传达的重要手段。我们需要在大众文化的批判视野中,审视传媒艺术“仿真”美学特征的背后对接受者的审美感知有哪些负面影响。批判是为了清醒,而不是为了扼杀,批判的话语背后是对传媒艺术的深深期待。
本文的文化批判更多是从大众文化角度出发的。本文认同的大众文化的三个基本框定维度是:(1)大众文化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尤其是一种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电子、数字媒介)为手段和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文化形态;(2)大众文化是社会的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3)大众文化认同审美的感性愉悦,它不是神圣的而是一种日常的审美文化[25]。而这些特征几乎全部符合传媒艺术的特质,所以以大众文化为切口来观照、反思传媒艺术,也便有了必要性[26]。
(一)躲避与庸常
我们需要非常遗憾地指出,传媒艺术日复一日地被生产出来,它的“仿真”特征在当下愈加“仿”出了一个琐碎、低俗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接受者在时光消耗中变得庸常,这个世界可供人们躲入其中。
在文化工业标准化与大众传媒大众化的要求下,传媒艺术必然会放低精神水准,以适应更多的个体接受者。而当下遭受物化与异化的个体,物质生活可能日渐丰富,但精神空虚。他们对现实不满,却又没有话语权和支配力,便开始寻找人类最广泛的普遍兴趣,也就是最原始、最本能的兴趣来麻醉自己如猎奇心理、求异心理、求快心理等。
这种社会氛围与后现代的种种消解趋向结合,把多数的人生归为低俗与平庸,本该用来深入思考与观察的时间,也被大众文化产品所占据。“电视一方面剥夺了人们阅读荷马、聆听贝多芬的时间,一方面又以大量浅薄、庸俗、无聊的货色,充塞人们的精神世界。有人干脆把电视节目称为‘美味垃圾’,将电视机讥为‘笨蛋机’。……法兰克福学派早就指出,貌似轻松愉悦的大众文化其实乃是异化劳动的延伸,因为它同样以机械性的节奏(如流行音乐)和标准化的模式(如畅销书、系列剧)榨取人的生命,耗费人的时光,窒息人的个性……电视之平庸还不在其电视节目内容,而在于它的强大诱惑力形成常人难以突破的屏障,从而隔绝了人对崇高与神圣的追求,对自然和人生的体悟。”[27]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鲁道夫·爱因汉姆也提醒到:“我们一方面使心目中世界的形象远比过去完整和准确,而另一方面却又限制了语言和文字的活动领域,从而也限制了思想的活动领域。我们所掌握的直接经验的工具越完备,我们就越容易陷入一种危险的错觉,即以为看到就等于知道和理解。”“到了只要用手一指就能沟通心灵的时候,嘴就变得沉默起来,写字的手会停止不动,而心智就会萎缩。”[28]
如今表象比深刻更容易被普遍接受,速度比精度更容易得到赞许,人变得知道得越来越多,而理解得越来越少,直至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丧失了反驳社会的能力。马尔库塞在1968年出版的《单面人》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文化工业让人沉浸在商品拜物教里,沉浸在文化工业生产出的程式化的消费产品中,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忘却了自己真正的自由需要,从而丧失了对现状的判断力、批判力,丧失了人的否定性、超越性,逐渐成为了单一维度人,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29](P111-182)。“电视机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特洛伊木马,它能钻进一般人的大脑和心灵,从内部瓦解他……电视将成为麻醉剂,这一合乎逻辑的趋势将把人变成自己的奴隶。”[30]人被庸常化的程度可见一斑。
我们还可以借助英国学者约翰·菲斯克的“躲避式快感”理论来理解传媒艺术“仿真”特征对接受者所带来的影响。“躲避式快感”是指观众在看电视时,能躲避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和现实,这些现实多为不快经历,这些地位也多为卑微低下。沉浸在“仿真”的世界中,可以暂时让人忘记不快与卑微,自觉不自觉地躲避在快感里,接受大众文化在闲暇时间里对人的异化。虽然菲斯克最初的阐释有为大众文化辩护的成分,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快感还是躲避都只是强压之下的被动应对策略,一味追求这种快感和躲避,只能使个体在时光消耗中变得更为庸常。
(二)均一化和去个性化
借助大众传媒手段,传媒艺术所仿之“真”可以迅速蔓延,社会中大多数个体可能同时沉浸于同样的议题与事件、故事与人物、流行与时尚;这其实是在“均一化”个体,窒息个体个性。
如前所述,传媒艺术是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与表达,“文化工业”中的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便是标准化生产与传播,标准化常常意味着去个性化,在“普遍适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包裹下,在清一色的认同中,在重复的灌输中,人渐渐丧失自我。传媒艺术貌似“仿真”出一个充满时尚元素、流行气质的世界,貌似给人以个性与自由,实则这种个性是每个人都能够用金钱等大多数人都能拥有的手段装扮出来的,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接近性。
这种对个性的窒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实质是以“量”的齐整消解“质”的差异。这一过程是将人规格化的过程,并美其名曰这是建构了“平等”价值。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所谓的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人民下层所分享。”[29](P9)
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传媒艺术是可以通过金钱来“定制”的,即使当代优秀的艺术家也常常走脱不出被“定制”而非自主创造的阴影。在天生与商品化、市场化密切关联的大众文化中,再好的东西也必会随着泛滥而贬值。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稍稍将其往前推一步,那么从崇高到戏谑或许就在一步之遥。
陆扬、王毅的《大众文化与传媒》一书对消费者“各得其所”的虚幻也提出辩驳:“文化工业的过程是一种标准化的过程,其产品就像一切商品那样同出于一个模式。另一方面,这些产品又有一种似是而非的个性风格,仿佛每一种产品,因此也是每一个消费者,都是各得其所。结果很自然就是遮掩了文化工业的意识的标准化控制。这是说,文化产品标准化的程度越高,它似乎就越能见出个性。个性化的过程反过来反倒蒙住了标准化的过程。”[31]
况且在大众文化里,传媒艺术还愈多地呈现着香车豪宅、奢侈之旅、珠光宝气、贵族美食,接受者对这样的被仿造出来的“真实”世界接触多了,便会不顾自己实际情况地追求它们,让它们变成了被均一化了的个体的生活思维。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由于自身条件限制,他们所神往的这些生活方式不能实现,被大众文化、传媒艺术改造了的情感与追求便没有了落脚点,于是人们感到痛苦,感到绝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曾说:“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要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常惨淡的生活。”[32]
(三)迷恋真实和缺少批判
由于传媒艺术的“仿真”特征,视觉真实俨然代替了客观物质世界,这容易让人们只乐于、安于沉醉在声画表象的流变之中,迷恋于传媒艺术所仿的“真实”之中,皈依现行的、被摹仿的物质世界体系之内,渐失跳出体系进行宏大批判的意识,较少的将落脚点放在意义与总价值上,导致研究时缺少辨认历史的否定性,将注意力只限于客观现实。这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人们不能辨别本质领域,而对摹仿的“真实”崇拜,对现实服从。总之,正如费尔巴哈所言,现代社会“重影像而轻实在,重副本而轻原件,重表现而轻现实,重外表而轻本质”[33]。
“人类社会的历史似乎总是受制于两种基本的冲动:一是风风火火走向世界的物质性渴望,即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一是清清爽爽走向内心的精神性追寻,即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这两种冲动代表着两种基本的人生哲学或人生观:走向世界,故追求成功;走向内心,故期望超越。”[34]如果说在传媒艺术的培养里,当下人愈多地以“酒神精神”心态安守于传媒艺术所“仿真”出来的物质性世界,安守于对世界的物质性渴望,迷恋现世与事功,那么,我们对“日神精神”的呼唤声声需要便愈加急促。人类社会的发展永远都不会放弃对跳出现世、追寻精神、走向超越、考察本质的敬畏。
当代艺术家、艺术研究者不能大面积躲避在反思之外,固守在闭塞、幽暗的小圈子之中。而是应在保持艺术个性彰显精神的同时,观照发展变化了的艺术生态,趋利避害,方能融融创造,为历史所保留。
[1]刘俊.论传媒艺术的科技性——传媒艺术特征论之一[J].现代传播,2015,(1):93-100;刘俊.论传媒艺术的媒介性——传媒艺术特征论之二[J].现代传播,2015,(9):107-111;刘俊.论传媒艺术的大众参与性——传媒艺术特征论之三[J].现代传播,2016,(1):98-103.
[2]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J].现代传播,2014,(1):72-76.
[3]胡智锋.《传媒艺术学书系》总序 [J],现代传播,2017,(7):158-159.
[4]王一川.美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5.
[5]Mogens Jacobsen,Morten Sndergaard.Mapping the Domains of Media Art Practice:A Trans-disciplinary Enquiry into Collaborative Creative Processes[J].Technoetic Arts:A journal of Speculative Research,2010,8(1):77-84.
[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M].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7.
[7]陈旭光.试论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理论挑战[J],浙江社会科学,2003,(6):148.
[8][美]约翰·拉塞尔.现代艺术的意义[M].陈世怀,常宁生译.张俊焕校.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1-2.
[9][德]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A].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99.
[10][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M].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1-62.
[11]J.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M].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5-6.
[12]颜纯钧.影像:仿真时代的美学[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04.
[13][法]让·鲍德里亚.仿真与拟象[A].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330.
[14]Walter Lippmann.Public Opinion[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1.xi-34.
[15]孔明安.物·象征·“仿真”[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0-104.
[16]胡智锋.电视美的探寻[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174.
[17]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2.
[18]周来祥.文艺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07.
[19]张晶.传媒艺术的审美属性[J].现代传播,2009,(1):17-24.
[20][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10.
[21][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81.
[22]张晶,于隽.文学与传媒艺术[J].现代传播.2008,(2):1-7.
[23]胡智锋,刘俊.需求与选择:谈中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J].艺术教育,2012,(3):28.
[24]Lum,C.M.K.Introduction: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J].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0,8(1):2.
[25]王一川.美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78-179.
[26]刘俊.台湾电视民生消费新闻叙事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7]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29-336.
[28][德]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M].杨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160.
[29][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89.
[30][苏]鲍列夫.美学[M].乔修业,常谢枫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453.
[31]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52.
[32][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30-131.
[33][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53.
[34]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90-292.
【责任编辑:周琍】
Ultimate Reality:Core Aesthetical Features and Cultural Predicament of Media Art
LIU Ju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24)
Media arts mainly include photography,motion pictures,radio and television,new media,and also some conventional art forms modified by modern media.“Simulation” is the third grade of Baudrillard’s idea of“simulacrum”.It refers to a reality of imitation,showing important aesthetical features of media arts.Media arts’imitation of real symbol groups presents illusion making the physical world so that the audience cannot distinguish the reality of“simulation” and the actual,objective,primitive,and simple reality.As they routinely,continuously use the“real symbols” of moving images to substitute for“the reality itself”,the media arts with moving pictures as basic artistic elements demonstrate the aesthetical features which go to extreme to present“actual” aesthetical features,which become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media arts and conventional arts in aesthetical features.Meanwhile,there exist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a arts and conventional arts in“simulation”:conventional arts focus on“meaning” while media arts focus on“form”;distance exists in conventional arts while distance is dispelled in media arts.In these influences there must exist pop culture predicament behind“simulation”,for instance,audience is prone to become mediocre,homogenized,and thus ignore intrinsic analysis.
media art;aesthetical features;cultural predicament;“simulation”;cultural criticism
G 206.2
A
1000-260X(2017)05-0148-10
2017-07-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战略与策略研究”(14ZDA055);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传媒艺术研究的必要性论析”(CUC15A72);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媒介融合时代中国电视时政新闻发展创新研究”(GD1709)
刘俊,传媒艺术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学报《现代传播》责任编辑,主要从事传媒艺术、影视文化、新闻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