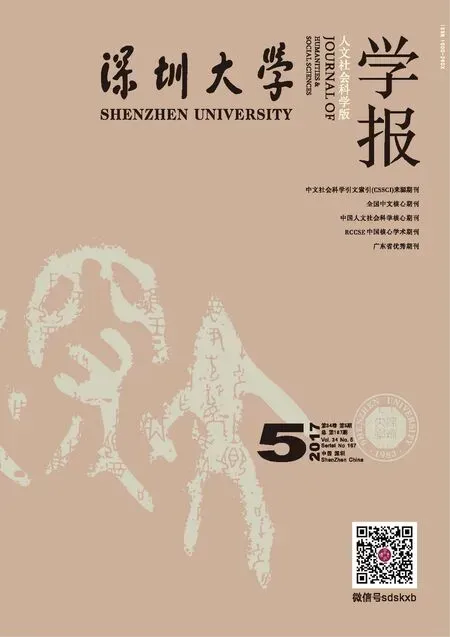从社会科学到社会工程:高校智库的定位策略、问题意识和未来走向
史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03)
从社会科学到社会工程:高校智库的定位策略、问题意识和未来走向
史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03)
中国高校智库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定位争议和问题意识模糊的问题,根源在于科学研究和政策实务相对立的传统观念。为此,中央设立了“国家高端智库”试点,从一系列文件中可以分析出决策层的考量与需求。而通过将“社会工程”与“社会科学”相区分,智库的一套选题框架可以展示其独特的问题意识。最后,“知行合一”的智库观念革新,既能引导学术研究产出更多可践行的思想,又克服了传统对策建议的短视。中国特色高校智库的未来走向,是扬弃美国政党政治下的智库模式,在思想市场上承担更多公共职责。
高校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权利距离;社会工程;智库定位策略;智库问题意识
智库是政治思潮和社会经济的产物和推动者。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到2015年启动的“国家高端智库”分批次试点,中国智库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智库的研究也成为显学。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的连续跨国别调查,在2016年全球7000多家智库的样本中,中国智库数量已经达到435家,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1]。
其中高校类智库的发展尤其迅猛。第一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名单中,有6家依托于综合性高校。各高校院所设立的应用型研究中心、研究院,也开始向智库升级整合。在思想市场上,高校智库如何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作为一门研究技艺,智库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又有何特点?
要向转型中的院校和学者发出正确的信号,前提是采取一种新的视角去定义智库:即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推动者。相比传统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智库工作者的身份更像是“社会工程师”,在高校这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孵化更好的思想,并促进思想向行动转化。
一、定位策略:权力距离下的比较优势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见》。2015年12月,中央召开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公布了第一批高端智库试点名单,并出台《试点工作方案》和《管理办法(试行)》。这一系列政策都强调智库要服务于决策。
但是“决策”需求到底有何特点?“国家高端智库”选拔与试点,就是决策层与潜在供给方的一次重要对话。正式文本中的要求,有助于指导高校结合自身禀赋特点,找到适合的方向定位。遗憾的是大部分院校并不在传统的智库联系通道中,相关试点工作方案的内容和来龙去脉,尚未被高校智库所熟悉。但高校在多学科和方法论上的优势难以替代,定位于中立、不走“背书型”或“鼓吹型”的道路,是高校智库的最优选择。
(一)中立客观是一种竞争策略
智库分类上,政府文件中对此有一个方便管理的界定。 但对于分析来说,“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2],即与决策权力的远近是一个更好的分析视角,以此可以界定三类不同的智库及其定位策略:权力距离最近的是“政府智库”。以第一批“国家高端智库”为例,既包括前10家党中央与国务院直属的机构,也包括由其衍生出的机构及部委下属的智库。权力距离最远的是“社会智库”,包括企业研究院(1家),研究型社会组织(2家),广义上还包括咨询公司等“思想产业”(idea industry)中的各种智力服务机构。处在中间的是高校智库,第一批名录中有6家,均衡分布于京沪、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
政府智库的优势在于和决策层沟通的管道顺畅,因为其自身就承接了大量政府的研究任务,具备很多独占性的信息。这方面高校智库无法比拟,但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因为目前相当多研究之所以委托给政府智库,考虑更多的是相互熟悉和按期交付的保障。
然而“中立性”却是下一步决策研究的强需求。部委分割的论证体系,是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一大问题。在传统交办式的研究体系下,决策层收到的报告中,大部分都有特定的部委或行业利益的痕迹。由部委及其关联机构主导的政策建议,在更高决策层的影响效力往往递减;而高校智库的核心优势就在于中立客观、尊重研究规律。坚持科学方法、不回避问题,这不仅是一种价值理性的要求,在工具理性上更是一种竞争策略。
在“国家高端智库”的试点方案中,释放了明确的信号。比如鼓励大学和科研院所智库在现有行政隶属关系中相对独立,内部治理可采用理事会制度。强调智库的非营利性属性,要求坚持客观公正立场,防止“谁出钱就替谁说话”[3]。而且允许每家试点单位成立智库发展基金,通过接受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筹措经费,保证研究的独立性与可持续性。
(二)协调短期和长期间的平衡
短期的对策研究,政府智库、社会智库就可以做;长期的研究是学术界的本职。对于需要把短期和长期协调起来考虑的问题,这样的智库设在高校内更加合适,以求提供严肃的洞见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弥合研究和政策之间的隔阂。
这一轮“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方向指引,也验证了这一判断:提倡服务决策、适度超前,要求智库制定中长期研究规划,确定相对稳定的领域,形成持续跟踪的长效机制[4]。这样的节奏和视角高校是熟悉的,而且还具备人才梯队和研究方法的优势,这也是试点评选中的重要标准。
举例而言,系列文件中明确鼓励“高端智库”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建设专业数据库、案例库和信息系统平台;鼓励深入开展实地调查和抽样,获取第一手数据;强调重视学术基础理论研究、政策模拟仿真和政策背景分析。这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和专业研究梯队,以及政策分析工具和跨学科平台的支持,目前大部分社会智库乃至政府智库难以顾及。
此外中国高校智库的机遇,还叠加了另一层背景:与成熟国家相比,因为社会(包括企业)智库尚弱,给高校智库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大量具体的经济、金融、行业研究在企业的专门智库里就做了,这对于微观决策是最有效率的,也是美国智库经常强调自己只做“战略性”研究的原因。在日本这一现象更加明显,很多企业集团设立的专门智库,其信息搜集能力和研究力量要超过官方机构。
最后在智库评价上,也要考虑短期和长期的平衡。智库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但并不意味着一味追求“内参”批示率。以领导批示评价高校智库的倾向,不仅不科学,而且会有扭曲效应。美国智库界有一句俗话,“任何一个智库建议,背后都有100位父母”。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也认为,“政府政策中多少意见来自于智库很难测定。有时与其说是智库影响政策,不如说是政府、党派想要通过智库(放风),使政策得到民众认可。”[5]
二、问题意识:避免正确而无用的分析
那么如何才能转化高校的研究优势,供给更多的思想产品?政策实务界常常批评部分高校智库脱离现实。高校智库应该更加强调“问题导向”、“决策导向”。第二、第三轮“国家高端智库”的遴选也呈现出一个倾向——优先发展“专业性智库”,这反映出对智库方法论的考虑:坚持研以致用,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6]。
但学术界要真正落实这类建议是有困难的,因为传统关于问题意识的“两分法”认为,学术研究关注“为什么”,政策建议关注“怎么办”。这一界定过分夸大了隔阂,很容易把智库研究简单归结为“递折子”的短期对策,也切断了“社会工程”反哺“社会科学”研究的联系。真正界定智库的不是声名,而是那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即关注那些做成的事,然后研究那些有意义的“为什么”[7],消除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隔阂。
(一)融合“学术”以及“智库”的选题框架
为了界定什么是够得上好的“问题”,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提出了一个框架,同样能很好阐述智库研究的“问题意识”。诺齐克的总结是,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及智库问题),包含五个组成部分[8]:
第一部分是目标,用于判断结果并认定所取得的进步。
第二部分是初始状态,即开始时的形势及可用资源。在学术研究中,通常指现有的研究文献;在智库研究中,则是现有的约束条件。
第三部分是可以带来改变的一系列活动。在学术研究中,指新数据、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在智库研究中,则聚焦于新视角、成功的亮点范例。
第四部分是限制性条件,用于识别不可行的活动。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中,都要明确结论外推时的限制。
第五部分是结果。好的学术研究必须有新的贡献:“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好的智库研究旨在催生行动:“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可行的活动,成功地将初始状态转化为满足既定目标的结果,且在此过程中没有违反限制性条件,那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une problématique)就得到了解决[9]。对照此标准,大量现有简单“递折子”的对策研究并非没有改进空间;而学术界的很多应用研究,同样可以转化为很好的智库研究。
这一框架,既适用于学术研究,也适用于智库选题。一个人在从事智库研究时,其身份更像是“社会工程师”。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最早提出了“渐进的社会工程师”[10]这一概念。他具备独特的问题意识,发掘能转化为行动的创新,警惕“正确但无用”的分析与“认知瘫痪”,深知结论外推的限制、避免提出“全面彻底解决”的轻率建议。
从这个视角出发,很多案例印证了从“社会科学”到“社会工程”的成功迁移。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再造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的智库评选中,唯一取得“A”的改革[11],来源于一位单枪匹马的哈佛教授:史蒂夫·凯尔曼领导只有20多人“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巧妙地选取“公务信用卡结算便利化”作为创新突破,搭配“过往表现追踪”的约束机制,成功改造了整个联邦系统僵化低效的政府采购制度[12]。
类似的,从英国首相的“行为洞察团队”(Behavioral Insight Team)、内阁的“关注奏效的研究网络”(What Works Network)、到智库参与公共政策的“行为助推”(nudge)计划与“循证决策”,依照马亮等学者的判断,英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与一线政策实务,也已在政府体系各个层面开始融合[13]。
(二)关注“亮点”而非“困难”的社会工程
如果定义智库的产出是思想,那也应该是能够转化为行动的思想(actionable ideas)。只有可践行而不是“空对空”的思想,才可能在政府、业界继续孵化。对应于智库选题框架中的五大要素(“目标”、“初始状态”、“创新方法”、“限制”与“成果改变”),20 世纪90年代杰瑞·斯特因针对越南儿童营养不良的干预案例[14],可以对社会工程独特的问题意识有一个很好的拆解分析。
斯特因的目标是代表慈善组织援助越南的儿童,面对的现状是当时越南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二存在营养不良。限制条件是没有政府权力支持,没有多少资金预算,甚至他连越南语都不会说,而且只有6个月时间。
区别在于传统学术研究关注的是“困难”:普遍贫困、糟糕的公共卫生系统、缺乏干净的饮用水、低下的教育水平。而智库的不同之处在于寻找“亮点”:什么是有效果的做法?背后有什么规律?如何复制更多?斯特因收集了数据,控制了收入、教育水平等变量,发现即使最贫穷的村庄,也有一部分孩子的身高体重是正常的。他以此追踪人的行为:尽管村民都穷得只吃得起两顿饭,但成功的母亲们会分成四次喂;尽管一般认为小鱼小螃蟹是成人吃的,成功的母亲仍然会炖成汤给孩子;还会采集身边的地瓜叶,尽管被认为是用来喂牲口的“低级”食材,但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维生素。
智库还重视促成行动所需要的改革动力学:斯特因将烹饪导则设计成清晰简明的指南,给村民树立了身边就能找到的榜样,并诉诸于母亲们的情感和希望;他建立了“烹饪示范小组”,让当地人感到这是他们自己想出的办法;当其他母亲们都行动起来之后,不这么做的母亲会感到压力,从而使当地文化在事实上得到了改变。
结果在6个月之后,65%的孩子获得了更好的喂养并且一直持续了下去[15]。相关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影响了越南265个村庄里的220万人。不同于泛泛的学术研究,智库的社会工程并没有进行“正确但是无用”(true but useless)的分析,进而陷在“认知瘫痪”中[16]。但对于现实改革,其投入之少而成效之大,远远超过其他研究机构的贡献,原因就在于观念范式的转换。
传统研究假设,如果问题是复杂而且相互交织的,那么一定得有“系统性的全面解决方案”,需要一本厚厚的报告,阐述政府、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但社会工程的范式认为,即使问题很大,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不一定要同样大,可行且短期见效的方案是有可能的。
传统对策建议中的套话是,既然问题是困难和长期的,就需要更高权力介入、增加更多投入、呼吁全面重视。但渐进的社会工程认为,只要遵循正确的问题意识并付诸行动,普通人也能够带来广泛、持久的变革。
传统研究往往假设,凡事要从“根源”上解决才叫解决。但是这一案例中,经济、社会、文化中那些深层次问题,一个都没有被彻底解决;但这并不妨碍上百万的孩子摆脱了营养不良,由此带来的国家人力资本提升,反而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帮助。
三、未来走向:超越“知”与“行”的隔阂
按照社会工程的视角,智库并没有固定模式,核心是面向需求的正确定位和一套独特的问题意识。倘若认为只有在首都政治中心、针对“宏大问题”做“战略研究”的才有资格叫做“智库”,其实是一种自我观念设限。
智库传统上强调信息和报送的渠道,既精通科学研究又了解政府运作的人才。这些固然都是优势,但其实只是伴随智库发展相辅相成的要素;唯一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对社会一线问题的紧密接触。隐藏于基层的那些行动“亮点”,才是智库研究的宝贵资源禀赋。在“一流学科”规划、高校改革、“有中国特色智库体系”建设中,地方性专业类高校只要定位清楚、选题得当,也能找到自己的机会。
(一)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高校的主要职责是教育和研究,智库建设对两者都可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现有的学科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总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公共政策: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口、教育、文化等领域,智库的实践都可以为学术研究反哺宝贵的洞见和实证证据;而在城市规划、环境治理、科技与工程制造领域,智库也亟需科学研究提供知识支持。
智库工作者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包括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统计计量的知识、对决策环节与政治规律的理解,以及开展实证研究的一系列技能。所以美国的教育实践中,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技艺”,并不从属于某一学科,而是作为单独学院,和法学院、医学院一样按照应用型体系培养人才[17]。同样,中国的高校智库,也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熟悉应用情景和问题意识,更好地走上各种岗位:从政府机关到企业的战略研究部,从中央的宏观政策研究到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等等。
(二)承担思想市场的公共责任
高校还需要承担其社会责任。在社交媒体时代,面对观念的“极化”(polarization)和破碎,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多的媒体乃至智库,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窄化”策略:与其面向公众服务,不如迎合一小部分受众投其所好,抓住这个群体的最大部分[18]。这可能是好的生意策略,但社会更多需要的是深思熟虑、更扎实的实证数据,以及不同群体的相互理解,高校智库更有可能承担这一职责。
好在同样因为技术的发展,好的思想只要能被识别出来,就可以迅速到达受众。理想的高校智库,既有中立地位,又有专业技能,对于思想市场可以扮演批判性的守护角色。决策者面对桌面上每天相互冲突的信息洪流,也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其信任的智库核查事实、选择立场。而且先前那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声誉调整滞后,会被媒体变革所击穿[19]:有质量的思想和有力的行动,当下就能被看见,新兴机构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三)避免被俘获为鼓吹型智库
从做课题、建中心到办智库,中国大学近年出现了一种思潮,将影响力缺乏归结为缺少宣传包装和改变形象的手段。加之受到“鼓吹性智库”(advocacy think tank)这一轮全球趋势的影响,带动了一轮智库上媒体、进榜单的热潮。这引起不少学者和智库管理者的担忧,刘元春的批评一阵见血:“如果只是简单搭平台,请人唱戏,那么一些高校智库或将沦为媒体中心和会务中心。”[20]
美国智库的发展也有过这么一个拐点:20世纪初进步主义推动政府改革,诞生了“布鲁金斯”、“卡内基”等老牌“研究型智库”;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兴起,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新兴智库以先验的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不再坚守客观性和中立性,转而注重影响力的提升[21]。现今美国智库越来越变成“压力政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即通过智库提供弹药,后面承接着游说机构和媒体公关,掩饰特定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对特定受众施加影响[21]。
这一趋势伴随着持续的争议,但是绝对不是高校智库的明智选择。高校不能只研究在新闻中出现的问题,还需要关注长期、困难的问题,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探索,拓宽人类的知识边界。在推进智库建设的过程中,中央的表述就有严格筛选的考虑:担心一哄而上,重复建设,无序发展,明确提出要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主要标准,不盲目追求社会知名度,避免出现急功近利、沽名钓誉、浮躁浮夸等风气。
未来思想市场上的竞争愈发激烈,智库当然需要拓展影响力的新途径。这方面可以与媒体合作,但并不意味着自己要变成“公关部”,成为聚光灯下的媒体明星。而且中国这轮“智库热”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新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内容供给能力的衰落,有学者愿意帮助撰写内容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但从研究资源分配来说,如果智库只是被俘获为撰稿的编辑部和鼓吹的管道,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四、小结:知行合一的智库观
利好因素在于,中国已经过了翻译介绍海外智库概念模式的阶段,对智库认识的理想化和神秘化倾向越来越少。而此前所赞誉美国智库的优势,中国也已具备或正在形成:决策层的重视支持、研究人员日趋成熟、业界资源的支持、公众参与的增强。202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体系,是一个可及的目标,高校需要找准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
对于智库工作者来说,做出严谨、可信的研究是核心能力,但还必须具备那种在简历上没法体现的品质。儒家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成己达人”的幕僚文化、特别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能够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注入本土特色。目前智库发展中“学术”和“实务”的隔阂,其实是西方二分法的传统。虽然有其分工合理性的因素,但中国古典哲学中并不这么思考问题。特别是“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认为不能转化为行动、带来改变的知识只是表面的理解:“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强调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健康反馈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而且并不把学术研究和行动实践看作对立的两件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22]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这样的观念还具有现代意义。互联网愈加发达,人与人交换想法越来越容易,基于连接的“虚拟智库”(virtual think tank)不再遥不可及[7];而新媒体平台打破了此前的话语权体系,让个体可以快速地建立起品牌和影响力,“一人智库”也不再是纯粹的调侃。但是要把思想付诸于行动,需要共享信念的一群人及面向变革的体系支撑[23],这才是实体智库存在并将延续下去的核心。
[1]McGann J G.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R].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7.
[2]Hofstede G,Hofstede G J,Minkov M.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M].New York:McGraw-Hill,2010.70.
[3]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工作方案[Z].2016.
[4]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Z].2016.
[5]李成.布鲁金斯学会今天如何思考[N].文汇报,2015-03-13.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4.
[7]Selee A.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11.
[8]Nozick R.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164.
[9]Grix J.The Foundations of Research[M].Palgrave Macmillan,2010.34.
[10]Popper K.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148.
[11]Donald K.Reinventing Government:A Fifth-Year Report Card[R].Madison USA:Brookings Institution,1998.
[12]Kelman S.Unleashing Change:A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Renewal in Government[M].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84.
[13]马亮.行为科学与循证治理:治国理政的创新之道[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6):11.
[14]Singhal A,Sternin J,Dura L.Combating Malnutrition:Positive Deviance Grows Roots in Vietnam in the Land of a Thousand Rice Fields[R].2009.
[15]Mackintosh U T,Marsh D R,Schroeder D G.Sustained Positive Deviant Child Care Practices and their Effects On Child Growth in Viet Nam[J].Food and Nutrition Bulletin,2002,23(4 suppl2):18.
[16]Heath C,Heath D.Switch:How to Change When Change is Hard[M].New York:Random House,2010.28.
[17]张康之,向玉琼.美国的智库建设与MPP教育[J].中国行政管理,2014,(9):109.
[18]Medvetz T.Think Tanks in America[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18.
[19]Lipton E,Williams B.How Think Tanks Amplify Corporate Influence[N].New York Times,2016-08-07.
[20]刘元春.智库不能变成高校的会务中心 [N].新华日报,2017-02-09.
[21]Carafano J J.Think Tanks Aren't Going Extinct.But They Have to Evolve.[N].The National Interest,2015-10-21.
[22]王阳明.传习录[M].钱明,吴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23]Bennett A.Are Think Tanks Obsolete?[N].Washington Post,2015-10-05.
【责任编辑:来小乔】
From Social Science to Social Engineering:Positioning,Problem Awareness,and Trend of Think Tanks in Universities
SHI Chen
(China Center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Beijing,100803)
The think tanks affiliated to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achieved great progress.In this process there arise problems of positioning controversy and vague problem awareness.The root of the problems is the traditional idea which contradicts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policies and practices.To solve the problems,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some pilot programs of“China top think tanks”.We can analyze policymakers’consideration and needs from a series of documents.Through separation of“social engineering” and“social science”,a set of topic selection framework of think tanks can demonstrate its unique problem awareness.Finally,the update idea of“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of the think tanks can not only guide academic researches to hatch more feasible thoughts,but also overcome the“short-sightedness” of conventional countermeasure strategies.Future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filiated to Chinese universities will surpass the think tanks in American party politics,and take more public obligations in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think tanks affiliated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ower distance;social engneering;positioning of think tanks;problem awareness of think tanks
C 932
A
1000-260X(2017)05-0010-06
2017-06-20
史晨,经济学博士,任职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曾任新华通讯社瞭望智库研究总监,主要从事智库实务工作与公共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