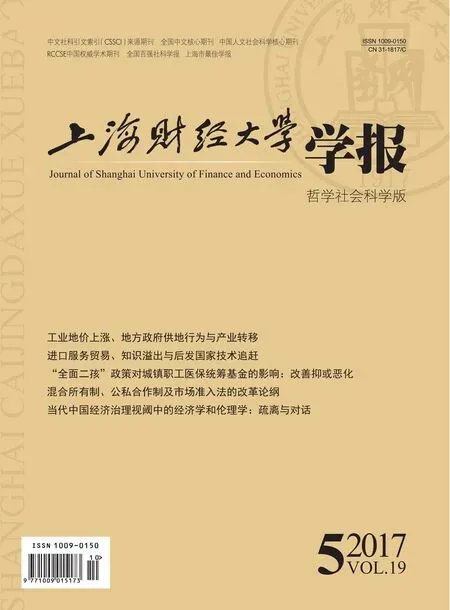混合所有制、公私合作制及市场准入法的改革论纲
刘大洪, 段宏磊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2.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混合所有制、公私合作制及市场准入法的改革论纲
刘大洪1, 段宏磊2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2.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改革是推动市场决定性作用得以发挥的“一体两翼”,二者分别着力于特殊行业和公共事业,分别落实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非公资本的投资和经营范围。当前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不能与改革需求相配套: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专注的特殊行业,存在对非公资本的显性准入壁垒;在公私合作制改革所聚焦的公共事业,非公资本则一直面临着隐形准入障碍。未来我国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体系应当对这一局面进行改革:一方面,以“规制放松”为主要形式对若干领域进行准入规制的卸载式改革,促使若干行业的准入壁垒降低、投资主体多元、市场竞争结构优化,竞争活力提高;另一方面,在拓展非公资本投资准入的同时,进行政府规制法律制度的结构性调整,即“规制再造”,保证在非公资本进入若干特殊领域时仍能使公共利益不受减损。
混合所有制;公私合作制;市场准入法;特殊行业;公共事业
一、前 言
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均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于近两年来颇受关注的重要改革政策,二者均涉及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合作投资或经营,但其内涵存在本质不同。混合所有制源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的重要部署。《决定》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国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事实上,从1993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改革方向,并将国企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时,公司治理结构对投资来源多元化的必然要求已然决定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向。①主要政策文本依据为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它明确提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反应现代企业制度精神的《公司法》也在随后的1993年12月底通过。混合所有制并非新提法,而是经典国企改革范式的延续,只不过核心关涉点发生了变化:得益于1993年以来的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形态已逐渐深入到我国市场经济竞争性行业的多数领域,②2010年的数据调研表明,即使是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概念外延严格限定为第一大或第二大股东必须为国有性质,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总量为950家的改制国有企业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总数也已经达到了735家,占样本总量的77.3%。参见张文魁:《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这些已高度实现混合所有制的大部分行业(以下简称“一般行业”)已不是本阶段改革的重点;此次改革核心实际上是国企改革的“深水区”——在意识形态习惯上长期保持国有资本控制局面的特殊行业,我国《反垄断法》第七条即将其界定为“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①对于这种界定所实际涵盖的具体范围,需要在法律文义解释的基础上,结合若干我国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充足的指导意见》时,国资委曾将其范围明确为至少包含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七个领域,这部分主要表现为传统上的自然垄断行业。参见许小年:《解析“七大行业”》,南方周末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1951,2017/5/2最后访问。另外,在2011年出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被明文纳入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垄断行业除前述七大领域外,尚包括邮政、铁路、公交、自来水、垃圾处理、有线电视、机车车辆制造等行业。参见戚聿东:《垄断行业改革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而对于“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则可根据我国相关的专营专卖立法与政策进行界定,如《烟草专卖法》、《食盐专营办法》等,这起码包含烟草、食盐、化肥、彩票等行业。但是,从近期披露的中央改革部署来看,盐业专营即将面临全面改革,待结束过渡期后,从2016年开始,中国将结束两千多年历史的食盐专营制度,届时国有资本在这个行业的一元化局面也将面临较大调整。参见吴婧:《政府不管“咸事”:2600年食盐专营谢幕》,腾讯财经网:http://finance.qq.com/a/20141201/002898.htm,2017/5/2最后访问。这类行业“基本还延续着行政命令控制体制进行资源的配置和管理,行业外的竞争力量无法进入行业内参与竞争……在一个缺乏充分竞争的封闭体制内必然导致利益集团通过寻租来维持垄断地位和阻碍市场机制的导入”②戚聿东:《垄断行业改革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与混合所有制着力于竞争性的行业不同,公私合作制(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起源于西方公共服务供给中引入私人部门积极参与的市场化改革运动,它适用的领域具有极强的公共性,我国官方政策文件使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一词,③存在类似表述的政策性文件有国发〔2014〕60号《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农经〔2015〕488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关于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的实施意见》,等等。它适用于“政府负有提供责任又适宜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项目”(以下简称“公共事业”)。④发改投资〔2014〕2724号《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将这些公共事业进行了如下明确列举:“燃气、供电、供水、供热、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设施,医疗、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项目,以及水利、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项目均可推行公私合作制模式。”依照合作模式的不同,有BOT(建设—运营—移交)、BOO(建设—拥有—运营)、TOT(转让—运营—移交)、ROT(改建—运营—移交)等类型。⑤参见财金〔2014〕113号《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
尽管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是我们近两年的重要经济体制改革内容,但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学界对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的研究由来有之。⑥中国较早对混合所有制展开专门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参见:张文魁:《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葛扬、潘薇薇:《发展民营经济,提升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运行质量》,《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较早对公私合作制展开专门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参见:湛中乐、刘书燃:《公私合作制协议中的法律问题辨析》,《法学》2007年第3期;卢护锋:《公私合作中政府责任的行政法考察》,《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8期。肖晓军、吕景春:《公私合作制在中国目前公用事业市场化中面临的问题——以特许经营制度为例》,《开发研究》2006年第5期。近两年来,伴随着政策和实践的重视,相关研究陡然增多。但两类研究的主题并没有明显的时代更迭:针对混合所有制的研究主要是以国有企业改革或民营资本发展等经济学研究为主题;而针对公私合作制的研究则主要是与特许经营权、行政审批权等公共管理学研究为主题。一方面,法学研究层面的著述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在已有的各学科研究中,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也通常未被纳入同一个框架或话题中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未得到重视。
本文即是在上述文献考察的基础上,结合近两年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发展的趋势所做出的研究,与过往研究相比,本文致力于达成如下创新:其一,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背景,打通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两大改革的内在关联性,进而在未来的制度规划层面做出更具有宏观要旨的整体设计;其二,探索出一个更有利于在法学层面领会和诠释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改革的基本范畴——市场准入法,进而一方面为两大改革奠定法学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切实提高经济法学研究的回应性和时代性。上文对两大改革内涵的分析清晰地表明,二者的内在关联不容忽视,它们均涉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改革,这意味着我国将在一系列市场经济的特殊行业与公共事业领域对非公资本开放准入资格,令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同一准入门槛的限制下同台竞争,获得“起点公平”。但是,我国目前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设计与两大改革的基本目标存在矛盾:在我国的若干特殊行业与公共事业中,准入规制设置的基本框架存在一定的资本歧视性观念,即偏好于国有资本,而对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则设置了不必要的较高准入壁垒。换言之,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的实现存在法律障碍,因此,我国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必须做出系统性改革,从而为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的稳步推进扫除制度壁垒,这即是本文欲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研究遵循如下分析进路:首先,要结合我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划,明确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改革的基本内涵、关系与意义。其次,要从市场准入法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析阻碍两大改革推行和发挥作用的制度性根源。本研究认为,在推行混合所有制的领域,存在着针对非公资本的显性准入壁垒;而在推行公私合作制的领域,则存在着针对非公资本的隐性准入歧视。最后,则要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改进框架,对我国的市场准入法进行基本架构上的改进,为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作制的推行扫除制度障碍。结合实践来看,本研究有利于推动我国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体系的改进和优化,进而间接推动我国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
二、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改革的关系及意义
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二者在称呼和内涵上都有相似之处,甚至有观点认为,公私合作制是从属于混合所有制的,将公私合作制视为“一种混合所有制的资源配置方式”,①陈婉玲:《公私合作制的源流、价值与政府责任》,《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笔者对此并不认同。从上文所述的基本概念界定来看,无论是《决定》中的若干语句,还是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一般认识,混合所有制均特指在投资上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合作,而不涉及其他;而公私合作制中的“公私合作”则意义更为广泛,它远超出投资的范畴,主要是指在经营方面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另外,在改革所涉及的领域问题上,混合所有制主要集中于竞争性领域,本轮的重点则为竞争性领域中的若干特殊行业,而公私合作制则主要针对公共事业。当然,二者所涉及的行业并非泾渭分明,在交通、能源等部分表现出自然垄断和公共服务色彩,但同时又具有推行市场竞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领域,则出现了竞争性特殊行业与公共事业的领域竞合,这便说明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两种改革部署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即使是从《决定》的文本上来看,二者的关联性也极强,其政策渊源均位于第二大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下设项目当中,目的均为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在国有资本和非公资本所共同构成的市场中,如何符合市场机制的规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妥善处理。一个长期难以改变的状态是,国有资本的投资和经营范围过大、所涉范围过宽,而非公资本却面临多处市场进入壁垒或隐形限制。整体规律是在竞争性领域的一般行业,非公资本尚且能实现进入自由;而在竞争性领域的特殊行业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事业,进入渠道则并不畅通,由此阻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在2008年左右的经济危机时期,国家更以政府主导并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的形式推动经济复苏,以至于加剧了前述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竞争环境的不均衡状态,一定程度扭曲了危机结束后的市场竞争结构。①应品广:《经济衰退时期的竞争政策:历史考察与制度选择》,罗培新、顾功耘主编《经济法前沿问题(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7页。危机过后,投资计划所产生的“国进民退”现象遭到来自经济学界的诸多批评,②对“国进民退”相关观点的争议和案例表现可参见钱凯:《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观点综述》,《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60期。而《决定》所部署的若干改革策略则致力于解决此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非有双重内涵,即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所谓深度即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官方语境中所称的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它表明对于市场竞争性问题,一切行政规制必须在以市场机制为前提下发挥作用,不仅一般行业应当推行市场机制,在若干被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行业,尽管其可能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属性,市场也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③自然垄断在传统上构成排斥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理由,但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整体上均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而通常是某一行业可以实现竞争性业务与自然垄断业务的剥离,对于前者并不需要寡头或独占经营,而有必要适度引入竞争。另外,伴随着市场需求和科技进步的变化,自然垄断业务也是一个流变着的概念,整体规律是所涉领域不断缩小,具体的分析可参见刘大洪、谢琴:《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研究——从自然垄断行业是否为合理垄断的角度出发》,《法学论坛》2004年第4期。而广度指的则是市场的普遍性作用,即使是在以提供公共物品为目的的若干公共事业领域,也并非必然交由国有资本垄断运行,而完全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④对市场决定性作用这两方面内涵的进一步解读可参见刘大洪、段宏磊:《谦抑性视野中经济法理论体系的重构》,《法商研究》2014年第6期。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改革的关系,实际上是在改革已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基本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推动市场决定性作用得以发挥的“一体两翼”:二者分别着力于特殊行业和公共事业,分别落实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尽最大程度地拓展非公资本的投资和经营范围,真正如《决定》所言,实现其与国有资本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三、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改革的市场准入法障碍
(一)市场准入法:基本逻辑与制度构成
市场准入是有关国家和政府准许公民和法人进入市场,从而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条件和程序规则的各种制度和规范的总称。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随着市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日益拓展和深化,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而规定与此相关的对市场准入制度的条件、标准、方式、程序和责任等的法律规定所形成的体系即为市场准入法。⑤刘大洪:《经济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01页。毫无疑问,市场准入法是政府规制市场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构成了规制法律制度的“脖颈”:通过赋予或禁止特定经营者对特定市场的进入,直接实现对经营行为最源头的规制,不符合准入规制要求的经营者索性被剥夺了经营资格。正因为如此,在对规制措施进行类型化的研究中,有学者得出了准入规制的刚性程度最高的结论。⑥有学者即认为,信息规制、标准规制和准入规制构成了规制的三种最基本样态,三种样态中政府干预市场自由的程度各不相同。信息规制只要求经营者披露特定事实而不限制其行为,其对市场自由程度的干预最轻;标准规制则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施加一定的目标、性能或规格上的标准,其对市场自由的干预居中;而准入规制则要求经营者必须获得事前审批或授权,否则被禁止从事特定领域的经营行为,属于最重的规制工具。参见Anthony I. Ogus. Regulation: Legal Form and Economic Theory,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4: 150-151。
市场准入法并非是一个被我国立法语境所认可的词汇,法律文本中并不见“市场准入”一词。在不同的部门法研究中,也经常以异质的学术词汇对此进行指代。商法上最常讨论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为“商事登记制度”,但严格来说,后者的外延小于前者,因为商事登记制度通常适用于一般竞争性行业,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①范健、王建文:《商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在形式审查之外通常并不附带具有实质规制色彩的准入审查。在规制体系较为深切的特殊行业乃至公共事业领域,由于市场竞争性有限,所需的在位经营者数量通常会受到限制,甚至会以特许经营的形式赋予某一经营者垄断地位,此时的市场准入则实际上是行政法上的行政审批行为,②严格来说,市场准入的概念外延小于行政审批,有代表性论述将中国行政审批主要做三种分类,即资源配置类、市场进入类和危害控制类,参见王克稳:《论行政审批的分类改革与替代性制度建设》,《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在三种类型各自的概念界定中,资源配置类审批指对国家所有或垄断的资源使用权或经营权予以出让,基本上相当于本文所述的公私合作制所着力的公共事业市场准入;而市场进入类审批则是对竞争性行业投资或经营行为的审批,基本上相当于本文所述的混合所有制所着力的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准入;而危害控制类审批则与行政主体的社会管理行为相关,通常与市场准入的概念外延无关。其对经营者附加了严格的实质审查。由此可见,市场准入法这一强劲的规制工具具有“双刃剑”效应,应当根据特定行业的具体情况,设定与之程度相当的准入规制方案,既不应当由于准入规制的过于松懈而造成不合格的经营者进入,引发市场失灵;更不应当设置过于刚性的准入规制措施,影响经营者的经营自由。
因此,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行业状况和准入规制的基本方式,我们可以对市场准入法的制度设计做出如下的类型化:其一,谦抑的准入规制。即对于大多数市场竞争程度高、市场失灵很少或没有的一般行业,市场准入法的制度设计应当保持谦抑,尽量不设计过多的准入壁垒,原则上仅以商事登记的方式做形式审查。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落实了这一原则。2013年新《公司法》已经取消了对于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这便是进一步减少乃至取消准入规制的体现。其二,适度的准入规制。即对于涉及公共利益或自然垄断,尤其是提供的产品具有一定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行业和公共事业,市场准入法不能缺位,此时应当设置必要的准入规制措施。这一方面能够防止在自然垄断的行业中由于过多的经营者进入而产生资源浪费或过度竞争,另一方面也能够设置对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经营行为的必要规制,防止不具有资格要求的经营者进入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其三,刚性的准入规制。即在必要时,国家基于产业政策、国家安全等特殊需要,会划定市场准入的“禁区”,除具有落实国家职能性质的行政型企业之外,原则上不允许民间资本准入。比如我国在彩票、烟草等行业进行的专营专卖制度、在铁路行业实行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独家经营的状态等,即实际上排斥了非公资本的进入。
(二)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的制度障碍:市场准入法的“傲慢与偏见”
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这种“一体两翼”式的改革,本质上是调整针对非公资本的准入规制体系。但是,对当前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体系的考察表明,它并不能与改革的实践需求相配套:整体来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专注的特殊行业,存在对非公资本的明确歧视性准入规制,若干立法明确要求对特殊行业必须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而公私合作制改革所聚焦的公共事业,则基于意识形态、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非公资本实际上也一直面临着进入障碍,这些障碍难以寻得实际制度依据的准入壁垒,却实足的长期存在。它们本应按照行业特点或市场规律的情况分别配置谦抑、适度或刚性的准入规制,而现行制度却是几乎统一匹配了刚性的准入规制。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的改革如果不能系统地破除这种“傲慢与偏见”,本阶段改革目标即有可能落空。
《反垄断法》第七条是特殊行业针对非公资本准入规制的典型立法。“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第七条实际上以一种宣誓性的语言建立了对特殊行业进行国家干预的框架性条款,①张杰斌:《特定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七条评析》,《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这一框架几乎囊括规制法律制度的所有基本手段,如准入规制(“专营专卖”)、价格和标准规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反垄断规制(“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等等。通过这种立法,准入规制措施实现了与反垄断规制的制度对接,从而构成了一个针对特殊行业的周延的规制法律体系。但是,具有资本歧视性的准入规制逻辑却在这条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体现,甚至索性明确了在特殊行业中国有经济“控制地位”的合法性,即以刚性准入规制的形式对特殊行业在位经营者的垄断地位进行了明确。《反垄断法》在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立法体系中通常被认为具有基本法的地位,即“经济宪法”,其在效力位阶上要高于其他规制立法,因此,第七条的规定将构成市场准入法的一个原则性条款,国有资本在这些行业的控制地位变成了难以撼动的高度准入壁垒。非公资本欲在这种准入规制框架下进入特殊行业,实现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目标,则根本不可能。
除了《反垄断法》之外,在各特殊行业的单行立法中,对非公资本的这种歧视性准入规制也随处可见。以民航业为例,②此处以民航业为例所做的分析援引了如下研究成果,段宏磊:《民航业反垄断执法的管制障碍及改革》,《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直至2002年,民航局才通过《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对外国资本开放民航业投资,而对民营资本开放投资则直到2005年出台的《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试行)》才正式开启。尽管如此,这两个文件所开放的投资范围都极为有限,外国资本对民航业的投资中,对于机场、运输等主体性民航业务,都必须由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③参见《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第六条。对民营资本的投资限制更是通过单列“投资准入”一章对民航业各个领域进行诸项规定。④参见《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试行)》第五条至第十一条。在这种有限的投资夹缝中,作为主管机关的民航局还时常会做出对国有资本的庇护性政策或对非公资本的排斥性规范,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在2007年整体民航国有企业经济形势窘迫的背景下,民航局索性于7月出台通知,暂停2010年前受理新设立航空公司的申请,⑤参见民航发〔2007〕101号《民航总局关于调控航班总量、航空运输市场准入和运力增长的通知》。为国有企业减少潜在竞争的压力。另外,对民用航空市场来说,航班时刻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紧俏资源,⑥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国外对于航空公司的并购,通常会附加限制性条件,要求其转让部分航班时刻,欧盟在2013年批准星空联盟整合部分跨大西洋航线时,即附加了此类条件。参见: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renders legally binding commitments from Star alliance members Air Canada, United and Lufthansa on transatlantic air transport passenger market.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3-456_en.htm?locale=en,2014-07-04,2017/5/2最后访问。非公资本即使在获准进入民航业市场的情况下,如果难以获得重要航班时刻资源,则相当于在若干核心竞争性市场上面临新的准入壁垒,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当前民营资本经营民航业的捉襟见肘之处。⑦相关报道可参见佚名:《航班时刻受限,民营航空被逼退居》,同程旅游网:http://www.ly.com/airinfoshow_7655.html,2017/5/2最后访问。
与特殊行业存在的对非公资本的显性准入壁垒不同,公共事业建设当中对公私合作制的推进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制度障碍。恰恰相反,公私合作制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度被视为推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有益手段,尤其是从1995年到2005年之间,堪称我国公私合作制的“黄金十年”,若干与BOT、特许经营等有关的公私合作制政策意见陆续出台,我国的公共事业建设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①这十年间较为重要的与公私合作制直接有关的政策文件包括:(1)1995年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以BOT方式吸引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2)199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进行项目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3)1995年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4)1997年国家计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进行项目融资管理暂行办法》;(5)2002年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6)2004年建设部《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而在2005年国发〔2005〕3号《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其所使用的语境力度之大、改革决心之坚定,已堪称前所未有。该文件明确指出要“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且所涉范围十分广泛,既涉及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特殊行业,明确提出允许非公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金融服务业等;更直接涉及公私合作制的公共事业领域,如文件中提到的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领域和社会事业领域等。但是,整体来说,我国公私合作制一直没能得到真正的长期发展,总被一些隐性的羁绊所影响。一方面,基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惯性,经济政策倾向于对非公资本进入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领域保持着较高警惕,它容易引起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难以获得或成本提高的顾虑。但实际上,这完全可以通过优化公私合作制协议中的义务条款或项目经营过程中的治理手段来解决,比如西方国家中的黄金股(golden shares)制度即确保了公益性目标和法令约束在私有化企业中的实现,②[美]热拉尔• 罗兰:《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这被称为国有资本“特殊权利(special rights)”。③特殊权利(special rights)指代西方国家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对部分控制权的保留,它往往通过政府在企业保留极少数乃至一股的形式来实现,但这些极少的国资股却被赋予了若干特权,拥有“黄金般的价值”,因此被称为“黄金股”。详情可参见张立省:《黄金股研究综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93页。在现实公共事业建设具有对非公资本的融资需求,但政策惯性上又排斥公私合作制的情况下,对推进公私合作制的现实制度供给易于出现徘徊不定的状态,一旦面临来自舆论或经济发展方面的风险(尽管这些风险可能根本与公私合作制不直接相关),公私合作制便容易草率中止。其典型地体现在2005年至2014年公私合作制重启的这个阶段内,我国已经罕见出现促进与公私合作制有关的政策文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以四万亿元扩张性的投资计划应对经济下滑风险,而这一投资结构中有超过一半被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对非公资本的投资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④王曦、陆荣:《危机下四万亿投资计划的短期作用与长期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公私合作制因此而遭受挫折。另一方面,公私合作制协议所特有的“行政合同”性质,使政府在这当中不仅是一个合同关系人的身份,更增加了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和协议的监管者等多重身份。⑤湛中乐、刘书燃:《公私合作制协议中的法律问题辨析》,《法学》2007年第3期。这种相对非公资本主体在信息获取和整体权力上的优势,使后者易于产生对政府违约风险的恐惧,再加上前述政策制定的循环往复性,非公资本在欲参与公私合作制时,容易产生无法满足信赖利益保护要求的整体评估,从而难以产生缔约激励。这一分析与近段时间来公私合作制在我国若干地区遇冷,难以获得非公资本充分加入的新闻报道是相符的。⑥一个典型报道可参见颜芳:《热推公私合作制项目遇冷,政府还需多补课》,新华报业网:http://news.xhby.net/system/2015/05/04/024589768.shtml,2017/5/2最后访问。
综上所述,在特殊行业实现混合所有制以及公共事业建设中推进公私合作制的本阶段改革目标,尚处于不恰当的市场准入法设计所造成的羁绊当中,这一制度困境不打破,改革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
四、市场准入法的改革:规制放松与再造
(一)理论基础:拓展市场的广度与深度
在发挥市场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整体规划下,对市场准入法进行系统改革,既是当前推行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一体两翼”式改革的需要,又是拓展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切合我国整体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中国目前所处的整体经济状况其实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加强,再加上战后的社会创伤又呼吁一个强有力的干预型政府,这造成了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欧美国家政府规制的膨胀现象。其基本表现便是,尽管市场机制在一般性的竞争行业仍是基本发挥作用的,但在政府艰深的规制体系下,存在一批以准入壁垒极高、国有资本集中为特点的规制性行业,这类行业多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或公共物品属性,如交通、能源、城建等,其所涉领域与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与公私合作制改革辐射到的特殊行业和公共事业,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在规制体系影响下,彼时欧美国家的政府组织及其行为表现出呆板和臃肿的特点,①顾丽梅:《规制与放松规制——西方四国放松规制的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仅七十年代美国的联邦规制预算就增加了六倍,常设岗位增加了两倍;②Stephen Breyer: Regulation and Its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市场竞争性活力严重不足,规制在相应领域的普遍实施促进了其“自我积累”③卢颂华:《美国放松规制改革的发展与启示》,《行政论坛》2002年第3期。,在位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者权力扩张,并诱发寻租行为,财政赤字攀升,宏观经济方面则陷入了“滞涨”困境。
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的上述特点竟一一投射到当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我国目前恰好表现出特殊行业与公共事业的规制体系艰深、市场竞争活力不足,公共服务方面的政府责任导致财政吃紧,宏观经济也面临一定压力。而欧美国家为了应对这一系列窘境所从事的改革措施,如调整国有经济的投资结构,部分实施私有化改革等,也与中国当前所实施的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作制改革相似。而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体系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欧美国家这一系列改革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一方面,以“规制放松”为主要形式对若干领域进行准入规制的“卸载式改革”,④卢颂华:《美国放松规制改革的发展与启示》,《行政论坛》2002年第3期。严格来说,欧美国家放松规制运动并不仅局限于准入规制,而是辐射了政府规制法律制度体系内的所有经济性规制,但其整体效果显然以准入规制的放松最为首当其冲,也最为典型。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始开展的放松规制运动,有些论述直接将其描述为“私有化”的过程,即逐渐对非国有资本开放准入的一次改革运动,参见[美]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1页。从而促使若干行业的准入壁垒降低、投资主体多元、市场竞争结构优化,竞争活力得到明显提高。⑤衡量这些行业的一个有用指标是OECD规制指数,即以准入规制和其他规制的若干方面作为指标进行测度,从而衡量出特定行业的具体规制程度,一般来说,指数越高,对非公资本的准入壁垒通常越大。以此为标准进行衡量,欧美国家放松规制运动卓有成效,以英国、美国为例,二者在航空、电信、电力、天然气、邮政、铁路、公路七大受规制行业1975年的指数分别为4.8和3.7,到2003年已分别降低到1.0和1.4。参见戚聿东:《中国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模式与路径》,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468-480、495页。另一方面,在拓展非公资本投资准入的同时,进行政府规制法律制度的结构性调整,即“规制再造”,保证在非公资本进入若干特殊领域时仍能使公共利益不受减损。因此,欧美国家在那一时期降低准入规制的同时,增强了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HSE规制,⑥HSE规制(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Regulation),即健康、安全与环境规制,在美国常被用来指代以社会公益性为目的的社会性规制的三大典型领域,参见文学国:《政府规制:理论、政策与案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第272-273页。并在开放准入壁垒的同时,在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领域进行国有资本的表决权(voting rights)或黄金股制度实现特权和法令约束,⑦参见[美]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以保证公共利益在非公资本参与时不受影响。
规制放松与规制再造,是协调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体系以迎合改革需求,不断地提高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的过程。基于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国当前进行的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作制改革也必须从事一场与之类似的法律制度改革运动,以回应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政策要求。
(二)规制放松:市场准入法去资本歧视性
规制放松是市场准入法改革的核心内容,其指导思想为在特殊竞争性行业和公共事业中去资本歧视性,原则上对国有资本和非公资本适用平等的准入资格要求,在这些领域破除国有资本的一元化局面。
对非公资本存在歧视性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体系,其本质上是以准入规制立法的形式实施了一种限制竞争行为,而在位的国有资本经营者则是其受益者。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的概念界定并不包含直接在立法层面对竞争的不正当限制;因此,这一与自由竞争秩序相悖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体系并无法直接援引《反垄断法》予以查处,恰恰相反,在《反垄断法》第七条未予修正的情况下,这一制度体系反而具有直接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市场准入法体系中的规制放松,就应当以修正第七条为首要任务,去除其中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正面确认,将该条还原为对相关行业政府规制权力的一般确认性规范。①包含准入规制在内的一切规制,均既有可能限制竞争,又有可能对竞争产生不正当的限制效果。因此,对第七条的修正并不致力于对特殊行业规制权力的废除,而是将其中性化,即仅对政府的规制权力予以确认,并去除可能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语词。作为政府规制体系的“龙头法”,《反垄断法》第七条的这一修正将对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体系产生重要的示范性作用,它将给各特殊行业和公共事业的单行市场准入立法树立去资本歧视性的范本。
首先,在竞争性特殊行业,要对显性的市场准入法律体系进行一次系统的清理和修正,对其中涉及的针对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歧视性法律规范进行修改甚至废除。这涉及庞大的法律规范群,包括各行业单行立法中的准入规制条款,还包括以法规、规章乃至规范性文件存在的市场准入制度,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当然,破除准入规制的资本歧视性并非意味着对国有资本和非公资本的准入规制应当完全一视同仁。而是应当区分准入规制在社会性规制体系和经济性规制体系中的不同作用,对于涉及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的社会性规制领域,对非国有资本施加一定限制是必要的,比如禁止其具有控股地位、要求投资的非国有资本必须履行公益性目标,等等;而对于涉及以促进竞争和实现效率为目标的经济性规制领域,则不应当对非公资本存在歧视。应当防止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幌子”之下,以准入规制的形式为维护国有资本垄断利益背书,而对于真正具有社会公益性需求的领域,对非公资本施加区别性的准入规制。比如在民航业中,对于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投资和运营即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属性,如果对这一领域开放外国资本控股性质的投资,则显然对我国国防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此时施加准入规制的限制就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民航运输业,则完全可以向非公资本开放准入,实现适度竞争的引入,从而保证民航业效益和作为乘客的消费者福利的提升。在具体操作上,由于具体个案中限制性准入规制的合理性并不是一个易于判断的问题,结合国外执法实践,可以考虑发挥反垄断执法机构“竞争倡导(competition advocacy)”的新型执法机制,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具有“立法优先咨询”和“规制竞争评估”的权力。②参见张占江:《竞争倡导研究》,《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对于涉及竞争问题的市场准入立法或政策的制订,需要事前咨询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意见,以判断是否会对市场竞争产生限制效果;而对于已然生效的准入规制法律制度,反垄断执法机构也会对其竞争效果做出评价,从而判断未来应予保留、修正还是废除。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即通过这种反垄断执法机构发挥作用的竞争评估,近年来大大减少了不正当准入壁垒等政府限制竞争行为,促进了规制法律体系的优化。①参见张占江:《中国法律竞争评估制度的建构》,《法学》2015年第4期。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反垄断执法的攻坚时期,又恰处于混合所有制在特殊行业的推进时期,这种有益的国际经验极为值得借鉴,它会为我国特殊行业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去除资本歧视性发挥“助推器”的作用。
其次,在公共事业领域,要对作为“潜规则”存在的隐性准入规制进行改革,这除了涉及法律制度的革新之外,更是社会观念和执政理念的重塑。其一,要通过出台高位阶的政策文本或国务院法规的形式,确保在推广公私合作制时的政府责任和对参与者信赖利益的保护,②理想地说,最为确保信赖利益保护的形式并不是高位阶的政策文本或国务院法规,而是人大层面的立法,它具有最为典型的规范性、确定性和严肃性。美国历史上的放松规制运动就极为重视改革法案出台的作用,比如美国铁路行业的放松准入便是通过1970年《国家铁路客运法案》、1973年《地区铁路改组法》、1976年《铁路复兴与规制改革法》、1980年《斯塔格斯铁路法》等改革法案的出台而循序渐进,参见王立平:《规制与放松规制:美国铁路体制改革的启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但是,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中国实践来看,对于这种改革过渡期内的规范调整,我国在习惯上并没有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层面立法进行的做法,而是更倾向于通过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进行。这便能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公私合作制的内在激励。2014年以来,我国在公私合作制政策文件上陡然增多,目前已有数十份对公私合作制所适用的领域、协议形式和相关产业政策进行指引,这表示整体情况是可喜的,决策层此轮改革表现出推行公私合作制的坚定信念。未来还可以考虑通过制定改革时间表的形式,对公私合作制适用领域和协议形式的扩展给出一个可预期的渐进方案,这一方面有利于确保民间资本的改革预期,打消其对政策循环往复和政府违约的顾虑;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处理过渡期的制度配套和利益交接问题。其二,要实现对政府规制机构的“再规制”,填补准入规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外空间,实现对任一行业或领域准入规制政策的规范化和透明化。隐性市场准入制度之所以存在,除了对参与者信赖利益保护不足使其积极性不够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共事业的各规制机构有在正式的政策文件和法律规范之外,设计非正式进入壁垒的权力,这便有可能构成对非公资本的排斥。因此,要通过对规制机构执法行为法治化的方式,限制其另设隐性进入壁垒的可能性,为非公资本参与公私合作制保驾护航。
(三)规制再造:以行为规制替代准入壁垒
徒规制放松不足以自行。为了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以开放非公资本准入解决相应领域中的竞争不足、财政压力等问题时,必须要跟进替代性的规制法律制度确保风险的可控性,实现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规制再造,这也正是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放松经济性规制的同时,增强了社会性规制的根本原因所在。具体来说,在非公资本由于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去资本歧视性而得以顺利进入相应领域的背景下,可能面临两种亟须规制的风险:其一为发生非公资本“私益”对“公益”的侵蚀,即特殊行业或公共事业领域中涉及的国计民生、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由于非公资本的进入而受到减损。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公私合作制的推进,非公资本过于以自身收益为目标,而造成基建普遍服务目的的丧失,或公共服务价格水平提高,等等。其二则恰好相反,即以“公益”为噱头侵蚀非公资本之“私益”,即非公资本仅在形式上进入相应领域,但仍然遭受公权力制约,无法实质享有经营决策权,在既得利益所造就的政策偏好之下,政府部门可能仅立足于以非公资本解决在提供公共服务或其他政府责任上的财政压力,而并无真正让非公资本参与经营并盈利的实质目的。两种风险均有可能产生,有必要以健全非公资本进入后的行为规制体系的方式,替代进入前的准入壁垒体系,从而充分保证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有效中和,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对于第一种风险,理想的做法是在降低准入规制之后,以优化投资和经营过程中的信息规制和标准规制的做法予以避免。比如要求在关涉普遍服务性、网络互联互通、公共服务等领域中,严格落实经营者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限制其盈利比率的价格管制制度,确保这些行业中的社会福祉在非公资本进入后不会受到减损。在美国国家放松规制运动的实践中,出于减少不正当规制的目的,日渐衍生出以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形式对规制立法进行预评估,在保证制度具有实足收益性时才会获准实施。①有关美国这一规制成本收益分析的实践演变可参见[美]W·基普·维斯库斯、小约瑟夫·E·哈林顿、约翰·M·弗农:《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第四版),陈甬军、覃福晓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4页。类似的逻辑也可以适用到非公资本经营者当中,比如在公私合作制的特许经营权授予过程中,除了对参与竞标的经营者予以基本的标准考察外,还应当要求其出具对未来一定时期内公共服务水平的评估,以确保未来公共物品的提供能稳中有升;另外,政府也应当在公私合作制达成前对此项协议未来财政的承受能力和取得收益予以预估,以确保此项公私合作制协议是“划算”的。事实上,2015年我国与公私合作制有关的政策文件已日渐展示这一倾向性,即要求以成本收益分析的形式确保公共利益在非公资本进入时不受减损。②最典型的莫过于财金〔2015〕21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其中第二条明确本指引的目的在于“识别、测算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公私合作制)项目的各项财政支出责任,科学评估项目实施对当前及今后年度财政支出的影响,为公私合作制项目财政管理提供依据。”除此之外,前述黄金股制度以及投资或经营协议中对非公资本的义务约束等,也均是防止私益侵蚀公益的有用手段。
相比第一种风险,第二种风险或许是在政府权力法治化程度尚较低的我国尤其需要防范的。随着政府经济能动性的提高,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某些地区通过改变交易规则或进行产权控制,对市场资源配置进行干预,这种“越俎代庖”般的不正当政府投资行为,③刘大洪、郑文丽:《政府权力市场化的经济法规制》,《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在非公资本获准进入的场合下,有可能进一步异化为对其经营自主权的直接侵犯。在上一轮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作制改革都曾陡然中止而损及参与者信赖利益保护的背景下,④公私合作制改革在2005年之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原因而临时中止,政府投资行为在危机中得以扩张,从而对非公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参见前述;而混合所有制亦曾出现过类似状况,其导火线为2004年的“郎顾之争”,彼时正处于以国有企业MBO的形式实现对国有经济投资结构的调整,但郎咸平对顾雏军借此侵吞国有资产的指责引发了决策层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视,在这之后,国企改革逐渐偃旗息鼓。如果本轮改革再忽视对参与者合法经营利益的保护,仅片面地以非公资本参与的形式解决政府财政危机,无疑将构成对公信力的践踏,后续将难以再行树立改革权威。对于此问题,应当剥离政府在实施混合所有制或公私合作制改革时的身份混同,实现“经营者”与“规制者”的分离。申言之,由于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作制中均涉及国有资本的参与经营,在规制执法中,规制者与被规制者均存在来自国有资本的天然联系,这便有可能造成执法偏离,有损非公资本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一定程度上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独立规制机构的经验,以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形式设立一个专司相关问题规制的机构,从而实现对直接操作混合所有制或公私合作制改革的行政机构⑤由于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作制均涉及多种行业或领域,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机构其实非常庞杂,但从宏观的主导机构来看,混合所有制主要涉及企业国有资产投资结构的调整问题,其牵头者应为国资委;而公私合作制多为公共事业领域,实际上多由各级财政部门予以牵头负责。的分离,保证有效的规制执法。除此之外,还有必要以健全司法审查机制的形式保证对非公资本参与者权益受损时的权益补救,比如鉴于政府在达成公私合作时的信息和权力优势,可以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再比如为了防止政府寻租行为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或相应行业公共利益的减损,可普遍性地推行公益诉讼制度,等等。
五、结 语
我国市场准入的理念和制度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伴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进程,逐步形成并发展的。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的市场准入及其制度,显然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①刘大洪:《经济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页。在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作制改革问题上,市场准入立法的这些系统性缺陷得到了整体性的暴露,若不进行这一法律体系的系统修正和变革,改革部署将面临着合法性的威胁和钳制,因此,以规制放松和规制再造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变迁,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真理往往蕴藏在这些老生常谈的话语中。从改革开放最初始起,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相比,特殊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便长期处于与改革步伐相异的垄断性空间当中,它在三十余年来总是游刃自如地与市场机制擦肩而过,由此构成了我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壁垒。而我国渐进式改革的“中国经验”,尽管屡遭挫折,却也总是执着地从一般行业的“浅水区”向特殊行业和公共事业的“深水区”进发。任何行业都不能构成法外空间,都应当在规范市场竞争的法律体系下实现公正和效益的整合。愿非公资本在这次改革中能真正获取与国有资本相等同的投资地位与资格,愿不同所有制来源、不同控股结构的企业能真正实现同台竞技,使经济生态焕发出多样性的溢彩。
[1]Ogus A I. Regulation:Legal form and economic theory [M]. Oxford:Hart Publishing,2004.
[2]Breyer S. Regulation and its reform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3]Sokol D D. Limiting Anti-Competit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that benefit special interests [J]. George Mason Law Review,2009,17(1):119-189.
[4]Gal M S,Faibish I. Six principles for limiting government-facilitated restraints on competition [J].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2007,44(1) :69-100.
[5]Cooper J C,Pautler P A,Zywicki T J.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etition advocacy at the FTC[J]. Antitrust Law Journal,2005,72(3):1091-1112.
[6]Johannsen K S. Regulatory independe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A survey of independent energy regulators in Eight European Countries[J]. Energy Research Programme and the Danish Research Training Council,2003,(2):156-162.
[7]Owen B M,Sun S,Zheng W T. Antitrust in China:The problem of incentive compatibility[J].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2005,1(1):123-148.
[8]Brooks S. The mixed ownership corporation as an instrument of public policy[J]. Comparative Politics,1987,19(2):173-191.
[9]Beladi H,Chao C C. Mixed ownership,unemployment,and welfare for a developing economy[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10(4):604-611.
Mixed Ownershi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nd the Reform of Market Access Law
Liu Dahong1, Duan Honglei2
( 1. School of Law,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Hubei Wuhan 430073,China;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ubei Wuhan 430070,China )
The reform of both mixed ownership system and public and private cooperative system are the “one body and two wings” which promote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The two focus on the special industries and public utilities respectively,carry out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market respectively,and expand the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cope of non-public capital. The current market access law system can not be matched with the demand for the reform:in the special industries on which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focuses,there are explicit access barriers to non-public capital;in the public utilities tha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reform focuses on,there are stealth access barriers to non-public capital all the time. In future,China’s market access law syste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form of this situation:on the one hand,the unloading reform of access regul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a number of areas mainly by deregulation,to promote the reduction in barriers to the access to several industries,diversified investment subjects,the optimization of market competition structure,and the increase in competition vitality;on the other hand,when expanding non-public capital investment access,it should make a structural adjustment to government regulation law system,namely regulation reconstruction,to ensure that after non-public capital enters into a number of special areas,the public interests still have no losses.
mixed ownershi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market access law;special industry;public utility
DF411
A
1009-0150(2017)05-0091-12
(责任编辑:海 林)
10.16538/j.cnki.jsufe.2017.05.008
2017-05-12
刘大洪(1963-),男,湖南武冈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段宏磊(1987-),男,山东泰安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