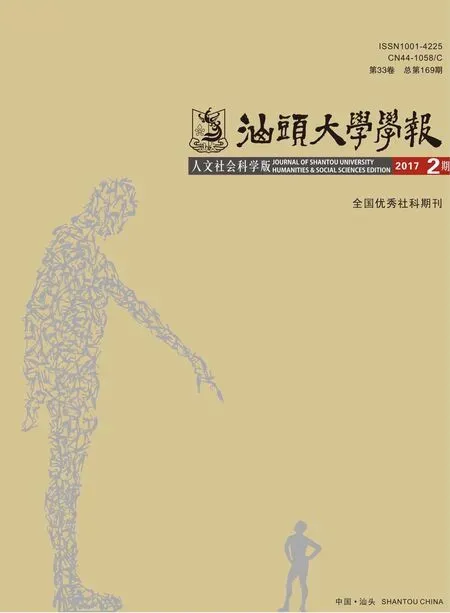论萧红晚期小说中的家园眷恋
贾颖妮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广东 广州 510521)
论萧红晚期小说中的家园眷恋
贾颖妮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广东 广州 510521)
萧红的晚期小说《后花园》《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是她阅尽人生沧桑后对曾深切体验过的世事的重新书写。这些作品一往情深地回望家园与童年,回归鲜活的个体生命体验,蕴含着对任性青春的反省和忏悔,显现了对女性解放的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疏离与反思。这种带有个人体温和气质的写作溢出左翼文学的宏大叙事洪流,提供了了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另一向度的心理切片,展现了历史巨变中新女性的抗争、迷茫和“疼痛”以及左翼文学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萧红;晚期小说;家园;左翼
一、家园:过滤的记忆与重构
萧红的创作,始于漂泊又终于漂泊。1932年离家出走身陷绝境的萧红,凭一封求救信因缘际会结识萧军,并成就一段文坛上英雄救美的旷世奇恋,随之与萧军走上漂泊之途亦踏上文学之路。1935年《生死场》的发表使萧红蜚声上海文坛。之后萧红的名字与抗战、左翼紧紧联系在一起。《生死场》既给萧红带来了声名,又客观上局限了对萧红的整体评价,以致多年后人们仍无视萧红创作的成长变化而简单地称之为抗战作家。创作于旅日时期的《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等作品摆脱了前期作品对阶级压迫、“革命”事件的生硬介入,开始有意识地回望故乡和童年,标示出萧红创作的转型。晚期萧红的创作虽有《马伯乐》《旷野的呼喊》《北中国》等与抗战相关的作品,但更能代表她晚期风格、也更多被评论者提及的是《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后花园》等满怀深情回忆故乡,并以之构筑自己精神家园的作品。对这些书写家园眷恋的晚期作品的评价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1945年,石怀池在《论萧红》一文中,依据萧红作品对政治意识形态要求呼应的强弱,把她的创作视为是一个“走下坡路”的历程,认为萧红的悲剧源自她自我改造斗争的失败,源自她局限于个人狭小的圈子。[1]茅盾1946年为《呼兰河传》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虽肯定作品在艺术上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对萧红晚期的人生态度,对《呼兰河传》的“思想弱点”都有明确的訾议。茅盾认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萧红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结果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中去,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因此难免感到苦闷而寂寞;这种灰暗心情使其创作对封建剥削和压迫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未加凸显。[2]石怀池和茅盾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之后的评论者多是延续此种论调,对萧红的晚期创作多有指责和非议。直至新时期这些作品才被重新“挖掘”出来,评论家纷纷赞许其“超前意识”和独特风格,在“左翼作家”总体遭受冷遇时,萧红却再度走红。
经历坎坷的萧红从一开始创作就定下了悲哀和苦难的基调。从东北“跋涉”时期的小说、散文到上海时期的《生死场》,生命中的苦难与不堪就扎下了根,并且一直延续到以后的许多作品中。而晚期的《后花园》《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更是萧红阅尽人生沧桑后对曾深切体验过的世事的重新书写。这些作品回望家园与童年,有意识地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固执地诉说个体心灵的悲欢。这种疏离与逆向的选择,使当时人们对萧红的评价江河日下,但萧红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也正体现于此。
“人文不分”似乎是民国文艺女性普遍的宿命,白薇、庐隐、萧红、张爱玲一个个经历传奇,但结局悲惨。她们的人生远比笔下的文字要丰富多彩,几十年来人们津津乐道她们的种种隐私,她们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早已纠缠不清。某种程度上,若不了解萧红的生命行旅,就无法走进她的作品,也就无法真正读懂她晚期创作中的家园眷恋。因此,本文将结合萧红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来展开论述。
抗婚出走的萧红一直生活在路上,经历了被困哈尔滨、转战上海、出走日本、导师鲁迅逝世、与萧军分手、与端木结合、蛰居香港等重大变故,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动荡艰难的岁月。她一直渴望能有安稳的生活,能有安静的写作环境。当她在1940年1月与端木蕻良飞抵香港时,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心写作的驿站。而且,端木此间担任教授和编辑,为萧红提供了较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安静的写作环境,为萧红的晚期创作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蛰居香港的萧红并不快乐。其时萧红重疾缠身,许多昔日的好友因她与萧军分手也逐渐疏远。她在孤寂的南天一隅遥望北国,写出了《后花园》《呼兰河传》等对故乡一往情深的恋歌。故乡的人事风景经由时空的过滤和成年经验的重塑而被美化了。无论是写东二道街的大泥坑、扎彩铺,还是乡民少有的精神盛举,如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虽不乏凄凉,但又别具风情。即便是对乡民们愚昧麻木的生存方式和浑浑噩噩的人生态度,她在讽刺中仍藏着不忍,甚至被他们本性中所固有的质朴、善良与坚韧所打动。不久,病中的萧红又完成了《小城三月》,这篇小说除了娓娓叙说故乡的人情风俗,还第一次充满温情的描写自己的家庭。过去被萧红写得不近情理的父亲,刻薄、阴险的继母,残暴不仁的族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父亲的开明和温和,继母的宽容和善解人意,以及整个大家庭的“咸与维新”、极乐融融。这种笔调与她过去那些带有自传性的作品相比,格调明显不同。之后,她又写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同样饱蘸着对故乡的深情:“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3]438可见,萧红的晚期作品流露出无尽的乡愁与乡恋。
二、漂泊:家园书写的背景与底色
早年与家族断然决裂的萧红为何在晚期作品中一再书写家园眷恋?最平常的解释是:
第一,人在他乡,眷念故土。萧红20岁逃离家庭,开始到处流浪的飘泊生涯,经受战争、饥饿、寒冷和病痛的折磨,颠沛流离于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北京、西安、武汉、重庆、香港之间,难得有安稳的日子。长期远离故乡、备受病痛流离之苦的萧红自然念念于故乡山川和故土子民,形成一种“眷恋故园的心理定向结构”[4],她笔下的故乡经由成年情感的投射而披上了美丽温情的面纱。
第二,承续了中国文学的“遗民”写作传统。中国历史上不乏“失国”的“遗民”书写故国山水风物来寄托“黍离之悲”。如李煜怀念故国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姜夔伤悼扬州的《扬州慢·淮左名都》等,都是一种别有怀抱的隐喻式写作。在上世纪40年代,除了萧红的《后花园》《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小说外,还出现了端木蕻良的《初吻》《早春》,骆宾基的《幼年》(又名《混沌》)《少年》等一批“童年回忆”的小说。这些流亡异地的东北作家追忆童年,描绘故土上的人物风情,未尝不隐含着“遗民”写作的家国之思与亡国之痛。
第三,寻找情感慰藉。对萧红来说,故乡是留有她点点滴滴生活记忆的地方,也是她文学创作灵感永不枯竭的根源。成年后的萧红与家庭渐行渐远,在她饱尝人间苦味之后,童年和故乡就成了规避现实困境的情感慰藉,于是在她的晚期小说中,一再满怀深情地回首故人往事,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现实处境的无奈和对往昔生活的眷恋。
这些论述或许从某一侧面解释了萧红晚期创作中的家园情结,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精神还乡蕴含着萧红对早年生活的反思甚至是忏悔。
萧红是一个感情胜于理智的人。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将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汪恩甲,初中毕业之际,汪家正式提出结婚要求。此时的萧红,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陶,一心向往去北平这样的大城市继续学习,不再甘愿做传统的贤妻良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成了当时中国一代新女性的仿效榜样,逃婚、叛逆、追求个性,自然是最富有时代色彩的浪漫选择。“富于理想、耽于幻想”的萧红面对求学梦与结婚的抉择,大胆、叛逆的她最终选择了娜拉式的出走,跟随表哥出走北平,成了一个现实版的子君。但正如鲁迅说的,“梦是好的,钱是要紧的。”萧红的梦想是在北平上学,追求更广阔的天地,可衣食无着的困难迫使她在出走北平几个月后,又极不情愿地回到了哈尔滨。
萧红的出走,使父亲张廷举颜面扫地。尔后,因教子无方,又被解除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一职。舆论甚至波及整个张氏家族。这还没完,未婚夫的兄长痛惜家族脸面,一怒之下解除了他们的婚约。萧红气不过,将之告上法庭。张氏家族虽然痛恨萧红此前的举动,但为了家族荣誉,张廷举、梁亚兰(继母)还有其他族人都参加了庭审。汪恩甲怕哥哥受处分,最终当庭承认是自己要解除婚约。庭审败诉无疑让整个张氏家族颜面尽失。一心想要维护家族脸面的张廷举对女儿的行为痛心疾首;遭受打击、渴望安抚的萧红对家庭的责难更是难以接受。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不肯妥协。
出于对家庭的怨愤,也源于接受了哈尔滨左翼文化圈“阶级论”观点影响,在早期的一些散文中,萧红宣泄了对与之决裂的家庭的敌视与怨怼,宣称宁可一个人在外流浪,也不愿回到家中,接受和自己势同水火的父亲的豢养。“跋涉”时期出现在小说《王阿嫂的死》《夜风》中的张氏地主家族,被塑造为迫害穷苦农民的残忍暴虐之徒,很容易让读者看作是她对家族的影射。作品流传后,给张氏族人带来一定的压力,长辈们视萧红大逆不道、侮辱尊长,1935年修撰族谱时,坚决将其开除族籍。
但是,十年漂泊,萧红饱受贫困、疾病和生育之痛,更经历了感情上接二连三的打击。她为了抗拒包办婚姻毅然离开家庭,可在北平却因汪恩甲的软缠硬磨与其同居并被骗回哈尔滨,身怀六甲又被弃旅馆。萧军的出手相救燃起了她对生活的希望与热情,但昔日“为我遮蔽暴风雨”的爱人而今“变成暴风雨了”,萧军的大男人主义和多次移情别恋深深伤害了萧红,最后两人分道扬镳。后来仅因为端木在她与萧军有争执的时候帮她说话,她便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选择了端木,结果在战乱中又一再被端木遗弃。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未给她带来预想中的幸福。人生阅历的丰富使那个此前任性的孩子已然成熟。萧红开始自觉审视自身,反思过往,对自己孜孜以求的理想与情感产生了怀疑。正像一位学者所说,“萧红的离家出走,固然带有反封建的‘抗婚’色彩,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便可发现,她的这种‘抗婚’行为,又是她童年情绪记忆的直接反映。……她的‘抗婚’是对她童年恐惧心理的一种规避与逃遁,是潜意识支配下的青春期女性的一种焦虑与不安,明显带有很大的茫然性”[5]。就像《小城三月》里的翠姨,眼见妹妹风光出嫁、婚后挨打,预见自己也将重复同样的婚恋轨迹,因此对自己的婚事并不热心。后来因缘巧合,翠姨暗恋上我在外读书的堂哥,觉得上过大学的人好,对女人和气,绝不会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经历到哈尔滨买嫁妆跟男学生的实际接触,翠姨就更不愿意出嫁了,但她又不知如何摆脱加在自己身上的宿命,只是直觉地认为读书好,于是她提出要读书,并以种种借口推迟婚期,最后郁郁而终。在这篇小说里,其实投入了萧红自己的经验。当年在哈尔滨求学时,萧红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高校的优秀男生,这也许影响到她对未婚夫的态度而想解除婚约,而对现代文明的渴望使她不顾一切踏上去北平的求学之路。解救她的萧军是个有知识的文化人,或许当年萧红也期许能有温暖安宁的家庭生活,萧军的拳头和暴躁打破了她的幻想。敏感的萧红在往后的经历中深切地感受到即便是“维新”的文化人,其骨子里也充满了男权意识,言谈说笑间也“常常要取着女子作题材”。端木的懦弱和淡漠,朋友的不解和疏远更使走到生命尽头的萧红感觉万念俱灰。此时的萧红,渴望重回呼兰河,渴望能见到父亲和继母,还有众多的亲人,甚至可能会因此反思,假如当初没有那么任性和决绝地效仿娜拉离家出走会怎样?父亲给她安排的生活道路是否真的就那么难以接受?也许她就是带着这样复杂的感情来回望故乡的。
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萧红念念不忘给她带来童年快乐的“后花园”,何以在《呼兰河传》中絮絮倾诉故乡的风土人情,何以在《小城三月》里展现温馨和美、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这位一向被人们视为反叛封建婚姻制度的“大智勇者”(孟悦、戴锦华语),在内心已与此前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家族和解,在她晚期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任性青春的反思和忏悔。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体会1941年底,萧红病危之际要求骆宾基送她北上的诉求:“我早该和T(端木)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6]99
三、家:寂寞绝望中的眷恋与想象
萧红的人生轨迹是上世纪初那场中国知识分子从闭塞乡村涌向文明都市的“胜利大逃亡”的缩影。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传统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和对“西化”现代性的追求。与此相应,从“五四”思想启蒙开始,新文学便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全面攻击,尤其是以“家”作为反封建的主体对象,最常见的处理策略便是把中国的“家庭”写成黑暗的坟墓和囚笼,血泪控诉其压制青年的累累罪行,完全排除中国“家”文化的亲情因素。[7]从谢冰心的小说《斯人独憔悴》到田汉的话剧《获虎之夜》无不如此。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更是把“家”的罪恶与黑暗做了淋漓尽致的暴露和渲染。这类作品把清算“家”的罪恶作为迈向进步与解放的必由之路,投合了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追求自由和光明的共同心理。社会的裂变和动荡拓展了女性生命活动的空间,萧红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潮里离家出走、投身文学创作。
这个在动荡岁月中受尽折磨的女人,后期没有像她的恩师鲁迅一样,以“精神导师”的身份批判国民劣根性,也没有像废名和沈从文那样,从单纯道德的角度将乡村美化为世外桃源,而是从切身体验出发,在她的晚期作品中深情回忆“不思量,自难忘”的故土和亲人,也不回避那片土地上的愚昧和苦难。尽管萧红一直被归入“左翼作家”的行列,事实上她与左翼作家也有广泛的交际,但在某种意义上她与革命、进步、左翼始终保持慎独的距离。笔者更愿把她看作是大时代中跟着感觉走的普通女性,无论生活还是创作。这样的女人不会站在精英立场上启蒙大众,她曾同聂绀弩说:“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8]她也不会将“清算家的罪恶”进行到底,时日无多的萧红在寂寞与绝望中对家萌生无限眷恋与想象。
造化弄人,一生在炮火中逃亡的萧红,病逝在陷于日军炮火中的香港。年少时一心想逃离的家庭和故乡,在生命弥留之际却是最眷恋与难舍的东西。当我们隔着几十年的人事,重读早年萧红作品对家庭、亲人的指责,不禁也想谴责她那狠心的父亲,然而,我们又怎能体会这位负载命运和时代双重磨难的父亲内心的隐痛。或许他也深爱着女儿,只是这个“虽新还旧”、略显粗粝的东北男人不懂得如何让那份沉重的情感转个弯,轻柔地落在女儿敏感的心上。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想规矩出一个好人来,萧红的父亲又何尝不是?萧红与父亲的冲突,更多源于父女间的观念差异和青春叛逆期女孩的逆反,但时代的推波助澜,加剧了这种矛盾,并使之染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不过世事难料,当年勇敢出走的娜拉在绝望和忏悔中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和亲人。一直被视为“卫道士”的父亲又怎样呢?据有关资料,1940年代末,张廷举叫人在张家大宅的门上张贴一副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革命家庭[9]
这位早年断然赶走女儿的父亲,转而颂赞早逝于遥远香江的女儿。生前不曾和解的父女,终因时事变迁互相原谅了对方。
在《呼兰河传》中,作者不吝笔墨书写“我”与祖父在后花园学诗的场景。时隔多年后,留在萧红记忆深处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和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细心的读者一看便知,这是萧红在表达一种物是人非、望乡情怯之意。不是“我”不想回家,而是故乡早已不认得伤痕累累、面目全非的“我”了。这种带有浓烈情殇色彩的“家园眷恋”绝非萧红一人的心灵体验,像庐隐、苏雪林、沉樱、石评梅、白薇等新女性作家,她们也都有相似的人生体验。所以,庐隐感慨“何处是归程”、沉樱悲叹“何处是归宿”,而早年打出封建家庭“幽灵塔”的白薇,当她逃家后首次回到湖南老家,她最急于寻求的竟然是父亲的谅解。新女性作家想要“回家”的心灵呼唤,表达了她们对当年鲁莽举动的反省和对女性解放的启蒙话语的强烈质疑。她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到自己的尴尬位置与悲剧命运——她们不但必须跟自己的父亲理论,还得跟父权的革命机制斗争。
四、逃荒:生命的溢出与个体的困境
前面提到,茅盾惋惜蛰居香港的萧红与“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隔绝了,既不能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又因为“陈义太高”,认为知识分子的各种活动全是“扯淡”“无聊”。这一评价对理解萧红的晚期创作颇有启发。作为新女性,萧红受到五四启蒙思潮和左翼文学思潮的双重影响。她以自己的人生实践了五四文学反封建家庭的召唤,但并没有获得启蒙神话所允诺的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相反却承受了鲁迅《伤逝》中子君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她受萧军引领,进入左翼文化圈,并以创作宣誓了自己的战斗姿态,但宏大理想与革命激情淹没了一个出走的娜拉追求安稳生活的朴素愿望。萧红的晚期创作不自觉地流露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困惑。这困惑印证了段从学所指出的鲁迅“五四”现代性启蒙困境:在“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结构中,“启蒙者”之所以成为“愚弱的国民”们的“启蒙者”,就在于丧失了对自身之“蒙蔽”状态的意识能力。也就是说,“启蒙者”和作为启蒙对象的“愚弱的国民”,均处在“蒙蔽”状态,这意味着“启蒙者”不再享有对后者进行启蒙的精英特权,更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0]萧红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体悟到启蒙神话和革命话语的虚妄之处,因此,她视知识分子(启蒙者、革命者)的各种活动是“扯淡”“无聊”,她由悲悯笔下的人物延伸至悲悯自己正是意识到自身的“蒙蔽”状态,想要“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举动。茅盾的评价反证了萧红晚期作品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和对左翼创作程式的超越。
美国学者阿瑞提说“意象不是忠实的再现,而是不完全的复现。这种复现只满足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使这个人体验到一种他与所再现的原事物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情感。”[4]也就是说,作家特定的心境和情感制约着意象的再现以及再现的程度。萧红晚期作品中密集涌现的镀上了温暖色调的故乡风物与故人往事,透露出作者怎样的心境呢?《呼兰河传》描写“跳大神”时有这样一段文字:“那鼓声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人,打得有急有慢,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着他幸福的短短的幼年。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她的儿子远行。又好像是生离死别,万分地难舍。”[11]737这一段话不正是萧红晚期创作心境的真实写照吗?历经沧桑的萧红,记忆深处的幸福在于她与家人度过的短短童年。这温暖的回忆,夹杂着“一个迷路的人”的“迷惘”,还有作者自知时日不多,无法还乡的“难舍”。《呼兰河传》的结尾部分交代,后花园的小主人逃荒去了。“逃荒”一词点出了萧红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概括:没有热血青年的豪情、理想与浪漫,只是一个无路可走的女孩的逃命之路。于此亦投射出作者思想意识从反家到恋家的蜕变。
钱理群曾撰文描绘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集体的心理转向:从“旷野”上的“流亡”转向对“归宿”的寻找,并最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延安。文学也相应地由“战争浪漫主义”转向“改造”文学与“颂歌”文学。[12]这一分析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文学选择。但是,萧红作为一位忠实于个人生命体验和自我情感书写的作家,并没有因为周身弥漫的激进革命风潮而放弃个体感受与思考。她选择了与走向延安有所差异的南下香港;而她的晚期创作也溢出左翼文学的宏大叙事洪流,回归鲜活的个体生命体验,显现了对女性解放的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疏离与反思。这种带有个人体温和气质的写作提供了了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另一向度的心理切片,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巨变中新女性的抗争、迷茫和“疼痛”以及左翼文学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因此,对萧红晚期人生态度和“家园眷恋”书写的探讨,便成为很有文学和学术意义的话题。
[1]石怀池.论萧红[M]//石怀池.石怀池文学论文集.上海:耕耘出版社,1945:92-105.
[2]茅盾.呼兰河传·序[M]//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698-706.
[3]范桥,卢今编.萧红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4]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4-64.
[5]宋剑华.灵魂的“失乐园”: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意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4):103-117.
[6]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7]宋剑华,杨红军.从反叛到皈依:论新文学“家”之叙事的复杂心态[J].文艺研究,2015(5):76-84.
[8]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序《萧红选集》[J].新文学史料,1981(1):186-189.
[9]王小妮.萧红写了两部生死场——作家被时代浸袭与原态写作的回归[J].文艺争鸣,2011(3):6-9.
[10]段从学.答复这个问题:“娜拉走后怎样?”——一个可能的出口[J].鲁迅研究月刊2012(7):11-21.
[11]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12]钱理群.“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M]//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43-64.
(责任编辑:李金龙)
I206.6
A
1001-4225(2017)02-0020-06
2016-10-17
贾颖妮(1974-),女,湖南益阳人,文学博士,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副教授。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