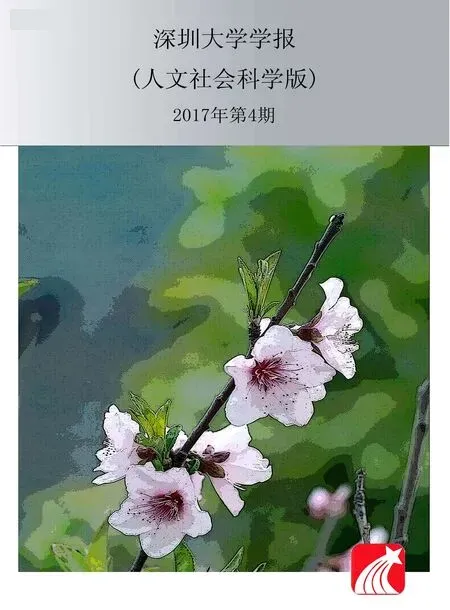角色、身体与空间:晚清民初禁戏与戏剧观演形态
陈仕国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角色、身体与空间:晚清民初禁戏与戏剧观演形态
陈仕国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晚清民初,禁戏政策语境下的戏剧观演形态,即角色扮演的性别意识、舞台演出的组合形式及观众群体的构成方式均发生嬗变。此种嬗变正是通过对以女性为主体的戏剧观演空间进行圈限,凸显官方的权力意志与民众约定俗成的戏剧审美要求之间,存在某种无法弥合的张力。男权社会对女性演员的性别歧视,使之无法摆脱既定空间权力的钳制而丧失身份地位;商品经济下所形成的男女合演形态,表面上是女性演员获取空间权力与身体解放的表征,却依旧体现其置于被男性窥视与操控的境地;女性观众群体的不断壮大,显示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却未颠覆现存社会机制以改变既定的戏剧观演关系。
晚清民初;禁戏;观演形态;身体空间
由于整个晚清民初社会传统分化、思想发生变革,昆曲逐渐走向衰落,传奇杂剧倾向案头,失去其观众和舞台,而此时的花部地方戏依然保持其繁盛势头。从剧目内容来看,大量改编移植历史演义和民间传说题材的剧作层出不穷,再现历史时代与社会生活,昭示底层民众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反叛精神的凸显;从表演风格来看,剧作的写实风格逐渐取代写意风格并成为舞台表演的主流形态;从剧类互动来看,各式各类的民间小戏充斥舞台,显示其强劲的生命力。由此,此前所未有的戏剧发展趋势,是由民众审美需求和情感需要决定的,并非官方的权力意志所能掌控。晚清民初禁戏政策语境下的戏剧观演形态,即角色扮演的性别意识、舞台演出的组合形式及观众群体的构成方式均发生根本性嬗变。即便官方出台各种禁戏明令与采取诸多举措对此进行压制,非但未达至完全禁止之效果,反而促使戏剧观演活动愈演愈烈,呈现一片繁盛之势。因此,对该时期禁戏政策与戏剧观演形态的具体情形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官方禁戏举措对戏剧观演形态所造成的影响,探究该时期戏剧发展的某些内在问题,而且有助于考察角色、身体与空间之间所充斥的关系,形成以戏剧观演形态来理解空间权力的某种独特视野。
一、女性演员身体空间的圈限与钳制
清朝政府沿袭前代禁戏策略与手段,对戏剧进行强烈压制和猛烈摧残,尤其体现在禁止女伶演戏上。康熙十年(1671),清政府颁布诏令,规定“凡唱秧歌妇女及堕民婆,令五城司坊等官尽行驱逐回籍,毋令潜住京城”[1](P1)。此明令驱逐吟唱秧歌的妇女,显示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空间的圈限与钳制。此种禁戏的圈限话语不断延续,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刑部下顺天府行苑、大两县并五城司诏令,“将秧歌脚堕民婆,速行尽驱逐回籍,毋令潜住京城。”[2]秧歌妇女化妆表演风俗歌舞,乃由民众审美需求和情感需要决定的。此禁语只不过是官方出于对社会治安进行维护的考虑。康熙五十八年(1719),官方以“不肖官员人等迷恋,以致磐其产业”为由,禁止妇女进入京城,否则“进城被获者,照妓女进城例处分。”[2]禁绝对象由原来的秧歌妇女扩大至戏剧女伶。此时的女伶一旦进京演唱戏剧,便被视同妓女而遭致指罪。由于 “男女两性对立和性别关系的社会化过程是构成权力内涵的基本要素,要改变其中某一方面,必将危及整个权力系统的安全”[3]。因此,官方此种禁戏的权力话语乃为维护和保持两性社会平衡而针对女性角色所采取机智之防范策略,即运用统治者的禁戏权力话语使女性性别“孤立化”和“放逐化”,并从常规的社会性别角色体系中驱逐而出,使之成为社会的异类,失却与男性平等的社会身份地位,最终变成社会“卑贱者”。此种重置性别角色的话语,显示男权社会消解戏剧女伶在舞台和现实中对性别制度可能带来的破坏与挑战。“当局因此制定种种律令,以抵消隐含在表演活动中逾越社会藩篱的任何可能性。这使得演员一方面可以随意地在舞台上扮帝王、妆权贵,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舞台下的现实世界里,却只能过着如贱民般的生活,所有逾越的可能性与空间被一笔勾销。而女演员被视为妓女般任人摧残,则还可能隐含着社会对她们在舞台上逾越‘性别’藩篱的进一步‘惩罚’。”[4]可见,男权禁戏话语对女性演员性别角色的圈限,凸显统治者对政治权力的维护和巩固。
晚清民初,统治者仍沿袭古代禁止女伶演戏之律令。光绪十年(1884)夏,“大吏严谕禁止,诸伶无大小悉拘归言鬻,且令定价二千,不得适听鼓人员与橐笔幕客。”[5]尽管官方不断出台各式各样针对女伶演戏的禁令,如光绪十一年(1885),“新正以来,忽有女伶数辈,借栢梁台茶室,开逐花鼓戏,于是逐臭之。……以其有碍风俗,驱逐出境,不准逗留。”[6]又如光绪十六年(1890),“嗣有某某等接踵而起,此风大盛,名园宴客,绮席飞觞,非得女伶点缀其间几不足以尽兴。英会审员蔡二源太守,以其伤风败俗,商诸麦总巡捕头,下令禁止。”[7]但女伶演剧现象却愈演愈烈。其“抛头露面”的演戏情形在官方文化视野里,一贯以来皆处于非法境地,往往以伤风败俗或破坏社会秩序为由予以钳制。然而,官方此种方式却收效甚微,因其出台的禁戏令往往以报刊此种媒体进行传播,实质效果则形同虚设,并未能对女伶演剧现象实行有效管束。光绪三十一年(1905),“厦门三升客栈近,招住流妓倚门买笑以诱狂,且附近天仙茶园,亦有女伶演剧。观者恒趋之如惊,匪徒混杂其间,往往因而滋事。……三升栈立将流妓驱逐,天仙女班亦即停歇。”[8]宣统二年(1910),天津“兴化茶园有女伶曰小七盏灯,十三日早演《小逛庙》一出,淫言秽语不堪入耳,淫状秽态尤属不堪入目。该管官盍查察之。”[9]民国元年(1912),上海宝善街“某女戏园正厅挂一大黑板……吾未见其改良,亦未见其警世,只见多排淫戏,而女伶之做作较男伶更淫。……如此淫戏,况又女伶所做,有不大坏风化者哉?”[10]民国八年(1919),广东 “现查投师者类多大家闺秀、名门宦族……总之,一入其途,虽冰洁之玉,难保其无瑕之玷。”[11]置身于危若累卵时势之晚清民初报刊者,其将挽风俗、启民智作为兴办办刊之宗旨。《申报》之主要宗旨是“寓劝惩以动人心,分良莠以厚风俗”[12];《游戏报》则为“寓意劝惩”“无非欲唤醒痴愚”[13]。报刊者此种正人心、挽颓风之宗旨,有效地延伸女伶演剧禁令。然而,“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14]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传媒的“公共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乃至冲击。此种通过报刊媒体传播的禁戏令,并非宣传官方的政治权力意识,而是为迎合广大民众的文化审美趣味,以吸引更多民众关注报刊本身的娱乐性与趣味性。
官方禁戏政策的松弛,尤其是对女伶演剧活动的疏忽,予以其崛起及登台表演提供极大的可能性。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初五,何荫柟“晚饭后,同到群仙看妙儿戏,尚属楚楚,观者亦众。吴新宝、林黛玉皆在演串,亦此中之巨擘焉。”[15]除戏园外,该时期还出现专供女伶演剧的固定场所。谈珵熙《上海黄莺儿词》云:“任意去盘桓,到愚园,又张园,男男女女纷相乱。马儿也喧,车儿也喧,洋房上下都展宽。好为欢,猫儿女戏,闲坐一回看。”[16]可见,清一色女性演员的髦儿戏班当时在愚园、张园热闹非凡的演剧景象。随着女班戏园蔚为大观,女伶的表演技艺得以提升。“光(绪)、宣(统)间,群仙(茶园)教授之女伶,应运而出。对于剧情及唱念,亦稍知改良。郭少娥之女凤仙,习武旦而兼演武生剧,武功尚称精熟,工架亦极老练,开坤伶武行之新纪元。”[17]这些女伶在戏园里彼此进行演艺切磋,相互得以提高。“……时赵智庵长内务,开放小班牌禁。……老俞(毛包)之子俞五(振庭)见有机可乘,遂尔招致坤伶,借以标新立异。当时递呈警厅,请解坤伶入京之禁。”[18]女伶登台演剧,不仅提升自我主体身份地位,而且扩展戏剧舞台对美之呈现范围,继而延续戏剧的娱乐性功能。然,女伶此种符合民众情感需求与文化消费之演剧行为,却被官方予以各种指罪。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会审分府属为出示严禁事。照得演唱戏曲,男女混杂,实属有关风化,本分府访闻同广东戏园有女伶混杂演剧,殊违禁令,业经饬差传谕该女优散去。”[19]光绪三十四年(1908),湖南常德府城华严庵满春茶园,“前因有女伶在内演剧,由巡警局查禁。……兹闻仍有女伶多名在内演唱,殊属有伤风化,且累酿争端,与前禀不符,自示之后,该女伶等赶速出境,毋得逗留,致干查究封禁云。 ”[20]
尽管对女伶的演艺水平予以认可,但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性别秩序的整体性并未得以改变。“(女伶)夜明珠……善演《小上坟》《珍珠衫》《卖胭脂》《打樱桃》诸剧,谑浪秽亵,春色撩人,致一般登徒子垂涎。不置究之,骚淫过甚,有伤风化,或曰:此女伶淫剧之所以不可不禁也。”[21]官方予以女伶演剧的种种指罪实非限其性别,而是对其表演内容及其形式进行钳制。在某种程度上,此种钳制为统治者所掌控,从而导致其空间权力异化,致使其身份与地位的丧失。“女性在历史上向来被排斥于一些空间之外,或局限于一些空间。与种族隔离一样,男女生存的空间从来就是‘隔离的和不平等的’,对女性的‘规范的空间’的建构往往能说明空间的性别。”[22](P48)晚清民初,官方的禁戏律令体现女伶难以摆脱空间权力的钳制,而性别歧视与环境逼仄直接导致女性演员身份与地位的异化,由此成为其空间权力圈限的重要表征。
二、男女合演身体空间的丧失与表征
随着花部地方戏的崛起及大量女伶登台演出,男女合演现象层见叠出。男女合演,肇始于同治九年(1870)之上海。“上海新北门外花鼓戏馆,至今未能禁绝。……近时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亵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为扮演。……若男女合演者,词曲情景无一非淫此,而不禁流毒,曷有终极。”[23]光绪三年(1877),上海租界“向有花鼓之戏,男女合演,淫声浪态,不堪逼视。……花鼓戏班,借楼开唱,男女皆坐而不演已,为人心风俗之忧。……务当除其根株也。”[24]官方以有伤地方风化为由,为维护社会治安与秩序,实行禁止男女合演举措。然,此禁令却显苍白无力。当时女伶虽盛极一时,却无法与男班竞争,致使戏剧女班经营惨淡,演剧活动日趋衰落。“群仙丹桂虽知互相砥砺,然总不如共舞台之营业发达。……即素抱廉价主义之丹桂(丹桂茶园之正厅,售价不过一二角)与类似科班之群仙,亦奄奄一息,势将不可收拾”[25]。为挽救女班命运,更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男女合演便势不可挡。
上海男女合演,工部局向悬为厉禁。光绪末年大新街丹凤茶园领得男女合班照会,即行开演,此实为上海男女伶合演之滥觞。然其时男女伶名虽合班,实不合演,嗣因营业不佳,经理者竟以男女合演为尝试,事为工部局查知,立将照会吊销,遂致十余年来无复继起者。法租界凤舞台则授丹凤成案接踵而起,始即男女合演,盖法捕房禁令较宽,而沪人心理日趋淫靡,实非此不足以号召也。[26]
囿于技艺偏低,女班未能独立经营,不得不依附男班以维持生活。恰如钝根所言:“及乎近十年,而女伶始露头角,渐与男子合演”[27]。因此,“共舞台又轫始男女合演,叫座力亦颇不恶”[17]。在男女合班基础上,男女合演便水到渠成[28]。
光绪三十一年(1905),徐绅士向天津直督详禀称:“津郡戏馆……竟敢男女合为一班合演淫戏,伤风败俗。莫此为甚,窃拟仿照上海租界章程,恳请照会各国租界领事等官,禁其男女合演,不禁其男女分演。”[29]风气既开,反对亦属徒然。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五日起,丹凤茶园“特请全班文武男女名角合演《新添五彩油画》新戏”[30]。此举随即便引起官方注意,会审公廨宝谳员就丹凤茶园男女合演之事上书上海道台蔡乃煌,称该戏园“虽名为分剧演唱,然经卑廨调阅戏单。其配角之中实系男女混杂。伤风化而败治安,莫此为甚,亟应严行禁止。”[31]尽管官方对丹凤茶园男女合演活动进行钳制[32],但男女合演却早为社会所体认,即“男女竞争久成事实,即以演剧而谕各国,亦无奈制。男女合演之举,况我国津沪地方,男女合演早已盛行,照请禁阻。法令未必允从,然有多数议员皆赞成。”[33]又如沪海关杨道尹“谓已与英法租界领事商禁,熟知言犹在耳,而法界即有男女合演之举,今英界又有以一戏团而日演女剧,夜间演男剧者,讵英工部局别有此种男女两用之照会耶,而省教育会与杨道尹之言故已等于弁髦矣”[34]。欧美各国,男女合演之风气早已有之。上海租界,多为外国人居住,故男女合演在此得以被广泛支持。
近年来,英界亦解放男女合演,天蟾、上丹桂更新及大舞台等亦争聘北平稍有声色之女伶来沪,如雪艳琴、新艳秋、孟丽君、筱凌云、刘艳琴、筱兰芳及久寓沪滨之琴雪芳、白牡丹等,藉以维持其营业。[17]
由于新式的戏剧舞台大量兴建,予以女伶更多的表演空间,同时亦能吸引大量观众。因而在租界的舞台实行男女合演后,华界舞台亦见势而动,纷纷邀请著名女伶加盟,“上海剧场中,乃无一不男女合演”[35]。在商品经济下,同工不同酬的性别歧视,使女伶工资低于男伶。因此,男女合演既可节省开支,又能吸引观众,从而获取更多利润。
人的身体具有双重性,即生理身体与社会身体。“社会的身体构成了感受生理的身体的方式。身体的生理的经验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正是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身体才得以被认知,所以,对身体的生理的经验就含有社会的特定观念。在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多种意义的交换,目的在于彼此加强。”[36]概言之,生理身体是传达某种社会意义的符号载体,而个体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便会对生理身体进行控制与压迫,以期符合特定的社会情境和规范。因此,社会的特定观念往往与时代背景和文化特征紧密相联,形成当下最具时代气息的思想理念和审美意蕴,成为主导性的身体文化符号。而在男权社会下,女性身体接受社会文化的规训,而规训则“使力量与肉体分离,一方面,它把体能变成了一种‘才能’,一种‘能力’并竭力增强它。另一方面,它扭转体能的运作——力量可能由此产生——并将之置入一种严格的隶属关系。”[37]可见,规训对女性演员身体空间进行操控,使之能按照统治者的意图行事,最终达至其自身的目的。换言之,在规训的作用下,女性个体无法保持其独立个性,而是被规训成千篇一律,甚至连思维意识皆同的整体。可见,规训是由性别意识、空间权力等级差异等信息所传达,从而表征女性的形象和地位,强化符号意义文化的建构和输出,同时亦表现空间权力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营建关系。
在商品经济下,女性身体成为消费的符号,成为依附男权社会的消费品。“女性通过性解放被 ‘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 ”[38]晚清民初,女伶依附男伶而获得“消费”,表面上示女伶获取空间自由与身体解放的表征。然,在官方禁戏话语权力下,男女合演却屡次遭禁。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天津“窃查近日津郡戏馆日多一日,男女合演淫戏亦日甚一日,丑态百出,肆无忌惮。妇女入座听戏,亦毫不知羞,伤风败俗,莫此为甚。”[39]宣统三年(1911),湖北荆州城,“日前吴道斌守等同日寿辰,竟各在其衙署内召天仙、丹桂两梨园连演五日,所获赏钱多至万缗以外,极称一时之盛,讵事为鄂督所闻,以男女合演淫戏最为风俗之害。”[40]实际上,男女合演遭禁并非仅仅源自于其本身有伤风化和扰乱治安之故。齐如山先生认为,男女合演遭禁是因“女脚叫座的力量太大,男脚恐受影响”[41]。经呈报京师警察厅批准后,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九日,内务部则下令,“再行伤知各班、各戏园一体遵照,并知照乐育化总会,男女分台开演,正所以维持风化也。”[42]可见,男伶及其戏班因惧女伶演剧吸引大量观众而动摇其舞台地位,才以维护风化为由,呈请政府禁制。
男女合演活动被指罪,显示女伶身体置于被男性窥视与操控的境地,并非从男权社会中彻底解放出来。宣统元年(1909),四川省泸州“各属之梨园子弟,有所谓窝班窝者。男女合演,丑态百出,地方官虽屡经示禁,依然阳奉阴违。……当经该县刘大令驱逐出境,以息事端而维风化。”[43]以男权为中心的晚清民初,男女合演使女伶虽获取某种意义上的身体解放,为其登台演剧提供极大可能性,然,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消费而已,是由某种被控制与压迫的状态转化为另外某种被控制与压迫状态,难逃被予以某种莫名之罪,无法争取其应有之社会地位,更遑论从男权社会中彻底解放出来。
三、女性观众身体空间的敞开与放逐
在男权社会下,妇女观剧则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致严厉禁绝。历朝历代统治者俱数次颁布禁止妇女观剧之法令,清朝尤为突出。自康熙至宣统年间,统治者均不同程度地颁布禁止妇女观剧之律令。康熙十六年(1677),“妇女台前看戏,车轿杂于众男子中,成何风化!且优人科诨,无所不至,可令闺中女儿闻见耶?”[44]雍正九年(1731),浙江发榜禁妇女游山听戏:“朱文端公轼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45]乾隆二十六年(1761),统治者认为妇女不可听唱说书,便下令“戏之忠孝节义者少,偷情调戏者多,妇女观之,兴动心移,所关匪细,不可不慎。”[46]道光年间,“京师戏园演剧,妇女皆可往观,惟须在楼上耳。某御史巡视中城,谓有伤风化,疏请严禁,旋奉严旨禁止。 ”[47](P5065)咸丰时,“张观准夙以道学自名,尝官河南知府,甫下车,即禁止妇女入庙观剧。”[47](P5066)嘉庆年间,陕西汉中地方政府颁布禁令,“严禁妇女游会烧香,以端风化事。”[48]清朝官方文告、朝廷谕旨亦屡屡禁止女性观众出入戏场。同治八年(1869),“御史锡光奏请严禁五城寺院演剧招摇妇女入庙,以端风化一折。”[49]妇女入寺烧香,游庙观剧,或因听信因果,或为娱乐休闲,或为群集交流。就连在家中演戏,妇女亦唯有望而却步:“家演戏文,不可垂帘设屏,使妇女窥望”[50]。作为社会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观剧往往以排解苦难、发抒内心不平之情为目的,然,此种正常的日常生活行为却被官方冠以各种罪名而遭致禁绝。
对女性而言,“现存的空间是造成她们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男性对妇女的社会空间的安排是男性控制妇女的一个重要工具”[22](P47)。晚清民初的禁戏令使女性观剧活动的空间范围仅集中 “闺门”内,实是对女性身体的窥视与操控。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之士对男女平等思想之宣传及其对女性独立自主的精神之召唤,女性解放思想得以大力宣扬,并为自身寻求某种新的社会角色而努力。此新的社会角色最为明显的标识在于女性观众的大量出现及其群体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由于身体是构成女性解放、建构平等社会秩序的基础。只有女性的身体自男性政治权力中挣脱开来,或始终进行反抗,其才有可能获取真正的自由与解放。恰如列斐伏尔所言:“整个(社会)空间都从身体开始,不管它是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是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的起源问题做出解释。”[51]女性这个观众群体的发展壮大,实质上显示女性正摆脱男权社会对其空间权力的圈限,以此构建自我主体意识。“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纷至沓来,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52]随着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女性逐而走出家庭,出入戏园,成为戏剧观众群体中的重要主体力量,不仅打破了女性与戏剧隔绝的局面,而且推动了适合女性审美趣味的戏剧风格的发展。
晚清民初,女性观众进而扩大,成为戏剧观众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光绪庚子,联军进京,各处演戏,都许妇女同看。”[53]对女性观众而言,由于其观剧历史不长,加之艺术熏陶时间较短,欣赏能力有限,故其进园观剧更多是以娱乐为目的,而随着女伶崛起,女性观众以其独特的审美取向,对女伶的造型与服饰表现出对美的追求,从而促使演剧形态发生嬗变,此种嬗变便是旦角逐渐取代须生:“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不到几年工夫,青衣拥有了大量的观众,一跃而居戏曲行当里重要的地位。后来参加的这一大批新观众也有一点促成的力量的。 ”[54]
女伶之崛起,不仅拓展戏剧舞台对美的展现范围,对演员装扮要求甚高,且进而增强戏剧的审美功能和娱乐性,恰好满足女性观众特殊的审美需求。“演戏刚逢二月朝,家家妇女讲深宵。看台宜与戏台近,吩咐奚奴预作标。邻家姊妹各商量,明日如何作晓妆。小婢点灯亲检钥,隔宵翻出好衣裳。一夜芳衾睡不成,晓鸡齐唱报天明。先挑锦帐窗前望,果否何如昨日晴。胭脂微点粉匀粘,早起忽忙启镜奁。”[55]可见,女性对戏剧投以极大热情,对那些名伶更是表现极大羡慕和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其不断构建的主体意识。“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56]由于杨月楼表演技艺精湛,吸引大量女性观众。
身体规训并非某个社会某个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37]身体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不断受到各种权力机制与权力意识的控制。晚清民初,各种戏院允许女性观众进入观剧,女性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公共娱乐领域。宣统元年(1909),由宋则久所创办的天津大观新舞台文明戏园,规定“进门处之北厢东首,每日留地位一段,专卖女客。”[57]在此,“性别空间的无形隔离,被娱乐消费的商业浪潮冲开了缺口”[58],表达女性获取个性解放与身体自由的强烈愿望。然,作为公共观演空间,旧式戏园和茶园存在严格的等级界限,使其成为儒家思想体系和社会原则的规训场所[59],而观众的身份及其性别则成为空间权力规训的对象。男女观众不能随便就坐,女性观众的座位被安排于戏院的第二层,男性观众的座位则位于楼下,此种界限实质构成强化女性性别的标识,致使 “女坐之远,几乎不能辨明眉目”[60]。某种意义上,此种文化现象实为官方禁戏权力话语的延伸,致使女性观众所构建的主体意识发生坍塌。“男女杂坐,秩序紊乱,诱奸及诈欺等事大都发源于此。……而其(演剧)弊,仅在秩序之紊乱。今为兴利除弊计,急宜使男女异席,严分界限。”[61]从社会治安角度来考虑,官方认为男女杂坐之行为势必会引起社会秩序的紊乱。此种莫名的指罪实出于戏院经营者对其经济利益的考虑:“以池子售价较廉于包厢,曩因分座之禁令,凡携眷或偕情人赴剧场聆歌者,势不能不购价值较贵之包厢票,今池子开放,群将舍包厢而去池子。其影响于营业之收入,岂可以道里计哉!”[62]
四、结 语
在官方禁戏律令掌控下,晚清民初的角色扮演意识、演出组合方式及观众群体构成等观演形态发生根本性嬗变,此种嬗变显示官方之权力意志与民众约定俗成的戏剧审美要求之间,存在某种无法弥合的张力。男权社会下,女性演员试图以身体空间作为载体,通过摆脱政治权力对其性别歧视,与男伶进行同台演出,却在禁戏政策语境下置于被男性窥视与操控的境地;女性观众群体的不断壮大,不仅改变观演关系中以男性为主体的观众群体构成方式,显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扩大戏剧消费的主体力量,使晚清民初演剧活动呈现繁荣之势,然,由于固有的社会运作机制及其秩序并未改变,最终难以获取真正意义上的空间自由与身体解放。
[1](清)延煦等.台规(卷二十五)[M].清光绪十八年刊本.
[2](清)孙丹书.定例成案合钞(卷二十五)[M].清康熙间刻本.
[3](美)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A].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74.
[4]周慧玲.女演员、写实主义、“新女性”论述: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剧场中的性别表演[J].戏剧艺术,2000,(1):4-26.
[5]王韬.凇隐漫录(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98.
[6]无名氏.驱逐女伶[N].申报,1885-3-19(3).
[7]无名氏.谕禁女伶[N].申报,1890-1-27(3).
[8]无名氏.驱逐土娼女伶(厦门)[N].申报,1905-4-27(10).
[9]无名氏.女伶淫浪[J].燕尘杂记,1910,2(18):1.
[10]钝根.诲淫之戏园[N].申报,1912-2-2(8).
[11]无名氏.女伶伤风败俗[J].广肇周报,1919,(23):7.
[12]无名氏.本馆自叙[J].申报,1872-9-9(1).
[13]李伯元.论《游戏报》之本意[N].游戏报,1897-8-25(1).
[1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15.
[15](清)何荫柟.鉏月馆日记[A].本社编.清代日记汇抄[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59.
[16]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 (上册)[M].上海:大东书局,1928.118.
[17]味莼.坤伶兴衰史[J].戏剧月刊,1928,1(5):1-5.
[18]醒石.坤伶开始至平之略历[J].戏剧月刊,1928,2(1):1-4.
[19]无名氏.示禁女伶[N].新闻报,1896-6-6(3).
[20]无名氏.示禁女伶演戏[J].吉林官报,1908,(105):7.
[21]剑云.梨花镜(花旦部)·夜明珠[J].繁华杂志,1914,(1):5-6.
[22]苏红军.时空观: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新领域[A].苏红军、柏椂.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3]无名氏.禁男女合演戏文[N].上海新报,1870-7-5(2).
[24]无名氏.花鼓戏宜禁[N].申报,1877-10-1(2).
[25]陈永祥,罗素敏.女演员的兴起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观念的变化[J].民国档案,2005,(1):65-70.
[26]王韬.瀛壖杂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4.
[27]钝根.论男女合演[N].申报,1914-9-20(13).
[28]唐雪莹.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6.
[29]无名氏.禁止男女合演淫戏及蹦蹦戏 (天津)[N].申报,1905-9-16(3).
[30]无名氏.丹凤茶园[N].申报,1909-1-26(7).
[31]无名氏.请禁男女合演之恶习[N].申报,1909-1-30(18).
[32]无名氏.工部局禁止男女合演[N].申报,1909-2-19(18).
[33]无名氏.鄂省议会大事纪[N].申报,1913-11-17(6).
[34]无名氏.男女合演之新剧[N].时报,1914-10-5(3).
[35]漱石.上海之男女合演[N].梨园公报,1929-1-20(3).
[36](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31.
[37](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8.
[38](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9]无名氏.天津县详请禁止男女合演淫戏及蹦蹦戏文并批[J].教育杂志(天津),1905,(14):48.
[40]无名氏.剧场忽来霹雳(湖北)[N].申报,1911-4-22(4).
[41]齐如山.京剧之变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8.85.
[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50.
[43]无名氏.驱逐女伶[N].舆论时事报图画,1909-10-12(2).
[44]全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7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7.540.
[45]钱泳.履园丛话(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25.
[46]钱德苍.新订解人颐广集(卷八)[M].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47]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8]严如熤.(嘉庆)汉中府志[M].郭鹏校勘.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988.
[49]清实录馆.清实录·穆宗实录(第五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757.
[50]醒醉生.庄谐选录[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
[51]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65.
[52]无名氏.邑尊据察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N].申报,1874-1-7(2).
[53]齐如山.齐如山全集[M].台北:联经出版社,1961.1646.
[54]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M].许姬传记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112-113.
[55]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387.
[56]忏情生.续沪北竹枝词[N].申报,1872-5-18(4).
[57]无名氏.论女戏[N].民兴报,1909-9-25(3).
[58]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9.
[59]林存秀.城市之声:戏院与都市生活的变迁[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5-60.
[60]无名氏.津门戏院之缺点[N].大公报,1924-1-12(4).
[61]邱辉东.剧场之急宜整顿[N].申报,1925-12-22(13).
[62]颖川.旧都见闻记[N].北洋画报,1928-10-25(8).
【责任编辑:来小乔】
Role,Body and Space:Opera forbidding and Performance and Audience Experience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CHEN Shi-guo
(Normal College of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518060)
Under the opera-forbidding polic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changes happened in opera performance and viewer experience,namely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role play,stage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 composition.Through restricting the women-dominated performing and watching space,these changes highlighted the irreconcilable tension between the authority’s power will and the established aesthetic needs of the public.The prejudice against women performers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made them unable to shake off the shackles for fear of losing their identity and social status.In the commodity economy,men began to share stages with women,which seem to indicate that women performers have achieved more power on the stage and liberation of their bodies,but it still reflects the fact that women performers are still watched and manipulated by men.A growing group of female audiences represent the awakening of thei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but do not overturn the existing social mechanism to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ence and performer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opera forbidding;opera performance and viewer experience;body space
J 8
A
1000-260X(2017)04-0018-07
2017-01-15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11&ZD107);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近代戏曲文献考索类编”(14ZDB079);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民国禁戏与演剧形态研究”(2015WQNCX131)
陈仕国,艺术学博士,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近代戏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