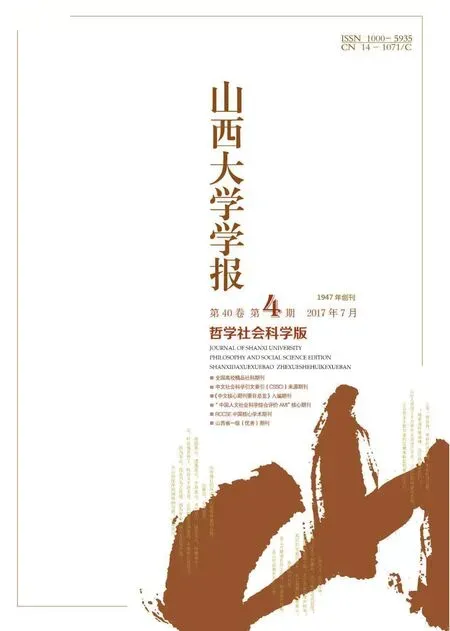媒介化体验: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研究
郑 欣,高梦媛
(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媒介化体验: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研究
郑 欣,高梦媛
(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文章通过实地调查,试图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围绕闲暇展开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媒介贯穿其中的角色与功能。研究发现,媒介之于闲暇的意义不仅是娱乐需求的满足,更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闲暇融入现代化生活方式、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价值工具。而闲暇之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意义,也不只是提供娱乐和休憩,而是存在着生活方式选择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层含义,它与其城市适应的能力与进程密切相关。因此,只有依靠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传播实践,才能不断构建出一个属于他们自身的新生活世界,并在这样的新生活世界中逐渐实现身份再造,从而促进其城市适应。
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城市适应;媒介化体验
一 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
休闲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作为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的新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再以“赚钱”作为外出务工的唯一内在动力,他们更渴望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享受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服务、精神文化,并寻求个人发展,实现人生价值。与城市同龄人一样,作为青年一代的他们也渴望现代化的休闲方式,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而农村相对落后的生存环境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高度发达、交流频繁的城市媒介环境为他们打开了通往精彩世界的一扇门。
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等领域,传播学则极少介入。早在2005年,朱力就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他提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1],认为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折射出的就是他们在文化心理层面的适应程度,健康科学的闲暇休闲生活会使他们的身心得到休息、心理得到慰藉、精神得到愉悦,会对所在城市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2]。
在现有研究中学者马纯红近年来的成果相对集中,除了系列论文,她的两部著作《农民工闲暇生活与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与《他乡的“他者”:一项关于农民工闲暇生活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都对农民工的闲暇生活问题给予关注。前者在深入调查农民工闲暇生活现状的基础上,深层次地剖析了农民工闲暇生活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对城市社区文化与农民工闲暇生活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3];后者采用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民族志文本”的建构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日常闲暇生活方式,归纳其闲暇生活模式,并提出了以社区为支撑的构建文明型农民工闲暇生活方式的主要路径[4]。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特征进行了数据分析。如一项基于北京市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证研究发现[5],其精神文化生活呈现:“个体性较强,社交性不足”的特点,较低的经济收入与结余,较长的工作时间和较高的工作强度,业缘为主、范围狭窄的人际交往成为制约该群体精神文化提升的主要因素。郭星华等通过问卷调查比较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闲暇方式的不同[6],指出他们闲暇生活匮乏的原因在于工作时间过长,工资较低以及社会网络的限制。何华莉以安徽合肥农民工为例[7],指出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具有生活模式的同质性、闲暇时间的不足性、闲暇活动的单调性和消极被动性、闲暇空间的封闭性、闲暇心态的无奈性等具体特点,在类型上则基本上是消遣娱乐型和闲呆型,社交型和提高型几乎没有,即他们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闲暇,更多的是为了恢复体力和打发时间。而其他研究结论基本类似:即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时间缺乏,闲暇活动形式少、层次低,交往方式单一乏味,闲暇生活满意度不高,缺乏闲暇的幸福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休闲生活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的研究成果的突破和创新还有所欠缺,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待提高。首先,就现有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的研究而言,多数研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并通过对闲暇生活方式的三个要素入手(即闲暇时间、闲暇内容、闲暇心态),以丰富的定量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最终得到其闲暇生活的基本概况与存在问题。这样的研究套路一成不变,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大同小异。这种过于笼统和单一的研究路径往往容易将农民工抽象化,我们只会看到一组组统计数据的推导和证明或理论演绎的结论,而看不到具体的、活生生的农民工形象。其次,多数学者对于农民工闲暇方式的关注主要还是针对上一代农民工的研究,而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且忽视了这一群体的内部分化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特点与变迁。
特别是在当今各种媒介已经渗透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媒介化社会,媒介与闲暇生活的关系开始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并且成为大众闲暇生活的主要形式甚至全部内容。媒介之所以能在闲暇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关键在于它既为我们提供各种关于生活的有用信息,帮助我们安排日常生活;同时还为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提供丰富的资源,尤其是随着整个社会媒介化程度的日渐提高,大众闲暇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加。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作为缺乏物质和文化资源的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很难像城市居民一样拥有丰富多元、随意自由的多种闲暇活动。此时,媒介作为一种廉价易得的工具与其闲暇生活的关系则更加紧密。
在媒介的引导和助力下,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在进城前后及与老一辈相比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必然会对他们的生活状态、心理态度以及城市融入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于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围绕闲暇展开的日常生活实践、闲暇意义的实现以及媒介贯穿其中的角色与功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基于传播学的分析视角,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及其变化的描摹,关照这一城市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与传播实践,试图将媒介这一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嵌入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来探究媒介贯穿其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关注其对他们的身份转变和城市融入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目前,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界定不尽一致,王春光于2001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8],并在2003年将其修正为两层含义[9]:一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差别;二是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务农经历较少,而外出动机发生了根本性转向。200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
本研究主要根据出生年代对新生代农民工做了界定,因为当前距离王春光提出这一概念已经有十多年时间,当时研究所指的第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如今已过而立之年,正在从新生代向中生代过渡,因此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涵盖最老的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不断更新换代的最年轻的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1995年以后)。也就是说,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到36岁期间,户口还在农村,又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相继到城市打工的青年农民工。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资料收集的需要,本研究主要采用以深度访谈为主的实地调查方法进行了研究。课题组自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以志愿者的身份适度卷入新生代农民工青年群体的工作场所或日常生活,进入“现场”,参与他们的生活情境,感受他们的生活氛围,并与被访者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在历时两年的调查中,课题组成员主要通过商场、超市、餐厅、奶茶店、理发店、美甲店等消费场所,还有KTV、网吧、台球室等休闲场所以及工厂、建筑工地、农民工聚居区等空间或渠道观察和访谈了不同进城时长和职业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另外,考虑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非常频繁地接触网络等新媒体,他们多数都有QQ、微信、微博等交流工具,并且相当活跃,甚至存在新生代农民工QQ群、微群等网络抱团现象,由此切入进行网络访谈,也是一种可行的资料来源。
本研究中大部分的访谈对象基本上是采取滚雪球的方法获取,多数目前在南京工作。南京作为长三角地区的大型城市,吸引了众多来自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四川等地的农民工。期间共访谈了来自上述不同地区、不同场所、不同年龄、不同进城时间、不同职业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30多名。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状况、媒介接触与使用状况、城市融入与适应状况以及媒介化体验在改变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乃至城市适应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等。
三 研究发现与结果分析
如前文所述,当我们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时候,一个不能忽视的变量是他们所身处的信息社会环境及其丰富的传播实践。随着传播媒介在新世纪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信息化过程已由20世纪90年代精英垄断或横向的局面进入更广社会内信息中下阶层和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紧密结合的新阶段[10]。尤其是草根群体以其庞大的基数已经成为中国新媒介技术的实践主体。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领域,复杂的城市媒介系统也为其带来了多元的体验。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娱乐消费工具,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闲暇中扮演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娱乐功能。但基于媒介的相关体验不止于此,除了基本且表面的媒介使用与接触,不同的媒介工具还可以分别从功能和心理上基于其闲暇以替代式的体验,使缺乏物质和文化资源的新生代农民工得以享受另一种满足。而且超越娱乐的媒介化体验还在于其建构体验,因为媒介不仅通过提供多元化信息,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觉意识,利用闲暇生活寻求自我发展的契机;而且他们也依托媒介实现其在城市中人际关系网络的建构,使得闲暇活动与媒介利用融为一体,为其城市生活的逐步适应与顺利融入奠定基础。
(一)媒介使用体验:基于日常娱乐生活需求的消费升级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媒介化体验的最基本层面就是媒介的使用体验。从农村到都市,他们所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对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从小成长在不太发达的农村,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对他们而言,童年玩乐更多的是与自然、同伴相处,媒介在其生活中是相对陌生与可有可无的一部分。根据对多数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可以发现,他们在进城之前的闲暇生活比较单一。来自安徽肥西农村的孙某(1987年出生),在南京某高校食堂工作,他表示“以前在家里,空闲的时候一般都出去玩儿,跟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们去捉龙虾、钓鱼之类的。”同样来自安徽六安农村的理发师郭某(1985年出生)也承认“在家的时候没什么玩的,去外面玩得比较多,不怎么在家,主要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
因此,当他们离开信息相对闭塞、生活节奏缓慢的农村,第一次与光怪陆离、繁华多姿的城市媒介环境相接触,初来乍到的他们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他们的城乡流动恰恰遭遇了城市媒介发展最为迅速的20年,媒介早已深深嵌入其城市轨迹和生命历程中,在城市生活的潜移默化之下,他们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休闲娱乐方式,媒介开始成为其闲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农村闲暇时间去捉龙虾、钓鱼的孙某现在的休闲方式就是围绕媒介展开:“我偶尔看看电子小说,网络小说那种,看看就睡觉。有时候看电视,住的地方有一台电视。上网的话就上上QQ聊天,还有就是看看空间之类的。看新闻的话我就在手机上看看腾讯新闻,偶尔听广播。”前文中的郭某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普遍认为进入城市后接触媒介更多、更频繁。
对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种转变并不像80后那样剧烈,因为他们生长的农村环境与80年代相比还是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大众传播媒介的触角开始延伸到农村,不少家庭也开始接触电视、广播等媒体,村里甚至已经开始出现网吧、卡拉OK等娱乐场所。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成长在媒介快速发展中的一代。例如出生于1997年的小晴,来自江苏泗洪农村,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她说“以前在家空闲时间我一般就会跟朋友出去玩,逛街或者去KTV唱歌,要不然就在家看电视、上网之类的。” 同样是90后,小晴的同事,来自安徽和县的小姚基本也是如此,“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比较宅,一般是待在家里看电视,或者跟朋友打打羽毛球。”
尽管如此,城市媒介环境的复杂多元仍然与农村有着天壤之别,媒介种类更加繁多,媒介技术更加发达,媒介接触也更加便捷,因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现在的闲暇生活更是与媒介使用密切相关。说起下班后的闲暇生活,小晴告诉我们:“看电视的话,我都是连无线网把电视剧下到手机上然后回去看,喜欢看《来自星星的你》,太流行了,我们都在看,我还在看《江南四大才子》。以前还经常看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还特别喜欢看一个真人秀节目,叫‘变形记’,觉得特别好看,特别感人。上网一般都是用手机,就是上QQ空间看看朋友的动态,或者聊聊天,要不就是玩游戏,看到朋友发的好一点的文章什么的,就转发一下,赞一下。喜欢在网上看娱乐新闻,关于明星的,还喜欢百度一下他们的照片。”一旁的小姚也补充道:“现在比原来上网多了,电视的话喜欢看电视剧,前段时间在看《需要浪漫》,现在在看《来自星星的你》,只要好看的剧我都喜欢看,都是下载下来用手机看。综艺呢,去年看了一年的‘快乐大本营’,以前看‘百变大咖秀’,还有相亲类的‘我们约会吧’,‘非常完美’啊,都看过。”从这些访谈资料可以明显看出与80后相比,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能够更快地掌握不同的媒介使用技能,享受不同的媒介带来的丰富娱乐内容,也能够迅速地跟上大众流行文化的步伐,在媒介所承载和传播的城市文化中得到熏陶渐染。
从农村到城市,实际上也是生活方式的转型,这样的转型使休闲的本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保守的乡村社会,休闲活动多在户外宽敞的场地开展,更多是户外游戏;而在较为复杂的都市生活中,休闲生活更多在特殊的空间或者就在家里,更多的是室内游戏;在乡村,休闲的参与方式更多依靠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在城市,休闲更多意味着保持一定距离的欣赏或观看,会更多地依靠大众传媒;在乡村,休闲活动倾向于群体为中心;而在城市则倾向于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个人为中心。[11] 49这些变化都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主要表现在他们在农村的群体性、交流性、自然性的闲暇生活逐渐转变为城市中个体的、观察式、依赖于大众传媒的方式。
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就是以大众媒介为消费工具,以传播内容为消费对象。媒介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时间实现文化消费和享受最重要的工具,也是他们在城市面对离乡愁绪、面对生活压力、面对辛劳工作、面对他人排斥时所赖以调节情绪、排解苦闷、驱逐空虚和寄托情感的有力武器。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并满足娱乐需求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满足的过程,即使是媒介带来的短暂轻松,也足以给他们平淡的日子增添几抹亮丽的色彩,使他们在闲暇之余能够重新鼓起勇气,继续在适应城市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二)媒介替代体验:超越身份弱势与资源限制的补偿满足
在探究媒介在给个体闲暇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时,多数研究往往停留在第一层面,即仅把媒介视作娱乐化工具,甚至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少批判性的观点,认为随着信息社会媒介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媒介的娱乐化功能愈发满足人们对于闲暇的需求,而闲暇时间的安排具有互斥性,使用媒介的时间便替代了从事其他多样化闲暇活动的时间。长此以往,这种娱乐消遣便会增加人们的被动性,降低其审美情绪,转移社会的注意力,限制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但事实上,媒介在闲暇生活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止步于此,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具有鲜明特征的群体而言,媒介更为其在城市的闲暇生活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替代性体验,使缺乏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他们实现了另一种满足。
首先,由实地调查可以发现,对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无论他们处于哪个年龄层次,看电视是他们打发闲暇时间的首选,这一点从上文所引用的实证材料中也可以发现。由于看电视作为一种随意休闲活动,它对注意力、技能要求和人际交往的强度要求均处于较低水平。于是,看电视这种闲暇活动的上述特点也使得它容易成为一种大众化的闲暇娱乐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农民工群体的偏好。但是另一方面,看电视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也许是一种无奈却明智的选择。
从社会认同的角度看,他们相对于城市居民依然属于弱势群体,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程度都比较低。从个人认同感角度看,他们仍然是“外来群体”,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中低阶层。这种角色认同增加了他们自我评价不高、自我效能感下降的可能性。再加上看电视这种闲暇活动具有相对高的可即性和相对低廉的费用两个特点,对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要求都不高。而且电视媒介具有声像并茂、视听兼容的优势,容易使观众产生真实感、现场感和参与感。同时,在选择电视节目内容时,电视剧往往是他们的偏爱。这也是因为他们在观看电视剧时,对这类结构性文本的不同解读方式会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体验。例如角色体验,他们在观看电视剧时,可以暂时逃离原有角色的束缚,而体验剧中的某个角色,分享这个角色的各种感情和经历。又或者他们通过看电视剧参与到一种“超现实的社会互动”中,即让自己卷入剧中,与剧中的角色互动,这种互动也许是现实世界中暂时无条件实现的。电视剧虚构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环境,在收看时,他们可以逃避现实厌倦的环境,而进入剧中不一样的世界。[12]
其次,在电视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替代性体验之外,如今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的爆炸式发展更是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功能性替代体验。这一点在手机这一融合性最强的媒介身上表现尤其明显。手机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所带来的替代性体验主要在于它所承载的功能性应用的出现。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尤其是高速宽带无线网络的快速覆盖和智能终端的快速普及,极大改善了手机应用程序(APP)的用户使用体验,因此这一市场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姿态。几乎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APP应运而生,正逐渐渗透到消费者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媒介技术的发展也深深地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和改变着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他们对物质、文化资源占有度较低,经济资本也比较缺乏,频繁地出入城市中琳琅满目的娱乐消费场所显然是一种奢望。但作为年轻人的他们又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渴望能够接触多种娱乐方式,体验繁华都市精彩迷人的休闲生活。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较轻,学习能力较强,媒介素养也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所提高,他们能够比较快速熟练地掌握智能手机和众多APP的应用。
因此,功能繁多的手机APP软件便以廉价便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生代农民工对闲暇活动多样化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享受。比如来自安徽滁州农村的小宋,1994年出生,目前在一家水果店做服务员,她说:“我还挺喜欢唱歌的,以前挺喜欢用唱吧这个软件,我听朋友说这个好用就下载了,我觉得挺好玩的,里面好多人唱歌太扯了,那天我听里面一个小女孩唱歌几乎全部都跑调了,太好玩了。虽然这个软件不能完全代替去KTV那种大家一起玩儿的氛围,但是有时候在里面唱唱歌听听歌还挺能满足我唱歌的欲望的。”比小宋小三岁的安徽女孩瑞瑞,在南京一家餐馆才做了一年的服务员,她也表示:“我经常用手机玩游戏,比如说闯关者啦,还有节奏大师,我都打到200多关了,我妹妹特别喜欢玩,我看她玩的好玩就下载了,刚开始觉得没意思,后来看朋友圈的人都玩,他们玩得分数特别高,我就想超过他们,就使劲玩使劲玩,觉得特别过瘾。玩这个很方便,空闲下来随时都可以玩,又不用花钱,比去游戏厅或者什么电玩城好多了。”
诸如此类的手机替代性功能还有很多,这些花样百出的APP也极大地丰富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为他们备受时间和金钱所制约的闲暇时光带来另一种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中充当的角色并不只是纯娱乐化工具,虽然它最基本的功能确实在于提供娱乐,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城市中相对弱势的群体而言,它意味着一种心理的慰藉,一种资源的补偿。
(三)媒介建构体验:源于传播实践和文化自觉的价值创造
从本质来看,媒介使用体验和媒介替代体验更多还是停留在媒介的工具性层面,即媒介以何种方式、何种内容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以娱乐需求的满足。但媒介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媒介环境带给他们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他们对未来世界和生活的想象、思维方式甚至个体意识等基本都是通过媒介来建构。在这样的媒介建构体验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青年人所特有的文化自觉意识得以激发,从而引导他们去利用媒介在闲暇生活中超越娱乐本身,获得自我发展。
前文中的孙某与女友一起在南京某高校食堂的早餐窗口工作,十六岁离开家乡外出闯荡的他开始在昆山一家服装厂工作,后来自己到北京,先给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创业,弄了十几台机器加工服装,现在则是完全为了女友而临时到南京工作。他的大部分闲暇活动与他人并无太大区别,但是早年的创业经历使他一直心怀创业理想,渴望通过自己创业闯出一番天地,因此在自己休息的时候,他会选择花一些时间在上网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我以前上网经常看李强老师的创业讲座的视频,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特别有道理,听得我心服口服,而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还是很实用的,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那会儿做得很盲目,下次我再创业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确实学到很多东西。”
除了创业,也有人希望利用网络帮助自己进一步学习深造。比如来自陕西宝鸡的90后姑娘曹某虽然生活安稳,但她自己对目前的生活有满意也有不满意,“满意的是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简单,比较安稳,没有什么钩心斗角,但待遇方面我一点都不满意,因为工资实在是很低,而且我跑这么远,除了这边的人比较好以外,就没有其他值得留恋的,至于升职什么的,就没有任何发展的空间。”因此在工作之外她也时常在寻求着突破的空间,“我一直想参加成人高考,因为我特别在乎我的学历,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实践,经常去网上查,也了解到一些这方面的信息,我看到南大很多学院就提供成人高考,我觉得这倒是个机会,我可以一边在这里工作一边去上这个。我觉得有必要给自己充充电。”
孙某和曹某的情况主要是他们本身有着自我发展的意识和需求,又有使用媒介搜寻特定信息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所以他们利用闲暇时间以互联网为依托,在有用信息的指导下寻找着发展契机。同时,也存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意向,而是在媒介所提供的多方信息引导下产生了特定的灵感和想法,也就是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世界的认知,并依据媒介传播的信息来指导现实生活。
例如前文中刚来到南京不久的打工妹小晴,现在的她只是餐厅一个小小的服务员,年龄尚幼的她对生活也没有过多的想法,但说起自己想趁业余时间学习什么东西时,她这样表示:“我想在自己业余时间的时候学一些手艺或者技术,比如说美容化妆之类的,或者做甜点蛋糕什么的。我觉得这两个都挺好的,你看电视里好多广告都是关于美容化妆的,这个手艺应该比较实用。做甜点蛋糕是因为看到电视剧里开这种店特别惬意,很小资,喜欢那种感觉。”这样的想法看似是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但这种梦境却是媒介所描摹和建构出的,可见媒介对其观念影响之大。而且事实上,她和小姐妹们也经常通过网络搜索如何化妆的视频进行学习,希望以后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如此看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对乡土文化的依恋和固守,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市具有更强烈的文化自觉,也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文化自觉所引导的是媒介自觉。首先,他们的闲暇生活会受到媒介内容的深刻影响,除了娱乐之外,这些信息也建构了他们对城市、对生活的认知,以及对自我实现的渴望;其次,在这种心理期望之下,他们能够凭借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利用媒介去搜寻有益于自身学习的知识、信息,在工作之外不断寻求着自我发展的契机。
同时,在建构个体的思想与认知之外,媒介还具有建构社会关系的功能。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比较丰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丁未关于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的研究。传统的社会学观点一般认为农民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如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13]而丁未则以一个典型流动人口聚集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致描摹都市里村庄所特有的媒介基础设施和以互联网和手机为现代通信技术和新媒体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展示了在全球化的网络社会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农民工群体以中低端媒介技术工具,按照自己的需求甚至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媒介化社会关系和传播实践。[14]
但不同于丁未以地域片区为框架自然形成的群体为研究对象,本研究所访谈的对象散落在城市中的单独个体,但他们也同样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互动和传播实践组成一个个小规模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网络,而且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则是与媒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或首先通过媒介的虚拟交往形成关系,然后从线上发展到线下。如来自安徽肥东农村的丁某,1994年出生,目前在一家餐馆工作,她在南京结交新朋友的经历便是如此:“在这边的朋友都是新交的,要么是一起工作的,要么通过一些软件认识的,比如说微信啊QQ啊,群里那种的。然后私下或者在群里聊得多了就一起出去玩玩啊吃吃饭啊,认识的人多了就感觉周围的信息量比较多了,比如他们在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感兴趣的事情他们都会跟你分享,有些就会对我有启发。”也有先在实际生活中形成关系,进而通过媒介交流巩固加强。如前文中的郭某,在闲暇时间经常与朋友相聚:“在南京的朋友基本上都是靠这样认识的,在一起吃饭唱歌的时候,朋友介绍朋友,慢慢地就成了圈子。不只是老乡,但圈子里的朋友多是南京郊区的或者其他外地的,多数也是理发圈子的。我们聚得也蛮频繁的,基本上半个月都会来一次吧,不是同一批人,会跟不同的人出去玩,基本上都是以前在那些店里的朋友叫,然后他们会带他们身边新的朋友,就能玩到一起,就互相加了微信以后再一起约。”
综上所述,媒介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建构体验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介提供的多方信息建构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生活和自我的认知,在媒介内容的引导下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得以激发,促使他们在闲暇中不只是追求娱乐,而是凭借主观能动性以媒介为依托寻求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媒介作为交流传播手段还同时建构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在城市孤单无援的他们能够建立起自己社交网络,并通过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得以巩固和维系。这样通过闲暇活动拓展关系网络的自觉性也使得他们能够接触更多的信息,获取更多的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慰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需求。
四 结论与讨论
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进程中,媒介以其丰富的功能带给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多元化的体验,在其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媒介之于闲暇的意义,不只是充当文化娱乐消费工具,它更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闲暇融入现代化生活方式、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工具。而闲暇之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意义,也不只是提供娱乐和休憩,而是存在着生活方式选择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层价值,它与其城市适应能力与进程密切相关。在这样的闲暇与传播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也正是在不断构建着一个属于他们自身的新生活世界。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只有依靠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传播实践,才能充分发挥媒介与闲暇生活互动的价值效果。
(一) 媒介化体验:从娱乐工具到闲暇价值的拓展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乡流动恰恰遭遇城市传播环境急剧变革的时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生存、适应等种种生命历程都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媒介已经深深嵌入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城市体验中,极大地影响和塑造着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因此,在考量他们的城市适应能力以及衡量城市适应程度的种种因素时,媒介都是一个贯穿其中、不容忽视的变量。
最显而易见的关系在于,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媒介为其闲暇生活提供娱乐和休憩,是他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文化娱乐消费工具。这是最基础的层面,也是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闲暇生活能够达致的层面。对多数80后年龄稍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童年闲暇记忆往往带有原生态色彩,大众传播媒介还尚未完全进入他们的生活。而多数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从小享受大众传播媒介带来的便利。尽管如此,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的渗透也比较有限,除了广播、电视保持着较高的普及率之外,农民对于报纸、杂志、互联网的采纳程度不高。因此城市复杂多元的媒介环境所带给他们日常生活的冲击是比较巨大的,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城市同化,被媒介塑造,尤其是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的普及和发展,对其闲暇生活方式的影响十分巨大,手机已经成为他们打发闲暇时间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除却这一层面的意义,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功能的多元化也使得媒介的这一功效发挥更加彻底,成为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替代性满足的一种工具。以看电视和智能手机APP为例,观看电视能够基于在城市中缺乏物质和文化资源的他们一种心理上的替代式体验,而智能手机所承载的花样繁多的APP则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替娱乐消费场所的某些功能,从而丰富了他们的闲暇体验。当然,这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媒介作为娱乐工具的体现,是伴随着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得以不断拓展的工具属性。
当然,众所周知,媒介的一大功能就在于提供娱乐,这种功能不管对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对城市居民都适用。但媒介之于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的娱乐意义更加在于,他们是一个在城市缺乏种种资源的群体,也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经济能力和宽裕的时间去拥有与城市居民无异的闲暇生活。而媒介以其廉价性、便利性、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媒介在其闲暇生活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与城市居民相比,更为重要。
以往研究多停留于此,但媒介之于闲暇还有更加深刻的第二层意义,它更有着使闲暇生活价值化的深层功用。但这并不是所有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够达到的层面,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只要利用媒介打发空闲时间获取简单娱乐即是闲暇生活的全部。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群体中具有更加敏锐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更加强烈的自我发展需求的部分。一方面媒介内容的传播会给具有文化自觉的新生代农民工以观念引导和信息支持,使其在工作之余主动寻求突破自我的契机;另一方面,媒介作为交流沟通的手段还建构了其在城市的社会关系,人际传播与媒介的互动使人与媒介结成相互关联的网络。当然,媒介价值化功能的实现需要以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媒介素养和主观能动性为基础,媒介本身只是客观的存在,如何利用则是依靠人的主体性。所以说,人与媒介也是不可分割的,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依靠媒介编织了自我的日常生活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全方位地渗透其中,带给他们愈发丰富多元的闲暇体验。
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的密切联系的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全面媒介化。作为被时代发展所裹挟的一员,新生代农民工自然也不能避免。在他们所移居的城市媒介化的过程中,自身也成为被媒介深刻影响的“媒介人”,尤其是其闲暇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所感官、信息等多方体验都是被媒介化的,媒介带给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直观体验,而是被媒介化的体验。这种媒介化体验融入闲暇生活之中,是重塑其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变量。
当然,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媒介不是万能的,媒介只是促使其个体化的其中一个要素,需要与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嵌入与交织,才能促成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媒介不应被忽略,也不应被夸大,我们要做的,是正确认识传播的力量,并恰如其分地将其展现。同时,媒介的作用和价值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关键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毕竟媒介自身是固定不变无生命的器物,只有仰仗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建构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依靠他们更加敏锐的文化自觉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传播实践,才能达到工具与人的完美契合,才能充分发掘和利用媒介作为一种资本和价值化工具的效果。
就目前而言,使用媒介进行娱乐已经是普遍存在的现状,而利用媒介创造价值则是一种未来的趋势,这样的变化将会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媒介素养的提高和城市适应程度的加深而变得愈加明显。他们对闲暇时间的有效利用,对媒介功能的充分运用,不但决定着他们闲暇生活的质量和层次,也决定着他们未来的自我提高与发展,也更加决定着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融入程度。
(二)新生活世界:从媒介赋权到闲暇意义的实现
闲暇不仅是人们调剂精神、丰富生活内容的一种手段,更意味着一种生活选择和自我实现,个体的自我表现充分反映在他们对闲暇活动的兴趣和对知识、信息的追求上。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以往的研究总是先入为主,概而统之地将他们的闲暇生活预设在最基本的娱乐层面,而没有考虑到其实他们中的某些个体也有通过闲暇进行生活选择和实现自我的意愿。他们在城市的多元传播实践构成了其日常闲暇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实践也是一种对自己愿意接受并有所体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虽然根据本研究的实地调查结果,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囿于闲暇时间的短缺、经济条件的匮乏等客观条件,闲暇程度相对于城市居民依然较浅,而且多数的传播实践也主要局限在利用媒介工具进行娱乐,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部分个体的闲暇生活已经达到较为丰富的层面,他们对于媒介的使用已经开始呈现价值化的趋势,从而把媒介变成有助于其适应城市生活的工具。
同时,闲暇与城市适应又是密切相关的。闲暇生活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状态直接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实践与认同,而生活方式上的适应则意味着其城市适应的第二个层面,即社会适应。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层面的交往和适应才能达到观念的转变,获得文化认同以及心理上的归属感。媒介作为一种中间力量,连接作为生活方式的闲暇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作用在于:多元的媒介化体验,如上网聊天、网络游戏、虚拟空间交友等城市化的休闲方式丰富了他们的休闲性娱乐活动和社交性娱乐活动,使他们的闲暇生活已经逐渐褪去乡村生活方式的色彩,初步呈现出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特点。而他们中的精英群体在满足了必要的物质生产生活需要之后,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也充分体现在他们的闲暇生活上。并且,媒介功能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的权利,扩大了他们能够自由选择生活的机会,使其在生活方式可以向城市居民趋近,从而缩短社会距离,弥合文化区隔。
总而言之,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传播实践构建的闲暇生活方式,实现向城市社会的逐步适应的过程,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生活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新生活世界也在慢慢建立。“生活世界”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意义则是主体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被给定的。简单来理解,人们的心理,无论是都市的还是乡村的,都无非涉及对生活世界的适应,也就是说,需要在生活世界中寻找一种确定的本体安全。吉登斯指出,本体安全的获得牵涉到日常生活的程式化和场所的区域化。日常生活的程式化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行动的标准和程式,使整个世界可以被理解、被解释和预期,从而使人们获得吉登斯所说的本体安全。[15]在这个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闲暇实践实际上时刻都在彰显着对城市生活世界的适应。从农村到城市,以闲暇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他们只有不断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模仿、靠拢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才能逐渐在城市生活世界中寻找到确定的本体安全,这是在城市社会获取安身立命的安全感的需要,也是彻底改变身份的需要。
但正如项飙所说,移民的流动“决不仅是人从厨房走到客厅的过程,也不仅仅是把厨房的稻草拿一些到客厅,把客厅的花瓶拿到厨房,在既定的结构框架下把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并置,而是要改建整套房子。稻草和花瓶不但被调换,而且花瓶不再是原来的花瓶,稻草也不再是原来的稻草。”[16] 511因此,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不断通过闲暇实践去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其生活世界不会成为与城市居民完全同质化的城市生活世界。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践既超越了原有农村生活世界的范畴,又不完全属于城市生活世界,这是一个他们所独有的新生活世界,一个伴随着他们的实践活动不断流动、变化的生活世界,他们在其中凭借自身的生活实践不断地促使着这一特殊空间的重建与整合,不断寻求着自我发展以期拥有更多的本体安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并不是简单地从农村到城市,生活被直接同化的单线条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走向也不是与城市居民完全无异的市民身份。新生代农民工复杂的流动体验、生命历程、情感波动、心理转变等都注定了他们在城市社会与众不同的独特身份。他们会不断通过实践去拓宽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世界,并在这样的新生活世界中逐渐实现新的身份再造,成为一种新型市民。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建构与赋权下的新生活世界整合与重建,是一个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城市适应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市适应的新空间和新路径。
[1]朱 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2]朱 力.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30-35.
[3]马纯红.农民工闲暇社会与城市社区建设研究[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7.
[4]马纯红.他乡的“他者”:一项关于农民工闲暇生活的文化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5]廉 思,陶元浩.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的调查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3(5):55-59.
[6]郭星华,胡文嵩.闲暇生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J].人口研究,2006(5):77-81.
[7]何华莉.城市农民工闲暇生活研究——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D].安徽大学,2006.
[8]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9]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5-15.
[10]邱林川.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5):71-99.
[11]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12]刘 娜.城市建筑业农民工闲暇生活方式研究——对武汉市建筑业农民工的实证调查[D].华中农业大学,2008.
[13]李培林.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42-52.
[14]丁 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5]李继宏.城乡心理和生活世界——从齐美尔到舒茨[J].人文杂志,2003(4):149-156.
[16]项 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0.
(责任编辑 魏晓虹)
Mediated Experience: A Study of the Leisure Life and Adaptation to C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ZHENG Xin,GAO Meng-yuan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
This study tries to describ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ounding around their leisure activities as well as media’s role and function which run through it by conducting field survey.It has foun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meaning of media to leisure is not only the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need for entertainment, but also a valuable tool for them to adapt to modern life style,promote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self-valu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aning of leisure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more than providing recreation and rest,in fact,it has deep implication in lifestyle choice and self-value realization,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ability and process to adapt to city. Therefore, only by relying on the workers’ awareness of their principal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ir communication practice with subjective initiative, can they continuously construct a new life world that belongs to themselves and reconstruct their own identities in this new life world,thus promoting their adaptation to city.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leisure life;adaptation to city;mediated experience
2017-01-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10BXW024)
郑 欣(1973-),男,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播社会学、乡村传播研究。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4.012
G206.3
A
1000-5935(2017)04-009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