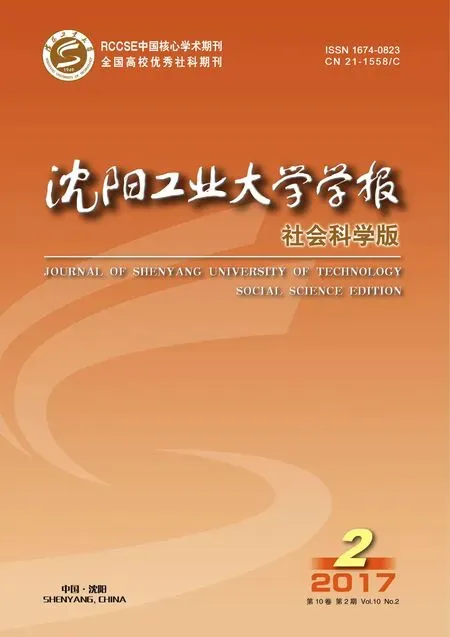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运行困境与破解之道*
吕中伟, 詹 亮(. 沈阳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 沈阳 0870; . 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 行政庭, 重庆 40500)
【民主与法】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运行困境与破解之道*
吕中伟1, 詹 亮2
(1. 沈阳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 沈阳 110870; 2. 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 行政庭, 重庆 405200)
“美丽中国”已然凝入中国梦的远大图景,但“一面是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一面却是令人胆寒的环境污染惨剧”的矛盾依旧严峻。作为对环境保护现实需求的立法回应,2015年《环境保护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既有规制基础上进一步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诉权主体予以明确,对诉讼范围予以拓展。然而,受制于一系列“原则规制”,其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清晰界定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与挑战,探寻环境公益诉讼由可能向现实转变的破解之道,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首要任务。
美丽中国;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法; 环境公益诉讼; 制度构建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专章论述,并首次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在“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当下我国正历经的一种新的、沉重的生存考验”[1]的严峻形势下,“美丽中国”的提出不仅代表着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执政能力的提升,更是对发展战略的崭新转变与生存语境的适时切换。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捍卫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递进式”尝试与回应,2015年1月1日生效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不但扩大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还进一步确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新修订《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 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自2015年1月7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明确了《环境保护法》第58条中的起诉主体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然则,现行立法仍然缺乏较为具体的制度设计,诸如没有较为完整全面的实体规范、缺失程序规则与保障机制等,使得新环保法构建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离人们期待或者理想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有一定的距离[2]。易言之,环境公益诉讼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会面临一系列困难问题,甚至遭遇既定模式所滋生的困境。
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
(一)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数量不足
2015年《环境保护法》规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这三个条件。首先,该社会组织必须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其次,该社会组织必须具有5年以上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经验;再次,该组织需无违法记录。然而,在我国2 000余家环保组织中,符合2015年《环境保护法》提起诉讼条件的仅有约300家[3]。易言之,2015年《环境保护法》虽然对提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条件作出普适性规制,但当前能够满足既定条件的社会组织绝对数量过少,平均到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足10家。即便是符合既定规制条件的约300家社会组织,亦会因经费保障与主观意愿限制而进一步限缩“实质履职”权利主体的数量范围:据相关协会的调查,我国81.5%的民间环保组织筹集的经费在5万元以下[4]。相较于高昂的诉讼投入(如2013年海南启动1起公益诉讼,仅诉讼费就需10万多元[5]),其所持经费便显得捉襟见肘,尤其是在具备丰富诉讼经验与能力技巧的法务人员严重缺失的条件下,环保组织基本没有能力提请环境公益诉讼。如此,在符合既定条件主体绝对数量较少、社会组织经费不足等多重因素交织下,实际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寥寥可数,近几年提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多集中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自然之友等少数几家较有影响的环保组织便是最好的佐证。
(二)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尚未明确
环境公益诉讼是崭新的诉讼形式,是“例外诉讼”“高尚诉讼”[6],“具有不同的内容,有民事公益诉讼,也有行政公益诉讼”[7]。《民事诉讼法》第55条已经确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甚至是作为其上位概念的行政公益诉讼)并未得到2015年《环境保护法》的直接确认,备受关注并于2014年11月1日审议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亦未涉及行政公益诉讼。如此,围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一场“无硝烟的论争”便悄然兴起,该论争主要围绕2015年《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否可以作出扩大解释,即该行为是否应当包括行政机关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渎职行为与不作为,如“行政机关违法履职、怠于履职等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行为”。诚然,即便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备其规制必要性与实施价值,且当前既有的法律规制未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出明确排除,然则受制于当前立法的原则呈现与相关司法解释细化规制的缺失,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尤其是涉及环境抽象行政行为的公益诉讼能否提起仍处于“豁然状态”。
(三)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特有审理规则缺失
无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抑或2015年《环境保护法》均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留存困境,即“是继续援用传统‘私益诉讼’的审理规则,还是另行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有审理规则”。此问题引发了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与探索,作为对此既有困境的现实回应,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7日起施行《司法解释》。该解释共计34条,分别从起诉资格、管辖范围、起诉条件、公益私益界定、举证责任分配、诉讼费用负担、法院调解等方面细化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程序。然则,基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实践需求,同时借鉴域外的立法与司法成果,该司法解释对既有法律的解释(尤其是2015年《环境保护法》)过于狭隘:一则,该司法解释过于重视事后救济而忽视预防性救济,从而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排除在外。二则,该司法解释未对2015年《环境保护法》第58条“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的行为性质作出明确界定,形成对“该行为是否包括行政行为”之论争的放任。三则,该司法解释排除禁止令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四则,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诉讼请求或者环境责任承担过于民法化,明显缺乏环境保护的“法质”。五则,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司法救助程度不够,容易压制或者抹杀提请环境公益诉讼潜在主体的诉讼意愿。最后,该司法解释涉及裁判效力的规定明显缺少扩张性,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
(四) 司法制度内生性障碍依然存留
司法改革实现了对传统司法制度的局部性修补,伴随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的出台,司法体制启动新一轮的深化改革,然则其效果虽初现,但长期以来民事诉讼制度中的内生性障碍并未彻底清除,还广泛存在于立案、审理、判决等过程中。
1. “司法地方化”的束缚犹存
“在现有司法体制的制约下,各级人民法院的人事、财政大权往往掌握在同级政府手中。”[8]即便是现有法院人财物由省级统管的改革规制,亦可能是对地方化制约主体的等级上移,未必能根除其束缚。环境公益诉讼中,法院可能沦为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被告的纳税大户或者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地方利益的保护者,裁判过程中依据的选择与运用呈现由法律向特定地方利益与地方领导意志的自然流转,其结果是“不同的法院适用不同的法律标准,相似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有着不同的判决结果。”[9]
2. 环境司法专门化程度不高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指“国家或地方设立专门的审判机关(环境法院),或者现有法院在其内部设立专门的审判机构或者组织(环境法庭)对环境案件进行专门审理”[10],并非一种全新的司法现象,而仅仅是司法专门化的新发展。早在1988年,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设立专门环境法庭的建议,虽最终未得到支持,但却为环境司法专门化提供了指引。2014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当然,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仅仅满足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硬件专门化的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其亦应推进诸如司法理念、审判体制、诉讼模式的软件专门化,实现“硬件+软件”专门化的双向聚合。同时,受制于各级法院对环境司法专业化重视程度不同及其所属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环境司法专业化的硬件与软件建设亦呈现出不平衡性及差距的动态性扩展。
3. 案例指导制度有待加强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及环境资源审判的典型案例尤其是涉及环境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数量严重不足,仅于2014年7月3日公布了9起涉及环境资源审判的典型案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9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件分别是:1.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与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水污染责任纠纷案;2.聂胜等149户辛庄村村民与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3.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与蒋荣祥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4.重庆市长寿区龙河镇盐井村1组与蒙城县利超运输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5.朱正茂、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江阴港集装箱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6.张长健等1 721人与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7.姜建波与荆军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8.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无锡市蠡湖惠山景区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9.王仕龙与刘俊波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2015年12月29日公布了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件分别是:1.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2.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3.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4.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5.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6.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7.梁兆南诉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8.周航诉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9.吴国金诉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10.李才能诉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粉尘污染责任纠纷案。。这些典型案例虽对诸如“单一审理程序模式不能满足环境资源案件审判需要,行政权力配置与生态系统割裂致跨区污染不易解决;污染者拥有信息资金和技术优势,原告不易收集证据”等问题均有所涉及,但仍然停留在局部探索层面,并未真正具备普遍的参考与指导意义,且这些典型案例中涉及社会组织提请环境诉讼的主体均系中华环保联合会,呈现“形式垄断”。
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一) 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的巨大威胁。不同样态的环境纠纷问题集中爆发,其中亦潜存着巨大的环境公益诉讼社会需求。相较于此,法律规制框架下提请环境公益诉讼“实质履职”的权利主体供应却呈现量与质的双项短缺,因此应明晰并拓展环境公益诉讼的作为主体,以激发环境公益诉讼的生命活力。
1. 明确界定“法律规定机关”的范围
当前,现行法律中除《海洋环境保护法》*2013年12月28日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对提请环境公益诉讼的“机关”作出明确规制外,其他法律尤其是2015年《环境保护法》并未对“法律规定的机关”作出明确规制,以致环境行政执法部门与检察机关能否提请环境公益诉讼仍然停留在论争状态:一则,具有环境保护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能否作为环境公益诉讼提请主体?单从操作层面,虽然“法律规定的机关”在短期内作为提请环境公益诉讼普适主体的可能性较小,但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具备与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同样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环境行政执法部门”作为环境公益诉讼提请主体具备以下优势:一则,赋予具有环境保护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是对其环境监管、环境行政处罚等行政手段的“司法手段”补充,由行政手段向司法手段的过渡即是由“行政机关主导的执法方式”向“司法机关主导的新型执法方式”的转变。二则,赋予具有环境保护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能够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化”优势,诸如证据调取、环境监测等。三则,赋予具有环境保护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仅仅是其履职形式的扩充而非一种新形式的建立,投入成本较低而成效颇高。。当然,此项资格的实现应予以严格限制,即“在穷尽处罚、限期治理、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手段后仍不足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情况下”[11]方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二则,检察机关能否作为环境公益诉讼提请主体?虽然“最高检察院曾经明确检察机关不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支持起诉、督促起诉等方式参与环境公益诉讼”,但是“检察院作为宪法授权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在公益诉讼中扮演角色”[12]确已成为各方共识,且司法实践中亦不乏检察机关提请或者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如山东省乐陵市检察院诉范金河污染案、广东省检察院诉新中兴洗水厂污染案等。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当然,对检察机关提请环境公益诉讼应予以适当限制,即“检察机关提请环境公益诉讼必须以公民或者相关组织的申请为前提;依职权径行提请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须以‘通过督促起诉、支持起诉等方式推动公益诉讼程序无效’为前置条件”。
2. “社会组织”的广义解释
2015年《环境保护法》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虽对提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予以拓展,同时明确将“通过诉讼以牟取经济利益的社会组织”予以排除,然则符合该项条件规制并实际实施诉权的权利主体甚少,因此,基于新法修订过程的目的倾向,即一审稿“社会团体”—二审稿“社会组织”—三审稿“有关组织”,应对“社会组织”作广义解释:一则,“社会组织”不应局限于环保社会组织,亦应包括诸如《基金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规定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二则,“社会组织”不应局限于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环保组织,而应逐步扩展至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企业法人”身份登记的环保组织。
3. “公民个人”诉讼主体的“渐次确认”
“环境的整体性和共有性决定了环境的普惠性和普损性,任何损害环境的行为必然对生存于环境之中的每个个体造成事实上的损害”[13],作为对公民个人公共环境权益的合法享有者与义务维护者的现实身份回应,应当赋予其环境公益诉讼之诉权:一则,赋予公民个人诉讼资格是否会真的导致滥诉困境?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特质决定了其对原告“诉讼能力”的潜在要求,诸如人力资源、财力支撑、庭审应变能力、公益性认知(或者“传统厌诉思想”转变程度)等,而能够具备以上软硬件标准的公民个人绝对数量甚少。其次,国外司法实践对滥诉可能性予以否定回应,如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发源地的美国,由公民个人提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即公民诉讼)仅占环境诉讼案件总数的极小部分;意大利、新西兰亦未出现在环境法院案件堆积的恶性膨胀;印度虽在制度设立之初出现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激增现象,但经适度调整后便实现正常运行。最后,公民个人提请环境公益诉讼在国内已有可借鉴的司法实践。公民个人提请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即蔡长海诉龙兴光水污染责任环境公益诉讼案不仅突破了公益诉讼主体限制,而且突破了利害关系的直接性限制,更是取得胜诉的积极结果。二则,赋予公民个人诉讼资格并非无条件的放任,而应设置适当的调适条件。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共环境权益,并非权利主体诉权的滥用,亦非执意与环境主管机关竞赛或者令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者难堪,因此,应对环境公益诉讼程序的启动条件予以必要调适:首先,诉前告知程序。即公民个人在提请环境公益诉讼之前应先以书面形式向主管机关告知相关事项,由被告知机关对所诉事项予以处理或者答复(以60日为宜),若被告知机关在规定期间内不作为或者瑕疵作为,或者未实施有效措施,公民个人便可以径直向法院起诉(法院亦应依法受理)。其次,利害关系范围界定。“无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还是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甚至任何人均有权获得原告资格”[14]。诚然,赋予所有公民个人以诉权资格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最终目标,然则受制于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缺陷、司法实践探索积累经验不足等主客观因素,对公民个人诉权主体的确认应呈现阶段性,即A阶段:确认直接利害关系个人的诉权资格,含能够证明损害公益的行为间接损害其合法权益的间接利害关系个人;B阶段:确认间接利害关系个人的诉权主体资格;C阶段:确认所有个人的诉权主体资格。当前,应对A阶段予以全面确认。
(二)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衡平发展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同居于“一体两翼”的地位,其中的一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得到法律明确规制,而另一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却被搁置,因此,为保证“一体”(环境公益诉讼)的结构完整性与功能均衡度,应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现行法律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然未置可否,但却留存了默许空间,即2015年《环境保护法》并未对环境公益诉讼可起诉行为作出其为民事行为的唯一界定。易言之,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予以确认:一则,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予以拓展,即行政机关因行政决策、行政审批等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损害公共环境权益的法定后果的,应当对其提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同时,考虑到基于环境公权特性的环境抽象行政行为较之环境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对公共环境权益造成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损害,亦应将环境抽象行政行为(尤其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则,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请主体范围应突出相对性,即除环境公益诉讼合法诉权主体(国家规定的机关与社会组织)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民个人主体应限于行政相对人范畴,且其合法权益应处于事实上的损害状态,即“只要利益代表主体的权益受到了实际侵害即可成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15]。三则,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保护或者调整利益范围的广义界定。通常意义上,行政违法或不作为或瑕疵作为对公共环境权益的损害被理解为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即狭义环境人格权),如环境自然资源的财产性损害、资源的生态性价值损害等环境要素的损害与传统意义上的人身财产损害等,然则其并未将如环境审美、娱乐消遣等非经济利益(或者单纯的精神享受利益)纳入保护或者调整的范畴。依据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应将诸如环境审美、娱乐消遣等非经济利益(或者纯粹精神享受利益)纳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保护或者调整的范畴(即广义环境人格权)。
(三)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特有的审理规则
环境公益诉讼较之于普通诉讼具备公益性、技术性、较大社会辐射效应等诉讼特质,因此诉讼规则亦应突出其特殊性,即“排除对传统诉讼审理规则的继续援用而另行建立其特有的审理规则”:一则,管辖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必须交由公共环境权益遭受侵害地、侵害结果发生地及被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环保法院集中管辖。二则,诉权实现的地域限制。中华环保联合会等国家级环保组织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提起公益诉讼而不受危害行为与侵害结果的地域限制;其他环保组织与法律规定机关(如环保行政机关)提请环境公益诉讼应限于职权范围与所辖区域范围之内;公民个人提请环境公益诉讼应区分民事与行政,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公民诉权资格的实现应不受危害行为与侵害结果的地域限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公民诉权资格的实现应限于行政相对人所属辖区范围之内。三则,举证责任。鉴于公共环境的权益属性,应实行严格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不应因原告系国家机关、环保组织或者公民个人而予以区分。四则,诉讼成本与风险负担机制。一是诉讼保证金制度,即法院立案受理环境公益案件时,先由原告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即物质性约束),以保证原告参加诉讼过程的完整性。二是诉讼费用减免或诉讼基金制度。原告案件败诉时应对其诉讼费用予以减免,或者从环境公益诉讼基金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以抵充原告诉讼费用。五则,诉讼请求与责任承担。即环境公益诉求应摆脱民事诉求的同化,诸如摈弃恢复原状等脱离实际的诉求类型,突出环境保护的“法质”:一是禁止令之诉。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为防止公共环境权益遭受更大程度破坏,法院可以依环境公益诉讼提请主体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发布禁止令,要求对方当事人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二是损害赔偿之诉。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诉求可由原告提出,但是该赔偿金并非原告所有,而应统一划入由国家设立或者监管的环境公益诉讼基金账户。三是其他诉求类型,如给付之诉(含修复环境之诉)、撤销之诉、履职之诉等。六则,胜诉判决的扩张适用,即原告胜诉的案件同样对其他未起诉的适格主体产生既判力,而原告败诉的案件并不能因此而剥夺其他未起诉的适格主体的诉权。最后,环境公益诉讼不适用调解、和解(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与公共特性封堵诉权主体对公共环境权益的自由处分空间与可能)与反诉(为防止被告恶意诉讼指控下对公共环境权益的二次侵害)。
(四) 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破除司法制度的内生性障碍
“传统司法体制”留存诸多制约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内生性障碍,因此需要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一则,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司法审判组织以破除司法地方化的束缚,“鼓励各地法院探索设立以流域等生态系统或以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实行对环境资源案件的集中管辖”[16]。二则,全面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首先,坚持以实际需要为设立前提,在环境保护纠纷案件数量较多的地区设立环境法院,同时可以“以年受理百件左右环境案件为参考标准”在环境法院管辖区域设立若干环境法庭,集中审理各类环境与资源保护案件。其次,积极探索环境资源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归口审理模式,不断创新改革“二审合一”或者“三审合一”的集中审判方式以统一裁判尺度,保证环保案件质效。最后,提升环保法官司法能力,打造专业型环保司法。环保诉讼涉及诸如物理、生物、化学、医学等众多学科知识,且“二审合一”或者“三审合一”的集中审判方式势必要求环保法官具有较高的复合素养,如此,便需要环保法院遴选具备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士组成专家智库,并通过法定程序任命其为咨询专家、人民陪审员、专家证人等直接参与环保案件审理并根据其庭审身份行使裁断权。三则,完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案例指导与参考制度。首先,针对当前典型案例较少的现实困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建立各级法院环保公益诉讼案件推荐与定期报送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亦可主动收集相关典型案例,经过筛选、审核、讨论、发布最终确定为指导与参考性案例。其次,典型案例的发布不应限于以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或者联合原告提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而应不断向以其他环保组织、国家规定机关为原告或者联合原告,尤其是公民个人提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扩展。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的内容应积极回应现实需求(如诉权主体资格与受案范围的拓展、诉求形式的多样呈现等)或实践探索(如对环境审判“三审合一”形式的确认等)。
三、结 语
卡多佐曾言:“如果根本不知道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17]然则,我们既已厘清摆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面前的事实困境,且破解之道亦已呈现,接下来即是“充满智慧地前行”。
[1]颜运秋,李明耀.“美丽中国”语境下塑造环境公益诉讼立案机制之策略 [J].法治研究,2014(7):49-52.
[2]王树义.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司法改革 [J].中国法学,2014(3):69-72.
[3]常纪文.环境公益诉讼需解决八个问题 [N].经济参考报,2014-09-03(3).
[4]王社坤.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及作用 [M]//晏晓东.中国环境法治:2013年卷(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64.
[5]刘毅.环境公益诉讼门槛高 专家呼吁给更多民间组织授权 [N].人民日报,2013-12-14(4).
[6]徐祥民.环境公益诉讼的若干问题 [M]//吴锦标.黄河口司法.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1-9.
[7]关庆丰.行政诉讼法首次修改 12种“民告官”法院应受理 [N].新京报,2014-11-02(2).
[8]王灿发.环境公益诉讼难在哪里 [N].人民日报,2013-05-18(10).
[9]盛爱玉.试论司法地方化的危害与成因 [J].法制与社会,2011(4):139-144.
[10]薛克鹏.经济法的定义:社会公共利益论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349.
[11]王灿发,程多威.新《环境保护法》规范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J].环境保护,2014(10):38-43.
[12]刘莘.公法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讼 [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48-56.
[13]黄萍,刘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J].人民论坛,2010(17):129-133.
[14]刘明明.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缺失与构建 [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71-76.
[15]吴安荣,严蛟,刘涛.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辨析:以2007年至2012年公开报道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样本 [J].沧桑,2013(6):129-134.
[16]袁定波.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首任庭长详解工作重点 环境公益诉讼将有可操作性程序规则 [N].法制日报,2014-11-13(3).
[17]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63.
(责任编辑:郭晓亮)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litigation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YU Zhong-wei1, ZHAN Liang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yang 110870, China; 2.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Chongqing Liangping People’s Court, Chongqing 405200, China)
“Beautiful China” has already become one part of Chinese Dream, however, the contradiction is still grim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miracle that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on one hand,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disaster that terrified people on the other”. As the legislation response to the actual demand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e Trial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me into effect in 2015, which further clarify the subject of litigation and widen the range of jurisdiction of litigation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based on existing institutions. But it is still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enslaved to a series of “principle regulations”. It becomes the first task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judicial practice nowadays to clearly define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current li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and explore the solution from possibility to reality of li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Beautiful 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2016-12-16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1DSH029)。
吕中伟(1975-)男,辽宁沈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证据法等方面的研究。
14∶35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70330.1435.024.html
10.7688/j.issn.1674-0823.2017.02.10
D 990
A
1674-0823(2017)02-01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