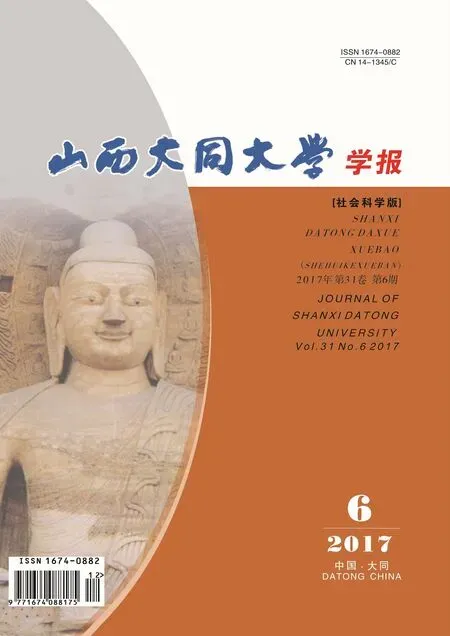论雁北作家群的“异质性”特征
郝春涛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论雁北作家群的“异质性”特征
郝春涛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雁北作家群是一群有着与“山药蛋派”迥异的艺术禀赋的、独特的、自成系统的文化群体。他们的创作文本中,用“窑言炕语”展现地方民俗,用“原欲书写”揭示残酷生存,营造出粗陋乡景中雁北人民的生活场景,显示出与山西本土文化不同的“异质性”特点。
雁北作家群;杂糅性;窑言炕语;原欲书写;犹疑茫然
“雁北”是指1970年成立的山西省雁北地区。1989年,国务院批准由原雁北地区划出朔县、平鲁县、山阴县,设立朔州市;1993年,原雁北地区撤消,所辖应县、右玉和怀仁划归朔州市;其他县(左云、大同、阳高、天镇、浑源、灵丘、广灵)归大同市。尽管行政区划发生变化,但雁北地区几乎完全相同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相同的民俗风情,相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氛围,尤其是相通的方言,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雁北文化圈”的文脉从未断裂。
“雁北作家群”,是指山西省原雁北地区文化圈之内以焦祖尧(后山药蛋派代表之一)、吕新(“第一个让世界知道晋北山区的作家”)、王祥夫(新世纪底层写作代表)、曹乃谦(被马悦然称为中国“头一流的作家”)、王保忠(乡土文学传承者)等为代表的近百名作家形成的群落。
傅书华先生把当代山西文学的发展分为“山药蛋派”、晋军(以成一、李锐为代表)和晋军后(以张平为代表)三个发展阶段;苏春生先生则把大同作家焦祖尧等称为继赵树理“山药蛋派”之后第二代作家的新进。但评论家们未把其他雁北作家考虑入内。从创作姿态看,雁北作家群有着与“山药蛋派”迥异的艺术禀赋。它与山西本土文化的联系不多,是独特的自成系统的雁北文化的产物;它不是对“山药蛋派”的赓续,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坚韧、孤独而默默奋斗的另类群落。其“斐然”之处不在于为主流文化的接纳程度,而在于他们的创作承载着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梦想,真实地反映了处于边缘地带的雁北人民的心路历程。它在被人们忽视的角落里闪烁着孤独而动人的光芒,记录着、再现着、承载着当地人们的生活和心灵。
一、“杂糅性”:民俗书写
雁北文化圈处于桑干河流域的核心地带,塞外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处。其中原文化与塞外文化交融的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特色在当代社会相当耀眼。从先秦到明清,这里一直是各民族杂居之所。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魏政权建都平城;直接导致北魏衰落分裂的尔朱荣部落,也是从这里起家;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均把大同作为陪都;唐末沙陀朱邪部首领朱邪赤心平叛有功被赐姓为李,并在五代时期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中原正统王朝和北汉这一个割据政权的沙陀族人,也曾长期袭据于此。宋元明清时期,这里也一直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兵戎相见的前沿阵地。在当代,原雁北地区13县的居民,均与内蒙古人民接触较多。这使得雁北地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有别于中原文化的“杂糅性”特点。这些特征,在雁北作家群那里都可以找到明显印迹。
如吕新《白杨木的春天》的丧葬习俗:
在当地有一个习俗,当有人死后,家里的人会摘下一扇门,将那个逐渐冷却僵硬的躯体停放在上面,等棺材做好以后,再进行入殓。
曹乃谦《斋斋苗儿》里的“煮鱼鱼”:
煮鱼鱼就像城里人常吃的烩面。鱼鱼是莜面搓成的,一寸长短两头尖尖,真像小鱼儿。
王保忠《看西湖去》里的“蒸糕”,算是雁北与内蒙一带最有特色的一道食品:
说着说着,婆婆嗅到了糕粉蒸熟的气息,就对老头子说,先不跟你说了,先给你弄饭去。就回了里屋,两只手掀了笼布的角,把糕提到瓷盆里,抟了又抟,抟成一个小团,又抹了点麻油,那糕就黄灿灿油亮亮的了。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民俗所蕴藉的文化内涵,诸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亲属称谓、服装系统、饮食习惯、各种艺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约定系统,无一不浸透着地方文化的濡染。雁北属于高寒地区,耐寒耐饥作物是满足生存需求的首选。曹乃谦《斋斋苗儿》里的“莜面”鱼鱼,本种植于内蒙古河套一带,其起源与汉武帝和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征战有关。乃是采纳大将军卫青建议,随军驻地垦荒,大量种植的耐饥寒、经酷暑的,并根据大臣莜司之名命名的。内蒙、大同地区流传的谚语:“四十里莜面,三十里糕,二十里荞麦面饿断腰。”生动诠释了当地人的生存现状。
雁北与内蒙多地有着几乎完全一致的话语系统,文学陈述所营造的“呈现场”(Field of Presence)确立的语词逻辑,可以在此时此地得以表述且在彼时彼地获得理解和描述,不管这种逻辑意蕴是明显的还是隐晦的。作家们所乐于使用的方言土语,还可以在雁北和内蒙之间形成“共存场”(Field of Concomitance),作品中那些涉及不同对象、领域的陈述,涉及不同话语类型的陈述,不仅不会产生误读、排斥、置换或不相容,反而会唤起两地人们的“记忆场”(Field of Memory,均为福柯语),由此领悟有关这些陈述的内涵。而几千年流传下的相互影响、相互包容的语言、风俗、习惯,也会直接进入文本并产生心领神会的效果。
二、本土性:“窑言炕语”
雁北作家群的本土性,既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站在启蒙者的高度,用现代文明的眼光审视农村的贫穷落后与愚昧,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也不同于“山药蛋派”对“新农民”的赞许和对旧传统势力的鞭挞,而仅仅是被雁北文化气息熏染的“窑言炕语”。“文以载道”的意味很浅,却有着“守望乡愁”的情怀。
“粗陋的乡景、石头堆砌的房屋和依势而开的土窑、裸露的山石和赤黄的土地、孤独的榆杨杏树、一窝窝山药蛋,都传递出北方乡村的浓厚气息和鲜明的地域性。”[1](P126)曹乃谦的小说均以应县农村为蓝本;被称为“先锋派”作家的吕新作品也呈现出“山村印象”,他的小说所营造的山区风景、农具、冷清的季节、淡淡的色彩和晋北农村(吕新为左云县人)的衣食住行,构筑了一幅有着强烈雁北农村特质的全景画;王保忠笔下的农村生活,同样有着通体透明的雁北文化讯息。
雁北作家群的小说文本意义大多是透明的,读者不需要填补由于语言流动而形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通过语言营造的雁北农村生活幻景蕴含的本土性,更多地表现为时间状态上的海德格尔所谓的“在场”,以一定的时间样式即“现在”去领会和传达(即使是曹乃谦笔下的“历史”,也是以当下的眼光去观照的)。吕新的先锋小说,也不像其他先锋派小说一样,“它给读者一种缺失感,它扰乱了读者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假定,并使读者和语言的关系发生了危机。”[2](P185)王祥夫、曹乃谦等人更无意于语言与文本、语言与历史、语言与世界的对立,他们笔下,德里达所谓的“原书写”和“声音”是一致的,那就是来自雁北的“窑言炕语”。
焦祖尧《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中那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王祥夫的《广场上有什么》的“邮电局前边的广场”、《登东记》中的“宋庄”、《六户底》中的“六户底”,王保忠《夜活儿》中的甘家洼等,原应县、朔县(现均属朔州市)作家赵治禄的《塔乡禾韵》(应县因有木塔而被称为塔乡)、郭万新《吉庄记事》、《草根吉庄》,郝丽云的《探朔》等,其叙事基点均为雁北实景。“先锋派”作家吕新的作品《白杨木的春天》,其叙事空间也为左云县的“雀山煤矿”:
烟山南麓下的水库那边似乎有马达的声音正在响着,但听上去不是太真切,反倒是雀山煤矿的鼓风机的嗡嗡声更近一些,几十台分别安装在不同位置上的鼓风机年复一年地这么响着,久远而熟悉,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某一天要是它突然不响了,周围听惯了的人们都会不由得愣一下,会明显地感到少了点什么,有一种熟悉的热乎乎的东西不见了,从日常的生活里消失了。同时,那又好像预示着有什么新的东西要出现吧?
雁北作家群笔下的“粗陋乡景”,其实只是作为叙事背景而存在的,作者的记忆与沉思一直纠缠着叙事,“文人都急于透过日记或回忆来把人格与作品联系在一起,在普通文化中可以发现的文学形象被垄断地集中于作者,他的人格,他的生活,他的兴趣,他的激情。”[3](P49)作者们显示出对语言控制的极大兴趣,而这种兴趣,也似乎仅仅局限在叙事动力上,即完成“故事”的陈述。“窑言炕语”的作用是作为故事的表征,将内在情绪与故事链扭结在一起。与山药蛋派不同,这些故事无意于对生活在此地的农民厚此薄彼,他们身上没有高尚与卑下的标签,而大多只是被生存欲求困扰的感性存在,农民之外的其他角色则均合乎主流话语对其内在特质的约束;与先锋派不同,吕新们的“窑言炕语”也仅作为背景一闪而过,叙事很快飘忽到更深层的心理体验;与当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变革文学等也不同,大多作品揭示的,也只是“雁北”那里,有一群人在“生活”而已;更有别于后现代主义的平面化叙事,将具体的、细微的、零碎的小叙事提升为本土叙事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可以引起有着相同生活经验的阅读者的兴趣,但也会因缺乏批评意识和现代视野而使其对“人”的思考止步。
三、底层性:“原欲书写”
雁北作家群笔下的人物,绝不简单地限于农民,而是把笔触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揭示不同阶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这其中,有包工头,有村长,有打工仔,有光棍,有寡妇,有残疾人,有性变态者,各色人等,众相纷纭。
雁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成为第一要务。基于此,雁北作家群中,曹乃谦用近乎残酷的笔墨,展示居于社会底层的男女们的“生存之战”,将对生命的拷问降低到对生存的漫画式书写,把人的动物性嵌入到语言的深层结构。“曹乃谦笔下的农民完全困顿于生理本能——饥饿和性饥渴,曹乃谦‘温家窑’系列小说的主题无不指涉性饥渴和饥饿。然而,刘震云认为,‘历史’和‘社会’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历史的‘真相’可能是被遮蔽的‘真相’,呈现出来的‘事实’常常是矜夸和装饰的‘事实’。”[4](P182)
曹乃谦对20世纪70年代雁北地区农民的生存书写,呈现出来的却不是“矜夸和装饰的‘事实’”,而是真实的再现。曹乃谦对《作家通讯》编辑室提出的问题“你的创作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食欲和性欲这两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对于晋北地区的某一部分农民来说,曾经是一种何样的状态。”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紧紧围绕食色主题展开。但小说有意将人们的“性”欲望夸大至变态的程度。不管是因无钱娶妇而“拉边套”的(几个男人养活一个女人)、或者是光棍之间“把对方搂得死死的,嘴唇吸得滋滋响”的,甚至将母亲作为他们意淫对象的,还有那些乱伦后自杀(如愣二、狗子和玉茭);与动物交配的(羊娃、玉茭),等等,都揭示了雁北农民被生存困扰的窘状。
食色原欲,本是和“羞耻感”联系在一起的。叔本华曾说:“所谓幸福这种东西是根本没有的,因为愿望不满足惹人痛苦,达到之后只带来餍足。本能驱逼人养育后代,养育后代又生出苦难和死亡的新机缘;这便是性行为和羞耻相连的理由。”[5](P307)食性本能在当代作家张贤亮作品中也有体现,不同的是,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与马缨花,是落难公子与风尘女子之间“沉沦与救赎”故事的翻版,而作为理性参照的“《资本论》是一个政治符号,它在文本中一再出现,缝合了因饥饿、爱情、苦难而产生的文本裂隙,照亮了文本中的阴暗面”[6](P359)。与张贤亮不同,曹乃谦笔下的“性”与政治无关,只与本能有关,他把“乡土性”降低到“食”与“性”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宏大叙事的“意义”的反讽,另一方面是作者对历史进行想象与重构欲望的文本表达。那种故意疏离“文革”场面、模糊时间与空间的叙事方式,是和“寻根派”们一脉相承的。叙述者的藏愚弄拙(即使全知叙事也并不居高临下),表现出其对于悠远长久的“食”与“性”本能的“似亲似疏”。这恰恰流露出作者对“当下”的恐惧与逃亡,以及在本能中寻找现代体验和自我救赎的努力。
曹乃谦的小说恰当地传达出雁北作家们普遍存在的历史与现代之间的犹疑。根植于本土的雁北地域特色和热衷于方言叙事的作家们,一方面以苍凉的笔墨,渲染“雁北”这块土壤中艰难生存的人们的现状,一方面又试图以“本土性”对抗现代性,那些嵌入到文本之中的乡村景象,与其说是为叙事贴上“当地”标签,不如说是作家们在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中无所适从而试图在“彼时彼地”找到慰藉,寻找灵魂栖身之所的一声叹息。
四、姿态:犹疑茫然
雁北作家群一直在现代和传统的缝隙之中寻找合适的“栖身之所”,那些与主流话语疏离、与地方文化贴近的创作,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现代民间叙事”。多数作家更乐于浸润在雁北地方文化的濡染中,创作有着地域色彩的文学作品。这种“地域色彩”大多立足于为“当下”。作家们在驻足当下的同时,也时常的把眼光投向深邃的历史,试图从历史中建构现代叙事寓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作品在“前往”现代性的表述上,呈现出半推半就、羞羞答答、欲说还休的状态。如王祥夫的《地下眼》中对“一片金黄,一片的金黄,那才叫个金黄”的“烟叶”的留恋,是对农耕文明“纯粹”生活的向往;《归来》中给温州人打工不幸失去一只胳膊的三小“给人家看门,还养了一只羊,是奶羊,给孩子挤奶吃。又说,还在房后开了一小片地,种菜,给自己吃,现在,有菜吃了”,是在城市文明中寻找一片心灵净土,试图恢复自给自足生活的愿景;王保忠《老瓜棚泪》表现出“出轨女人”在传统思维与现代“性解放”中的挣扎“或许为了报复天成,她把和那个人约会的地点选在了瓜棚……”;王保忠的许多作品中出现的“普通话”(而非“窑言炕语”),则是试图在形式上向现代迈进,却在生存方式上找不到契合点的“浅尝辄止”。
如前所述,尽管雁北作家的创作文本中仍保存了许多传统内涵,但在“游牧民族”已成历史记忆,农耕文明也将退出历史舞台,信息文明排山倒海地冲击着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大背景下,无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准确的契合点,“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作家们,在创作上表现为多种多样、复杂犹疑。在与现代文明的契合上,也多少表现出若即若离的复杂心态。对于雁北作家而言,哪些是地域文化之本,哪些是传统文化之基;哪些需要固守,哪些需要扬弃;传统与现代之间,理性与感性之间,怎样找到作家站立的姿势,是雁北作家群共同面对的困境。找不到准确位置,很容易导致作家边缘化;哲学底蕴较浅,对“人”思考不深,就会出现“跟风”现象;视野局促受限,缺乏探究动力,思想与艺术水平就会肤浅。把目光投向深邃的历史,不见得能找出与现代性对应的东西,也难以掌握主体交互中的主体间性。多元化的时代,怎样守住地方文化的“根”,是每个作家和地方文化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1]李 娜.山西当代小说创作与三晋地域文化[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
[2]杨大春.文本的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R.Barther:To Write:An Intransible Verb.参见 Modern Literary Theory.
[4]陈树义.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A].赵新主编.女孩最喜爱的哲理美文[C].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
[5]罗 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程 麻.文学价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A Study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Author’s Community in Yanbei
HAO Chun-t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The Author’s Community in Yanbei is a cultural group provided with disparate artistic endowment,unique and selfcontained system.Their creative texts show local folk custom by dialect and local expressions,rcvealing the cruelty of existence by unbosoming the original desire,and create a landscape in Yanbei people’s coarse and crude life scene.It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terogene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Shanxi native culture.
the Author’s Community in Yanbei;hybridity;dialect and local expressions;unbosoming the original desire;hesitation
I206.7;I207.42;I247
A
1674-0882(2017)06-0058-04
2017-08-25
郝春涛(1965-),男,山西山阴人,教授,研究方向:地方文化传播与地方作家创作。
〔责任编辑 裴兴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