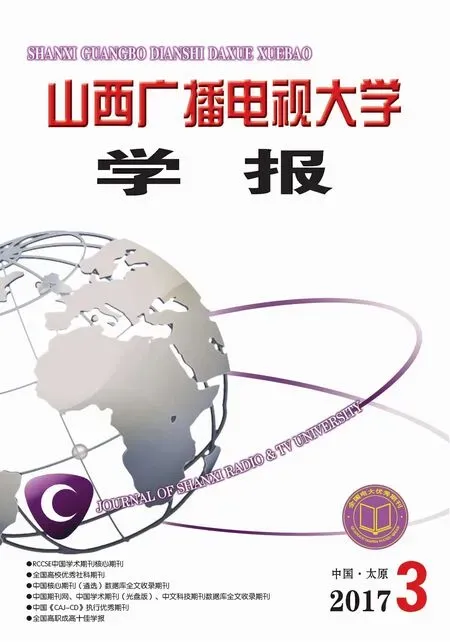《路边野餐》意识银幕化的现实表达
□郭 锐
(吕梁学院 中文系,山西 离石 033000 )
《路边野餐》意识银幕化的现实表达
□郭 锐
(吕梁学院 中文系,山西 离石 033000 )
《路边野餐》以高度“意识银幕化”的视听语言,展现了普通人“诗意”的精神世界。通过纪实性的拍摄手法,开辟了视听语言表达的新视角。让我们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屏幕上,重新感受电影创造时空的魅力。
色彩;声音;长镜头;非线性叙事
1989年出生的青年导演毕赣,其处女作《路边野餐》一经面世,便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奖项。《路边野餐》的影像风格在近几年的中国电影中独树一帜。影片通过对纪实性视听语言的运用,实现了意识化的时空表达。影片中的时空,在影像呈现上是现实时空,而在叙事表达上却是“意识”时空,模糊了现实与超现实的界限,达到了对影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
一、“陌生化城市”的现实表达
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维·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陌生化”就是对现实和自然进行创造性的变形,使之异于常态方式出现在作品中。[1]《路边野餐》在影像表达上,通过声音和色彩的配合,勾勒出了贵州凯里这个南方小城的特有气息,使它在心理感觉上如梦如幻,而这便是主人公陈升意识里的凯里。
(一)潮湿伤感的城市色彩
小城镇在银幕叙事上,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很少被表达的地域。我们在繁花似锦的屏幕上,看到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全都充斥着物质的味道。城市在影像表达上失去了情感,我们不再“触景生情”。而毕赣的《路边野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诗意的、充满潮湿伤感气息的城市影像。影片中,画面大都呈现出泛蓝的冷色调。
影片的色彩是导演的主观选择,在电影中“主观变异的”色彩运用,就是陌生化表达的技巧之一。《路边野餐》的整体影调是偏蓝的冷色调,也许这种与日常最为疏离的色调,才是陈升心中生活的描摹。层云密布的天空;昏暗潮湿的地下通道;大雾弥漫的山间公路;台球厅里蓝绿混杂的旧墙面;蓝色花纹的窗花贴;蓝色的桌布;空荡的偏蓝色车厢等。这种凛冽的色调,构成了区别于日常的凯里影像。这既像是一种残酷,又像是一种畅想,是一首关于时光的蓝色记忆。不同于张艺谋那情感强烈的色彩选择和表现,毕赣更多的是基于现实色彩基础上的小幅度变异。所以在视觉上,我们会觉得这是真实的凯里,好像又不是真实的凯里。一个偏远省份的南方小城,被赋予了梦境般的色彩与故事。这个中国地图上明确存在的“凯里”,变成了陈升意识游走的空间寄托。那些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里相互交织却又绕不开的轮回,是一个普通人对宿命的思考。
(二)梦呓般的声音语言
声音语言是画面造型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往往关乎影片的节奏和情感。《路边野餐》通过声音语言塑造出的陌生化城市,主要体现在方言诗歌朗读的疏离感与方言对白的现实感之间的冲撞。而陈升那“无处安放的人生”就隐含在冲撞中。
方言诗歌朗读的疏离感。陈升的身份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大夫,在常态的概念里应该离诗歌很远。但是毕赣却让陈升这个普通人有了“诗人”的特质。影片中插入的方言诗歌朗读,会产生一种与日常的疏离感,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诗意。第一次诗歌朗诵的插入,是在影片开始没多久,陈升晚上睡觉醒来之后;第二次是陈升梦醒之后;第三次是陈升坐上去镇远的火车之后;第四次是陈升进入荡麦之后,大卫卫带着他去找吹芦笙的人,路上陈升的独白再次响起。直至影片结束,还有两次诗歌朗读的声音赋予。每一次的朗读都与“梦”有关系,或在梦中,或在梦醒时。再配合陈升舒缓、低沉的声音节奏,就给凯里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色彩。而陈升的人生就放置在这似梦似幻的时空里,不可捉摸。
方言对白的现实感。一般情况下,现实主义的电影都喜欢使用方言对白。如贾樟柯的电影,几乎都是方言对白。《路边野餐》也是用了这种手法,但却没有产生一般意义上的现实感。相对于影片中的诗歌朗读,方言对白是具有现实感的。让我们时刻感觉,这是一个发生在南方小城的故事。而相对于其他使用方言对白的影片而言,这里的方言对白就显得相对“梦幻”了。影片中,大多数情况下,人物的对白都是较为平和的语气,再加上南方语言特有的味道,现实感就降低了不少。尤其是陈升从监狱里出来,开着车行驶在大雾弥漫的山间公路上,画面声音是陈升叙述在监狱里的遭遇。随着讲述的不断递进,画面上山间的雾气越来越重,陈升的声音又像是低声的梦呓。这一段长镜头,仿佛是一段梦游。通过声音与画面的组合,毕赣成功地“陌生化”了我们对南方小城的常态认识。而影片更重要的突破是对“心理时空”的现实表达。
二、“心理时空”的现实表达
苏联电影艺术家塔尔柯夫斯基曾在《纪录下来的时间》一文中指出:“我所关注的时间,并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人对时间的一种内心的心理上的量度……我所感兴趣的是每个人对时间的可能感受。人的主观含义上的、主观感受中的时间。”[2]《路边野餐》呈现出了塔尔可夫斯基的这种时间观念,影片中的时间流动就是主人公陈升对时间的主观感受。陈升在踏上去镇远的火车之后,影片所展现的时空就开始交叉,未来、现在与过去流淌在他的梦境里。
(一)时空交织的符号化呈现
影片中有很多体现时空交织的符号,这些符号串联起不同时空里的人物,实现非线性的交叉叙事。
钟表。小卫卫在墙上画钟表、在手上画钟表,因为喜欢钟表跟着花和尚去了镇远;大卫卫为了心爱的姑娘在火车上画钟表;花和尚因为自己死去的儿子喜欢表而开了钟表店;陈升找到花和尚之后,他的车里倒走的钟表等。钟表作为一个时空符号,串联起了人物之间的关系。花和尚想留小卫卫在身边,何尝不是对自己死去儿子的一种怀念;倒走的钟表是陈升想要时光倒流的一种暗示;小卫卫与大卫卫因为同样的喜好,而让我们去思考不同时空里的他们之间的关系。
花衬衫与磁带。光莲托陈升去镇远给她的“爱人”送磁带和一件花衬衫,这件衬衫是光莲与她“爱人”的约定。到了荡麦之后,陈升衣服的扣子掉了,送到一间裁缝铺缝补。当他看到貌似自己妻子的女人之后,匆忙追出去却穿上了这件花衬衫。花衬衫连接了陈升与林爱人。陈升是现在在诊所与光莲朝夕相处的人,而林爱人是曾经与光莲朝夕相处过一段时间的人。如果以衬衫的归属来考量,那穿衬衫的人必须是与光莲有特殊情感的人。花衬衫穿在陈升身上以后,那他与光莲的关系就变成了值得考量的。这样,陈升与林爱人的角色符号就变得具有同质性,这两个在不同时间段出现在光莲生命里的人,现在汇聚成了一个统一的符号;陈升跟着那个女人到她的发廊理头发,与她讲述自己与妻子的故事。之后他跟着那个女人去听小乐队的演唱,突兀地陈升开始唱《小茉莉》。唱完之后,他把光莲给他的磁带,送给了那个女人。而在之前的情节中,画面闪回到舞厅时,他妻子让他唱一首歌,他并没有唱。后来陈升到了镇远找到林爱人时,他已过世。陈升对林爱人的儿子说,有人托他带给林爱人的磁带,他给弄丢了。磁带连接了那个女人、光莲和林爱人。从磁带的归属来考量,它应该属于林爱人,但是陈升却给了那个女人。林爱人是过去时空里与光莲有特殊情感的人,那个女人是在荡麦时空里与陈升有特殊情感的人。陈升将自己的情感嫁接在光莲的情感寄托——磁带上送给了那个女人。
扣子和望远镜。在荡麦时空里,陈升衬衫的扣子掉了。衣服放在洋洋的铺子里修补,洋洋多给了他几个扣子。到了镇远之后,花和尚说卫卫手工课需要扣子,他没有。陈升正好有从荡麦带过来的扣子,他把扣子洒在花和尚车里倒着走的时钟上。如果说影片在陈升到了镇远之后,时空由梦境转为现实的话,那扣子便是连接两个时空的符号。如果荡麦是一场梦,那扣子为何在现实时空里存在?通过扣子这个符号,导演就营造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虚幻心理时空。或许,那只是陈升心里的一次想象;在荡麦时空里,大卫卫把自己的望远镜送给了陈升,到了镇远的现实时空以后,陈升仍然带着那个望远镜。望远镜也是连接现实时空与非现实时空的符号。
(二)长镜头下的虚幻时空
长镜头最主要的美学特征是纪实性,但毕赣却用它来表现一段“意识化”的时空,充分体现了他对影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陈升去台球厅找老歪,镜头从台球厅切到十几年前陈升帮花和尚“平事”的镜头,镜头跟着陈升做弧形运动,画面停留在雨水滴答的桌面上,之后再继续圆周运动,而此时画面已经从十几年前的内容变成陈升找老歪问卫卫去向的镜头。一个连续运动的长镜头中,画面内容实现了时空转变。这种用纪实性的镜头实现心理时空的跨度,是影视语言的一次创新。
影片中有一段长达40分钟的长镜头。陈升拿着光莲的信物,踏上了去镇远的火车。随着芦笙的声音响起,陈升进入了“荡麦梦境”——他坐着大卫卫的摩托车去找吹芦笙的苗人,途中换乘一个小乐队的车到了乐队演出地,在一个小摊坐下吃饭,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打酒喝的男人,而这个人正是之前情节中的酒鬼;之后他在一个小发廊里,遇到了自己曾经的“妻子”;洋洋说要去对岸看乐队演出,上了岸之后又从对面饶了回来;大卫卫被欺负以后,套着水桶在马路中间数数。陈升带着小卫卫去玩儿的时候,小卫卫也在数数;结束完小茉莉的演唱以后,大卫卫载着陈升去荡麦河边,在路上大卫卫对陈升讲了野人的事情。之前陈升都是从电视新闻里听见野人的消息,这次大卫卫说他们这里真的有野人。最后在荡麦河边,陈升胳膊上绑着对付野人的棍子,之前在凯里酒鬼也这么做过。人物通过相似性的符号和动作在这个虚幻的时空里联系起来。这段长镜头最后由一双梦境中的蓝色绣花鞋转入现实画面,陈升到了镇远,找到花和尚。所有的这一切对陈升来说就像一场梦一样。
三、结语
会有人拿毕赣与贾樟柯作比较,毕赣在访谈中会在不经意间提到贾樟柯导演。相差二十岁的两人,都跟山西有渊源,毕赣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贾樟柯的故乡是山西,而且他们都是作者型的导演。贾樟柯描述的是“物质”的故乡,是现实主义的客观展现,毕赣描述的是“精神”的家乡,是现实主义的感性显现。他们实现了从聚焦群体符号到个人意识的转变。在中国社会极速发展的今天,小城镇群体有了精神层面的律动,他们关注世界的目光从物质转到“诗意”。就像影片中的陈升,虽然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小城,物质生活一般,但他却会写诗,用诗意手段描述自己的人生。如此,才有《路边野餐》意识银幕化的现实表达。
注释:
①梁小昆著,影与调电影影像的影调美学效应,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06,第108页。
②颜纯钧著,中断与连续:电影美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12,第273页。
[1]毕赣,李迅,符榕. 在落差中发现电影的美感[J]. 当代电影,2015(12).
[2]黎明轩. 瑶山深处[J]. 电影文学,2013(7).
[3]尹鸿,梁君健. 通向小康社会的多元电影文化——2015年中国电影创作[J]. 当代电影,2016(3).
[4]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林洪桐.电影化叙事技巧与手段:经典名片优秀手法剖析[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本文责编:安春娥
Realistic Expression of Conscious Screen in the “Roadside Picnic”
Guo Rui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Lvliang College, Lishi, Shanxi, 033000)
The "Roadside Picnic" displays the poetic world of ordinary people with a highly conscious screen-oriented audio-visual language. By means of documentary shooting, the new visual audiovisual language expression has been opened up, which lets us feel the charm of the film creation time on the screen of the "squandering charming eyes".
color; voice; long shot; nonlinear narrative
2017—03—29
郭 锐(1986—),女 ,山西临汾人,吕梁学院中文系,硕士。
JQ05
B
1008—8350(2017)03—0080—03
——解读影片《路边野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