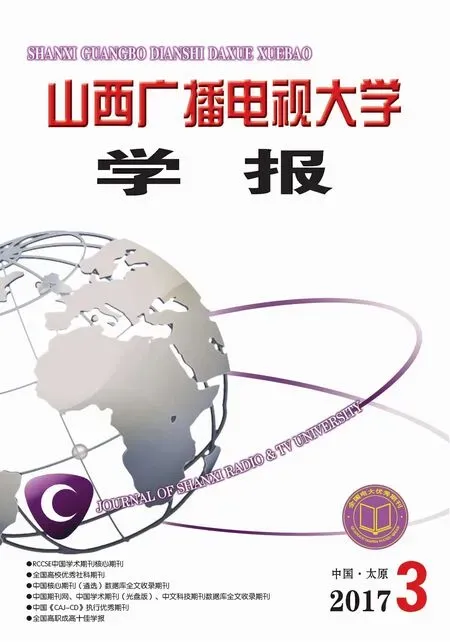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完善现代重彩画创作探析
□翟志华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系,山西 晋中 030600 )
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完善现代重彩画创作探析
□翟志华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系,山西 晋中 030600 )
现代重彩画以其特有的表现形式,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喜爱。从现代重彩画与本土民歌艺术的音画相通、视听相连、情感共鸣等方面努力寻求和探讨现代重彩绘画的新思路,深入研究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创民歌与现代重彩绘画的有机结合,以求表达重彩绘画来源于“人文通俗性、本土文化性、母语同源性”,达到以神写形、以形表意的效果,为现代重彩画的创作开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借鉴;开花调元素;完善;重彩画效果
民族文化始终影响着现代重彩绘画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特别是经历了新中国长达60余年相关专业人员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现代重彩绘画创作题材、造型、技法表现日益多元化,产生了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代表画家,如:林风眠、蒋彩萍、黄永玉、陈孟昕等。通过对这些画家探索内容的学习和研究发现,他们大多集中在重彩绘画表现形式的研究上,诸如对自然物、人物等表现形式的探索和研究,而对民俗风情与重彩绘画之间的相互启迪、传承、拓展和升华方面研究的不多。在长期的美术创作与教学中,由于受地方民俗文化中的原生态民歌的浸染,特别是受新时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忘初心,为人民而画,讲中国故事的教育,深深的启发自己,把积极探索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质朴、鲜活、雅俗共赏的左权民歌“开花调”所表现的日常生产、生活情景与重彩绘画创作有机的结合起来,拓展绘画创作题材的新视角,提升现代重彩画的借物抒情意境,以期更好地为广大喜爱现代重彩画的人民服务。
一、现代重彩画与左权开花调的简述
中国现代重彩画作为民族文化的形态之一,是由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继承传统,顺应现代文化审美条件创造出来的新画种,它始于70年代初,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程,它融汇西方抽象与装饰美感,利用现代色彩的特长,以其特有的造型、色彩、肌理交织形成视觉美感,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中国的绘画表现力,强化了绘画的本质特征。
左权民歌涵盖范围广,蕴意丰富,其中尤以“开花调”最具代表性。2006年,左权“开花调”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他的词取材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表现花鸟鱼虫、自然风景、仁孝礼仪等,上句起兴、下句点题,深情感人;他的曲委婉清秀、旋律规整、感染力强,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二、现代重彩画创作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的理论依据
我们知道,一旦回溯绘画创作的核心之源,它的源头活水一定是一种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借此感慨的特定介质。现代重彩画的创作离开了这一宗旨,如无源之花,必将枯萎。现代重彩画创作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传承民族文化和现代审美变革的有机结合。经过多年的美育教学和创作,深深感悟到重彩绘画中民俗与抒情元素具有同源性,特别是左权“开花调”民歌中用“赋、比、兴”手法,将彼物比此物,言物咏情,能形成鲜明的形象性和画面感,为现代重彩画提供了鲜活的灵感和质朴的素材,拓展了现代重彩画的创作视野,传承了民族文化,升华了画魂意境,凸显了真、善、美价值,树立了审美自信,这也正是当前学校美育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一)现代重彩画创作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体现了中华文化本土性
现代重彩绘画创作注定离不开与他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风情,那特定的自然性与文化性, 都打上了本土文化的烙印。现代重彩绘画中流畅而蜿蜒的线条、浓重古朴的色彩、高度提炼的纹饰、极度夸张的造型以及民俗韵味的装饰语言,正是一方风土人情与纯朴生活的原生态直观呈现。“开花调”作为文化形态中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和重彩绘画一样以“通感”的形式体现本土文化性,共同体现艺术源于生活。重彩绘画借鉴开花调元素,就会使得这种绘画生命力完全表现出一方水土的原汁原味的率性、质朴的乡情,从而触动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使人们能感受到一种人文情趣与稚拙天真的语言相交融的意境,映现出“天人合一”的本体论美学思想。
(二)现代重彩画创作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表现了中华人文通俗性
传统的重彩绘画和“开花调”民歌艺术,蕴涵了浓浓的乡土人文情感,是深受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性文化形态,如寺庙、观宇及庭院中的重彩壁画,新农村处处可见的重彩宣传画,以及“开花调”中的曲调节奏、方言唱词、情境意蕴等,都是那么的让人感到通俗易懂。“开花调”作为民歌艺术其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人们的生活积累,具有浓厚的民俗情节,一首山歌就是一个甜美的故事,加上独特的方言节奏和艺术唱腔,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其直抒胸臆的“真善美”、散发浓郁乡土气息的“民俗美”、浅显易懂的“通俗美”、一方水土的“天然美”,无不阐释出灵魂深处的一种情感精神效应,正如我们所说的“重彩抒情情更浓”,把“开花调”里表达的内容嫁接到现代重彩绘画中,达到音画相通,可以说恰到好处。
(三)现代重彩画创作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凸显了中华母语同源性
众所周知,艺术是反映审美文化的形态语言,其核心是文化内涵。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博大精深,生生不息。传统绘画与民歌艺术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母语土壤,经数千年的发展,融汇了民族独特的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意识、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形成了各自完整的艺术体系,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点。左权开花调民歌,总是让人联想到一幅幅动情的画面。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一文中讲到“音乐与绘画有着密切的亲族关系”[2],这种音画自然联系和转换正说明了其母语同源性。所以在重彩绘画中注重发挥想象,在自然而然中将“开花调”中的曲词音调转化为重彩绘画中的画面,能凸显出母语同源性。
三、现代重彩画创作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的创作创新意义
高尔基说:“任何艺术,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启发人们的矛盾情感,培养它对生活中某种现象的这样或那样的态度”[3]。重彩绘画的创作也基于这样一个通则。探索民歌“开花调”与重彩画的联系,拓展重彩画创作的新思路、新视野,升华重彩画的艺术表达意境在实践中得到的启发如下:
(一)现代重彩画创作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启迪了创作灵感
“开花调”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来源于生活的真实表述,歌曲与绘画虽属不同的艺术体系,但二者在言物咏情、借物抒意上具有共同性,我们常说的音乐有画面感就是这个意思的直接表达。日常创作中,我们常常为找不到创作素材或创作灵感而苦恼,而“开花调”中广大人民群众上千年积累下来的表达天地人、花鸟虫、事物理、情景趣,如大海一样的意境素材不正是我们重彩绘画和美育工作者所追求的创作灵感来源吗?笔者曾借鉴王志信老师改版的左权开花调“桃花红杏花白”创作了重彩画,在省展中获奖,作品把歌曲中男女主人公的对白,形象生动地融入绘画的意境中,形神并茂、意趣质朴,取得了创作多年难得的艺术效果。
(二)现代重彩画创作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拓展了绘画空间
马克思曾说:“民歌是惟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这样就赋予了开花调“活的历史”的特色,左权开花调具有重要的叙事特点,我们通过歌词能联想到一个个故事情节和一段段生活历程。在绘画创作上,我们以歌词为元素,领悟变换的旋律表达和传递给我们的视听感想,一个个意象场景、形象、时空画面在脑海里如诗如画般闪现,使现代重彩绘画创作空间不断得以拓展。例如:开花调里有歌唱大自然的色彩的:桃花开花红似火,杏花开花白云飘;有歌唱劳动人民秋天丰收景象的:玉米成堆似金山,男歌女舞似神仙。自然清纯的原生态美景画卷展现眼前,创作空间豁然开朗。
(三)现代重彩画创作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升华了作品意境
意象、意境是重彩绘画作品的最主要特征之一。能把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人、事、物刻画到抽象的作品中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使人浮想联翩,触景生情,就基本达到了创作的意义。意象、意境的形成不能离开特定的环境因素,离开了也就没有了真情实感。“开花调”歌于心,源于情,他的生命力完全是歌者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对着大山、小溪、羊群、心上人等,情感交融而发自内心,想唱就唱,是情与景,天与人的完美合一。古人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画者,人物相通也”[4],开花调讲求的情感美与重彩画创作中的意境美,交相融汇所表现出来的诗情画意不正是我们美术创作所追求的一种意境吗?如开花调中“桃花来你就红来,杏花来你就白,盼望和(妹妹)结成双呀,啊格呀呀呆”……,把这种抓住事物本质美的表达方式,运用到重彩画的创作中,以形写神,就会形成有情有景、表情达意的功效,使现代重彩之画作形成表达人们心理和感情的胸中之“象”。
四、现代重彩画创作中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的基本切入点
现代重彩画创作,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在实际应用中有许多切入点,但最基本的应把握住音画相通、视听相连、情感共鸣这几个原则。在情、景、意上领会开花调元素,在形、色、神上重彩提炼升华。
(一)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强化造型“以神写形”
“艺术表现人的情感,也表现人的思想,但并非是抽象的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是艺术的特点”[5]对于现代重彩绘画的视觉艺术形象,画家们更加注重一种装饰性、秩序性的提炼。传统造型艺术讲究“以形写神”,现代重彩绘画造型则更多地体现着一种构思与秩序,更加呈现一种写意性,作为对一种民俗型题材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以一种“以神写形”的主观意象理念为指导,以此体现自我造型语言的内在美学。绘画作品中憨哥哥、小阿妹主人公形象塑造,相关联的桃树、杏树和体现吉祥民俗文化性的三羊(开泰)、七彩鸟等形象的塑造,都是在生活形象基础上融入个人主观感情,注重夸张化地把握神态,以一种装饰手法,大量植入民俗“祥云纹”,用以装饰人物眉毛、衣纹线、衣服装饰纹样、树干裂纹、羊儿皮毛、鸟儿结构线、羽毛组合等,达到造型手法既体现精炼又突出特征,既条理统一又变化多端,造型意味被赋予了一种装饰图式的写意情趣,形成具备民俗特色的审美意象趣味,塑造出一种高于生活的意象,达到张彦远画论之“若气韵为先,则形神在其间矣”[6]的艺术创作效果。
(二)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把握色彩“主观自我”
现代重彩画家们在语言层面上有一种显现的倾向,那就是色彩探索。左权开花调表达生产、生活场景,包罗万象,映现了主客体相融相合的“随意赋彩”效应。在如何转化为画面色彩的审美情趣表达上,一方面要注重重彩画材质之彩,另一方面注重把主观性与民俗观念糅合在一起,体现出自我主体性,在自然色彩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和提炼,形成意象上的协调与对比处理,以一条隐形的视线和情感文化线牵制画面之色,使之震撼人心,如在人物和场景的处理上,以黄色与绿色水性色,恣意融合铺底后撒粗颗粒贴铜箔做底,除发挥材质肌理美效外,主要在色质上取得一种既显厚重又不失明快的效果,主体形象勾线渲染红、白、黄色,配景勾线渲染少量蓝绿橙白,与背景形成大调和小对比的虚实相生的金灿灿暖黄色调,相映成趣,用以表达温润喜盈之甜美情调和错彩缕金色效。
(三)借鉴左权开花调元素,布局场景“节奏调动”
如果把绘画画面认为是一个定格的瞬间,那么这个瞬间必呈现着某种意境,意境激发人们的联想,实现绘画功效。将“开花调”转化为画面,决定意境高低的,首先是形象化、典型化的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深意。在创作画面意境时,形象之间既注重内发情感文化性联系,也注重节奏韵律形式处理,使单纯条理化、秩序化、情趣化、规律化的形式与内容交相呼应,使画面富有装饰韵味,以此达到一种民俗性意蕴呈现,即画面意境。例如画作《桃花红,杏花白》里,我们看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在漫山遍野的花海中,沉浸在爱情的喜悦里的美好瞬间,那扭动的身姿、含情的微笑并略带羞涩、若即若离的情态,夸张的造型,衣纹、三羊、飞鸟、祥云以及桃树、杏树都绘以吉祥的民俗纹饰,较好的展示出改革开放后新农村青年男女幸福甜美的生活场景,从而达到创作目的。
五、结语
积极探索从民俗原生态中的左权开花调中挖掘意蕴,用于现代重彩画创作中,使现代重彩画的创作灵感、创作空间、创作意境、创作效果都得到了拓展和升华。充分体现了现代重彩绘画源于生活、扎根生活的艺术创作归源性,尽显了民族文化气韵、审美意境和写意精神。现代重彩画通过对左权开花调中原生态元素的借鉴,将其淳朴本真的生产、生活哲理,定格在画面中,提纯了艺术的本真意蕴,满足了大众的喜闻乐见要求,唤起了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和热爱,达到了现代重彩画创作的目的。现代重彩画中借鉴民俗文化元素的天地非常广阔,相关研究也非一蹴而就,这有待于广大美术爱好者和学者、专家更深入地去研究和探索,以期使现代重彩画不断传承创新。
[1] 王占文.流传千年的歌舞[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2] 黑格尔.美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3] 高尔基 .无产阶级作家文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4] 乐记·乐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6.
[5]薛宣林.薛宣林艺术论[M].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
[6] 葛路.中国画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本文责编:赵凤媛
A Study on Borrowing Ideas from Zuoquan’s Blossom Tone Elements and Improving the Creation of Modern Heavy-colored Painting
Zhai Zhihua
(Art Department of Jinzhong Teachers’ College, Jinzhong, Shanxi, 030600)
The modern heavy-colored painting is concerned and lov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because of its unique form of expression. From the similarities of sound and picture, the audio-visual connection, and the emotional resonance between the modern heavy-colored painting and the local folk art, this paper tries to seek and explore a new idea of modern heavy-colored painting, search for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original folk songs and the heavy-colored painting derived from the great majority of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to express the heavy-colored painting derived from “humanistic popularity, native culture and native language homolog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conveying the form through describing the spirit and conveying the meaning by form, thereby to create a broader perspective for the creation of modern heavy-colored painting.
borrowing ideas; blossom tone elements; improvement; effect of heavy-colored painting
2017—05—11
翟志华(1971—),女,山西晋中人,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系,讲师。
J50-05
B
1008—8350(2017)03—008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