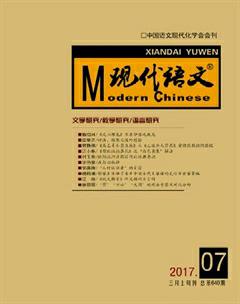诗语、框架与海外经验
摘 要:张斯桂于《使东诗录》中运用大量的典故成辞来“转译”使日所见之新事物、新经验,努力探索用旧诗诠释新世界之道。然旧体诗的形式对海外经验的容纳是有限度的,旧诗语始终无法准确捕捉和描摹新世界,这不仅是古代汉语的局限性,更是旧诗语背后思维的局限性。在中国传统关联式思考方式和物类体系下,旧诗语仿佛触动旧有知识框架的枢机,使得诗人难脱华夏中心主义的框架,因而对域外事物充满成见和道德优位优越感。另一方面,旧诗语也充当着不透明的传译“介质”,不可避免地扭曲或者切割着新世界,成为其时中国士人客观认识域外世界的阻碍。
关键词:使东诗录海外经验旧诗语框架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二(1877年1月5日),清政府任命正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人前往日本,是为晚清向日本派驻长驻使团之始。[1]适逢日本明治维新风气渐开之际,身负调解中日“琉球案”的使节之职,三人十分留意所看到的异域新鲜事物,并通过诗文将沿途及驻日期间的所观所感记录下来,是为何如璋的《使东述略(附杂咏)》、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及张斯桂的《使东诗录》。对于前两者的诗文,前人已有丰富完备的研究,而对于张斯桂,却鲜少问津。这固是因为其诗歌的成就不高,“立意、运思、用典、造句都不免庸滥之嫌”[2],但其思想价值却不应被忽视。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批亲历海外的旧式文人,不管是他眼中的日本,还是这个经他“建构”出来的日本所映射的他自身,都值得我们细细考量。
在此之前(1863年),张斯桂曾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万国公法》作过序,序中,他极富创造力地将其时中国与列强的关系比作春秋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3],具有新旧杂陈的特点,即运用熟悉的文化资源理解陌生的经验,动用旧有的概念范畴来诠释新知。《使东诗录》及何、黄二人诗文亦如此,作为旧体诗,其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成辞来“转译”新兴事物与陌生经验,试图在不打破原有旧诗体内部和谐的前提下展现新知。林岗先生在《海外经验与新诗的兴起》一文中认为,这种努力恰是“显现了旧诗的语言和形式在海外经验、新观念面前的表达极限”[4],即在旧诗的框架内,旧诗语无法准确有效地摹写新事物。而郑毓瑜教授则指出,“已知的典故背后牵涉一套认知世界的方式、组合事物的关系”[5],文人在选择了“旧诗语”的同时,亦即选择了其背后一套传统的认知方式、思维框架。换言之,这不仅是“词不达意”的问题,更是新旧两套知识体系、认知方式的龃龉,两者相互拉扯与渗透,直至一方经裁剪切割,编排整合入另一方的框架内。以下,将沿此思路,通过对张斯桂《使东诗录》诗作的详细分析,检视张氏的旧诗语对新经验的容受效果,进而论及诗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更深层的认知方式、知识框架及价值认同等问题,及诗语的选择对作者客观“打量”域外事物的局限性。
一、旧诗语与新事物的“断裂”
张诗中颇多对新式的交通工具(如轮船、火车)的传译与改写,比如前几首记述赴日出使途中的诗作:
造成鬼斧与神功,王濬楼船跨海滩。霹雳数声惊远到(开船升炮),烟云一抹曳长空;飞轮掉尾波翻白,直突冲天焰透红。无翼能飞不胫走,涉川差胜布帆风。(《轮船起程出洋》)
艨艟飞驾出吴淞,花脑山前舱转东。(《傍晚过花脑山出大洋》)
船快似龙人似簸,风狂如虎浪如山。(《过绿水洋》)
探源古迹汉时夸,继世重乘博望槎。(《过黑水洋》)[6]
纵观作者所用以指称其所乘汽轮之典故成辞:“王濬楼船”承自刘禹锡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塞山怀古》),取晋武帝灭吴典事;“艨艟”是古代以浆为力的战船[7];“博望槎”取汉武帝使张骞乘槎至天宫事,“槎”是小木筏[8]”。
这种“转化型典故”[9]的使用固然是可以照顾到以传统士大夫文人为主体的“预设读者”[10]的阅读习惯,但同样可以看到,任作者如何搜肠刮肚地运用典事(不管是楼船、战船还是木筏)都无法准确呈现以蒸汽机为主要推动力的新式轮船的面目,只能通过勾连相关事物(“波翻白”,“焰透红”等)尽可能向所指称的对象靠拢。在提到轮船行驶速度之快时,也只能用“船快似龙”,“无翼而飞不胫走”这样的模糊比喻,有趣的是,在张斯桂另外一首歌咏轻气球的诗里,他也用了同一句诗(“无翼而飞不胫走”)来形容轻气球[11]。同一句诗用来形容两个完全不同的新事物,可见旧诗语并不能十分精确地勾勒和描摹新事物及其特征。这一点,张斯桂恐怕也是深有所感,所以才会在诗作中频繁加注,如《和竹添鸿渐赠诗原韵》中,“飞车碾铁雷声动(火轮车路),驰传闻钟电气通(电线信局)。如果不看括号内的注文,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新事物的面貌的,确如林岗先生所说,“传统惯用的语言抓不住新鲜的海外经验”[12]。
二、旧诗语背后的华夏中心主义
在述及日本或者中日关系时,张斯桂亦运用了大量旧的典事语词:
“入海去寻徐后裔,平倭还记戚元戎。”(《傍晚过花脑山出大洋》)
“駪征不惜鬓毛斑,忝列皇华绥百蛮。”,“平倭我愧将军戚,投笔群随定远班(随员十余人)”(《过绿水洋》)
虽然其时中日双方因为琉球案有所争议,但出使日本是中日两主权国平等、友好地交往,而张斯桂却以“平倭”“绥百蛮“代之,甚至自比于戚继光抗倭,其所用语汇确实不符合真实的历史状况。如果说前述对火车、轮船等新事物的不准确“翻译”主要表现在古代汉语的局限上面,那对日本的这些指称更集中在語言背后思维的局限性上面。因为指称日本国的语词有很多,”东瀛”“扶桑”等尽管延续了三神山的传说或者对于日出之地的神话幻想,但并无褒贬之意,只是作为文人最为熟悉的典故成辞方便使用。但表示矮小猥琐的”倭“以及对少数民族的蔑称“蛮”则都带有“文明”对“野蛮”的居高临下的意味,反映出张斯桂依然未脱华夏中心主义的知识框架,他在选择了旧语词同时,也选择了一种面对异族的优越意识。
另一方面,随着与国外的接触渐深,视野日广,这个框架也是可以局部变动和修正的:
鲸吞孰逞吴封豕,豚畏吾思晋瘠牛。(《咏琉球》)
颛臾毕竟东蒙土,季氏萧墙恐有忧。(《咏琉球》)
秦晋惠分鸿雁泽(戊寅山陕荒歉,竹添君曾运粮助赈),楚齐情岂马牛风。(《和竹添鸿渐赠诗原韵》)
前一首里,他运用“封豕长蛇”[13]、“瘠牛偾豚”[14]、“祸起萧墙”[15]等典故,针对琉球问题警戒日本不要太过贪心,在这几个典故里,他先后用吴国、鲁国影射日本,颛臾古国影射琉球,而中国则作为虽然权势衰落(瘠牛),但依然有实力压垮鲁国(指日本)的晋国出现。在后一首里,中日两国甚至变成了势均力敌的“秦晋”与“齐楚”。可以看到,张斯桂虽然延续为《万国公法》作序的思路,在诗中以诸侯争霸譬喻现今的国际关系,但已经不再把中国置于“首善之区”的周王室位置,而把中国看作众多诸侯国中的一个,华夏中心主义的“政治”优位感已不复存在了。
三、旧诗语对客观呈现异域事物的局限
郑毓瑜用“引譬连类”形容中国传统的关联式思考方式及其所建构的物类系统,即“传统中国对于天地万物的论述,不必然是为了探讨个别“物”的究竟,而是为了开展更多论述“物”的可能性,让“物”在不断跨越类别,跨越时空距离中彼此亲附接合……”[16]。在这样的思考模式下,中国的旧诗语及其所指称的事物都轻易地跨越时空与物类牵连更广阔的物类体系与历史经验,中国的诗歌语言因而太过沉重也太不透明。就比如在中国,提到月就联想到思乡一样,触动了旧诗语的机关,也触动了其背后一整套知识体系和思维架构,甚至包括充塞其间的各种历史遗留的成见。毫无疑问,这样一个不透明的介质对于传译异域事物来说是不理想的,任何客观的事物在经过旧诗语时都要经过其背后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的筛选和变形。
概而言之,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知识体系对外表现在华夏中心主义,对内是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凡是符合这个知识框架的新事物,就会被认可,反之,则会遭到批驳。比如在涉及到关乎礼乐文明的服装问题、关乎政权更迭的历法问题或是关系孝道伦理的丧葬问题时,张斯桂固守的这套华夷秩序便会格外强势,不容辩驳,体现在语词上面就会对异己文明充满讽刺和抗拒:
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看他摘帽忙行李,何似从前惯折腰。(《易服色》)
万千红紫乖风信,三五团□误月圆。桐叶添时非纪闰,葭灰飞后即编年。(《改正朔》)
生前岂作焦头客,死后应登照胆台。太息火攻真下策,青磷夜逐鬼风来。(《火葬》)
以第一首为例,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积极面向经张斯桂旧诗语的“传译”反成为“沐猴而冠”[17]、“狗尾续貂”[18],带有浓厚的贬义色彩。以“沐猴”(猕猴)学人来譬喻日本学习西方着装的不伦不类,更是透露出“文明——野蛮”的优越感,认为日本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不过是徒有其表。可见,张斯桂虽然已经打破了政治层面的华夷思想,于文化、道德层面却依然固守着“中体本位”思想,而帮助呈现、加固这套知识框架的正是带有贬抑性的旧诗语。
结语
在新事物与新经验的大量涌入下,张斯桂原有的知识框架虽有突破,但却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新知甚至成为原有知识框架的附庸,与之相合时,便较为顺畅地填入其中,与之相悖时,便会经反面性的传译遭致批驳。而这其中,旧诗语(典故成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一方面勾连起堆叠着无数成见的过往经验,从而加深固有知识框架的效力,另一方面作为“传译”的媒介,不可避免地扭曲或者切割着新事物。莱考夫在《别想那只大象》中认为:“框架是塑造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重塑框架改变着公众看待世界的眼光”,而“因为语言激活框架,构建新的框架也就需要新的语言”[19]。旧的语词无法根本动摇旧有的框架,也无法激活和重塑新的框架。就像我们无法想象,在“国家”“国民”等词语真正如其所用前,中国人如何在“天下”“万民”的书写中想象平等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进化”“进步”等词语兴起前,又是如何在对“三代”的回望中理解时间的线性前进、一去不返。这也是王汎森先生在谈及戊戌前后中国的巨变时强调“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的原因,“新的词汇、概念工具使得人们在理解及诠释他们的经验世界时,产生了深刻的改变”[20]。只有当中国人能真正地“曲体其情,俯从其议”,运用新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来认识世界,才能跳出原有语词和思维的框架,在他者的目光中更好地认识和建构自我。
注释:
[1]戴东阳:《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2]王晓秋、钟叔河等点校:《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4页。
[3]《万国公法·序二》:“间尝观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四海会同,万国来王,遐哉勿可及已。此外诸国一春秋时大列国也。”,引自丁韪良译,[美]惠顿:《万国公法》,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2期。
[4]林岗:《海外经验与新诗的兴起》,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26页。
[5]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70页。
[6]王晓秋、钟叔河等点校:《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5-155页。以下所引《使东诗录》诗句均出自本書.
[7][东汉]刘熙:《释名·释船》:“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
[8][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杜少陵六》,引[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张华《博物志》:汉武帝令张骞穷河源,乘槎经月而去,至一处,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云:‘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榰机石与骞而还。”
[9]孙洛丹译,[加]施吉瑞:《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10]廖志鹏:《「吟到中华以外天」--析论黄遵宪域外诗的「抒情维新」》,中极学刊,2016年,第10期,第9页。
[11]张斯桂:《观轻气球诗》:“盘旋夭矫半空中,无翼而飞不胫走。”,引自刘雨珍编校:《近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92页。
[12]林岗:《海外经验与新诗的兴起》,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24页。
[13]《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
[14]《左传·昭公十三年》:“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
[15]《论语·季氏》:“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16]郑毓瑜:《1870年代中、日汉诗人的视域转换——以博物知识、博览会为认知框架的讨论》,淡江中文学报,2011年,第25期,第104页。
[17]《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18]《晋书·赵王伦传》:“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
[19]闾佳译,[美]《乔治·莱考夫. 别想那只大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期。
[20]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88页。
参考文献:
[1]戴东阳.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1.
[2]林岗.海外经验与新诗的兴起[J].文学评论,2004,(4):21-29.
[3]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M].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2:268-325.
[4]王晓秋,钟叔河等点校.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5:135-155.
[5]丁韪良译,[美]惠顿.万国公法[M].上海:上海书店,2002:2.
[6]孙洛丹译,[加]施吉瑞.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98.
[7]廖志鹏.“吟到中华以外天”——析论黄遵宪域外诗的“抒情维新”[J].中极学刊,2016,(10):191-227.
[8]刘雨珍编校.近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692.
[9]郑毓瑜.1870年代中、日汉诗人的视域转换——以博物知识、博览会为认知框架的讨论[J].淡江中文学报,2011,(25):94-130.
[10]郑毓瑜.类与物——古典诗文的“物”背景[J].清华学报,2011,(1):3-37.
[11]闾佳译,[美]乔治·莱考夫.别想那只大象[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
[12]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3:181-194.
(田紫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