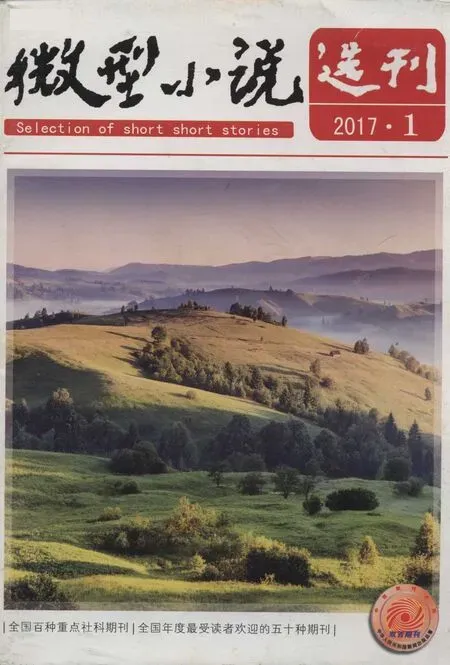清明
□羊 白
清明
□羊 白

1935年清明 刘长根
天空阴沉,要下雨的样子,却一直没下。刘长根从院子里走出来,腿在打战,人是飘的。他感觉自己就是一头牲口,已完全被饥饿攥住了。他的舌头已嚼不出苦涩,被胃里的疼痛隐隐地牵着,他的身体已开始浮肿。
他告诉自己,不能做一头牲口。仅有的半袋红苕干,他要留给媳妇和儿子。万一,万一自己倒下了,儿子刘茂盛也好有个活路。
他本来不想带上儿子。八岁的孩子,懂什么?连年战争,饥荒不断,这青黄不接的当口,活人都顾不来,谁又顾得了死人?可他想,万一自己死了,儿子连自家的坟场都不知道,成何体统?于是他把儿子也带来了。他要当着儿子的面祭奠祖先。他要给儿子做个榜样,将来儿子也好这样来祭奠自己。这人啊,不能昧良心。他到二十岁,才知道自己是个弃儿,是被刘东山老汉收养的。他的生身父母究竟是谁,姓什么?他一概不知。他曾觉得遗憾。现在他不遗憾了。他感念长眠于此的刘东山老汉,虽然脾气不好,没少打他骂他,虽然家里穷,但总把他养大了,还给他娶了媳妇,如今又有了儿子。刘长根—他细细咀嚼老汉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不禁泪水长流,觉得做他的儿子值得。他就是他的祖先。他要把刘家的血脉传下去。他甚至有了一种使命感,传下去,就是对老汉最大的回报,不是吗?虽然活得艰难,但他一定会咬牙坚持。他来给老汉上坟,就是要让他知道,他这个儿子,是把他当亲爹对待的。他就是他的祖先。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下一个清明。他要趁着这个清明,把该了的心愿了了。
刘长根跪在坟前,让儿子刘茂盛也跪下。他磕头,让儿子也磕。磕完,他低沉地喊了一声爹,让儿子喊爷。刘茂盛难为情,不喊,因为他自出生就没见过这个爷爷。他不喊,刘长根打他屁股。逼急了,刘茂盛说:“他是谁?能听见吗?”刘长根说:“他是我爹,我是你爹,喊吧,你喊他就能听见,他会保佑你的。”
“什么叫保佑?”刘茂盛怯怯地问。刘长根嫌儿子啰唆,屁股上又是一巴掌。
喊过爷爷,刘茂盛要逃。刘长根觉得过意不去,这清明上坟,没有祭品,连烧纸都没有,算什么祭奠?他叫住儿子,让儿子把坟上的荒草拔了,点把火,也算是给亡人捎去一点活人的消息。
儿子在坟头拔草,拔出了一个块状的东西,刘长根一看,是茯苓,贵重的药材。他喜出望外,在周围一刨,是一大窝,有七八个。
正是这窝茯苓,让刘长根一家渡过了难关。他不相信鬼神,但他相信,这是先人在保佑他哩。他让儿子永远要记住这件事情。
1958年清明 刘茂盛
天上飘着小雨。刘茂盛领着儿子刘红军和刘红兵,在刘长根的坟前跪下,烧纸,磕头。
这是刘长根老汉死去的第三个年头,按乡俗,要兴陵的,可“大跃进”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是要破除的陋习。刘茂盛用六七年时间经营起来的药材铺子,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被没收了,家里一贫如洗,哪有财力给父亲立碑?想来想去,他决定在坟上植两棵树,以树为碑。当年,在爷爷坟上挖出茯苓的事,他记忆犹新。正是因为爷爷的庇佑和启迪,他后来做了江湖郎中。父亲刘长根一辈子老老实实,小心翼翼,如今长眠地下。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如当年的自己一般大了……烟雾缭绕之中,他恍惚觉得世界是静止的,村庄依然是原来的村庄,不过是替换了人物而已。
父亲的坟在爷爷坟的脚下,这是父亲生前自己选定的。他赞同这布局。他本想告诉两个儿子,自己死后,就像父亲这样埋在他父亲的脚下。可他怕吓着孩子,毕竟,他们还太小,不懂得生死。在两座坟之间,他左右各挖了小坑。孩子们听说要种树,很高兴。问父亲:“这是什么树呀?”刘茂盛说:“是柿树。”听说是柿树,两个孩子尖叫起来,似乎很快就有红柿子吃了。
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样子,刘茂盛苦涩地笑了一下。他考虑种柿树,而不是柏树,除了纪念,确实有实用的意思。以后的日子,谁说得上来?饿极的时候,有几个果子,说不定能解决大问题哩。
1989年清明 刘红兵
晴,阳光明媚。这是刘茂盛逝去的第三年,刘红军出力,刘红兵出钱,给父亲兴陵立碑。刘红军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皆种地务农。刘红兵继承了父亲的医术,改革开放后进入乡镇医院,后名气渐大,被调往县医院,成为刘家第一个摆脱农民身份、吃公家饭的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刘云帆,天才少年,获得过全国数学竞赛金奖,后被清华大学录取。
2015年清明 刘景明
阴天,有零星小雨。刘红军的小儿子,叫刘景明。早些年,他是一个卖苦力的瓦匠,进入新世纪后,开始包工程,规模渐大,名声日响,成为当地富豪。前一年,他给父亲过寿时,提出一个想法,要把祖爷爷刘东山的坟墓好好整修一下,立一方大碑,把刘家祖上的事记录下来,传给后人。刘红军同意,刘红兵也同意,原本说好两家平摊出资的,可因为刘红兵在县城,刘云帆在北京,三下五除二,刘景明把该办的事都办了。清明前一天,刘云帆从北京赶回来,到家坟上一看,两棵柿树不见了,祖爷爷的坟被水泥砌成高大的拱形,下面贴有瓷砖,正面的坟头是门楣的造型,左侧的碑高大不说,上面还描绘有龙纹,碑文密密麻麻,是漂亮的行书。刘云帆当即表示了不满意,嫌刘景明事先没和他商量,墓和碑造型太夸张、太花哨,没有古意。其次还嫌刘景明自作主张,把两棵柿树砍了。这两棵树,父亲多次给他讲过,包括茯苓的事,他也有所耳闻。而且,小时候上坟,父亲、伯父在柿树上刻有他们几个孩子的高度,后来查看,随着树的生长,虽已模糊,但总有痕迹。至于秋后的红柿子,他们这帮小辈,举着顶部有裂口的长竹竿,左旋右转地把红柿子往下夹,忙得不亦乐乎。兴许因为坟墓里埋着的都是自己的亲人,他们从来没觉得恐怖。
刘景明听刘云帆有怨言,随口道:“你不满意,不掏钱就是了。”
清明这天,刘家坟场上熙熙攘攘。一帮儿孙会聚一堂,鞭炮声声,热闹异常。
因为飘有零星小雨,地是湿的,不方便磕头,再说死者已离去太久,刘红军、刘红兵、刘景明、刘云帆他们象征性地烧香磕头,其他家眷交头接耳,议论着俗世中的事情。
仪式快结束时,不知刘云帆说了句什么,刘景明不高兴了,不就清华大学毕业吗,有什么了不起!他凶神恶煞地指着自己的儿子,以及平辈的一帮孩子说:“快,跪下磕头,尽管磕,磕一个一百元,我决不食言。”
刘云帆面红耳赤地站着,不知说什么好。刘红兵拽儿子,示意他不必计较。刘红军左右为难。在刘景明的屁股上踹一脚,吼道:“烧包,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吧?跪下,咱们统统跪下,再给我们的先人磕个头吧。”
(原载《佛山文艺》2016年第7期 作者自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