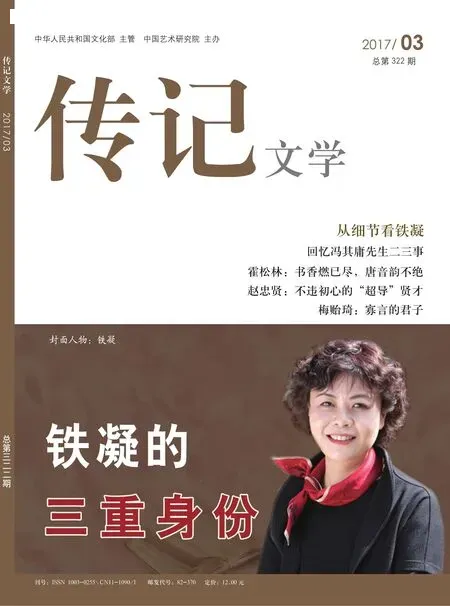“历史的真实”与“诗的真实”
——传记片《黄金时代》与《黑蝶漫舞》的异同比较
文 刘玉红
“历史的真实”与“诗的真实”——传记片《黄金时代》与《黑蝶漫舞》的异同比较
文 刘玉红

电影《黄金时代》海报
《黄金时代》与《黑蝶漫舞》两部传记影片,前者讲述中国女作家萧红的传奇故事,后者描摹南非女诗人英格丽・琼蔻(Ingrid Jonker)的多彩人生。两部传记影片在题材、人物和情节设置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整体效果却差别甚大。
《黄金时代》由许鞍华导演,李樯编剧,汤唯、冯绍峰等主演,主人公是性格卓异的萧红。20岁的萧红与表哥私奔,被抛弃后投靠未婚夫汪恩甲,不久又被抛弃;后来和萧军相爱,并通过萧军结识了许多文艺界人士;和萧军分手后,与端木蕻良结婚;后病逝于战乱中的香港,终年31岁。
《黑蝶漫舞》(Black Butterfiles,又译《黑色蝴蝶》)由保・范・德・奥斯特导演,格雷格・拉特编剧,鲁特格尔・哈尔、卡里斯・范・侯登等主演,主人公是被南非总统曼德拉称作“南非最伟大诗人”的英格丽・琼蔻。英格丽与父亲失和,尤其表现在两人对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的政治分歧上。同时,她又与丈夫不睦,先后与迈克、尤金等作家有过情感纠葛,最终患抑郁症投海自尽,年仅32岁。
两部影片中的主人公都是富有浪漫色彩和传奇经历的女作家,都处于混乱动荡的时代,最终也都逃不过早逝的命运。题材、主题相近,上映后的反响却迥然不同。那么,它们究竟存在哪些不同,差别又在哪里呢?本文尝试从影片的整体效果、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文学世界的呈现三个方面来解读分析。
一、影片的整体效果
两部影片都希望通过主人公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黄金时代》试图直接铺开一幅时代的巨图;《黑蝶漫舞》则倾向于从个人入手,以小见大。
为了营造跨越时空的艺术效果,《黄金时代》大胆采用了双重叙事时间,即萧红实际生活的时间和众人回忆萧红的时间。影片中,那些人物身处历史现场,却直视观众,如同接受采访,讲述着后来发生的事情。如聂绀弩直面镜头,从人群中径直走来,对着观众说:“去还是留,萧红和萧军坚持了各自的选择。”《黑蝶漫舞》则秉持着相对传统的讲述方式,从主人公小时候直至其自杀身亡,选取其生命中有代表性的几段人生经历,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缓缓道来,可谓详略得当。

电影《黑蝶漫舞》海报
两部影片均围绕多条线索展开,其中一些线索还十分相似,但展开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同。《黄金时代》横跨数十年,穿行六七个城市,涉及十几位文学家,导演试图面面俱到,将所有线索均匀展开。《黑蝶漫舞》则从主人公的角度出发,从个人情感到文坛状况,再到时代背景,影片有取舍,有侧重。
诚然,两部影片都把情感经历作为重要线索。不同的是,《黄金时代》把这条线索当作影片的核心,把萧红与表哥、前夫、萧军、端木的四段感情一一展开,除了先后顺序不同和所占篇幅不同,并没有明显的侧重,线索的作用似乎也仅限于说明萧红的情感经历而已。《黑蝶漫舞》也把英格丽的情感经历当作影片的重要线索,但不是核心。就情感线索而言,影片明显侧重于英格丽和迈克的感情,压缩她与尤金的段落,与丈夫的感情生活更是一带而过。这条线索不仅有的放矢地展示了英格丽的几段情感,恰到好处地展示出了她的独特个性,而且也为其他线索的展开作了铺垫。情感线索中除了爱情,还有亲情。两部影片都涉及了主人公与父亲、与手足碰撞和相处的内容。《黄金时代》将萧红与父亲的隔膜置于开篇和结尾,把萧红和弟弟的交流置于散文《初冬》的情景再现。这种集中化处理的方式,使得亲情的内容似乎成了为了影片的完整性而不得不交代的背景。《黑蝶漫舞》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按照时间顺序,将英格丽与亲人相处的段落贯穿全片。从她与父亲不和,多次想用作品赢得父亲的认可,到多次受到父亲的侮辱和刺激,随即产生异常行为,再到最后的精神崩溃;从和姐姐十分亲近,到争吵并分开,再到最后和好如初。镜头不多,但的确形成了一条若隐若现的完整线索,不但增加了影片的连贯性,强化了影片的矛盾冲突,还从不同的角度显示出英格丽的独特性格。
从整体上来看,《黄金时代》试图逐一展开萧红的情感经历、众人对她的回忆和评价、她的文学作品等以及所处的社会状况。双重叙事时间的运用,表现出摄制者巨大的野心,但实际效果却显得庞杂、松散、不尽如人意。《黑蝶漫舞》则是按照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将多条线有侧重、分阶段地糅合为一体,以主人公的认识和精神状态为中心,娓娓道来,呈现出从个人到社会、从小我到大我的层次,显得清晰、有序、浑然一体。
电影作为一种时空艺术,需要创作者把诸多段落以恰当的方式排列组合,呈现在银幕上。段落间的微妙关系和过渡方式,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影片的整体效果。以下简要梳理两部影片开场(3-4分钟)的几个段落。
《黄金时代》:
段落1:萧红讲述自己的出生和死亡。
段落2:萧红回忆童年的自己在后花园玩耍。
段落3:萧红与萧军讨论丧母的话题。
段落4:萧红回忆与祖父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
段落5:萧红与表哥出走被弃,与家人迁往老家,随后逃至哈尔滨。
《黑蝶漫舞》:
段落1:英格丽读诗。
段落2:童年的英格丽从海边抱回鱼。
段落3:祖母去世后,英格丽的父亲出场。
段落4:迈克救起在大海中游泳的英格丽。
面对相近的内容(主人公的事迹)和相似的目的(想要表达的意义),以及相仿的情感设定,两部影片采取了相同的展开路径。具体来说,都是先奠定影片的情感基调(《黄》段落1,《黑》段落1),接着回忆童年(《黄》段落2、3、4,《黑》段落2、3),然后进入影片的主要内容(《黄》段落5,《黑》段落4)。由于具体的处理方式不同,使两部影片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黄金时代》开篇是一个长达38秒的长镜头,黑白,近景。萧红面对着镜头,正襟危坐:“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整体气氛呈现出灵堂般的阴郁和肃穆。随即切换到一组特写镜头,盛着几枚鸟蛋的鸟窝,在虚化的嫩绿色背景中,显得异常醒目。一个身穿红色衣裙的少女用木棍捣着鸟窝,背景音是清脆的鸟鸣和萧红抒情的旁白声:“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几组俯拍和不同角度的特写镜头,营造出一种梦幻、唯美且富有生机的氛围。接着是一个中景镜头,在一个昏暗的旅馆中,四周堆放着凌乱的杂物,萧红身着深蓝色旗袍,挺着突起的肚子,萧军穿着墨绿色外衣,两人面对面讨论着丧母的话题,无论是画面结构还是色彩搭配,都给观众带来一种凄凉之感。一个移动镜头,从屋外墙壁移至窗户,窗中映着小女孩苍白的脸,伴随着萧红的旁白:“我或许永远不会明白我父亲那样的人,他对待仆人、对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整组镜头是阴郁的蓝黑色。随后是三个场景的平行组合段(“两个以上场景交替呈现,但其时空关系并不具有确定无疑的直接相关性。”——戴锦华《电影批评》):第一个场景中,萧红的弟弟站在门旁,他直面摄影机,讲述姐姐逃婚被弃的经历;第二个场景中,夕阳下,萧红和表哥从远处走来,经过摄影机又走远,背景是秋冬的树林和黄屋顶红柱子的北平建筑;第三个场景是一个虚化的蓝黑色小全景,萧红一家坐在马车上迁往乡下,同时伴着凛冽的风雪声和弟弟的旁白。影片开场的三到四分钟包含了多个段落,时间转换了7次,相邻段落(或场景)的氛围反差较大,加上段落(或场景)的过渡多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直接切(换),呈现出孤立、生硬和片段化的整体效果。
《黑蝶漫舞》开场时,银幕全黑,首先出现的是英格丽富有磁性的读诗声,随即银幕逐渐变亮,主人公略显苍白的脸在特写镜头下逐渐清晰,淡蓝色的眼睛望向一边,镜头的一角是窗外的大海。镜头转向翻滚着波涛的灰色大海,整组镜头都贯穿着英格丽的旁白:“……劝君忘了正义,世上没有这东西;忘了手足,都是云烟一场;忘却爱情,它全然没有道理。”影片开场就营造出了主人公浓郁的诗意世界。随即,大海由灰暗变为蔚蓝,预示着氛围的转变。特写镜头下,一片黑色的羽毛随着海水的波动而荡漾,预示着主人公的人生结局。音乐渐起,特写转为全景,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少女走在海边,望着蔚蓝色的大海。此时段落1与段落2转换完成。接下来的拍摄视角较有特点,从海边到小屋的一组镜头,被一路奔跑的小女孩串成整体。从小女孩的视角仰拍祖母略显苍白的面庞,紧接着特写桌上张着大嘴即将窒息的鱼,随后祖母去世。之后依然是小女孩的视角,一组主观的移动镜头,从屋内到了屋外,我们看到父亲开着黑色轿车出场,段落3结束。切回蔚蓝色大海的远景空镜头,银幕中心出现“BLACK BUTTERFLIES”(《黑蝶漫舞》)。接着,十分自然地过渡到海面上的近景镜头,已经长大成人的主人公在碧蓝的海水中游泳,镜头3到镜头4的过渡堪称圆融无间。影片的开场同样存在多个段落,因段落是按照传统的线性顺序排列,加上段落之间采用溶入、音乐串联、空镜头等过渡方式,使得开场浑然一体。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除了影片的整体效果,两部影片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有明显不同。
《黄金时代》中的萧红,行为被动,形象模糊。具体说来,她与表哥私奔被弃,回家又逃走;走投无路之下投奔前夫,身怀六甲再次被弃;向报馆求救,进而与萧军相识;战乱之下,与萧军分开,又和端木结婚……影片事无巨细地展示了萧红遇到的人和经历的事,却没有展现出她的内心状态和思想变化,显得她的选择似乎都是为形势所迫。相比之下,《黑蝶漫舞》中的英格丽就显得具体生动、个性鲜明。她与迈克的争吵,透露出她的放荡不羁和敏感不安;她和父亲的冲突,显示出她渴望认可而不得,压抑痛苦而无法释放;她与姐姐的疏离,展现出她思维独特、卓荦特行,而无法以常人的方式来理解她。影片呈现出的英格丽,其行为、状态与精神变化紧密交织,不生硬,无冗长拖沓的无谓之笔。
两部影片呈现出的其他人物形象的效果也相去甚远。总体来说,《黄金时代》中的其他人物呈现为标签化的孤立个体。萧军是谈论萧红时不可不提的人物,影片中的萧军思想独立、行为鲁莽、敢爱敢恨,但明显缺少作家应有的文学气质,也未展示出他与萧红的精神互动。两人为何相互吸引,彼此欣赏?矛盾如何产生?影片中均未提供合情合理的答案。鲁迅是萧红生命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影片将创作中的鲁迅和生活中的鲁迅混为一谈,甚至直接将鲁迅作品中的字句挪用为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显得异常生硬。对于鲁迅与萧红的关系,影片的处理方式是文学作品片段的再现。至于鲁迅为什么重视萧红,如何影响萧红,萧红对鲁迅意味着什么,影片同样未作解答。如此一来,鲁迅与萧红的相处片段,似乎只证明了萧红曾与一代文坛领袖有过交集。相比较而言,丁玲是影片塑造的较为成功的形象,她那不拘一格、爽朗豁达的性格,通过独特的说话方式、处事风格淋漓尽致地被展示出来。同样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辅垫她和萧红的关系。以至于萧红说出“我和她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时,显得有些突兀。
《黑蝶漫舞》中的其他人物形象塑造是为了烘托出主人公英格丽的一生,每个人物都具有受她影响或影响她的特点。迈克是英格丽的第一位情人,影片中通过表现英格丽读了五遍迈克的小说,迈克也惊叹于英格丽的诗,显示出两人在精神上相通,在文学上彼此欣赏。同时,影片又以两人的冲突和纠葛,表现了英格丽的率性自由和迈克的世俗化的一面。尤金是英格丽的另一位情人,与迈克不同的是,仅是她情感失意时的发泄对象。影片大量压缩了英格丽与尤金的情感段落,尤金的形象相对于迈克较为模糊,不过,却恰到好处地烘托出英格丽个性中歇斯底里的一面。在塑造尤金的形象时,影片侧重于表现他和迈克的共性,即都被英格丽吸引,都无法承受英格丽的热情,都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You drained me”(你把我掏空了)。英格丽的父亲是影片中十分关键的人物,他既是带给英格丽精神压迫的父亲,也是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文化高官,影片在父女的博弈过程中,同时塑造了二人的形象,一箭双雕。
简而言之,如果以画作类比,《黄金时代》类似一幅中心散漫的工笔画,创作者力图精雕细刻每个人物,主人公仅是其中之一;《黑蝶漫舞》则更像是一幅遵循透视原则的油画,主人公居于最突出的位置,轮廓清晰,色彩分明,其他人物则按照与主人公的关系次序排列,进而逐渐模糊为背景。

《黄金时代》剧照
三、文学世界的呈现
如何在银幕上呈现主人公所处的文学世界,是难点,也是关键。两部影片都运用了情境再现、人物旁白和景物特写等方法,效果却不尽相同。
《黄金时代》相对独立地使用了以上几种方法。首先,较为突出的是情境再现,如在开篇和结尾回忆童年的《呼兰河传》,与弟弟见面的《初冬》,和萧军喝酒吃肉的《商市街》,听鲁迅评点“红上衣要配黑裙子”的《回忆鲁迅先生》;其次,将文学作品作为旁白,如丁玲回忆萧红的《风雨中忆萧红》,萧红回忆五月杏子的《青杏》。此外,还有对文学作品的特写镜头,如《商市街》《八月的乡村》。由于影片倾向于单独使用各种呈现方法,就造成了一定的重复。如影片三次提及散文《初冬》,第一次是萧红坐在椅子上以画外音的方式回忆,第二次是萧红与弟弟在咖啡馆见面的情境再现,第三次是弟弟对着镜头说:“我们这次见面,被她写成了文章叫《初冬》。”再如散文《弃儿》,第一次是萧红和白朗在医院中的情景再现,第二次是萧红写下的“弃儿”两字的特写。诸如上述,多次的展示非但没有增强影片的文学氛围,反而造成了机械的重复感。当然,影片也有把多种手法融于一体的努力,如在对《商市街》的情境再现中,在银幕上打出了“电灯照耀着满城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的字样,效果却并不理想。影片未能将萧红的文学世界很好地呈现出来,原因可能在于:展现文学作品的段落未能与其他段落很好地融合,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紧密,即未能把萧红的作品和萧红的人生很好地结合起来,萧红的文学世界和现实生活呈现出分裂孤立的状态。
相比来看,《黑蝶漫舞》将情景再现、人物旁白和景物特写等多种方法融于一体,同时配合使用慢镜头、背景虚化、音乐渲染以及特殊意象等方法,增强了影片的主观色彩,将主人公的文学世界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凸显。这一特点在影片的开场就显示出来了。开场时银幕一片漆黑,以英格丽的读诗声作为旁白,随后画面逐渐变亮,她的脸也逐渐清晰……这样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氛围。影片的前半段并没有急于呈现英格丽的文学世界,而是先展开她的实际生活,她与迈克的情感、与父亲的隔阂,期间仅穿插了一些诗歌的线索,如英格丽给迈克送诗、墙面上的诗句等。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英格丽的认识和精神状态逐渐变化,直到影片的中间点(50分钟左右,影片全长100分钟),她目睹了那个被枪杀的孩子,这一事件成为影片的拐点。随后,影片的剧情紧紧围绕着英格丽的诗《尼昂加死去的孩子》逐步展开。从目睹孩子被枪杀、构思和修改诗作、请求父亲读诗被羞辱,到迈克发现并整理手稿、去欧洲领奖、经过电击治疗后无法再创作,再到暴雨夜里让迈克读诗,最后死去。影片的后半段多处暗示英格丽命不久矣,对于一位诗人来说,文学世界崩塌了,精神支柱不在了,肉体的生命也不会长久。影片最后以南非总统曼德拉朗诵这首诗歌的旁白为结尾,与开篇英格丽读诗的旁白相呼应。《黑蝶漫舞》糅合了英格丽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将她的诗歌和生命融为一体。
综而言之,两部影片都为塑造主人公的文学世界做了许多努力,然而,《黄金时代》并没有把萧红所说的“因为世间有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的内容展示出来。《黑蝶漫舞》则把英格丽的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融为了一体,汇成一首生命的诗歌。
传记影片的主要情节会受到历史人物本身事迹的制约,不能凭空虚构,但允许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合情合理的添加和润色。《黄金时代》与《黑蝶漫舞》的不同,究其根本是对“真实”的理解和把握有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了两种真实——“历史的真实”和“诗的真实”。《黄金时代》秉持着一种还原历史的客观态度,使用仿纪录片的方式,通过众人的作品、书信和回忆录等方式,就像史料汇编,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黑蝶漫舞》则是将确有其事的历史和合乎情理的虚构相结合,创造出一种胜过具体历史的“诗的真实”。
实习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