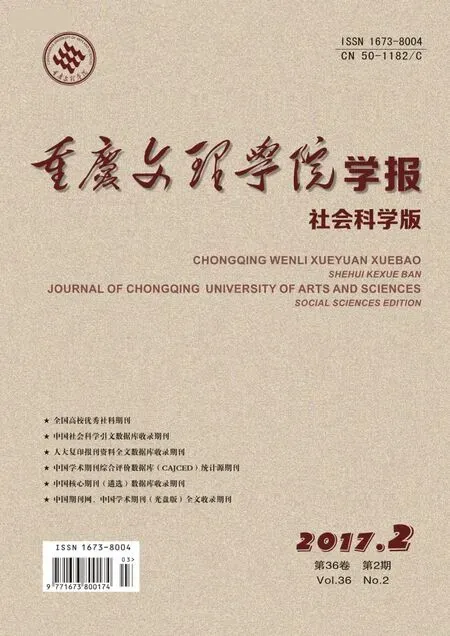“美在意象”的双重困局
刘鲁嘉
(重庆市作家协会《红岩》文学杂志社,重庆渝中400015)
“美在意象”的双重困局
刘鲁嘉
(重庆市作家协会《红岩》文学杂志社,重庆渝中400015)
文章针对北京大学叶朗教授在《美学原理》中提出的“美在意象”理论展开论述,在充分肯定其理论建构的意义与价值的基础上,指出了该理论的缺陷和问题。笔者一方面系统梳理了意象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对西方美学与文化的发展历史作了梳理。在中西文化与美学的比较视域中,指出了“美在意象”理论的双重困局,即要么固守中国古典美学的立场而无法涵盖西方的美,要么将意象泛化,只保留其情与景作为艺术品存在的基本条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
美在意象;情景交融;天人合一;体验;审美文化;意象泛化
“美在意象”是北京大学叶朗教授于2009年出版的《美学原理》中提出的关于美学本体论的概念。这一观点直接上承80年代叶教授在《现代美学体系》中关于美学本体论的回答。二十多年过去了,叶教授依然沿着曾经的研究思路一路走来,丰富、完善了“美在意象”的理论,并在《美学原理》中做了最后的总结:“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1]55
关于“美是什么”的回答,历来都是美学最核心的问题。在西方,早在古希腊就开始了美学本体论的研究。而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也是一个备受批判的研究方向,原因在于,美学已经告别了本体论的研究阶段。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厚的美学资源,但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我们对于美学的理解没有什么本体论、认识论这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我们没有被认为是美学的美学,我们拥有的是类似“妙”“气韵生动”这样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概念和美学理论……20世纪以来,西方美学传入,在中西美学的碰撞、渗透和互补之中,我国的美学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但我们真正开始美学本体论的研究,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虽然中国古典美学中已蕴含了美学本体论的思想。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发生在一个贫瘠的学术环境中,虽然形成了所谓的“四派”,但真正的美学成果很少。最后四派合归为一,被统一在了实践美学的旗帜下[2]。实践美学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美学成果,它对于“美是什么”做出了清晰的解释:“‘自然的人化’。人通过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物质实践,改造了自然,获得了自由。这种自由是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自由的形式就是美。”[1]42简单地讲,“美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的自由创造”。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众多美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美学在突破实践美学的藩篱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叶朗教授的“美在意象”就是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相比较而言,“美在意象”更好地整合了古今中外的美学资源,改善了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美学严重疏离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20世纪最新美学成果的状况,形成了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这样的功绩是应当被美学史记忆的。但我们也认为,这个美学理论体系同样存在问题,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存在,对它的批评与质疑,正是新理论的生长点。因此,本文并非是要否定“美在意象”的理论,而是要从“美在意象”接着讲。
一、意象的审美文化和审美体验内涵
意象究竟能不能上升到美学本体论的高度,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历史现场,系统梳理出意象的基本概念及其审美文化内涵,才能有更好的答案。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中,意象作为美学范畴第一次出现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刘勰的意思是说,在艺术构思活动中,外物形象和诗人的情意是结合在一起的。诗人凭借外物形象驰骋想象,外物形象又在诗人的情意中孕育而成审美意象。”[3]72-73紧接着,刘勰又更具体地分析了意象:“‘秀’是指审美意象的鲜明生动、直接可感的性质。”“‘隐’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审美意象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内容不直接用文辞说出来,不表现为逻辑判断的形式”。二是指“审美意象蕴含的情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丰富的”。“‘秀’和‘隐’,一是说的文学作品的具体生动的形象,一是说的文学作品不直接说出来的多重情意……不直接说出来的多重的情意要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3]226-228然后刘勰又提出了“风骨”,对审美意象作了进一步规定。“‘风骨’是对‘意’的进一步分析:它一方面有情的因素(表现为‘风’),另方面有‘理’的因素(表现为‘骨’)。”“‘风骨’这对范畴确实是讲情感和思想的关系。”[3]233-234二者和谐地统一于“意”中。紧接着刘勰又论述了“神思”。通过“神思”,“进到了对于审美意象的创造过程的分析”。“艺术想象是创造性的想象,它的结果是产生审美意象。”“艺术想象活动一方面结合外物的形象,一方面又包含作家的情感。正因为有这两个特点,艺术想象活动才能产生审美意象。”[3]236-238然而,刘勰对于意象的论述仅仅是开了个头,他基本在形式上建立起了意象的定义,至于意象的丰厚内涵,还有待于后代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的开掘。
“唐五代书画美学家认为,‘意象’应该具有和造化自然一样的性质,即所谓‘同自然之妙有’。”[3]243这样的思想显然和老子、庄子的思想相连。“按照老、庄的哲学,造化自然的本体和生命是‘道’,是‘气’。书法艺术的意象如果表现了‘道’‘气’,就通向了‘无限’,那就是‘妙’,就叫‘同自然之妙有’。”[3]244这里对于意象的描述已不再是干枯的形式定义,而是有了内在的情感体验。把意象和自然、气、道等概念相连,实际上是从中国的哲学和文化精神上对意象作了规定。意象不仅仅是情景交融,这里的情生发于天地之道,自然之基,与气和谐,因此,这里的情感体验就是万物静观、玄化无言、天人合一的状态。紧接着,荆浩又提出了“度物象而取其真”的命题。“真”就是要通过绘画“表现自然山水的本体和生命——‘气’。‘真’就是用‘气’来规定(要求)审美意象”[3]247。显然,这个命题和前面的“同自然之妙有”是相通的,对于意象的情绪体验有了明确的规定。接下来张璪又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八个字是对审美意象创造的一种高度概括。”[3]250它和刘勰的“神思”是有相通之处的,也是对“神思”的进一步说明和丰富。
宋元诗歌美学中有大量关于意象的研究。比如“情景交融”,范晞文、方回、姜夔、吴渭和梅尧臣等人的著作中都对它有较丰富的解释。总的讲来,就是情和景是不可分离的,诗歌意象都是情景交融的产物,所谓“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这是对刘勰美学思想的回应,“情景交融”是对“隐秀”命题的丰富和发展。“朱熹强调诗的意象是一个活的整体,它的内部有血脉流通……因此读诗的人必须通过反复涵泳,把握这个活泼泼的意象,把握它内部的血脉流通。”[3]306这是从鉴赏角度对意象的研究,“涵泳”就是要反复把握、体味和咀嚼意象之美。“韵”也是对审美意象的一种规定,指的是意象要有内涵、有余味,要“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艺术作品要以“韵”胜,“韵者,美之极”[3]310-311。在这里,韵虽然主要是对艺术作品审美等级的评判,但也显露出中国美学精神的特色和风格,“韵”和前面提到的“道”“气”“真”“自然”都是有关系的。“兴趣”是严羽《沧浪诗话》的中心范畴,“它指的是诗歌意象所包含的审美情趣”[3]314。这种情趣由外物触动内心而发。严羽又提出了“气象”,这个概念更为重要。“‘气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乃是概括诗歌意象所呈现的整体美学风貌,特别是它的时空感。”显然,这里又把意象和中国的审美文化联系起来了。“‘气’这个范畴,无论在中国古典哲学或是中国古典美学中,都是指宇宙万物的本体……诗论家用‘气象’一词来概括诗的整体风貌,特别是诗歌意象所呈现的时间感与空间感,恐怕与‘气’的这种含义是有关的。”[3]320“气象”的提出,把意象再一次引向中国哲学的天道,是“同自然之妙有”“度物象而取其真”等概念的推进,它加深了意象的审美文化内涵。
到了明代,美学理论中也有大量关于意象的研究。王履揭示了“意”(情意)和“形”(形象)在艺术作品中的矛盾,“也就是审美意象的内在矛盾”[3]322-323。祝允明又阐述了“象”和“韵”的关系,意象是“韵”和“象”的统一。王廷相“明确把审美意象规定为诗的本体”[3]332。
意象在明末清初进入到它理论的总结阶段。“王夫之的美学体系是以诗歌审美意象为中心的”[3]453。首先依然是意象的情景关系问题。“王夫之明确地把‘诗’和‘志’‘意’加以区别。另一方面,王夫之又明确地把‘诗’和‘史’加以区别。”[3]453-456这样,诗的意象美既不在主,也不在客,于是就自然得出了情景交融的结论。这是对从刘勰以来经过宋元诗歌美学对意象规定的总结。但王夫之更进一步,强调了“情”与“景”的统一方式,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外在拼合,而是有机的内在统一。基于此,王夫之对意象的具体形态作了分析,他举出了“情中景”“景中情”“人中景”“景中人”,并指出意象的具体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几种呆板的模式。然后王夫之又对诗歌的意象作了具体分析,规定了意象的整体性、真实性、多义性和独创性[3]466-479。叶燮的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深度,他提出:“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3]502叶燮首先说明,艺术的本质在于反映世界的“理”“事”“情”。“‘理’,就是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事’就是客观事物运动的过程;‘情’,就是客观事物运动的感性情状和‘自得之趣’。”紧接着叶燮又提出了“气”这个概念,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既然“理”“事”“情”是对世界客观规律的反应,那么它们和“气”也就是一回事,“气”是万物之根、之本、之源,“理”“事”“情”就是“气”的具体表达和说明。同时,“理”“事”“情”并不是一般性的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审美的反映,这样,“理”“事”“情”也好,“气”也好,就成了叶燮的艺术本源论,或称“现实美”[3]495-498。然而,仅仅是这样,还无法说明叶燮在审美意象上的贡献,于是他提出了“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艺术要写‘理’,但并不是‘名言之理’,即不是以抽象概念所把握的‘理’,而是通过审美意象反映的‘理’;艺术要写‘事’,也并不是‘可征之事’,即不是像历史实录那样照抄普通生活中的实事,而是通过审美感兴,创造审美意象,从而达到更高一级的真实。”[3]503于是,“情”也就不同于人之常情,而是从审美意象中生发出的艺术体验的情感。这样,叶燮就把现实美和意象美结合了起来。叶燮提出的“胸襟”概念也很值得重视。“‘胸襟’是审美感性的基础,它决定着审美意象的深层意蕴。”[3]517那这深层意蕴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生之感与历史之叹,以及审美意象的哲理性,这就又接通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和审美文化的情绪体验。
到了近代,对意象的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是王国维。王国维的美学著作中频频出现“境界”“意境”两个概念,但根据叶朗教授研究,这两个概念“并不属于中国古典美学意境说的范围,而是属于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说的范围”[3]603。而且,其中有很多是重复了前人的研究。他对意象研究的新贡献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他借用西方美学概念解释了‘情’与‘景’,把‘景’规定为‘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把‘情’规定为‘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态度’;二是明确把“情”也列入‘景’,指出:‘喜怒哀乐亦人心之一境界’;三是把审美意象分为‘以意胜’‘以境胜’‘意境两浑’;四是艺术的认识功能是由审美意象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五是‘境界’(实指‘意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比起其他美学范畴更本质、更重要,这几乎已经隐含了‘美在意象’的命题了。”[3]622-623接下来,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理论。其实,任何艺术创造都有作者的感情投入,因此并不存在真正的“无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分,其实是作者不同的情感状态和精神境界的分别。“有我之境”其实是“有情之境”,即作者依然执着于人世情感,欲罢不能;“无我之境”是对情感的超越,在这个境界中,作者走到了更高的阶段,看破人间万象,不再执着于感情,走向拈花微笑。尤其是“无我之境”,更能体现中国的艺术精神。王国维又提出“造境”与“写境”,其实是再次重申审美意象的情景关系,有偏重于情,有偏重于景,但作为意象的基本因素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中国古典美学中还有很多和审美意象有关系的概念,以上所描述的是最直接的对意象研究的内容。从这些大致的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意象存在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是情景交融,情和景和谐地统一在意象中;第二是意象和中国的本体论哲学紧密相连,与“道”“气”“真”“自然”“玄冥”“天人合一”等概念相同一。这样,由意象产生的审美体验,就是一种和谐、圆满、统一、静谧、浑融、恬淡、超然、物我两忘、拈花微笑和天人合一的状态。
二、意象难以涵盖西方的美
在西方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几乎找不到意象这一概念。唯一可以举出的反例,就是20世纪初美国的意象派诗歌,但它只是一个非常狭窄的诗歌流派,和我们古典美学中的意象不可同日而语[1]64。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核心概念的意象不见于西方美学和文论,不是偶然的,这完全是由中西文化的差异决定的。首先从地理上看,中华文明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发展,与外界缺乏交流,西方文明内部没有明显的地理阻碍,因此发展变化剧烈。据权威历史学家研究,文明的性格是由他们生存的环境决定的。就人类的发展来看,越是相对封闭的环境,由于缺乏竞争,没有被淘汰的危机,文明的进程就越缓慢[4]。因此,中国和西方拥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国是本分、安逸及和谐的黄土文明,西方是热烈、激进和冒险的海洋文明。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人生有三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向前奋斗;二是调和、持中并安于现状;三是朝欲望相反的方向去要求。西方文明走的第一条路,中华文明走的第二条路[5]64-65。受不同文化性格决定,又形成了不同的审美性格。
不过,西方文化虽然总体上走的是第一条路,但内在的路径并不如此简单,因此,与中华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审美性格要复杂得多。西方文化的一个源头,是古希腊文明。“罗伯特森论希腊思想有数点甚为重要:一是无间的奋斗;二是现世主义;三是美之崇拜;四是人神之崇拜。可见他们是以现世幸福为人类之标的的,所以就努力向前去求他。”[5]65-66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概括了古希腊的审美精神:“古代希腊人心灵所反映的世界是一个Cosmos(宇宙)。这就是一个圆满的、完成的、和谐的和秩序井然的宇宙。这宇宙是有限而宁静。人体是这大宇宙中的小宇宙。他的和谐、他的秩序,是这宇宙精神的反映……他的哲学以‘和谐’为美的原理。”[6]122-123这里可能有点疑问,照理说,既然文化上是无间的奋斗,似乎审美上不应该是和谐的。为何在此时此刻,希腊文明体现出了和中华文明相类似的审美风格?其实,这两种和谐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华文化是一种整体和谐的文化,人与自然相融,是一种静态的和谐,因此美学上才有在情景交融之中的大化流行、天人合一。在希腊文化中,“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地位高于自然,这是一种世俗人本主义的文化。它所指的和谐,主要是人性的和谐,即人从客观世界中独立出来,处于单纯的内部和谐的状态,而与客观世界相对立。这种和谐是局部的、动态的,也是不稳定的。“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丰富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在这宁静和雅的天地中生活着的人们却在他们的胸中汹涌着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中。”[6]199另外,希腊艺术重于再现,正是人们强调、突出人性,从而对有限世界崇拜、模仿的结果。这就完全不同于意象所强调的情景交融、天人合一了。
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是希伯来文明,它主导了西方文明的第二个阶段:中世纪文明。“他们与前叙希腊人的态度恰好相反,是不以现实幸福为标的——几乎专反对现世幸福,即所谓禁欲主义。他们是倾向于另一世界的——上帝、天国,全想出离这个世界而入那个世界。”[5]66如果说古希腊时期,人的地位高于自然,那么在中世纪,人的地位又反过来低于自然(上帝或世界)了。不过,在美学方面,中世纪倒是继承了古希腊的一个原则——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时指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两千余年。”[7]但是这个时候,模仿已经变换了它的含义。古希腊的模仿表现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崇拜和热爱,中世纪的模仿则是人对神的皈依。“艺术家进行创作就是对上帝的模仿,艺术家之所以模仿自然,是因为自然万物为上帝所造,只有模仿自然才能掌握上帝的‘技巧’。”[8]两者都注重再现,但前者是万物皆备于我,为人服务;后者则是拜物,通过拜物通向上帝。然而不管是哪一种,都不是情景交融的境界。其次,中世纪的美学风格是神本主义的,不管是奥古斯丁还是托马斯·阿奎那都认为,美源自上帝,上帝是美的本体。这当然也和意象所要求的审美风格大相径庭。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西方再次确立了人的重要地位,回到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立场。当然,这种回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阶段综合提高。宗白华先生指出:“文艺复兴以来,近代人生则视宇宙为无限的空间与无限的活动。人生是向着这无尽的世界作无尽的努力……近代西洋文明心灵的符号可以说是‘向着无尽的宇宙作无止境的奋勉’。”[6]123由于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压抑,这个时候西方人对人本主义的强调是空前的,人性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空前的欲望。同时,由于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近代西方人对宇宙的认识也递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已无法再回到古希腊的宁静和谐之中,再也不能和众神一起生活在大地上。神灵已被科学去魅,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于是美学终于打破了和谐和圆满,成了雄心勃勃、彷徨不安的浮士德精神。在情与景的关系上,这个阶段显得更为复杂。一方面,模仿说的影响更大了,塞万提斯、达·芬奇、布瓦罗、狄德罗、歌德、雨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黑格尔等一流的哲学家、艺术家纷纷强调艺术对于自然模仿的重要性[9]16-17。由于主体性的空前凸显,它便表现出对客观世界的强烈好奇心与占有欲。表面上看,再现是偏向客观,但这个时候的模仿却是主体对客体的掘进和征服。另一方面,艺术上的表现论作为与模仿相对立的另一极逐渐壮大起来,康德、席勒、柏格森、弗洛伊德和克罗齐等哲学家、美学家都是艺术表现论的倡导者[9]17-19。表面上看,强调表现与强调模仿完全相反,其实是相通的。表现论在近代西方的兴起,显然也是由于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导致心灵成为艺术表达的重点。它和模仿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朝着宇宙作无止境的奋勉,恰恰形成了互补。在这里我们发觉,和中国意象的情景交融、主客相统一不同,西方的艺术本体始终处于摇摆不定之中,时而偏向主,时而偏向客,时而重表现,时而重模仿。当然,表现的侧重点固然在主体,但模仿的重心却并不一定在客体,模仿也可能依然是对主体的强调。
20世纪是西方世界新的转折,不断向前去追求固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负面的影响也几乎让人类自掘坟墓。一方面,人类已无法重返神的怀抱,但重新确立起来的主体性又遭遇到挫折。在20世纪,人类失去了头上的一片天,又抽空了脚下最后的一块地,成了荒原上彷徨的孤儿,既不能向前走,也无法往后退,又很难就地寻得个安身立命之所,这样的状态就是“荒诞”。另外,20世纪的审美表达也和以前有巨大的不同。首先是艺术主体的衰落,这是不难理解的,向前的动力已经消失,蓬勃向上的主体自然会逐渐枯萎,主体失去了合法的依据,世界变成了存在的现象。而客体是由于主体才存在的,主体不见了,客体自然也不存在了。“由此,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的理论话语抛弃了传统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模仿、再现、意指和心—物关系等概念,转而使用诸如文本、结构、能指和所指等概念,语言观成了这种美学和艺术话语的核心。”[10]这既不同于西方的传统美学理论,更和中国美学大异其趣。
三、“美在意象”的双重困局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到,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概念,有其自身的存在特征,不管是其表层结构(情景交融)还是其审美实质(天人合一),都难以涵盖西方的美。换句话说,意象作为美的本体,不具有叶朗描述的那么大的兼容性。叶朗在《美学原理》第59页列出了意象的四个核心概念,他对这四个核心概念的论述贯穿了整本书:
第一,审美意象不是一种物理实在,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和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也就是中国美学所说的情景交融的世界。
第二,审美意象不是一个既成的、实体化的存在……而是在审美活动过程中生成的……审美意象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中。
第三,意象世界显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即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
第四,审美意象给人一种审美的愉悦……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使人产生美感。[1]59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叶朗对于意象的论述,基本还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立场。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却时有偏移,显露出调和中西美学的努力与困难。叶教授在书中一再强调,美是体验,美不是认识,美不是“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而是“天人合一”的存在论模式。对于前一点,笔者是赞同的,但却认为,审美体验未必就一定发生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之中,“主客二分”亦未见得就一定是逻辑的、概念的。前面分析过,在西方美学中,人与世界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主体与客体始终在变换着它们的关系,从总体上讲,都不是天人合一的模式。但审美同样在发生,当主体面对客体时,他好奇、紧张、征服和皈依,他因失败而悲壮,他因荒诞而滑稽……主与客并未走向物我浑融,而是始终在复杂的关系中搏斗。
叶朗在《美学原理》中反复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一方面疏远了中国古典的美学资源,另一方面对西方20世纪的美学理论资源的陌生。对于后者,他有相当的重视。他指出,西方美学发展到20世纪,已经突破了曾经的主客二分的模式,走入了天人合一的模式,代表性人物就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和杜夫海纳等。叶教授提到的这几位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家,都属于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这个系列,他们的理论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但实质是不一样的。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此在”“澄明”“诗意的栖居”以及杜夫海纳的“灿烂的感性”等概念,是建立在西方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主体与客体反复较量的结果。这和中华文明在童年时期就进入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早熟的文明,一个是按普通次序发展的文明。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结果而忽略过程。将20世纪西方的现象学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相类比,是有理论意义的,但也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中国美学一开始就达到了西方20世纪美学的发展水平,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而这种中西美学形态上的倒错格局,也透露出中国美学的某种缺失。其次,现象学美学家的“生活世界”“澄明之境”的背后依然是基督教文化,而并非中国“天人合一”背后的“道法自然”。
多年以来,一些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比如李怡教授就借穆旦的诗歌表达了对中国美学的看法:“追求物我浑融的‘意境’效果的古典诗歌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空间结构艺术,即往往从诗人的视角出发,勾勒出一个‘天容时态,融合贻荡’的宇宙空间来,‘俯拾即是,不取诸邻’……空间结构意在建构完整的空间画面,以勾连式的自然过渡联系情感,也平衡着情感,尤其重视思绪发出之后的收回,‘众鸟高飞尽’的最后必定是‘只有敬亭山’(李白),‘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终究要落回‘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卞之琳)”,“打破‘天人合一’,挣脱了自然形象的束缚,强化主体意识,凸显自我,穆旦诗歌获得了异常丰富的表现潜能,传达着微妙、幽深而复杂的现代情绪。”[11]
其实,以上这些问题,在叶朗的《美学原理》中是有所显现的。由于建立哲学上的概念都是不完全论证,因此,在论说过程中,叶教授主要选择的是那些符合情景交融、天人合一模式的艺术作品,像西方文学艺术中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神曲》《巨人传》《莎士比亚全集》《堂吉诃德》《浮士德》《唐璜》《荒原》和《等待戈多》则完全没有提及。而且,叶朗的意象也存在分裂的情况,换句话说,我们经常感觉到他所说的是两个意象。当他对意象做理论上的总体规定时,他固守的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当他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意象往往是泛化的。比如他分析梵高的作品《一双鞋》,就只强调鞋不是物理实在的一双鞋,而是一个充满感性的艺术世界,但这样的论述其实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几乎任何人都知道艺术作品中的鞋不是现实中的一双鞋,而是作者表现的对象。如果这样就叫意象,那意象就大大地泛化了。梵高作品中的那双鞋,破旧、斑驳和阴暗,它表现的是一个农妇的苦难世界,这里只有现实的悲剧命运,而没有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在另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比如说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就是能不能“兴”,能不能产生审美意象和美感。显然,此时此刻,作者已经把中国美学的文化内涵抛到一边去了,也把天人合一抛到一边去了。
因此,总结起来,“美在意象”的双重困局就是,要么固守中国古典美学的立场而无法涵盖西方的美,要么就是将意象的概念泛化,只保留其情与景作为艺术品存在的基本条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这就是“美在意象”的悖论所在。“美在意象”的双重困局,植根于中西美学以及文化的根本差异。在当代的中国美学界,这样的理论建设自有其价值和意义,但对其局限的指出和研究,也同样是必要的,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中西美学和文化之间的一些问题,并在中西美学和文化的语境下,更深入地推进21世纪中国美学的基本理论建设。
[1]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章启群.百年中国美学史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0.
[5]梁漱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29.
[8]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缪灵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1.
[9]吴中杰.文艺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牛宏宝.西方现代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5.
[11]杜运燮,周与良,李方,等.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G].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19-120.
责任编辑:罗清恋
The Double Dilemma of the Theory that“Aesthetics Lies in the Image”
LIU Lujia
(“Red Rock”Literary Magazine,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ongqing,Yuzhong Chongqing 400015,China)
In the paper,in terms of the theory that“aesthetic lies in the image”put forward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Ye Lang in his book named“Aesthetic Principle”,a research was made based on the fully affirm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ory construction,and the defects and problems were pointed out.On the one hand,the related study of image in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history was clarified;on the other hand,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and culture was described.In the comparative field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aesthetics,the double dilemma of the theory that“aesthetics lies in the image”was pointed out,that is,either to stick to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and no cover of the western aesthetics,or to generalize the image,and only to maintain the feelings and views as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art.As a result,it is in the double dilemma.
aesthetic lies in the image;combination of emotion and scenery;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people;experience; aesthetic culture;image generalization
B83
A
1673-8004(2017)02-0080-07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2.015
2016-06-12
刘鲁嘉(1983—),男,山东青州人,编辑,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及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