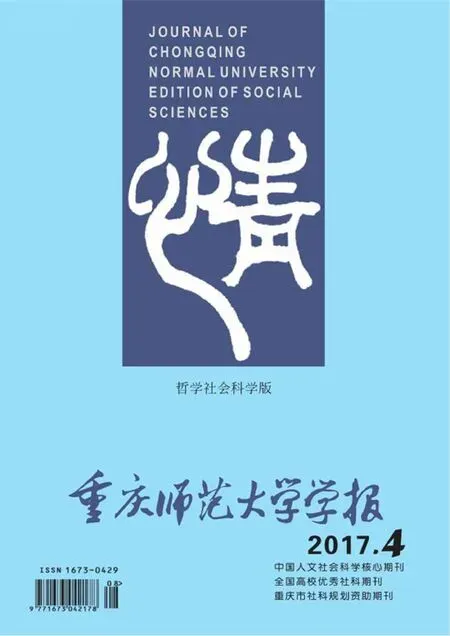古代斯里兰卡与中国的交流与互动
刘 耀 辉 唐 春 生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古代斯里兰卡与中国的交流与互动
刘 耀 辉 唐 春 生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交往历史悠久,最早可以回溯到汉朝。在中、斯交流史上,两国存在多种形式的联系,包括文化互动、经贸往来和官方外交。佛教文化是连接两国的重要桥梁,这种信仰还促进了两国的经贸和政治交流。两国之间以和平为主旋律的交流与互动,大大促进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中斯两国的交往是印度洋贸易和全球交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往来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之间联系的加强,为世界的整体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斯里兰卡;交流;互动;佛教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海上新丝路”途经的国家多达几十个,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北非和欧洲连接起来。对此,大多数国家高度认可,印度洋地区的斯里兰卡明确表示支持。事实上,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往来,早在汉朝就开始了。
关于古代中斯之间的往来,中国、斯里兰卡、希腊和罗马等国的文献都有不少记载。斯里兰卡古代文献把中国称为“支那国”(Cinaya)或“摩诃支那国”(Maha-cinaya),而中国古籍关于斯里兰卡名称的记载,至少有30多个。[1]1,104汉平帝(公元1—6年在位)时,汉朝曾派出使团抵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沿海地区)。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说到“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2]卷28《地理志下》,1671。有些人认为,已程不国即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方面来看,公元1世纪初的一些文献,也记载了斯中两国的通航信息。[3]52-53魏晋以来,双方在文化、经贸和政治上开始了频繁而友好的往来。古代历史上中斯两国的这种交往,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葡萄牙人对斯里兰卡的殖民活动。
一、以佛教为核心的文化交流
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中心,有“佛法之岛”的美誉。公元前3世纪,佛教教义传入斯里兰卡,公元1世纪,上座部大藏经得以用文字记载下来,这是僧伽罗人对人类知识遗产作出的重大贡献。[4]20在中国方面,两汉交替之际,佛教开始传入,汉明帝(57—75年在位)时,佛教得到正式认可。此后,中国与南亚佛教社会的交流开始增多。
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斯文化交流
佛教传入中国后,许多虔信的僧人不畏艰辛,前往印度和斯里兰卡游历和求取真经,归国后,带回大量佛经。同时,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南亚许多僧人也来到中国,他们致力于译经和弘法。这些人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文化的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呈兴盛状态。此一时期,许多中国僧人西行取经,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399年,法显(337—422)与同伴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在游历了印度许多佛教圣地之后,又决心去斯里兰卡继续求法。410年,法显自印度南渡斯里兰卡(师子国),在岛上生活两年之后,于义熙八年(412)归国。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求法期间,法显抄写了大量佛经,其中在斯里兰卡抄写的经书有四部:《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以及《杂藏》。
法显归国后,著《佛国记》一书。他在书中对斯里兰卡历史传说、地理、气候、物产、社会风俗以及佛教文化都做了记载。《佛国记》是研究斯里兰卡的珍贵资料,多次被译成僧伽罗语,书中的一些内容,甚至斯里兰卡的历史文献也未曾提及。法显对佛教的虔诚以及求法时不畏险阻、勇于探索的精神,在中斯两国备受推崇。国内有学者指出,他在中斯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上的贡献有三:记叙和介绍斯里兰卡,取回经、律以及为两国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道路。[5]82法显不仅是中斯友好交往的象征,同时也是古代世界跨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此一时期,斯里兰卡积极推进双方文化交流。斯里兰卡国王优波底沙(Upatissa I, 365-406)听说晋孝武帝崇佛,派沙门昙摩前往中国,并带来一尊玉佛像。《梁书》卷五四《诸夷列传》载:“晋义熙初,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6]卷54《诸夷列传》,800
公元428年(刘宋元嘉五年),斯里兰卡国王刹利摩诃南(406-428)派使团携国书和礼物到达中国,在致宋文帝的国书中说道:“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7]卷97《夷蛮传》,82在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有一座“牙台像”,即供奉佛牙的台座模型,在斯里兰卡,该物件被视为向外国赠送的最珍贵礼品。[8]26
429年,斯里兰卡有八位比丘尼来宋;433年,斯里兰卡舶主难提带来比丘尼十一人。[1]99434年,师子国比丘尼共同为中国300余尼众重授尼戒。自此以后,中国佛教始有比丘尼戒。
北魏时期,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在455年(太安元年)“奉佛像三,到京都(今大同)”[9]卷114《释老传》,3036。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师子国僧人参与了云冈石窟的修造。[8]27
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502-549年在位)被称为“皇帝菩萨”,曾多次舍身同泰寺,南朝佛教也在此时达到鼎盛。梁大通元年(527),狮子国国王的使者所携国书声称:“谨白大梁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方国诸王……无远不至……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6] 卷54《诸夷列传》,800
由此可见,在法显之后的南北朝时期,海道比较通畅,中斯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斯里兰卡僧人和比丘尼到中国传播佛教教义和戒律,促进了南朝佛学的繁盛和宗教艺术的发展。
第二,唐宋时期中斯文化交流
唐朝时期,中斯两国佛教文化的交往进入又一个高峰期。唐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对外采取了开放姿态。当时有许多僧人西行求法,其中著名的有玄奘和义静。他们未曾去过斯里兰卡(当时通常被称为师子国),不过,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都较详细地记载了斯里兰卡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此外,有许多中国僧侣到达师子国,他们或“观风弘教”、或“披求异典”、或“观礼佛牙”。[10]81
斯里兰卡也非常重视与唐朝的交往。7-8世纪,斯里兰卡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大唐。斯里兰卡也有多位僧人来到中国。唐中宗时,僧人目加三藏来到中国,并拜访了中国僧人兰若。[11]147最著名的当属僧人不空金刚(705-774),他推进了唐朝与斯里兰卡的友好往来。不空原为婆罗门教徒,后随叔父来中国,并且定居下来。他最初跟随在中国弘扬佛法的印度人金刚智学习,后来又前往印度和斯里兰卡求法。746年(天宝五年)初,不空返回长安,并且带来斯里兰卡国王呈递的国书和礼品。[12]150-151此后,他在中国致力于译经和弘法。
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斯里兰卡沙门妙德献舍利和佛经,受到宋真宗的赏赐。不过,公元9-11世纪,中文文献关于中斯两国交流的记载较少,其原因在于南印度强大的朱罗王国侵占斯里兰卡,并掌控印度洋海上交通,从而对其他国家与斯里兰卡的来往造成阻碍。[13]164,141
第三,元明时期中斯文化交流
元朝时期,中斯之间官方往来又呈现出频繁之势。斯里兰卡国王波罗伽罗摩巴忽三世(Parakramabahu III, 1287-1293)曾向元朝派遣使团,他的军队里有中国士兵。[3]53-54而元朝统治者也多次派人去斯里兰卡学习佛法。比如,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世祖派亦黑迷失去僧迦剌国(斯里兰卡)观佛钵舍利。[14]卷131《亦黑迷失传》,3198-3199
明朝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时,多次随行的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和巩珍(著《西洋番国志》)等人的著作,都对斯里兰卡做了记载,而且内容比以往作品更详尽。这些著作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对斯里兰卡的了解和认识。
二、频繁的经贸往来
在古代印度洋贸易体系和东西方贸易中,斯里兰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公元1世纪,罗马史学家普林尼就对僧伽罗人的航海做了考察,当时,僧伽罗人可以到达西南部的阿拉伯,而红海地区的水手也能够抵达印度和斯里兰卡。5-7世纪期间,红海地区的阿杜利斯、波斯湾的奥波拉黑、印度西海岸的巴里加扎和南部的古吉拉特以及斯里兰卡,成为印度洋贸易圈的重要贸易中心。斯里兰卡是贸易中转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波斯人和阿克苏姆人通常只航行到斯里兰卡,然后在那里等待从东方来的商品。另外,斯里兰卡本地盛产宝石、珍珠、布匹和贝壳等,同时,还可以为远道而来的商人和航海者提供必备的航海设备。6世纪,斯里兰卡成为印度洋贸易的枢纽,东西方产品在此汇集和重新分配。[15]13-1411世纪以后,随着僧伽罗人政权的南移,斯里兰卡西南沿海兴起一些重要的港口,最著名的是别罗里。[16]50别罗里与印度洋地区的其他港口形成了一张贸易网络,把印度洋以东地区与阿拉伯世界、非洲东海岸和欧洲连接在一起。
中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者,这种商道又有海陆之分。海上丝绸之路连通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以及地中海世界。斯里兰卡正好就是这条商贸要道的必经之地。中国丝绸和瓷器在斯里兰卡很受欢迎,而斯国输往中国的物产主要有猫眼宝石、麝香等。中斯两国在贸易上互通有无,这种经贸往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
第一,中斯贸易源远流长
汉朝开始大力拓展经由海上通往西方的商道。汉武帝平定南方后,在今广东地区置郡,然后派船只携带丝绸和黄金从徐闻(今湛江附近)、合浦(今北海附近)出发,途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再到南印度地区,去换取当地特产,并且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是中国丝绸经由海路外传到这些国家的最早记载。当时中国丝绸已经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主干线传入斯里兰卡。[17]162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航线和贸易都有记载,提及了都元国、邑庐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庐国、黄支国、已程不国等地。[2]1671普林尼(23—79)的《自然史》一书,就有斯里兰卡与汉代中国贸易往来的内容。出访罗马的斯里兰卡使臣也谈到斯里兰卡与中国的贸易,并且宣称自己在出使的路上碰到过赛里斯人(中国人)。[15]13当时,由于航海、造船技术的制约,以及穆斯林的阻碍等原因,罗马与中国之间还没有实现直通,东西方贸易往来必须经过南亚次大陆南端和斯里兰卡中转。因此,在公元1世纪东西方贸易中,斯里兰卡表现得很活跃。
法显西行求法期间,在斯里兰卡住了两年。据记载,有一次,他在寺庙参拜时,看到一尊玉像旁供有一把晋地白绢扇,勾起思乡之情。由此可见,中国丝货当时已经被人带到斯里兰卡。法显出发时走陆上丝绸之路,回国时乘商人大船经海道返回,大船上还载有众多商人。这表明,在法显之前,中斯两国商人早有来往,自斯里兰卡经爪哇到广州的航道,也已经为商人所熟悉。[10]77公元6世纪初,希腊人科斯麻士(Cosmas)对经由这条海道进行的东西方贸易做了记载。他指出,中国和东方其他地区输出到锡兰(斯里兰卡)的物品有丝、伽罗木、丁香、檀香等。[18]45当时,锡兰是中西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和中转站,东方的这些商品再从这里销往阿拉伯世界、非洲东部沿海和欧洲。
第二,官方外交促进双方贸易
自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和产品尤其是丝绸的外传,中国对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很多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来与中国通好,以求获赠丝织品和获得贸易机会。历史上,斯里兰卡多次向中国派遣使团贡献物品,中国统治者则予以回赠。从公元2世纪开始,斯里兰卡国王就不断派使团到中国,有些访问纯粹是为了宗教目的,但毫无疑问,他们旨在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以争取更大的贸易往来。[3]54
南朝刘宋时,公元430年和435年,师子国两度派使者贡献礼品。[7] 卷5《文帝本纪》,79、83至唐朝时期,斯里兰卡多次派人朝贡。唐高宗总章三年(670),斯里兰卡国王就遣使朝贡。[19]卷221下《西域列传下》,6258睿宗景云二年(711)十二月,狮子国“遣使献方物”[20]卷970《外臣部》,11404。玄宗天宝初年(742),斯里兰卡国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氎。[19]卷221下《西域列传下》,6258
辽圣宗统和七年(989),师子国曾遣使到辽国入贡。[21]卷12《圣宗本纪》,133元朝时期,海外贸易更加繁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元朝建交的国家达220多个。[22]36早在忽必烈时期,元朝多次向斯里兰卡派出外交使团。至元十年(1273)正月,忽必烈派长子阿不合至师子国购买药品。[23] 卷8《世祖本纪》,148斯里兰卡国王也多次向中国派遣了使者。13世纪,斯里兰卡不仅积极与中国贸易,而且也希望支配西印度洋贸易,例如,1283年,国王布瓦列卡巴胡派遣使者前往埃及宫廷,表达了在贸易上合作的愿望[15]17。
明朝时,斯里兰卡多次遣使来朝,《明史》均有记载。明初的“海禁”妨碍海上贸易的发展,不过,郑和的航海进一步把海上丝绸之路推向新的高潮,也促进了印度洋贸易的繁盛。明成祖时期,斯里兰卡国王波罗伽罗摩巴忽六世(Parakramabahu VI, 1412-1467)三次遣使来朝,此后还在1433年(宣德八年)、1435年(宣德十年)、1445年(正统十年)和1459年(天顺三年)向中国派遣使团。16世纪,西方殖民者开始向亚洲殖民,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先后侵占斯里兰卡,天顺三年来华成为斯里兰卡沦为殖民地之前的最后一次觐见。
第三,斯里兰卡出土大量中国瓷器和钱币
唐朝国力强盛,空前开放,中外交流频繁。中国的丝瓷和茶叶等商品经丝绸之路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同时,这些地区的宝石、药材和香料等特产不断运到中国。
唐朝中期以后,陆上丝路日趋衰微(元朝时期一度畅通),海上贸易繁盛。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中国船只频繁出现在波斯湾地区。唐代宗时期(762—779年),每年来广州的商船可达4000余艘,广州城阿拉伯侨民多达数万。[15]15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斯里兰卡的地位相当重要,它不仅是中国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经贸往来的中转站。此一时期,中文文献有关中斯贸易的记载,也越来越多。《唐国史补》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24]卷下,199
宋代,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对外贸易主要依赖海路。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繁盛,政府也鼓励海外贸易。此时,泉州港异常繁盛,与外海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00多处,港口货物堆积、品种繁多、船只无数、商人肤色各异。此时,中国的远洋船只远达非洲东北角。
唐宋时期,陶瓷成为中国输出的主要产品之一。在斯里兰卡古港口和一些寺庙遗址中,比如西北部的港口曼泰和古都阿努拉达普拉附近的无畏山寺等地,都出土了大量中国瓷器及其碎片,其中一些可以回溯到唐朝。[13]96-107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也对斯里兰卡一些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查和分析。[25]143-145
随着丝瓷的外销,中国商品货币经济的影响也扩及海外,中国的铸币成为交换媒介,也带动了当地货币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古钱币陆续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和寺庙中被发掘出来。其中重大的发现有两次。1911年,考古学家在耶波弗伐(Yapahuw)发现了1452枚中国钱币(最早的为“半两”钱)。2009年,有农民在库鲁内拉加发现了4000余枚中国古钱币,在将近一半散失之后,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收购了剩余的2000余枚。[13]61-62
三、中斯合作前景广阔
在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斯里兰卡与印度次大陆息息相关,不过,历史上斯里兰卡多次遭到来自南印度国家的入侵。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大肆进行殖民活动,也给斯里兰卡人民造成灾难性影响。与此相反,中国的外交策略,无论是历史上的“怀柔远人”,还是当代的“和平共处”原则,都有助于推进新时期中斯关系的发展。
首先,历史上两国友好交往增强互信。
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始于汉朝。此后,两国在文化、经贸和官方外交上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时至今日,法显在斯里兰卡仍然备受尊崇和赞美,他是两国友好交往的见证。法显之后,两国友好往来不断。1911年在斯里兰卡港口城市加勒(Galle)发现的郑和布施碑,是中斯两国友好往来的又一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斯里兰卡无视西方对中国的敌视和封锁,在1952年与中国签订《米胶贸易协定》,此后双方往来频繁,进入21世纪,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建设投资大幅增长,两国联系进一步加强。
其次,中斯两国发展战略契合。
斯里兰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被誉为“印度洋上的珍珠”,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转运中心,连接着中西方的贸易,今天依然扮演着这种角色。现今,东亚、东南亚地区与中东的石油贸易,都需要途经斯里兰卡,而中国进口石油的九成需要经过斯里兰卡中转[26]10。因此,建构中斯友好关系对中国能源和国家安全尤为必要。
2013年5月,中斯关系发展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斯里兰卡。习近平主席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后,斯里兰卡予以高度认可。中国的这个构想与斯里兰卡在2009年提出的“马欣达愿景”高度契合(即把斯里兰卡打造成为海事、商业、能源、旅游和知识中心)。另外,从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平衡来看,斯里兰卡也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以此增加在印度洋地区的外交筹码,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
第三,佛教文化交流巩固两国关系。
宗教和文化认同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南亚地区,不少国家的民众信奉佛教,因此,以共同的文化信仰来推动双边或多边合作,成为常见的外交手段。在亚洲,斯里兰卡是培养佛教人才的中心,也是中国佛教徒最喜欢前往的留学国家。中国佛教留学僧在带去中国文化元素的同时,对斯里兰卡社会和生活方式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和更正确的认识,最终促进了中斯两国的文化交流。[27]1、9
纵览中斯两国交流史,在官方外交背后,佛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佛教也能够发挥这种积极作用。事实上,中斯两国高层的互访,通常都伴有与佛教相关的活动。通过佛教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认同,可以进一步巩固两国的联系。
第四,中斯两国合作领域广泛。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区和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中国在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斯里兰卡在内战、海啸之后,急需恢复遭受破坏的国内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中斯可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目前,中国是斯里兰卡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斯里兰卡则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6]12中斯双方的合作,涉及工业、投资、能源、科技、基础设施以及旅游等领域。此外,随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文化也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斯里兰卡对中文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当前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斯里兰卡民众对中国的认可,我们在向斯里兰卡投资时,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向民生工程,让当地人民从中斯合作中获得切实的利益。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的交通枢纽,长期以来扮演了连接中西方贸易的角色;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起点,而丝绸之路又是古代世界中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由此可见,历史上中斯两国大力推进了古代世界联系的加强。当前,在新机遇面前,两国政府和人民会继续发扬友好交往的传统,为地区稳定和繁荣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1] 索毕德.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研究[D].山东大学,2010.
[2] 班固.汉书 [O].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W.S.A.Padmi Dilrukshi Wanigasundara (迪茹茜),吕军,阎晶宇.试论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以文献及相关文物为中心资料[J].博物馆研究,2010,(2).
[4] K.N.O.Dharmadasa.法显在斯里兰卡[J].佛学研究,2011.
[5] 邓殿臣,赵桐.法显与中斯佛教文化交流[J].南亚研究,1994,(4).
[6] 姚思廉.梁书 [O].北京:中华书局,1973.
[7] 沈约.宋书 [O].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索毕德.晋代至唐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教文化交流[J].安徽大学学报,2009,(4).
[9] 魏收.魏书释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 许道勋,赵克尧,范邦瑾.汉唐时期中国与师子国的关系[J].复旦学报,1980,(6).
[11] 杜拉(D.Sarananda).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文化比较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12]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3] 查迪玛.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兼谈古代中斯贸易关系 [D].山东大学,2011.
[14] 宋濂等.元史[O].北京:中华书局,1976.
[15] 李柏槐.古代印度洋的交通与贸易[J].南亚研究季刊,1998,(2).
[16] 李大伟.公元11—13世纪印度洋贸易体系初探[J].历史教学,2013,(2).
[17] 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J].历史研究,1982, (3).
[18] 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 [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19]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 [O].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O].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本).
[21] 脱脱等.辽史 [O].北京:中华书局,1974.
[22] 梁励.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9).
[23] 宋濂等.元史 [O].北京:中华书局,1976.
[24] 李肇.唐国史补[G]//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5] 三上次男.斯里兰卡发现中国瓷器和伊斯兰国家瓷器——斯里兰卡出土的中国瓷器调查纪实[J].江西历史文物,1986,(1).
[26] 司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架下深化中国—斯里兰卡经济合作研究[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6,(2).
[27] 惟善.当代中国佛教留学僧运动——以斯里兰卡国佛教留学僧为例[J].世界宗教文化,2006,(2).
[责任编辑:刘力]
TheCommunicationsandInteractionsbetweenChinaandSriLankainAncientTimes
Liu Yaohui Tang Chunshe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ri Lanka have a long history, dating back to Western Han Dynasty. There were multiple forms of connect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ancient history, including cultural interactions,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nd official diplomacy. Buddhism acted as an important bridge and promoted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ti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The peaceful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ri Lanka greatly adv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in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 the exchange between two countrie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webs of Indian Ocean trade and global trade, and has facilitated the links between various regions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hina; Sri Lanka;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uddhism
2017-04-07
刘耀辉(1976-),男,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唐春生(1964-),男,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校级项目“全球史视野下斯里兰卡历史上跨文化交流研究”(项目批准号:2014GB01)阶段性成果。
K358
A
1673—0429(2017)04—0088—06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李石岑的两层人格诠释及启示
-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 论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科学化理念
- 职业教育教师培训集团构建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