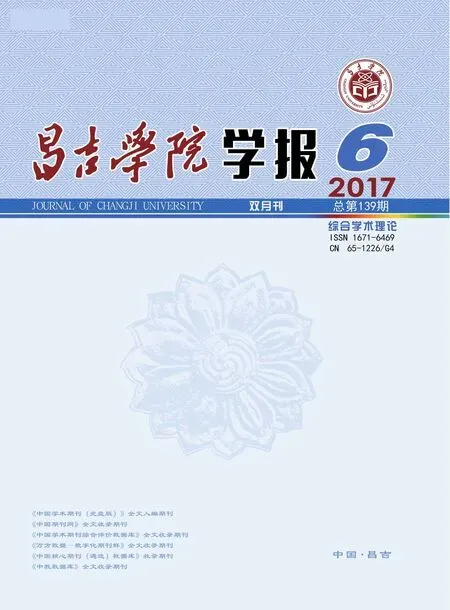唐·德里罗《天秤星座》中的后批判与反思
邓伟英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 广东 罗定 527200)
唐·德里罗《天秤星座》中的后批判与反思
邓伟英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 广东 罗定 527200)
《天秤星座》作为后现代作品,具有多元化、独特性等特点,文中包含社会、文化、情境描述、政治、种族、个人等多维度的冲突和矛盾。德里罗通过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深入解构和重构,剖析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以及基于霸权地位所施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天秤星座》中后批评与反思还依赖于对德里罗的深入解读,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深入的解构,有利于打破社会、国家、人文、传统等束缚,使人们对于人生、社会事件具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人们的思想达到空前的水平。
后现代批判;反思;唐·德里罗;《天秤星座》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多重艺术融合的结果,没有精准的界定和规范,具有多元化、独特性等特点。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从哲学和建筑学领域到文学等领域的不断发展的历史,分别始于哲学和建筑学领域的反对全球性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和法国的结构主义。综合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对统一界定、道德以及权威的解释,肯定一切事物发展的可能性的艺术派别,包括社会、文化、情境描述、政治、种族、个人等多维度,在文学、建筑等多领域占重要地位。基于后现代主义对事物发展可能性的认知,在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一系列高水平的后现代文学作品,打破社会、国家、人文、传统等束缚,使人们对于人生、社会事件具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人们的思想达到空前的水平。
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天秤星座》是后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解构,分析这一遇刺事件所包含的社会、政治、种族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采用渲染等手法弥补历史对这一事件的空缺,对美国当时的社会现状、政治黑暗等进行后批判和反思。后现代主义与批评相结合,充分利用后现代主义在政治派别、信仰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深刻揭露政坛、社会等存在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天秤星座》中存在的政治、政策等问题进行后现代主义批评,依赖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解构和重构功能,这样有助于实现对政治等问题和矛盾的反思,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提供参考。本文通过对《天秤星座》中存在的意识形态进行解读,从《天秤星座》的隐喻方面进行探讨,进而研究对《天秤星座》进行后批评和反思,提供社会和国家对历史、制度、政治等的反思。[1]
一、《天秤星座》中存在的意识形态
《天秤星座》作为肯尼迪遇刺事件的第一个后现代主义作品,使得其在出版后就受到广大群众的追捧和喜爱,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想象再现,是作者对社会、国家制度等方面的批评与讽刺,包含多种意识形态,只有真正理解和认识《天秤星座》中的意识形态,才能进一步了解《天秤星座》的隐喻,为《天秤星座》的批判与反思奠定理论基础。弗兰克·伦特屈夏认为《天秤星座》中的枪手奥斯瓦尔德是美国社会中部分人的代表,暗指受媒体导向指引,深陷卡里斯玛(Charisma)媒介的社会病理人物,弗兰克·伦特屈夏的观点在《天秤星座》的后现代解读中居于关键地位。彼得·耐特从《天秤星座》的主旨出发,从文章目的、叙述风格以及观念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认为《天秤星座》的目的是围绕事件发生的时间巧合性进行事件的阴谋理论评述,进而剖析其蕴含的因果观,为小说的主旨认知提供参考。卡瓦德罗从《天秤星座》中蕴含的情感角度进行剖析,结合小说人物心理构建的暴力事件,分层次的分析肯尼迪遇刺事件,构建了一幅充满阴谋论的历史事件画作。[2]
小说人物主体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是认识后现代文学的重要视角,有助于深度分析小说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充分了解《天秤星座》中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天秤星座》的后批评和反思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反映其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反抗意识。基于意识性的马克思发展,《天秤星座》中意识形态包括大众和媒介意识形态等,具有不真实、虚假的特点。《天秤星座》中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在阴谋家希望逃避“猪湾事件”的责任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奥斯瓦尔德本身对于托洛茨基的崇拜和模仿,希望通过行动改变自身的历史地位,他本身就是一个受意识形态控制的人偶,通过分析奥斯瓦尔德进行大众和媒介意识形态的探讨,对于理解《天秤星座》的意识形态具有推进作用。[3]
(一)《天秤星座》中的大众意识形态
从大众意识形态来说,奥斯瓦尔德在美国的历史中不断希望改变自身在历史制造的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采取一系列行动进行反抗,但他的一生都处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受阴谋家的摆布,没有突破自身在意识形态的地位,是一个悲剧的人物。随着场景等空间布局的转变,虽然奥斯瓦尔德受不同的意识形态控制,但不变的是从来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些都是基于奥斯瓦尔德成长经历。奥斯瓦尔德在少年时期跟随妈妈生活,一直生活在贫穷困苦之间,受经济、人际关系等的影响,经常处于被欺负的困境中。奥斯瓦尔德希望通过努力学习摆脱这种困境,进行命运的抗争,在学习的过程中奥斯瓦尔德发现了新的大陆,是一个与现实的贫穷困苦截然不同的世界,通过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的大量阅读,使奥斯瓦尔德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以及工人的抗争,同时还深切认识到自己是时代和人类知识的产物。基于阅读就是抗争的认识,奥斯瓦尔德更加沉迷于阅读和写作,希望通过阅读开拓眼界,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改变自己社会地位边缘化的现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影响奥斯瓦尔德最深的理论。[4]
但马克思主义不是驱使奥斯瓦尔德接受刺杀总统任务的重要原因,奥斯瓦尔德刺杀总统主要是基于其成长的特殊的时代所决定的,就如不同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美国人那么多,为什么是奥斯瓦尔德在那个时机进行刺杀总统。奥斯瓦尔德还是基于冷战时期美国文化的大众化产生的,是受大众化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美国文化正在从高雅化、文学化的方向向通俗化、流行化发展,是文化发展大众化和流行化的产物。奥斯瓦尔德非常喜爱弗莱明(Fleming)的《詹姆斯·邦德》,这本小说就是流行文化的产物,主人公詹姆斯·邦德在追逐罪犯的过程中总是能凭借聪敏才智化险为夷,邦德认为世界上的人物分为两种,即主张非黑即白观念。奥斯瓦尔德对詹姆斯·邦德的喜爱使得其世界观处于二元化状态,认为世界的问题和人都能归于善和恶的分类中,使得其自身具有两种属性,既可以受正义力量的引导成为正义的化身,也可能受阴谋家等反派人物的蒙蔽成为帮凶。在德里罗对奥斯瓦尔德眼中的城市空间格局描述中就有其二元世界观的伏笔和体现,是德里罗对奥斯瓦尔德二元世界观的构建和准确描述。奥斯瓦尔德利用希尔德(Hidell)作为自己的假名,其中饱含其对权力的渴望,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奥斯瓦尔德简单、机械的二元世界观。奥斯瓦尔德不断想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贫穷困苦地位,但却往往将自己置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将自己的社会地位置于边缘化的境地[5]。
奥斯瓦尔德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认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理论,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使得奥斯瓦尔德的二元主义世界观并没有产生转变。这是因为奥斯瓦尔德处于大众的影响中,接受的文学熏陶和感染不仅有高雅的,大部分还是大众化、多元化的文学,这些导致奥斯瓦尔德对权力等的欲望不断加深。基于多元化、大众化文学熏陶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奥斯瓦尔德影响中的作用不断弱化,奥斯瓦尔德认为的利用“马克思主义”观念进行的意识控制和行为实施,实质是大众意识作用的产物。但大众意识形式并不是一直控制奥斯瓦尔德的意识形态,在奥斯瓦尔德屈服后现代掌控(Lentricchia)的过程中,媒介意识形态在奥斯瓦尔德的转变中处于较高地位。
(二)《天秤星座》中的媒介意识形态
基于媒介的操作性、可控性等特点,资本主义利用媒介意识欺骗大众的方式比早期的通过权力、强迫等方式进行压榨具有明显的先进性,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统治形态,在社会和国家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意识形态通过对大众的思想灌输,从而达到意识控制的目的,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奥斯瓦尔德在英雄主义小说、流行化小说、电视、广告等媒介的影响下,受殖民主义的控制为统治阶级所迷惑。现实就是掩藏欲望的城堡,使得冷战时期的美国受虚幻的意识形态所笼罩,是人们用来掩藏欲望的国家,受虚幻的媒介意识形态的控制。德里罗所塑造的奥斯瓦尔德正受现实的压迫,使得现实在其眼中就是虚幻的现实。基于奥斯瓦尔德对于现实的认识,奥斯瓦尔德在社会分工中具有创伤的属性,詹姆斯·邦德等个人英雄主义为其提供了发泄的机会,奥斯瓦尔德在“现实”中模仿和带入人物的主体性,使得其表现出表面上的抗争,实质上沦为阴谋家的棋子,对其创伤性社会分工没有明确的改善。[6]
奥斯瓦尔德在观看《白噪音》中杰克死亡的过程中仿佛自己正在经历死亡,透过杰克的死亡,奥斯瓦尔德将自己的世界与外界的世界联系起来,找到所谓的实现价值、命运抗争的途径,这个过程实质是奥斯瓦尔德去人格化的过程,是受媒介意识形态控制的体现,在奥斯瓦尔德悲剧的过程中起着转折的作用。由此可见,媒介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思维,控制人们行动。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具有控制性、去主体性、去人格化的特点,在《天秤星座》中体现为奥斯瓦尔德在不断观看《白噪音》中杰克死亡的过程实质就是不断谋杀自己、去人格化的过程,是媒介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从中也可以看出德里罗对社会、制度等的后现代批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等高科技媒介逐渐出现,科技媒介是传统媒介的升级,在帮助人们构建“完美生活”的同时,实现媒介意识形态的掌控。此外,基于科技媒介的透明性、严密性等特点,科技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易被发现,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世界观、价值观等,人们处于媒介的影响下,逃离媒介的控制具有较大的困难。
由此可见,通过对德里罗在《天秤星座》的意识形态分析发现其中饱含许多颠覆和隐喻,这些颠覆和隐喻的实质就是利用后现代的手法对创伤性社会分工、人们地位、阴谋家等社会制度、政坛黑暗的批判,希望通过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渲染解构重构,让社会大众意识到奥斯瓦尔德代表的是大部分人民群众的悲剧人生,是在自以为是的反抗中被阴谋家等统治阶级利用的棋子,是美国冷战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产物。
二、《天秤星座》中的后批评与反思
《天秤星座》包含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种族冲突等多方面问题,深刻揭露了美国冷战时期所谓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对美国当代社会和政治的后现代批判和讽刺。奥斯瓦尔德个人的命运是冷战时期部分人们命运的象征,基于奥斯瓦尔德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中的作用,整个小说又包含许多政治隐喻,通过奥斯瓦尔德的行动为主线描绘出一幅新社会理想构建中的迷茫与困难的新篇章,引发人们对国体的思考。《天秤星座》中的政治隐喻在文章的多个部分都有体现,从不同角度解读有助于了解美国冷战时期的性质,进而对政治、种族等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天秤星座》同时包含社会、文化、情境描述、政治、种族、个人等多维度的隐喻和批判。[7]
从美国所处的历史角度来看,奥斯瓦尔德生长在美苏对峙的世界两极分化时期,美国希望巩固和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掌控达到空前的状态,这就造成奥斯瓦尔德式悲剧人物的产生,进而导致肯尼迪事件的发生。美国应该转变意识形态,改善种族冲突、政治问题,为国家和人民的平稳安康奠定意识形态基础。基于遏制苏联霸主地位的目标,美国的政治呈现明显的“杜鲁门主义”,实施各种措施遏制全世界范围内的进步运动,企图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这从奥斯瓦尔德自身的权利欲望就能体现出来。从小说所折射出来的美国政治问题,实质是德里罗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判,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导致政治、种族等一系列问题,希望人们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促进国家转变意识形态,避免奥斯瓦尔德式悲剧的产生。美国的经济在霸权主义政策实行的条件下呈现明显的扶持和控制日本和西欧的态势,导致国内经济发展低迷,奥斯瓦尔德代表的大部队创伤性分工等级处于贫穷困苦的折磨中。美国也大力发展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希望通过武力达到控制和威慑的效果,这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体现,国家和政府通过自己这种意识形态实行控制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构建自己的霸权地位。德里罗并没有用过多语言描述美国冷战时期实行的政策,但通过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发展中无不隐含美国的霸权主义策略。[8]
从《天秤星座》的写作手法看,《天秤星座》主要采用叙事体进行事件演化的写作手法,可分为奥斯瓦尔德的成长经历、奥斯瓦尔德母亲对官方指控的不合理控诉、中央情报局的刺杀举动以及阴谋家的角度等四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叙事线索。从奥斯瓦尔德的成长经历出发进行肯尼迪事件的还原,既有助于揭露美国意识形态的弊端和劣势,又有助于增进读者对美国政治、种族等问题的深度认识,有助于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为人民进行批判和反思提供事实支撑。[9]从后三个角度进行肯尼迪事件叙述,有助于增强读者从多方面了解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充分认识到人们处于意识性的控制下,虚幻的意识形态容易造成悲剧式的人物,是政府政策作用的结果。只有充分认识国家的政治缺点,才能进行批判和反思,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发展。[10]
从《天秤星座》的题目来说,以“天秤星座”为题包含多种隐喻。以肯尼迪事件为主要论述目标的小说,题目竟然是毫不相关的“天秤星座”,由此可见,“天秤星座”必定包含一定的寓意。“天秤星座”作为十二星座中的风象星座,具有钟爱正义、公平的特点,奥斯瓦尔德作为典型的天秤星座代表人物,标榜英雄主义,存在二元化世界观,对权力具有较大的欲望,是冷战时期美国大众的代表。奥斯瓦尔德处于创伤性社会分工中,在小说中逐渐从积极改变社会地位的青年转变为被阴谋家利用的政坛棋子,奥斯瓦尔德悲剧的一生饱受美国霸权政策等政治制度的影响。奥斯瓦尔德本身充满正义与邪恶、秩序与非秩序等的矛盾,这些是“天秤星座”的隐喻,文章饱含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批判和讽刺。[11]“天秤星座”的隐喻深切契合奥斯瓦尔德悲剧的命运选择,隐喻美国的例外神话,实质是对美国阴谋论、权利纷争充斥的政坛的批判。此外,从美国的例外神话和政治来看,“天秤星座”是对美国例外神话和极端政治的隐喻,暗指美国的例外神话不会长久,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美国的例外神话的破灭。奥斯瓦尔德的人生悲剧同时隐喻美国的例外神话的悲剧,文章题目就充满批判和讽刺意味。[12]
由此可见,《天秤星座》中的政治隐喻在文章的多个部分都有体现,从不同角度解读有助于了解美国冷战时期的性质,进而对政治、种族等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从美国所处的历史角度来看,奥斯瓦尔德生长在美苏对峙的世界两极分化时期,美国希望巩固和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掌控达到空前的状态,这就造成奥斯瓦尔德式悲剧人物的产生,进而导致肯尼迪事件的发生。从《天秤星座》的写作手法看,《天秤星座》主要采用叙事体进行事件演化的写作手法,可分为奥斯瓦尔德的成长经历、奥斯瓦尔德母亲对官方指控的不合理控诉、中央情报局的刺杀举动以及阴谋家的角度等四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叙事线索。从《天秤星座》的题目来说,一方面隐喻奥斯瓦尔德的悲剧人生,另一方面隐喻美国例外神话和极端政治,文章处处就充满批判和讽刺意味。[13]
《天秤星座》作为后现代作品,文中包含种族、政治等多方面冲突和矛盾,这就决定了文章中对社会政治制度等的批判与讽刺。德里罗通过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深入解构和重构,剖析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以及基于霸权地位所施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奥斯瓦尔德作为冷战时期的美国一员,深受美国霸权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胁迫,最终导致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发生,也导致奥斯瓦尔德悲剧的一生,文中处处充满批判和讽刺。《天秤星座》饱含许多颠覆和隐喻,这些颠覆和隐喻的实质就是利用后现代的手法对社会分工、地位、阴谋家等社会制度等的批判,奥斯瓦尔德代表的是大部分人民群众的悲剧人生,是在自以为是的反抗中被阴谋家等统治阶级利用的棋子,是美国冷战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产物。《天秤星座》中的政治隐喻在文章的多个部分都有体现,从不同角度解读有助于了解美国冷战时期的性质,进而对政治、种族等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14]
《天秤星座》中后批评与反思还依赖于对德里罗的深入解读,德里罗作为著名的后现代作家、批评家,经常关注美国的政策等,基于德里罗对于美国霸权主义的认识和肯尼迪事件的深入剖析,就产生了《天秤星座》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批判作品,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深入的解构,充分发挥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独特性等特点,进行社会、文化、情境描述、政治、种族、个人等多维度的美国社会探讨,从而主张打破社会、国家、人文、传统等束缚,使人们对于人生、社会事件具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人们的思想达到空前的水平。后现代主义就决定《天秤星座》是对社会、文化、情境描述、政治、种族、个人等多维度的探讨,同时有助于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重构美国历史。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天秤星座》解读,对国家社会、政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天秤星座》中存在的意识形态进行解读,从《天秤星座》的隐喻方面进行探讨,进而研究《天秤星座》中的后批评和反思,提供社会和国家对历史、制度、政治等的反思。
从意识形态来说,奥斯瓦尔德代表的是大部分人民群众的悲剧人生,是在自以为是的反抗中被阴谋家等统治阶级利用的棋子,是美国冷战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产物。
从《天秤星座》政治隐喻来说,包含政治、种族等多方面。从美国所处的历史角度来看,奥斯瓦尔德生长在美苏对峙的世界两极分化时期;从《天秤星座》的写作手法看,《天秤星座》主要采用叙事体进行事件演化的写作手法,可分为奥斯瓦尔德的成长经历等四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叙事线索;从《天秤星座》的题目来说,一方面隐喻奥斯瓦尔德的悲剧人生,另一方面隐喻美国例外神话和极端政治。[16]
由此可见,《天秤星座》作为后现代作品,文中包含社会、文化、情境描述、政治、种族、个人等多维度冲突和矛盾,这就决定了文章中对社会政治制度等的批判与讽刺。
[1]Rowe,W.Nabokov’s Spectral Dimension[M].Ann Arbor:Ardis,1981.
[2]Alexandrov,V.Nabokov’s Otherworld[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3]Montrose,Louis A.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The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The New Historicism.Ed.H.Aram Veeser.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9.
[4]Cain,William.Making Meaningful Worlds:Self and History in Libra.Critical Essays on Don De Lillo.Ed.Hugh Ruppersburg and Tim Engles.New York:G.K.Hall& Co.,2000.
[5]Lyotard,Jean-Fran ois.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Geoff Bennington andBrian Massumi.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9;1984.
[6]周敏.媒介意识形态的诡计——德里罗《天秤星座》的文化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4):82-85.
[7]史岩林,屈荣英.《天秤星座》:德里罗对美国例外论的批判与反思[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856-861.
[8]范小玫.文学重构历史与后现代批评——评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J].江西社会科学,2013,(1):94-98.
[9]陈俊松.历史创伤和文学再现——肯尼迪遇刺与《天秤星座》中的反官方叙事[J].国外文学,2012,(2):138-145.
[10]吴玉琳.将历史虚幻化:简评唐·德里罗小说《天秤星座》[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84-186.
[11]沈谢天.德里罗小说的后世俗主义批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3):139-145.
[12]桂艳平.历史与虚构的平衡[D].上海师范大学,2010.
[13]蒋美京.唐·德里罗在《天秤星座》中对历史的解构与重构[D].四川外语学院,2010.
[14]吴云.论唐·德里罗小说《天秤星座》中美国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病理的话语特征[J].外语研究,2015,(4):98-104.
[15]马群英.阐释美国当代社会:德里罗作品的互文性研究[D].厦门大学,2013.
[16]沈非.超真实——唐·德里罗小说中后现代现实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I106
A
1671-6469(2017)-06-0043-06
2017-01-02
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师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院教学研究课题“新课标下英语教育专业人才技能培养研究与实践”(2016T013)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邓伟英(1970-),女,广东罗定人,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大学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