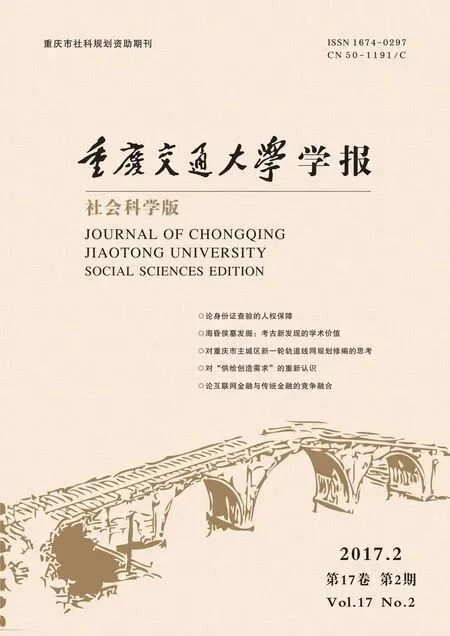颠覆与抵抗帝国中心文化
——J.M.库切的流散写作特征
堵文晖
(江苏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文学艺术·
颠覆与抵抗帝国中心文化
——J.M.库切的流散写作特征
堵文晖
(江苏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后殖民流散作家J.M.库切采取女性叙事对经典作品《鲁滨逊漂流记》进行改写,并通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之口来揭露帝国殖民文化的本质,展示其颠覆性、抵抗权威性的写作特征,达到立足边缘、重建帝国中心文化的目的。
女性叙事; 颠覆性; 抵抗权威性
出生于南非的荷兰后裔作家J.M.库切拥有双重身份。从血统而言,他隶属殖民者的荷兰;从出生成长地而言,又属于被殖民者南非。双重身份带给库切的并不是和谐互补的生活体验,完全对立的立场及文化政治背景使他被边缘于主流文化,而其笔下的白人女性一方面受到男权压迫,另一方面在面对被殖民者时又占优势地位,形成独特的叙事视角。文章通过文本细读,深入研究库切《福》中的女性叙事及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一发言人来揭示库切颠覆经典,寻找话语权和抵抗权威的流散写作特征。
一、以女性叙述来颠覆帝国男权话语
库切的《福》是对经典作品《鲁滨逊漂流记》的改写,其中令人瞩目的是叙述者的转变。叙述者是“叙事文本中的话语”[1]。《鲁滨逊漂流记》中男性叙述者鲁滨逊掌握话语权,为殖民者高歌颂曲,忽略了女性角色和被殖民者的心声,而《福》采用独特的女性叙事,一举打破以笛福为代表的经典文学中的父权制话语权以及殖民者为美化自身殖民行为的各种表象。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第一部殖民小说,处处体现出殖民意识。面对一部描绘英国早期殖民主义和帝国扩张的文本,库切通过转换叙述者主体的方式颠覆其殖民话语。原主人公鲁滨逊在《福》中不再是勇敢无畏、坚忍不拔、充满冒险精神和顽强意志的西方殖民者代表性人物,而是一个冷漠、毫无生活激情、毫无作为的颓废形象。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搬着石头,没有工具,不种粮食也不捕捉驯养野畜,支撑着屋顶的柱子和床脚上“都没有发现任何雕刻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刻痕显示他在计算自己流放了几年,或是月亮的周期”[2]12。库切没有对克鲁索浓墨重彩,而将一笔带过的苏珊塑造成小说的中心人物。她信念坚定地寻找失散的女儿,身处险境却积极求生。库切将《福》中的主人公设定为苏珊,赋予女性合法的地位和发声的权力,“希望能通过说话的孤独女性来为广大无声的沉默女性寻找到一个代言人”[3]152。被救后,船长建议苏珊将自己的历险故事写出来,找人对其调整润色。苏珊非常坚定地说:“如果我不能以作者的身份出现,发誓自己的故事是真实的,那还有什么可以值得读的?”[2]35库切通过苏珊明确地表示女性不再是失语和虚无的。当克鲁索想要掌控苏珊,苏珊直言:“如果他以为凭他生气的面容就可以吓住我,让我像奴隶一样对他言听计从的话,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打错了如意算盘。”[2]16当福怀疑苏珊的女儿是否真正存在时,苏珊指出:“你和我们一样,也是有实体的,我们都是活生生的,有实体的个体,我们都存在于相同的世界中。”[2]141苏珊除了在语言上把握主动权,在身体的掌控中亦如此。苏珊与福的性爱中采取主动,骑在他的身上并感到四肢充满活力。女性身体在父权制社会中有着双重意象,既是美丽动人的、也是邪恶的象征,是引发男性欲望的罪魁祸首。苏珊对自己身体的掌控脱离了男权社会为女性所设定的框架,占据主动权。
库切通过女性苏珊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搭建整本小说,以完成对父权制的解构,同时,用苏珊的语言、日记撕开帝国文化虚构历史的假面。《鲁滨逊漂流记》记载着鲁滨逊积极主动地教星期五学英语,向星期五展示帝国的先进性以受到星期五的敬畏和崇拜,使其自愿成为他的奴隶。帝国为自己的殖民行为打上了温情脉脉的标签,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地渗透,但是披着文明外衣的帝国殖民在《福》中露出了真实的面孔。帝国的殖民史从来都充满血腥暴力。起初,刚漂流到荒岛的苏珊“将星期五看作影子一样的人,对他的关注不比对在巴西的家仆多多少”[2]19,直至听到星期五“以低沉的嗓音哼起歌来”[2]18,才注意到星期五的舌头。苏珊同情星期五,试图教会他用语言、文字来了解世界,但很快她意识到“我使用文字是为了找一条捷径,好让他听从我的命令”[2]53。帝国的殖民通过语言文字等方式侵入殖民地的方方面面,被殖民者已经无话可说,只有用沉默来表示。苏珊在教导星期五的过程中逐渐明白所谓西方的文明教育从开始就不是平等的、真心的。在帝国殖民者心中,殖民地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需要西方文明的引导才能走向光明大道。到达伦敦后,苏珊发现星期五无精打采,和几个月前荒岛上的人换了个样,令人难以置信。“那时的他站在石头上,海水溅在他身上,阳光照耀着他的四肢”[2]50,活力四射。帝国的文明、科技的发展改变了自然环境,剥夺了星期五的自由。星期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用芦笛“重复吹奏一首只有六个音符的曲子”[2]23,穿着袍子在光线下跳舞,“让他陶醉在其中的绝不是在岛上挖掘或是搬运的乐趣,而是之前他在野蛮人之中过着野蛮生活的时候”[2]85。星期五用音乐和舞蹈来纪念曾经丰富多彩的非洲文化。最终苏珊决定要送星期五回家,回到难忘的故土非洲。
小说从头至尾,苏珊始终纠结着星期五被割掉的舌头,“或许他们是为了不让星期五说出自己的故事:他是谁,家在哪里,如何被带走的”[2]19。到底星期五经历过什么无人知晓,“唯一能说出这段经历的只有星期五自己的舌头”[2]59。被割掉的舌头象征着失去话语权的殖民地人们,历史任由殖民者们随意虚构。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露东方与西方之间交流的“自由总是西方人的特权;由于他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他可以窥探……亚洲的巨大秘密,他可以无休无止地纠缠这一秘密,他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塑造和解释”[4]。库切在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改写中选择女性叙事视角,颠覆经典,使该作品具有多层深刻含义:一是女性发声,质疑当权者对自己的虚化和无视,挑战男权话语权;二是揭露殖民主义虚构历史的真面目,以解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二、以女性声音来揭示殖民本质
女性与流散作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同样处于边缘地位,缺乏话语权,而历经几十年的女性运动,女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获得显著的提升,以女性的视角看待其他边缘阶层更具有共鸣感和指导性,也更能清楚地揭露帝国殖民的隐蔽方式和残酷本质。
如同被边缘化的女性一样,拥有多重身份的后殖民流散作家同样失去发声的权力,并在试图让自己被帝国文化接受的过程中逐渐习惯其介绍人的角色。流散作家们生来便具有历史文化带来的局限性和压迫性,无论是自己主动流散还是被迫流亡,流散作家们对于多重文化身份所带给他们的困惑迷惘和孤独、受歧视,都有着深刻的切身体验。对于本土文化,他们感受颇为复杂,往往在作品中会有意或无意识地运用母国素材来丰富自己的写作,或体现母国的风土人情和价值取向,同时又流露出对本土文化的疏离;对于帝国文化,他们流露出向往且小心翼翼地靠近却不被接受。夹杂于多种文化中的流散作家们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归属,流散于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此外,评定文学作品的好坏标准也掌握在强势帝国一方,只有迎合主流,那些殖民地本土作家或生活在殖民地的作家们才能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伊丽莎白指出:“非洲小说不是非洲人写给非洲人看的。非洲小说家可能会写非洲,写非洲的经验;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目光都向着远方,看着那些将要阅读他们的外国人。”[5]58伊丽莎白毫不客气地揭开后殖民流散作家的伤口,无论是否喜欢,“他们已经接受了自己作为介绍人的角色”[5]58,以符合帝国文化审美的方式将非洲介绍给西方读者。在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后殖民作家们渐渐迷失在帝国文化承认自己的美梦中,与本土文化渐行渐远。
库切安排伊丽莎白发表一些激进、极端观点,听众们对她进行反驳、批判和审视,以听众们与伊丽莎白的交锋触发读者在对同一话题的多维度探索基础上凝练出自己的思想,传达出开放式交流态势,从而构成多话语模态来揭示帝国殖民的危险性和残酷性。小说中一个地道的非洲作家伊曼纽尔·艾古度和伊丽莎白对峙,两者分别代表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视角来看待非洲问题。伊丽莎白觉得艾古度“是个装腔作势的人”,“看起来不是他自己,看上去跟我们有哪些相同之处呢”[5]42。以巡讲为生,习惯于流亡在各国的艾古度在流散中已然满足自己目前的生活,他告诉伊丽莎白:“一个从非洲来的乡下孩子,居然会有如此好的结局,躺倒‘奢华’的怀抱里了?”[5]43透过伊丽莎白和艾古度的对话,逐渐勾勒出“殖民者的自我从高处往低处来俯视被殖民的他者,对他们进行肆意而不负责任的探测”[3]153的蔑视者形象,以及部分殖民地人民在帝国文化的糖衣炮弹中迷失自我,丧失保卫本土文化意识的心理。
从伊丽莎白的演讲和对话来看待如今的非洲和非洲人,可清晰地发现非洲的模样任由西方描绘,且帝国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殖民地文化,而殖民地作家却为改变而欣慰自喜。库切通过伊丽莎白的声音将隐蔽的帝国文化殖民方式和本质赤裸裸地展示在公众面前。
三、以女性代言人来抵抗权威
库切为人低调,很少直抒己见,擅长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思考和观察,使读者自行在阅读中揣摩其含义。纵观其作品,不难发现作者本人的影子,如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约翰、《凶年纪事》里的C先生、多次出现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尤其是伊丽莎白屡次出现在库切的演讲、小说中,是库切的一个重要代言人。库切选择女性作家为自己的代言人,跳出男性殖民的框架,用一个女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约定俗成的男权世界,旨在摆脱付诸自身的两大枷锁——作家权威及南非审查制度。
《慢人》中出现女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一虚构人物在库切的笔下频频出现,且与库切的人生轨迹、爱好习性有着惊人的相似。伊丽莎白作为澳大利亚的知名女作家活跃于各大学术机构和大学,这是库切现实生活的反映。伊丽莎白对《尤利西斯》进行改写,出版了《爱科尔斯街的房子》,而库切的《福》同样是《鲁兵逊漂流记》的改写。伊丽莎白和库切一样喜欢骑自行车。他们性格上同样孤僻,不善于同他人沟通交流。库切在佛蒙特州贝宁顿学院做讲座时第一次出现了这一人物,随后在一系列的讲座中不断出现,且将这些演讲稿收集,并于2003年出版《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作品主题极为广泛,涉及现实主义、南非人文、哲学伦理、动物权利等,这些都是库切本人所关注的话题。毋庸置疑,伊丽莎白的背后始终有库切的影子。以虚构的作家形式发表演讲,通过伊丽莎白之口述说着自己对这些主题的见解,表述作家应该是“有闻必录的书记员”,既不提问,“也不对那些我所听到的话作出判断”[5]228。作者的写作目的不应是灌输和宣扬自己的观点,需保持客观,不带偏见,搁置自身信仰,让读者聆听不同意见,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思考。按常规,“叙述者是绝对的权威,小说人物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这些人物与叙述者权威的关系”[6]143。 然而,作为库切代表的伊丽莎白不断面对各种质疑,尤其在最后一章,她必须参加听证会来辩解关于自己的信仰问题。“在演讲中塑造虚构的人物,由他们来发表意见,并在叙事中展示他们的思考、怀疑以及所受到的挑战,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消解演讲者所拥有的话语权威。”[7]通过与各类型的人物对话,库切瓦解作者权威,使读者从多角度思考同一话题,形成自己的观点。
库切的一生都受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该制度的实施最大限度地保障白人殖民者们的利益,由既得益者制定各项制度,掌握话语权,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侵占南非本土民族的生存空间。殖民者们以权威的姿态对南非指手画脚,殖民地本土作家或生活在殖民地的作家们想要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迎合主流,作品符合帝国文化的审美,附和权威。后种族隔离时期,虽然该制度被废除,但南非同样不是自由发表言论的国度,审查制度的确立使他们仍然不能直抒其意。库切认为:“在旧南非我们有禁令,在新南非我们似乎又要有禁令了。在我看来,禁止什么,是次要问题。查禁的制度都是一样的。”[8]因此,无论种族隔离制度是否废除,殖民地作家们都不能以自已的身份直抒己见。库切借伊丽莎白之口宣称,“一个称职的书记员不应该拥有任何信仰”[5]228,以无信仰来反抗审查制度中的不能“亵渎神明、冒犯人口中任何部分人宗教信仰和感情”[9]。
众所周知,作者权威是“由所谓优等阶级的男性白种人的话语所构建的”[6]5,而丑陋的南非审查制度堵住了殖民地作家的发声渠道。库切反其道行之,选择女性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从多维度重新审视历史,一举打破权威的束缚和压制。
四、结语
库切将《鲁滨逊漂流记》中被忽视的女性苏珊作为《福》的叙述者,赋予女性发声的渠道以反抗男权社会的压抑,同时透过苏珊对星期五被割舌头的关注,揭开帝国殖民温情的伪面具。为避过南非审查制度的政治文化限制,库切通过伊丽莎白的演讲,自由且明确地表达出自己对作者权威、非洲、动物、信仰等各种话题的观点,并从伊丽莎白与听众的对话辩论中揭示如今殖民地所面临的危机,给人以警示。库切将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融入写作,从女性叙事看待世界,坚定不移地为边缘者发声,抵抗权威,重建中心文化。
[1]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7.
[2] 库切.福[M].王敬慧,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3] 程亚丽.后殖民视域下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系列小说[M]//蔡圣勤,谢艳明.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4] 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54.
[5] 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课堂[M].北塔,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6] 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 秦海花.作为公共演讲的虚构叙事:读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M]//蔡圣勤,谢艳明.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219.
[8] 约·马·库切访谈[J].黄灿然,译.书城,2003(11):83.
[9] COETZEE J M.Giving offense:essays on censorship[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185.
(责任编辑:张 璠)
Subversion and Resistance of Imperial Center Culture J.M. Coetzee’s Diasporic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DU Wen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1, China)
Post-colonial diasporic writer J.M.Coetzee rewrites the classicRobinsonCrusoefrom the femal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reveals the essence of imperial colonial culture through Elizabeth Costello. Coetzee displays his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subverting and resisting the authority in order to fulfill his purpose of reconstructing imperial center culture by standing the marginal position.
female narrative; subversion; resisting the authority
2016-07-15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全球化视角下J. M. 库切的流散写作研究”(2015SJB442)
堵文晖(1981—),女,江苏常州人,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106.4
A
1674-0297(2017)02-008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