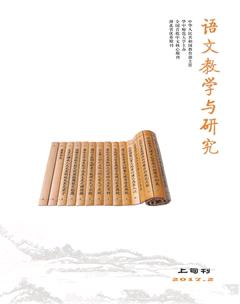到底该怎样来认识林冲形象
张怡春
读了杨大忠先生《对林冲形象的再认识》(见《语文建设》2016年第9期)一文,如鲠在喉。杨先生“以一眚掩大德”,否认包括《水浒传》作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林冲作为英雄的基本认识,实在值得商榷。
1.杨先生对林冲形象的分析,实质是在“人民”名义下的倒退。
杨先生不认同“英雄”是“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而以“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作为“英雄”的唯一评判标准。因而认为,“为使自己有容身之地而视他人生命如草芥,为保证自身安全而不惜强行休妻,面对仇人无动于衷麻木得令人震惊,这就是原著中的林冲。这样的林冲能是英雄吗?”表面看来,杨先生似乎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来评判英雄的,但是别忘了,“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总是与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可是综观全文,杨先生实际上都是在“人民”的名义下,完全用“人性”的标准来分析的。(不是说人性论就绝对不能跟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但二者的区别确是还是很大的)正因为如此,他认同刘再复先生对林冲纳投名状的分析(“这说明,在他的潜意识里,也把普通人不当人,以无辜的人头作为自己的入门券也无妨”),更认同吴越先生的说法(“自从林冲答应王伦下山杀人,善良而安分守己的林冲就已经‘死了。从此以后的林冲,就是失去善良人性、不讲是非、只求自己活命的歹徒了”),而吴越先生原文的标题却是《〈水浒传〉究竟是写英雄豪杰,还是写土匪强盗》!把林冲等梁山好汉看成“歹徒”,看成“土匪强盗”,实在不是吴越等先生的首创,不说历代封建统治者均这么认为,单说文人们吧,俞万春的《荡寇志》早就持这种观点了。这种观点实在早已是封建统治者(包括依附它的封建文人)的共识,却与普通百姓的看法水火不相容,普通百姓(包括作者在内)是认同《水浒传》,认同梁山好汉的。在《水浒传》语境下,林冲等英雄好汉的行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有血腥、暴力的一面,(农民起义嘛,肯定离不开血腥、暴力的)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根源在哪?社会制度该不该负主要责任?我们以为,与其否定这些英雄好汉,不如去否定那导致社会失常的社会制度。就社会来说,制度建设永远是第一位的,社会之恶、制度之恶远甚个人之恶,所以,社会改造、制度建设远较个人改造重要。
2.“敢于反抗,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也是英雄。
毫无疑义,“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肯定是英雄,但“敢于反抗,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也是英雄,《现代汉语词典》对“英雄”的解释既全面又准确。长期以来,包括《水浒传》作者在内,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这么来认识英雄、认识梁山好汉的。在老百姓眼里,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就是正义,就是英雄该为之事,这么做的人就是英雄;这样,“本领高强、勇武过人”自然也就更多地跟英雄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就是尽管梁山人马千千万,但只有林冲等一百单八将扬名的原因。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梁山英雄好汉的行为很暴力很血腥,他们不讲“法制”,不守“规矩”,做事不顾“程序正义”,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历史条件下,他们那么做是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的,他们是也只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所处社会制度下的英雄,是那个时代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反抗压迫的好汉,是高压统治下难有活路的百姓的希望的種子。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群众才喜欢《水浒传》,喜欢里面的英雄好汉。我们从人民立场出发,就应与人民群众保持共同的阶级感情、阶级趣味,就应正确对待梁山这群农民起义的兄弟,而不能站在童贯、高俅、蔡京等的立场上,视他们为“歹徒”“土匪强盗”。
3.对作品形象的认识要有全局观念,要看整体,不能死抠细枝末节。
文学形象当然有其复杂性,并且越是经典越如此。但就像现实中的真人一样,文学形象也是有其基本面的,其性格、思想再复杂,总还是有其主要的一面,我们要看主流,看本质,而不能主次不分甚至本末倒置。我们当然要关注细节,但绝不能死抠细枝末节。我们应该看主流,抓住主要方面,从整体上把握人物形象。置大体于不顾,一味死抠细枝末节,是很难准确把握人物形象的。
作为英雄的林冲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肯定是有缺陷的,人无完人嘛。皇皇一部《水浒传》,林冲“替天行道”干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但杨先生愣是视而不见,看到的只是“为使自己有容身之地而视他人生命如草芥,为保证自身安全而不惜强行休妻,面对仇人无动于衷麻木得令人震惊,这就是原著中的林冲”!死抠细枝末节,故意置轰轰烈烈的大事于不顾,这样能正确认识林冲形象吗?用这种方法、这种态度来进行《水浒赏析》,最后只怕绝对是以取消《水浒传》的经典资格,取消《水浒传》在中小学教材里的存在空间而告终。这种否定《水浒传》的经典地位、反对《水浒传》进中小学教材的意见并不新鲜,早就有了。问题是,取消《水浒传》进中小学教材就一定能杜绝血腥、暴力?社会就进步了?学生就能敬畏生命了?我们认为,这是庸俗社会学观点,很要不得。我们不应抽象地反对所谓血腥、暴力,为了正义而流血甚至迫不得已而进行战争还是必要的,世界到底还没能完全消除战争、消弭争斗,以正义反对邪恶还是必要手段,尽管它不一定表现为暴力。
4.对杨先生所说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
(1)林冲纳投名状实为迫不得已,一定要记账的话,最该记在王伦甚至社会制度身上。
林冲遭高俅陷害刺配沧州,一直极力隐忍,奈何高俅绝不放过,一定要结果了他的性命才罢手,野猪林不成,又派陆谦、富安火烧大军草料场,这样,林冲“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走投无路之下,蒙柴大官人柴进推荐投奔梁山,王伦却怕他本事强过自己不肯收留,故意刁难,要什么投名状。起先林冲还以为要投名状无非是写个保证书之类,可王伦却是一定要他在三天之内杀个人!这才有了林冲下山斗杨志的事。事出有因,实为迫不得已,,能一味责备林冲不把人当人、不讲是非、失去人性吗?从根本上讲,要想社会没有杀戮,就得提供一个没有杀戮的社会环境,就得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人的杀与被杀就很可能是身不由己。所以要记账的话,最该记在王伦甚至社会制度身上。
(2)林冲休妻的动机还真不是自私自利。
林冲休妻是在被发配沧州的时候,“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况兼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且是当着丈人张教头和众邻舍的面进行的,若是自私自利,丈人张教头和众邻舍还会那么待林冲吗?说林冲此时休妻“就是把妻子拱手相送高衙内,免得自己再受其害”,简直血口喷人!林冲刺配沧州,自知“去后存亡不保”,自身都难保,他又怎么去保护家人?此时他真的是怕牵累家人,倒不如将妻休了,丈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她回家,由丈人张教头保护。此事早已闹得满城风雨,由丈人来保护妻子实在是明智之举,张教头就说过,“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内便要见也不能勾”。从后来火烧草料场时“又一个道:‘张教头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没了”,张教头越不肯应承”来看,林冲休妻对保护妻子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3)妻子受侮只找陆谦算账,并非说明“在林冲的心目中,娘子的重要性还比不上富足安稳的生活”。
妻子前后两次受到高衙内调戏,林冲并非“没有做出男子汉应有的举动,连埋怨的话都没有”。第一次他是想要“下拳打”,第二次在陆谦屋子内寻高衙内不见。第二次陆谦骗他喝酒时,林冲对陆谦说自己叹气的原因是“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林冲此时当然有其隐忍的一面,一是这时的他还是太理性、太守规矩,“不怕官,只怕管”,二哩高衙内也确实没有“点污”到妻子,自己前后两次的举动应该说也等于给了高衙内警告,一般的人是会收敛的,所以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责备此时的林冲不像个男人实在没有道理,难道一定要林冲冲进太尉府将高衙内打伤或打死才算男人?这不算血腥、暴力?况且,太尉府是他林冲说进就进的吗?林冲被迫杀了人就说他血腥、暴力,林沖隐忍不杀人又说他不像个男人,那么我们倒要问,你说林冲到底该怎么办!正如余党绪老师所说的那样,“如果我,或您,不幸遭遇了林冲的遭遇,我们该如何选择呢?”(余党绪《关于〈水浒传〉的阅读与教学,兼与黄玉峰老师商榷》,见《语文学习》2014年第11期)他砸了陆谦的家,并非欺软怕硬。一是身为好友的陆谦确实做了猪狗不如的事,二呢在陆谦家里林冲没能找到高衙内,只好砸了陆谦的家。
(4)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以及他的处境不允许林冲时时刻刻向娘子报平安,《水浒传》也不是言情小说,不允许也没必要像言情小说那样去写,但这并不表明林冲对妻子就没有“思念”,对妻子就“冷漠无情”。
(5)林冲不对被擒上山的高俅复仇,只是因为他到底是正规军出身,比较理性,组织、纪律、大局观念强,又讲义气,绝对服从宋江的号令。“再说宋江掌水路,捉了高太尉,急教戴宗传令,不可杀害军士”,这样,他林冲不可能像李逵等那样冲动,有意做出冒犯军令的事情来。这当然也可以说是林冲的性格弱点,但绝非“面对仇人无动于衷麻木得令人震惊”。
(6)“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绝对是“高大威猛、器宇轩昂”。
“豹头环眼”“燕颔虎须”都是传统小说(话本)常用来形容人相貌威武的话语,不一定“俊朗”,但也绝不就一定是“粗憨鲁莽”!朱仝之所以让“知府先有八分喜欢”,当然是他的“美髯过腹”实在有特点,极易引人注目,在这一点上,林冲确实比不了,但这并不就说明“林冲的外在形象极其普通”,因为他到底还是“豹子头林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