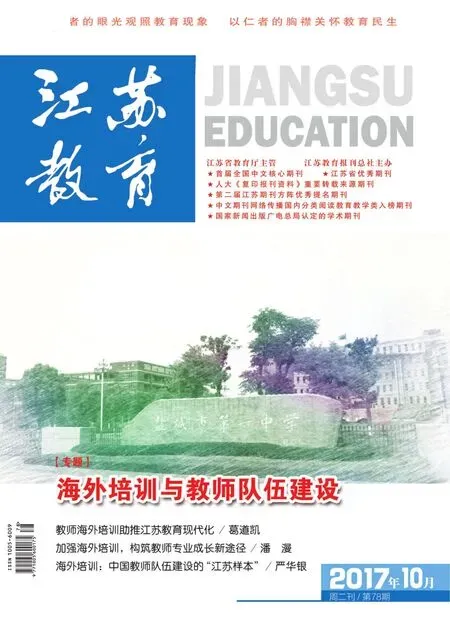我读《课程论》
·名师阅读史·
我读《课程论》
孟晓东
——〔英〕泰勒和理查兹《课程研究导论》
一
“课程”,对于今天的教师来说已是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了,但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教师,“课程”这个词就相当于今天的“翻转课堂”“数字原生代”等词那么新鲜,甚至比之更为鲜见。当时,最为常见的教育用词,大体是“大纲”“教材”“教案”“教法”“双基”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原江苏省洛社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一待就是9年,可能是因为在班主任(少先队)工作、语文教学等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25岁那年就被提拔为副校长。不久又被调往江南古镇梅村,任当时无锡县唯一的实验小学的副校长,分管教学和科研。当时,梅村实小正在进行着一项教育科研项目“农村小学教育整体优化实验”,这是彼时一般学校不敢涉猎的课题研究。该研究的指导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比较研究所的杜殿坤教授,杜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苏俄教育研究家、翻译家、教学论专家,也是中国高校最早的走到基层做研究的少数学者之一。杜教授带领着我们心无旁骛地、纯粹地做着学问,不计报酬,无怨无悔……就是那时,我知道了什么叫“Z检验”“T检验”“卡方检验”“显著性差异”等专业术语,也接触到了“课程”这个词。这个课题后来被评为江苏省首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是江苏省小学范围内唯一的集体一等奖,同时获得个人奖的是李吉林老师的 “小学语文情景教学研究”和邱学华老师的“小学数学尝试教学研究”。
“农村小学教育整体优化实验”结题后,研究如何深化?成果如何运用?接下去再做什么?这是摆在我们一班人面前的严峻课题,更是我这个年轻的分管校长必须要直面的现实。几番思辨、争执、搜索、比较,又请教了杜教授以及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桑新民教授等几位学者,我们确定了要做“课程”。但课程是什么?课程的功能与定位是什么?在这样的远离城市的农村实验小学中,我们该呈现怎样的学校课程形态?我们脑中一知半解,心中也毫无底气。
二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课程”方面的著作只有一本,那就是陈侠先生的《课程论》,1989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此书当时还购买不到,幸好时任江苏省无锡市教科所所长的唐迅先生手中有一本,我们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当时我和教科室几位同事为了能够更迅速地读到此书,采取了抄录、翻印、传阅、分章阅读等方式,真有点“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那本淡黄色封面、24开简装的《课程论》寄托了我们多少年轻人的求知欲望。后来我们才知道,陈侠先生的《课程论》是我国第一部“课程论”专著,对我国课程论的重建具有先驱性、奠基性的贡献。
我们以前学过的《教育学》中,“课程”只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而“教学内容”这一章主要讲的是有关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编写教科书的事,与一般教师仿佛没有多大关系,从而造成了对“课程”的误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解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有一门教育学。后来虽增加了一门教学论,却并没有讲课程论,大家对课程论这门科学十分陌生,对它的基本概念和外延内涵也不怎么清楚。而陈侠先生著的《课程论》,开章就简明扼要地对“课程”“课程论”做了说明:“课程一词为我国所固有。课,指课业,就是现在所说的教学内容;程,有程度、程序、程限、进程的意思。课程就是课业的进程。”简单地说:“课程论就是关于课程的理论。”课程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有:(1)为什么教?(2)教什么?(3)怎样选择要教的东西?(4)怎样组织最有效?(5)根据什么标准和原则?(6)谁来选择和编订?(7)怎样评价?这是一本既填补我国教育科学空白又具有多功能的好书。
正所谓好事成双,几乎是同时,华东师大钟启泉教授编著的《现代课程论(新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从而形成了课程史上“北陈南钟”的说法。全书共15章,分“课程理论与课程研究”“课程实施的国际比较”两部分,在第二部分中重点强调了与日本现代教育的比较。书中指出“课程是由知识、技能及与之相应的学生的活动组成的。课程不是单纯的知识、技能的堆积,它还包括了教师组织指导下的学生的活动。学生有计划地掌握一定的系统的知识、技能,在解决各种问题的同时,发展起一定的能力、习惯和态度”,这为21世纪初新课程改革“三维目标”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阅读到的《现代课程论(新版)》是由钟启泉先生在1989年版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并于2006年出版的。全书删去了原书中的第二部“课程实施的国际比较”(第10—15章),以及第一部中的第8—9章;增添了“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作为第二部的内容,也重新调整、充实了第一部前7章的内容。这样,全书分“课程理论与课程研究”“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两大部分,更贴近了国际课程研究的前沿,贴近我国课程改革的实践,勾画课程理论的发展轮廓。新版着重向我们介绍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课程学说及其特点,并对学校课程的传统与变革作了回顾与展望,论述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
在当时没有网络,更没有“百度”“云盘”的年代,陈侠先生的《课程论》和钟启泉先生的《现代课程论(新版)》如两盏明灯,开启了我们对于“课程”的启蒙之旅,又如鸟之双翼,托举我们在“课程”求知的天空飞翔。
阅读就是一种挑战,慢慢穿越,一定有所收获。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将学习成效转化为自己的理论武装和自我修养,学习才是真正有效的行为。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化和内化,我们正式申报了“八五”科研课题“开设微型课程,优化课程内容和形态”,先期启动了“综合课程”和“短期课程”的改革尝试。我们开宗明义地提出,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课程改革,要切实改变以往小学课程设置中分科课程和学期课程一统天下的格局,丰富课程门类,使课程形式灵活多样。
小学教育具有普及性、基础性、全面性的地位。小学开设综合课程和短期课程,既符合义务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又契合世界课程改革的趋势,还整合了课程内容的滞后性、学生认知的规律性、解决问题的综合性等因素。在积极进行课题研究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发表自己的主张和策略。我和当时的学校教科室负责人顾万春老师撰写的《应加强小学综合课的建设》刊发在《现代中小学教育》1993年第3期,《对小学设置短期课程的认识与思考》刊发在《普教研究》1993年第6期。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也引起了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初教处副处长成尚荣先生的关注。他邀请我在全省的“深化素质教育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还接受了《中国教育报》的独家采访。与此同时,梅村实小一系列的课程行动也随之展开,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数学Ⅰ~Ⅲ类课程(Ⅰ为学期课程,Ⅱ、Ⅲ类为短期课程)、学科性短期课程(高深型、拓展型)、活动性短期课程(趣味型、职业型)……一时如火如荼,次第纷呈,也涌现出了一批物化成果。
1994年,我有幸参加华东师大硕士课程的学习,有缘求教于一大批著名教授的门下,叶澜、袁振国、施良方、陈桂生、单中惠、杜成宪、熊川武、胡慧闵、王晓玲等都先后给我们上课,耳提面命。这对于中师起点,后经函授专、本科的我来说,倍加珍惜,如饥似渴。两年的学习,可谓手不释卷,聚精会神,对于“课程”的理解也逐渐加深,视界被慢慢打开。
尤其是施良方先生教授的《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和《学习论》,给了我关于“课程”的极富营养。我国教育界对课程问题的研究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和相当广泛的经验,但对课程理论体系的构建则刚刚起步,施老师通过对课程的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探讨,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整个编制过程的分析与反思,对课程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的思索,对一些课程基本问题的探讨,对课程的历史、现状的剖析以及对未来课程的展望,从而确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课程理论的框架……当时施先生的这两本专著尚未出版,他曾经在课上说:“我现在的讲稿,到了你们毕业时,就可以发成出版的书了。”施先生没有食言。1996年,我们真的拿到了他的第一本专著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这是我国第一本提供了课程理论分析框架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深化与发展我国课程教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令我们万分悲痛的是,时隔一年,施先生因脑血管破裂,倒在了他钟爱的讲台上,年仅45岁。他教授的《学习论》,于2001年出版,捧着他的书,我泪如雨下……
三
2001年6月8日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了课程改革的时代。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学习型的课程改革共同体,一种共同的课程愿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对话、合作与探究的课程文化,努力把一种开放的、民主的、科学的课程奉献给新世纪的中国儿童。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8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发展”的宏伟理念下于新千年肇始拉开了序幕。
很荣幸,我所在的无锡市锡山区成了国家首批课程改革实验区,也是那一年,我任职锡山区教育局分管教育教学的副局长。16年来,我伴随着“新课改”一路同行,既是见证者,又是践行者,既做“教练员”,又做“运动员”。16年课改,风风雨雨、磕磕碰碰,也潇潇洒洒、无怨无悔。
如今,翻开各类教育专著,极少有不提及课程的。自1989年陈侠著《课程论》、钟启泉编著《现代课程论(新版)》始,近30年时间里,国内有关课程论的专著或教材已达数十本,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但对课程的界定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课程论研究对象这个基本的、影响深远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言人人殊。对待这些定义的一种合适的方式是,考察这些作者是如何使用这个术语的,其隐含的基本假设和取向及其对教育实践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
在我国,“课程”一词始见于唐宋期间,唐朝孔颖达在为《诗经·小雅·小弁》中“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句作疏:“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依法制。”但他用这个词的含义与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课程的意思相去甚远。宋代朱熹在《朱子全书·论学》中多次提及课程,如“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作工夫”等。虽说他只是提及课程,并没有明确界定,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即指功课及其进程,这和西方最早提出“课程”一词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Spencer)的解释如出一辙。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年)一文中,指出“课程”一词源自“跑道”,根据这个词源,最常见的课程定义是“学习的进程”,又称“学程”。
到了近代,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施行,赫尔巴特学派“五段教学法”的引入,人们开始关注教学的程序及设计,于是课程的含义从“学程”变成了“教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课程”一词便很少出现。
在阅读文献中,我们发现很多学者关于课程“跑道说”又有了更多的阐发和解释,争议的重点是,从词性出发如何理解“跑”和“道”。因为“课程”一词是从拉丁语 “Currere”派生出来的,“Currere”一词的名词解释为“道”,则意为不同的学生设计不同的轨道,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从而引出了一种传统的课程体系。而“Currere”的动词形式是指“奔跑”,重点是“跑”上,课程就意味着“对自己经验的认识上”,“个体体验”便成了课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就得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课程理论和实践。
20世纪20年代,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标志着现代课程理论的诞生,该书围绕着学校应达到何种教育目标(确定目标)、提供哪些教育经验才能实现这些目标(选择经验)、怎样才能有效组织这些教育经验(组织经验)以及怎样才能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实现(评价结果)这几方面来进行研究。从此,“泰勒原理”一直为课程编制指明着前进的方向。
2000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小威廉姆·多尔的《后现代课程观》,其基本观点是课程不再被视为固定的、先验的“跑道”,而成为达成个人转变的通道,即“绕着跑道跑”,课程有起点,但是没有终点,课程是生成的,而非预先界定的。多尔指出,课程不再是静态的跑道,而是围绕“跑道”跑的动态过程,是跑的经验,强调的是个体对其“自我经历”进行“概念重建”的能力。国内的一些学者,如张华教授等将后现代课程的一些主张与思想引入“新课改”实验,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2007年5月,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张华教授主持的第一届教学改革国际会议在上海举行,小威廉姆·多尔等一些著名学者都到会作了主旨演讲,会上发出了“让课堂产生学生的思想,让教学建立在倾听之上”的教学主张,我也应邀在大会上作了《课程·课题·课堂》的专题介绍。
我想,对于广大教师而言,其实“课程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如何实施课程。课程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因而它不同于一般纯自然的客观事物。追问课程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指导课程实践。归根到底,与其在追问“课程是什么”时,没有明确地答复,不如反过来思考“课程不是什么”的问题。课程的宗旨是关注人的发展,至少那些不利于人发展的因素,肯定不应归为“课程”范畴,也不能出现于课堂实践中。因此,课程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是什么”这样所谓的“事实”问题上,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做”这样的“价值”问题上。
因为陈侠先生《课程论》、钟启泉先生《现代课程论(新版)》的启蒙,我较早地接触了“课程”概念;因为华东师大、辽宁师大两度硕士课程的学习,我步入了“课程”领域;因为国家级课改实验区,我践行在“课改”的前沿阵地;又因为众多师友的专著、论文,我在课程改革的实践中且行且思……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也期待着我心中的那棵“课程”小树伴随着课改的深化能够慢慢地生长。如今,我也发表了上百篇关于“课程”“课改”的文章,我的两本专著《用生长定义教育——孟晓东与语文生长课堂》《从原点到远点——守望在生长教育的田野》也于2016年出版。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欧阳修有言:“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为此,我读《课程论》,将永不停息!
课程是教育事业的核心,是教育运行的手段,没有课程,教育就没有了用以传达信息、表达意义、说明价值的媒介。正因为课程在教育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课程也就具有了研究的价值。
(作者系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教育局副局长,江苏省特级教师)
【推荐书单】
1.《现代课程论(新版)》 钟启泉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2.《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施良方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
3.《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美〕拉尔夫·泰勒著,罗康、张阅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
4.《课程与教学论》 张华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5.《后现代课程观》 〔美〕小威廉姆·多尔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