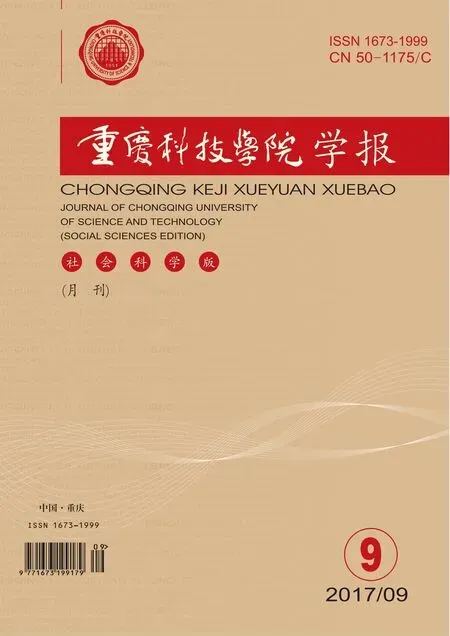模式反讽经典之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镇》
徐小芳
模式反讽经典之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镇》
徐小芳
盖斯凯尔夫人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以写作“社会问题小说”“工业小说”“乡村小说”著称。《克兰福镇》是盖斯凯尔夫人的重要代表作,作品通过虚构一个超然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之外的大龄单身女性社区,既戏仿式反讽了当时的“男权社会”,也戏谑了“家里的天使”;既深刻揭露了“机械时代”突出的社会问题,也客观敲响了乡村田园的“挽歌”,是一部运用模式反讽的经典之作。
女性小说;《克兰福镇》;盖斯凯尔夫人;反讽
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1810—1865)是 19世纪英国著名的女作家,闺名伊丽莎白·克莱格亨·斯蒂文森(Elizabeth Cleghorn Stevenson),以写作“社会问题小说”“工业小说”与“乡村小说”著称。盖斯凯尔夫人一生发表了6部长篇小说、1部富有盛名的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以及许多中篇小说。《克兰福镇》(Cranford,1853)是盖斯凯尔夫人的重要代表作,被公认为是她最成功的小说作品,亦是她本人最为喜欢的一部作品[1]。有关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学界通常将其与《玛丽·巴顿》(1848)以及《北方与南方》(1855)等区别开来,将其简单看作是描写田园风光的乡村小说,没有看到作品中的言语反讽、情节反讽、结构反讽,尤其是模式反讽所隐含的问题意识、思想主旨与批评锋芒。实际上,盖斯凯尔夫人欲通过虚构一个大龄单身的女性王国,刻画她们不同于现实社会的“克兰福镇式”的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念,既戏仿式反讽了当时的“男权社会”,也戏谑了“家里的天使”;既深刻揭露了“机械时代”突出的社会问题,也客观地敲响了乡村田园的“挽歌”。
一、反讽与模式反讽
反讽(irony)这一术语,源出古希腊喜剧,最初指的是一种固定的角色类型,即“佯装无知者”。在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式的论辩技巧中,经常使用反讽。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概念与苏格拉底同时诞生”“苏格拉底假装一无所知,这个最大的智者在伪装的无知身份下,用反讽诱导所谓智者显露出真正的无知。”[2]229反讽后来逐渐演变成小说中常用的修辞艺术,从类型上看,主要有言语反讽、情节反讽、结构反讽与模式反讽。反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的,而语境不仅有共时性,还有历时性;不仅具体地指代作品的语言、故事情节、结构安排等文本语境,也包括广义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舆情风俗以及约定俗成的叙述方式、写作风格、文学样式。相较于言语反讽、情节反讽、结构反讽,模式反讽是一种更高形态的反讽修辞格,它不仅反讽故事之中相关的人物与情节,而且互文性地反讽故事之外的人和物,乃至整个社会。“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针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的存在,而是针对某一时代和某一情势下的整个特定现实……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视为在反讽外观之下的整个存在。”[2]271同时,模式反讽也是对既定的文学样式的颠覆,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对骑士小说的反讽[3]。
在《克兰福镇》一书中,盖斯凯尔夫人以儿时的纳茨福镇为艺术原型,试图展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浪潮席卷下乡村小镇的社会变迁与风土人情。这样“亲切”“熟悉”的素材以及书写社会大转型不可逆转的思想主旨,非常适合采用反讽修辞格。因而,盖斯凯尔夫人也一反前期作品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在这部作品中大量运用了言语反讽、情节反讽、结构反讽,语言诙谐、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对此,盖斯凯尔夫人自己也是相当满意的,她曾这样写道,“每当我身体不舒服或者生病的时候,我都会看《克兰福镇》,而且我还想说,我很享受这本书带来的乐趣!一次又一次地大笑!这是真的,只要我看见那头穿着灰色法兰绒背心的母牛,还有那只因为吞了福列斯特夫人的花边而被送去医生那里吃催吐剂的小猫。”[4]国内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丰富,然而,基本上都没有深入揭示与挖掘作品的模式反讽。盖斯凯尔夫人刻画的“克兰福镇”的典型“气质”——“女人王国”“乡村田园”“高贵的节俭”“门第、等级森严”,与19世纪中期的英国社会状况完全格格不入,模式反讽的意蕴极其强烈。需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深邃的思想家,盖斯凯尔夫人的模式反讽是“双向”“双轨”的,既反讽过去的迂腐陈旧,也反讽“机械时代”的社会问题,是模式反讽的经典之作。
二、“女人王国”:对“男权社会”与“家里的天使”的双重反讽
(一)对“男权社会”戏拟反讽
尽管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堂而皇之地宣称“人人平等”,但它们所说的“人”多半是指男人,并不包括占人类半数的女性[5]。盖斯凯尔夫人刻意虚构“克兰福镇”这个由大龄单身女性组成的“女人王国”,就是强烈反讽现实的“男权社会”,在意识形态和性别政治上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模式反讽的特征特别明显。“首先要说的是,克兰福镇是个女人王国。”[6]1这是《克兰福镇》开篇的第一句话。盖斯凯尔夫人将小说的背景就设置为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由大龄单身女性和年老的寡妇组成的女性社区。这里生活着贾米逊夫人、狄布拉·詹金斯和玛蒂尔德·詹金斯姐妹、福列斯特夫人、波尔小姐等。此外,盖斯凯尔夫人不厌其烦地叙述在这一单身女性社区里,太太小姐们应付大大小小的事情“绰绰有余”:“把种满名贵花卉的园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没有一点杂草呀;吓跑那些隔着栅栏打这些花儿主意的眼馋的孩子们呀;轰走趁大门敞开时闯进园来的鹅群呀;不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推理和争论上,而给所有文学和政治上的问题作出结论呀;把本教区内各人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呀;教那些干净麻利的女仆循规蹈矩呀;对穷人施些恩惠呀,以及在不幸中互相帮助、互相慰藉呀……”[6]1
在《克兰福镇》中,盖斯凯尔夫人除了篇首这样用特写镜头对“男权社会”进行模式反讽以外,还成功刻画了“男权社会”的象征与符号——狄布拉·詹金斯,充满悖论的是她还是一位女性,还曾叫嚣“女性比男性要强多了”[6]18。 在小说中,狄布拉·詹金斯的戏份很少,在第2章之后就撒手人寰了,但其影响无处不在,特别是与她妹妹玛蒂如影随行。《克兰福镇》如果沿用盖斯凯尔夫人给书名命名的习惯——以女主人公命名,如《玛丽·巴顿》《露丝》,还有她曾想将《南方与北方》命名为《玛格丽特·黑尔》,那么这本著作应该命名为《玛蒂尔德·詹金斯》。在小说中,围绕玛蒂的那些故事情节,基本都是关于如何走出狄布拉的影子的问题。比如,如何调教女仆,如何接待男宾,该不该去拜访老情人,是否可以允许女仆谈恋爱,甚至自己的名字称呼等等。小说中总是会重复着玛蒂这样的声音:“我真不清楚姐姐那时是怎样安排这一切的。她最有办法了。”[6]35“要是狄布拉在世的话,她是一定知道怎样接待男客的。 ”[6]38“要是姐姐在世是不会赞成的。”[6]44不仅她的妹妹如此,甚至整个克兰福镇亦然,“詹金斯小姐长久以来是克兰福镇的领袖,现在她去世了,人们几乎弄不清楚该如何举办茶会了。 ”[6]34“詹金斯小姐一死,再没人熟悉待人处事那套规矩礼节了。 ”[6]90“第一人”叙述者玛丽·斯密斯感叹,“也真怪,像她姐姐这样的人靠自己的意志就能让别人服服帖帖,事事听从她指挥。”[6]167
(二)对“家里的天使”的戏谑反讽
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1937—1901)的社会是男性中心的社会,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也是男性中心的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男性支配一切,女性是附庸;在文学中,男性则按照自己的意愿臆造“天使”般的女性形象,并用以规范与约束女性。从理查逊的《帕美拉》到狄更斯的《小杜丽》,几代作家笔下的女性典范,个个都是美丽温柔,贞洁自守,以侍奉男人、操持家务为己任[5]。于是观之,她们就是现代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笔下所谓的“家里的天使”:“她温柔可爱,善良无私。她擅长持家,富有牺牲精神。如果餐桌上有一只鸡,她拿的是鸡脚;如果屋里有穿堂风,她就坐在那里挡着。总之,她没有思想,没有渴望,只会附和与赞同。她最为引人注目的,不必说,是她的单纯。单纯是她最为动人之处,那羞怯,那优雅,实在令人倾倒。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末期每间屋子里都有这样的天使。”[7]然而,这些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妇女观,是男权社会里男子心目中的理想妇女形象。这种理想形象盛行于整个19世纪,甚至沿袭至今,无怪乎伍尔夫怒气冲冲地号召女作家“杀死家里的天使”,否则妇女就不能从精神上解放。其实,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一大批女性作家已开始致力于“杀死家里的天使”,盖斯凯尔夫人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在《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女主角之口直接喊出“我不是天使,我就是我自己。”[8]与这样的女权宣言书式的直接表述不同,盖斯凯尔夫人是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尤其是反讽修辞格,戏谑地反讽了“家里的天使”。如果不刻意纠结生活在克兰福镇中女性的颜值、年龄与婚姻状况的话,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盖斯凯尔夫人描绘的那些贵族遗孀或单身老姑娘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当时“家里的天使”的形象来塑造的,她们富有同情心、善良、高雅、高贵。在盖斯凯尔夫人笔下,“家里的天使”们标榜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能应付得“绰绰有余”,但实际上她们非常依赖男性,离不开男性。在小说中,她们对布朗上尉从拒斥到接纳与尊重,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布朗上尉能帮助她们处理家中一些棘手的问题。“谁家有做不来的事,他总有法子对付。”“谁家烟囱漏烟,他都无所畏惧的走上楼去。”[6]6此外,面对子虚乌有的“强盗”“抢劫”,她们“惊慌失措”,无比的害怕与恐惧,甚至惶惶不可终日,而解救之道还是向男人寻求慰藉:“波尔小姐向医生霍金斯先生讨了一顶旧帽子挂在门厅,好让外面的人以为她家是有男人的。”[6]126“玛蒂怕强盗躲在床底下,时刻准备着拉响报警的铃子故意喊叫约翰和哈里这样男性仆人的名字。”[6]137盖斯凯尔夫人不仅在这种隐晦的意义上揭示“家里的天使”的形象是男权社会的臆造,而且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即玛蒂因投资入股的县镇银行破产而倾家荡产变成了一种现实的拷问。如果是“家里的天使”到底能做什么呢?通过玛丽·史密斯为玛蒂小姐策划种种谋生职业,其中包括教书、“用花纸做成点蜡烛用的‘小捻儿’”,“用各种漂亮的针子织袜带”,“朗读、书法和算术”,结果都不具有现实性,只能做最简单的买卖生意——“卖茶叶”[6]180-182。即使是做这种简单的茶叶买卖,玛蒂小姐都“吓了一跳”“但并不是觉得这有失身份,而是不相信自己有本事过这么一种新生活”[6]195。这样的反讽让人很辛酸,也充满着同情。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9]“家里的天使”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局限性归根结底还是父权制社会力量对其进行限制和压制的结果。希拉里·绍尔认为,《克兰福镇》的世界被分成了两极:“男性控制财务和工业世界”,“女性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居家世界中,在那里探亲访友、唠叨家常和操持婚丧嫁娶”[10]。如果看不出这层反讽,《克兰福镇》的写作意图与思想主题就会被误读。
三、建构“新克兰福镇”:用“传统”反讽“现代”,用“现代”反讽“传统”
维多利亚时代既是大繁荣时代,又是充满变革的时代。就盖斯凯尔夫人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而言,经济上,工业革命与自由贸易如火如荼;政治上,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工人阶级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思想领域,占据维多利亚社会主流的是功利主义,在道德与性别方面,用“绅士”与“淑女”观念对男人和女人进行规训与塑形深入人心;科学领域,最具冲击力的理论是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国际关系事务中,最显著的成就是“日不落帝国”的强势崛起[11]。在《克兰福镇》中,盖斯凯尔夫人没有线性地看待这些变革与进步,而是坚持客观的、辩证的双轨思维,用“传统”反讽“现代”,用“现代”反讽“传统”,既正视了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也深刻揭示了“机械时代”的突出社会问题,体现了作者建构“新克兰福镇”的社会理想。
(一)对“机械时代”的忧思:用“传统”反讽“现代”
与盖斯凯尔夫人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对他那个时代的特征作了广为传颂的研判:“假如我们需要用一个词语来描绘我们自己时代的特征的话,我们不能称之为‘英雄的时代’‘虔诚的时代’‘哲学的时代’或‘道德的时代’,而应当首先称之为‘机械的时代’(the Mechanical Age)。 ”[12]在卡莱尔看来,当一切奉行“机械”原则,人们所崇拜的不再是“美”与“善”,而是“物质的”或“实用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盖斯凯尔夫人无疑非常熟谙托马斯·卡莱尔对“机械时代”的深深忧思,她刻意虚构的“温情脉脉”的克兰福镇就是对“现金联结”“利益算计”“尔虞我诈”“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的过度商业化、市场化社会的反讽。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分开详细阐释,仅简单把文中这类反讽的意蕴粗线条勾勒出来。
克兰福镇的土著居民“向来不谈金钱,因为这个话题有些做生意的铜臭”[6]4;也向来不炫富,“如果晚间待客时在吃喝方面摆阔还会被看作是‘俗气’”;当然她们也不哭穷,因为“贫穷和死亡一样,都是无处不有的普遍事实”,布朗上尉曾经因此深受诟病[6]5。“克兰福镇的人有一种高尚的团结精神”[6]4,经商之道不会搞相互拆台“竞争”,不会认为同行是冤家。在玛蒂为维持生计而筹备经营茶叶时,非常担心影响同行的约翰逊老板的生意,为此特意去征求他的意见,这个举动被玛丽·史密斯的父亲认为是“胡闹”“要是做生意的都这么你来我往的商议照顾对方的利润,那还讲什么竞争,买卖又怎么做得下去?”[6]198-199颇具反讽的是,在克兰福镇,对人毫不设防的玛蒂受到了约翰逊老板的照顾和顾客的信任而生意兴旺,反而是书中的“经济权威”玛丽·史密斯的父亲处处小心提防,还是被骗走了上千镑的钱[6]199。
除了这种言语的反讽,《克兰福镇》也深刻揭示了“蒸汽文明”“机械时代”英国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一是留守妇女、剩女的问题。维希努斯指出:“在中产阶级评论者眼里,单身女人过剩这个社会问题象征了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机能失调。”[10]《克兰福镇》凸显和放大了维多利亚时期突出的大龄单身女性“过剩”问题。1851年英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20~40岁的女性总数不到300万,其中有124.8万处于未婚状态,被迫单身的约有75万[13]。二是贫富分化。“现代化理论中著名的‘库兹涅茨定理’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其对应关系呈现为一条马鞍形曲线,要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贫富差距才会下落。而在下落前的曲线顶点上,社会呈现出危险的分裂倾向。”[14]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维多利亚时代就正处在这一曲线的顶点上,据统计,当时0.48%的英国人分享了国民收入的26.3%,包括中产阶级上层在内的10.0%的人分享了国民收入的50.6%[15]。在《克兰福镇》这部小说中,“高贵的节俭”诚然反讽了一群“高贵”的遗老遗少对针头线脑、纸张蜡烛和面包糖块之类生活物品过分节俭和吝惜,但也尖锐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严重两极分化,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的土地贵族与中产阶级都如此拮据,下层劳动群众的处境可想而知。盖斯凯尔夫人作为“工业小说家”与“社会问题小说家”本色未变。三是上文揭示的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此处不再赘述。
(二)“乡村田园”的挽歌:用“现代”反讽“传统”
在批判现代化进程给社会带来的诸多消极影响的同时,盖斯凯尔夫人没有愤世嫉俗地拒绝新时代,而是带着平和的心态冷静地观察这个充满丑恶与矛盾的世界。她没有落入文学传统中过度美化和颂扬逝去美好田园生活的窠臼,而是清醒意识到现代化进程正在以无可阻挡的威力日益加速发展,成为席卷英国和世界的潮流。尽管《克兰福镇》中弥漫着一种挽歌的基调,怀念美好田园生活的一去不复返[16]。在《克兰福镇》中,用“现代”反讽“传统”较为隐蔽,是一条“暗线”。如果看不到这层反讽,就有可能把《克兰福镇》定位为“乌托邦小说”,尽管就“克兰福镇”完全是虚构的一般意义而言,它确实是“乌有之乡”,但它并不是盖斯凯尔夫人所完全认同的“美好世界”,而是她力图要去改变的世界。笔者从以下3个维度去观照作品的模式反讽技巧。
一是在时代情境的描写上,盖斯凯尔夫人经常有意地让乡村小镇克兰福镇与周边的商业重镇德伦布尔、甚至国际大都市伦敦同框出镜,折射出巨大的时代落差。《克兰福镇》的时间跨度大约80年,上可以追溯到詹金斯先生与太太莫丽通信的1774年前后[6]61,下至该书1851年刊载。这期间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发展与完成的历史大时期,是英国城市化势如破竹的大发展时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领域强势主导的时期。这一时期同样意味着农耕时代的落幕,乡村社会的解体,土地贵族与乡绅的没落,乡土伦理的式微;而后者正是克兰福镇不可逆转的历史宿命。
二是在生活情节的叙事上,盖斯凯尔夫人毫不掩饰克兰福镇的封闭、陈腐、守旧、落伍,比如坐马车、抬轿子、撑旧式的红色丝绸伞、给掉毛的奶牛穿法兰绒背心、用报纸挡地毯上的阳光防止褪色、用报纸垫摆成通道为地毯保洁、摸黑织毛衣等等。更不用说作者着力拒斥的门第、等级的观念了,客观地反映了贵族阶级的没落。
三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新”与“旧”反差与对比强烈,如布朗上尉与前教区长詹金斯先生、布朗上尉与狄布拉、格兰玛夫人与玛蒂。布朗上尉与前教区长詹金斯先生代表新旧不同的“绅士”形象。布朗上尉与狄布拉·詹金斯代表着不同的“趣味”,以狄布拉·詹金斯小姐为首的“亚马逊族”女性喜欢的是以约翰逊博士文学作品为代表的古典式哲思和归隐出世的田园生活方式;其文化象征符号是花园和家庭。而布朗上尉喜欢的却是以狄更斯文学作品为代表的工业化和重商入世的城市生活方式;其文化象征符号是铁路和工厂[17]。玛蒂是旧式“门当户对”婚姻的殉葬者,格兰玛夫人是新式的冲破门第藩篱婚姻的受益者。
四、结语
盖斯凯尔夫人与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等人一道被马克思誉为英国19世纪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认为“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8]长期以来,这样的殊荣往往仅仅属于描写劳资矛盾、工人阶级斗争题材的《玛丽·巴顿》与《北方与南方》。作为盖斯凯尔夫人最具影响的一部代表作,《克兰福镇》的反讽性、批判性及其所显露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辩证思考的真理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乃至还常常被解读为讴歌牧歌式田园风光的乌托邦小说。
如果说《玛丽·巴顿》《南方与北方》代表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作品“社会意义”的最高成就,那么《克兰福镇》无疑是其文学造诣的卓越代表。在《克兰福镇》中,我们可以从形式多样的反讽修辞格,尤其是模式反讽中读出盖斯凯尔夫人敏锐的审美感知、深邃的道德关怀,让人在淡淡忧伤中体会温情、在幽默与含蓄中思考世态炎凉、在揶揄和反语中理解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如果说《克兰福镇》的反讽手法还有缺憾的话,那或许就是不够辛辣、尖锐,太过于善良了。正如好友夏洛蒂·勃朗特曾经质疑的:“你可曾情不自禁要把你的人物写得比生活更和蔼可亲,为的是使你的思想迎合那些居心虽善但所见不公的人的思想? ”[19]396盖斯凯尔夫人在《克兰福镇》中所描述的小镇风土人情,大多出于她对于童年生活的回忆,而回忆往往总是美好的,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对乡村田园生活的留恋之情。更重要的是,在创作了《玛丽·巴顿》这样一部揭露残酷现实的作品之后,盖斯凯尔夫人受到很多诟病与指责,在转而描写乡村小说时,她不同程度地用反讽的艺术稀释了现实的矛盾与残酷。瑕不掩瑜,这部《克兰福镇》还是得到了许许多多人的喜爱。夏洛蒂·勃朗特曾在给盖斯凯尔夫人的信中写道:“我读了两遍,一遍读给自己听,一遍读给爸爸听。读起来真叫人愉快——生动、有力、精辟、敏锐,然而和善而宽容。”[19]397这几个形容词是对这部模式反讽的经典之作最为中肯的评价。
[1]周颖.《克兰福镇》的反讽:与米勒先生商榷[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11).
[2]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M].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杨钓.试论小说中反讽的四种类型[J].学术交流,1994(6).
[4]EASSON A.Elizabeth Gaskell:The critical heritage[M].London: Routledge, 1991:198.
[5]刘晓文.建立女性的“神话”: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文学[J].外国文学评论,1989(1).
[6]盖斯凯尔夫人.克兰福镇[M].刘凯芳,吴宣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7]WOOLF A V.Professions for women[M].London:The hogarth press, 1966: 4.
[8]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08.
[9]西蒙娜·德·波夫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书版社,1998:309.
[10]VICINUS M.Independent women: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1850-1920[M]//Mappen E F.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3.
[11]陈礼珍.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
[12]CARIYLE T.Signs of the times[J].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omas cariyle.Chapman and hall, 1858(3).
[13]GREG W R.Why are women redundant[M].London:General books LLC, 1869:12.
[14]邹穗.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福音运动[J].世界历史,1998(3).
[15]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3.
[16]陈礼珍.建构女性乌托邦的困境:《克兰福德镇》故事与话语的断裂[J].叙事丛刊,2012(4).
[17]陈礼珍.出版形式与讲述模式的错位:论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J].江西社会科学,2011(11).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95.
[19]夏洛蒂·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书信[M].上海:三联书店,1984.
(编辑:王苑岭)
I106.4
A
1673-1999(2017)09-0057-04
徐小芳(1980—),女,硕士,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朱熹文旅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翻译与西方文化。
2017-04-15
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教育科研规划课题“地方技能型大学建设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语言技能提升研究”(AZJXH1641);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复数的启蒙’与文明的多样性”(AHSKY2014D143);安徽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夯实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涉外专业群跨境贸易技术技能型人才——以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例”(RW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