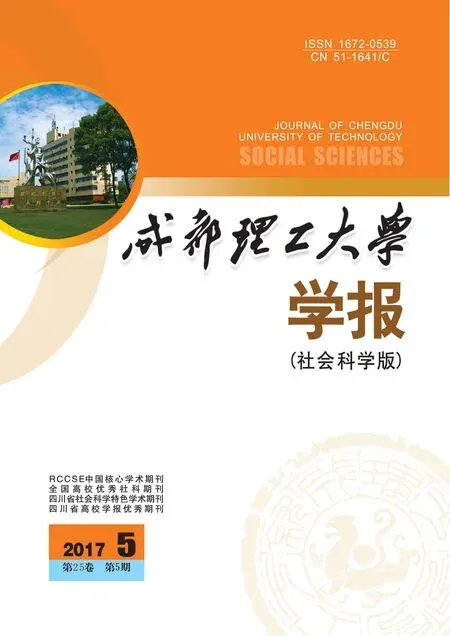论邱华栋小说中的反都市书写
乔 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8)
论邱华栋小说中的反都市书写
乔 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8)
面对日渐复杂的都市社会,当代作家们在想象的世界里开始了对都市发展的反思与救赎,邱华栋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小说中的反都市书写有对物质文明下欲望化生存方式的写照与反思,也有对现代科技的理性批判,还有对经济繁荣下都市文化现状的焦虑以及对人们所处的道德困境的担忧。
邱华栋;小说;反都市书写
在现代社会里,都市仍以极大的物质丰富性和欲望满足性,牵引着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都市情结。然而,都市之美往往与都市之恶并存,现代都市的高速发展并非是没有代价的,它时常以巨大的生命强力、于不知不觉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众多的负面影响。
面对日渐复杂的都市社会,当代作家们在想象的世界里开始了对都市发展的反思与救赎,邱华栋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的文本叙写,常常从都市的病理入手,对都市进行着诊断式的探索与解剖;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符号化、平面化的病态形象;他的叙述声音,常常是都市里失控式、肺腑式的呐喊……这些无不表明了邱华栋强烈的反都市心理。但是,他的反都市书写并非是对都市的绝对否定,从本质上来说,是他站在都市情结的基础上,对都市有了切身体验后,对于现代都市社会的清醒认识与深入反省。
一、物质文明下欲望化生存方式的写照与反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城市快速步入了现代化进程,城市逐渐取代乡村跻身于中国现实社会的中心舞台。都市生活作为一种区别于乡村的新的生活方式,表现在文学上也形成了一套新的审美价值体系。事实上从表层现象看,都市自诞生的那天起便意味着它将拥有迥异于乡村的醒目的物质景观,正如波德里亚所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1]。
邱华栋小说中都市的表象呈现,常常被冠以“景观化”的叙写特点,他是以一种影像式的展现方式,书写都市在发展过程中、物质文明笼罩下的繁荣景象。在他的都市营构中,充满着千篇一律的都市符号: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都市建筑,大饭店、大酒店、购物中心、写字楼、立交桥、公寓、俱乐部、高速公路等;另一方面是快速流动的文明景观,豪华轿车、时装等。这种物态景观的展演,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2]这些繁华的都市景观轰炸着人们的内心,在这样的冲击下,真实的都市往往被湮没在都市的影像里,而都市中的人便于无意识中将这种虚假的都市影像当作都市的美好与本真渴望拥有,并以一种强烈的欲望为支撑竭尽全力去追逐。人们于都市文明笼罩下强烈的物质追求,在邱华栋生长的年代里得以释放;人物欲望化的生存理念,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彰显无疑。
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人的物质欲求在被释放、被满足的循环过程中不断滋长,都市中的人逐渐呈现出一种欲望化的生存状态。事实上,欲望于每个人而言都是存在的,且不仅仅是物欲(包括金钱欲),还有性欲、情欲、名欲等。因此邱华栋的反都市书写并不是对于欲望直接的或全部的否定,而是通过小说中众多人物的那种极具观赏性的欲望化的生存方式来使作品具有批判性意味。本雅明也曾说:“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他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3]邱华栋的小说正是通过写照都市穿行者在都市中的诸多遭遇与选择,描摹与关怀都市人的生存境况,从而进行着物质文明下欲望化生存的反思,呈现出明显的反都市倾向。
邱华栋笔下的都市穿行者包括大学毕业生、小报记者、诗人、流浪艺术家、小商人、打工妹,等等,作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理性的思考,洞察这些穿行者的生存方式并提出质疑。根据邱华栋小说的具体书写,笔者认为将这些都市穿行者分为女性与男性对其进行探讨更为合理有效。在物质文明的渲染下,一方面描摹女性在都市社会里灵魂的堕落,进而沦入代码式的困境;另一方面书写男性在都市社会里理想的缺失,进而成为没有信仰的无根者;而这两者最终都无力逃脱欲望满足后的精神焦灼,时而出现那些生命消亡与无力寻找的悲剧性结局,以此来表明欲望化生存对于人们精神的桎梏。一方面,邱华栋表现女性灵魂的堕落,常常通过女性对于物质、爱情的诸多选择来体现。《生活之恶》中的眉宁以爱为名用初夜获取房子,失去爱情后成为了交际花;《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利用多个男性来提高自身地位,成为了亿万富婆;《环境戏剧人》中的龙天米与六个男人的混乱性欲,荒诞背后竟不知道怀的是谁的孩子;《手上的星光》中的林薇以性为交换、以爱情为牺牲来获取名欲,成了名副其实的“小脏孩”等。在作者反复的书写中,女性的物欲、情欲、性欲、名欲得到了疯狂地释放,她们的生存呈现出一种以欲望为指南针、以利用男性为手段进而满足自我欲望的荒唐状态。各色欲望如泉涌,物欲与情欲相交织,在以身体、情感、心灵为代价的交换中,女性的灵魂已经陷入无法自拔的欲望境地,成为都市的欲望代码。另一方面,男性企图用各类女性来满足性欲,如若没有男性性欲的过度表达又何来女性利用身体获取物质的途径呢?同时作者重在刻画他们思想追求上的欲望化与精神的无所皈依。在这个高度物质化、欲望化的时代,他们的理想不再只是纯粹意义上的精神追求。他们时常将某种欲望满足当作自己的精神理想,以世俗化消解理想,使理想化为精神与物质的混合物,从而支配自己的现实行为,最终沦为没有信仰的无根者。如《手上的星光》中乔可虽追逐着理想,却也为了钱答应了书商增加一万字的性描写的要求,他的理想已然世俗化;《天使的洁白》中的袁劲松以追求富人生活为目标,享受过后却更觉焦躁;《公关人》中W先生的事业成功、家庭圆满后精神的无所依托等。
欲望化的追求成为生活的杠杆,决定着都市男女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作者不加怜惜地让他笔下的人物在欲望的诱惑下踏上了不归路,眉宁们、乔可们都没有逃脱心灵的审判与惨痛的结局。事实上,邱华栋对于都市男女的刻画并不以深入细腻为笔法、以心理挖掘为阵地,他的故事叙写往往是以重复的模式来展现都市女性选择的可悲和男性苦痛的可感。作者写这些人物,并没有对其欲望化的生存状态给出一条明确的出路,但他却极力展现这些人物的悲剧与虚无的结局,在笔者看来,这恰恰表明了他对于这种物质文明下欲望化生存方式的质疑、反思甚至绝望。
二、现代科技发展中的深层隐忧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迅速将人们置入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对人们的社会实践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便捷。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现代科技也不例外。人们在享受发达科技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科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然而,人们对现代科技的盲从、迷信以及膜拜,却使人们陷入一种迷误之中,对于这种负面效应不予及时的反省,以至于这种负面效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而威胁着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命。
与人们“不予及时的反省”的态度相异,作为都市生活的观察者,邱华栋很快洞悉了现代科技的两面性。因此,在他的小说里时常闪现现代科技对人们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具体书写,以此来挖掘现代科技发展中的深层隐忧、彰显他对于现代科技的理性批判。一方面是对于强大威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工具化、信息化繁荣对人的主体性的无情倾轧的挣扎书写,一方面是对于现代科技的潜在风险如环境污染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等的真实写照,邱华栋正是以此来不断叙写在强大威力、潜在风险的现代科学技术影响下人类生活的诸多困境,这不失为反都市书写的又一重要体现。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技的发达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电灯、电视、电话、钟表、微波炉、汽车、飞机等逐渐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现代都市人群的生存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节奏加快,机械化、信息化的生活方式不断加强。在这种变化下,人们一方面追求物质生活的便捷化,另一方面也被这种“巨大变化”抛入一个怪圈:这些都市人群尽管享有了机械化、信息化的便利,但却生活得更加疲惫,精神之累在人们解放双手之后日益加深,甚至沦入科技文明对人的全面围困与束缚之中。邱华栋小说对于这种围困与束缚进行了深入的解读:《钟表人》中的“我”生活在一个被“钟”与“表”覆盖的都市世界,都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不断切割着“我”的生命节奏,最终,“我”也成为了“钟表人”、沦为了钟表的奴隶;《直销人》中的妻子作为物的狂热追求者,将最新的超薄电视、加湿器、红外线取暖器、第X代抽油烟机等强行加入“我”的生活,使得“我”处于一个被物追赶、被物窥视甚至被物代替的荒唐境地,在孤独的反抗下砸碎了所有物品、打碎了婚烟与生活;《电话人》中男女主角的情感交往甚至性爱表达对于电话这一通讯工具的荒诞依赖等。钟表、电视、电话这些人类所创造的科技产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进而替代、支配着人。邱华栋的叙写,使都市人在这种科技产品的极度围困下,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生命表达,在物的无情倾轧下失去了自由意志与主体意识,这无疑是作者对科技产品碾压人的空间的一种反思。
弗洛姆曾说过:“工业社会蔑视自然界和非机器生产的东西以及那些不能生产机器的人们。今天,使人们着迷的是机械性的东西、无生命的东西、巨大的机器,人甚至开始越来越迷恋毁灭力。”[4]在这个迷恋科技的时代,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往往处于被无情忽视的地带,邱华栋对于现代科技的理性批判,还显露于对现代科技的潜在风险如环境污染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等的真实写照中。首先是环境污染的风险。《鼹鼠人》中“鼹鼠人”眼中由人类的排泄物及医院下水道排出的各种废弃器官组成的污水全景图;《后视镜》中的雾霾荼毒;《白昼的躁动》中汽车带动的呛人的灰尘;《天使的洁白》中汽车尾气、粉尘、订书机铁钉以及复印机油墨的残渣余孽;《环境戏剧人》中堆积至“大阪”的易拉罐等。作者通过文本对都市生存环境的恶化现状进行不断地申诉,从这里看出他对于都市生活环境的一种否定和批判。其次是化学产品的风险。《化学人》中的江枫从试吃各种化学工业的新产品如机制的速冻饺子、方便面、火腿肠和色拉油等,沦为直接吃防腐剂、保鲜剂、糖精等化学品,在怀孕后依旧吃着这些产品,最终生出了个不会睁眼、不会发声的化学婴儿;《代孕人》中“我”和妻子,因为疯牛病、禽流感、猪链球菌等食品安全问题一直不敢要孩子,还有铅含量严重超标的地下水、接连出现的癌症村等不断挑战着“我”和妻子的生活;《塑料男》中大量的洗涤剂、人的排泄物和其他化学制剂的催生下的不能食用的“化学鱼”,毒奶粉、毒平鱼、毒蘑菇等食品安全问题,以瘦肉精、洗衣粉为饲料养殖的猪等。作者对于化学产品的风险阐述常常给予超现实的处理,以此来突出这些化学产品对于人们的生活与生命的严重危害。最后是基因工程风险。《克隆人及其他》中的“我”和妻子因为年纪原因换掉了已经衰竭的多个器官,猪、海豚、大猩猩和其他人的器官共同构成了他们的身体,也支配着他们行为和思维方式,最终他们感叹道:“我们已经变成了非我了,但是我们‘健康’了,我们还能够活很多年,但是我们现在该算什么人?”[5]在基因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一旦面临这样的灾害,那将是毁灭性的。
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这些人们曾经唾手可得的东西似乎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中的奢侈品,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已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邱华栋通过他的文本书写,将现代科技发展中的多种隐忧表露无遗,也给现代都市中的人以醒目警示。
三、繁荣经济下的文化焦虑与道德警醒
从整体意识来看,都市好似一个巨大的物质存在,但它绝非只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现象,它还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发酵地、一种都市审美综合体。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进入社会经济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我国都市化进程加快,各色相应的文化在这个发酵地中应运而生,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文化以及媒介文化等构成了繁荣经济下新的都市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在带给人们激情与欲望的同时,逐渐控制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影响着都市的社会道德风尚,并一度使人们的精神处于一种荒原境地。邱华栋小说的反都市书写,还体现在对都市文化现状(如时尚文化、大众俗文化等)的反思、对人的道德困境的警醒上。
现有的都市文化催生了人们得意忘形、欠缺内敛、行为时尚、生活前卫的都市气质,在这种文化“暴力”下人们往往失去了原有的精神特质,异化为符号化的个体,甚至沦入精神的空白地带。邱华栋对于现有都市文化的质疑,首先表现在时尚文化对人的影响甚至异化。《飞越美容院》中上美容院、使用假臀、假乳、假睫毛等,成了都市女人追求流行的标配,都市中虚假的东西正在不断泛滥;《时装人》中的时装是一种时尚文化的象征,但人们对于时装的盲目追求却使得时装吞没了人们的个性、固定了人们的灵魂,使人们化为一种符号化的个体;《平面人》中的“平面人”等都体现了时尚文化对于都市人的身体乃至精神上的异化。其次,邱华栋叙写了大众文化时代下高雅的灵魂艺术被摧残、被替代的现状。《城市战车》中的作家老K玩儿文字卖弄和作品炒作,画家“我”曾为一个画廊作伪画,连音乐这种充满灵性的东西也被音乐工厂通过现代化流程包装制作,机器的刻板瞬间替代了歌手灵动的原唱;《都市航船》中也揭示着大众俗文化现象对于高雅的灵魂艺术的摧残,在这个以包装、趋时、仿制、造假、变化快为文化特色的时代里,艺术成为了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文化商人们为了钱财毫无顾忌地去造假、盗版等,这些都使得艺术处于一种被摧残的状态。摇滚音乐、先锋艺术、午夜狂欢成了人们普遍的精神追求,高雅艺术的被破坏反映出来的是人们在利益熏心的时代对于艺术的不重视以及面对多元文化选择上的一种误区,表达了作者对于都市文化现状的一种焦虑。最终,频频出现的文化符号和商业的潮涌使得人们呈现出一种精神的荒原状态,进而沦为精神荒原者。邱华栋笔下常有这种人物,他们被商业、文化、梦想裹挟着前进,企图进行一场精神与理想的寻找与追逐。《乐队》中盖迪以西藏之旅来冷落都市、填补心灵的空白;《花儿花》中的马达企图用长途漫游来摆脱人与世界的纠葛;《所有的骏马》中乔可两次逃离都市,试图找到一个灵魂的避风港;《环境戏剧人》中胡克、龙天米为了理想排练戏剧《回到爱达荷》所进行的乌托邦追寻等,他们都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锚地,然而,他们的追逐似乎都没有实现,马达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香女”,乔可也在无奈下重回都市,而龙天米最终没有出演戏剧就陷入了死亡的境地。所有的这一切表明,他们的寻找是无效的,在这个文化焦虑的时代,作者只能赋予他们以悲剧性的结局,由此来渲染人在现实中精神的无所皈依感。
邱华栋的小说中还包含关于都市人类道德困境的篇目,这一角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其虽似有与文化同属精神层面的嫌疑,但笔者以为单独突出更为合理。在都市人与人的交往中,人们时常以利为先,传统中国所提倡的“道义”在现代都市里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责任与道义已经不能对人们构成一种自觉、理性的束缚。道德的缺失,让人们开始为利忘友,《飞越美容院》中的“我”作为费力的好友,在费力出走后利用一系列的计划将其公司的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还有现代社会中突出的婚外恋、第三者问题,如《看得见的音乐》中的她和他在历经贫困、物质丰裕后,由于第三者的闯入原本完满的家庭已然破灭;《离同居》以一种看似荒诞的笔法描写了一对幸福和谐的夫妻因矛盾离婚,但离婚不离房,仍旧住在一起,甚至偷情,他们的幸福感因没有了责任和道义的束缚甚至超越了从前。而有关为追逐利益不惜牺牲他人健康甚至生命的人们的刻画,更是彰显出一种无底线的道德沦陷。《塑料男》中所提及的那些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反映了化学产品的风险,而这些风险的背后还有人类的大量参与,是人以主导性的地位去使用某些化学品,从而加剧了这些化学品风险的隐患,等等。在社会生活世俗化的今天,人们很有可能还会一直处于这种道德滑坡、精神萎缩、信仰虚无的状态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邱华栋的这些反都市书写无疑具有深远的现代意义。
四、结语
邱华栋的反都市书写具有强烈的批判意味,他的书写不仅给出了一个评判都市社会诸多现象的参照系数,也给现代都市中精神迷惘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和思考的标尺,试图使人们实现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和拯救,从而得出人类存在价值的正确答案。
[1]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2]邱华栋.城市中的马群[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2.
[3]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6.
[4]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0.
[5]邱华栋.新美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179.
编辑:鲁彦琪
On Anti Urban Writing in Qiu Huadong’s Novels
QIAO 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ly complex urban society, contemporary writers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began to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redemption, Qiu Huadong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In his novel anti urban writing of portrayal and reflection of existence on the materi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desire to have rational criticism o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tatus quo of urban culture under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the anxiety, the moral dilemmas of people’s concerns.
Qiu Huadong; novel; anti urban writing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5.020
2016-10-30
乔芳(1992-),女,湖南张家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
I106.4
A
1672-0539(2017)05-0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