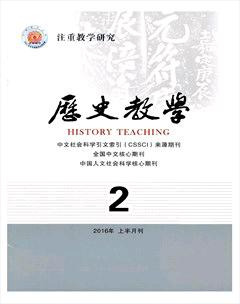“抗战时期的中国与天津"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键词]抗战,中国,天津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67-06
2015年9月17至18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天津市档案局(馆)、天津市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教学》社协办的“抗战时期的中国与天津”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会议从抗战时期的行业状况、全民抗战与社会动员、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态、抗战时期的慈善事业、思想与文化宣传、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抗战胜利后诸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七七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加快制定非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振兴,应对战争状态;日本及其傀儡政权在沦陷区进行经济统制,强化了沦陷区的战争经济。关于抗战时期的行业状况,学者们分别从工商业、农业、金融业、运输业等行业入手,研究这一时期的行业状况。李健英(南开大学经济学防和李娟(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抗战期间政府的合营策略与基础化工产业的发展——国民政府尝试入股永利、天原的考察》一文以永利、天原为个案,探讨了国家资源与民营企业技术优势相结合的问题。抗战期间,天原公司选择与政府合营,依赖政府的财力,酸碱工厂顺利建成投产,但保持民营性质的永利公司仍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四联借款成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作者认为,政府投资及授意下的贷款是促进抗战期间基础化工产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国家与大企业合作,是促进新产业发展的良好途径。熊亚平和万亚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战争冲击下的华北中小城镇商业——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石家庄为例》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石家庄为例,通过考察其货栈业、棉花交易、杂粮贸易的变动,分析石家庄由“自由发展”转变为“统制”状态,由“中转市场变为消费市场”,使山西与河北间交通中断和经济交流受阻,华商迅速减少、日本商人和商社迅速增加、势力日益壮大,京汉线棉花协会和市场公司的成立,正太铁路由窄轨改为宽轨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并指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打断了华北中小城镇原有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使之由“自由发展”转向“统制”状态,或畸形发展态势,这种发展状态对其未来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张博(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日伪时期经济统制与天津工商业的衰落——以天津烧锅业为个案的考察》则以天津烧锅业为个案,从日伪经济统制的苛捐杂税,由于战争而引发的市场萎缩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日伪经济统制对天津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并直接造成了城市工商业的衰落。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认为,天津沦陷之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其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关于农村、农业的研究,则有安宝(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战争与灾难: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北粮荒》,该文探讨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及伪政府对华北沦陷区农村的耕地、劳动力、牲畜、工具等农业生产要素进行的疯狂掠夺和大肆破坏,导致了沦陷区农村的农业生产环境恶化,造成沦陷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以及由此产生的粮荒。关于金融业的研究,龚关(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日本对华北的金融统制与天津金融业变迁》探讨了日本对华北实施的金融统制,如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统制金融机构,实施货币统制,一是推广联银券,排挤、禁止法币流通,二是进行汇兑统制。日本的金融统制政策改变了天津金融业的格局,使天津金融业由银号、华资银行和外商银行构成的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形成了日本的独占局面。同时,也推动了天津金融制度的某些变化,如票据交换所和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冯剑(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的《联合与抗争:日伪时期的天津典质业》探讨了沦陷时期天津的典质业面对日本人的控股和降息的威胁,从原来的竞争走向联合,利用关系、策略使日本人谷内嘉作合股的计划破产,要求当局提高当息并打击小押,这些抗争,虽然使行业利益蒙受了损失,但是却赢得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声誉,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主义精神。关于运输业的研究,有刘凤华(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抗战时期天津地区的航运业》,该文认为,抗战时期日本控制下的天津航运业遭受巨大损失,七七事变后,日本首先接管天津航运业的管理机构,日本华北方面军陆续出台政策,对华北和天津地区的航运业进行政策上的“指导”。1939年4月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成立后,华北交通实现一元化统制,天津航运各业为日本及其所设公司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化了对天津地区航运业的统制,但在美国封锁和游击队的打击下,损失严重。此外,李惠民(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的《沦陷时期石门市竞马大会述论》则独辟蹊径,梳理了1939年至1944年石门沦陷时期举办的12届竞马大会,竞马大会以娱乐活动为形式,强调为“改良马种及增殖马匹而谋产业之开发”服务,竞马大会以满足侵华战争对军马需要为目的,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粪溺业这一既关涉城市又关涉农村的行业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任吉东(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沦陷时期天津社会底层行业变迁——以粪溺业为中心》认为:沦陷之后,一方面受到天灾战乱的影响,另一方面更受到日伪政权的层层盘剥与不良商人的侵占,天津粪溺行业举步维艰,陷入低迷发展时期。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在八年抗战中,国共双方及其领导的人民都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参加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张燕萍(解放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政工系)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人力资源动员研究》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织开展了人力资源动员:首先满足兵员补充的需要,同时招募技术员工到后方从事工矿业生产,对一般人力、技术员工进行管制,对与国防无关系之工商业或奢侈消耗品制造业使用人力进行限制或禁止,以保证战时前方和后方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些举措为赢得战争胜利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但总体而言,国民政府人力动员成效比较差,兵员动员人数多,但质量参差不齐;人力资源清查工作不到位,技术员工严重缺乏;人员损耗严重,造成战时宝贵的人力资源严重浪费。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防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与原因探析——兼论抗日战争爆发对乡建运动的影响》认为,民国乡村建设的动力源于近代社会组织,这既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的基本特性,也规定了社会建设为其重心。由于政府力量的介入和主导,1935年后乡村建设面临歧路之分,并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终被演变为政府主导的农政,其社会建设主旨遂消解于无形。乡村建设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运动,它也确乎构成整个国家建设和社会一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国家以及学术的共同动员和参与,乃至如何在合作互动中适度区分社会与国家的界域,以保持其久远的活力和目标之实现,是一个时代性命题。渠桂萍(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的《乡村游民与抗日战争——一个解读抗战的底层视角》认为,抗战期间,乡村游民大量涌现,在诸多场合崭露头角,他们或为保甲组织公职人员,或为日本人利用,成为下层小汉奸,或成为国民党士兵的来源之一。透过乡村游民的镜相,可以从最深层社会结构中解剖与分析战争发展进程,把握草根社会力量与战争的关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构成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关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也一如既往地受到学者的关注。江沛和王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三寸金莲”之变:战时华北中共区域女性身体与政治》探讨了抗战时期华北中共区域妇女的放足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审美观念及习俗的改变,如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妇救会、青救会的工作,一批女性以“妻休夫”的形式实现了男女婚姻平等,一些女性以嫁军人或干部为荣,不少婚外情影响了抗战后勤工作、乡村社会秩序及伦理状态,甚至有些波及前线军心的稳定,一些女性的身体因政治而变异,审美及心态也因革命及意识形态的输入而产生了重要变化。李军全(淮北师范大学)的《节日与教育抗战时期中共儿童节纪念述论》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共借助儿童节动员儿童,通过阐释纪念话语塑造儿童成人化的社会形象,又利用纪念大会、政治测验和儿童游戏等纪念活动传播政治理念,激发儿童对中共政策的热情和支持,推动了中共在乡村社会中政治工作的发展。李俊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探讨了1939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这两项祭礼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礼,而是被设计成为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对政治进行仪式化运作的机制与效能。另外三篇则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张振勇(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天津人民城市抗日斗争》梳理了天津人民的城市抗日斗争,肯定了这一斗争为华北抗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的重要贡献。张新华(天津市委党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天津的实践》论述了中共天津党组织在天津周围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在市区开展秘密斗争,使二者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李俐(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沦陷时期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工人中开展的政治动员》探讨了天津沦陷后,中共中央、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工人中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认为天津地下党组织在促进工人参加抗日的热情,提高工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广大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动员成效。
全民抗战期间,在中国生活的社会各色人等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其他外侨以及处于优势地位的日侨又有怎样的经历,这些也是与会学者的兴趣所在。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易代同时与遗民拟态——北平沦陷时期知识人的伦理境遇(1937~1945)》分析了七七事变之后,滞留在北平的知识人复杂的遗民姿态、遗民话语和伦理境遇。丁芮(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沦陷区另一种形式的抗争:以1939年董毅日记为中心的分析》以辅仁大学青年学生董毅的1939年的日记为中心,分析了一个青年学子在沦陷区北平的思想彷徨和内心挣扎以及学习和生活状态。王静(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浅析沦陷时期的天津律师执业活动》认为,沦陷后律师执业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总体而言,天津律师群体在业务拓展方式、业务语言上,甚至在公众舆论引导上都处于一种集体沦陷的状态。黑广菊(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防的《抗战时期金城银行职员薪酬调整与生活水平》一文以档案史料为基础,探讨了金城银行不停调整行员薪酬,增加生活津贴,但是工资增幅远远低于物价的通胀,因此行员的生活质量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作为银行家等管理层的薪酬却居高不下,与基层职员的差距越拉越大,严重影响职员的积极性。沈成飞(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的《在因袭与突破之间——抗战前后广州市保甲制度的推进与基层社会控制》一文以广州市为个案,探讨了战前、战时、战后国民党、日伪势力在控制广州基层社会时推行的保甲制度之变迁及其因袭,讨论其因袭的政治传承与突破的现实需求。侯杰和常春波(南开大学历史学防的《南开大学与抗日救亡运动(1919~1949)》认为,近代的南开大学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却在张伯苓校长的引导下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自建校起,无论是在学术研究、学生运动,还是在直接对日作战中,都有南开大学师生的身影。尤其是1937年7月29日的轰炸,不仅没有摧毁南开大学,反而造就了南开大学新的光辉历史。张献忠(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雷鸣远的抗日实践及其救国思想》论述了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在中国的抗日活动,作者认为,具有“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雷鸣远在七七事变之后,积极组织救护队和野战医院,全力救护伤员:成立公教便衣队,对抗日军,开展抗日宣传和舆论动员。雷鸣远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尽管如此,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他对中国抗日事业的贡献。万鲁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沦陷时期的天津日侨》梳理了天津沦陷时期日侨的生存状况以及抗战胜利后日侨的遣返情况,七七事变后日侨人数激增,大多住在日租界,生活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战后日侨遣返,景况凄惨。
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的慈善公益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但大多研究或止于1937年,或不涉及沦陷区,即使涉及沦陷区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沦陷区的日伪政权或民间慈善机构做了什么?如何评价沦陷区日伪政权或民间慈善机构的慈善救济活动,这些问题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探讨。王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的《论日伪统治时期山东的慈善救济活动》梳理了日伪统治时期山东历年的赈灾救荒措施,并分析了慈善机构的设置与活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山东的慈善救济事业遭受重大挫折,陷入低谷;山东各地红十字会成为山东最主要的慈善机构;日伪政权在山东的慈善救济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难民的痛苦,但同日本侵略给山东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不及万分之一。蔡勤禹(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的《青岛沦陷期间慈善事业述论》则将青岛沦陷时期的慈善组织分为三类:一类是原有的名称延续下来但进行了重组和再建,一类是新设立的,一类是第三国的宗教组织,这些慈善组织对沦陷时期的慈善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对沦陷区慈善组织的评价需要从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两个维度来进行,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曾桂林(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的《共赴国难: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地区的慈善救助——世界红十字会的个案研究》则以世界红十字会为个案,梳理了卢沟桥事变后,世界红十字会创设救济组织和筹备善款的经过,并梳理了该组织开展急赈、冬赈、难民妇孺的救护与收容、尸体掩埋和医疗救治的史实,并对其做出评价,认为该组织的战区慈善救助业绩显著,虽是一个秉持救灾恤患宗旨的中立性慈善团体,而在民族危亡之秋,也基于民族主义情怀,共赴国难,为抗战贡献了一份力量。王娟(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民国京津地区慈善事业的互动关系初探——以沦陷时期为中心》认为民元以来尤其是在抗战沦陷时期,京津两地慈善事业的联系比较密切,互动相当频繁,同时也颇有效果。时代最强音民族主义、两地独特的政治环境、相近的慈善传统与文化氛围、便利的地理位置等,均对双方慈善事业互动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王绪杰(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的《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民间慈善组织的困境及应对》则探讨了抗战时期沦陷区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困境如合法性和物资人员匮乏,以及它们在夹缝中施行的慈善救济活动。另外两篇文章则从不同的组织,探讨了这一时期的慈善公益活动。向常水(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抗战中的军人服务事业》认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从1918年开始进行军人服务工作,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日间多次爆发战事,它就更积极地从事军人服务工作,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为军人提供物质和精神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帮助,取得了很大成功。田涛、白玉(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天津地方协会与1933年的国难救济》分析了在1933年日本侵略军进逼关内、威胁华北的形势下,天津地方协会发动大规模募捐活动,积极支援、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并在后方医院服务伤兵,竭力救助流落难民,在国难危机面前,为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彰显出天津民间社会的力量。
思想文化宣传战一直是各方政府机构的关注点之一,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李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骂战”:近代中国对日怒称之一——以(申报)中的“倭寇”为中心》以南方的《申报》为中心,对“倭寇”一词进行检索,认为,“倭寇”是近代中国使用最广的对日怒称之一,其呈现频率与日本侵华历程相对应。尽管国人附着在这一名词之上的情感一直是仇恨与愤怒,但从长时段体察,则不难发现其背后的意象逐渐由甲午战争时期的“忧愤”过渡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激愤”,从而汇入全民对日怒吼大潮之中。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七七事变前后(大公报)的对日观察与对日态度》则以北方的《大公报》为中心,分析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大公报》对日本扩大侵略的野心已有清楚的认识,并已对报社的撤离做了相应的准备。七七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仍然不愿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显示了弱国面对强权的无力与无奈。二文一南一北,互相呼应,可谓相得益彰。阎书钦(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试析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的工业化思潮》认为全面抗战时期是知识界工业化思潮演变的关键时期,国力、现代化、建国、科学等论题构成知识界讨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的重要话语语境。中日之间大规模现代化战争是知识界认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视角。关于工业化问题的讨论,对战后中国尤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经济建设理论有深刻影响。许哲娜(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日本“兴亚”旗号下的反英美运动(1937~1949》则认为,1937年起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在“兴亚”的旗号下,相继在日本、中国等地掀起了数次反英美浪潮。这既是日本贯彻其排挤英美、独霸远东的既定国策的重要步骤,又是日本将侵略战争美化为帮助东亚人民摆脱英美殖民桎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舆论工具。葛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大东放送局与战时日本宣传——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为中心》认为大东放送局的使命,最初主要是向旅居上海的三万余日侨宣传日本当局的政策,迅速传达信息,抗战爆发后,大东放送局使用日、英、俄,以及上海话播送新闻,成为日本在华东地区实施广播宣传的支柱之一。大东放送局与战时日本当局的宣传政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任云兰(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沦陷时期日伪政权对天津的思想文化统制与重构》认为,天津沦陷时期,日伪政权为了配合日本的殖民统治,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制定了亲日媚日政策,通过推崇孔教,强化同文同种的观念,宣传反共灭党,排斥英美影响,宣传“中日提携”。其次,强化中日交流,进行奴化教育,重构殖民教育体系。最后,整合报刊,查禁广播演出,统制新闻,实行传媒与娱乐场所监控,企图在殖民城市天津重构亲日媚日的思想文化体系。成淑君(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电影院与日本在京津的殖民统治》认为,京津沦陷期间,电影院由于其独特的功能和地位,成为侵略者和抗日爱国者共同瞩目的焦点和争相利用及传达声音的舞台,这与它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及其在都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紧密相关。同时,也充分反映出日伪对沦陷区政治宣传和思想控制的重视,以及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政治渗透和控制的强化。
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也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宋芳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东亚省与日本侵华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论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设立的大东亚省的侵华经济政策在“以战养战”和维护占领地秩序之间摇摆不定,并探讨了在小型熔矿炉建设政策的实施上,大东亚省虽煞费苦心,确保了大东亚省的侵华钢铁政策的领导权力,但小型熔矿炉建设最终失败。张利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华北的政治经济入侵》一文首先论述了日本中国驻屯军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扩大,分析了天津作为日本侵华前沿的背景:其次,揭露了七七事变前后驻屯军的军事行动最后,通过驻屯军指挥下的社会经济调查,系统分析了驻屯军在不同时期策划和制定的对华北社会经济掠夺的方针政策和各种计划。作者认为,日本中国驻屯军是日本策划对华北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在华北的大本营和指挥部。
八年抗战结束以后,社会面临新的状况,收复沦陷区,接收旧政权,铲除旧势力,建立新秩序,政治动荡不安,暗流涌动,各方势力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意欲一显身手。因此,对抗战胜利以后各方势力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刘海岩(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受降1945:天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刻》以不同的角度梳理了天津受降一幕和遣返德侨、日侨的大致经过。夏秀丽(天津市档案馏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天津的肃奸工作》梳理了抗战胜利后,在舆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在天津清算汉奸的工作。王勇则(天津市河北区政协文史委)的《天津市忠烈祠入祀资格与尺度把握——以1946年第一次入祠的98位抗日烈士为例》探讨了天津市忠烈祠1946年至1948年入祀标准和尺度把握。另外,杨颖(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近年来天津抗战研究综述》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津抗战的有关研究成果,为抗战时期天津史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线索。
检视这次研讨会,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论题相对集中,关于沦陷时期及战后华北和天津的研究占有较大比例。从提交会议的论文来看,虽然地域涉及国统区、根据地和解放区、沦陷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人物等多方面,但关于沦陷时期的华北和天津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应该说,这些论文均有一定的新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二,在一些相对传统而又与本次会议主题相关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如关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关于乡村建设的研究,关于城市保甲制度的研究,关于战时乡村游民的研究也很有新意。此外,关于抗战前后《大公报》的对日观察与对日态度、近代中国对日怒称、大东放送局与战时日本宣传、雷鸣远的抗日实践、国民政府人力资源动员等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同的进展。
第三,在研究方法、理论和史料运用方面,既有一定的继承性,也有一定的创新性。具体表现在对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多领域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运用、对“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借鉴,对日文资料的发掘、整理与运用等。这些都对沦陷时期和沦陷区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我们看到,关于沦陷时期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还大有可为。以天津史研究为例,以往关于天津史的研究,多以全面抗战前即1937年前为重点。关于抗战和沦陷时期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日本对天津的经济侵略与统制、暴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天津人民的反抗等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而且也不够系统深入,对沦陷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研究不多,对普通民众的内心世界关注不够,今后应汲取新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更多地关注普通人、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世界,以期推动沦陷时期天津史相关研究的深入。就华北区域史的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北京、天津、青岛、石家庄等少数城市,关于其他城镇的研究仍然偏少。就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这一局面仍未改变,仍需要研究者多加关注。
要克服以上不足,将沦陷时期和沦陷区历史的研究推向深入,还应在史料发掘上下大力气。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关于沦陷时期和沦陷区的研究,离不开对日文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虽然有部分论文引用了一些日文资料,但比较而言,仍显不足。另外,对封存的日伪档案也应解放思想,加强开发与整理研究,以期促进这一时期研究的深化。
总之,本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沦陷区研究,尤其是沦陷区城市史的研究,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做强做大关于沦陷区各方面的研究,使之与国统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相匹敌,使抗战时期的研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