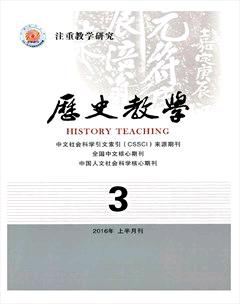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活动初探
付家慧
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最终确定了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以及国王对教会的统治,为了巩固其宗教政策,女王采取了多方面压制天主教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天主教的英格兰教师和学生,在自愿或被迫的情况下流亡欧洲大陆,构成了英格兰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群体。
国内学界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宗教史研究大多集中在国教和清教上,对于当时的天主教状况研究相对较少。但是英国宗教改革并不仅是国教统一,清教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天主教改革和抵抗的历史(Catholic Reform-Catholic Resistance)。因此研究天主教状况,有利于全面了解当时的宗教改革史;探究天主教对于宗教改革的抵抗,有助于解释英国天主教缘何没有绝迹,从而能影响到英国之后的历史发展。
一、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流亡及其原因
1558年天主教的虔诚信徒玛丽女王去世,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她隐藏自己的宗教倾向,制定了较为中庸、最有利于国家稳定的宗教政策,即1559年的“伊丽莎白决定(Elizabeth Settlement)”。其宗教政策在整体上偏向新教,但在教义上保留了浓重的天主教色彩,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英国国教会。政策制定初期,女王推行其宗教改革的手段较为温和,仅要求臣民参加国教会的礼拜活动和宣誓顺从女王的至尊地位,达到外表上的顺从,而不探究其真正信仰。女王不追究灵魂的宗教政策减少了在英国国内外发生宗教冲突的可能性,也获得了大部分英国臣民的忠诚。但是仍有一部分天主教徒不满其新教政策,试图恢复英国的天主教信仰,他们之中最具代表性和威胁性的就是英格兰流亡知识分子这一群体。
在伊丽莎白时期流亡到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徒大约有3000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对于天主教知识分子而言,国家教育政策的新教转向影响到了其切身利益:为了断绝天主教的延续,英国政府从1559年就开始净化校园里的天主教徒,对大学进行阶段性的审查,确保所有教师和学生都宣誓信奉国教和《39条信纲》,这种检查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除此之外,1563年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所有教师,无论是学校教师还是私人家庭教师,都必须获得经过国教会审查发放的执照。同时,所有大学学生想要取得学位,也必须以宣誓为前提条件。这些带有明显宗教目的的教育政策,限制了很多天主教教师的职业发展,也阻断了不愿宣誓的天主教学生深造的道路。因此,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很多英国的天主教教师、学生因对抗宗教政策而流亡海外,另辟职业发展和求学的途径。其中包括后来天主教的精神领袖威廉姆·艾伦,杜埃版圣经的翻译者、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格里高利·马丁(Gregory Martin),其他还有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弗兰西斯·巴宾顿(Francis Babington)、英国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新学院的管理者和教师尼古拉斯·桑德尔(NicholasSander)等等。除了大学的学者,当时还有很多英国的天主教家庭教师或是文法学校的校长主动或被迫加入流亡者中,他们有些加入欧洲大陆国家的教会成为神职人员,并接受指派回国继续传教,并传播天主教书籍。
这些知识分子的流向较为统一,最先离开英国的教师和学生,普遍将低地国家作为其目的地,低地国家的地理优势在于距离英国较近,方便他们回国和了解英国的情况;而且当时低地国家由西班牙所控制,他们因此可以获得天主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庇护。在低地国家,这些知识分子依托于大学,将弗兰德尔的鲁汶大学作为主要的避难所,并在大学里形成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聚集区,鲁汶也因此成为早期英国流亡知识分子的中心。后来随着1568年杜埃英格兰神学院的建立,流亡知识分子的中心又转移到杜埃,杜埃也成为其后的两百年间英国天主教的宗教中心。
二、流亡欧陆的英格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
流亡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在海外安身之后,延续了他们反对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态度,并且在海外的“天主教温床”中产生了对抗英国国教的具体举措。一方面在海外建立英格兰神学院培养传教士,输送其回国传教,与国教争夺信徒。另一方面通过著书立说,与英国国教会争夺宗教话语,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而这些行为构成了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多重面相,形成了新教改革与天主教抵抗的互动局面,反映了宗教改革的复杂性与持续性。
1.建立海外英国神学院
建立英格兰神学院,首先是以威廉姆·艾伦和罗伯特·帕森斯为首的流亡知识分子响应罗马号召的结果。威廉姆·艾伦在1567年来到罗马,表达了其在欧洲大陆创办神学院的意愿,并得到了教皇的首肯。于是1568年9月在教皇的财政支持下,在杜埃当地本尼迪克特修士提供的土地和房屋上建起了海外英格兰的第一所神学院,即杜埃神学院(Douai English Seminary)。杜埃神学院作为英格兰流亡天主教徒的主要据点,提供以宗教内容为主的高等教育,在学院里,学生虽然可以得到学术上和人文主义方面的一定指导,但占据其主要课程版图的当然是宗教方面的知识。杜埃英格兰学院重视对圣经的学习,学生要学习希腊文及希伯来文以加深对原始圣经的了解,并被要求背诵圣经的所有章节;在内容设置上反宗教改革的成分也很突出,学院每天都会开展关于新约的讲座,并在此基础上两天组织一次对新约和旧约的评论,每周举行一次辩论,要求学生对异端,即新教进行攻击。神学院仿照修会的简朴生活,严格控制学生的作息生活,要求学生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八点半祈祷,饮食和娱乐条件也极为简陋。神学院的学制一般设置为七年,前三年或四年主攻逻辑、文法等基本课程,后四年则专门研究神学,相比牛津和剑桥的国教教士的课程更加具有职业导向。
后来,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主要敌人——罗马教皇和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意识到神学院对其宗教与政治利益的价值,因此支持流亡知识分子建立新的神学院。1580年艾伦响应教皇的号召,协助教皇在罗马成立了第二所海外英国神学院,格里高利教皇给予这所神学院可观的财政支持,除经常性的捐款外,还为其扩充学舍以提高办学规模,到1581年罗马的英国神学院已经有70名学生。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是伊丽莎白的最大敌人,英格兰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成为西班牙在1588年英西战争前后借以针对伊丽莎白宗教政策及统治的工具。为此,菲利普二世支持与他联系较为密切的罗伯特·帕森斯在西班牙境内建立了三所英国神学院,即1589年的巴利亚多利德学院,1592年的塞维利亚神学院和1593年的圣奥默学院,通过这些神学院来加强海外英国天主教的力量以威胁伊丽莎白女王。
其二,主导的“人”被禁锢或者被庸俗化。历史教师本该是历史的追问者、教材的开发者、教学的创意者。历史教师要遵循课程标准并依据教材内容,围绕学习目标和核心主旨,进行历史素材的再创作。然而,由于某种既定知识结构的限制,教材静态内容的框定,现实功利要求的禁锢,教师的独立思考和自主意识渐渐消失。周而复始地在“背景目的-进程经过-性质认定-后果影响”的程式中肢解历史;抱殘守缺地在“一分为二-辩证分析-主观客观-必然规律”的圭臬中分解历史;味同嚼蜡地在“纲要信号-概念链接-知识构图-教条语录”的模块中理解历史。教材不仅成了全部的历史,而且成了教师思想的紧箍咒。在课堂上为学生呈现历史,组织学生习得历史的教师,变成了僵化理论的木偶和完成教材的仆人。
其三,主体的“人”被忽视或者被驯服化。由于“师道”的尊严,“书经”的至上和“应试”的魔咒,作为历史课堂主体的学生往往被沦为“师道”的信徒、“书经”的容器和“应试”的机器。我们的教学常常无视主体的独立性,驱赶着他们在思想上轻易地渡越许多原本难以渡越的思维空间。他们的“天真”被历史课上那些冷峻艰涩的所谓“道理”所扑灭;他们的“童趣”被历史课上那些生僻僵硬的所谓“概念”所摧毁。与此同时,他们的“困惑”无法在看似行云流水的课堂上得以显现;他们的“疑问”无法在貌似常识的规律中得以释怀;他们的“见解”无法在仿佛无懈可击的论述中得以表现,甚至他们连暴露错误、流露幼稚的机会都被“教学环节”的完整逻辑和“教学计划”的完成要求所剥夺了。实际上,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的许多知识漏洞、思维缺欠和价值偏差,正是在这种被冷落和被藐视的情况下积少成多并积重难返的。
多年以来,一种看似合理,实则荒唐的现象大行其道——在谈论历史教学“有效性”的时候,人们的话题中心不是围绕目标的达成程度,就是课堂的活络热度,技术的配合力度,问题的驱动密度,等等。而在教学设计、运行、反思、评价等环节中,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特殊性学情和个体化学生。尽管,在我们的教学设计中也有所谓“学情分析”,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关注到学生的兴奋点和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学生“游离”“迷失”“不解”,或者是学生“奇想”“发现”“新意”呢?于是,学情分析沦落为履行书写程式,形同虚设。即或是不同的学情,依然将那些被“经典化”和“套路化”的教参设计方案,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史学即人学”,没有了历史中的人,历史教学就成了“规律”反复运转,“概念”层出不穷,“教条”大行其道的一架可怕的机器。它会窒息历史的活性和思想的灵性。“教学即育人”,没有了课堂中的人,历史教学就成了扼杀人性和泯灭天性的屠宰场,师生关系就会变得冷漠,历史的智慧和思想的力量就会在“无情”中被堵塞、被淹没。
三
课后说课、教学反思、观课交流等教学研究的叙事方式,通过对往昔教学故事的回味与反思,不仅可以及时叙说分享自己设计思想和心路,还可通过所有教学“亲历者”的观感、体会和商榷,丰富教师的教学经验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这也是沟通历史理论、教育理念、教学设计、课堂实践的一种有效教研模式。它以特定的历史课堂教学为视界,促使理论向实践的渗透,又以理论为引领推动历史课堂教学具有理论的跃升。
遗憾的是,叙事方式的优化却没有引出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向的变化。教学的操作者往往关注教师自身的设计、操作和表现的成败得失,而很少注意到学生在课堂上的诸多反应。例如,一位老师在讲到王莽改制关于“王田”“私属”,强调其企图仿行上古井田制,倒行逆施时,要求学生指出其弊端和实质。在经过大家讨论之后,大多数同学按照老师的预期做了看似圆满的回答。但是,其中有一位同学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从汉武帝拒绝接受董仲舒等关于“限田”的历史教训谈起,说到西汉后期土地兼并、豪强猖獗,贫富分化、矛盾尖锐、社会动荡的乱局。王莽恰恰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上述措施,不能简单地看做是倒行逆施。这位同学还认为王莽是一位有胆识和远见的政治改革家,只是因为他的改革失败了,所以历史才给他戴上了反动的帽子……然而,这位老师不仅没有给这位同学任何鼓励,而且要求该同学“看看教材是怎么说的”。课后,我除了与这位老师就王莽改制进行探讨外,特意问道:“你为何会要求学生停止回答,并引导他依附于教材的表述?”他的回答令我无语:“这样下去会影响教学进度,也会影响考试成绩。”
姑且不说老师们在教学创意设计和教学实施操作阶段,无意间忽视了“课堂主体的人”。单就教学反思交流阶段而言,正如前面这个事例所反映出的现象,老师也在习以为常中忽视了作为“目标主体的人”。我们经常看到一节课结束后,在教师说课反思的时候,往往把视点聚焦于设计意图、资源整合、流程安排等方面。而老师们的观课交流的也往往将关注点集中于教师的素质。至于说这节课的目标达成或者学生学习的效度,则任由“旁观者”评说。
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吴江‘问史论坛”让人感觉到了一种新的气息,那就是此次研讨中的学生评课活动。围绕论坛主题,在《中学历史参考》杂志主编任鹏杰的建议下,决定在评课交流环节中,一改以往学生“退场”,由执教者、观课者反思交流和专家点评的“封闭式”研讨模式,而是学生与老师聚集一堂共议教学与学习的体验和收获。
通过学生看似青涩和略显幼稚的发言,让在场的老师顿有所悟!从学生对教师鼓励他们质疑和探索的称赞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追求课堂民主和平等的诉求;从学生对课堂相关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程度中,让我们感受到了教师在设计与实施教学中的缺欠;从学生对老师讲授的一些内容的不同看法中,让我们觉察到了对学生现状认识的偏差。
由此,引起了我的一个新的思考。我们以往的评课、反思和交流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盲区”,那就是对作为课堂主体和目标主体的“人”的感受的无视和剥夺。我们往往乐道于在学生缺席的情况下谈论教学的“有效性”,教学执行者和旁观者的宏论替代了作为目标行为主体的感受,最有发言权的学生却在这种话语霸权体系下,变成了失语者。正因为在寻常的教学时空中目中无人,学生在课堂上“即时性和随机性”的问题质疑、表达迷惑、偶发奇想……的机会被忽视了。因此,那些看似精彩和到位的反思和评价,实则是远离了目标主体的臆想和推论。于是,那种带有“滞后性”的考试应答便成了检验测量学生目标达成和评价学生学业成绩的“单一性”手段。其实,学生的问题和缺失早在常态教学中已经存在,只是由于我们“善意而暴力”地没有给以他们暴露问题和显现缺失的机会而已。
敬佩唐琴老师的心机和智慧。论坛结束后,她整理了学生评课实录,还以“你对‘学生是否有资格评课有何想法?”为题的问卷,让学生表达了他们的心声。(现择录几则)
我认为这是尊重学生的体现,我们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人,只有学生参与评课,老师才能知道我们真实的想法,也有利于老师不断改进,教学更加严谨、完善。
学生当然有权评课,一个老师说好的老师,学生不一定觉得好,学生眼中的老师某种程度与老师眼中的不一样,应该倾听我们的想法。
让我们评课就是给我们民主,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是比较开心的,使上课的老师感到尴尬,才会知道学生也是有想法的,老师也会更加认真地对待课堂。
我们是上课最直观的感受者,感受最深的当属我们,学生对老师讲课优劣的评判最具有说服力,也给学生锻炼的机会。
课堂本就是学生的课堂,我认为学生才是最有权说话的那个,我们不再只是一个听众,我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让学生敢去表达想法。让老师更明白自己的不足。我们并不权威,我们不一定能发现课程中的错误,也可能会对所学内容产生误解。所以我觉得老师的评课也尤其重要。
只有听课的人才知道一节课下来,自己还缺乏什么知识,从而提出建议。我们在探求历史感受是最真切,感触也是最多的。
的确,历史教育所追求的目标,绝不单单是传道、授业、解惑。历史教育的学科价值在于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形成作为合格公民应具备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得到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和个性发展。所以说,历史课应该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而存在。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