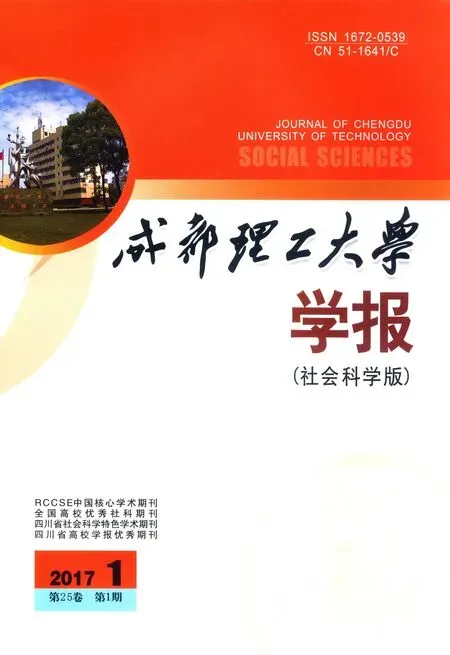理性悖论与语言的“失真”
肖福平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39)
理性悖论与语言的“失真”
肖福平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39)
与其说康德“悖论”的产生源自理性自身纯粹形式的表现困境或有限理性存在者在认知过程里的超验企及,不如说源自纯粹的先验语言形式在自然语言中的不可言说或自然语言对于超验对象的经验呈现,其结果自然地带来语言命题及其语言存在问题在先验性与经验性方面的混同;理性“悖论”既是理性存在的必然发生,又是语言经验过程的“失真”表现,自然语言的“尺度”不在自然的进程,而在理性存在的先验语言形式之内;辨明“悖论”的原因和形成就是辨明理性与知性、自然语言与先验语言形式的分野,确立清晰的具备不同特征的语言存在的统一。
悖论;语言;失真;理性
从句法意义来看,作为悖论的语言判定双方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更没有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优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语言“悖论”是同康德的理性思辨中的悖论联系起来的,而非语言学单方面意义上的分析,因为理性的悖论不仅涉及人类认知的困境,而且也涉及人类存在的语言困境,为此,康德从其先验哲学的视角提出了著名的“二律背反”,在经验的语言表述里体现为既是又不是的命题,而这样的命题除了作为理性思辨的结果以外,并不能为双方带来“真”的确定,也正是这种“真”的缺失使得人类的语言迷失于自然的过程而与理性的先验形式相脱离,如何寻回语言存在之“真”,以及如何摆脱语言经验应用在悖论上的困境,分析康德关于理性悖论及其语言表现的对立命题成因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因为康德的理性悖论及其语言命题不仅涉及说明理性困惑的需要,而且也涉及说明人类语言应用困境的需要。
一、理性“悖论”中的语言“失真”与作为理念语言存在的地位
倘若理性存在者的一切语言应用所涉及的概念和命题都具有意义(就康德的“知识论”而言),那一切语言应用的结果都没有缺少经验直观的对象,所有表示概念或思想的语言单位都将是可以经验印证的,语言应用的“既是又不是”命题就不会出现。因此,在我们面对理性悖论的语言“失真”时,我们所遭遇的应该是自然语言的无“意义”应用,或者说,在自然语言的进程中,我们将理性存在的先验语言形式及其作用范围进行了经验化的判定,其结果必然带来语言应用的困惑;作为“消极”的先验形式存在,纯粹语言形式的 “积极用处”如同柏拉图、康德的理念一般,不可在知识的意义上来加以确定,更不可确立为自然语言的意义内容;如果我们将先验语言形式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逻辑形式,那所有自然语言的语句便成为这种逻辑形式下的经验内容,并且体现为自然语言的各种语言规律。所以,先验语言形式一方面可以引导一切语言的经验趋向最大统一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通过理性批判,将自然语言的应用限制在经验的认知范围之内,这样就为理性存在保留了一片圣洁的语言之地,从而为语言实践确定了一种“真实”的标准;尽管我们难以判定这样的标准是什么,但它一定会是理性存在的必然,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理性存在者的语言首先是被自然世界所注入的。实际上,从先验语言形式的“消极”到其“积极作用”的过程必然体现着理性存在的真实,而且,总要在语言的先验形式存在和语言的实践两个方面被体现;总之,理性“悖论”的语言“失真”问题既不可能立于完全的经验,也不可能完全立于纯粹的先验形式。
人类认知过程的语言命题为何会出现“失真”的情形呢?其原因就 “仅仅在概念之间来回探索”[1]51,即我们所言只有纯粹概念的综合而无经验对象的验证,作为这种探索或综合之结果的语言命题就不可能完全是关于自然经验的命题,自然语言的有效应用范围也就没有了保证,而自然语言的无效应用总是同知性概念的超验应用伴随而生;“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理性仅仅为了知性原理的运用而用在经验的对象上,而是冒险把它扩展到超出经验对象的边界之外,那么就产生出一些玄想的定理……”[2]358这里的“玄想的定理”就是没有经验直观的语言命题,它就是因为自然语言的“无能”而“玄”。面对这种超验的世界,语言应用的过程在理性的引导下就不会是那样的安分守己而要进入先验形式的领域中去试图表现纯粹的先验语言形式。在如此情形里,康德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家们全然不知自己所在,仍然将自然语言的概念与经验对象同在的方式加以应用,似乎认为超验的世界同自然的世界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认为在关于语言的命题中断定超验的世界比经验的现实存在更完满、更真实。但他们却未注意到,他们所获得的这种更“真实”的语言命题完全属于先验的“综合统一”,属于“消极”的纯粹形式存在,因为它没有了判别自身真假的任何经验直观之物,任何对这种“真实”的肯定判定都会造成关于其否定判定的“真实”,并同等地获得各自存在的理由。既然理性悖论下的语言表现困境被归因于“仅仅在概念之间来回探索”,而不顾自己是否具备可直观的经验对象,那么,对其克服的方法就是要从语言所指的经验对象入手,将作为知识产生的语言命题与作为理念产生的先验语言形式命题进行区别,将自然语言的表达对象确定为时空中的存在物,一种在具体语言、语型和语法框架下的现象存在,并将存在物的如此“事实”同主体性存在所使用的自然语言的架构联系起来。那么,语言应用的有效性问题成为我们分析语言“失真”及其原因的关键所在,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将所有的语言概念词与经验事实相结合,我们就会避免语言命题在关于同一“指称”或“意谓”上的对立,当然,这一过程的实现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确实有点远不可及。
由此看来,解决语言命题中的“失真”,拯救语言“失真”之困境应该可以具备正确的方向,因为语言的“失真”并非自然语言的句法错误或功能缺失,而是它跨越自身有效应用范围的结果。在语言的存在问题上,它不仅仅是自然的,它更是理性的,或者说,语言在作为自然层面的知识对象时,它应该基于了理性存在的前提条件,于是,语言存在的自然与理性两个层面也正好符合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对象存在形式的二分;当然,康德也继承了这样的观点,提出了现象世界与其理性原因世界的区分。在这里,现象世界对应于自然语言的表现部分,而理性原因的世界则应该对应于先验语言形式的所指领域。根据康德关于纯粹理性原因世界无法被认知的观点,我们在认知“先验语言形式”方面同样是没有结果的。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先验语言形式存在的本体世界为纯粹理性思辩的领域,其内容是没有任何经验对象印证的纯粹语言或“理念对象”,这样的对象在康德看来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知识的对象。就语言而论,它永远区别于自然语言的存在,区别于我们经验的语言系统;无疑,这是对语言表达困境产生原因的最好诊断,但诊断并不能消除理性存在下的语言困惑;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语言存在的形上世界,也不管它是多么地远离我们的经验语言,它总是要一往情深地眷恋着它那种非时空条件的自由之在;如果对于理性存在下的理念语言只进行否定性判断,或者以先验幻想之类的谓语来界定,那探索先验语言学之路还会有意义吗?如果将康德的先验哲学观放置于语言存在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语言一旦作为理念的存在,它便成为了一种非认知对象,一种关于语言的“永恒之在”,它是拷问语言现象的所有“存在物为何如此”的最后依据所在,“在任何时代,不仅是哲学家,就是在普通的理性那里也承认了这样的‘永恒之在’,而且是作为了所有现象变化的基底。”[3]214在这里,不论是世界的永恒,还是语言的永恒,只要理性的存在不可否认,“永恒之在”就应该是自明的,它应该属于康德哲学里自明真理的范畴;所以,作为理念形式的先验语言世界永远是一个在理性引领下的语言本质的居所,我们因为拥有这样的居所而拥有世界的如此语言呈现和我们的“此在”过程的语言经验。显然,我们无法将作为“基底”的先验语言形式置于经验的过程,一旦我们使用自然语言对其加以判断,我们就无法避免语言“失真”的出现。对于这样的先验语言的存在,我们无法消除它,也无法肯定它;前辈的人已经言说了它,现代的人和将来的人也同样会言说它;不论言说的结论是否具有意义,我们或许相信:这样的“言说”就在形而上学的思辨中揭示了语言存在的自由状态,只要我们不企图将它带到自然语言中来。
二、基于理性前提的语言表现困境的“辨明”
从先验哲学的视角来看,语言“失真”的实质就是理性的背反论,是理性背反论的语言存在表现。只要我们人类没有背弃语言的存在之路,理性存在的世界显现就仍然会保持着当下的状态与趋势,即我们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总是要在使用自然语言描述经验世界的同时不满足于语言及其世界的现象,从而导致关于如此“语言现象”的本体性探寻,并习惯性地视之为经验语言的现实,造成纯粹语言形式与语言现实的混同,结果,自然的语言层面在无限与绝对的意义上展开,形成关于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的判断,如此而言,自然语言也就等同于了先验语言形式的存在,那么,自然语言就一定会将有限理性的人类提升到一个神性的地位,这样的情形显然只能是人类的一种奢望。在这里,只要我们涉及理性条件下语言存在所追求的“世界”、“灵魂”和“自由”等概念时,我们将会发现,语言在经验意义上的应用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矛盾的处境,因为对这些概念的描述已经超越自然语言的有效应用范围,这样的描述除了作为一种类比性的经验描述外并未对这类概念说明什么,也更不可能体现为一种知识的获取过程,或者说,人们在面对当下的语言现象(自然语言)时顺从了理性的要求而对非经验性的“语言恒在”(permanence)进行了认知或判定;当然,理性条件下的纯粹语言形式存在有别于人们因个体爱好兴趣而产生的主观随意性的心理语言现象,它是理性的标示,是语言现象及其知识体系的原初根据;对于语言现象而言,先验语言形式就好比一个万能的涵项,它包容所有语言现象中的语句表达而又不等同于它们。一旦我们将先验语言形式区别于语言的心理或自然现象,先验语言形式本身就会合乎康德的先验哲学思想而具备普遍性特征的存在地位,从而保证了语言形式的纯粹性,而不至于成为经验的对象或跑到变幻不定的主观幻想上去,即使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在这种幻想里同样能体现出某种一般性或统一性,那也只能是语言经验过程的语法规律而已。在语言经验的纯粹原因寻觅上,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正是基于语言现象的规律思考来完成了对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现象的超越,将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建立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语言形式之上。显然,语言哲学家所看到的语言世界同一位劳作的人在休息之余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前者所凝视的是关于语言世界作为绝对整体性的存在,是关于行为人“存在家园”的语言“恒在”,而后者只能是关于“此在”的暂时性语言状态,即经验的语言现实,是在言说中发音、表意、理解等的经验语言对象的过程。经验的语言对象除了表现为自然语言的内容外,它不可能成为其先验形式的内容。于是,通过区分语言存在的先验性地位和经验性地位,我们便将语言“失真”的产生原因归于了自然语言的超验性应用,或者说,我们使用了自然语言来述说理念的存在,对于理性存在的语言而言,语言存在的绝对原因正是这样的理念所在。那么,我们对于原因的辨明是否就能消除经验语言过程的“误判”并使语言的应用从此变得明晰呢?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肯定都只能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奢望,一种超越我们自身有限性的奢望;不论是柏拉图的关于“是”与“真”的探讨,还是现代弗雷格、罗素等人关于语言涵义与指称的探讨,语言的现实还是一如既往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这样的“辨明”只有相对的意义,它只是在我们对语言表现悖论的命题判断缺乏足够感性经验时的“辨明”,只是在我们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权利去判断先验语言形式的世界是什么时的“辨明”。同时,关于“辩明”的语言对象,它不仅是作为自然语言的对象,更是作为理性存在的先验对象,它既可以是关于具体内容的,又可以是关于纯粹先验概念的;要使先验概念的辩明成为知识的辩明,先验概念的辩明必须具有可经验性的特征,即具有可以感知的音、形、意等特征。因此,理解语言“失真”产生过程的“辨明”在确定的意义上只能是关于有限与无限的澄清,以及语言“失真”必然地作为了源于理性存在的结果。
语言表现困境的出现不可缺少理性主体的存在,否则,连同语言困境在内的一切语言现象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语言存在的本身就是理性的存在过程,它包括了体现理性本质的先验语言形式和作为描述世界的自然语言呈现,并且,后者总是作为前者的结果而存在,尽管两者的联系超越了我们人类的认知范围。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我们人类在面对自己的语言存在问题时常常将语言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外在的自然对象,或者说,它就是一种异己的交流工具,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势必要面对理解的困惑:外在世界必然地遵循自然律而表现为一个完美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里,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都具有因果的,当然,作为自然对象的语言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不可能想象这样的语言会存在表现困境,或作为“既是又不是”的存在,同时,不论是完美的自然过程,还是完美的自然语言,它们的完美意义对于自身而言将会变得什么也不是。因此,作为自然律的发现和语言“失真”的存在无一不是源于理性存在自身,无一不是理性存在的表象与生成。自然过程的语言“失真”一定是理性存在所带来的、超越感性范围的自然语言命题,并试图通过这样的命题将先验语言世界的存在赋予可经验的对象地位,或将先验语言形式的理念地位看成是具有经验可能性的概念,这事实上就是造成语言应用过程之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显然,语言应用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在“经验”的尺度之上,而这样的尺度对于理性思辨和先验语言形式就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了。语言表现的困境或“失真”所体现的就是纯粹理性背反论在语言问题上的表现。从语言作为先验形式的存在来说,它所关注和应用的对象及其范围完全有别于可经验的自然语言的应用世界,它的世界应该是一个纯粹理性思辨的世界,表现为理性条件下的语言存在的绝对统一,但是,一旦我们使用作为知识的语言系统(自然语言)对纯粹领域的存在做出语言判断,那语言“失真”问题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因为这样的语言判断超出了合乎自然语言的句法规则之外,我们不能为它带来任何“真”与“意义”的判定。通过对理性思辨过程所涉及的语言先验形式和语言的经验应用的综合分析,作为经验的自然语言存在必然地涉及如此存在的起源、必然涉及语言经验对象的因果关系的无穷延伸、必然涉及自然语言体系的绝对理由,同时,这些“必然”的指向又远非自然的对象世界或自然语言可以认知的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经验的自然语言是有限的,倘若忽视这种有限地位,自然语言的应用过程便会越过有效的界限而将自身等同于先验形式的存在,这样的结果对于理性而言只能是一种难以克服的假象,因此,理性存在的语言在人的“此在”过程里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表达的困境,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在于逃离当下的语言现象,回归到语言的本质所在,并获得无限意义的语言形式。然而,人的如此“回归”遥遥无期。因此,对理性存在的语言“失真”只可加以“辨明”,而非消除,这样的事实就是康德所说的“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存在事实。
由于语言存在所要求的绝对统一离开了经验的自然语言的帮助便不可言说,因此,我们在使用自然语言来判别先验形式领域(包括语言自身的先验形式)的存在时,我们所遵循的规则与经验认知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都是立足于语言的现象世界来判别一个未知的存在,或者说,它就是一种经验的类比,只不过经验对象的自然语言的综合统一同理性要求所要达到的关于语言的绝对统一来说,其范围和彻底性是不能相比的,至于说经验的自然语言的规则体系是否有效于先验语言形式的领域,我们对此是无法回答的,否则,理性悖论和语言“失真”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作为知识的语言体系要求下的统一只能是一种相对性的统一,它是就某个语言概念词或语言意义单位而言在可能经验领域所能达到的统一,它所表现的部分在纷繁的语言现象系列上来看只是一个发生在经验认知方面的语言片段,或当下的一个“语言对象”。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将语言存在的“真实”不仅仅作为了知识的存在,更作为了理性本身的先验形式存在,因此,在我们使用自然语言体系并对此进行认知时,我们往往不会满足于这样的知识对象而要去询问如此语言现象的原因、结果,理性存在的过程在语言的问题上就表现为一种朝向先验语言“目标”、向往绝对的语言统一性的过程。由于这种绝对的统一性对于相对的自然语言体系来说“太大”,而自然语言体系的相对统一性对理性目标来说又“太小”,一旦使用有限的自然语言体系来同时对付表象的世界和智性的世界,那经验语言过程的命题就会发生不能解决的冲突,产生关于同一概念或对象判断的“既是又不是”结果,其根源就在于自然语言的相对统一应该反映表象的自然世界的统一,而非纯粹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的统一。因此,不同的出发点便出现不同的语言视野与洞见,造成命题的绝对相异。长期以来,语言“失真”表现的命题在语义的基础上被划分为了正论与反论的区分,并试图通过实质分析的过程来忽视语言的存在问题,殊不知,所有思辨和认知的过程都不曾离开语言的存在,都不曾避开“是”与“非”的语言表现。当然,语言经验过程的“既是又不是”源于理性存在的悖论、源于语言的理性本质的遮蔽,或者说,归结于自然语言的有限性和经验性。因此,语言命题中的“S是P”和“S不是P”在我们人类这里都拥有自身成立的理由和原因。在康德的先验哲学里,这样对立的语言命题被视为了理性二律背反的语言表现形式,其目的不是赞成一种形式而排斥另一种形式,它就是要使语言表达的对立双方都能依据各自的主张获得尽可能的展现,以便为理性在困境中找到一条通达语言确定性的道路。
三、先验哲学视野下的语言表现“失真”
在论及语言“失真”的表现形式时,我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康德关于理性“悖论”的语言表述,其双方各自的命题结构都可归属于传统的逻辑形式:S是P,S不是P,或者说,所有的S是P,所有的S不是P。如果我们将这里的语句名称S转换成表示概念的语词,如世界、宇宙、时空等,我们就可以取得了康德关于理性悖论的四个语言命题,并将主词的涵义展现为相互对立的部分,即P与-P,前者为正论形式,后者为反论形式;就康德先验哲学来看,悖论双方的出现无不表现为理性存在过程的必然发生,或者说,悖论是理性存在过程的悖论,是理性自身目标在有限世界的矛盾展现,它所明示的就好像一种本体存在的现实展现。当然,这样的展现可以为我们指示某种先验对象的“是”或“存在”,正是在这种明白无误的指示里,我们才会将“是”与“悖论”表现的语言问题抛在了一边,这种情况一直到了现代哲学或逻辑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时才得以重新审视。我们或许要问这样的问题:理性悖论的展现是否属于理性本身的特征?理性悖论本身的结构是否等同于语言的结构?等等,倘如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上采取肯定的回答,那我们的结论就是:理性存在本身就体现为“是”与“非”的对立,所有后天经验的限制、认识的局限、自然的杂乱等都应该源于理性本身,于是,我们会缺失自然的有条不紊与自身知识概念的系统统一性(即使是相对意义上的),同时,我们也会有理由说:理性存在本身在先验意义上就不具备综合统一性,而这样的结论无疑有悖于先验哲学基础,即理性存在具备先天形式的综合统一,因此,理性本身的特征与理性的现实表现特征应该分属不同问题,可以说理性悖论是理性存在条件下的现实经验过程的必然发生。
倘如理性悖论具有自身的结构,那它就一定可以展现为在正论与反论两个方向的构成,也可在对象存在的意义上展现为世界的有限与无限状态。在这里,我们对这种结构或状态赋予了“是”或“存在”的意义,但这样的赋予却必须建立在语言的表述上,或者说,我们所面对的理性悖论的结构或呈现的状态首先应该是语言的层面,即自然语言的表现结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一方面,只要我们还不是先知先觉,任何缺失语言层面的“是”或“存在”都是无法讨论的,更不用说理性悖论的直接呈现;另一方面,没有了自然语言的表现现实,语言本身结构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次,语言的层面只有局限于自然语言的范围以内才能带来悖论的表现形式,否则,不同形式的对象存在便会在各自适合的语言形式引领下达到清楚明白的表现。可以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一旦超越了自然语言的范围,我们就要面对语言的全部存在,将作为理念形式的语言存在用于描述先验形式的内容。尽管我们不清楚这样的内容及其描述过程,而将作为经验对象的自然语言用于描述现象的世界,结果,作为绝对统一的理性存在之先验语言形式总是要完美地适合于作为理念世界的存在,同时,先验语言形式下的经验现实,即自然语言的现实,也会对应于自然表象的世界,从而使所有经验的对象都会获得自然语言的标记,使得自然语言描述也会摆脱歧义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科学。显然,这仅仅是一种理想,一种将我们自身神性化的遥远的希冀;正是基于理性的攀升,自然语言的现实就失去了经验直观的有效性保证,所以,它因脱离自己的经验之“真”而“失真”,因应用于先验的领域而“失真”,这就是语言的现实困境。此外,在考虑理性悖论结构与语言结构的问题时,我们是在面对有限存在与无限存在的结构,假设可以认知这样的结构,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这样的世界结构应该为语言存在的结构,这一观点在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思想里已有相当明确的阐述[4]130。当然,这里的语言存在远非我们经验的语言对象;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里获得启发,那就是:“世界——事实——思想——句子”,如果这里的句子仅仅指示自然语言的部分,那它对应的世界就应该是可以言说的;如果这里的句子暗示一般的语言表现模式或作用过程,那世界就涵盖了不可言说的领域。由此看来,言说与不可言说的范围划分也不失为一条通向语言意义的明晰之路。
理性悖论无疑是哲学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又必然表现为正题与反题的语言描述,因此,它也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一旦关于世界的语言命题出现对立或悖论,那关于其原因的探究会使我们去思考、去质疑“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当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决非易事,同时也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此只能搁置不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发现:同其他认识论问题一样,语言的“失真”或语言表达的悖论问题也遭遇了“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独断论揭示,因为在语言命题的正题和反题里,我们所获得的内容表明,“正题代表了传统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主流,反题代表的是非主流的看法”[5]276。如果我们将正题的视角从先验哲学转移到语言的认识上来,语言的存在就应该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即从语言现象开始的过程一定会有一个先验的语言之源。如果语言的先验之源可以体现为某个单一概念,则它的谓词F或谓语部分就会超越自然语言的特征描述而成为“元谓词”存在的先验模式,这样的模式在康德看来只能作为理性存在下的自然语言的调节原理,而非自然语言的构成原理,或者说,作为先验语言模式的存在不能成为语言知识的对象,不能在自然语言的要素中称为感知的对象;对于这样的“元谓词”模式,它所要求的“单一概念”在任何经验意义上的确定都是不可能的,否则,它就是关于自然的语言的概念,它就是关于自然语言的描述,即语言的涵项模式(x)Fx,就完全属于自然语言的领域,当然,限制在自然语言中的模式不能代表作为正题的先验语言观。为了区别于一般语言逻辑形式的表达,我们暂且用(x’)F’x’来表示正题的模式,当然,在蒯因的客观性翻译里,它是无意义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先验哲学的体系确定其地位,同时,由于无法经验化这样的模式,我们也不得不采用一种类似自然语言的形式来表达和处理,即作为先验语言存在形式的(限制性变元)x’总是在语言的先天统一中表现为语言的先验特征F’,其存在意义就是作为语言现象的调节性原理。可语言存在问题上的“唯理论”对此总会有自己的独断论,或者说,同世界、灵魂、上帝等概念一样,理性存在的语言本体地位在他们那里只能被视为肯定的事实判断,并以此抗衡语言问题上的哲学“经验论”,而这里的“经验论”则体现为反题的语言命题或表达形式,即语言变元x由于体现自然律的作用而表现为无穷意义的语言概念的延伸。在这样的经验论中,(x)Fx不仅作为自然语言的涵项模式,更是作为了语言存在在自然因果联系上的无限模式,所以,语言变元x永远指向一个相对的语言个体(包括经验的或超验的)而非某个终极语言因。同样,F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总之,在先验哲学的悖反论上,语言命题的意义悖论区分为“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下的不同世界的图景同时也是语言存在的不同形式的图景,只要理性存在的前提不容置疑,如此世界与如此语言的图景存在就具有自身的必然性,正反双方的语言命题除了表现为P与-P形式之外,任何语义上的“真”或“意义”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不会取得的,所以,任何一方的“被肯定”或“被否定”都会导致独断论的结果,并直接导致双方逞能的“战场”,在交战的任何一方都认为自己必定赢得胜利时,它不仅坚信了自己命题意义的正确性,而且要将对立命题进行彻底的摧毁来证明自身;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有一个假设的前提:被摧毁的一方永远不要具备攻击方的优势,“只要它们(胜利者)留心保有采取最后进攻的特权而没有经受敌方新的袭击的义务,他们也保准能戴上胜利的桂冠。”[2]359
康德认为:“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6]257那么,作为理性悖论下的语言“失真”命题是否拥有成为真正知识的可能呢?如果它不能在知识的意义上建构什么,那它所依据的哲学对象或原理又该如何看待?通过上文的分析,在世界、灵魂、上帝等概念的命题里,语言命题表现的对立双方由于各自立足于自然语言的要素和经验的现实来描述或指向非对象性的超验目标,这样的语言命题或语言行为在知识的构建和增加方面没有任何意义,尽管它也反映了理性存在对于绝对性、完美性和统一性要求的必然趋势。在弗雷格的语言观中,上述关于理性悖论的语言命题当然是假的,因为作为主词的专名无对象指称。罗素则通过自己的摹状词理论来消解自然语言中的专名,并取得消解传统语法的主谓结构以及专名对应对象的必然联系,从而搁置专名对于目标的指称。因此,在我们必然地面对这样的语言“失真”时,我们并没有权力取得知识的宣称。就康德的知识论而言,不论是关于语言描述的表象世界的知识,还是关于语言自身作为现象知识,经验直观无疑成为了判别的标准。由此观之,关于语言命题的意义或知识构成要么与概念的对象、要么与概念的经验直观是否具备联系起来;当然,在如此突出语言知识的经验地位之时,我们必须清楚,语言的经验与知识在整体性存在的意义上都仅仅是作为了某种原因的结果,即某种理性所具有的先验形式的结果,所以,语言现象(自然语言)与语言知识体系作为结果的理性绝对前提首先不在作为经验过程的语言现象,而在理性的主体性存在自身,即语言知识的形成源于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的先天语言条件,或用乔姆斯基的话说,人类具有关于语言的先天能力。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借助康德的“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部分来加以分析,理性存在的纯粹先验形式(也必然包括先验语言形式)应该成为一切人类知识获取的绝对条件,因此,语言的知识总是要作为其先验形式决定的经验结果而存在,尽管这样的结果常常使得我们暂时忘却语言的先验形式。只有在先验语言形式存在的条件下,我们才能遭遇关于语言现象的经验过程,才能取得关于语言对象的知识和拥有所有关于语言认知过程的发生。根据康德的先验认识论,人类对于语言问题的认知也表现为一个由感性进到知性,再由知性进到理性的过程,而感性和知性的应用只能发生在语言现象的世界(自然语言的世界),或者说,语言现象统摄于感性和知性的形式之下。相对于感性和知性而言,理性思辨的对象则是作为绝对统一的先验语言形式,因为理性的本性就是要把握语言现象存在的绝对总体性,并获得一个绝对的语言之源。然而,(人类)理性自身是否具有这种认知语言之源的能力呢?在语言之源的纯粹形式世界的存在里,我们没有知性概念和概念的自然语言呈现,一切关于它的存在都只不过是借助自然语言所进行的经验类比描述,至于这种类比描述的先验语言形式究竟是什么,我们是无法认知的;然而,“无法认知”并未阻止这种认知行为在理性存在者那里发生,即人们在认知语言现象存在(自然语言对象)时,也在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式和规则认识先验的语言形式或绝对原因,从而导致语言现象中的句子、陈述、命题等的无意义或意义悖论的出现,并带来关于先验语言形式存在的无穷幻想。
于是,康德认为:“理性在我们的求知欲最严重的一件事上不仅遗弃了我们,而且以假象迷惑了我们,终于欺骗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信任它!”[7](P242)不论我们是否信任它,理性引领下的先验语言形式认知总要发生,语言存在问题的困境总要出现,其结果总要动摇人类理性在认知语言上的至上性和绝对性。因此,不管是理性悖论问题,还是语言悖论问题(这里的语言悖论就是理性悖论的语言表达形式),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语言存在问题上寻求一个认知的范围或有效性界限,将语言的意义表达和有效性应用建立在对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认知的批判中。
综上所述,理性悖论下的语言“失真”或表现悖论的产生源于语言存在自身纯粹形式的表现困境,源于有限理性存在者在语言应用过程中的超验应用,其结果自然带来语言存在的先验性与经验性的混同;理性“悖论”的语言“失真”在先验哲学中典型地表现为正题与反题的命题,并在哲学的意义上体现为“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辨明理性悖论下的语言“失真”的原因和形成就是辨明理性存在与语言存在、先验语言形式与经验语言现象的分野,从而在理性存在的前提下确立语言之先验性与经验性的统一。
[1]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杜,2001.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 1929.
[4]王路.逻辑与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特生(John Watson).康德哲学原著选读[M].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编辑:黄航
Kantian Paradox of Reason and Its Significance
XIAO F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9,China)
It is more evident to say that Kantian paradoxes originate from the unspeakable transcendental form of natural language than from the representation of pure form of Reason itself, and by applying natural language to its transcendental form, it necessarily brings the result of identifying natural language with its transcendental form; Reason’s paradoxes necessarily happen because of Reason itself, and they are also represented by the falsehood of using natural language, which is valid only in experience and gets the standard of being true only from its transcendental form; to be clear about the reason of producing paradoxes is to be clear ab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s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ural language and its transcendental form, and at last to be clear about the united existence of language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paradox;language;falsehood;reason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1.006
2016-04-30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1LZUJBWZY005)
肖福平(1962-),男,重庆璧山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语言哲学研究。
H0-0
A
1672-0539(2017)01-002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