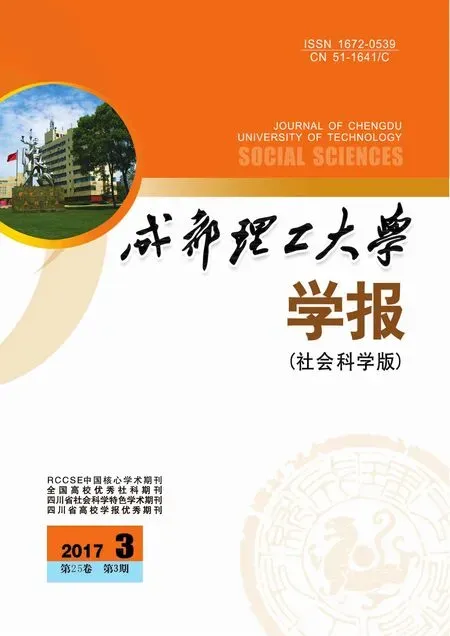陈寅恪“史学救国”思想渊源研究
——从任蔡锷秘书谈起
王 跃,郭士礼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59)
陈寅恪“史学救国”思想渊源研究
——从任蔡锷秘书谈起
王 跃,郭士礼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59)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虽然自少年时期起便留学日本、欧洲,学习经世之学,但由于其家学渊源深厚,深受晚清乾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留洋期间又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洋与东洋的“中国学”的刺激,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1915年春他曾到北京,任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的秘书,经界局的“分译东西图集,详溯中国经界源流”工作更促使其坚定了“史学救国”的志向。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提及,但这段经历随后又促使他继续留洋欧美,研究梵文、巴利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对其毕生的学术道路影响至深。
陈寅恪;蔡锷;史学救国;经界局;秘书
陈寅恪先生是民国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学贯中西,其做学问的态度和做学问的追求是学人们之楷模。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三十年来的陈寅恪研究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即起步期、繁荣期和深化期。研究人员可分为四个群体, 即陈氏门人、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以及港台及海外学者。研究重点相对集中在八个方面:史学、语言文学、晚年著作、文化观及知识分子观、家族史、与同时代人比较研究、治学研究以及诗歌笺注等”[1]。其中,学术界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他1925年留学回国后任清华学校国学门导师之后的研究,学术界对其回国前的经历并未进行深入挖掘,尤其是陈寅恪1915年曾任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秘书的经历,对其最终确立“史学救国”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然学术界对此一问题的认知尚有未发之覆,而理清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了解陈寅恪的“史学救国”思想渊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研究近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也会有很大的启发。
一、家学与早年留学生涯奠定的史学素养
陈寅恪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客家人。五、六岁时已入家塾,其祖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期间,他和五兄陈隆恪等延师在巡抚署中读书。1900年,其父陈三立寓居金陵(南京),在家里兴办思益小学。陈寅恪在较为宽松的气氛中学习经学、历史、舆地、算学、格至、体操、音乐、图画等,陶冶性情,接受新知识,并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为后来的脱颖而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2]。除了置办新学外,陈三立还兴办实业,从后来相继派送子女出国留学可以看出其开阔的视野。
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进行了现代化,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在日本得到了很大发展。因此,甲午战败后,中国派出了许多官派留学生到日本求学,寻找救国救亡之道。当时出国留学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陈三立先生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虽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但视野开阔,又很有风险意识,加上经济实力允许,于是积极派送自己子女出国留学。最终,留洋求学成为这个家族命运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更证明了陈三立的高远眼光。
陈寅恪先生有过六次(长达约二十年)留学经历。他13岁(1902年)便与长兄陈衡恪先生(字师曾,民国时期著名画家,曾与鲁迅共同就读于南京路矿学堂)东渡扶桑,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与其同年入学的留学生中有鲁迅,二人同室而居,关系甚密。15岁(1904年)冬初,又与其五兄陈隆恪先生一道考取官费留日。初入庆应大学,后转东京帝大财商系[3]22。1905年陈寅恪因脚气病回国,归国后1907年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为插班生,系高中程度。同窗者有竺可桢、徐子明等。陈寅恪先生留学日本期间,曾学习经世之学,这可能与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经世致用和实业救国思想盛行有关。这一留日背景与下文提到的蔡锷的早年留日经历相似,拉近了陈寅恪和蔡锷之间的距离,为其后来担任蔡锷北洋经界局督办秘书一职埋下了伏笔。
1909年,从复旦公学毕业后,陈寅恪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开启了旅欧求学历程。陈寅恪先生22岁(1911年)就读于瑞士苏黎世大学,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便从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原版阅读,欲了解马克思和共产主义。陈寅恪阅读《资本论》与其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经世之学的专业基础也密不可分。1912年春天,陈寅恪自瑞士抵达上海,回国探亲。1913年春,他再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中无法读书,是年秋,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回国阅留德学生考卷,并允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3]35。陈寅恪因此二事而回国。这次回国,1915年春,陈寅恪到过北京,他曾回忆说:“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公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4]可见,在时间上,他确实具有任蔡锷秘书的必要条件。
1915年8月,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在思想上与梁启超较为接近。11月 ,蔡锷以治病为名,脱离袁世凯的监视,离开北京,经海外绕道南下护国[5]。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以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与陈寅恪先父陈三立有旧,乃聘寅恪至湘,掌湖南交涉使署事[6]26。蔡锷离开北京,陈寅恪入湖南任职自在情理之中。据清华大学部第三级同学卞僧慧在其《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文中说:“先生曾言:昔年在长沙,初任职交涉使署,终日翻阅档案,看交涉案例。涉外交涉,不仅须熟悉条约,且须知过去交涉案例,临事不至仓促应付,贻误事机。”[7]由此可见,当时的陈寅恪先生已经基本显现其在史料应用上的功底,而且这段工作经历对其后来从事史学研究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之后,陈寅恪又到南昌江西省教育司阅卷,直至1918年冬赴美留学。关于这几年的事,他曾回忆道:“连阅考卷三年,其间曾病痢疾甚重,因当时缺乏医药几死。更因看卷时间久,又患神经衰弱失眠,并肠胃不消化等病。因家修养,同时自修。”[3]37至于陈寅恪的回忆里未述及其曾任蔡锷秘书一事,这可能与其为人性格有关,就像其从未在回忆里提及留日友人鲁迅一般,他说:“鲁迅名气大,谈这些事会有攀附名人之嫌”[8]。自在情理之中,可见陈寅恪的谦虚品格。
二、任蔡锷秘书渊源略论
蔡锷在其《〈中国历代经界纪要〉绪言》(1)(1915年7月)的“编辑起源”中指出:谨按:1914年12月11日,奉大总统申令:“经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于中央设立全国经界局,呈奉大总统策令,特任督办,主持局务。以四年一月成立筹备处,编制草创,经纬万端。因念考镜所资,必求贯澈中外古今之故,乃能确定方针。节经遴派专员,设所编辑,分译东西图集,详溯中国经界源流。盖攻错必咏他山,而数典不可忘祖。凡以考异同之迹,综得失之林,大輅椎轮,胚胎创造,亦万不容缓之要图也”[9]351-352。通过这个绪言,蔡锷详细叙述了当年任北洋经界局的原委和背景。邓江祁在《蔡锷年谱简编》一文中也提到:1915年1月22日, (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10]11。蔡锷任经界局督办后,开始着手经界局工作,是时早年湖南的故人陈三立之子陈寅恪求学回国,特聘陈寅恪为其秘书。
关于陈寅恪任蔡锷秘书一事,陈寅恪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先生在其《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说:按《蔡松坡先生集》所载蔡《年谱》:“1915年,三十四岁。正月成立全国经界局筹备处。遴选专员,设所编辑,分译东西图籍,详溯中国经界源流。”本年十一月蔡锷即逃离京。先生如有任“蔡锷秘书”事,当在本年春以后。为时当甚短[3]36。同样,据陈寅恪先生长女陈流求抄录的《吴宓自编年谱》(未刊)载,在吴宓(1894-1978,字雨僧)与陈寅恪未认识之前,俞大维向吴宓介绍陈的经历时,有“1915年,在北京为经界局局长蔡锷秘书”一语。而汪荣祖先生认为“寅恪当过蔡锷的秘书,自有可能,但难以证实”[6]26。从以上文献记载来看,学术界许多学者在其著作中都提及了此事,但对此有不同的声音,且没有比较系统的论述。
其实,陈寅恪任蔡锷秘书一事,与蔡锷早年在陈之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求学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据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记载:“(先祖)年过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11]188陈寅恪先生先父陈三立的《巡抚先府君行状》中亦云:“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诏陈宝箴授湖南巡抚。”[11]197陈宝箴(1831-1900)早年跟随曾国藩(1811-1872)故官湖南已久,对湖南民情了解至深,深得当地士民信爱,时任湖南巡抚一事,自不必说。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1853-1937)是清末著名诗人,与沈增植(1850-1922)等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是“清末四公子”之一。1886他参加丙戌会试,蒙当时主考官陈宝琛(2)(1848-1935)慧眼识人才,陈三立中式,成进士,授吏部主事职。然三立虽有经世大志,却难以施展。文廷式曾说:“陈伯严吏部曰:举五千年之帝统,三百年之本朝,四万万人之性命,而送于三数昏妄大臣之手。”[6]13可见陈三立当时的不满之情。于是,三立在吏部任职未久即辞归侍父。甲午战后,三立与其父宝箴合作湘中改革。
1897年至1898年,陈寅恪先生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人都热心维新,他们邀请在湖北的谭嗣同和在上海的梁启超到长沙来兴办新政。1897年10月,陈宝箴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特邀梁启超和李维格分任中、西总教习,唐才常、韩文举等为教习。陈三立对陈宝箴帮助极大。时务学堂开学时,陈宝箴原打算聘用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陈三立却向父亲推荐了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他认为梁启超已经超过其老师。在邀梁启超入长沙一事上,陈宝箴也听取了儿子三立的建议。至此,“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社,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11]198湖南长沙的维新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882年12月,蔡锷出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市),字松坡,15岁(1898年)9月底, 参加湖南时务学堂第一期招生考试, 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入选中文内课生(后又补入第一期西文留课生), 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研习《公羊春秋》、《孟子》及西学[10]6。维新运动期间,蔡锷就读于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学习新学,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深受陈宝箴父子维新思想的影响。据蔡锷当时的同学石陶钧记载,在时务学堂学习期间,江标勉励他和同时入学的石陶钧,说:“邵阳先辈魏源你们得知吗?读过他的书吗?你们要学魏先生讲求经世之学。中国前途极危,不可埋头八股试帖,功名不必在科举。”[9]1在时务学堂学习期间,蔡锷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发奋读书,与梁启超等论学。蔡锷在头班年龄最小,“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9]2另外他还积极参加南学会的活动,并在《湘报》上发表文章,锋芒初露。从此,蔡锷便与陈宝箴父子湖南新政产生了历史渊源,与义宁陈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8年8月,湖南地方选拔学生到日本留学,蔡锷成绩名列前茅。然而,恰同学少年的美好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一场政变让眼前的所有都化为泡影,让人难以预料。是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中文总教习梁启超逃亡海外,时务学堂解散,赴日留学成为了泡影。1899年蔡锷考入南洋公学,是年夏天接到梁启超的来信相招,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东亚商业学校,学习经世之学,初步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此时的蔡锷依然受到湖南时务学堂新学的影响。1900年应时务学堂教习唐才常之邀曾短暂回国,参加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重返日本东亚商业学校,看到祖国风雨飘摇,他决心学习军事。1901年蔡锷考入陆军成城学校,继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毕业回国。在日本期间,他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之道。所以,陈寅恪担任蔡锷秘书一职,可能也与他和蔡锷的留日经历和所学专业类似有关。
综上,可以断定陈寅恪先生任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秘书一事实为事实。其一,陈寅恪先生的家学渊源和多年海外留学经历与经界局的工作性质相契合。陈寅恪早年留学日本,留洋期间受到当时盛行西洋与东洋的“中国学”的刺激,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后又留欧多年,语言知识广博,与经界局工作要求高度契合,为其任秘书职埋下伏笔。此外,蔡锷早年留学日本也学习经世之学,二人之间留日所学专业类似,更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增加了二人合作的可能性。其二,蔡锷早年求学湖南时务学堂,深受陈氏父子维新思想影响,与陈氏三代之间历史渊源深厚,且当时世家之间关系交往频繁,陈寅恪任职蔡锷秘书自在情理之中。其三,陈寅恪先生旅欧归国后曾至京,且至京世间与蔡锷任职经界局督办时间上吻合,自不必说。这一系列的巧合,使偶然发展成必然,共同构成了陈寅恪曾任职蔡锷秘书一职的内在逻辑与间接证据,毋庸置疑。而且这段经历对其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陈寅恪“史学救国”思想的确立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工业革命和市场化,纷纷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并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把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时代,以天朝自居,加上清朝的闭关锁国,始终未能转型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疆界观念。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没有维护疆界主权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华民族屡次遭受列强侵略,数次割地赔款令人悲愤不已。无数仁人志士围绕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苦苦追寻,不断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各行各业的人士都做出了自己的一定程度的贡献。其中,就有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通过编撰地理图册,来抵抗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林则徐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41年,他因禁烟运动被革职。魏源受林则徐的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3)。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中,对其编撰此书的原因作了说明,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后来,左宗棠以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复新疆伊犁、中俄以签订《尼布楚条约》来划定中俄疆界的思想应该也是受到了林则徐、魏源思想的启发。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从上文中湖南时务学堂时期学政江标勉励蔡锷等学生的话语,即可反映出,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海国图志》也有自己的缺陷,它依然没有摆脱古代以来的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到了北洋政府时期,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海国图志》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一个更具时代性的地理图志被时代呼唤着。
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日本、沙俄、英国等列强环伺中国,企图把满、蒙、回藏、鲜分离出中国。面对这样的形势和压力,北洋政府成立了经界局。据蔡锷《〈中国历代经界纪要〉绪言》(1915年7月)的“搜讨资料”中载:“查东西各国调查土地,制备清册,复有登记法制,无非使国家周知其方舆,人民确定其权利。意良法美,前事可师”,“编辑起源”中载:(北洋经界局的任务是)“分译东西图集,详溯中国经界源流”。[9]352-353即翻译东西方地图,为申明权属、划定国家疆界,研究提供历史和法理依据。经界局的工作思路也是延续了近代以来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此时的蔡锷将军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且由于多年留日历练和军事实践,对国家了解至深,早在湖南时务学堂时就听学政江标说过自己邵阳同乡魏源的事迹,更深知经界局工作的重要意义,于是接下经界局工作,并聘用故人陈三立之子,家学与留洋经历丰富的陈寅恪担任其秘书一职。虽说陈家自陈宝箴后就有“不从政,不置产”的祖训,但史学素养深厚的陈寅恪也深知经界局工作的重要性,1915年春,陈寅恪还是决定来到北京,任职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的秘书。
虽然陈寅恪早年留学学习经世之学,但据陈寅恪先生的表弟俞大维回忆: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归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说文解字》,东汉许慎编著)与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3]48联系到下文中提及的陈封怀的回忆,可以断定陈寅恪有扎实的史学功底。而且后来陈寅恪回忆,因为家世因缘,当年他曾经听到过“京师胜流”中议论,如1942年在其《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一文中说:“曩以家世因缘,犹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12],可见其家学渊源深厚,而且深受晚清乾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加之他在外留学多年,拥有一定的外语基础,所以能够胜任经界局的工作。陈寅恪早年留学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而以现代方法研究中国的学问主要还在外国,留洋期间又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洋与东洋的“中国学”的刺激。陈寅恪先生的侄子陈封怀(陈衡恪次子,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在其回忆录里曾说:“第二次和六叔(陈寅恪在家族中排行第六)在一起是在南京。他刚从湖南长沙回来。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及文学等。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3]39他知道国际学术界的动态,一定要让中国的史学研究“预流”(4)。[13]1929年陈寅恪给北京大学毕业班学生提了两首诗。第一首诗的前两句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14]可见,陈寅恪先生对当时到国外研究中国史的趋势感触至深。
陈寅恪早年旅欧的时代,当时欧洲的一些东方学家因为探险、殖民等活动,对中国的边疆、印度、中亚以及东南亚等地都有研究。且这些区域语言复杂、宗教复杂。晚清以来就有人说过,很多人视西方人为帝天,西方人讲的都对。像当时的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以及瑞典学者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等欧洲汉学家的名字,已经被很多人都知道了。而且很多西洋人的研究兴趣,往往成了中国人的模版[15]16。然而,从事经界局的工作,涉及的中国古代以及外国文献太多,就必须学习另外一些语言文字。因此,在从事经界局工作期间,陈寅恪深受语言文字与宗教的影响,遇到了自己的短板,感觉到当时的语言文字水平离自己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陈寅恪也深受蔡锷爱国精神和救国思想的影响。遂1918年,陈寅恪踏上了长达八年的欧美留学历程,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分别跟随C.兰曼(5)( Charles Rockwell Lanman,1850-1941)和路得施(Lueders)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以及其他东方古文字。通过学习这些语言文字,陈寅恪1925年回国后在前人西北史地之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在佛经与边疆民族史等方面研究出大量成果,在学术界至今影响深远。虽然五十岁前后研究重点转到中古史领域,但都与前期语言文字的积累分不开。可以说,在经界局工作这段时间更促使陈寅恪坚定了“史学救国”的志向,以至影响了其一生。
陈寅恪先生任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秘书职虽仅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可是这段短暂的工作经历对其确立“史学救国”思想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其背后的故事更是一个近代历史的缩影。通过厘清这段历史,可以对近代学术史和思想史有一个大致的观照,丰富中国近代史(包括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内容。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与学术上,也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对于民族独立的渴求。通过研究陈寅恪先生,我们会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会对陈老的学术思想和学人精神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为当下中国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精神养料,从而促进中国未来学术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也会对陈寅恪先生和蔡锷二人崇高的爱国精神有更加深刻的感受,他们的家国情怀会为我们当代民族精神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养料。
注释:
(1)《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全书七万余字;《各国经界纪要》,全书九万余字;《经界纪要法规草案》,全书十一万字。三书均为1915年蔡锷在全国经界局督办任内主持编撰。“纪要”于同年七月先后成书,“法规草案”于1916年印行,后来都收入《蔡松坡先生遗集》。
(2) 陈宝琛(1848-1935),福建闽侯人,同治七年(1868)成进士,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内阁学士,与张之洞、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号为“清流”,名倾朝野。
(3) 此后,魏源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847年刻本达到60卷,1852年全书达到100卷。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流传到日本后,一度成为日本天皇和大臣的比读书籍,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但在此书中,魏源没有摆脱中国中心论观念的影响,依然需要改进。
(4)陈寅恪在当年给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中开篇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世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5)有关C. 兰曼的生平,参看“Charles Rockwell Lanman”,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Gale Biography in Context,Web.25 Oct.2010.
[1]刘克敌.20年来之陈寅恪研究述评[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60.
[2]叶绍荣.陈寅恪家世[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228.
[3]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2,35,37,36,48,39.
[4]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G]//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66.
[5]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304.
[6]汪荣祖.陈寅恪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26,13.
[7]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上海:中华书局,2010:64.
[8]王子舟.陈寅恪的治学方法[M].郑州:新视野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50.
[9]毛注青,李鳌,陈新宪.蔡锷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3:351-352;1;2;352-353.
[10]邓江祁.蔡锷年谱简编[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6-11.
[11]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G]//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88,197,198.
[12]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G]//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62.
[13]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G]//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66.
[14]陈寅恪.北大学院已巳级史学毕业生赠言[G]//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9.
[15]葛兆光.预流的学问:重返学术史看陈寅恪的意义[J].文史哲,2015,(5):16.
编辑:鲁彦琪
The Origin of Chen Yinke's Thought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Studying History”: Begin with the Secretary of the Supervision of Cai E
WANG Yue ,GUO Shili
(College of Marxism,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China)
Chen Yinke is a famous historian of our country,enjoying a great prestige in the academic world. Although he had studied in Japan and Europe in his early age, learn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with his deep origin of family education, his study was influenced by the school of Qianjia textual research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During studying abroad, he developed a good value of historiography, affected by the contemporary prevailing “Sinology” both by the west and east academic fields. In the spring of 1915, he went to Beijing, and served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Border Bureau of Beiyang governmen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Cai E, charging the Border Bureau’s work of the “pictures’ translation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specific analysis the origin”, which also prompted him to set up a firm ambition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studying history”. This period of history was seldom mentioned, and after that, he continued to study abroad in Europe and America to study the languages, such as Sanskrit, Pali and other oriental ancient words, which threw a deep effect to his later academic research.
Chen Yinke;Cai E;saving the nation by studying history;Border Bureau;secretary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3.016
2016-09-15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现代史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研究”(13XZS017);2015年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陈寅恪‘史学救国’思想渊源研究”(MYLX1626)
王跃(1990-),男,安徽寿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郭士礼(1982-),男,山东鄄城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与学术。
K82
A
1672-0539(2017)03-00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