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寅恪的讽谕诗读他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上)
子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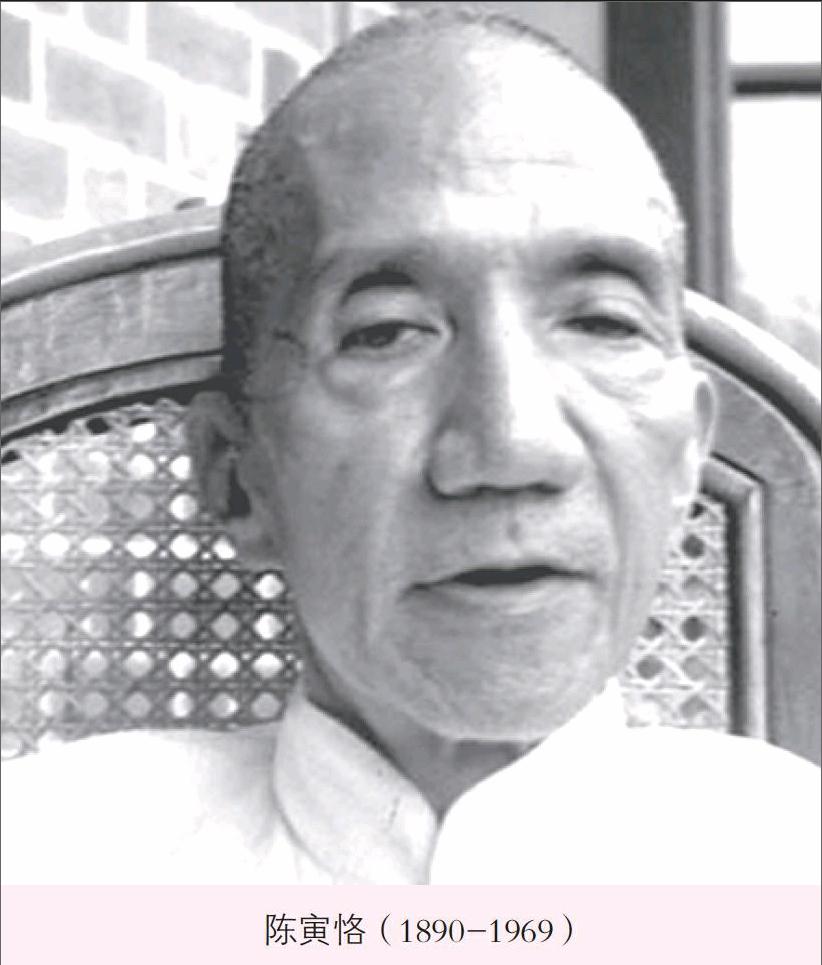
陈寅恪现存诗歌三百余首,以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收罗最夥。陈寅恪在文化上尊宋,因为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集大成者:最完备、最丰富、最具美感、最富人格精神与自由价值;但其在诗歌创作中,却并不以宋诗、宋词为宗,亦学唐诗、崇唐诗。就这点而言,他与父亲“同光体”诗派领袖陈三立大有不同。
唐诗中,陈寅恪最服膺白居易与元稹,特别是白居易。赵翼《瓯北诗话》说:“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这是讲,元、白能够用平易近人的语言表达大众想要表达(却未必能表达出来)的声音。陈寅恪的诗,已达到“言人所共欲言”的境界。这里赵翼所讲“坦易”并非文字粗糙,内容平淡;至于陈诗,则是劲爽而苍朴,格调高,意境深,每每蕴含丰赡,耐人寻味。罗韬先生甚至认为,在这方面,陈诗已然超越了元白。罗韬在为《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所写序言中说:“义宁(指陈寅恪)之压倒元白者,以其诗关乎天意,所寄宏深,伤国伤时,最堪论世。义宁常自比元祐党家子,而胸罗中古兴亡之迹,撑持天坼地解之际,独立于礼崩乐坏之时;责己以文化托命之大,讽世在士节出处之微。故其诗秉国身通一之义,造今古交融之境,望之气沈郁,扪之骨嶙峋,史识诗情,盘屈楮墨。每读之,未尝不掩卷低回,愀然而叹:此变风变雅之音也。”此言甚确!
陈寅恪同历代优秀知识分子一样,关注民生、更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忧国愤时,疾恶如仇;又以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自励,立足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试图以一肩之力,力扛近世颓落的中国文化大闸,并将其赋予新的生命与活力。他的诗歌,便传递出这样的思考,反映出这样的心声。我们看他于1916年所写《寄王郎》,1929年所写《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1930年所写《阅报戏作二绝》,1938年所写《蓝霞一首》诸诗,均反映出他在民族危急、国家危急之时的焦虑不安和奋拔之状。他的《蓝霞一首》系七律,全文如下:
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
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
甘卖卢龙无善价,警传戏马有新愁。
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
按“蓝”指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以代指国民党;“霞”(红色)则指红军,以代指共产党。卢龙,在今河北喜峰口附近,典出《三国志·魏书·田畴传》。据胡文辉的解释,旧时用“卢龙”指割地,出卖国家利益,但此处指共产党向国民党委屈求全,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戏马,即戏马台,在江苏铜山县南,原属徐州府,此代指徐州。陈寅恪写此诗时,正值日军发动徐州会战之际(1938年5月)。其时国民党四十万军队在徐州陷入日寇南北夹击的合围中,形势岌岌可危。陈寅恪获此消息,心急如焚,祈愿我军能全身而退;更祈愿国共两党能捐弃前嫌,共同对敌,否则,必将造成亡国之祸,遗恨千古。陈寅恪此诗,既反映出当时国人、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又有高出他们的更深刻认识——这从其以“蓝霞”冠题可见隐秘。尽管陈寅恪同国统区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不甚了解,以为其对国民党“委屈求全”不过是实用主义而已,但他对国民党的态度则嗤之以法西斯主义,忧虑共产党不是其对手。所以他的“此恨绵绵”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侧重于对国民党的警惕与责难。《吴宓日记》在1938年5月有段记述,很能说明问题:“因忧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不能圆满合作,故宓诗中有‘异志同仇之语,而寅恪又有《蓝霞》一诗。”之所以对国民党多有责难,是因为对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了解颇深,对刚艰难辗转、万里长征才至延安,却又风尘仆仆、立马走上抗日前线的共产党殊为惜怜。陈寅恪在1936年7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写有《吴氏园海棠二首》呈吴宓,后者即在其手迹后加附注云:“寅恪此二诗,用海棠典故(如苏东坡诗)而实感伤国事世局(其一即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书之内容——‘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本描写红军长征的书,就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6月—10月访问陕甘宁边区后的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陈寅恪《海棠》诗之一有“蜀道移根销绛颊,吴妆流眄伴黄昏”句。胡文辉笺释说,其时“红军处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剿下,显得前途黯淡。故陈诗当是以海棠移植后红色转淡比喻共产主义赤潮的低落”。陈寅恪于此诗流露的“亲共”情绪是很明晰的。再回过头来看《蓝霞》一诗,自会对陈氏同情看似弱者的红军、责难处于强势的国民党而心有戚戚焉。
《蓝 霞》中的“楼高”犹言“高楼”,谓最高当局。《杜甫》《登楼》云:“花近高楼伤客心”即此。1940年3月22日,陈寅恪作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之一,与竺可桢等在重庆应蒋介石之邀赴蒋官邸晚宴,“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覺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1]。陈寅恪返回在渝所寄住的妹夫俞大维宅后,遂有《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抒怀,中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句,显示出对身居最高位的蒋介石的不屑与忧惧。
无须讳言的是,陈寅恪同国统区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抗战的前途比较悲观——这也大量地表现在其于这一时期的诗作中。不过,这丝毫无损陈寅恪的爱国立场。他1940年在写给傅斯年的信函中说:“弟素忧国亡”。他当时对抗战前途之所以感到悲观,一是缺乏对国际大势的通盘把握;二是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入认识;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对蒋介石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彻底失望。陈寅恪于1932年所作《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诗中写道:“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就是对蒋介石政权无力阻止日本并呑东三省,更无力掌控全国大局的批评。在先,1929年5月,陈寅恪有《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诗,其“读书不肯为人忙”句,则是对国民党欲在包括大中学生在内的全国人民中推行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以实行思想统一政策的不满与嘲讽。
注释:
[1]吴学昭整理《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0页。 (下期续完)

